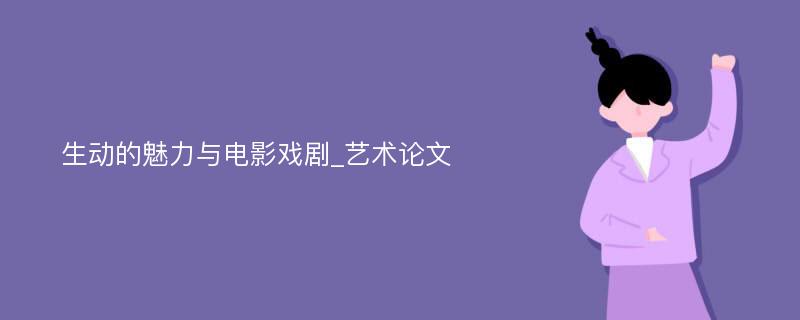
“气韵生动”与电影剧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气韵论文,剧作论文,生动论文,电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些年里,西方电影和西方电影理论大量涌入中国,它在促进我国电影面貌的改变,拓新我国电影工作者的电影观念,使我国电影走向世界等方面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电影如同音乐一样,有着很强的国际性,是各国和各族人民相互了解和交流的重要手段,这也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改变过去闭关锁国状态带来的一股新气象。
与此同时,一些理论工作者运用西方的理论如结构主义,符号学、弗洛依德学说等来研究中国电影的热潮也随之兴起,其中包括我们通常说的如何读解电影。这一切都表现出我们的虚心好学与“拿来主义”的精神。但是这几年,电影界实在“拿来”太多,俨然变成一种时尚,几乎言必称巴赞、麦茨。我从来不反对借鉴西方,但我不赞成在借鉴西方的时候,忽略了或忘记了我们中华民族自己优秀的哲学和美学传统。难道我们没有自己独特的有别于西方的美学,没有自己独到的艺术理论吗?难道我们的美学、艺术理论都是落后的,过时的,无法解释作为现代艺术的电影了吗?我想不是的,只是一旦打开国门,我们被五光十色的外部世界所吸引,所迷惑,还没有将目光从大洋彼岸收回来,认真关注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自己的文化和文学传统。根基是至关重要的。例如我们观看苏联1989年摄制的影片《国际女郎》所引起的良久的激动和思考,不仅感到作家、艺术家对自己祖国那份深情,那份热望,那份炙人的苦恋,那份赤子之爱,而且,我们还强烈感受到深厚凝重的俄罗斯文学传统,不自主地想到普希金、列夫·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归根结底,电影艺术作品的丰富内涵和思想深度,决定于作家、艺术家生长的那块热土上的文化和文学根基。其次,如果我们仅仅知道一点符号学或者生吞活剥地了解一点结构主义的皮毛,当我们与西方学者交流或探讨符号学和结构主义时,很可能像俗话说的:“圣人门前卖《三字经》”,连和人家对话的资格都失掉了。
本文就试着探讨一下我们的传统美学的“气韵生动”与电影剧作(我曾说过,电影剧作是包括从电影文学剧本到影片完成的全部创作,即包括导演的主要创作在内),目的是抛砖引玉。由于自己在这方面的知识的欠缺,谈这样的题目颇有捉襟见肘之感,可是犹豫再三,还是大胆写了出来,以就教于大家。
“气韵生动”与电影剧作,这确实是有相当难度的课题。印象中好多好多年前,似乎有人在一篇短文或一篇谈话中提及电影创作中的气韵问题,可现在已无法想起它的具体内容,也找不到这篇文字了。但它确实有过,所以我“不敢为天下先”啊!
通常我们都知道并承认“气韵生动”主要表现在书法与绘画方面。我国的诗论、文论中也都有相似说法,即画家、书法家作为创作主体的个人,可以将真气运到笔端而作画或作书法。电影是集体创作,如何体现出“气韵生动”呢?这也许就是研究这个课题的难处,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原因之一吧!但是,客观地说,我们又不能不承认某些影片的确存在着生动的气韵,或者说,观众能通过这些影片感受到那“气韵生动”的存在。例如根据台湾作家林海音的小说改编,由伊明编剧,吴贻弓执导的影片《城南旧事》,根据柯岩散文《深谷回声》改编的由陈凯歌执导的《黄土地》,黄蜀芹导演的《童年的朋友》,黑泽明导演的《八月狂想曲》,侯孝贤导演的《悲情城市》等等,这又如何解释呢?这是否说明作为艺术的电影也确实有某种途径可以使“气韵生动”存在,并能有效地传达给观众呢?”
现在,我们试着解一下电影剧作中的“气韵生动”之谜,能否解开,实在不大有把握,我只能说说自己的一点认识而已。
为此,我们不得不首先简略地对“气韵生动”一词作一点介绍和解释。
通常人们都认为“气韵生动”源于南齐人氏谢赫。他写了一部书,叫《古画品录》。他在品评27位画家时,说了这样一番话:
虽画有六法,罕能该尽。而自古及今,各善一节。六法则何?一曰气韵生动是也。二曰骨法用笔是也。三曰应物象形是也。四曰随类傅彩是也。五曰经营位置是也。六曰传移模写是也。”
这就是通常说的“谢赫六法”。那么,“气韵生动”的主要意思是什么呢?为了说得清楚起见,先将“气”和“韵”分开来讲。“气”,从我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宇宙观来看,气是宇宙间生命的本源。有关这方面的论述是很多的,如“观于人身及万物动植,皆全是气所鼓荡。气才绝,即腐败臭恶不可近。诗文亦然。”(方东树:《昭昧詹言》)“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曹丕《典论·论文》)又如,“气者,生之源也。”(《淮南子·原道训》)等等。近代,如著名美学家宗白华也讲:“气是生气远出的生命。”总之气是宇宙万物生命之本。如庄子说的“通天下一气耳,故圣人贵一。”那么,“韵”又是什么意思呢?韵是和谐、节奏、音乐感、余味、余音等等。“韵,和也。”(《玉篇·音韵》);“同声相应谓之韵。”(刘勰:《文心雕龙》)。现在,我们再看看“气”与“韵”的关系。气和韵比较,气是主要的,有了气才有韵,而有了气的韵则是美的极致。可见气和韵是辩证的统一,如蒲震元说的:“气韵合观,在哲学上合于《易经》‘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要求。在审美上,体现了阳刚与阴柔之美的有机统一,是大宇宙生命动静相生的整态美的综合体现。”(《文艺研究》1994年第4期),不难看出韵在文艺作品中也相当重要,甚至有人认为,“有韵则生,无韵则死;有韵则雅,无韵则俗”。关于气韵生动,还有许多问题可探讨,如气韵与气势,气韵与风骨,等等。这不是本文要详尽论述的题目。下面我们再谈两点,就进入电影剧作与气韵生动的具体讨论。一是谢赫讲的气韵生动作为艺术的审美标准,与顾恺之的“传神”说,基本上是一个意思。“传神”也罢,“气韵生动”也罢都讲的是作品的生命力。一部作品没有生命力,哪里还有“气韵生动”,还会“传神”呢?
二是有人说,“气韵生动”指的是作品的风格。这种解释虽然简单明快,也有几分道理,比如“气韵”与“风格”都融于作品之中,都有作者主观精神注入,都显现为作品形式的统一。即便如此,它们之间更多的是表面的近似,在实质上则有重要区别。换句话说,风格不能代替气韵,更不用说代替气韵生动了。
我们说过“气韵”是一种生命力,而“气韵生动”则是生命力的律动,生命力的火花,生命力的展示。它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体现在作家、艺术家身上,特别是作家、艺术家的人品、修养、气质、素质、艺术功力等等。二是体现在未来作品的对象上,如小说家描写的对象,画家作画的对象,电影表现的对象。这个对象既包括人物,也包括自然景物等等。三是体现在作家、艺术家与被表现的对象之间的中介物上。这个中介物对画家来说,主要是画笔、墨、颜料、画纸、画布等等。对于电影创作者,除了纸、笔,还有摄影机、布景、道具、服装、化妆等等,也可以说中介物是我们通常称为工具的那些东西。
读者可能提出这样问题,生命力之于作家、艺术家,这很好理解,因为作家、艺术家本来就是生命的主体。生命力之于创作对象也还比较易于理解,比如人物和他们生存的环境:阳光、雨露、树、河流、草、花,总之大自然的一切确实是有生命的。人物住过的房子,用过的东西也是有生命的,甚至化石,对于地质工作者来说都是活的生命。比较难理解的是作家、艺术家与表现(描写、再现)对象之间那个中介物,比如摄影机、布景、道具能有什么生命呢?这正是我们要弄清楚的比较微妙的问题。
其实,稍加细想,这问题也不难理解。比如作家使用的笔。据我所知,很多作家都有自己习惯用的笔,如果那支笔不见了,临时换一支笔写作,就会感到非常之别扭。可能坐在那里很久都写不下一个字,或者写几行就将稿纸撕掉,或索性把笔扔掉。又比如作家写作习惯用的桌子、稿纸也是如此,它们都变成了有生命的了。往往作家都有用于专门写作的房间,作家一走进那房间,往桌子前边一坐,就会文思泉涌。我有位俄罗斯朋友,他写作就在厨房里(厨房大而洁净),他随时要喝一点威士忌酒,打开碗橱拿点什么东西吃。同样道理,摄影机对于摄影师来说也同笔之于作家一样。一些作家不愿意用电脑写作,就是怕离开自己习惯了的笔,换另一种工具会无法写下去。当然,也有习惯于用电脑写东西的作家,电脑成了他的知心朋友,像两个初恋的情人那样彼此分不开,彼此深深了解。这更说明电脑作为写作工具是有生命力的了,类似例子可说不胜枚举。
如上所述,气韵生动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即有生命的创作主体的作家、艺术家,有生命的表现对象,有生命的工具。这三部分能够有机地和谐地统一起来,那么就会产生气韵生动。这样,就可想而知,并非所有艺术作品都能达到气韵生动。可以说气韵生动主要表现在少数优秀作品里。那些匠气十足的,或按一定公式、模式编排起来的作品,以及那些完全胡编乱造的东西,自然不会有什么气韵生动了,因为这类电影剧本和影片中没有灵性,是不传神的,它们根本无气韵可言,也无“神”可“传”。
其次,应该强调的是,造成气韵生动的作品的三个部分中,最主要的是作家和艺术家这部分。自然,我们应当看到,有些电影剧作家、艺术家本人主观上并没有明确地去追求气韵生动(他们多半追求电影剧本和影片的品位、内涵、风格),可却也使作品达到了某种气韵生动。这又如何解释呢?这是由于这些作家、艺术家自身的品格、修养、素质等已经具备了创造气韵生动的作品的条件或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他们对“气韵生动”缺乏理性的认识与把握,很可能在某一部电影剧本或影片中有了气韵生动,而在他后来的作品中失去了气韵生动,失去了这种艺术创作中最可宝贵的东西。因此,本文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所有视艺术为生命的作家、艺术家,对“气韵生动”都能有一种自觉意识,不致迷失自己,从而不断创作出第一流的电影剧本和影片来。
关于气韵和气韵生动,我们已经作了初步的概括的介绍,现在,我们对几部电影剧本和影片作些分析,以加深我们对“气韵生动”的理解、追求和把握。
《城南旧事》影片在80年代初,曾经是脍炙人口的佳作,今天再看这部影片,不论是对中国人还是对外国人,它仍然能给人们以艺术享受。何以会如此,这正是这部影片中的气韵生动所致,也就是说,无论到任何时候,任何年代,任何国度,它都是有生命力的。
首先,无论是小说家林海音,电影编剧伊明,还是导演吴贻弓,他们都对古老的北京城怀有一份深深的眷恋之情,保存一份难得的温馨。也就是说作家、艺术家是充满生命感地回忆逝去的老北京的生活,回忆浸过情感的一切,那熟悉的厚厚的城墙,那辘轳井,那水车,那骆驼,那驼铃声,那秋千,那小油鸡,那校园,这一切静止的东西,经过作家、艺术家观照便都有了生命,都在向观众倾诉一些什么……旧北京城的那几个人物,宋妈、小英子、小妞子、秀贞、英子的妈妈、爸爸、小偷、小偷的弟弟还有宋妈的丈夫,都以他们各自的日常生活态,不急不躁地淡淡地潺潺小溪一般倾诉着。那是一种没有倾诉的倾诉,也就是没有作家、艺术家的任何刻意,在自自然然地倾诉着。银幕上的人物,在表面上像湖水一般平静的生活中,在不知不觉中显露出并完成了各自的命运:英子爸爸平静地离去,化作台湾墓地里的一方石碑;秀贞牵着小妞子去寻找她的意中人,在火车吐出浓浓的气雾中悄悄地结束了她俩各自的不幸。宋妈告别了英子一家,骑上丈夫牵来的小毛驴回家乡去了,等待这位善良女人的已经是失去儿女的空洞与无奈。小偷是为了让弟弟能上学读书,才不得已去偷东西,在被官府抓走时,他并没有悲伤,相反他为能帮助弟弟上学而感到某种满足……这部影片的剧作显示出作家、艺术家的祥和,在他们平稳的叙述中透出几许哀惋。换言之,作家、艺术家选择了电影的散文样式作为叙事的载体,这表明作家、艺术家在叙述时,与所要叙述的对象在韵律上、格调上、情感上、节奏上、语气上都是一致的。也可以这样说,作家、艺术家的气韵与所描述的对象的气韵是一致的、统一的、和谐的。尤其是英子与小妞子玩油鸡等几处出现短暂的无声的“顿歇”,真可谓妙不可言,是气韵生动的一种极致,它恰恰如同国画中没有着墨的空白部分,这空白部分常常是国画中内涵最丰富,也是最精彩的地方。广大观众是如此喜欢这部影片,一遍又一遍地去欣赏它,这绝非偶然,它的最大成功恰恰在于气韵生动,即有赖于自身的生命力,特别是作家、艺术家自身的气韵的主导作用。因为我们从银幕上看到的城南旧事,它已经不是也不可能是事情原来的样子,它是英子眼睛里的事情,是作家、艺术家回忆中的,想象中的那段往事,是他们记忆中残留的、抹不去的那部分生活,因此也是作家、艺术家用自己的灵性、心血滋润出来的那部分城南旧事。总而言之,是作家、艺术家在描写对象这个第一自然的基础上,完成了的第二自然。所谓第二自然,就是经过作家、艺术家重新创造过的自然,即真正的艺术品。这部分影片就如同中国的气韵生动的风俗画卷。台湾徐复观教授在他所著的《中国艺术精神》中说道:“一个艺术家的最基本的,也是最伟大的能力,便在于能在第一自然中看出第二自然。而这种能力的有无、大小,是决定于艺术家能否在自己生命中升华出第二生命,及其升华的程度。”(《中国艺术精神》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81页)《城南旧事》影片正是作家、艺术家生命的升华的结晶,也是气韵生动所包含的三个部分(作家、对象、工具)的统一与和谐的结晶。
如果说影片《城南旧事》的剧作,突出了气韵的似水柔情一面,是有通常人们说的“曲则有情”的特点,那么,影片《黄土地》的气韵生动则突出了阳刚之气的一面。它是棱角鲜明的,直线式的,在叙事上也打破了我国观众习惯了的讲故事的模式。作者关注的不是观众的欣赏习惯,而是自己在描写对象中的发现,那是民族的历史、民族的命运、民族的沉重感、民族的希望。这一切都使影片如同用刀刻出来的版画。那无边无际寸草不生的黄土坡,那沉寂得令人透不过气的莽莽高原,那奔腾不息的滔滔黄河,那遮天蔽日的黄沙,那高亢凄凉的信天游,还有那些好像用高原黄土捏出来的老人与孩子,男人和女人。他们那刚毅、忧郁的脸庞,那榆树皮似的粗手,那披着破棉袄的放牛娃,那几百年、几千年前就使用的那种水罐、木犁,还有在黄土高原上蠕动的小小人影、虔诚的求雨的人群,腰鼓队脚下荡起的沙尘,震天响的鼓声……人们哪怕只看过一遍影片,能够忘记影片的情节、人物、故事,可却永远忘不掉属于黄土高原上的这一切,自然也忘不了挑一担水要走十里的山路(比日本影片《裸岛》所描绘的生存环境还艰难),也忘不了14岁就出嫁的山村女娃。黄土高原成了窒息人们生命的巨大的力,而窒息生命的力自身却也是一种生命,它就是黄土高原!它的确太悠久了,太凝固了,太沉重了,从古至今,这里的任何人都没力量改变它,又难以离开它。它像一块天造的磁石,紧紧吸住想要弃它而去的人。它太强大了,强大到无论是谁都只能顺从它的意志,顺从它的摆布。作家、艺术家能在一部影片里展示出如此恢宏的气势,如此沉重而深刻的内涵,让看过影片的人,尤其是我们这些炎黄子孙们,不能不和作家、艺术家一起站在这片黄土高原面前作认真的深深的思考:我们自己是谁,我们从何而来,我们该做什么,我们能做什么。
1993年,陈凯歌导演的影片《霸王别姬》,虽然更注重故事,注重了情节性,但是他在《黄土地》中所显示了的构思的博大、深沉、凝重仍然保留下来,并在新的样式中寻找到自己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将其称作《黄土地》的续篇。
如果说《城南旧事》影片体现出一种阴柔的气韵之美,《黄土地》体现了阳刚的气韵之美,那么,影片《童年的朋友》则是将阳刚与阴柔融为一体了。这部影片,是没有亲自经历过那个火与血洗礼的年代的年轻艺术家对那个时代的感应,对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人的理解。虽然影片中也有人物如班长、战士、伤员、炊事员、指导员等等,但他们主要不是以有个性的人存在,而是以一个革命人的整体形象而存在,并与艺术家的心灵相照应。换句话说,他们是艺术家用自己的感情、愿望、思想创造出来的,致使这个整体的人群被无私的、纯洁无瑕的光环笼罩着。这部影片,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是艺术家灵魂的外化,是艺术家追寻的梦。这个梦到了老干部乘小汽车到幼儿园看战友时才中断。这个“中断”是不对的,因为它打破了这部影片的生动气韵。这也许是年轻艺术家始料所不及。但是我们依然能准确无误地看到艺术家纯净的灵魂,即艺术家气韵的外化,这外化是通过剧中人物的一系列动作体现出来的。比如炊事员大声吆喝着给幼儿园孩子发饼干了,那不过是一些小米饭锅巴。其实,在炊事员乐观的声调里,在那些不规则的小米饭锅巴里都含着纯净的感情。又比如班长从集镇上回来送给女战士一把木头梳子。这在当年,对于战士来说,远比今天送一条金项链更珍贵,它深藏着多么纯洁的感情啊!又比如总是梦见上前线的爸爸骑着白马勇敢杀敌的孩子,那是孩子心中神化了的父亲,也是艺术家神化了的八路军英雄。特别要提到影片中精彩的一笔有着典范意义的一笔,那就是女战士给伤员献过血之后,又去挑了一担水。她挑着水吃力地穿过房子中间狭窄的长长的过道,来到茅草搭的伙房,将水倒进锅里,然后在灶堂点起火,接着无力地靠着灶坐下去,慢慢合上眼睛休息。天空飘下来大片大片的雪花,雪花轻轻地落到她乌黑的头发上,落到她的肩上、脸上,落到插在房檐茅草中的木梳上。雪花好像生怕扰醒了女战士的梦,轻轻地飘着,落着。女战士的样子是那样美丽,那样宁静,那样安详,那样幸福……一颗纯洁的灵魂,就这样离开了人世,悄悄地不为人知地,没有任何索取地走了。也许有人会说,这是艺术家将生活美化了。从现象上看,好像是艺术家对第一自然的某种美化,但我以为这与通常说的美化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美化是将不美或不够美的东西给以粉饰,在《童年的朋友》这部影片中则是艺术家有意摄取了那个年代、那种生活、那些人物的美质,然后把它们化作银幕形象,而这银幕形象恰恰让我们发现艺术家自身的气韵、灵性、精神。
上面所举的三部影片给我们的共同启示,就是我在本文开头讲的,“气韵生动”最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是作家、艺术家自身的品格、情感、修养、素质和艺术功力。正是他们自身的气韵涵盖了他们所要表现的对象,使得对象的生命力得以显现、活跃、展示出来,造成气韵生动的作品。这是不是说,描写对象,如果没有作家、艺术家气韵的灌注,那对象的生命力就会潜藏着,不露声色呢?我想,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这样的。比如,黄土高原在不同的人的目光中,不同的人的心中是不一样的,甚至可能截然相反。它在一些人心目中不存在什么生动的气韵,还可能是枯燥的乏味的。但在《黄土地》的作家、艺术家的眼睛里,它却充满了生命力,它能向他们倾诉许多东西。延安八路军的生活,在一般人看来也是没有多少浪漫主义色彩的。远离那个年代又没在那里生活过的人,看到和想到的大多是比较表层现象,什么延安的宝塔山啊、延河水啊、窑洞啊,可是在《童年的朋友》的艺术家的眼睛里,延安和八路军却在平凡中显示出一种纯洁女神般的气质,非常富于浪漫主义气息。毫无疑问,所有这些都源于作家、艺术家自身的气韵。问题在于作家、艺术家是否善于在表面上似乎没有生命的对象中发现它们的生命,并在灌注自己的气韵后,使对象活起来。假如没有作家、艺术家的气韵的投入,描写对象即使是非常丰富的宝藏,它依然会远离艺术之外,不会被发现。比如影片《山神》所描写的对象是长白山和那里挖人参的山民。这无疑比黄土高原,比延安八路军更有生命力,更有情趣,更富于浪漫气息。可惜的是,作者没有将自身的生命力(气韵)灌注于描写对象,也就未能发现长白山和这些挖人参者的内在品质。换句话说,作者没有发现描写对象的气韵,因为作者没有将自己的气韵灌注于那对象,那对象自然也就不可能将自己的气韵显示给作者,因为作者是站在描写对象之外去表现那些对象,所谓隔靴搔痒,这样一来,必然流于事物的表面,也就只能表现长白山与挖参人的外在的一般化的表面的某些特点。是的,如果作者没有气韵,对象也没有气韵,影片哪里会有气韵生动呢?观众对这样的影片也就兴味索然。又比如影片《悲烈排帮》所描写的对象也是很有生命力的,可惜它同样存在《山神》中那些问题。作者不是将自己的气韵灌注于描写对象上,演员不过是某种工具,是供作者做某种游戏、某种实验的符号。不管有人怎么用西方符号学对它加以注释,这部影片的没有气韵生动是无法改变的。请注意,凡是没有气韵或有气韵而不生动的影片,几乎都是品味较差,既不能“传神”,更不可能“传世”。
我们运用“气韵生动”这一审美尺度来观察国产影片,我们很容易就能区分出它们的艺术档次。凡是内涵丰富、有独创性、百看不厌、和谐、统一、完整的,基本上都是气韵生动的影片。余下的基本上都该列在“气韵生动”的影片之外,这类影片问题较多,带有普遍性的主要有这样一些:一是作者带有强烈的宣传目的;二是不把描写对象当作有生命的实体,刻意地或随心所欲地处理人物关系或安排情节;三是不把艺术创作当作生命现象,只想在艺术上“玩一下”。还可列举一些,一句话,其根源是作者自身缺少或没有气韵。
“气韵”对于作家、艺术家来说,实在是一种天赋,那么,没有这种天赋怎么办?那就更要下苦功夫去学,去研究,去实践,如明朝的董其昌所讲:“然亦有学得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脑中脱尽尘浊……”这位先生的精辟见地更说明,一部作品气韵生动,关键在于作家、艺术家对“气韵生动”的真正理解与把握。作家、艺术家自身气韵生动并能灌注到描写对象中去,作品自然就有了生命,就会“传神”,就可能造成艺术精品。一切将电影作为艺术来追求的人,一切视艺术为生命的人,难道可以忽视“气韵生动”吗?
最后,我想再回到本文开头的问题上,就是书法家、画家,甚至小说家、散文家都可以将自己的气韵,通过手中的笔或其它工具来体现,电影是集体创作的艺术,如何体现气韵生动呢?关于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一部影片所体现出的气韵乃是电影剧作家、导演(或编导集于一身)的气韵。其它如摄影师、美工师、剪辑师、化妆师等专家都是作家、艺术家的气韵的具体的体现者。他们是为了完成作家、艺术家的“气韵生动”而集合于作家、艺术家周围的。他们的创造性必须是有利于作家、艺术家气韵的完满体现,而不可相反,所以,首先作家与艺术家的气质必须是相投相通的,他们再选择合作者时,也应当选择能够理解和准确体现作家、艺术家气韵的专门家。世界上,一些电影大师如法斯宾德、伯格曼、黑泽明、莱兹曼等等都有比较固定的合作者,就是为了保证作家、艺术家的气韵得以创造性地再现。我们不能设想在一个摄制组里,作家、艺术家的气韵得不到与之合作的专家们的理解,不能将它体现出来,果真如此,影片获得“气韵生动”是不可能的。
写到这里,也就是我们即将结束本文的时候,我依然忐忑不安,我觉得我说清楚了我的本意,并且我越发相信“气韵生动”在电影剧作中极为重要的位置和作用。作家、艺术家能真正理解它,把握住它,这样的作家、艺术家将一生受用不尽,优秀作品将源源而出,否则写了多年电影剧本,拍了多年电影,都还会滞留于电影艺术的表层,始终没有真正跨入那气韵生动的美妙境地。
人们通常说,对艺术的把握,除了勤学苦练,还有一个“开悟”问题。艺术家与艺术大师之间常常就像隔着一条小溪,可是作家、艺术家没有“开悟”,他就永远跨不过去那条神秘的小溪,不能到达艺术大师的彼岸。说到底,就在于作家、艺术家对“气韵生动”透彻的认识、理解与把握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