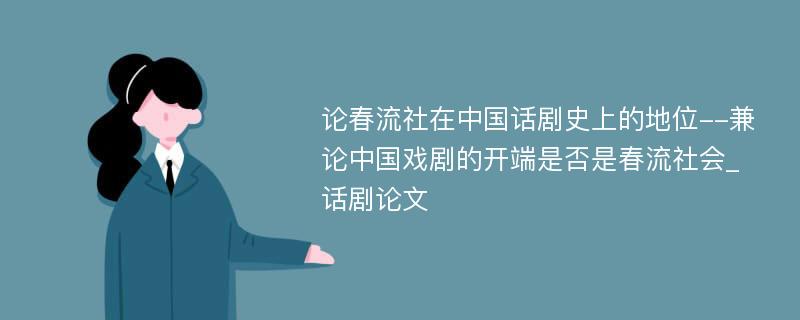
再论春柳社在中国戏剧史上的位置——兼谈中国话剧的开端是否为春柳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上论文,话剧论文,开端论文,中国论文,位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943X(2014)03-0057-08 一、问题所在 2007年中国戏剧界举行了庆祝中国话剧一百周年的各种活动。一百周年的起点是1907年春柳社的演出活动。但也在2007年,中国国内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此后,2009年在华南师范大学召开的清末民初新潮演剧研讨会上也产生了意见分歧。我本人一直认为中国话剧的起点是春柳社,所以在此要重新探讨春柳社在中国戏剧史上的位置以及中国话剧开端的问题。 除了片段性发言以外,傅谨先生的《重新寻找话剧在中国的起点》是质疑中国话剧开端问题的第一篇论文,该文后转载于《新华文摘》2007年第22期。[1] 紧随其后的第二篇文章是王凤霞女士的《重探百年话剧之源——中国话剧不始于春柳社补证》,[2]该文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舞台艺术》2008年6期,后来收录于其文明戏专著《文明戏考论》(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以下简称《考论》)[3]的第六章第二节。 第三篇文章则是朱栋霖先生等的《清末民初的新潮演剧(笔谈)》,后作为代序,收录于《清末民初新潮演剧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4]在此,朱栋霖先生就“春柳社不是中国话剧的开端”进行了具体的阐述。 依笔者浅见,近来讨论中国话剧开端问题的文章主要有以上三篇。我们先来了解三位先生的主要观点。 首先,傅谨先生在其文章开篇中指出:“如果以话剧在中国的首次公演作为标志,当然轮不到春柳社;以中国人首次演话剧为标志,也轮不上春柳社;春柳社不是中国最初的戏剧演出团体。”同样,王凤霞女士说:“笔者认为把春柳社演剧定为中国话剧的开端有一定的道理,也有较大的偏颇……但春柳社为标志也有偏颇,它遮蔽了春柳社之前上海已经培育了话剧产生的温床,其学生演剧已具有明显的早期话剧形态这一事实;还容易颠倒中国话剧产生的因果关系,是上海的学生演剧促生了日本的春柳社,而非一种外来艺术品种被某个偶然组织的学生团体奇迹似地移植到中国。并且,这一说法会使人们过分夸大中国话剧的日本影响,从而削弱我们对其他影响源和影响途径的关注。”[3](P.165)接着,朱栋霖先生也指出:“长期以来中国现代话剧的开端,一直被误解为1907年春日本东京留学生春柳社演剧活动。其实,在1907年之前,沪上学校的新剧演出就相当活跃,而且已成气候。”[4] 对此,笔者以为傅谨先生和朱栋霖先生虽然指出春柳社以前存在清末学生演剧,对清末学生演剧和春柳社的剧目及其演出活动并未加以具体分析。而王凤霞女士的文章较系统地提出她对中国话剧开端问题的想法,同时挖掘新的资料,对清末学生演剧活动有具体的探讨。 王凤霞女士主要提出了以下四个问题: 1.“春柳社是中国话剧的开端”的提法,是20世纪中期,即1957年才确定的。 2.学生演剧已具有明显的早期话剧形态。 3.春柳社是某个偶然组织的学生团体,其演出内容奇迹般似地移植到中国。 4.“春柳社是中国话剧的开端”这一说法使人们过分夸大中国话剧的日本影响。 笔者在此主要针对王凤霞女士提出的问题进行讨论,当然,同时也是对傅谨、朱栋霖两位先生的回应。 二、“春柳社是中国话剧的开端”这一说法是怎样形成的? 王凤霞女士指出:“春柳社在什么时候正式被确定为话剧诞生标志的?笔者认为可能跟20世纪中期中国的文化建设运动有关。”[3](P.164)王凤霞女士提到的“文化建设运动”,指的是1957年中国官方开始大规模庆祝中国话剧五十年。虽然这以前洪深等人“就认为中国话剧源于春柳社”,但王凤霞女士认为洪深的观点“毕竟是一种个人说法,不是官方论断”。[3](P.164) 首先要讨论王凤霞女士的这个说法是否妥当。 据笔者了解,在文明戏最繁荣的1914年,朱双云的《新剧史》已经指出春柳社在中国话剧史上占重要位置,即“丁未春二月,春柳社成立于东京。留日学生曾存吴、李叔同、吴我尊、谢抗白等慨祖国文艺之堕落,发起春柳社于东京。……上海各日报亦提倡不遗余力。因是而新戏之价值日增,流至今日。而其风始昌”。[5] 以上持否定“春柳社是中国话剧的开端”之论者均以《新剧史》作为重要的参照资料,因为《新剧史》明确指出了清末学生演剧的存在,而且比较详细,是我们了解清末学生演剧的重要资料。当然,也正是《新剧史》指出了有价值的新戏始于春柳社,即春柳社是中国话剧的开端。 其后,20世纪10年代到20年代初,谈新剧开端的文章不多,这时期穆儒丐1923年2月1日至7日连载的《说新剧》中介绍春柳社是中国新剧之始。① 至20世纪20年代末,即现代话剧确立不久之后,也有文章明确提出春柳社在中国话剧史上占重要位置,洪深《从中国的新戏说到话剧》可能是其中最早的一篇。洪深指出:“勇敢而毫不顾虑地,去革旧有戏剧的命,另行建设新戏的先锋队,不是中国的戏剧界,而是在日本的一部分中国留学生。他们……后来认识了藤泽浅二郎,得了他的帮助与指导,成立了一个春柳社。”[6]洪深的这段话后来被《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导言引述,并广泛流通。 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类似的文章越来越多。 郑伯奇在《中国戏剧运动的进路》中说:“文明戏最初的发生,诚然是和旧剧对立的……在这风潮中,比较规模稍大的戏剧运动要推‘春柳社’一派的运动。现在所有各种文明戏的团体,直接间接,都可以算为“春柳社”的分派。就是以后相当忠实从事新剧的人们,还有许多是‘春柳社’的健将。”[7] 剑啸《中国的话剧》也说:“清光绪丙午,(光绪三十二年,即公元一九零六年)有些留学日本的学生,鉴于中国旧戏应当改良而西洋话剧应该介绍和研究,于是纠合同志,在东京组织了一剧社,定名曰‘春柳’,社员约八十余人……十一月某日,假地青年会举行,在游艺项目中有一出新剧,剧名《茶花女》……这一次可以说在中国戏曲史上开了一个新纪元,更兼当时‘春柳社’的表演,也很不坏,因此极受欢迎……自‘春柳’迄如今,已然二十八年了,在这二十八年的长时间里,我们的话剧,也曾奋斗过不知若干时,也曾实验过不知若干次……”[8] 欧阳予倩在《自我演戏以来》中说:“这一回的表演可说是中国人演话剧最初的一次。我当时所受的刺激最深。我在北平时本曾读过《茶花女》的译本,这戏虽然只演亚猛的父去访马克和马克临终的两幕,內容曲折,我非常的明白。当时我很惊奇,戏剧原来有这样一个办法!……我向人打听,才知道他们有个社,名叫春柳。”[9]② 很明显,这些论者都认为中国话剧的开端是春柳社。 1934年穆儒丐也谈“在中国首创话剧者不能不归功于春柳社”。[10] 1935年还出现了一篇重要文献,即《国立戏剧学校之创立》(无署名1935年)。此文在创立国立戏剧学校之际,对学校的宗旨和目的进行了说明。该文章说:“至于话剧之传入中国,为时已二十余载。最初倡导者,当推春柳社。”③众所周知,国立戏剧学校(后来的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国立剧专)是民国时期实质意义上的第一所国立戏剧教育机构,此文可说代表当时的官方想法。由此可见,1935年官方便已经论断了春柳社是中国话剧的开端。 另外,1937年还有《中国剧运先驱者怀旧座谈会》,指出“予倩、李息霜、曾孝谷、唐恳这几位多还在,李和曾是用中国话来演剧的最初的尝试者,也可以说是开脉的两个人”。[11] 以上这些文章是笔者目前所掌握的,但疏漏难免。而通过这些文章,我们可以知道20世纪30年代,即抗日战争爆发以前,中国戏剧界已经形成了春柳社是中国话剧的开端这一观点,并非王凤霞女士指出的20世纪中期即1957年才形成的。 在此之后,春柳社是中国话剧的开端的说法得到进一步巩固。在此,笔者引用1957年官方正式宣布以前的几篇重要文章。 1938年徐慕云在《中国戏剧史》中说:“自一九○七年(光绪三十三年即民国纪元前五年)到一九三七年,恰好整整的三十年。在这三十年中中国的戏剧运动一共可以分五期,第一期即是‘新戏’与‘文明戏’,这一期的戏剧运动为留日学生所发动,首先公演于日本东京,后来他们回国,才在上海兴起,在中国诞生了文明戏。”[12] 1941年上官蓉在《文明戏与话剧》中说:“据说中国最初之有文明戏(姑且把原先的话剧称做文明戏吧)是发轫在留日学生团体里,当时“春柳剧社”便是轰轰烈烈的一个。”[13]④ 1944年欧阳予倩在《西南剧工大会欧阳予倩讲述话剧运动史》中说:“欧阳予倩先作剧运工作之开端报告,详述中国新兴戏剧运动自清末以迄‘八一三’各阶段之演变,略云光绪卅年左右,日本留学生在东京组织春柳社,演《茶花女》《黑奴吁天录》,以激发当时之民族思想,旋因满清之压迫而解散。辛亥革命后,春柳同人归国,在沪湘等地演出,颇受社会欢迎,一般人士亦开始认识戏剧为教育之重要部门。”[14]⑤ 1954年张庚在《中国话剧运动史初稿》中说:“春柳社的处女演出是在一九○六年十二月……剧目是《茶花女》……这次演出的规模虽然小,但是它却不像同时期国内那些新剧似的怎么也跳不出旧剧的圈套:不是放不下锣鼓,就是丢不开唱腔,至少也脱不出旧戏的动作姿态;而是完全另外一种样式,真正的话剧样式。”[15] 1957年徐半梅在《话剧创始期回忆录》中说:“日本留学生的开始演话剧,发动在一九○七年,这是借一个赈灾游艺会,在东京神田区青年会举行的。其中有一出《茶花女》……这第一次中国人正式演的话剧,虽不能说好,但比国内已往的素人演剧,总能够说象样的了。”[16] 1957年,中国戏剧家协会决定年底举行话剧运动五十年纪念活动,并在《戏剧报》1957年第7期上刊登《中国戏剧家协会将于今年底举行话剧运动五十周年纪念活动》,该文明确指出“中国的话剧运动是……从‘春柳社’时期受民主革命影响的演剧活动开始”,[17]确定了春柳社是中国话剧(运动)的开端。 三、为什么春柳社被认为是中国话剧的开端? 笔者认为,春柳社被认为是中国话剧开端的理由主要有以下五点: 1.《茶花女》《黑奴吁天录》,尤其是《黑奴吁天录》的演出本身质量高,获得了很大成功,留下了报道、剧评、剧照、回忆录等诸多资料,我们也因此能够了解春柳社演出的基本内容。 2.东京演出的反响迅速传到了中国国内,给国内尤其是上海戏剧界以很大影响。 3.春柳社孕育培养了欧阳予倩、陆镜若等中国戏剧运动的骨干人物。 以上三点已有诸多文章进行过详细论证,在此不做具体展开。笔者想要强调另外两点未受研究者广泛关注的理由。 4.春柳社不但受到日本新派剧的影响,而且也受到坪内逍遥领导的文艺协会影响,所以春柳社的演出比较明显地具有写实戏剧或者说现代话剧的特征。文艺协会是日本新剧(话剧)肇始时期的代表性团体之一,创立于1906年,1913年解散。春柳社在日本受到来自新派剧和文艺协会的双重影响。黄爱华女士的《中国早期话剧和日本》[18]、刘平先生的《中日现代演剧交流图史》(2012年)[19]等专著已经做过详细研究。⑥笔者仅在此举几个例子。 《春柳社演艺部专章》写道:“一演艺之大别有二:曰新派演艺(以言语动作感人为主,即今欧美所流行者),曰旧派演艺(如吾国之昆曲、二黄、秦腔、杂调皆是)。本社以研究新派为主。”[20]《春柳社演艺部专章》内容很像(前期)《文艺协会规约》。《专章》里的新派演艺显然不是指戏剧流派“新派”,而是新的戏剧的意思。 文艺协会以1909年为界限,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文艺协会是以戏剧为主的综合性艺术团体,后期文艺协会则成立了专门的戏剧团体,但其领导人都是坪内逍遥,所以艺术宗旨没有改变,即期求在日本树立写实的戏剧——新剧。春柳社骨干李叔同参加过前期文艺协会,陆镜若参加过后期文艺协会,陆镜若还在文艺协会《哈姆莱特》《傀儡之家》中担当角色,亲身体验过日本新剧(话剧)演出。文艺协会的演出是日本国内首次正式上演《哈姆莱特》《傀儡之家》,《哈姆莱特》演出也是在日本首次正式演出莎剧作品。陆镜若回中国后,1914年在《俳优杂志》第一期上发表了《伊蒲生之剧》,[21]介绍了坪内逍遥的易卜生论。 过去大家只注意新派剧(歌舞伎和日本新剧中间形态)影响了春柳社,不太注意文艺协会也影响了春柳社,但现在来看文艺协会的影响也非常重要。 王凤霞女士指出,“春柳社演剧和中国早期话剧(新剧)的形态并不十分一致”。[3](P.165)笔者同意此说法,春柳社确实和中国早期话剧(新剧)的形态并不十分一致。春柳社重视剧本、演出幕数较少、排练严格、演剧作风严肃、重视写实表演、重视国语(普通话)等等(语言问题将作为第5点在下文进行探讨)。前期春柳社(在日本)正是这样,后期春柳社(回中国后)也基本继承了前期春柳社的演剧形态和特征。春柳社的这些特征是当时的学生演剧以及后来的文明戏剧团没有或者根本缺乏的,但却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确立的现代话剧相同。也就是说,春柳社演剧比中国早期话剧更接近中国现代话剧的形态。笔者甚至认为春柳社演剧是不彻底的写实主义戏剧或者现实主义戏剧。通过遗留至今的《黑奴吁天录》剧照,我们也能了解春柳社演员的表演是比较圆满的写实表演。正因为春柳社保持着现代话剧的特征,所以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现代话剧成立后,话剧界人士常常回顾春柳社,认为春柳社是自己正在从事的戏剧形态即现代话剧的先驱和开端。 5.春柳社戏剧的最重要特征之一是用国语(普通话)演出。欧阳予倩在《回忆春柳》中说:“当时他(陆镜若)表示要参加春柳社,但因为他是常州人,不太会说普通话,孝谷认为他不能演戏,过了一晌,才勉强让他参加为社员。后来他为学习普通话,的确下了一番功夫。”[22]这段记述证明了春柳社是用普通话进行演出的。 世界各国均以用本国普通话演出作为现代话剧成立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中国也是如此。确立中国现代话剧的标志性演出是1924年上海戏剧协社的《少奶奶的扇子》。此演出被视作标志性演出的重要理由在于以国语(普通话)演出。现代话剧的成立和现代国家的成立有着密切的关系。现代国家的重要特征是国民的平等化和均一化。为了实现均一化的国民之间的相互沟通,原则上语言需要统一,于是国家开始建设并普及其通用语言,以消灭或者限制方言。现代话剧为现代国家建设服务的同时也促进了现代国家建设,并企图成为现代国家的国剧。 那么,清末学生演剧使用怎样的语言?有关清末学生演剧的资料不多,但徐半梅在《话剧创始期回忆录》中明确指出清末学生演剧使用的是上海方言。“中国人办的学校中的演戏,往往不是学校当局所主张,而是学生们自己发动,要求学校当局让他们参加,作为余兴的。所演的戏,并不像那天主教学校用外国语,而是用上海土白的。”[16](P.8)学生演剧之后的文明戏(除春柳社以外)也都是用方言演出的。 四、质疑“春柳社并非中国话剧的开端”说 在此,笔者想探讨王凤霞女士提出的有关春柳社的几个问题。 1.春柳社是否“偶然组织”的学生团体? 王女士说“一种外来艺术品种被某个偶然组织的学生团体奇迹似地移植到中国”。这个说法是否妥当? 春柳社成立的1906年、1907年是中国人留学日本的第一个高潮期。“随着‘新政’的推进,需要大批掌握各领域新知识的新式人材(才),但当时的中国刚刚摆脱了旧的教育,还难以适应培养新式人材(才)的需要。为了应对这种形势,清政府采取了派遣官员出国考察、奖励留学以及招聘外籍教师等措施。与此同时,随着科举制度的改革和废除,知识分子,特别是年轻人为了寻求新的知识,自发地前往海外留学。在这种背景下,日本留学迎来了兴盛时期。人数最多的1905年大约有8000人,另说有1万人,甚至呈现出超过2万人的空前盛况。”⑦这些留学生大部分集中在东京。在20世纪初的文化背景下,如此众多的学生(年轻知识分子)集中在一个地方,其中爱好戏剧的人组织剧社是很自然的事情。当时也是日本新派剧的全盛期,同时文艺协会也开启了日本的新剧运动,换句话说当时是先锋戏剧团体开始涌现并朝气蓬勃的时候。年轻的中国戏剧爱好者被日本戏剧所吸引并受其影响也是很自然的。也就是说,春柳社的成立以及春柳社受日本戏剧影响绝非一偶然现象,而是时事所趋之必然。 2.春柳社演出内容是“奇迹似地”移植到中国的吗?“春柳社是中国话剧开端”这一说法使人们过分夸大中国话剧的日本影响吗? 笔者刚才指出春柳社成立的20世纪初是中国人留学日本的第一个高潮期。众所周知,清末新文化运动给中国文化带来非常深刻的影响,而从梁启超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新小说》等刊物开始,清末新文化运动先发生于日本,随后才移植到中国国内。中国学者指出:“由于中日近现代文学相同的历史背景、相似的文化条件,的确存在着一种‘极为类似的文学倾向’,接受日本文学思潮的最实际的效应,便是使中国的‘潜在倾向’得到开发,并以日本为楷模和桥梁,进行卓有成效的中国文学的‘革命’转型。”⑧科学文化其他领域也是一样,春柳社仅仅是这种文化大潮中的一例,春柳社演剧内容传到中国国内并非所谓的“奇迹”。近现代中国文化深受日本文化的影响,正如日本古代文化深受中国文化影响一样。 五、如何认识清末学生演剧 首先需要确认的是,现在主张“春柳社是中国话剧的开端”说的人,包括笔者在内,从未否认或者忽视过清末学生演剧的存在。也就是说,大家是在知道清末学生演剧存在的前提下,还仍然主张春柳社是中国话剧的开端的。笔者对中国话剧成立问题的看法在《中国话剧成立史研究》[23]中有详细论述,另一篇文章《试论文明戏历史分期和它在中国戏剧史上地位》(《戏剧艺术》2006年第1期;董健、荣广润主编《中国戏剧——从传统到现在》,中华书局,2006年)[24]是《中国话剧成立史研究》第一部(文明戏部分)的汉语压缩版。两篇文章都谈到清末学生演剧(主要谈它作为话剧的不足之处)。 清末学生演剧的具体内容如何?大家都强调资料匮乏,现在能看到的,尤其是当年的报道等第一手资料大都是些片段性的报道,只提及剧名、演出日期、演出团体名字、演出场所等。王凤霞女士挖掘了当时报刊上的很多有关学生演剧的报道,并在《考论》中有所介绍。这些资料非常珍贵,但不可否认,这些资料也还都是片段性的,通过它们,我们可以知道春柳社以前在上海的学生演剧很活跃,但仍然无法把握学生演剧的具体形态。 谈及学生演剧的具体形态的是后来的一些回忆录。1957年徐半梅说:“那些学生们仅仅得到了可以公然在学校中演剧的权利;至于戏剧的本身都是就近抄袭那京班戏院中所谓时装新戏。他们剧情的选择、剧本的编制,实在都很马虎,既无人导演,又没有相当的练习,不过学生中几个爱好戏剧的人,过过戏瘾罢了。这个与京班戏院中所演的新戏,没有什么两样;所差的,没有锣鼓,不用歌唱罢了。但也说不定内中有几个会唱几句皮簧的学生,在剧中加唱几句摇板,弄得非驴非马,也是常有的。”[16](P.8-9) 徐半梅说的意思是清末学生演剧基本上属于京剧(戏曲)的变质物罢了,还不能算新的戏剧形态——话剧。(徐半梅认为春柳社是中国话剧的开端,我们在前文中已经确认过。) 《考论》中介绍了关于1906年女医学堂学生演剧的报道,但此报道仅提到表演“描绘入微”感动了观众,对演出的具体内容和形态没有进一步的介绍。且此次演出为女学生演剧,应为比较特殊的例子,不能将其一般化。 有当年从事学生演剧的人回忆,春柳社出现的时候学生演剧已经碰了壁。他就是汪优游(汪仲贤)。1934年汪优游记述到:“那时我已经编过好几种新剧本,而屡次演出之成绩,都觉得与我的理想相差太远,但是我只知道演得不好,却始终说不出一个理由。要怎样演法方能合我的意思。因为我们当时所看到的戏剧,无论是京、昆、粤以及一切杂剧,都是一个模型里印出来的东西,我们编剧也难脱离这形骸,老是在这臭皮囊中翻筋斗,顶破了脑袋也钻不出一条活路来。”[25] 正是这个时候从日本传来了春柳社演出,即新的戏剧形态的演出信息,中国国内戏剧界从中获得了如何克服困难的启示,于是创造出后来的新剧-文明戏。虽然汪优游没有这样记述,但已显而易见。 徐半梅、汪优游都曾在中国(早期)话剧史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二人均在回忆录中指出清末学生演剧的历史性限制。遗憾的是,王凤霞女士在《考论》中没有讨论这些重要的回忆,只说学生演剧已具有明显的早期话剧形态。笔者认为,《考论》是近几年文明戏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学术成果,笔者也从中获益颇多并深受启发。但《考论》在讨论中国话剧开端问题时,由于没有论及徐半梅、汪优游等当事人的回忆,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其结论的说服力。 王凤霞女士还指出:“春柳社之前上海已经培育了话剧产生的温床”。[3](P.165)笔者非常赞同这个观点,但“温床”毕竟跟“花草”不一样。 文章最后,笔者想谈谈研究中国话剧开端问题的态度。学术讨论跟政治讨论不同,学术讨论的目的不是决定谁赢谁输,百家争鸣乃学术欣欣向荣之表现。笔者虽然坚持认为春柳社是中国话剧的开端,但并不想将此观点强加给他人。王凤霞女士也认为“春柳社确实在中国新剧上占有重要地位”。[3](P.174)这说明笔者和王凤霞女士之间既存在不同认识,也存在很多共识。 清末民初新潮演剧研究还有很多未开拓的地方,中国话剧开端问题也是其中的一个。由于资料的匮乏,现在还不是对这个问题下结论的时候,还需要我们今后不断讨论、互相学习,同时共同挖掘资料,继续推进文明戏和新潮演剧研究。 注释: ①大江千晶的《穆儒丐思想轨迹之一端——以旧剧改革为中心》(“新潮演剧与新剧的发生”研讨会论文,2012年12月23日,中国戏曲学院),介绍了穆儒丐对春柳社的观点。 ②该引用依据神州国光社版本,和新中国成立后的版本有所不同。 ③中央戏剧学院图书馆、国立剧专江安史料陈列馆收藏着该文。 ④笔者所见文章收入梁淑安编《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1919-1949·戏剧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⑤笔者所见为广西戏剧研究室、广西桂林图书馆主编的《西南剧展》(丽江出版社,1984年2月)中收录的文章。 ⑥吉田登志子的《中国話劇黎明期における日中演劇交流》(《演劇学論集日本演劇学会紀》48号2009年6月)发掘新资料,也详细谈这个问题。魏名婕《论日本新剧运动对陆镜若的影响》(《戏剧艺术》,2012年第4期)也谈同样的问题。 ⑦参见李协京的《近代中国的赴日留学生:学术研究领域无亮点》(《教育史研究》,2004年第3期)。 ⑧参见徐美燕的《“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P.10-11)。 ⑨参见《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1919-1949·戏剧卷》中收录的文章,P.3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