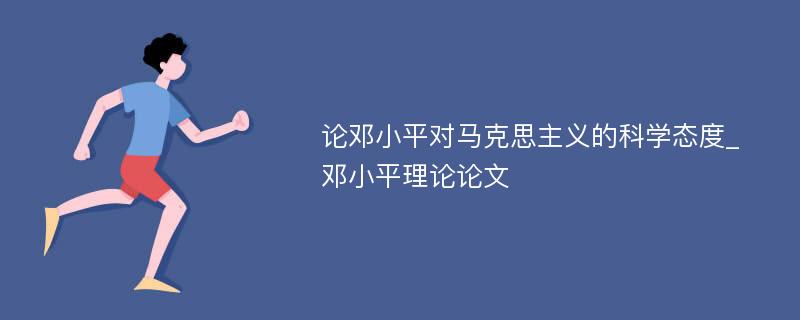
学习邓小平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态度论文,科学论文,学习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泽民同志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面对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形势、新情况,当前要着重解决好“四个认识”的问题,即: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过程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如何认识当今的国际环境和国际政治斗争带来的影响。解决“四个认识”问题的关键是要端正思想路线,在这方面邓小平同志为我们作出了表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在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探索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逐步搞清了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道路,同时也集中体现了邓小平同志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邓小平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可以概括为如下四点:
一、始终不渝地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不息
邓小平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奋斗一生,说到底来自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无论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白色恐怖,还是战斗在白区的刀丛虎穴;无论是百色起义时的危急时刻,还是在中央苏区蒙难含怨的日子里;无论是在太行山上搏战拼杀,还是在“文革”中被错误地批判,他都始终如一地坚信马克思主义真理,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仰。正如他自己所总结的:“为什么我们过去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1:110]“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搞共产主义。在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多少人牺牲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1:137]他还讲道:“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词叫共产主义。我们过去干革命,打天下,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因为有这个信念,有这个理想。”[1:173]面对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遇到大曲折,世界上盛行一般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逆流时,邓小平以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满怀信心地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1:383]即使是退休之后,他仍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肺腑之言告诫全党:“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1:369]信念的坚定来自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他说:“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1:382]是靠着对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邓小平同志眼光深邃,坚定沉着,处变不惊,以大无畏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率领中国人民改革创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二、从本国实际出发来运用马克思主义,而不是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
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通过革命实践改造现存世界,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本质特征,也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应持的科学态度。列宁从俄国实际出发而不是固守社会主义“共同胜利”的教条,在落后的俄国实现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毛泽东也不是在书本里,而是立足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找到了在落后的中国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道路。然而,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除了列宁在1921年实行新经济政策等少数场合以外,几乎全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不顾本国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基本国情,去照抄照搬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设想的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革命胜利后建设社会主义的某些论断,从而脱离了本国的国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走了弯路。
前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就存在理论指导思想上的失误。如斯大林在批判季诺维也夫“把俄国的落后性,把它的农民性放到列宁主义的定义中去”的偏向时,又走上另一极端,说如果认为“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实际情况中的应用”,“这就是把列宁主义从国际无产阶级的学说变成俄国特殊情况的产物”[2:14]。在斯大林之后,苏联共产党长期以来一直把马克思主义和各国实际的结合、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当作什么“反共的民族主义”来批判。这说明他们没能正确理解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即共性与个性、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二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共性寓于个性之中,共性只能通过个性表现出来,无个性即无共性。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性必须也只能体现在同各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之中。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上,斯大林早在1936年就宣布苏联已基本建成社会主义。二战结束以后,斯大林再次不顾苏联生产发展水平还不高的现实,提出要建设无阶级的社会主义和逐渐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任务。企图毕其功于一役,犯了急性病。他们还推行大党大国主义,把自己的经验作为世界共产党人的“必读教科书”,把苏联模式强加于兄弟党和兄弟国家。赫鲁晓夫上台后进一步加深了这一错误,在1959年苏共“二十一大”提出苏联已进入“一个新的重要的发展时期——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时期”,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上甚至制定了具体的时间表:“在二十年(1980)内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宣称“这一代的苏联人将要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3],提出各社会主义国家大致同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设想。这种教条主义和“左”倾错误倾向不仅给苏联,而且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灾难性的破坏。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我党虽曾提出以苏联为鉴,力图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工业化道路,但却并没有从苏联的错误中吸取深刻教训。相反地,还把这种错误倾向同所谓越穷越要革命的想法结合在一起,一度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遥远将来的事情了。在生产力上急于求成,助长了浮夸风、“大跃进”;在生产关系上盲目求纯、“一大二公”,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结果是生产关系人为地超越了生产力的发展,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直到酿成“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历史悲剧。
邓小平同志鉴于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重新明确了实践标准,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而解决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纪性新课题。邓小平说:“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63]“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1:191]而在这个问题上,最大的实际就是对我们所处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基本国情,要有一个准确的把握。
1987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客人时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处在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4:252]我们党正是以此立论,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纲领,制定了改革开放政策,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可见,正是邓小平同志领导我们党从本国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才有效地发挥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作用,保障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
三、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科学体系同它的个别论断区分开来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反复讲过,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毛泽东也一再批评那些把马列主义当作教条看待、把马列书本上的某些字句看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圣药的人,批评那些只会片面地运用马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其立场、观点、方法去研究、分析、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人。可是,在现实生活中的某些时刻和某些场合,还是存在着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条化的错误倾向。例如,在毛泽东晚年的时候,林彪就鼓吹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毛泽东去世以后,又出现了“两个凡是”,即所谓“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企图照抄照搬毛泽东晚年的个别论断,阻挠党和人民拨乱反正强烈要求的实现。
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邓小平强调“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4:42]在这里邓小平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科学体系同它们的个别论断明确地区分开来,强调要从基本原理和科学体系上来把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不应该把它们肢解、割裂开来,把它们的个别论断绝对化、神圣化。他指出:“至于个别的论断,那么,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4:171]即使这些个别论断就当时当地的条件来说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3:43]
正是依据这种认识,我们党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果断地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停滞封闭转到改革开放等战略决策上来。也正是根据这种认识,我们党在批评和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同时又充分肯定了毛泽东为我党、我军、我国的创立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的不可磨灭的功勋,肯定了毛泽东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各个方面的卓越贡献,指出毛泽东思想在今后还将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对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的批评不能过分,不能出格,因为否定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意味着否定我们国家的一段重要历史。这就会造成思想混乱,导致政治的不稳定。”[1:284]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科学体系同它的个别论断区别开来,体现出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为我们正确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四、依据历史发展的要求,把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统一起来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必须坚持和继承。同时,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穷尽真理,而要依据历史的变化,不断总结人类实践和认识的成果,及时回答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把理论推向前进,因此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说明,坚持继承和发展的统一,必须既要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凝固化的教条主义倾向,又要反对抛弃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倾向。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往往两极相通,有些人在教条主义地照抄照搬失灵之后,就跳到另一端去鼓吹“马克思主义危机论”或“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抛弃马克思主义。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代表就是戈尔巴乔夫。早在1983年,自称坚持社会主义的戈尔巴乔夫就说过:“我们的社会要改头换面,彻底改变自己的性质。”苏联解体以后,他竟踌躇满志地说:“就我的工作而言,我一生的主要目的已经实现,我感到安宁。”1999年他在一次讲演中作了坦率的自供:“我生活的目的就是要消灭对人民实行无法忍受的独裁统治的共产主义。”[5]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败在戈尔巴乔夫手里,这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戈尔巴乔夫之流背叛马克思主义、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
和这种态度相反,邓小平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一开始,就强调要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继承观中解放出来。早在1979年初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他就指出:“我们当然不会由科学的社会主义退回到空想的社会主义,也不会让马克思主义停留在几十年前或一百多年前的个别论断的水平上。所以我们反复说,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4:179]我们“绝不能要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1:291]小平同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既没有丢马克思主义老祖宗,又不断总结、推出一些老祖宗没有说过、而又符合时代特征和客观实际的新理论。而这些新理论的典型,当首推社会主义本质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
关于社会主义本质,长期以来囿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解,把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当作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征。邓小平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1:370]邓小平把发展生产力列入社会主义本质中,是对马克思主义历来重视生产力的基本原理的继承和发扬,而把解放生产力也列入社会主义本质中,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
同时,邓小平还继承了《共产党宣言》中把共产党人的理论概括为“消灭私有制”的传统,强调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1:138]和我们在改革中要始终坚持的“根本原则”之一[1:142]。与此同时,邓小平又总结我国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几十年来离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去盲目追求更高形式和程度的公有化,反而阻碍了生产力发展的历史教训,在谈到社会主义本质时,把社会经济制度方面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蕴含在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之中,从而使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可以根据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实际要求以及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实际进程具体确定。
在市场经济的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根据他们所处时代的状况,针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弊端,在预测未来社会发展趋势时,曾设想在资本主义以后的未来社会里,最终将走向统一的全社会公有制,商品生产、市场经济也将随之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计划经济。他们倾向于把市场经济连同资本主义私有制一起加以否定,同时对计划调节在资源配置中所起的作用也估计偏高。
但是,现实生活的发展却在不断冲击着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从属于社会基本制度的概念。一方面是进入垄断阶段、特别是国家垄断阶段以后,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计划对经济进行的干预和调节大大加强;另一方面,则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把取消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的思想付诸实践以后,计划经济本身管得过死、难以调动群众积极性的弊端日益暴露出来,而且还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难以解决物质匮乏和消费品不足等问题。从列宁到斯大林、毛泽东以及东欧一些国家的经济学家,都曾为此进行过探索,但都没能取得突破。邓小平同志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大胆创新,从根本上破除把计划和市场看作是从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地从理论上解决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问题。邓小平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373]正是破除了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思维定势,我们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回答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未能解决的在经济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现实课题。
可见,邓小平之所以能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崭新阶段,创立我们党称之为邓小平理论的这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在于他对马克思主义所抱的科学态度,这就是:始终不渝地坚信马克思主义,从本国的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科学体系同它的个别论断区分开来,以及依据历史条件变化把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统一起来。这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创新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相信,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继续不断地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我们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必将取得最后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