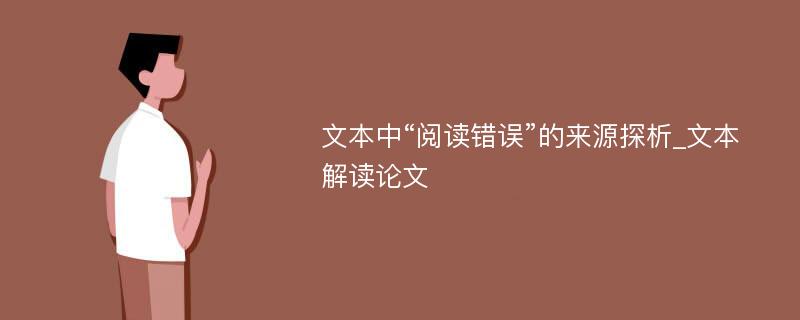
文本“读误”探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本论文,读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语文学习》2007年第3期刊发了拙作《正确认识文本解读的价值》一文。在文中我对“鲁提辖是杀人犯吗”的教学方式进行了辨析,认为这种阅读教学不能体现经典文本的价值,不值得提倡。可是,在我们的语文课堂,类似于“鲁提辖是杀人犯吗”的教学方式却屡屡出现,甚至作为优秀范例展示于报刊杂志。比如“孔乙己告状”“鲁提辖打官司”“祥林嫂死因调查报告”“精神胜利法利弊谈”等等。不少教师以对文本的“创新”处理为能,也以学生的奇谈怪论为荣,使中学阅读教学陷身于浮躁和肤浅之中。王荣生先生认为,这种阅读不是因为对文本的不了解而产生的“误读”,而是为了哗众取宠、标新立异,刻意曲解文本的结果,他把这种文本阅读方式称为“读误”[1]。为了更好地了解“读误”,从而避免“读误”,我们有必要对“读误”的产生原因作一点探析。
一、读者中心论和多元解读论对阅读教学的影响
随着本体论阐释学、接受美学、文本学和读者反应理论的兴起与发展,当代文本解读观摒弃了过去只注重“作家—作品”的解读模式,把文本解读的重心转向文本—读者,视读者的解读为文本的本体存在。现代阅读学认为,读者不仅是作者创作动机的最初激发者,而且是创作的最终完成者。读者有权对作品作出独立的不同于作者意图的阐释。“解构主义指出:重复性阅读寻求的是译解,梦想寻找到真理或源泉,批评性阅读不再关注真理,不再寻找源泉,它只肯定阅读的游戏。”[2]
叔本华认为,“记录在纸上的思想无异于在沙上行走者的足迹”,“我们也许能看到他所走过的路径,但要想知道他在路上看到了什么,则必须用我们自己的眼睛。”钱钟书先生也曾说:“我主张作者对自己的作品不应插嘴。”于是甚至有人发出这样的呼声:“作者死了!”这种“读者中心论”的文本解读观点对我们中学语文教学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语文课程标准》就提出了“注重个性化的阅读”“应尊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独特体验”等等“尊重读者”的教学要求。正因如此,有些老师在阅读教学中就走向了片面,认为只要是学生有独特感受的阅读就是成功的阅读,有“创造”的阅读就是好的阅读。只注重感受、创造的形式,而忽视方法、态度的指点和价值的引领。
其实,我们必须认识到,阅读学所指的“文本解读”和中学语文教学的“文本解读”有着很大的不同。阅读学意义上的读者是“成熟的读者”,而中学语文教学里的读者却是“不成熟的读者”。正因为学生和文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所以才需要教师去引领和点拨。王尚文先生说过这样一段话:“教师对这个世界中的许多东西应该已有所知,因为他已在前人的引导下进入过其中,他已听过前人的介绍,他也已有过自己的探索和发现。在这个世界中,教师要引领学生走安全的道路,要通过师生心灵的相互沟通,让学生知道哪里有沼泽陷阱,哪里有悬崖峭壁,哪里有激流险滩;让学生知道哪些是会伤人的野兽,哪些是会夺命的毒菌,哪些又是会害人的罂粟花……”[3] 这就形象地指出教师在教学中的作用。所以,我们强调以学生为阅读的主体,鼓励学生有独特的阅读体验,并不意味着对学生理解的纵容和放任。阅读教学其实就是“教师帮助学生成长为成熟的读者”的过程。
《课程标准》提倡“多角度、有创意的阅读”,认为对文本可以有不同的感受,得到不同的结果。于是有不少老师在上课时为了体现新课程理念,刻意追求新、异、怪,并认为这样就是在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这是对多元解读的误解。为多元而多元的课堂固然是有创新,但更多的是对文本和他人观点的漠视,最后形成“求异式阅读、抬杠式阅读”的泛滥——你说愚公不愚,他偏说愚公愚蠢;你说岳飞是民族英雄,他偏说破坏民族团结;你说阿Q对吴妈说“我要和你困觉”可笑可憎,他偏说那是阿Q淳朴坦诚的真情告白。这种根本不尊重作者和文本的“多元解读”有何价值可言?
阅读教学不同于一般阅读,我们需要文本解读理论的指导,但是更需要辨清它在教学上的适用范围和价值。
二、“言语教学论”和“阅读对话论”被泛化和曲解
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论著《普通语言学教程》经过不少专家的介绍与发展,对语文教学产生了极大影响,而他们的核心论断——“语文教学就是言语教学”的观点也被很多教师所接受。然而在实际教学中,由于“言语”和“言语能力”内涵的相对宽泛,使教师在具体教学时容易产生“脱轨”。因为任何形式的课堂都会产生阅读、思考、倾听、表达等等“言语活动”,而这种“活动”的量和质都很难以显性的方式来呈现——让学生朗读一节课是言语活动,让学生讨论一节课也是言语活动;讨论出理想的结果是言语活动,讨论不出结论也是言语活动。而事实上是,有结果的不一定对提高学生的言语能力有利,而没有结果的可能让学生的言语技能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锻炼和提高。因此,由于对“言语能力提高”评价的困难和对“言语”内涵理解的泛化,使语文教学内容也随之泛化。如教《我的第一本书》的时候,就让学生大谈“你的第一本书是什么?内容是什么?你当时有什么感受”;教《事物的正确答案不止一个》就搞“脑筋急转弯、一题多解”的游戏;上《出师表》就弄个“三国故事会”,评选故事大王。对于一篇课文,朗读、表演、辩论、讨论……各种课堂形式百花争艳;语言欣赏、形象分析、写法指导、借古思今……各种教学内容随你而定。“因为都是言语活动,所以都是语文教学”——这种对于“言语教学”的片面理解在当前语文教学中很有市场。
与“言语教学论”的遭遇类似,“阅读对话论”也在教学实际中遭到了泛化和曲解。《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文本之间对话的过程”,这里的“对话”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话语交际,而是在彼此独立和尊重的基础上,通过了解、询问和思辨,进行倾听和表达的活动。这种活动,不是以对话为目的,而是谋求通过对话来达到“视域共享后的一致”。可事实上,有不少老师把质疑文本当成对话,把和前人观点唱反调当成对话,类似“父亲爬月台是违反交通规则”“武松景阳冈打虎是滥杀珍稀动物”“关羽过五关斩六将是恩将仇报”等“创造性阅读”屡见报端;也有不少老师把“问答”“讨论”“辩论”等课堂形式当成对话,把争论得热烈、讨论出新意看成是对话的成果,只关注是否思考,是否表达,是否倾听而不关注思考是否正确,表达是否合理,倾听是否有效。“教师如果能在教学中引导调动得出现学生与自己‘面红耳赤’争辩的情景,可以说,我们的对话教学就走上了真正对话教学的成功之路,走向了对话教学的艺术佳境。”[4] 这种对“对话”含义的曲解和操作的泛化,是阅读对话和教学对话流于肤浅的重要原因。
三、教材教学内容的不确定使阅读教学随意性大大增强
教材是实现课程目标的重要途径,然而现行的教材大多只是给教师以用来教学的文本,却没有明确该文本的教学内容。比如“感受亲情”这一单元里的几篇文章,它的教学内容难道就只是通过这些文本来感悟亲情么?鲁迅的《风筝》也在这一单元,它的教学内容该是什么?光一个“感悟亲情”显然太肤浅也太玄虚了。
《课程标准》指出教师也是课程的建设者和创造者,看似给予了教师更大的自主权利,而事实上是给教师增添了更大的障碍。对于同一个文本,不同的教师会有不同的处理方法,但是,在这些不同的处理方法中应该有一个着眼于课程目的和学生实际而定的基本教学内容。而由于教材没有提供这一“基本的教学内容”,使目前的阅读教学随意性很大。不同的教师面对相同的学生时所选择的教学内容可能截然不同:你上人物形象分析,他上写作手法鉴赏;反之,对不同阶段的学生所选择的教学内容则可能相同:八年级的课文可以放到七年级去上,高中的课文也可以让初中生去学习,而且方法一样,目标一致。这种阅读教学显然是违背教学规律的。
不同的学习阶段,我们应该选择不同的教学材料和教学内容。对于不同的文本类型,我们所选择的教学内容也应该有所不同。对此,王荣生教授作了较为中肯的阐述和有效的尝试。比如,他把文本分成为“定篇”“例文”“样本”“用件”等四种类型,对这四种类型的文本提出了不同的教学内容取向。[1] 《语文学习》上刊载的一系列“单元样章”的文章,也正体现了这种思想,对改变教学内容的随意性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如“鲁提辖是杀人犯吗”“孔乙己告状”“祥林嫂死因调查报告”等案例所涉及的文本,大体上应该归类为“定篇”。我们认为,作为一个经典篇章,它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共性的教学内容。这种教学内容的确定既是文本自身价值所决定的,也需要和某一学业阶段的学生特点相适应,而不能带有太大的随意性。因为阅读经典,不仅在于获得阅读方法,也在于得到文化传统的启蒙和文化精神的熏陶。“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它们带着先前解释的气息走向我们,背后拖着它们经过文化或多种文化时留下的足迹。”[5] 经典已经不是一般的文本那么简单,它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思想和文化。对于经典的阅读,用朱自清的话来说是“不在实用,而在文化……在教人认识经典一番”,是在于“了解和欣赏”。王荣生先生也认为,对于中学教学来说,经典的解读是有答案的,这个答案就是“当前学术界所推崇、所认可”的观点。它们是我们进行经典解读的“内化”要求和立足点。[1] 我们没有必要抛却前人的研究成果,放弃“巨人的肩膀”而去闭门造车。
在阅读教学时产生“读误”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教师自身认识的局限和教材编撰的不足,也有社会价值评价的负面影响和教育观念在变革中的泥沙俱下。要改变和消除“读误”现象的泛滥,还需我们擦亮眼睛,静下心来,实实在在做一点努力,让理论、观念和教材真正为教学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