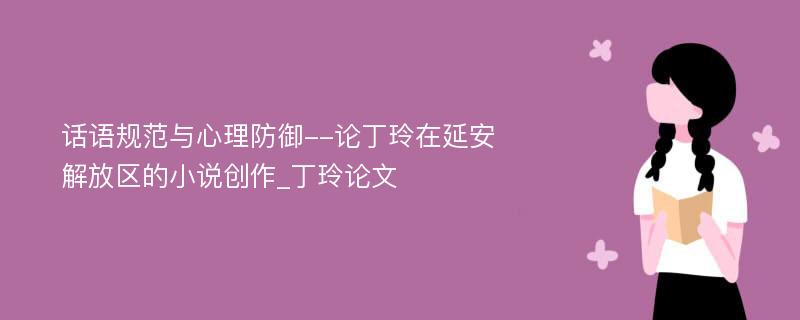
话语规范与心理防御——论丁玲在延安解放区时期的小说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延安论文,解放区论文,话语论文,时期论文,心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602(2013)02-0107-11
一
在现代中国作家中,恐怕再也没有人比丁玲(原名蒋冰之)的命运更让人扼腕叹息的了。作为现代中国最具有叛逆精神和艺术才华的女性作家之一,她先是在解放前被蓄意制造“白色恐怖”的国民党统治者囚拘于“魍魉世界”,后又被其毕生追随的共产党“红色政权”在建国后不久放逐于“风雪人间”,这两次牢狱之灾耗费了她生命中最美丽的青春和黄金般的盛年。前一次是遭罪于立场过“左”,后一次又得咎于太“右”,丁玲的人生境遇显得是如此的尴尬而困窘,她的一生似乎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冤”,她那倔强的生命始终在权力的炼狱中挣扎,这一切恰被其早年师友瞿秋白所不幸言中:“冰之是飞蛾扑火,非死不止”。①
直到有一天,当人们听到“文革”后复出文坛的丁玲居然鼓吹“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②的时候,他们不禁震惊了,困惑了,最终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苦涩的现实:昔日的“莎菲女士”早已被湮没于历史的尘埃,如今替代她而浮出历史地表的人只能是“劳模杜晚香”了。叹息之余,人们不禁又惊异于红色文学话语秩序的威力。自从1936年辗转奔赴红色解放区以后,丁玲便开始在红色革命熔炉中重新铸炼自己。近半个世纪以来,虽然也曾有过迷惘和徘徊,但她最终还是被改造成了红色文化工程在文艺界的一个“样板”或曰“模范”,所有原本属于知识分子的“灰色”“小布尔乔亚”情调已然被逝去了的红色时代洗刷净尽。实际上,当年走进延安红色文学秩序的丁玲并非一位纯粹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她的身上早已刻下了“左联”时期革命文学话语规范的深深印痕。丁玲步入文坛之时恰逢中国新文学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话语裂变时期。在当时的左翼知识分子心目中,“五四”启蒙文学话语及其深层话语构成规则系统——现代启蒙“知识型”必将而且正在为新兴的革命文学话语及其内在的红色革命“知识型”所取代。③于是,以集体价值为本位的“阶级解放”话语思潮对以个体价值为本位的“个性解放”主流话语发动了猛烈的抨击和系统的话语清算,立足未稳的“五四”启蒙知识型及其文学话语逐渐退居时代的边缘。最初的丁玲似乎未曾意识到时代话语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型,她依然陶醉在“莎菲女士”式的个人主义的话语迷梦之中。然而,丁玲终究未能抵御得住时代话语的诱惑,不久她便创作了《韦护》,“陷入恋爱与革命的冲突的光赤式的阱里去了”。④其后由于“红色恋人”胡也频惨遭国民党杀戮,丁玲开始加速“左倾”,创作了被冯雪峰誉为是“新的小说的诞生”的标志的《水》,该作以其正面展开农民阶级集体反抗地主官绅统治者的宏大叙事为革命文学的发展确立了新的“版型”。⑤但丁玲文学生涯的革命化进程为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所中断或减缓了,囚居南京期间留下的《意外集》成了她“最不满意的一个集子”,⑥由于人身和言论的不自由,她的早期作品中沉郁灰暗的格调重新又取代了一度曾激情洋溢的革命文学风貌。我们必须清楚,当年的丁玲正是以这种复杂而又矛盾的文化身份去的延安解放区,等待她的命运是全面接受红色革命话语秩序的深入净化和重新改造。
“左联”时期的上海在革命化的程度上显然不能和抗战后的延安同日而语。当年上海滩上的“革命文学”理论话语纷纭驳杂、时有变异,难达到共识以成创作定规,且又遭到国民党“文化围剿”的暴力干预。而自从中国工农红军胜利抵达陕北后,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便开始以延安为轴心,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文艺诸方面全盘着手构筑一个中华大地上史无前例的红色社会秩序,历史表明,这其实就是后来红色共和国的雏形。在红色政权的制度依托下,经过毛泽东根据历史情境加以选择、改造并发展了的“革命现实主义”理论话语体系,很快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为标志,一跃成为主流文学话语规范,从而支配了整个红色区域的文艺话语实践,甚至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国统区和沦陷区进步作家的文学话语方式。可以说,1940年代的延安解放区文学,正是当时中国红色文学话语秩序形成的中心。
丁玲是延安红色文学话语秩序接纳的第一个来自“亭子间”的著名作家。她曾先后在红军军营、不同的文艺组织团体以及党的核心报刊中接受过正规化训练并担任过重要职务。丁玲明确反对那种认为延安是在抗战后由于知识文化人的大量涌入才有革命文艺的说法。⑦实际上,从1936年“中国文艺协会”的成立到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乃至以后,毛泽东始终在谋求建构一套完整的中国化的红色革命文艺规范体系来服务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军事目标和红色政治理想。⑧显然,《讲话》的发表标志着延安红色文学话语秩序已基本建立,因为它其实是从内容(“为什么人服务”)到形式(“如何去服务”)整体上为当时的解放区文学“立法”,一种红色的革命文艺话语生产范型已初具规模。不难想像,《讲话》发表之前和以后,红色文艺话语规范对延安解放区作家的创作实践在规范力度上是有强弱之分的。也就是说,当时延安解放区作家作为话语主体,在《讲话》发表的前后,面对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学话语规范的制约,他们在具体的文学话语实践中并非简单化地认同或反抗,而是有着不同程度的抵御或超越。这一切在丁玲延安解放区时期的小说创作中有着鲜明而集中的体现。本文将首先分析丁玲在《讲话》发表前的小说创作中所暗含的三种心理防御方式,即自我投射、体验“他者”和忏悔仪式,然后以红色经典《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为著例,集中剖析丁玲在《讲话》发表之后,经过四年多的规训和调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恢复或修正了前期的三种心理防御方式。
二
丁玲在《讲话》发表之前的小说创作集中产生于1939—1941年,那时正处在延安红色文艺话语生产范型日趋成型的历史语境之中。这首先表现在文学话语内涵中的红色意识形态日益紧密的强力渗透,其次表现为红色革命文艺的话语方式正沿着“大众化”和“民族形式”的艺术轨道强力推进。如何使自己个人化的小说话语实践不至于沦为红色意识形态的简单图解,并有限度地从红色文艺生产范型中出轨,避免写作政治传声筒式的作品,这对于当时的丁玲来说已经成了必须策略性地应对的艺术困境。
自我投射曾经是丁玲最热衷的文学话语方式之一。在冯雪峰看来,早期的丁玲正是凭借“非常浓重地把自己的影子投入”到莎菲式的人物中去达成“同感”,从而“建立自己的艺术的基础的”。⑨然而时过境迁,置身于红色文学话语秩序中的丁玲已不可能再像早年那样自由地塑造女性知识分子形象来投射自身的思想情感内蕴了。因为,在红色文艺话语生产范型中,知识分子只能够以否定的形象或形态出现,即作为工农兵政治文化体系改造的对象而存在,而一旦创作主体背离了这一文艺生产范式就会遭到主流意识形态权力话语的攻讦乃至惩罚,丁玲的短篇小说《在医院中》及其主人公陆萍在延安文坛中受批判的遭遇就是明证。但是,延安的红色文艺生产话语规范并不能彻底地压抑住丁玲内心深处自我渴望投射的艺术激情。与塑造知识分子陆萍时创作主体采取的显性投射方式不同,丁玲在塑造贞贞(《我在霞村的时候》)时运用了隐性投射方式,即让主人公在披上“农家女”这件红色外衣的同时,曲折含蓄地传递着话语主体自身隐秘的思绪和情感。实际上,这种隐蔽而机警的话语防御方式对于身处泛政治化的历史语境中的丁玲来说更为适宜,至少运用这种艺术策略而写成的作品在延安时期并未招致大的非议(建国后“反右”“再批判”时受株连那是后话),这说明它们基本上还是为当时的红色文学话语秩序所接纳,当然只能是处在秩序的边缘而不是中心。
作为艺术话语方式,投射是一种普遍的心理转移机制,它把话语主体的精神心理内涵转移至作为话语客体的艺术形象之中。在荣格看来,“投射总是一种无意识作用”。⑩这一方面意味着对于话语主体来说,自我投射在艺术话语实践中始终处于不自觉的无意识状态,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自我投射在本质上是一种补偿性的心理防御策略,它是在话语主体的直白宣泄和明确传达方式遭到外在话语规范的强制阻遏后应运而生的,故而时常处于不自觉的无意识状态。总之,自我投射是话语主体潜在地反抗或突破话语规范的压抑的途径之一,它是话语主体对自身话语权力的一种隐形“自卫”方式。其实按照西方深层心理学的普遍说法,荣格所说的投射的无意识性质可以理解为两层内涵,即前意识性和潜意识性。前意识居于无意识域的表层,与意识域相毗连,而潜意识则深藏于无意识域的底层,二者共同构成了话语主体心灵的无意识家族。
不难看出,丁玲在知识分子陆萍身上运用的显性投射策略是在创作主体心灵的前意识层面上运行的,而在农家女贞贞身上采用的隐性投射策略则是在创作主体心灵的潜意识层面上运作的,二者超越和防御的目标则潜在地共同指向了作家所置身的延安红色文学话语秩序及其文艺生产话语规范体系。实际上,作为心理防御方式的自我投射也是一种文本话语防御方式或叙述策略。文本的话语防御功能体现在文本的意义生成过程之中。《在医院中》其实传达的是女医生陆萍与她所置身的环境(医院)之间的尖锐对立,以及由此所衍生的强大心理焦虑。陆萍的理想是切实履行医生的职能,然而“医院”简陋的自然环境和粗俗的人文环境却充当了反对者的角色,甚至连原先的好友黎涯和郑鹏也因为误解而无意中站到了她的对立面。至于最后为陆萍指点迷津的那位匿名的伤残英雄,他本质上是“医院”“合理化”秩序的代言人,陆萍在他的训导下终于决定由对秩序的反抗转化到皈依的立场上来,以此缓解自己内心由于与环境的对立而导致的焦虑。因此他与陆萍的关系是双重性的,表面上他是陆萍的拯救者,实际上却是陆萍的“灵魂的驯化师”。他与陆萍在医院中的角色也发生了置换,陆萍由医生变成了“病人”,他却由病人变成了“医生”。这其实暗示了知识分子在延安红色话语秩序中的命运,本想“疗救”民众的启蒙知识分子最终却沦为了被工农兵“疗救”的对象。陆萍就是启蒙知识分子的化身,在她的身上投射和凝结着丁玲当年内在的心理焦虑,以及其所由生的作者与延安红色话语秩序的隔膜,这在作者同期的散文《风雨中忆萧红》里有着明确的表达。此时作者的小说话语实践显然已经变成了释放自身心理焦虑的艺术场所。也许正是考虑到了这种显性投射方式的风险性,即意识到了自身这种“前意识”的心理焦虑外化不会见容于当时延安红色话语秩序及其文艺话语规范,丁玲写于1940年的这篇小说并未及时发表,直至1941年才公开面世,随后便遭受批评,作者的忧虑终于变成现实。
相对而言,“霞村”就不会像“医院”那样容易被接受者视为对当时延安社会秩序的隐喻,农女贞贞也不可能被轻易地说成像知识女性陆萍一样是各自所属的社会阶级的代表,然而这一切并不能否认贞贞及其所属的霞村仍然是创作主体在深层心理上的外向投射物,只不过意味着,此时作者的心理或话语防御策略运用得更加隐蔽和娴熟,即更加“无意识”罢了。尽管在文本的显在形态上《霞村》与《医院》各具风采,然而它们的文本潜结构却具有同一性,均指向主体与其置身的环境之间的对立,及由此所生的深重心理焦虑,当然焦虑的内涵有所不同。贞贞在霞村中无疑是孤立的,她的亲人非但不同情她的遭遇,反倒视其为家族的耻辱;邻人就更不必说,对她不是公开或背地里加以嘲弄和谩骂,就是冷漠地把她的痛苦经历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连情人夏大宝也不能真正理解她,他的同情举动在贞贞看来不过是对自己良心的赎罪。“我”虽然自始至终都是贞贞的精神知己,但作为叙述人,“我”和主人公实质上是作者丁玲灵魂中的两种不同的声音,区别在于,“我”代表作者的理性人格发言,而贞贞却暗中传递着作者潜意识的消息。由此可见,“我”和主人公原本是作者心理人格有机构成的一体两面。总之,贞贞和“我”遭受到了“霞村”所象征的现实社会秩序的深重压抑,由此导致的“现实焦虑”与陆萍在“医院”中的焦虑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然而贞贞不仅有“现实焦虑”,更有其独特的“道德焦虑”。(11)贞贞在日寇的魔掌中无辜受辱(先被动,后主动),但她崇高的牺牲并未得到霞村人的认同,反被诬为人格的堕落,由此酿成了她无法排解的道德焦虑,甚至“道德恐惧症”。联系丁玲当年在南京“魍魉世界”里的遭遇,人们不难体味到在贞贞的身上其实移置和凝缩着作者潜意识中所纠结的巨大心理创伤。当年的国统区自是不必说,即令是在后来的解放区丁玲也同样因为自己的囚居生涯而没少遭到他人的误解甚至攻击,她内心深处的道德焦虑乃至恐惧是不难想见的。
在延安时期的小说创作中,丁玲深层心理中的道德焦虑始终在寻找释解的渠道。还是在初到延安后红色激情飞扬的时期,丁玲便写了《东村事件》(1937),从中也可见到道德焦虑的踪迹。女主人公七七被婆家作为人质推进地主老财的魔爪,她得到的不是同情而是打骂。与七七命运相近的还有独幕剧《重逢》(1938)中的抗日女战士白兰,她在狱中坚持韧性战斗并承受了痛苦的心理冲突。无论是白兰、七七,还是贞贞、陆萍,在她们身上都投射有作者灵魂中的道德焦虑或现实焦虑,通过在文本叙述中运用自我投射的心理防御方式塑造她们,创作主体在不同程度上完成了对延安红色话语秩序及其文艺话语规范的超越。
三
丁玲当年所置身的红色文学话语秩序实际上是一套以理性主义为思维取向的话语规范体系。它在很大程度上尊奉理性(理性有别于理性精神),排斥并贬抑非理性话语(非理性不同于非理性主义),乃至最终将其放逐于“唯理型”的主流话语规范体系之外。这再恰当不过地体现了福柯1968年在法国的红色“五月风暴”前夕所作的历史诊断:“在我们自己思想的时代中,我们最为害怕的是设想他者”。(12)福柯毕生醉心于对“他者”的再发现,即对被历史文化规范所掩盖的非常态话语(包括疯癫、疾病、犯罪、性等)进行深入发掘,他由此把自己的工作命名为“沉默的考古学”。(13)其实,早年的丁玲便是一位在文学界里大胆探测人类心灵深处“沉默的他者”的“考古学家”。她最初的作品集中塑造了一系列反常规的边缘性人物形象,包括不同形态的神经症患者、自杀者、妓女,甚至同性恋者(《暑假中》),藉此冲破中国传统道德文化规范的藩篱。但随着丁玲后来接受了“左翼”革命文学规范,她关注的对象也由“他者”逐步转向了工农大众。及至走进延安红色文学话语秩序中,经过一段时间的自我调适和摸索,丁玲开始“探究”工农大众及革命知识分子的隐秘“灵魂”,“送出使人心惊肉跳的塑像来”。(14)这意味着丁玲重新有意无意地运用一种体验“他者”的话语策略来防御当时已日趋成型的红色文艺生产范型对自身个人化艺术激情的压抑。
初到陕北时的丁玲似乎偏爱以“儿童”视角来结构作品。《一颗未出膛的枪弹》是丁玲来延安后的第一篇小说,它通过塑造一个掉队了的“红小鬼”别具一格地叙述了党在当时所宣扬的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宏大时代主题。《压碎的心》和《县长家庭》也与此相类,寓宏大的革命主题于细微的儿童心理体验之中,举重若轻、别有风味。以即将和正在走进社会化工程的主体——儿童来透视现实,这其实是丁玲寻求“他者”,以期发出个人化声音,从而抵御红色文学话语规范制约的开始。然而,作为丁玲延安时期小说创作中的一种话语或心理防御方式,体验“他者”更重要的还是指作者注重考掘小说主人公的“疯癫”人格。福柯指出:“疯癫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癫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癫的历史。”(15)这意味着人类用“另一种形式的疯癫”,即“至高无上的理性”禁闭了自己的非理性话语,并用“一种非疯癫的冷酷语言”摧毁了理性与非理性对话的基础,从而完成了“理性对非理性的征服”。(16)在当年延安透明而冷静的红色文学话语秩序中,非理性的疯癫体验在红色真理话语的压抑下只能保持沉默,只是在丁玲的小说话语实践中有过惊艳的现形。《泪眼模糊中的信念》中平素寡言少语的陈老太婆,在逃离日寇的魔窟后竟然变成了一个像祥林嫂一样成天絮絮叨叨的“疯子”,一度招来村民的侧目并给亲人带来难堪。她疯疯癫癫地主动向众村民“残酷”地讲述自己和孙女以及其他姐妹“受辱”的情形,毫不顾惜自己的颜面和痛苦,更不管众人的态度和反应。究其变“疯”的根本症结,无疑是源于她内心深处无法平复的巨大创伤,正是这种心理创伤驱使她猛然丧失了“理性”,即冲破了传统道德规范的枷锁,沦为了一个非理性的“疯子”。然而她的非理性话语实际上传达了她真实的心理体验,这是穿越生命的暗夜而来的灵魂的声音,它是如此的异乎寻常,以至于被真理话语强加了“疯癫”的罪名。但身处红色文学话语秩序的丁玲显然不能无视自己宣传抗战的宏大使命,她必须高扬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淡化女主人公的生命悲剧色彩,即让陈老太婆由被“误解”的“疯子”变成被“理解”的英雄母亲。正是出于同样的红色激情,丁玲不久将该小说易名为《新的信念》。与陈老太婆相比,《霞村》中的贞贞虽有着相似的屈辱史,但生命的悲剧意味却更为浓郁。贞贞并未通过话语宣泄的途径来排解自己内心的块垒,她竭力强颜欢笑,将精神郁闷埋藏心底。这种不合常理的“乐观”让“我”大感意外,更令霞村人不能接受,他们误以为贞贞已丧尽“廉耻”,无可救药。终于,贞贞在“理性”的霞村人的威逼下陷入“疯狂”,就“像一个被困的野兽”,又“像一个复仇的女神”。作为被看者,贞贞的沉默和疯狂在作为看者的霞村人眼中无疑属反常行为,倘若将看者/被看者加以置换,则贞贞的“疯癫”不过是“另一种理性”,而霞村人的“理性”却变成了“另一种疯癫”。这样,丁玲不仅于反常中发现了正常,而且在正常中看出了反常。贞贞最终未能与霞村人达成和解,因为他们各自的话语系统之间无法对话,她只能去延安谋求被红色话语秩序接纳。虽然贞贞以后的命运不得而知,但从《医院》里陆萍的遭遇中却足以不作乐观的推测。知识分子陆萍满怀理想主义激情去“改造”医院,却在医院中人的眼中变成了一个“怪人”,属于“被改造”的对象。原自以为像屈原那样既“清”且“醒”的陆萍,在众人眼里却变得又“浊”又“醉”。在医院中各种“无名的压迫”下,陆萍患上“神经衰弱症”,她居然开始“同所有人斗争”,“寻仇似地指摘着一切”,并扬言“要控告他们”。陆萍可看作是延安红色话语秩序中的唐·吉诃德,她的疯癫本质上是一种“浪漫化的疯癫”。福柯指出:“正是由于这种疯癫,另一种时代、另一种艺术、另一种道德的价值会引起质疑,但是,疯癫也反映出人类的各种想像,甚至最漫无边际的遐想。”(17)这表明,陆萍的疯癫的出现意味着在延安红色话语秩序中开始有了“质疑”的声音,同时也暗示了知识分子的人文政治社会理想的乌托邦性质。实际上,陆萍最终经人点拨还是回归了革命理性和红色真理,她突然意识到自己的疯癫不过是知识分子的“幼稚病”而已。然而,这种突如其来的醒悟难道不是“一种刚刚进入她脑际的新疯癫”吗?
作为一种话语防御方式,体验“他者”还表现为作者在小说话语实践中经常穿透人物的理性意识域,而径直抵达人物心灵的沉默地带,即非理性的无意识域中去。与深掘主人公的疯癫人格相比,体验“他者”的这一话语方式被运用得更为普遍。由于较成功地运用了这种话语或心理防御策略,丁玲延安时期的代表性小说文本实际上已构成了具有悖谬性的“双重文本”。也就是说,这些文本一方面尽量满足红色文艺话语规范的要求,另一方面又有意无意地试图摆脱主流话语规范的束缚,总之是既迎合又消解。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文本当推《夜》。《夜》的显文本明确指向革命工作必然战胜私人情感的宏大主题,它完全合乎当时主流的红色文学话语规范。然而《夜》的潜文本却暗中解构了这种宏大叙事,它暗示着主人公何华明已陷入无法摆脱的二难困境之中:作为乡指导员,何华明必须遵守革命行动规则,但作为一个“人”,他又无法拒绝内心深处欲望的诱惑。在二者不可兼得的情形下,何华明无论做出何种选择都会使自己的生命陷入悲剧性的困境。丁玲通过细腻的心理分析将笔触伸到何华明的潜意识中,冷静地把主人公近乎无声的悲剧呈现了出来。首先,何华明与他早衰的妻子之间存在着灵与肉的双重隔膜,他无法隐瞒对妻子的嫌厌甚至憎恶,但又为此稍感不安。其次,何华明虽然明知妇联委员侯桂英对自己心仪已久,但为顾及“影响”,他只能竭力压抑自己的本能冲动。最后,对妻子和情人深感绝望的何华明只能到一个与自己毫无利害冲突的女性身上去寻求想象态的补偿。于是我们发现他无意中被“发育得很好”的清子所吸引,尽管此时作为党的干部的他必须在口头上大骂清子及其地主父亲的落后。尤值称道的是,丁玲让男主人公这一系列的心理颤动发生在夜的帷幕之下,从而暗示了自己的艺术旨趣,即通过穿越人物心灵的暗夜去谛听其潜意识中“他者”的声音。当然,这一切必须以小说的显文本大体上符合延安红色文学话语秩序的基本规范为艺术前提。
四
福柯指出:“忏悔是一种话语仪式,在这种仪式中,说话的主体同时又是陈述主体;它同时又是在权力关系之中展开的仪式,因为不当着合作者的面,谁也不会去忏悔。”(18)这其实点明了忏悔话语的本质和功能。首先,作为一种话语仪式,忏悔是权力的产物,它内在地具有权力等级结构。在忏悔仪式中,说话者处于弱势地位,而对话者(主要是作为听者)居于强势位置,后者对前者具有支配性和统治力量。说话者的话语背后隐藏着听者所掌握的深层话语构成规则系统,即权威的“知识型”,因此说话者在很大程度上仅止于一个被动的言说机器。反之,听者是支配者,是它从说者身上“压榨”和“挤出”了忏悔话语,并且拥有对其进行最终裁决和处置的权力。其次,忏悔仪式是一种双重性的话语策略。福柯所说的陈述主体其实是某种“位置”。(19)这意味着在忏悔仪式中,说者和听者,忏悔者和裁判者本质上都是一种功能性的“位置”,前者可以由各种可能的越轨者来置换,后者则可以由各种现实的立法者来替代。当越轨者忏悔自己的犯禁行为时,一方面它作为陈述主体,通过否定自己来迎合立法者,以求后者拯救自己,另一方面,它又作为真正的说话主体,凭借话语的力量再次隐在地宣泄了自己的犯禁冲动,从而通过这种有意无意的心理补偿肯定了自己。
在丁玲延安时期以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小说文本中,我们发现作者在不同程度上运用了忏悔仪式这种双重话语策略来实现对当时的红色文学话语秩序的抵御和超越。相对于红色的工农兵来说,“灰色”的知识分子在延安革命文化秩序中因其对革命的“两面性”显得黯然失色。因此,作为话语主体,丁玲唯有将知识分子处理为否定的对象才能够获取“合法”的言说知识分子的权力,这就先在地决定了这类文本中必然内在地具有某种意识形态上不平等的权力结构。《秋收的一天》透视了两个女性知识分子在延安马列学院劳动“改造”中的心理嬗变。身体偏弱的薇底“执拗地决定参加重劳动”,以此彻底洗刷自己身上的“娇气”,而“患着厉害的神经衰弱”的刘素在学员们高涨的劳动热情中也不甘或不敢怠慢。终于,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薇底变得更加“单纯、愉快、坚定”,而刘素也认识到“人是应该明朗的、阴暗是不可爱的”。显然,在文本中明朗和愉快的薇底与阴暗和忧愁的刘素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们可以分别视为作者心理结构中的不同人格,即被延安红色意识形态所同化了的“新我”和即将或正在向其认同的“旧我”。她们之间的对话实际上是“红色”与“灰色”两种不同性质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之间展开的对话。这种对话本质上是不平等的,前者高踞“上位”,后者屈从于“下位”,前者是裁判者和支配者,后者是忏悔者和犯规者。在这种忏悔话语仪式中,作者一方面通过女主人公立场的转变表现了对延安红色话语秩序的认同和皈依,另一方面又通过展示刘素内心的隐痛来曲折地表达了自己的隐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当时红色话语秩序及其文学规范的制约。
尽管和《秋收的一天》内在地具有同样性质的权力结构,但《入伍》中的具体表现形态却并不相同。《入伍》中的两个主人公,“新闻记”徐清和勤务兵杨明才,一个是知识分子的代表,一个是“工农兵”的化身。作者将徐清比喻为唐·吉诃德而把杨明才视为桑丘。这意味着徐清所代表的知识分子在红色话语秩序中是一种简单、幼稚的理想主义者形象,这从徐清在行军途中在危险来临之前对战争所作的浪漫化理解,在危险来临之后又对战争的残酷感到本能的恐惧,以及一路上处处想利用杨明才来保全自己的阴暗心理中得到了确证。而杨明才则无时无处不显示出桑丘那样的实干家风采,他的存在使知识分子徐清相形见绌。这样的“红”“灰”对比使得《入伍》的文本成为了一种意识形态压倒另一种意识形态的“战场”,同时也使得整个文本成了边缘话语对主流话语表示认同和臣服的忏悔话语实践。在这种忏悔话语实践中,作者一方面通过嘲讽徐清来否定知识分子,以此谋求被延安红色话语秩序所接纳或拯救,另一方面,作者又通过描述徐清作为“新闻记”在以工农兵为本位的红色话语秩序中所产生的苦闷和寂寞,譬如他表面上脆弱的自尊和骨子里深沉的自卑,在一定程度上潜在地传达了当时延安知识分子真实的矛盾心态,这无疑是对延安红色话语秩序及其主流文学规范的某种防御和超越。写于《入伍》之后的《在医院中》暗示着丁玲对当时延安红色话语秩序的防御和反抗所能达到的最高限度。从知识分子陆萍的结局来看,《医院》其实在宏观上也具有内在的权力结构。陆萍最终还是接受了“工农兵”话语秩序的“招安”,她对自己过去的“犯规”行为感到愧悔,这实际上意味着整个文本可以被看作是她的一次忏悔话语实践。只不过和前述两个文本相比,忏悔仪式的话语防御功能在《在医院中》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增强,而其对于权力话语规范的迎合功能则被减弱到了最小的限度。
五
在1942年《讲话》发表以后,丁玲迅速遵照毛泽东所确立的红色文艺生产范型进行人格和文学上全面而深入的改造。她认真地“到群众中去落户”,先后写下了一系列以《田保霖》、《袁广发》等为代表的纪实性文学作品,忠诚地实践着文艺的工农兵方向。丁玲迫切地想做一个“投降者”,“缴纳一切武装”,“从那一个阶级投降到这一个阶级来”。(20)实际上丁玲转变的成就也的确有目共睹,她的《田保霖》还因其“新写作作风”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赏。(21)然而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丁玲已彻底地被延安红色话语秩序所同化和驯服,也不意味着丁玲在,《讲话》后的小说话语实践与此前相比有着根本性的“断裂”,实际上我们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部红色经典文本中仍然能发现作者内心深处那种属于知识分子的“灰色”情怀。也许正是作者心灵中这种拂去还来的“灰色”激情的涌动才使得这部长篇在同类题材的作品中别具一格,堪称翘楚。
作为一种话语防御方式,自我投射在这部长篇小说中的运用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一篇题名为《生活、思想与人物》的文学讲话中丁玲曾说:“我收到读者的信,最多的是询问黑妮。”(22)尽管作者迫于思想的压力“把为她想好了的好多场面去掉了”,并未充分地去发展她的性格,但黑妮还是赢得了读者最多的青睐。这意味着普通读者(而不是作为红色文学话语体系的阐释者的权威批评家)在接受丁玲的作品时始终无法拒绝一种“阅读期待”的诱惑,即莎菲女士在他们的接受心理中所积淀的“成见”的召唤。事实上这也情有可原,由于童年经验和早年生活经历的潜在渗透,丁玲最善于塑造那种莎菲式的孤独者、矛盾者和叛逆者形象。然而历史已行进到了红色中国诞生的前夜,置身于红色文学话语秩序日益深入人心的历史语境中,丁玲已经不可能像《讲话》之前那样去着力刻画“改头换面”过的莎菲(如贞贞和陆萍)了,她只能把心中那份别样的激情尽量压抑在心底。丁玲并非不知自己在新时代的艺术使命是去塑造“新人”,但她“还是写进了一个黑妮”。这种执拗的艺术冲动暗示着作者无法彻底拒绝内心深处自我的召唤,当她真正进入艺术创造境界中时,那个发誓做“毛泽东的文艺战士”的丁玲有时也不得不退避三舍。这样我们才有幸见到了黑妮。黑妮是丁玲不由自主地运用自我投射的话语策略来抵御红色文艺生产范型的限制的艺术结晶。在同一次文学讲话中丁玲还说:“一个人他有了一种思想作主导,他就容易发现在别人身上的这种品质,因为他喜欢的就是这种品质。”(23)如果结合作者创造黑妮的实际情形,这里其实点明了丁玲创作中自我投射的心理运作机制,即由最初对客体的双向“同情”,再到外向“移情”,最终则完成对客体的内向“自居”。据丁玲说,她是在一个偶然的机遇里,从一个刚出地主家门的漂亮女孩向她蓦然回首的一刹那间捕捉到黑妮这个人物的。那女孩复杂的眼神唤起了她内心深处的共鸣,“马上我的情感就赋予了这个人物”,然后情不自禁地与她同喜同悲。黑妮人格上的孤独,情感上的忧郁,行为上的叛逆等无不是丁玲被迫埋藏在深层心理中的“灰色”激情的外向投射物。可惜作者无法根本上超越自己时代的话语规范的制约,她只能“忍痛割爱”,将黑妮的也是她自己灵魂的寂寞与苦闷驱逐回潜意识域中去。今天看来,这不能不说是这部长篇小说在艺术上人为的一大损失。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当时的主流文学话语规范是如何控制、净化或销蚀了艺术家固有的审美激情的。
根据前面的分析,丁玲在《讲话》前所运用的体验“他者”的话语防御策略大致上有三种形式:寻找“另类”视角;考掘“疯癫”人格;深入无意识域。然而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部长篇小说中我们却再也见不到作者那深挖人物性格中“疯癫”因子的话语冲动,倒是另外两种形式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保留,甚至有了某种程度的发展。黑妮其实就是作者运用“另类”视角而造就的“另类”人物,此处不再赘述。这部长篇中真正体现了作者刻意寻找“另类”视角的努力的典型人物是顾涌。顾涌是个被错划为富农的富裕中农,在他身上凝聚着丁玲无法按捺的同情,同时也体现出丁玲竭力突破当时红色文学话语秩序的拘囿的艺术勇气。还是在那次以《生活、思想与人物》为题的文学讲话中丁玲指出过这样的事实:当她开始塑造顾涌形象时,中共中央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尚未出台,当时在农村土改斗争中划分阶级成分时“根本没什么富裕中农这一说”;而且写作中途她便在会上听到不点名的批评,说她有“地富思想”。这说明对顾涌的形象塑造不仅表现出了丁玲思想和艺术上的独到眼光,而且还意味着丁玲的这种“另类”话语实践需要她承担极大的政治风险。丁玲日后的蒙难实际上正说明了这种政治代价的沉重。丁玲确实是一个恪守艺术良知的人,她不仅写了尚未获得“合法化”身份的“富裕中农”,而且让“富裕中农”顾涌成了整部长篇小说中第一个进入读者视野的人物,甚至是以他为线索展开了一系列重要的故事情节,使其成为了小说中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顾涌的形象来源于丁玲所参加的土改斗争实践的经验。当丁玲被生活中一位勤劳节俭一生的“富裕中农”的尴尬命运所深深打动时,她便再也抑制不住心中为“另类”请命的艺术冲动与政治热情,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当时革命文学话语规范的控制。《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地主群像因其各具性格向来为人所称道。据丁玲在上面提到的那次讲话中说,她在钱文贵身上也颇费“考虑”。其实丁玲之所以选择“摇鹅毛扇的”钱文贵而不是选择“恶霸地主”陈武那样的人作重点刻画,同样体现了她在思想和艺术上的独具慧眼,钱文贵实际上是作者谋求突破当时塑造反面人物时普遍遵循的“脸谱化”和“概念化”模式的产物。至于体验“他者”的第三种表现形态:深入无意识域,虽然丁玲也曾试图在这部长篇小说中依循《讲话》之前的话语策略将笔触深入进人物的“个体无意识”,就像塑造贞贞和何华明那样去刻画黑妮和农会主任程仁,但在1940年代末日渐强大的红色文学话语秩序中这已显得太不合时宜,因而作者的艺术尝试并不是很深入(不愿或不便),阅读中我们不难体会到作者在竭力透视黑妮和程仁的深层心理时的那份欲说还休的谨慎与困窘。倒是在侯忠全这种老式农民的身上作者得以将笔触深入到人物的“集体无意识”之中。侯忠全是那种不仅“奴在身”更是“奴在心”的人,用胡风的话说就是染有“精神奴役的创伤”,这其实是中国漫长而强大的专制主义政治文化在国民灵魂中所造就的集体心理积淀。因而对于侯忠全而言,翻身难,“翻心”更难。这在作品中描写的两个典型细节,即他在地主侯殿魁被斗争后仍然去为其扫地和陪跪中有着深刻的反映。也正是在这里,丁玲悄然接续上了“五四”文学的启蒙精神,从而在红色文学话语秩序中拨响了不谐之音,以至于后来被诬为“丑化农民形象”。
文采无疑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最抢眼的知识分子形象。据作者在该书的俄译本前言中说,她塑造文采的真实动机是为了表明:像文采那样“尚未克服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知识分子”如果在实际斗争中接受改造,是可以转变为“真正的战士”的。(24)作品中的文采正是走了这样一条知识分子自我改造之路:从起初“文绉绉”的“书呆子作风”,到在群众工作中遭遇挫折,及至最后幡然悔悟,“与个人主义决裂”。不难看出,小说中关于文采的叙事话语内在地具有权力结构,这实际上是知识分子的“灰色”启蒙意识形态向以工农兵为本位的红色意识形态的认同和皈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有关文采的叙事话语整体上视为知识分子在红色政治语境中的忏悔话语实践,同时也可以将作者的这种叙述姿态视为经过“革命洗礼”后的知识分子作家在红色文学话语秩序面前所举行的一种忏悔话语仪式。而忏悔仪式作为一种话语防御策略,它一方面表达了作者通过知识分子的自我否定、自我改造,以求“政治生命”获得新生,即谋求被红色文学话语秩序接纳和认可的理性愿望,另一方面它也满足了作者凭借知识分子自我忏悔的形式而获得“言说”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力的潜在需求,因为在当时泛政治化的历史语境中知识分子话语已被放逐到了边缘。然而,和丁玲在《讲话》前塑造的知识分子形象相比,在文采的忏悔话语中我们发现,作为忏悔策略的双重功能之一的反抗作用已被减弱到最低限度,而迎合功能则被强化到了极致。关于作者创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的心态,丁玲曾有过这样的说明:“那时我总是想着毛主席,想着这本书是为他写的,我不愿辜负他对我的希望和鼓励。”(25)毛泽东显然是这部书最权威的“隐含读者”,他的“期待视野”对文采形象的塑造无疑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延安时代的毛泽东就已十分注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在他有关整风运动的经典著作(26)中我们能读到这方面的大量论述。在毛泽东看来,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对他们尤其应该发动一场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运动”,使其从“三股歪风”的蒙蔽中解放出来。“三股歪风”包括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其中党八股是前两者的集中表现形式。(27)鉴于此,毛泽东专门拟定了申讨党八股的“八大罪状”。(28)有趣的是,如若我们把丁玲笔下的党内知识分子文采的“行状”跟毛泽东所谓的“八大罪状”逐一比照,二者之间竟是那么样地吻合。简直可以说文采就是毛泽东严辞抨击的“党八股”的化身,而且文采以后的转变也完全符合毛泽东“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改造方针。这意味着,丁玲在塑造知识分子文采形象时基本上是按照权威红色理论经典“图解”而成的(尽管有些细节很生动),在这种“化概念”和“化公式”的过程中,忏悔策略的话语防御和超越功能几乎被窒息,潜在的反抗的声音异常微弱。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一本给丁玲既带来荣誉又带来苦难的书。在很大程度上,上述三种类型的话语防御方式或心理防御策略在这部长篇小说的褒贬毁誉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事实上,倘若从整体上观照丁玲延安解放区时期的小说话语实践,情形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怎奈斯人去远,沧桑无言,唯有那依稀的“叮咛”声还在历史的深处回荡……
注释:
①丁玲:《丁玲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67页。
②丁玲:《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文艺理论研究》1980年第3期。
③知识型是福柯在《词与物》中提出的著名概念,但这位“千面”思想家并未对其下过明确统一的定义。路易丝·麦克尼认为“福柯将知识型定义为一套在任何既定时刻决定能够思想什么和不能够思想什么、能够说什么和不能够说什么的先验规则”。见麦克尼:《福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1页。本文认为,中国现代启蒙知识型初步成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它是一套以知识分子为本位的,以现代意义上的“人的解放”为价值取向和思维中心的深层话语构成规则系统。而中国红色革命知识型酝酿于1920年代至1930年代,直至1940年代在延安解放区才基本成型。它是一套以“二农兵”为本位的,以马列主义的“阶级解放”为价值取向和思维中心的深层话语构成规则系统。
④丁玲:《我的创作生活》,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0页。
⑤何丹仁(冯雪峰):《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第251页。
⑥丁玲:《〈意外集〉自序》,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第113页。
⑦丁玲:《丁玲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16—217页。
⑧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1—256页。
⑨冯雪峰:《从〈梦珂〉到〈夜〉》,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第295页。
⑩荣格:《分析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50页。
(11)卡尔文·斯·霍尔:《弗洛伊德心理学与西方文学》,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60—68页。
(12)路易丝·麦克尼:《福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页。
(13)福柯:《前言》,《疯癫与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3页。
(14)冯雪峰:《从〈梦珂〉到〈夜〉》,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第299、298页。
(15)参见福柯的《疯癫与文明》的封底文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16)福柯:《前言》,《疯癫与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页。
(17)福柯:《疯癫与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5页。
(18)福柯:《性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3页。
(19)福柯:《知识考古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19页。
(20)丁玲:《关于立场问题我见》,《生活·创作·修养》,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页。
(21)毛泽东:《致丁玲、欧阳山》,《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5页。
(22)丁玲:《生活、思想与人物》,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第157页。
(23)丁玲:《生活、思想与人物》,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第156页。
(24)丁玲:《作者的话》,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第121页。
(25)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重印前言》,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第165页。
(26)毛泽东关于整风运动的经典文献包括《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整顿党的作风》(1942)、《反对党八股》(1942)、《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等。
(27)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73、785页。
(28)毛泽东给党八股定的“八大罪状”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象个瘪三;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流毒全党,妨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90—797页)前六条概括了党八股的表现形态,后两条指明了党八股的实际危害。毛泽东对前六条重点评析,后两条则一笔带过。对于文采同志而言,除第六条安在他头上有些言重之外,其余则无不贴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