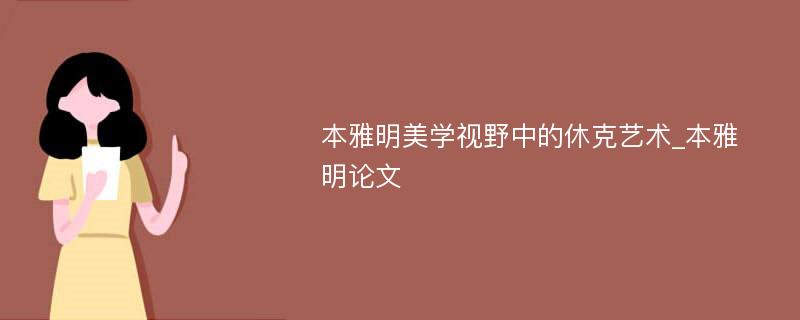
本雅明美学视野下的“震惊”艺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视野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和“灵韵”一样,“震惊”也是本雅明美学思想中的重要元素之一。而如果说在其理论中,“灵韵”是传统艺术审美特征的总体规定的话,那么,机械复制时代艺术的总体美学特征便是“震惊”。在他看来,现实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在猝不及防的现代人面前改变,人们传统的感知方式陷入了瘫痪,往昔的“经验”萎缩甚至失效,“震惊”已成为机械复制时代人之生存状况的普遍反映。
一、“经验”与“体验”
本雅明认为在以手工技术为主的前工业社会,人们的活动主要是依据传统的“经验”来进行的。“经验”,在他看来,“是一种传统的东西,在集体存在和私人生活中都是这样。与其说它是牢固地扎根于记忆的事实的产物,不如说它是记忆中积累的经常是潜意识的材料的汇聚。”[1]p126 可见,“经验”是随着时间流逝人们对知识的积累和总结,是积淀在人们心理结构中的文化传统和智慧结晶。人们正是借助于“经验”来理解和同化现实的世界,应对各种遭际。
但当进入了以机械复制技术为主的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经验世界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它开始贬值,而且一贬再贬,朝向一个无底洞贬下去,最终有可能变得一文不值。人们不可分割的、最放心的财产——经验交流的能力被剥夺了。尤其是一战结束后,“从战场上归来的人们变得少言寡语了——可言说的经验不是变得丰富了,而是变得贫乏了……因为从来没有任何经验遇到过如此根本性的挑战:战略经验遇到战术性战争的挑战;经济经验遇到通货膨胀的挑战;血肉之躯的经验遇到机械化战争的挑战;道德经验遇到当权者的挑战。”[2]p292 经验的失效使得人们之间进行精神、情感甚至言语交流的可能性降低到了最低点,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程度也达到了顶点。技术的发达、外部空间的拓展和物质利益的驱使,使得人们把现实利益的满足视为生存的目标,而忽视了很多人性化的东西,人类社会空前地受到了信任危机、精神危机等现代病的挑战和威胁。
与之相适应,本雅明认为随着“经验”在现代社会的萎缩乃至消亡,作为传递“经验”的传统的讲故事艺术走向终结也就在所难免。在传统的手工业社会,技术不发达,人员地域上的流动和信息的时空传递相对较少,所以“经验”的交流便显得尤为重要,以讲述经验为主的讲故事艺术便应运而生,并且逐步占据了传统社会文学的主流地位。在此,故事成为了“经验”的承载与传递性存在。
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叙事能力逐渐被逐出日常言语的王国”,[2]p294 讲故事艺术便渐趋消亡了。因为工业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交通、通讯手段都变得极为便利快捷,以往借助于讲故事者才能获得的“经验”,可以通过亲身经历去获取。而且生活节奏的加快,使得人们的生活愈益紧张,每天奔波忙碌,再也难以进入听故事的松弛状态之中。于是,适应工业技术社会特点、能够反映人们在技术文明时代生存境遇的小说顺势兴起了,它借助于现代印刷技术得以大批量的印制和传播并逐步取代了故事的主流地位。另外,一种新的交流形式——新闻报道也应运而生。人们能够借助于新闻记者得到准确、及时、快捷的当下信息。“新闻报道和小说一样,都是讲故事艺术面对的陌生力量,但它更具威胁。”[2]p296
当人们用“经验”的方式越来越无法同化周围世界的材料时,便催生了“体验”这种新型的把握世界的方式。在本雅明看来,在工业文明时代,“经验”的萎缩意味着现代人与传统意识的断裂,意味着个体(经验主体)在面对异己的社会现实时产生的尴尬与困惑。“体验”则是“经验”连续性断裂的标志,它呈现了个体被摘除了情感、想象、意志后的分裂、片面的生活状况,其产生是现代人面对日新月异的变化和各种无法预知的挑战时,借助于世代相传而积累下来的传统经验却无能为力,感到束手无策的心理状态下所作出的迫不得已的选择,也就是说,它的产生与现代人的普遍心理体验——“震惊”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
二、“震惊”
本雅明借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对“震惊”本质作了心理层面上的解析。在弗洛伊德看来,意识抑制兴奋的功能使其成为生命组织的保护层,“该保护层由它本身的能量储备装备起来,它力求维护一种能量转换的特殊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它的能量抵制着外部世界多度的能量的影响。”[1]p131 这些能量本身对人的生命即构成了某种威胁,“意识越快地将这种能量登记注册,它们造成伤害的后果越小。”[1]p131 但是如果这种能量突破了意识防护层就会进入无意识领域,而假如人对此毫无思想准备就会陷入“震惊”。由此本雅明找到了与弗洛伊德理论的契合点,“经验”多停留于人的无意识领域,当外部的能量刺激突然闯入无意识领域,以至于人的内在“经验”对这一不速之客感到如此陌生,便会陷入束手无措的尴尬与惊讶之中,于是“震惊”体验就产生了。所以简言之,“震惊”就是人在陷入外界事物或能量的刺激时,毫无思想准备的心理反应。
本雅明运用“震惊”理论成功地分析了具有强烈“体验”色彩的现代都市生活场景。现代人处于“大规模工业化的不适合人居住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时代”,[1]p127 都市大众传统的经验结构已发生改变,人们以往真实的经验已经被都市文明大众的标准化、非自然化了的生活体验所取代,因而人们普遍具有“害怕、厌恶和恐怖”的感觉,具体体现在:首先,醉心于安逸的人们被进一步的机械化了。钟表、电话等科技产品的发明使人们的手突然一动就能引起一系列的运动。“如今,用手指触一下快门就使人能够不受时间限制地把一个事件固定下来。照相机赋予瞬间一种追忆的震惊。”[1]p146 其次,报纸的新闻报道或大城市交通同样给人此种感觉。新闻报道诉诸感官而与“传统”无关,其意图不是帮助读者把它提供的信息吸纳为读者自身经验的组成部分,而是“把发生的事情从能够影响读者经验的范围里分离出来并孤立起来”。[1]p128—129 其潜在的功能是使人们了解当下、遗忘过去,其源源不断的新闻,如日历一样不断地刷新着过去。于是面对铺天盖地的新闻信息,传统经验日益萎缩,人们陷入“震惊”之中。而都市行人一方面步履匆匆,彼此互不相干,“只有一点上建立了默契,就是行人必须在人行道上靠右边行走”;[1]p137 另一方面,在来往的车辆行人中穿行,个体被卷进了一系列的惊恐与碰撞之中,“在危险的穿越中,神经紧张的刺激急速地接二连三地通过体内,就像电池里的能量。”[1]p146 最后,“过往者在大众中的震惊经验与工人在机器旁的经验是一致的”。[1]p148 正如马克思所言:任何一种资本主义生产,不是工人使用劳动工具而是劳动工具使用工人。本雅明认为,在技术文明时代,工人们已被机器异化为物的工具,人丧失了主体性。为了使自己适应机器而不被机器贬黜,工人们必须接受各种机械主义训练,从而被日趋“机械化”,这种境况下的工人只能机械地表现自己,已丧失了自己的经验与记忆,“他们的行为是一种对震惊的反射”。[1]p148 而且,“工人在机器旁的震颤的动作很像赌博中投掷骰子的动作……工人在机器旁的每一个动作都像是从前一个动作照搬下来的,就像赌博中投掷骰子的动作与先前的总是一模一样,因而劳动的单调足以和赌博的单调相提并论。”[1]p149 由此可以看出,本雅明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的一脉相承性,这也是人们把其归为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根本原因所在。
总之,对本雅明来说,“震惊”是社会发生转型后,现代人对社会现实的感受特点,是现代人的特有心态。对于“震惊”体验所产生的深刻后果,本雅明引用瓦雷里的话说,“住在大城市中心的居民已经退回到野蛮状态中去了——就是说,他们都是孤零零的。那种由于生存需要而保存着的赖依他人的感觉逐渐被社会机器主义磨平了。”[1]p146 频繁的刺激感受让人们对非人化的“震惊”体验见怪不怪,人们变得麻木了、“机器化”了。“震惊”之后的麻木适应正是一种人的异化,在异化中达到与现实认同,从而可悲地将资本主义历史自然化、永恒化了。于是,本雅明把对“震惊”体验的抵制与克服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寄希望于现代“震惊”艺术。当艺术把“震惊”作为自己的内容时,就产生了新兴的艺术观念和艺术形态。
三、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震惊”艺术
本雅明认为,现代社会的转型导致了艺术发展的裂变,在工业社会中走向边缘的以叙述为主的古典艺术是以一目了然、意义确定和传递“经验”为主导特征的;而现代艺术则丧失了这些特征,走向了费解,以表达现代人的“震惊”体验为主导特征。换言之,现代艺术大多把“震惊”体验放在自己的中心,将震惊转化为一种美学形式,目的是给现代心灵建立起一种保护。因为,消化震惊是一个比获得震惊更为重要的任务。面对外界不断增加的能量刺激,消化震惊的途径只能是以毒攻毒,即借助于艺术形式提前激起的“震惊”体验,让读者和观众提前感受和体验,从而起到某种缓冲作用,然后再抵御现实的震惊。在本雅明看来,电影无疑是现代“震惊”艺术的典范。
依本雅明看来,“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一种对刺激的新的急迫需要发现了电影。在一部电影里,震惊作为感知的形式已被确立为一种正式的原则。”[1]p146 电影作为机械复制时代的新型艺术形式,它体现了艺术与科学相互结合的典范,它带来了我们艺术接受中的感知方式的革命:通过上升或下降,通过对画面的分割和处理,通过对事物的放大和缩小,通过对过程的压缩和延长等一系列技术手段,摄像机能把肉眼不易觉察的真实世界加以凸现;它能够把我们对外物的感知中习焉未察、但潜伏着的东西剥离出来,使我们对之进行分析;它能够引导我们对我们生存于中的“乏味环境”加以探索,磨砺我们在现实世界中已经钝化的感觉器官,重新认识我们已经熟视无睹的生存环境,从而深化我们对现实及其自身的认识。电影所展示的画面拓展了我们的视觉空间,而且这视觉空间是以一种异样的方式更为鲜明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这样的展示使我们了解到自己的“视觉无意识”,就像通过精神分析了解到“本能无意识”一样。
首先,电影“通过最强烈的机械手段,实现了现实中非机械的方面”,[3]p114 而现实中非异化的、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的活动和变化等非机械性方面正是现代人有权要求现代艺术展示的方面。这就是电影所独具的以“机械”手段创造“非机械”世界的价值。摄影师利用蒙太奇手法将现实中的形象分裂、剪辑和重组,然后按照某种艺术逻辑将其组合成新的形象过程,从而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异样的世界。换言之,电影粉碎了人们对现实世界的习惯感知和日常感知的完整性,它通过一幅幅画面的蒙太奇组合,超越了绘画和戏剧的局限性,把人们的视觉经验重新组织成一个整体,其中所呈现的每一个画面只有在这一整体中才获得其应有的意义。借助电影人们可以发现社会被遮蔽的本来面目,了解到其真实的生活境况和其被“物化”的悲剧事实,从而引发了观众强烈的“震惊”体验和心理焦虑,激发其积极改变现实的革命意识。
其次,电影具有协调人与机器之间平衡的社会功能。电影可以通过一系列的荒诞的情节和演员滑稽幽默的表演,让观众在开怀大笑中,缓解技术化及其后果带给大众的巨大的精神压力,提供某种宣泄性治疗,从而获得心灵的净化与升华,维持人在机械面前的人性。惟其如此,他对卓别林电影赞赏有加。总之,电影艺术以其对资本主义异化现实揭示的全面性和纵深性,逐步在现代艺术王国中崛起,成为体现现代人心灵和克服“震惊”体验的艺术新宠。
四、“震惊”艺术的政治功能
尽管本雅明一直对传统“灵韵”艺术恋恋不舍,但考虑到当时欧洲的政治时局,他不得不走向激进,他选择了代表了艺术发展的走向,适应进步艺术生产力发展的“震惊”艺术,此种选择“标志着本雅明由占支配地位的审美维度向历史的和政治的维度迈进”。[4] 在他看来,在技术占主导的现代社会,人们传统的感知方式陷入了瘫痪,“震惊”成了现代人普遍的心理体验。而以“震惊之美”为特征的现代艺术,作为一种解放的艺术和抵御“震惊”的途径,潜藏着激活大众革命思维、积极改变现实的政治契机。
1.艺术政治化。本雅明一生饱受战争摧残,一直处于颠沛流离的状态之中。在其短暂的生命后期,正是法西斯主义横行欧洲之时。独特的时代环境使他直接面对的是法西斯主义所宣扬的“政治审美化”。在本雅明看来,传统“灵韵”艺术的叙事整合能力,它的唯一性和神秘性同权威和膜拜价值相联系,极易成为法西斯主义的温床。因为法西斯主义无非是一种基于巫术礼仪和宗教崇拜的恶性膨胀势力。显然在当时一味地发展传统“灵韵”艺术势必成为纳粹法西斯的帮凶。本雅明敏感地意识到,“诸如创造力和天才、永恒价值和神秘性等一些传统概念——对这些概念的不加控制地运用,就会导致用法西斯主义意识处理事实材料。”[3]p80 所以,本雅明对“灵韵”艺术表现出一种否定的态度,而热情赞扬机械复制时代的到来,同时积极支持共产主义用“艺术政治化”来对抗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审美化”。
所谓“艺术政治化”即是以政治化革命之名来放逐艺术和美,艺术除了其审美性以外还应反映一定的政治倾向性,把艺术改造成教育人们、改造大众的强大思想武器,其是以牺牲艺术的主体性和自律性为代价的。具体到当下,就是积极肯定摄影、电影等以机械复制为特征的“震惊”艺术。因为机械复制技术以众多的复制品取代了独一无二的原作,瓦解了艺术的神秘色彩和神圣意识,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机械复制艺术打破了法西斯以集权政治和专制国家来谋取艺术曾经拥有的独立地位和膜拜价值的迷梦。加之复制艺术的跨时空的无限可传播性,可以便利地让全世界人民知晓法西斯的罪行,从而成为了抗击法西斯的有力武器。
2.艺术民主化。本雅明认为,前机械复制时代的“灵韵”艺术由于其独一无二的原真性,必然使其高高在上而被人敬畏,很容易成为少数精英和权贵的“家私”,从而剥夺了人民大众参与艺术活动的权利,也进一步增加了其神圣性,这便为“拜物教”提供了可乘之机。
而在破除艺术拜物教上,使“家私”艺术转化为共享艺术,复制技术可谓功不可没。因为机械复制技术彻底改变了艺术和大众的关系,增加了艺术品的现实活力,使得大众可以不受时空限制地自由欣赏艺术,从而打破了贵族们对艺术的垄断。它不仅便利了大众对艺术的接受,而且为其提供了参与艺术创造的机会,增强了艺术创造过程中作家与读者的互动性,使得读者和观众成为作家进行艺术创作的合作伙伴。本雅明发觉新闻报纸上的“读者专栏”即为人们提供了发表看法、展示自我艺术才华的平台;电影则满足了“每个现代人都被拍成电影,成为电影角色的要求。”[3]p109 借助摄影机人人都可以捕捉艺术瞬间,铸造永恒之美。所以说机械复制时代的“震惊”艺术具有巨大的革命潜能,使得人们大众不仅能成为了艺术表现的主体,而且成为艺术生产的主体,实现了艺术的民主化,激发了大众的主体意识,使其能够积极改造现实,推动革命的进程,实现自我的救赎。
不可否认,本雅明所谓的“震惊”艺术具有激发大众革命思维、积极改造现实,从而实现审美救赎、自我解放的政治潜能的观点,是其针对法西斯所鼓吹的“政治审美化”所作出的坚决回击,体现了其变革社会现实、克服人类异化的积极努力和人道情怀。但技术不能决定艺术,艺术也不能实现社会的变革,和其他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一样,其艺术思想带有明显的虚幻色彩。本雅明企图以“技术革命”、“艺术革命”去发挥只有社会政治革命才能担负的变革功能,实现社会的变迁,无异于空中楼阁。因此其“艺术政治学”只能是一厢情愿的乌托邦美学。
[收稿日期]2007—10—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