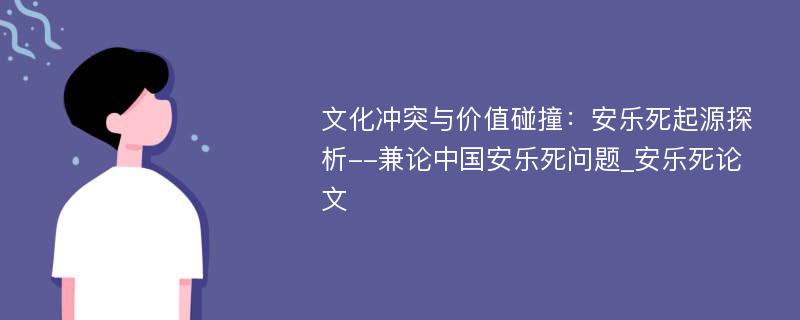
文化冲突与价值碰撞:安乐死问题根源探究——兼及反思国内安乐死问题之讨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安乐死论文,根源论文,冲突论文,价值论文,国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回日期:2010-02-28
中图分类号:R-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772(2010)04-0020-03
2008年4月~8月间,笔者在有百年历史的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医学院医学人文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时有幸聆听了名为“影视中的生命伦理学”(Bioethics in the Film)课程,在该课程设置的内容中生命中止问题(End-of-Life Issues,主要围绕安乐死问题)占全部课程的1/3课时,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该问题在西方医学教育中的地位,也为此引发了笔者对安乐死问题及中国的安乐死问题讨论的思考。国内关于安乐死的讨论始于20世纪80年代,已热热闹闹地进行了30多年。但仔细检视社会公众对安乐死的认知状况,却不容乐观。近年来,不断有医学界人士在人代会上提出“安乐死立法”提案;在医学伦理学、卫生法学教学过程中涉及安乐死问题时,医学生的观点也难有分歧,认为安乐死就是一个立法问题,一旦合法化,安乐死就不是问题了。从医学生对安乐死问题的理解甚至不少医学专业人士关于安乐死的言论使人们不能不反思:为什么在中国支持安乐死的理由主要地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而不是其它?安乐死问题在中国从无到有不过30多年,人们就已将安乐死立法问题上升到安乐死问题讨论的关键?学术界关于安乐死问题的讨论是不够彻底或深入,还是关于安乐死问题的恰当理解没有普及而使得国人对安乐死的误读与谬见不断?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在进一步分析国外涉及安乐死问题的案例及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并对比国内安乐死问题的讨论重点,似乎不难发现中西方对安乐死问题的关注不是在同样意义与层面展开的:安乐死问题在西方备受关注在于其文化与价值内部以及相互之间的冲突或碰撞,而在中国,安乐死似乎只是个法律或卫生经济学问题。
1 安乐死作为问题及其论争
安乐死(Euthanasia)一词源出于古希腊语,据记载是指称在古希腊、古罗马有允许病人或残废人“自由辞世”的所谓“好死”之道,而后淹没在基督教文化日渐盛行的中世纪,至17世纪前后方有法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在其著作中提到让医生采取措施加速病人死亡或任其死亡的说法,而英国哲学家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亦提到乌托邦人对待不治之症病人或临终患者也适用任其死亡的做法。19世纪后期在欧洲特别是英伦三岛及荷兰等国家兴起轰轰烈烈的“安乐死”运动,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科学医学成功地延缓了死亡的悖论性的逻辑后果”。现代医学及生活条件的改善使得人的寿命得以增加,但对一些人来说他们会认为“更长的寿命的礼物很可能是无价值的,如果最终它不得不付出疼痛,无能力或丧失尊严的话。”[1]598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对犹太民族以安乐死名义实施的种族清洗给一度升温的安乐死运动致命一击并使之蒙羞。
20世纪60年代安乐死重新进入公众的视野,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媒体对一些典型案例的报道激发了公众关注的兴趣。自此之后安乐死才真正地成为了一个问题,而在此前的所谓“安乐死”事件都尚未真正构成安乐死问题,其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人们的无奈选择,有些甚至是个别群体借安乐死之名对他者的暴行。成为问题的安乐死论争在于其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影响,其不再仅仅是一个医学问题或私人事件,而是引至社会公众的整体性关注,并影响到制度制定、人们社会生活和价值观念等。安乐死成为具有普遍意义、可能会涉及社会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并因此成为几乎每一个人都应当谨慎地思考的问题。由此荷兰的安乐死合法化、美国的夏沃案件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我国对安乐死的讨论较晚并围绕几个核心事件,历经三次高潮:1986年陕西“汉中安乐死事件”、1990年代初期学术讨论与公众对安乐死态度社会调查、2001年荷兰通过安乐死合法化法案。有些关注是对国外安乐死事件的回应或跟进,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安乐死”对中国人而言是个“拿来主义”的命题。但有意思的是,事实上很多人并不真正明了严格意义上的安乐死、不少中国人依然奉行“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人生信条的背景下,有限的数据调查显示,无论是在农村、城市赞成安乐死的比例甚高。为何源起于西方文化中的安乐死被长期论争而终无共识,而在一个大多数国人仅仅是听过安乐死这个词汇的文化中,人们对安乐死问题的答案却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或认同。
对比中西方选择或意愿安乐死的死亡方式的人群,不难发现真正的安乐死问题是在医学的生命维持技术得以发展后现代人所面对的一种生存困境和文化困境,即文化冲突和价值观念相互碰撞:主要体现在宗教文化、政治文化与医学职业文化中。相比之下,中国缺少同样的文化与价值背景,可见,中国的安乐死讨论与西方文化中的安乐死问题是不同质的,真正的安乐死问题是西方文化的结果。
2 安乐死问题:宗教文化冲突
安乐死问题首先是宗教文化冲突。对多数欧美国家来说,宗教文化(特别以基督教或分支教派为代表)的影响无处不在。即使是有了政教分离、宗教影响日渐式微的近代以来,宗教对人们的社会生活影响依然存在,宗教教义与文化塑成了教徒的价值观念也辐射到整个社会生活,在西方社会中宗教是反对安乐死的中坚力量之一。以基督教为例,虽然《圣经》中没有明确提到赞成或反对安乐死,但基督教教义对自杀和主动放弃生命的态度明确而肯定,任何人选择自觉放弃生命的行为都是一种罪恶。人们也可以在《圣经·约伯记》中找到基督教反对基督徒选择安乐死的例证:约伯受撒旦击打,不仅失去家产财富、众多子女,而且“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他极其痛苦。”难忍的痛苦使约伯吐露心声:“受患难的人为何有光赐给他呢?心中愁苦的人为何有生命赐给他呢?他们切望死,却不得死;求死,胜于求隐藏的珍宝。他们寻见坟墓就快乐,极其欢喜。”[2]830-831但是,约伯却不能选择自主的死,皆因人是神的造物,其生死依赖造物主的命令,“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我问你,……是谁定地上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天下万物都是我的。”[2]874-875基于基督教教义,人是不能选择安乐死的,赞成安乐死对基督徒来说是一种罪,因只有创造人的创造者才有终止人之生命的权能,除此之外任何人不可借着任何理由放弃生命。
但同时对于上述教义可能会有不同的解读而引致完全相反的行为选择。首先,基督教教义为人们选择安乐死奠定了一定的文化与认识基础,即基督教教义中死后进入天堂的观念消除了“自信”的基督徒对死亡的恐惧,而新约中关于基督为救赎众人而死无罪的教义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主动放弃生命为罪的观念。对死亡或死后世界的恐惧一直是人们“谈死色变”的根源,而基督教文化中的天堂观念则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其信徒甚至不局限在信徒范围内,即使某些对天堂半信半疑或宁信其有的人——因生活于基督教文化的氛围中——也有几乎同样的效力,毕竟对大多数的信徒而言,他们对基督教的教义接受和理解可能既是简单的又是极其实用的。其次,现代医学中的生命维持设施对生命的延长也可以看做是对上帝意志的违背。美国“昆兰案”中,少女昆兰因服用大量镇静剂与酒的混合液后而处于持续昏迷状态,当其父亲要求撤掉女儿的生命维持设施遭到医生拒绝时,他在法庭上说:“我不希望她死,我只希望她能恢复到原先自然的状态,让主来引领她。如果主希望她生活在自然的状态下,她就会活过来,如果主希望她死,她就会死。”昆兰父亲的解释与要求同基督教基本教义并无冲突,由此可见,在基督教文化内部基于对教义的不同解读,人们可以得出反对安乐死与赞成安乐死两种不同的意见,正是这两种基于不同解释的宗教立场部分地构建了西方文化中的安乐死问题。
3 安乐死问题:政治文化冲突
安乐死问题在西方世界日渐表现为政治文化冲突。人们对安乐死问题渗透着政治气息的认识是2005年的关国“夏沃事件”:一个女植物人的命运搅动了美国政坛,国会两院紧急开会、布什总统提前结束休假等。“夏沃事件”并不只是政治家偶尔借以做秀的舞台,而是安乐死问题本身就蕴含着政治文化冲突。在西方政治文化中,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不仅是政治生活中的两大派别,也是左右人们社会生活的基本力量:自由主义坚持人的自由至上的理念,而保守派则主张人的生命至上的观念,二者的思想基础即当下政治哲学的两大流派:新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在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拥趸者来看,权利应被置于现代人类社会生活的首要位置,因其是保障我们正常生活的前提。生命权、健康权已经成为被国际社会所共同承认的基本人权,其中生命权自然就应当包括自主支配生命的权利,由此推论,只要是患者自愿地选择的安乐死就不应为法律所禁止;但在社群主义政治哲学来说,责任才是人类生活的根本。康德的责任伦理中明确说明保存生命是人的完全的责任。麦金太尔更认为:“在中世纪临近结束之前的任何古代或中世纪语言中,都没有可以恰当地译作我们说的‘一种权利’(指‘人权’)的表达,……而且试图为相信存在有这种权利而提供充分理由的所有努力都失败了。”[3]社群主义者认为,从责任和人权的角度来说不应当对安乐死选择者轻易说“可以”。而且一些对安乐死选择者及社会公众调查显示,意愿选择安乐死的人并非仅仅因为疼痛而是对生活的绝望,特别是生存尊严的丧失。以社群主义的观念,社会“绝不应仅仅因为患者精神抑郁,厌倦生活,担心成为负担,或担心要依赖他人生活,便允许对其实行医生协助自杀或安乐死。这可能恰恰表明人们尚未竭尽全力。”一个正常的、有希望的社会不应使其公民有选择安乐死的无形压力,自己生存和也使他人生存是一种社会责任。一些人选择安乐死是不想继续欠债于他生活的社会,作为他者的社会应当的责任是尽可能地减少或降低此种负债感。
在新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这两种政治哲学对立非常明显的美国,很多的安乐死案例中都表现出明显的政治文化对立与冲突。在“夏沃事件”中保守派坚持从保护人的生命为出发点,认为这种责任是社会必须要予以保障的。小布什就夏沃事件发表声明时说:“像这样关系重大和容易引起争议的案件,我们的社会、法律和法庭在考虑问题时应该从爱护生命出发。”而自由主义者则坚持人的自由与权利,尤其是人对自己生命的决定权。成中英在《哲学门》第三卷第一期的“论德性本体伦理学与权利后设伦理学之综合”一文中曾说,这种权利首先从“要求不再遭受饥饿和恐惧的权利以及拥有没有烟尘、噪音和其他污染的纯净空气的权利”开始,继而发展到“在新的科学和技术下,……争取安乐死、通过基因治疗恢复青春,甚至以某人为样本造出令人满意的后代”的权利,甚至最终发展到对出生权利的要求,尽管这似乎是一个悖论。对自由主义者来说,是否选择安乐死是每个人的权利——自主决定死亡(死亡方式)的权利,对这种权利的强调有时候会变得让人不可思议,如1973年的“达科斯案例”(Dax's Case):当事人达科斯因父亲经营的加油站爆炸而导致身体2/3烧伤,烧伤所导致的疼痛和残疾使达科斯不断请求医务人员中止对他的抢救和治疗,但每次都遭到拒绝。1974年他联系德克萨斯电视台拍摄“请让我死(Please Let Me Die)”的录像以期社会声援,无果。1986年达科斯从德克萨斯工业大学获得法律学位。2008年夏天达科斯在德克萨斯大学医学院演讲对其当初的选择依然坚持不改。他认为“人的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利是生而即有的权利,不需要任何他者同意,包括政府、为你治疗的医生甚至你的近亲的同意。……没有你的同意,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在你身上进行任何的医疗行为。”[4]在“夏沃事件”中,主张拔掉饲管的夏沃丈夫之所以胜诉就在于其提供了夏沃在健康状态时声明其不愿意以人工方式维持生命的证据,所以,法院所支持的不是夏沃丈夫的诉讼请求而是夏沃本人的请求,是对夏沃个人意愿和生命决定权利的尊重。
4 安乐死问题:职业文化冲突
安乐死问题最终落脚在医学职业文化的冲突中。在西方医学职业内部蕴含着对安乐死问题完全相左的观点。1870年,当英国人塞谬·威廉姆斯正式提议,不仅可以利用麻醉剂来缓解疼痛,而且可以用来有意结束病人的生命时,结果遭到了当时英美国家医学界的广泛反对[5]。但是在一个多世纪的岁月流转之后,情势呈现出几乎完全不同的局面,越来越多的医生开始赞成、允许给病人实施安乐死。一位美国肿瘤医生伊曼纽尔说:“由医生结束患者的生命是错误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个别情况下,当所有其他治疗手段(所有的药物、外科手术、心理疗法、精神治疗等等)都已试过后,我们仍否认应当实行安乐死,作为最后手段。”另一位美国医生凯沃尔基安等则把自己塑造成不顾身家性命,敢于突破法律、道德界线,甘冒舆论风险而给病人执行安乐死的英雄。而在“昆兰案”中,当昆兰养父母提出拔掉昆兰的生命维持设备时,却遭到医生们的强烈反对并被起诉到法庭,这与中国医生通常会尊重家属的意见情况很不一样。对于医学职业中的医生们来说,为什么在对待安乐死的问题其观念会有如此大的变化与差异?
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医学职业文化内在的矛盾和冲突。在医学职业形成的初期,《希波克拉底誓言》曾对“安乐死”有明确的态度:“吾将不对任何求死者给予致命之药,亦不作此种授意”[1]92,中国医学职业传统亦坚持“医乃仁术”。“人们为什么如此推崇医术呢?就是因为医术手段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与死亡抗争。”[6]希波克拉底学派的“不伤害原则”是对安乐死问题的反对或中医传统中的“医乃仁术”可以说是医学职业文化的核心或精髓,是医学界与社会达成承诺的基础,医学职业基于此得以和社会建立互信关系,它所申明的是医学职业决不利用自己的技术对患者的生命造成伤害,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终止病人生命。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以及医学自身的发展,医学职业核心文化的这种内在统一性受到了挑战,现代医学职业中的不伤害原则可以作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解和解释:在原来医学职业文化的意义上,不以医学的手段终止患者的生命符合不伤害原则;而在现代医学中维护患者利益更明确地成为医学职业的核心目的,而尽快结束出于患者自己意愿且十分痛苦的生命正是符合此目的的表现。故而对医学职业来说,一方面不否认由医生结束患者的生命是与医学职业精神相违背;另一方面医学职业的宗旨应当是对病人的仁慈行为而不应是将其“杀死”。有些医生认为,二者之间的鸿沟可以轻易跨越,但目前人们关于安乐死问题的争论则说明这种跨越并不容易。
5 结语
有学者说“本质上,安乐死并不是一个法律问题,甚至不是医学问题,而是一个哲学问题。”[7]安乐死是一个哲学问题,毕竟生死事大,而生死问题归根结底就是哲学问题。但是从安乐死问题的出现、形成的根源上讲,安乐死更是关涉文化与价值的问题。安乐死问题为什么首先在西方文化语境中出现被强烈地关注和争论,为什么不是生于中国文化背景中的人士首先讨论安乐死的观念和问题?究其根源,安乐死问题是一个文化问题、价值问题,而且是由于文化或价值之间的内在冲突使得安乐死成为问题:在西方社会的宗教文化、政治文化和职业文化中,不仅其各自之内部存在着冲突,而且不同文化所指向的价值也相互直接碰撞。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社会,选择安乐死的人永远是社会中的极少数或例外者,但安乐死作为问题被提出决不在于使其以合法化的面目风行于世,而是要使人类通过安乐死问题认识生命及体会生命意义。而中国的安乐死问题则主要不是在文化的层面却是在经济的层面上进行探讨,但并不否认其或多或少地起到了认识生命的作用。但是因为我们缺少如上造成安乐死问题的文化背景,所以中国的安乐死讨论是非常不同于西方的。究竟我们应当在何种意义上讨论安乐死问题,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思和探讨的问题。
安乐死源远流长的历史并不意味着现代人所谈论的安乐死问题一定要与历史上的安乐死现象有某种联系,可能恰恰相反,现代人对安乐死问题的讨论和强烈关注正是要摒弃作为安乐死历史之源头的古希腊时期马其顿人式的“安乐死”,同样更重要的是避免纳粹德国所声称的那种“安乐死”,如此方显现代人在对待安乐死问题上的明智与进步。在西方的语境中,安乐死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其多元文化的冲突与碰撞,但其如此被激烈讨论的宗旨却是一致的,即捍卫人的生命的尊严与神圣。但在中国的语境中讨论的安乐死问题却深深地烙上了经济的、功利的和世俗的印记,且主要地将对安乐死问题的关注聚焦于安乐死的合法化问题,而唯独缺少了对人的生命尊严和生命神圣价值的强调和重申。要明白,我们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有太多的人渴望生命能够延续的物质和精神支持而不得,而不是真正地希望安乐死而不能的情况。以目前中国的社会现状观之,从各个层面来说我们所缺少的主要是对人的生命尊严、生命神圣予以尊重的社会共识与制度保障。因此,尽管有文化传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但在尊重人的生命尊严这一点上中西方应当是共识的,故而中国的安乐死讨论亦应当以此为出发点和最终目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