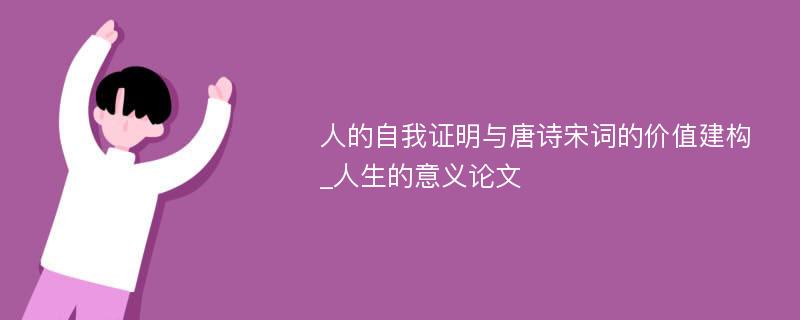
人的自证与唐诗宋词中的价值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诗宋词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所谓人的自证,即人不依赖于外在价值评判系统的内在价值的自我贞立,其依据是人类总体意识。人类总体(人类总体意识、人类总体观念)是指在历史实践中建立起来的有利于人类总体的产生、存在与发展的历史合理性,这种历史合理性不受具体价值观念和个别历史阶段的价值评判系统的束缚,而是以人类总体的存在与发展为最终依据,导向人类价值观念的自足。这种人的自证的价值建构方式在唐诗宋词中有着丰富多样的表现。 一、人的“自足性”与价值建构 人的自证来源于中国文化中人的“自足性”。所谓人的“自足性”,是指人自身的价值完全依靠自己建立,不依待任何外在因素。孔门仁学不奉鬼神,不依他人,一切都是面对死亡——人生有限性——的自我设立,使人具有了最彻底的“自足性”。这在《论语》中有着十分完备的论述。 在孔门仁学中,人的价值建立与鬼神的有无没有任何关系,对鬼神的无待使人获得了价值的“自足”。“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也’,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篇》)对于鬼神的问题,其实有两个思路:一是思考鬼神的有无,对此,人类至今无法达成共识;二是思考人和鬼神的关系,如果认为人和鬼神是没有关系的,那么,鬼神的有无就是一个无需考虑的问题。在此,孔子认为,人生的全部意义就在于现实道德的圆满,对鬼神的祷告与鬼神是否“豁免”人的责任以及是否“赦免”人的罪过对于人的道德的圆满毫无意义。因此,孔子在此彻底解决了人和鬼神的关系:人和鬼神没有任何关系就是人与鬼神的唯一关系。“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先进篇》)孔子之意是说,未做好“事人”、“知生”之事,不必问鬼神和死亡的问题;如果做好了,就完善了道德,超越了鬼神和死亡,也就不必关注鬼神和死亡。“朝闻道,夕死可矣”,人生的全部意义就在于“闻道”,人的价值的建立,无待于鬼神,只靠自己。至于“敬鬼神而远之”,那是“神道设教”,指的是“神鬼”的现实实用性,而不是指鬼神的存在。 鬼神不可靠,死亡不可知,没有外在的依据,人便陷入绝待的虚空中。人生来未必是有价值的,却是必须有价值的,既然鬼神不可靠,人只能依靠自己:“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篇》)“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篇》)“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篇》)。人所以要“欲仁”、“弘道”,是出于对人类总体存在与发展的基本责任,不“欲仁”、不“弘道”人类就要走向倒退和灭亡,因此“欲仁”、“弘道”是人类历史的必然要求。“为仁由己”同样也是对他人的无待。“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篇》)这是对上天和他人的无待;外在因素既已剪除,人的“自足性”便得到确认;“下学而上达”是进德的方式,即从现实实践到人格的超越;而“知我者其天乎”是人格境界的提升和归宿。 对鬼神和他人无待,“为仁由己”,其方式必然是内省,因为在无待的自足状态中,人只有依靠内省才能提高人格境界。“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篇》)而内省的依据就是人类总体。“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颜渊篇》)中国文化中无宗教性原罪,所忧所惧者,惟道之不行,德之不足,故有知命不忧,足德不惧之说。后来孟子说“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公孙丑上》),更是将内省与人的“自足”关系显豁地表达出来,明确指出了在历史实践中建立的正义、道义观念是内省的根本依据。 “五十而知天命”(《为政篇》)、“畏天命”(《季氏篇》)、“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篇》),人的“自足”最终归于“天命”。天是宇宙总体,是物质与超物质(被赋予意义的物质)、情感与超情感(以理性为指导的情感)的总和,是物质情感化、情感物质化的统一体,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实践中建立起来的最终的物质—精神依托。命本具有个体意义上的无定的偶然性,但“命自天降”(见郭店楚简),命必然具有超越偶然的品格,因此,人类总体的必然谓之天命,了解并奉行这种必然叫做知命,即所谓“君子知命”。如果将人类总体的必然机械地照搬到个人命运上,则谓之宿命。君子知命是指君子对人类总体的光明前途与个人为实现这种光明前途而必然遭遇命运的坎坷有清醒的认识。“子畏于匡”(见《论语·子罕篇》、《史记·孔子世家》),“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篇》)是“知命”的典型体现,孔子所表现出的自信,不是毫无根据的自我安慰,也并非相信人格神的上天,而是基于与“天命”相通的人格境界,这也正是超越鬼神和死亡,将人生最终着落到“天命”的极致体现。 二、人的自证与人类总体意识中的价值建构 唐诗宋词作为民族文化最凝练的表现形式,其中的很多优秀篇章与深层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有着内在的密切联系,这也是那些诗词能够超越历史时空而具有恒久艺术魅力的根本原因。其中,人的自证——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价值建构方式——在唐诗宋词中的丰富表现就是铸就唐诗宋词恒久艺术魅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人的自证不是虚幻的空想,而是以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人类总体为依据的,这样,人的自证就有了对具体现实时空的超越性。如刘长卿的《长沙过贾谊宅》:“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留楚客悲。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吊岂知?寂寂江山摇落处,怜君何事到天涯!①首联写贾谊的遭遇及其情感,点出其悲剧性人格,激起了人们对人生和历史的悲剧感;颔联写寻访贾谊宅所见所感,找不到人生与历史的意义,“独”、“空”二字表现的是人的孤独和历史与自然的无意义,是上联悲剧意识的发展和深化;颈联诗腰,所谓“诗腰必挺”,直写对人事和自然的绝望,由否定人事而至否定自然,是悲剧意识的高潮,同时也隐含着“人生来未必是有价值的,却是必须有价值的”这一中国文化中价值建构的思路,隐含着在否定中人的价值的崛立;尾联几乎是无声的呐喊,表达了对贾谊的同情和对命运不公的愤懑,同时也是自我肯定。全诗的基调是否定性的绝望,但否定本身就是一种最大的建构,否定了外在的人事和自然,却肯定了贾谊和自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自身就具有建构正面价值的内在能力,可以不受外在条件和价值评价系统的制约,体现了人的自证原则。抒情主人公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自信,就在于他摆脱了具体历史时空的限制,以最为合理的人类总体意识为观照,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人的能动性。人摆脱外在依待的自由感和畅快感,是该诗激动人心的艺术力量的来源。 在这方面,杜甫的有些诗作也很典型,如《蜀相》:“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②首联起句邈远,铺开了无垠的时空,引人遐思:何以要在浩渺的宇宙中寻找一个祠堂?那位丞相究竟是什么人?颔联写眼前景色,但极为曲折藏物:碧草和黄鹂难道是无情的?还是年年春色,时时好音,它们不为诸葛亮的逝去而悲伤,难道诸葛亮的功业没有意义?不,春草之美和黄鹂动听的歌唱并不能使我快乐,我为诸葛亮的赍志而没感到无限的悲伤;我悲伤的情感告诉我,人的价值是由人自己建立起来的,人是可以自证的。颈联写人事,诸葛亮于小义是报知遇之恩,于大义是实现明君贤相和为国为民的理想,诸葛亮的一生追求是小义与大义的完美合一,是人生的理想状态,这就为上两联的情感找到现实基础,挺立起全诗。尾联揭示了功业无限而人生有限的悲剧真相,不仅是对诸葛亮的缅怀和对历史的感喟,更是在洞悉悲剧真相后的毅然挺立——英雄流泪之后并不是走向消沉,而是以泪洗涤凡庸,以形上价值的建立来超越现实中有限的生命!该诗在中性的宇宙中痛快激昂地挺立起人的价值,历史的价值,正如前人所说,是“一篇绝大文字”。该诗还表现了中国人以自证的方式建立价值的精神流程:寻找—找不到—找到—在悲剧识中价值的崛立(对“找到”的深度确立)。在这一意义上,该诗真正体现了杜诗的“沉郁顿挫”。 一些表现隐逸生活的诗也有这样的突出特征,如王维的《送别》:“山中相送罢,日暮掩柴扉。春草年年绿,王孙归不归。”③在隐居生活中流露出本真的价值感。诗作以隐居的合理性来对抗官场生活的异化,以自然的永恒对抗人事的短暂,充满着对自然韵律和本真生活的体认,还不经意地散发出某种青春的气息。而刘长卿则不同,他身处中唐,历史的喧嚣已逐渐散去,他以更加纯粹的心灵来贴近历史和现实,也能更加冷静深入地审视自己,因而他的诗境也就更加幽微和深邃,如《却赴南邑留别苏台知己》:“又过梅岭上,岁岁此枝寒。落日孤舟去,青山万里看。猿声湘水静,草色洞庭宽。已料生涯事,唯应把钓竿。”④该诗意象和意境仍有廓大和浑融之处,但其中已透显出落寞和萧索;不过,尾联则是自证式的坚挺,“惟应”二字是他勘破历史和现实后的应然选择,这不是对命运的感慨,而是对喧嚣与浮华的否定。刘长卿的很多诗都有此意味,实际上,这类诗对于人的心灵成长和价值建构有着特定的意义,但这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许浑的咏史怀古诗较为著名,佳作不少,其中有一些也与人的自证有关,如《秋日赴阙题潼关驿楼》:“红叶晚萧萧,长亭酒一瓢。残云归太华,疏雨过中条。树色随山迥,河声入海遥。帝乡明日到,犹自梦渔樵。”⑤首联点出时令、地点和宦游的身份,自然与人事合一,已隐含了对自然的亲切体认和对自然而然的本真生活的向往;颔联写得风淡云轻,承接上联,更加充分体现了作者对自然的亲和感和明澈的心境,展示出丰沛的宇宙情怀;颈联作为诗腰,本应提出价值诉求,但还是写自然,这种现象在许浑诗中大量存在,成为削弱许浑诗作思想和艺术价值的一个因素,但由于该联意象营造十分出色,还是体现了作者悠远的神思和高洁的人格;尾联在上三联的写景中猛然翻出,直写人事,抒发自己不愿意奔走官场,希望过本真渔樵生活的强烈愿望,收煞并统一全诗,干脆有力。尾联中的“自”字含自发、本真之意,它是由人类总体决定的人的必然选择,也是对最合理的文化因素的自然体认,是人的本真存在状态。 许浑的《谢亭送别》以更加隐晦的方式表现了人的自证:“劳歌一曲解行舟,红叶青山水急流。日暮酒醒人已远,满天风雨下西楼。”⑥诗作展现了一个完整送别的流程,首先是在惜别的歌声中解开系舟的缆绳,目送友人,红叶青山与湍急的流水形成的意象使人的情感鲜明而显豁;友人已去,独自酒醒,面对日暮人远的不可改变的现实,在满天风雨中,那个书生的背影,踽踽独行,消失在西楼下。这与李白的“唯见长江天际流”的悠远思念不同,指向的是对世事不可知、人事不可预的迷惘,展现的是知命而不乐天的情绪状态。向这种情绪状态的沉入最终导致的是人的自证的崛立。需要看到的是,送别是日常之事,诗作表现的是一种日常的情感,在这种日常情感中展示出了对习以为常的世事的迷惘和思索,正说明了人的自证的普遍性。 三、人的自证与“向空而有”的价值建构 “向空而有”是指在价值建构的过程面向价值之空而毅然崛立,为自己建立起价值,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⑦将此意说得最为清楚。中国文化中价值建构的一个重要理路是:人生来未必是有价值的,却是必须有价值的。其间的关系不是形式逻辑的推理,而是靠客观社会性来保证的。这种论证方式看似独断,恰恰是最合理和最可靠的,因为它依据的是“客观性推断”,以历史实践为根本,避免了一切概念游戏(“主观性设定”),从人自身的最深刻最真实处出发,以在历史实践中产生的人类总体观念为根本保障,通过人的自证指向人类自身的必然建构。 在这方面,许浑的怀古诗有一定的代表性,如《金陵怀古》:“玉树歌残王气终,景阳兵合戍楼空。松楸远近千官冢,禾黍高低六代宫。石燕拂云晴亦雨,江豚吹浪夜还风。英雄一去豪华尽,唯有青山似洛中。”⑧首联写隋军攻陷金陵,直逼景阳宫外,陈在《玉树后庭花》的靡靡之音中覆灭,一“空”字彰显出历史之空,价值之空;颔联极写金陵坟墓上茂盛的松楸和宫殿废墟上弥望的禾黍,将一“空”字落到实处;颈联则写金陵的晴雨风浪、石燕江豚一如往昔,并未因金陵的盛衰而有变化,历史的无常与自然的永恒形成鲜明对比;尾联写六朝中所谓的英雄都逝去了,对于金陵,什么都没有留下,金陵之地,“唯有青山似洛中”(李白《金陵三首》有“山似洛阳多”句)。又如《咸阳城东楼》:“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溪云初起日沈阁,山雨欲来风满楼。鸟下绿芜秦苑夕,蝉鸣黄叶汉宫秋。行人莫问当年事,故国东来渭水流。”⑨首联写诗人登上咸阳城楼南望,景物很像长江中的汀洲,犹如自己的家乡;颔联写登楼时环境的变化,蕴含着对政治局势的深刻体验和预测,也为下联对历史的感慨做好铺垫;颈联写秦、汉两朝故都的颓败景象,展示出巨大的历史沧桑感和空没感;尾联明写不让追问历史的价值与意义,但恰恰引起追问,指向的是在恬淡悠长的韵味中向宇宙自然的沉入,是对历史的喧嚣的否定,追求的是与自然亲和的本真的历史情态,是价值的建立。许浑的这类诗典型地体现了“向空而有”的价值建构方式——通过对浮华喧嚣历史的否定和对永恒不变的宇宙自然的肯定积淀起具有历史合理性的价值观。 杜牧一些诗作也有这样的特点,如《独酌》:“长空碧杳杳,万古一飞鸟。生前酒伴闲,愁醉闲多少。烟深隋家寺,殷叶暗相照。独佩一壶游,秋毫泰山小。”⑩开篇就揭示了人生的悲剧真相—— 一个如孤独飞鸟般的人在无限的时空中找不到价值和依据;杜牧的诗经常出现“孤独飞鸟”的意象,往往象征价值的虚空,提示强烈的悲剧意识。接下来写“闲愁”,“闲愁”是诗词中的重要内容,在很多情况下它是一种试图超越而尚未超越的状态,关涉到对生存真相的追问;第三句写历史之“空”,在唐诗怀古咏史诗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最后一句用刘伶典故和《庄子》义,齐一万物,破除心灵的栅栏,解构意识形态,消解悲剧意识,“闲愁”消散,获得升华。该诗前两句写悲剧意识的兴起、体味和追询,中间两句是心理过渡,最后两句在人的自证意识的观照下以“向空而有”的方式建构富有历史合理性的价值,在唐诗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刘禹锡的怀古诗在这方面就表现得更为突出。如《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11)诗作运思的过程,就是拨开浮华寻找永恒的过程。前两句否定浮华历史,写历史之空;后两句写历史之真,为历史找到归宿,建构起本真的历史观。这在此类诗中具有典型意义。再如《石头城》:“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12)运思过程与上诗相似,不同之处是找到了宇宙自然的真实,在人事喧哗的短暂与宇宙自然的永恒形成的强烈的对比中感悟价值。在这类诗中最著名的当数《西塞山怀古》:“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索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番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13)前三联对历史无常和自然永恒进行了对比,透显出强烈的历史悲剧意识。尾联一般解释为如今天下一统,四海一家,所以西塞山的故垒废置不用,长满芦苇;但这样似与诗思不合,更会使诗意趋向卑庸,似应解释为处处都可为故乡的心灵的洞彻,指向的是觉悟了历史的本真后对“金陵王气”等拘囿观念的耸身摇脱和人生的境界打开。 总的看来,刘禹锡的怀古诗慨叹世事兴亡,深寓历史教训,即景抒情,由情及理,令人叹惋不已。这些诗之所以具有那样大的影响力,主要是由于它们契合了中国人重自然而轻人事的文化心理结构。自然的真实与人事的虚幻,自然的神圣庄严与人事的卑下荒诞,自然的永恒与人事的短暂,在自然与人事的比照中,透显出浓烈的悲剧意识,并由对自然的体认而达至境界的开启。中唐晚期的士大夫们正是在振兴无望的心态中重新思考起自然与人事的关系,展露出这种美丽的伤感,“向空而有”地积淀着价值。 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则在开篇直接提撕人的价值空虚:“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14)面对万古流淌的浩浩长江,即便是风流人物也是渺小的,何况芸芸众生!此作开篇第一句就毫不留情地撕开了人生的悲剧真相,将人抛到虚空之中:人的价值何在?人的意义何在?既然无论百姓还是英雄都要被“淘尽”,人生还有意义吗?这就是价值悲剧意识!从“乱石穿空”至“樯橹灰飞烟灭”,是在对自然与历史的亲和、认同中寻找价值——历史通过心理体会而呈现,周郎的抗敌豪气及其风仪神韵难道不是值得向往的吗?“故国神游”一句是写词人因“多情”而感悟!至于“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则并非消沉,而是解脱——因价值的建立而达至的解脱。该词从慷慨壮志到悲剧意识的消解,再由消解而升华,概括了悲剧意识的兴起、消解、升华的民族文化的心理历程,是“空而有”的价值建构模式的更彻底的形式;它不是先否定负面历史,然后彰显宇宙自然的永恒性,而是开篇直接提撕人的价值虚空状态,使人在彻底的绝望中进行自证,毅然崛立。 四、人的自证与“向有而空”的价值建构 所谓“向有而空”,是指对宇宙自然和人事情感描绘后加以否定,这种否定不是否弃,而是对美好事物不再的惋惜和留恋,对合理事物成空的不满与愤懑,指向的是对更深层更美好价值的建构。 在这方面,秦观的词表现得比较突出,如《千秋岁》:“水边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乱,莺声碎。飘零疏酒盏,离别宽衣带。人不见,碧云暮合空相对。忆昔西池会。鵷鹭同飞盖。携手处,今谁在。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15)上片回忆苏轼与门人往日相聚游冶的美好情景,南宋诗人范成大最欣赏“花影乱,莺声碎”一句,专门为建“莺花亭”;下片则写今日众人不知流落何方,未来也不可测度。结片最为著名,此类词句在秦观词中极多,如“无奈归心,暗随流水到天涯”(《望海潮》)、“绿荷多少夕阳中,知为阿谁凝恨背西风”(《虞美人》)等。陈郁《藏一话腴》(内篇卷上)说:“太白云:‘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江南李主曰:‘问君还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略加融点,已觉精彩。至寇莱公则谓:‘愁情不断如春水。’少游云:‘落红万点愁如海。’青出于蓝,而青于蓝矣。”(16)李白所处的是政治本体化——以现实政治为“信仰”——的时代,他的诗表现的是政治一现实的失意;李煜处于唐宋之间,此时政治本体基本消解,对文化本体的探询尚未得到充分发展,故李煜表现的是追询价值而未得的“闲愁”;秦观表现的则是在对文化本体进行追询后的失望,是价值追索失败后的绝望!这三个历史阶段的“愁”的悲剧意识的文化内涵呈现出层层递进的状态。但秦观的绝望仍然不是否弃,而是在对无比美好的情事的追忆中唤起了新的价值建构冲动。“向有而空”的“空”恰恰是激起人的自证的根本动力,在该词中,上片描写的美好情事就是人应该追求的生存状态,就是人自证的内容。 又如《江城子》:“西城杨柳弄春柔。动离忧,泪难收。犹记多情,曾为系归舟。碧野朱桥当日事,人不见,水空流。韶华不为少年留。恨悠悠,几时休。飞絮落花时候、一登楼。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17)上片写当年美好的情事都消逝了,只有河水空自流淌,表达的是对人事—自然的否定和绝望。过片彰显生命的悲剧意识,使生命的本体性威胁得到了显豁的表达;接下来的“恨悠悠,几时休”则是写情绪的长期积郁;“飞絮落花时候、一登楼”是情绪积郁导致的存在最彻底的敞开,将一切非本真都加上括号搁置起来,于是生存真相显现:“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这是对解决生命有限性问题的彻底绝望和对价值追询的放弃,也就是所谓的“向有而空”,但人生来未必是有价值的,却是必须有价值的,全词对人生美好情事的描绘必然会激起人们追询价值的欲望,新的更具合理性的价值观念必然会得以积淀。 中唐时期社会动乱,很多诗人忧时念乱,往往在吊古怀今,咏物抒情中表现出“空”的思想情绪和彻底的悲剧意识。如杜牧的《登乐游原》:“长空澹澹孤鸟没,万古销沉向此中。看取汉家何事业,五陵无树起秋风。”(18)面对无垠的时空,一切都消失于其中,遑论汉家事业、五陵豪杰!人的价值、历史的价值无从说起。再如《悲吴王城》:“二月春风江上来,水精波动碎楼台。吴王宫殿柳含翠,苏小宅房花正开。解舞细腰何处往,能歌姹女逐谁回。千秋万古无消息,国作荒原人作灰。”(19)当然,这种价值的虚空导致的不是绝望和放弃,而是进一步通过“空而有”的心理净化机制,积淀起更多的正面的价值。 李贺的诗中有相当一部分体现出鲜明的“向有而空”的特色,即在诗的前半部分把人生情事描写得无比美好,但在诗的后半部分甚至是最后一句,猛然翻出,残酷地揭示出人生的悲剧真相。如著名的《天上谣》:“天河夜转漂回星,银浦流云学水声。玉宫桂树花未落,仙妾采香垂珮缨。秦妃卷帘北窗晓,窗前植桐青凤小。王子吹笙鹅管长,呼龙耕烟种瑶草。粉霞红绶藕丝裙,青洲步拾兰苕春。东指羲和能走马,海尘新生石山下。”(20)前面五句将神仙世界描绘得无以言喻的美好,可谓达到浪漫主义的顶峰,但最后一句猛然翻出:时光永逝不停,无常巨变还在,宇宙间的一切都不可靠。再如《三月》:“东方风来满眼春,花城柳暗愁几人。复宫深殿竹风起,新翠舞襟静如水。光风转蕙百馀里,暖雾驱云扑天地。军装宫妓扫蛾浅,摇摇锦旗夹城暖。曲水飘香去不归,梨花落尽成秋苑。”前面都是写春天的美好,但最后是“曲水漂香去不归,梨花落尽成秋苑。”(21)又如《将进酒》,前面这样写:“琉璃钟,琥珀浓,小槽酒滴真珠红。烹龙炮凤玉脂泣,罗屏绣幕围香风。吹龙笛,击鼍鼓,皓齿歌,细腰舞。”可谓名物精美,恣意享乐,但后面接下来的却是:“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劝君终日酩酊醉,酒不到刘伶坟上土。”(22)在至为强烈的对比中使人生的悲剧性显豁出来。另外,像《大堤曲》前面写青春的美好,最后是“今日菖蒲花,明朝枫树老。”(23)《二月》表现的是生活情景的极度不和谐,前面写的都是春天的美好和生活的欢乐,最后是“津头送别唱流水,酒客背寒南山死。”(24)《梁台古意》前面写梁王台沼的宏伟富丽和骄奢淫逸的享乐,最后是“寥落野篁秋漫白”。(25)李贺诗歌的生命悲剧意识充分展现了人生价值之“空”,指向的是对现实世界的否定。从表面上看,李贺的这类诗歌似乎没有什么积极的社会意义,也没有什么正面的价值取向,但却最为著名,最为人们喜爱,根本原因就在于这种“空”在李贺诗歌的艺术倾向和艺术感染力的特定作用下为我们提供了价值崛立的自由。 “向有而空”的“有”往往是美好的,这个“有”具有应然的合理性,是人自证追求的目标和精神内涵,而“向有而空”的“空”具有特定的深刻文化内涵和心理机制,是激起人的自证的根本动力。 人的自证是“绝处逢生”的产物,不到精神的逼仄处,不到外在条件不足依侍时,人一般不会兴起自证意识,因此,人的自证意识往往与悲剧意识相联。人的高贵之处就是在绝无可能之处建立起价值来,吟诵这些诗词正是积淀具有历史合理性价值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 ①④褚仲君:《刘长卿诗编年笺注》,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3、210页。 ②《杜诗详注》,(清)仇兆鳌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36页。 ③《王维集校注》,陈铁民校注,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565页。 ⑤⑥⑧⑨(唐)许浑:《丁卯集笺证》,罗时进笺证,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25、709、295、311页。 ⑦《张载集·近思录拾遗》,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376页。 ⑩(18)(19)吴在庆:《杜牧集系年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23、229、1206页。 (11)(12)(13)《刘禹锡集》,卞孝萱校订,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10、310、300页。 (14)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98页。 (15)(17)(宋)秦观:《淮海集笺注》,徐培均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63、45页。 (16)张惠民:《宋代词学资料汇编》,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版,第166页。 (20)(21)(22)(23)(24)(25)《李长吉歌诗编年笺注》,吴企明笺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10、23、664、679、21、2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