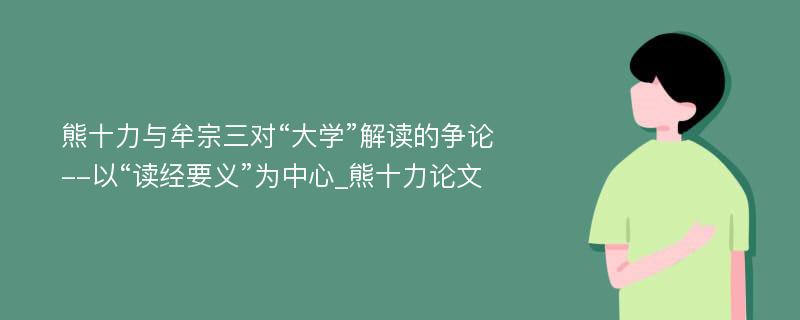
熊十力与牟宗三关于《大学》释义的辩争——以《读经示要》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释义论文,大学论文,中心论文,熊十力论文,宗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4年冬,熊十力在重庆北碚写成《读经示要》,次年12月正式出版。出版前曾分讲油印若干册,送诸同好。牟宗三当时在重庆随熊十力游,获赠此书之第一讲,旋即致函熊十力,就其中关于《大学》的解释与熊十力商榷,熊十力复信答辩。(注:此信收于《十力语要》卷三,题名“答牟宗三”,信前附录牟宗三的来函。) 熊牟师弟关于《读经示要》的这场辩争,焦点集中在对《大学》“格物致知”的解释上,涉及对儒家根本精神的理解,本体的诠释方向,以及在天道和人心、价值和知识等问题上的不同立场,从中可以看出二人思想发展中的一些重要关涉。
一、对儒家根本精神理解上的一致
熊十力在《读经示要》第一讲中对儒家经典的根本精神做了阐发,并据此对佛教和西洋学术进行批评。他认为,六经内容虽然不同,但皆在宣示天地万物的本原,为人性立形上学基础。天地万物的本原是道,道是世间事物的总原理,是人性的最终根源。所以,欲究明天地万物的根本法则,读儒家经典是最简捷的途径。儒家之外的学术,归纳起来,其精神趋向不外两大宗:佛教和西洋学术。佛教的最终目的在求超脱轮回,出离苦海,达于彼岸世界。其内部各宗派虽在理论上千差万别,最后的归宿都在“涅槃寂静”。故学佛者皆耽空守寂,与《周易》乾德刚健,万物各正性命,不欣生,不厌死,在大化流行中各极其致的学说不同。西洋学说肯定外在世界,对人生不厌不弃。但西洋学术着力者在物质的创造和社会生活资具的更新,一意向外弛求,不内敛凝默,易物化而不返,与《周易》自宇宙本体而来的对物的观照和利用不同。若套用王船山的话,可以说佛教为“耽空者务超生,其失也鬼”;西洋学术为“执有者尚创新,其失也物。”[1] (P578)所谓“鬼”,用张载语:“鬼者归也”,指精神内敛,卒归于空寂。“物”指为物所化。佛教与西洋学术的精神方向皆背离了人文精神,而以六经为代表的儒家则“体道以立人极”,虽究玄而不耽于空寂,成物而不执著于物,可谓大中至正之道。
牟宗三同意熊十力本《周易》哲理对佛教和西方学术所做的批评,他在给熊十力的信中说:“昨奉《读经示要》第一讲油印稿,喜甚!细读一过,大义昭然。据六经之常道,遮世出世法之僻执,遮表双彰,可谓至矣。”[2] (P307)其中世法指西洋学术,出世法指佛教。“遮”指对耽空执有者的批评,“表”指对六经特别是大《易》思想的阐发。牟宗三以上话语表明,他对乃师以儒家人文精神、以即活动即存有的本体世界为价值标准是首肯的,对乃师据此价值标准对佛教和西洋学术所做的批评是赞同的。这对他以后对宋明理学、佛教的研究和判释有很大影响。
熊十力在《读经示要》中对群经治国原则的概括,也为牟宗三所赞同。熊十力认为,六经所言,是人类之常道,常道贯彻为治术。六经之治术,可概括为以下九点:一、仁以为体。仁者,宇宙之本原,治国之根本,本仁以立治体,可以有万物一体之襟怀,可以撙节物竞之私,可以实现互助之美,堵塞利害相攻之祸。二、格物为用。在立仁体的前提下,必须精切研究社会组织、政治制度、风俗民情及人本身的性质。“徒善不足以为政”,治国理想必须落实在实际问题的研究与解决上。三、诚恕均平为经。此处“经”乃根本法则之意,与“权”相对。六经致治原则,在诚、恕与均平。诚者诚信,不猜忌,不欺诈,是处理国际国内事务所应遵循的原则。恕者不自私。国际间的侵伐,宗族间的杀戮,多起于无恕心。均平即强弱相济,大小互助,抑高补低,可以杜绝强者垄断、侵削、贪污诸恶,亦可以消弭弱者揭竿而起。恕本于诚,均平本于恕。四、随时变化为权。此“权”为权变之意。经立常道,权应变化;权本于经,守经而观变,变不离乎常。经济制度、道德信条、习惯俗尚、政策法令皆在变中,而不离乎诚恕均平之大经。五、利用厚生,本于正德。此点是儒家与西洋治术最显著的不同。近世列强皆以利用厚生为本,儒家先哲亦重利用厚生,但强调必出于正德。非此则易堕入专趋功利一途。正德为本,利用厚生必本于正德,这是无论强国弱国皆当奉行的原则。六、道政齐刑,归于礼乐。这一条针对专尚法治所导致的弊害,认为“徒法不足以治国”,须以礼乐陶养,培育向善的民风。对民众的教育,重在精神陶养,不在刑法约束;在内心的自律,不在外在的强制。第七、第八,始乎以人治人,极于万物各得其所。所谓以人治人,本于《中庸》所谓“以人治人,改而止。”即以人所制定的礼乐育人,使其能改正己过,达于理想人格。礼乐的依据是人性之本有,故非冰冷的律条。在适性惬情之渐进中归于万物各得其所。第九,终之于群龙无首。此条是糅合《春秋》所说的太平世和当时盛行的无政府主义二者,而比附于《易》之“群龙无首”。万物各得其所,人人皆为君子,是为“群龙”;此世天下大同,达于至治,无有种界、国界,人人皆平等,无有首领君临于众人之上,是为“无首”。人类的最高愿望是至真至善至美之境,人以此为目标,精进不已。大同之世即这个最高目标在政治生活上的表现。熊十力认为,这些治国原则,总而为一,可曰仁术;六经之所昭示,可曰仁学,仁术本于仁学。所以他的结论是:“经学者,仁学也;其言治,仁术也,吾故曰常道也。常道者,天地以之始,生民以之生,无时可舍,无时可易也。而况经学之在中国也,真所谓日月经天,山河行地,其明训大义,数千年来浸润吾国人者,至深且远。凡所以治身心、立人纪、建化本、张国维者,何一不原于经。”[1] (P626)
熊十力对于经学的这些意见,为牟宗三所认同;对以上治术九义,更是赞叹不置。牟宗三在信中说:“继陈九义,始于仁以为体,终以群龙无首,规模宏阔,气象高远。盖吾师立言,自乾元着手,会通《易》、《春秋》及群经而一之,固若是其大也。……孔孟立人极,赞化育,本于此为根本精神。理学家杂以释老,此义渐隐没不彰。德国哲人立言,庶几乎此,而英人则全不能了此。时下人心堕落。全无志气,闻之必大笑。然非圣贤心思,不能道之矣。”[2] (P307)牟宗三认为熊十力以上见解,有体有用,有儒家最高理想,有本此理想融合中西古今学术而成之措施,代表了孔孟根本精神,是一幅陈义甚高的治国蓝图。此中所言之本道德而体现为治术,仁为本体等,与牟宗三后来一系列著作中所表示的道德的理想主义基本精神一致。惟“群龙无首”义所说的无国家、无政府的乌托邦式的君子国,则由于牟宗三没有熊十力那样强烈的空想色彩,没有熊十力那样强烈的对《春秋》、《礼记》中所说的大同世界的信仰,没有熊十力那样对经典直接信用不加怀疑的态度,故不信奉持守。而对道德的理想主义,则有一系列创造性诠释。熊十力所赞扬的“德国哲人”,指以康德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所贬斥的“英人”,则指当时在中国流行的英美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对这些学说的融摄、改造,是牟宗三后来一系列著作的重要内容。
二、对“格物致知”的不同解释
牟宗三认同熊十力者,主要在儒家的根本精神方向和实践原则上,对《大学》诸条目特别是其中的“格物致知”,与熊十力解释不同。熊十力是先把“格物”与“致知”分成两个部分,再总合起来说两者的关系。他的总的指导思想是,统合朱熹与王阳明,以致知统合格物,在道德理性的范导下来安排知识,以知识融入道德,使知识活动成为一个有价值参与的整体。
在对“致知”的解释上,熊十力用阳明义而不用朱子义,他认为,《大学》所谓知,即阳明所谓良知;良知之知非知识之知,他说:“致知之知,即是良知,何以云然?如非良知,则必训此为知识矣,若是知识之知,则经言正心诚意,何可推本于知识乎?知识愈多,诈伪且愈甚,老子所以有‘绝圣弃智’之说也。经言‘诚正必先致知’,则此知绝非知识之知,而必为良知也,断无可疑矣。孟子言良知,盖自此出。”[1] (P656)熊十力所理解的良知即本心。这个本心,是道德理性与知识理性的统合体。就道德理性说,它是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的道德情感。就知识理性说,它是经验知识得以成立的根据,即佛家所谓“缘虑”的主体。而致知之“致”,即正心、诚意诸工夫,它推致、保任良知本体,使流行于一切处而不改变其主宰常明的状态。
熊十力反对以“知识”释知,更反对以情见释知,所以朱熹、郑玄对致知的训解,他都加以反对。他认为,朱熹《四书集注》中所谓知,是知识之知;朱熹的致知,是扩充知识,使达于极点。他对这个解释的质疑是,对于个体来说,知识是否可以扩充达于极点尚在不可知之列。此姑勿论,而知识之多寡对于正心诚意是否能有所影响,这是大有疑问的。这个疑问与王阳明在龙场之时质疑朱熹“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可格?纵格得草木,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完全一致。对郑玄格物之训:“由善恶之知,来善恶之事,事缘人所好来”,熊十力径斥之为以情见释知,为学不见本原。[1] (P663)熊十力还认为,他所谓良知,与佛家所谓“性智”是同一层次的概念。性智不同于理智,性智是心之本体。对此本体的识认,只能是“亲冥”。所谓亲冥,即性智之内证,性智之自了自见。它是能证与所证的统一,而实不可分能所。它超绝对待,独立无匹。自证自知后涵养不失,是良知本体流行的功夫和过程,即致良知。致良知对证量此本体者来说,是“逆觉体证”;对本体自身来说,是开显和朗现,它对具体的格物活动表现为纵贯中的横摄。熊十力用王阳明的致良知去解释《大学》的致知,就是要使本体成为价值性的实体,成为体证的对象,以免沦落为纯知识的对象,失去价值的范导。
熊十力虽然不同意朱熹对致知的训解,但对朱熹格物之说,则表赞成之意。他说:“愚谓物者事物,格物者即物穷理。朱子《补传》之作,实因经文有缺而后为之,非以私意妄增也。夫经言‘致知在格物’者,言已致其知矣,不可以识得本体,便耽虚溺寂,而至于绝物;亡缘反照,而归于反知。此经之所以结归于‘在格物’也。”[1] (P668)又说:“如只言致良知,即存养其虚明之本体,而不务格物;不复扩充本体之明,以开发世谛知识,则有二氏沦虚溺寂之弊,何可施于天下国家而致修齐治平之功哉?故格物之说,唯朱子实得其旨,断乎不容疑也。”[1] (P670)他认为,朱熹的格物穷理之说,有使人广泛地充分地获取知识之意,有非常强的重视知识的意向。这种意向不仅反对老庄的绝圣弃智和佛家的耽空守寂,而且作为一种知识传统,下启近代以来重视实证科学的风气,所以他说:“余以为致知之说,阳明无可易;格物之义,宜酌采朱子。”[1] (P667)认为朱熹格物之义,在重视事物的规律、理则上,在重视知识的积累与互相发明上,可以说“与西洋哲学遥契”。
熊十力反对王阳明训格为“正”,训物为“事”,格物为“正念头”,认为太偏于内,于知识的获取有忽视之嫌。他主张“格物”取古义:释格为“量度”,物为具体事物。格物即对具体事物进行量度、实测、研究。格物活动可概括为朱熹所谓“即物而穷其理”。这样,熊十力的“格物致知”,“致知”取阳明义,“格物”取朱熹义,格物致知实际上是纵贯中的横摄。熊十力自认为这样的训解既保住了价值根源,又不废知识;既不弃大贤阳明,又不弃大贤朱子;既继承传统,又加入近代科学的新义,是一种比较全面的训释。关于这一点,他有很鲜明的表述,他说:“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如不能致良知,而言即物穷理,则是徒事知识,而失却头脑,谓之支离可也。今已识得良知本体,而有致之之功,则头脑已得,于是而依本体之明去量度事物,悉得其理。则一切知识,即是良知之发用,何至有支离之患哉?”[1] (P668)
他所谓物,可谓含古今中外一切事物,格物即致知中的格物,故即良知之发用:“如事亲而量度冬温夏凊与晨昏定省之宜,此格物也,即良知之发用也。入科学实验室,而量度物象所起变化,是否合于吾之所设臆,此格物也,即良知之发用也。当暑而量舍裘,当寒而量舍葛,当民权蹂躏而量度革命,当强敌侵凌而量度抵抗,此格物也。皆良知之发用也。总之,以致知立本而从事格物,则一切知识莫非良知之妙用。”[1] (P669)而“良知之妙用”即良知之应物现形,随缘做主,也就是良知在流行过程中,遇物感而应,物之形色即现于良知前,为良知所量度,而后为良知的一部分。良知随所遇而量度,随量度而收摄,随收摄而为此形物的主宰,随主宰而赋良知本体之明于形物。这一过程即“致知在格物”。
熊十力这些思想,实际上已经有后来牟宗三“两层存有论”、“纵贯之中有横摄”、“良知坎陷”诸说的端萌。牟宗三就是沿着这些思路或说精神方向而有开发,有邃密。熊十力自佛学入,对本体的描述孱入了《易传》与王阳明、王船山的思想;对现象界的描述,主要取义于唯识学和朱子学。而牟宗三则收摄此诸家,一归于康德哲学,以现象与物自身分两界,以智的直觉为连通二者的桥梁。智的直觉熊十力本想于量论详细发挥,但量论迄未作出。牟宗三则对知识论有系统开发,遂驾其师之说而上之。再则,熊十力非常重视《大学》,把它视为六经的总括。将其中的格物,置于致知的统领之下,两无偏弊。他尝说:“《大学》总括六经要旨,而注重格物。则虽以涵养本体为宗极,而于发展人类之理性或知识,固未尝忽视也。经学毕竟可以融摄科学,元不相忤。人类如只注重科学知识,而不求尽性,则将丧其生命。”[1] (P673)牟宗三则看重《论语》、《孟子》、《中庸》、《易传》,视《大学》所讲仅为“认知的横摄”,于正宗儒家学说为歧出。从中可以看出,二人对《大学》的诠释完全不同。
牟宗三对于熊十力以上以阳明义释致知,以朱子义释格物,合朱子阳明为一解释“格物致知”不惬于心,他在给熊十力的信中直接表明了这一质疑:“后面讲《大学》,宗三微有不甚了然者,即‘致知在格物’一语。据吾师所演释,似不甚顺妥。致知之知,若取阳明义,指良知(本心)言,而‘格物’一词,复因顾及知识,取朱子义。今细按‘致知在格物’一语,则朱王二义实难接头。”[2] (P307)他认为,《大学》“致知在格物”一语,不能取朱熹阳明二义合释,因为二义正相反对。依朱熹,格物为“即物而穷其理”,只成就知识,与诚意、正心等价值性活动无有若何必然关系。朱熹义于“物格而后知至”所讲甚为顺适,然知至而意不必诚。王阳明即看出此点,将朱熹向外功夫全转为内,以知为良知,物为意之所在,格物为正念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一时并了。这样一转,格物与正心、诚意步步皆有关联。
此处牟宗三的质疑,直从王阳明致良知的根本意思入手,将朱熹的格物完全解释成向外求取知识,与正心诚意等价值活动无关涉。牟宗三的这种理解,并未将熊十力所阐明的“致良知”是良知本体流行,遇所收摄的外物即变化之、赋明之、开显之、润泽之的意思理解透彻,只将致良知视为一实然的伦理性活动,如去除习心遮蔽,诚意正心等。熊十力已经将阳明的良知本体论化了、形上学化了,而牟宗三此时仍将阳明学视为一横向的伦理学说,而非合伦理与知识为一的“纵中有横”。此时还没有他后来在《心体与性体》中那样将宋明理学的真精神理解为一纵贯的“逆觉体证”。他后来将具体事物解释为本体的朗现、伸展、遍润,可以说就是吸收了熊十力以上“格物致知是良知本心体万物而流通无阂”、“良知之明周运乎事物而度量之”、“良知之应物现形,随缘做主,是则良知自然妙用”诸义,加上周敦颐、张载、程颢、陆九渊等关于宇宙本体的思想而体证、融释、推绎,成就一宏阔精深的本体论。此中熊十力的影响昭然不可没。
三、在致知方向上的不同看法
牟宗三与熊十力在致知格物上的分歧,还表现在对致知功夫究竟是向内义为主还是向外义为主这一点理解不同。牟宗三根据王阳明,认为致良知就是回复良知,因为良知虽是本心,其体为至善,但良知必为私欲习气所遮蔽,故须回复,复的功夫即格物,因此格物即诚意正心。此即向内功夫。牟宗三同时认为,阳明之致良知,也有向外推扩的意思,如“致吾心良知所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答顾东桥》,《传习录》中),说的就是向外推扩之意。牟宗三虽然承认阳明的致知内外二义皆有,但认为究以向内的“回复”义为主,并认为熊十力以上解释全为向外之推扩义,意亦有偏。他在给熊十力的信中说:“阳明之‘致’,究其何义,并未表明清楚。然无论如何,总持言之,内向、外向义虽有别,次序亦异,而总不冲突,惟关键在‘复’。立言之着重处亦在‘复’,而外向则是其委也。”[2] (P308)熊十力并不以牟宗三致知之“致”字为内向之复为然,亦不以外向之推扩义为偏,他在复信中当即反驳,认为牟宗三以上质疑“推求太过”。
王阳明的致良知,其主要意思究竟是向外的推扩还是向内的回复,这是阳明学的一个重要问题。按之阳明著作,可以说二义都是致良知的重要义项,但其侧重有早晚年之不同。阳明自龙场确立心学宗旨后,其学有几次变化。黄宗羲据阳明高弟王龙溪所述,将阳明一生学术定为六变,龙场之后有三变(注:参见黄宗羲:《明儒学案·姚江学案》。)。我们认为,阳明学术确有一个从前期的兢兢业业,亹亹翼翼,侧重内敛扩充,到晚年境界高迈,本领阔大,侧重于向外推扩的变化。特别是擒宸濠,处忠、泰之变,在江西揭“致良知”三字宗旨为教法后,向外推扩是其致良知的主要意思。晚年服父丧之后的居越讲学,向外推扩的意思更加增多。可以这样说,阳明学说以揭“致良知”三字宗旨为界,之前多向内回复义,之后多向外推扩义。因晚年内敛积累渐多,功夫熟化,须推致良知于实事上之故。此义学界说之已多,本不必详述。但于熊牟师弟间关于致知的辩争有关涉,故在此重提并非无意义。
牟宗三以向内之复字为重,说明他此时学问尚未广,(注:这一点牟宗三并不讳言,他曾对学生说:“1949、1950年我刚到台湾的时候,就写了一本《王阳明致良知教》的小册子。那时我对王学与其他理学家间的关系并不很清楚。”并说:“至于我五十岁以前写的那些书,你们不要看。”见牟宗三著:《中国哲学十九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84—385页。) 对阳明的理解,还侧重于伦理学的正心诚意。而熊十力此时已从佛家营垒中杀出,融大《易》、王阳明、王船山与佛学空有二宗为一的本体论已告成。这时的本体已有流行不息、健进不已、随所遇而收摄的纵贯中之横摄义。他的重视向外扩充是必然的。本体如此,本心亦如此。所以此时熊十力所谓本心,着重的是向外推扩义:“夫心无内外可分也,而语夫知的作用,则心有反缘用焉,似不妨说为内向;有外缘用焉,似不妨说为外向。但内外二名,要是量论上权宜设施,实则境不离心独在,虽假说外缘,毕竟无所谓外。且反缘时,知体炯然无系;外缘时,知体亦炯然无系。知体恒自炯然,无定在,而实无所不在,何可横截内外而疑其内向外向之用有所偏乎?”[2] (P309)此中反缘指本体之自证自知,外缘指心攀援经验之物而对之起了别。反缘外缘皆就知识论上分内外,心本体则恒炯然而明,流行无系,无所不在。由此纯然大明、时时流行、时时推扩之本体而观,牟宗三所谓致良知主要为向内之回复义实不谛当。因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四者,“诚意”、“正心”之向内回复的意思最为显明,但所谓正心,实即诚意;而诚意之实下手处,又在“吾人只依此内在固有之知而推扩去。知是大本,推扩则大本方立定。大本既定,则私欲不得潜滋,而意无不诚矣。”[2] (P310)
诚意是推致自己的良知而得,此不同于具体的为善去恶。这表示熊十力赞赏现成良知派的决澜冲堤之法:本体流行所至,具体的善恶皆如洪炉点雪,触之即化,任良知流行,即是功夫,不必再做具体的善恶意念之搏战。这是熊十力在明定本体流行扩充之后在正心诚意上的基本观点,这个功夫方向决定了他在致知方向上必然主向外推扩义。
而在向外推扩义上,熊十力为了保住其中的扩充知识义,又对推扩的本体——良知做了更进一步的开掘,这就是,他将良知具体展开为本有与继承、先天与后天二个层面。前者他叫做法尔道理,指良知本体自然如此,无所待而然。后者他叫做继成道理,指良知用后天功夫去除私欲习气,实现其本体,丰富其本体。就法尔道理言,它自然推扩:“本体无待,法尔圆成,似不待推扩。然所谓圆成者,言其备万理,含万化。易言之,即具有无限的可能。非谓其为一兀然坚住的物事也。故其显为大用,生生化化,无有穷竭,即时时在推扩之中。”[2] (P310)这个法尔自在者,不是佛老所谓无为无造者,而是《诗经》中“维天之命,於穆不已”这样恒健动不息、精进不已的本体,故永远是推扩的、创进的。就继成道理言,本体在人表现为本心,本心只在可能性上具有无限的知。必须在实践上保住其本体,因其明而推扩之,使它日益盛大,抽象的变为具体,可能的变为现实,在推扩中完成保任。“保任自是推扩中事,非可离推扩而别言保任也。推扩者,即依本体之明而推扩之耳。”[2] (P312)
可见无论本体、功夫皆推扩,本体所至即是功夫。本体是在健动流行中来充实、来摄聚。专恃保任而不事推扩,则失去本体健动不息之意。由于此,熊十力反对程明道“识得仁体,以诚敬存之。不须防检,不须穷索”的功夫要领,斥之为道家之内守,并批评宋明理学中奉守明道《识仁篇》者只有保任,而无推扩,有偏于内之弊:“充其保任之功到极好处,终近于守寂,而失其固有活跃开辟的天性。其下流归于萎靡不振,而百弊生。宋明以来贤儒之鲜有大造于世运,亦由儒学多失其真故也。”[2] (P313)从这里可以看出,熊十力从佛家归宗大《易》之后,反戈一击,以《周易》的健动开辟来批评佛道的内敛会聚,其本体之意指、涵蕴是很清楚的,希图以此来纠正宋明理学偏于内、偏于静的用心是很明显的。
熊十力更以本体之健动推扩义来批评佛道本体之空寂,他在复牟宗三的信中谈到“诚意”时说:“阳明诗云:‘而今说与真头面,只是良知更莫疑。’如此觌体承当,得未曾有,然自识得此大本已,必须依从他推扩去,如渊泉时出不竭才是。本体良知原是推扩不容已,功夫亦只是推扩不容已,即功夫即本体,焉有现成具足之一物可容拘隘而坚持之乎?佛家说到知体,喻如大圆镜,此便无有推扩。吾谓以镜喻知体,不如以嘉谷种子喻之为适当。须知一棵谷种原具备有芽、干、枝、叶、花、实等等无限的可能,非如镜之为一现成而无所推扩之物也。后儒言知体皆受二氏影响,故其功夫偏于单提保任,其去经言致知之推扩义盖甚远。”[2] (P313)此处头面、大本皆良知,推扩之即致良知,本体、功夫皆是此。他在批评老庄道家时也说:“夫良知非死体也,其推扩不容已,而良知始通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故《易》言‘智周万物’,正是良知推扩不容已。若老庄之反知主义(自注:老子“绝圣弃智”,其所云“圣”、“智”,即就知识言之,非吾所谓“智慧”之“智”也。庄子亦反知),将守其孤明,而不与天地外物相流通,是障遏良知之大用,不可以为道也。故经言‘致知在格物’,正显良知体万物而流通无阂之妙。”[2] (P315)认为道家违反了良知在健动推扩中收摄知识之精义,使良知成为一孤明自闭之体。可以说,熊十力的本体之推扩不已,是《周易》的健动不已,《诗经》的“於穆不已”、“纯亦不已”,和王阳明的“良知渊泉而时出”等意思熔铸为一。他说读他的书须通《周易》、王阳明、王船山,非虚骄自大之语。
熊十力这些思想,亦为后来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中所立为正宗儒家标准的道体、性体、命体、天体、诚体、神体、仁体通一无二,其本质为即存有即活动等思想所本。其中的健动义、推扩义、开辟义等,是熊牟本体论的核心。在本体的推扩流行中收摄知识,既保证本体的健动不息、流行不滞,又保证其充实丰满,非一抽象的、光板的本体,这是牟宗三后来所着重阐发的,并且因为加入了西方的逻辑学和知识论因而更加阔大、邃密。只是牟宗三此时尚无此识度。
其实,此时牟宗三也并非只承认良知的内向义,他也承认良知的外向义,认为向内回复与向外推扩是一个整体的来与往。但他认为致良知是向内回复为主,并批评熊十力之主外向义与阳明原意不符。他在给熊十力的信中说:“若揆之‘致知在格物’,则内向义为顺;吾师所讲者,则似为外向之推扩义。致知之知,既是良知或本心,则‘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一语,便是内向之最高峰。是则此语中之‘致知’,以复义为重。然本体非只是虚寂,亦不可以识得本体,便耽虚溺寂,而至于绝物;亡缘反照,而归于反知。此经之结归于‘致知在格物’也。吾师训‘格’为‘量度’。下举诸例,如事亲,如入科学实验室等,皆明本良知以量度事物。凡量度事物,皆为良知之发用,是则‘致知在格物’一语中之‘致’字,全成外向之推扩义,既与前语中之致知不相洽,而按之经文,宗三总觉其不顺妥。”[2] (P308)这里我们发现,牟宗三之坚持内向为主,表明他此时理解的良知,还只是本心,还没有熊十力那样打通天道与人心,天道即人心,两者一而不二这样的识度。他谨守阳明本义,不欲过度诠释,所以他理解的良知只是本心,致良知只是扩充此、纯净此本心。这与熊十力合天道人心为一,天道在自然运行中充实、丰富、现实化自身之义很不相同。这时牟宗三还没有熊十力这样的识度和境界,他的诠释方式也是不离文本,据原文作合理解释的,还没有后来那样大胆的、创辟的诠释风格,故多处有“按之经文”之说。他后来的一系列著作中对天道性命的阐发,除了方式上更加清脱,更加具有熔多种学养为一炉而有的厚重、恣纵之外,在内容上也相当多地吸收了熊十力的思想。其中一个非常大的突破就是,改变此处以内向的道德心为主的格局,以天道本体即存有即活动的外向义为中心,纵贯中有横摄,道德心上升为天道本心。这时他不是在道德论中处理知识问题,而是在本体论中处理知识问题。因此,知识也就成了本体中的自然含蕴,而不仅是纯净道德本心,提高道德境界的助缘。这一转变,使他的证量层次、境界内容乃至诠释方式等都发生了根本升华。这其中受熊十力的启发、润沃是很明显的。
熊十力在《读经示要》中非常强调知识的重要,也很注意在讲本体论时收摄知识于其中。但这种收摄只是表明了方向,以回应当时十分强劲的实在论、唯物论思潮。但因为他是把知识作为本体的一个方面,以王阳明的致良知为主收摄朱熹的格物而立论,所以知识论在他这里并没有独立的地位。他在《新唯识论》的境论完成以后计划写量论,但始终没有写出来。牟宗三晚年批评熊十力学力不足,主要是针对他在知识论上薄弱这一点。熊十力的贡献在本体论,这一点牟宗三是肯定的,他晚年曾说:“熊先生之生命中是有‘真’者在,这‘真’者就是儒家的本源核心之学。这点抓住了,就可以挺立于世而无愧,俯仰群伦而开学风。这一点是儒家之为儒家之关键,我们就从这点尊敬我们的老师。但他的缺陷我们也应知道。”这个缺陷就是熊十力没有造出知识论。牟宗三还说:“因为熊先生的所得就只有一点,只那一点,一两句话也就够了。一提到儒家大《易》乾元性海,体用不二,熊先生就有无穷的赞叹,好像天下学问都在这里。当然这里有美者存焉,有无尽藏,但无尽藏要十字展开,才能造系统,所以后来写好多书,大体是同语重复。”(注:皆参见《客观的了解与中国文化之再造》,《当代新儒学论文集·总论篇》,台湾文津出版社1991年5月版。) 从牟宗三一生的发展看,这里的批评并无偏激之处。牟宗三后来就是在熊十力缺乏知识论这个问题意识的推动下,在早年的《逻辑典范》的基础上,深入研究西方知识论和康德哲学,写成《认识心之批判》、《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现象与物自身》等,建立起了自己哲学中的知识论系统,弥补了熊十力的不足,将现代新儒学乃至整个现代中国哲学推进了一大步。
结合1944年熊牟的通信,毋宁说,牟宗三当时反对熊十力在格物致知上朱王两家合讲,就是想把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当作回复心体的道德学说,而把朱熹的格物说当成知识论,将这二种学问体系各自独立地进行研究,克服中国古典哲学的浑融性、模糊性,使之成为既广大又精微的近代形态。在迟至二十余年《心体与性体》完成之后,才在二者分别得到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将两者统合起来。这时牟宗三的体系也是以本体论统合知识论的,但这种统合不是指示方向的,不是以知识辅助本体的,更不是为了堵反对者之口不得已而为之的。此时的牟宗三是“十字打开”,纵中有横的,知识论是他全副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牟宗三在整个哲学成就上超过乃师的重要标志。从1944年熊牟师弟关于《读经示要》的通信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两人思想趋向的分歧点。而对照当时的分歧来观照各自晚年的哲学成就,更可以看出其中的补充、转折、递进等等关节。这些关节对中国现代哲学和当代新儒家思想发展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标签:熊十力论文; 牟宗三论文; 儒家论文; 大学论文; 读经示要论文; 易经论文; 读书论文; 宋明理学论文; 国学论文; 朱熹论文; 王阳明论文; 心学论文; 哲学家论文; 致良知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