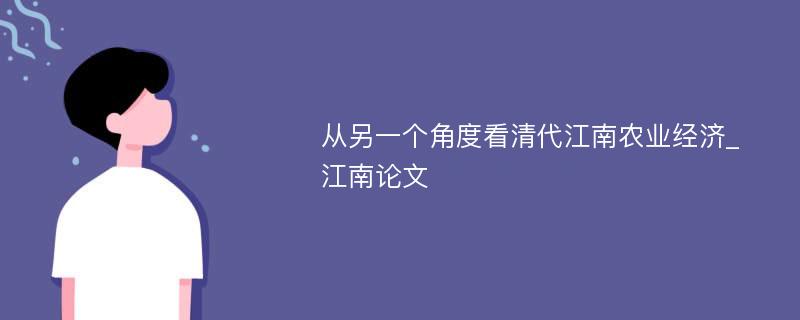
用另一种眼光看清代江南农业经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业经济论文,江南论文,眼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南农业的发展(1620-1850)》
李伯重著,王湘云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重新审视江南经济的学术背景
《江南农业的发展(1620-1850)》一书,是以大量数据为基础的实证性研究,而作者提供的数据和解释,都是为了证明明清江南农业经济走着一条与西欧完全不同的道路。因此,此书看似是一项实证研究,实际上是带有强烈论辩色彩的理论著作。其抨击的对象,就是近年几乎已成为过街老鼠的“西方中心论”。
正如李氏所说,以往对于明清或者说帝制中国晚期经济史的研究,主要存在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而这些观点事实上都主要以江南经验为基础:一种观点是日本学界较早提出的“明清停滞”论和与此相近的西方学界的“中国社会停滞”论,以及我国大陆学者所持的“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论,这种观点的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是以近代西方经济发展为标准去评价帝制晚期的中国经济;另一种观点则为“明清发展”论,一些西方学者称之为“近代早期中国”论,我国大陆学者则大多称做“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这种观点的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是将西欧经验视为中国历史发展必然遵循的模式,并致力于在明清经济中寻找导致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那些因素。在李氏看来,两种观点实质上都是“西欧中心论”,即把西欧经济成长的道路当做中国(以及世界上其他地区)遵循的唯一发展模式。①(2-6页)
上述两种思路和观点,近些年受到反对“西方中心论”的学者们的仔细检视和强烈批评。其中黄宗智和“加州学派”的新看法(在研究旨趣上,“加州学派”与黄宗智颇有相近之处,所以有学者将黄氏归入此派,但他们之间的学术观点是针锋相对的),都引起较大的反响和争论。所谓“加州学派”(Califonia School),系因其中坚人物集中在加州而得名,但它并不是一个封闭的地域性学派,而只是建立在思想倾向相近基础上的松散组合,主要包括彭慕兰、王国斌(R.Bin Wong)、李中清(James Z.Lee)、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金世杰(Jack Goldstone)等人②(209-210、1-2页)。黄宗智和“加州学派”的著作,曾获得多项学术大奖,说明他们确实抓住了学术焦点,站在了学术前沿。
黄宗智考察了中国和西方的学术研究,认为中国学术的主要模式源自马克思的古典理论,而西方学术的主导模式主要源自马尔萨斯和亚当·斯密的理论,但两者明显有许多共同点,均把停滞与前商品化相联系,把近代化等同于商品化,从而形成一种“规范认识”(paradigm)。在他看来,实证研究已向这种规范认识提出挑战:明清确实存在着蓬勃的商品化,但农民的生产仍停留在糊口水平,农村中并没有发生近代式的经济发展。为了说明这些与规范认识赖以建立的英国经验相悖的现象,黄氏提出“过密型增长”和“过密型商品化”的概念,认为明清江南的商品化是由人口对土地的压力推动的,也就是说,农场面积的缩减,迫使农民扩大经济作物经营(尤其是植棉与棉纺织手工业)以增加单位土地面积的产值,然而单位工作日收益却是下降的,“这样的主要由人口压力推动的过密型的商品化,必须区分于推动近代发展的质变性的商品化”③。
黄氏提出新解释模式,是不满意“中国史领域长期借用源自西方经验的模式”,试图“建立中国研究自己的理论体系”。这明显带有反思“西方中心论”的色彩。但在更加激烈地反对“西方中心论”的“加州学派”看来,黄氏对明清经济发展状况的判断是令人无法接受的。弗兰克虽未直接与黄氏对垒,但他的看法明显与黄氏相左。他认为,直到18世纪,基于在工业、农业、运输和贸易方面所拥有的绝对与相对的更大的生产力,中国都在世界经济中处于“核心”地位,而处在世界经济边缘的落后欧洲,只是因为在美洲找到了大量白银,才得以通过参与亚洲内部贸易获取利润,并最终赶上和超过亚洲④。彭慕兰则对黄氏使用的数据和结论直接提出质疑,认为18世纪以前,中国和欧洲人口密集的核心区域有着共同的重要经济特征:商业化,商品、土地与劳动的互相修正,市场驱动的发展,家庭根据经济趋势对其生育和劳动力配置的调整;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因为美洲新大陆的开发和英国煤炭优越的地理位置,终使欧洲和中国出现分道扬镳的“大分流”⑤。李中清、王丰也不同意黄氏关于“中国的人口变化受死亡率变化所决定”以及长时期里江南“一直是维持生存水平收益的小农经济”的看法,认为控制婚内生育、溺婴以及男性独身等这些人口机制相结合,构成了人口与经济反馈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得中国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持续增长,而没有出现马尔萨斯所预料的长期饥荒和死亡率水平⑥。
由于曾在加州访学和讲学,与“加州学派”的学术理念十分相近,李伯重也被视为该学派的中坚人物,《江南农业的发展(1620-1850)》则被认为是“加州学派”的重要著作之一。当然,李氏的学术观点,经历了一个自我反思和否定的过程,才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当黄宗智的新说刚提出时,李氏虽然指出其存在不足之处(如认为黄氏对农民的年劳动生产率及其与工作日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应做进一步分析),但认为“过密型增长”理论“在逻辑上是比较完备的”,也是“符合明清江南史实的”,“可以从明清江南经济史的实证研究中得到印证”;后来随着研究不断深入,李氏发现,尽管“过密型增长”是黄氏“在挑战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占有统治地位的‘西方中心论’时提出的一种新说”,“但是他所得出的结论在实质上与过去的‘西方中心论’的研究结论仍有相同之处”,该理论与1850年前江南历史实际也是不相符合的⑦(63-91页)。尽管并非仅仅针对黄氏,但《江南农业的发展(1620-1850)》的主要论题,实际上构成对黄氏理论的全面反思和辩诘。读者如果将李氏的《江南农业的发展(1620-1850)》与黄氏的《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对照阅读,必将会有更大的收获。
对流行观点的全面颠覆
《江南农业的发展(1620-1850)》共有十章,除第一章导论外,其他九章分为三编。第一编题为“生产要素的变化”,探讨了清代前中期江南农业的物质基础及其变化。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包括劳力、资源、技术和资本,由于前人对资本问题已经做过大量研究,作者只探讨了其他三项因素;此外,作者认为生态环境(尤其是气候)也属于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因而对气候变化也进行了讨论。第二编题为“农业生产的变化”,主要从农业资源利用的合理化、农业生产的集约化、外向型农业的形成等方面,探讨了清代前中期江南农业发展的途径和模式。第三编题为“农业的发展”,通过论证土地产值的增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生态农业的出现和普及,展示了清代前中期江南农业发展的具体成就。在本书中,作者以大量资料和数据为基础,对清代前中期江南农业各个方面的变化,都进行了细致梳理和深度分析,提出了迥异于以往的全新评价。
按照过去流行的观点,明清时期江南农民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甚微、甚至有所下降,当时出现的那些引人注目的变化,如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农产品加工和农家副业发展、农业商品化程度提高等,也是由人口压力和封建剥削推动的。如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认为,清代农产量的增长主要是由集约耕作而来,但单位面积产量并不能与投入的劳动力按同比例增长,因而农民的劳动生产率有所下降;人口增加是导致农业集约化的主要因素之一,在人口压力与封建剥削的驱动下,小农只能从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中找出路,从而加强了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以致愈是手工业发达的地区,农业的经营规模愈小⑧。黄宗智则用“过密化”解释江南的变化,认为明初长江三角洲已出现了人力非常密集的经济,其后人均耕地面积持续下降,而提高作物复种程度已几无余地,只能转向劳动更为密集的经济作物的生产,从而导致商品化的小农经济的扩展,这种商品化主要为榨取剩余及维持生计所推动,因而“主要是过密型增长,而不是真正的发展”⑨。
应该说,许涤新等人与黄宗智的理论预设并不相同:前者相信明清时期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而后者认为明清时期的商品化不会导致向“资本主义转化”。但他们对清代江南农业经济状况的看法却极其相似,共同描绘了一幅阴郁黯淡的图景。李伯重的看法,则与他们完全相反,他描绘的清代江南农业经济图景,洋溢着光辉灿烂的色调。无论是在具体问题还是总体认识方面,李氏都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看法,限于篇幅,这里无法一一罗列,只能列举几个最具颠覆性的新观点:
其一,以前人们认为清代前中期江南农业技术停滞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清代前中期,在传统农业技术的改进与推广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优良水稻品种数目大为增加,牛力的使用普及化,发生了以豆饼使用为核心的“肥料革命”,一年二作制成为主导性的种植制度等,这些进步使得对现有资源的利用变得更加合理,农作变得更加集约。
其二,清代前中期江南并不存在以前人们普遍相信的人口压力。首先,由于存在有效的人口控制机制,江南的人口增长率相对较低,增加的人口中有很多被城市化及农村工业所吸收,以致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在总劳动力中的比重实际上在下降;再者,尽管江南人口密度之高,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也是相当惊人的,但由于江南农民更合理地使用了资源,因此清代前中期耕地与劳动力的生产力都得到了提高。
其三,关于清代前中期江南农业生产率停滞的旧观点毫无根据。无论从土地生产率还是从劳动生产率来观察,清代前中期都是江南农业在1950年代以前的一千年中进步最大的一个阶段,各种作物的亩产量不仅大大高于此前的各个时代,也远远高于1850年以后江南传统农业最繁荣的两个时期(1911-1937、1951-1957)。
其四,家庭农场面积的缩减主要是追求经济合理化的结果,而不是由人口压力造成的。在清代前中期的江南,水稻与春花作物结合的一年二作制是增加耕地亩产量的最佳途径,而在这种种植制度下,“一夫十亩”为最佳经营规模,妇女从事育蚕、缫丝、纺纱、织布比从事大田农作收入更高,可以说,“一年二作”、“人耕十亩”、“男耕女织”三者结合在一起,组成了江南农民家庭经济的最佳模式。
在李氏看来,以往明清经济史研究中影响广泛的那些成说,如“人口压力”说、“技术停滞”说、“劳动生产率下降”说,以及“高水平均衡陷阱”、“过密型增长”等理论模式,其出发点都是西方中心论。在《江南农业的发展(1620-1850)》一书中,李氏运用自己发现的大量新资料,并充分吸收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这些成说进行了全面的批驳。无论是从实证还是理论意义上衡量,本书都是一本价值极高的学术著作。在学风浮躁的当下,本书树立了一种学术研究的典范。
数据和事实的检视
同为“加州学派”的代表性著作,《江南农业的发展(1620-1850)》与《白银资本》、《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以下简称《大分流》)在风格上差异颇大。后两种著作在理论阐述上虽然酣畅淋漓,但由于都是依靠第二、第三手材料建构其理论,不免给人这样的感觉:他们刺中了“西方中心论”的心脏,可惜手持的是银样镴枪头;他们构筑了一座华丽的理论大厦,可惜建造在松软的地基上。在讨论学术标准问题时,李氏曾谈道:“对于一部经济史研究著作,一些经济学家可能会认为最重要的是运用了什么理论,提出了什么模式。至于对所用具体史料的订正,似乎可以说是‘旁枝末节’。但是对于一些历史学家来说,情况可能相反,最重要的是史实的可靠,而理论和模式则是第二位的。”⑩也许,对于《白银资本》、《大分流》这样以挑战成见为宗旨的宏观理论著作,从史实和细节的角度加以挑剔和评价是过于苛刻了。
李氏的情况与弗兰克、彭慕兰大不相同。早在有意识地构筑这套江南经济史理论之前,他就已经在从事扎扎实实的实证研究,他提出的理论模式,是以大量第一手材料和数据为基础的,而且这些材料和数据有许多都是他发掘出来并首先使用的。由于篇幅的限制,《江南农业的发展(1620-1850)》主要是概述了他的研究结论,而无法充分展示他的论证过程,其实他的每个观点都有相应的专题研究论文。在本书序言中,吴承明曾指出,李氏从1982年起,就致力于明清时期江南经济研究,针对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发表了大量专题论文和研究报告,“读者常以其论证之周详和新发掘的与罕见的资料之迭出而叹服”。洵为的确之论。
不过,由于明清时期并不重视经济数据的收集,甚至田地、人口等与赋税直接相关的数据也严重失实,李氏虽然花费大量时间收集、整理和分析相关资料,但相对于他提出的重大理论概括而言,他提供的数据和证据仍给人以薄弱之感。在一篇评论《大分流》的文章中,布伦纳(Robert Brenner)及爱仁民(Christopher Isett)曾评论说,关于明清时期江南的人均粮食消费额、粮食输入量、水稻种植面积并没有进行“复杂运算所需的合格数据”,李伯重的结论“是基于完全不可靠的估算方法之上”,“李实质上最后是在假定他所必须证明的东西”(11)。这种评论或许有些偏激,但即便是与李氏同一阵营的彭慕兰,也感到李氏的数据无法为其论点提供充分证明,他在评论中写道:“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主要的难题将依然是数据问题:李氏对中国经济史的重新解释产生出一个新的假定。这个假定提出得太快,使得我们还不能找到材料来解释各种的疑问。”(12)
以作为李氏理论支柱之一的稻米亩产量为例。文献中保留下来的明清水稻亩产数字,相当零散而且相互歧异,因此现代学者有的认为自明到清亩产量没有变化,有的认为有所提高,也有的认为有所下降。李氏早期也认为明清江南水稻生产中劳动投入虽然明显增加,亩产量却没有提高,黄宗智即曾借助其观点论证“过密化”理论。但后来李氏的观点发生大转变,认为清代江南劳动生产率有大幅提高,而要证明这一点,就必须证明最主要的粮食作物水稻的亩产量有大幅提高。但从那些相互歧异的记载中,显然无法令人信服地得出这种结论,于是李氏不得不另辟蹊径,通过估算稻米消费量的办法估计亩产量。据李氏估计,明清江南的耕地面积均为4500万亩,其中水稻种植面积明代后期为4240万亩、清代中期为4040万亩;稻米消费(包括食米、酿酒用米、稻种、税米)总量,明代后期约为7400万石,清代中期约为11800万石;外米输入量,明代后期可以忽略不计,清代中期约1500万石。因此,明代后期水稻亩产量约为1.7石(7400万石÷4240万亩=1.75石/亩),清代中期约为2.5石[(11800万石-1500万石)÷4040万亩=2.55石/亩],两相比较,清代中期的亩产比明代后期增加了大约47%①(121-113、138页)。
李氏的估算看起来很细密,但其逻辑链条却不够坚实。在上述数字中,只有耕地面积一项是有原始统计数据作根据的。不过,关于明清江南的耕地面积,文献记载的数字前后不一,李氏经过斟酌,决定采用1580-1583年间的统计数字,他认为这次统计是近代以前在中国进行的统计当中最为可靠的,而且为了实行“按亩纳税”,统计的只是实际的耕地亩数,而池塘、沼泽、堤坝都从“耕地”类排除出去。李氏采用的数字是否合理,笔者目前无力加以验证,但可以肯定,他采用这些数字的理由是建立在误解的基础上:其一,他采自万历《大明会典》的数字,根本就不是1580-1583年间的统计数字,该书明确说明此系万历六年(1578)实在田土,此时江南清丈尚未展开,江南的清丈结果是万历十年(1582)才奏报朝廷的;其二,应天巡抚孙光祜奏报江南11府州清丈结果时,明言“田地山塘”共45万多顷(13),显然并未将池塘之类排除;其三,朝廷颁布的清丈条例要求“额失者丈,全者免”,江南是否认真进行了履亩丈量也还需要进一步研究(14)(63-65页),“最为可靠”之说缺乏根据。
还有一些数字,几乎完全没有可资参考的原始统计资料,李氏只能根据各种零散记载,大胆作出猜测。与其他学者的同类估计相比,往往存在很大差距。比如,他基于一系列假设估算出来的18世纪前期江南的豆饼使用量,就遭到黄宗智强有力的质疑(15)(154页)。再如,李氏认为明代后期江南输入米可以忽略不计,而吴承明则估计可能要输入“几百万石”(16)(124页)。至于清代江南输入米数,更是众说纷纭,甚至李氏自己在不同场合也有不同说法。本书采用的稻米输入数字,是每年1500万石,但李氏后来又觉得此数过低,认为应在2400-3200万石之间(17)(348-349页)。余也非、闵宗殿主张清代中期江南水稻亩产量停留在2石的水平,李氏对此表示反对,因为基于他对江南稻米消费量的估算,如果亩产2石,“即使有1500万石的输入,缺口仍达2300万石之多”①(138页)。但倘若输入量真的达到了3200万石,则缺口就降到600万石了。由此看来,李氏对明代后期和清代中期稻米亩产量的估计,是建立在环环相扣的多重假设基础上的,只要其中一个数据偏差较大,得出的结果就可能背离实情。不少学者对李氏的估计表示怀疑,并非吹毛求疵。相信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李氏会提出更有说服力的新证据。
除数据问题外,李氏对一些事实的陈述,似乎也存在不一致之处。比如,本书在讨论技术问题时,将牛耕的普遍使用视为清代江南农业技术进步的重要表现,认为唐代以来牛耕变得重要起来,但在明代,牛耕逐渐被人耕替代;而到了清代,尽管种植面积缩小到“人耕十亩”,牛耕却出人意料地“在江南再次变得普遍”,“牛的饲养相当普遍并成为农户的重要财产”,“牛力的使用在清代前中期已很普及,这一点十分重要”①(50-53页)。但在后面讨论水稻生产中的资本投入时,又认为“明清江南大多数农户不养牛,故此项投资可略去不计”①(93页)。在《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中,作者对江南畜力匮乏有更详细的说明:“虽然江南各地城乡都有畜牛者,但总的来说,畜牛并不普遍……而且,畜牛少的现象似乎还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加剧。”“本地养牛不多,输入数量又甚微,因而牛在明清江南成为一种稀缺之物。”作者还分析说:“导致明清江南牛紧缺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由于各种条件,江南养牛的费用太高,一般人家承担不起,只好不养……此外,明清江南地狭人稠,寸土必耕,早已没有天然牧场。如饲牛稍多,青草来源又是一个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江南养牛减少的趋势难以扭转。”(17)(278-280页)对照两书的论述,不知明清江南养牛是“相当普遍”还是“并不普遍”,是逐渐普及还是日益减少。
时段和范围的局限
近年来,在反对“西方中心论”和“近代至上论”的浪潮中,近代以前的江南经济得到越来越高的评价,李氏就是代表性学者之一。李氏的评价是如此之高,以致彭慕兰也感到惊讶,指出李氏的观点虽然与“加州学派”非常接近,“但是在某些方面,他甚至比‘加州学派’的学者走得还要远:尽管大多数‘加州学派’的学者认为到了18世纪,经济增长(或者至少是人均经济增长)在三角洲地区已经开始缓慢下来,但是李氏在这两本书中却认为(尽管此后并不总是这样)江南地区的基本增长动力在中国19世纪中叶的大灾难来临前并没有变化。”(12)即使李氏的评估是恰当的,也不能说明由“一年二作”、“人耕十亩”和“男耕女织”三者结合组成的“最佳模式”不存在任何缺陷和问题。在批驳“西方中心论”时,李氏指出,明清中国经济与近代早期西欧经济之间存在差异,“并不能说明中国不能沿着自己的道路出现经济近代化”①(178页)。但另一方面,李氏描绘的“最佳模式”,不可能有无限的发展潜力,至少李氏没有向我们充分证明其无限发展的可能性。相反,从李氏的论述中,笔者感到,到19世纪中叶,这种模式已达到其发展的极限。在《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中,李氏还断言,明清江南经济发展属于“斯密型成长”,由于缺乏煤铁资源,不可能出现近代工业化。无论在农业还是工业中,几乎都看不到出现结构性根本转变的迹象和动力,江南农业如何避免进入“高水平均衡陷阱”或“过密型增长”状态?中国将沿着怎样的道路出现经济近代化?
在时段上,李氏的实证研究以1850年为下限;但李氏的理论视野,却并未局限于此。对于1850-1949年间的情况,他也略有涉及,认为太平天国战争之后,“江南经济状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与过去在许多方面已大不相同了”①(5页)。从他零散的论述中,可以看出近代江南工业和农业出现了相逆的变化:一方面,1850年以前江南农业的发展,“使得江南比中国其他地区更易于实现工业化,到1930年代,除日本,江南变成了东亚地区近[现]代工业化最为成功的地区”①(15页);另一方面,“农民家庭经济‘三位一体’模式的瓦解,事实上是近代工业的发展所致,因为作为这种经济的三大支柱之一的农村纺织业遭到了近代工业的致命打击”①(170页)。对于1949-1979年间的情况,他同意黄宗智的看法,认为“过密型增长”理论“是研究1949年以后江南农业经济的变化的一个关键”①(179页)。但对于1979年后江南突破“过密型增长”的机制,他却不能接受黄氏的见解。黄氏认为,1979年后的发展,是因为劳动力被吸引到农村工业,这些工业尽管大部分位于农村,但在技术装备和管理方式上都属于源于西方的近代工业,因此性质上与传统的农村工业已完全不同。李氏认为,黄氏的看法“与过去的‘江南停滞’论颇为类似,亦即假若没有近代西方及其技术到来,这种停滞就会永久不变”①(179页)。李氏自己的看法是:“1979年开始的经济改革之后,江南农业在很大程度上又回复到1850年以前的形式。”①(15页)“今日江南农业和农村经济现代化中的主要传统因素大多源于清代前中期,因此若没有这些早些时期的因素,便很难想象会有今日江南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现代化。”①(195页)
尽管李氏对各时段都有所论述,但读者很难自己串连成一条完整的理论链条,而且不免有些疑问,比如:1850-1979年间的江南农业史,只是打断正常历史进程的一段插曲吗?如果没有这段插曲,中国将沿着“斯密型成长”的道路实现经济起飞吗?只要回复到1850年以前的经营模式,不需要任何西方技术和近代工业,就可以使江南农业经济“去过密化”,导致1979年以来出现的巨大变化吗?期望李氏也能像黄宗智那样,对明清以至现在的江南农业史作一长时段的、通贯性的分析,这样或许可以使他的新理论变得更加丰富,更有解释力。
此外,黄宗智在研究农业和农村发展问题时,除生产力之外,还综合考虑了生态环境、国家政权、村社结构、阶级差别等因素的影响和作用。但李氏在本书以及其他论著中,则主要将研究范围局限在生产力(包括技术、资源利用、生产率等)方面。这样做并非没有理由,正如李氏所指出的,我国以前的经济史研究,主要集中在生产关系方面,带有强烈的“唯生产关系”色彩,以致生产力研究十分薄弱,成了一部“残缺不全的经济史”。但问题是,如果作者只停留在实证研究层面,他当然可以置生产关系于不顾;但如果想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炼出一个通贯性的理论模式,就不能将生产关系排除在外。在明清那样的社会里,很难设想国家权力、赋役制度、土地关系等因素对经济发展毫无影响。为了避免“炒冷饭”,作者可以不去研究这些问题,但在建构经济发展理论时,却不能忽视这些问题。完全撇开生产关系的经济史,恐怕也是一部“残缺不全的经济史”。
如对本文有任何评论或补充
请发信至chinabookreview@163.com
或登录www.cbr.org.cn
注释:
①李伯重:《江南农业的发展(1620-1850)》。
②参龙登高《江南市场史——十一至十九世纪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吴二华《“加州学派”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现代中国学的范式转换》,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
③参黄宗智《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1期;《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
④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高寿仙:《真实与虚幻:全球视野中的近代早期世界经济图景——对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的几点反思》,《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1期;于沛主编《全球化和全球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⑤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史建云:《重新审视中西比较史:〈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述评》,《近代史研究》2003年2期。
⑥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三联书店,2000。
⑦参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
⑧参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85)第一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三章第一节、第六章第一节。
⑨参黄宗智《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第一章、第十五章。
⑩李伯重:《论学术与学术标准》,《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3期。
(11) Robert Brenner,Christopher Isett,"England 's Divergence from China's Yangzi Delta:Property Relations,Microeconomics,and Patterns of Development"(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ume 61,Number 2,May 2002).引自读与思网站(www.readthink.xilubbs.com)转发的张家炎的汉译本《英格兰与中国长江三角洲的分岔:财产关系、微观经济学与发展型式》。
(12)彭慕兰:《评李伯重著〈江南的农业发展,1620-1850〉与〈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
(13)《明神宗实录》第126卷,万历十年七月辛酉条。
(14)参何炳棣《中国古今土地数字的考释和评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15)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岔: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研究》2002年4期。
(16)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三联书店,2001。
(17)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
标签:江南论文; 经济论文; 农业经济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黄宗智论文; 明清论文; 经济学论文; 大分流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