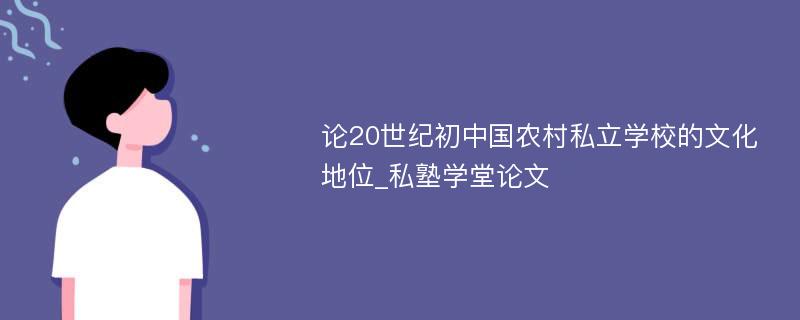
论20世纪初叶中国乡间私塾的文化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初叶论文,私塾论文,乡间论文,中国论文,地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私塾,是一种由民间个体设立的承担着中华民族文化传承重任的基层教育机构。从春秋战国私学诞生到19世纪末,它一直是被历代王朝承认并倡导发展的一种教育组织。从1862年中国第一所官办的新学教育机构——同文馆创立以来,晚清长达五十年的教育革新始终没有触动乡村社会这种历史悠久的、占统治地位的私塾教育模式。
清末学制改革后,在政府强有力的推动下,新式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在乡村社会纷纷涌现,打破了千年以来以私塾为中心的传统教育模式。代表新文化的新式学校以政府为后盾,不断地向乡村社会渗入,而代表传统旧文化的私塾在百姓的支持下挣扎生存,并回击来自新学的“挑战”,两者交锋对垒,形成了别具特色的新旧并存的二元教育模式。在这种新旧对峙的二元教育结构中,乡间私塾以其特有的灵活性和乡土适应性位居乡间文化的霸主地位。乡间私塾不仅在数量上超过了乡村学校,而且在社会功能上仍然是社区的文化活动中心,并更显突出。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迟迟没有走上正轨,始终带有新旧杂陈的过渡性特征,其中乡村教育的二元结构和滞后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以往关于近代教育史的著作大多将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过程简单化、片面化,在传统—现代的二元模式下,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过程往往被看成是以西方科学知识为主的新教育取代传统的旧教育的过程,一个新式学校建立、扩展的过程。于是,传统作为一种被动的、停滞的一方,束手待毙,整个现代化过程就可以被简化为现代性征服传统、大获全胜的历史。而历史上更有生气的一面,即传统和地方社会对现代性的反抗、调适、接纳以及创新则被忽视了。因此,本文主要从数量和社会功能两方面粗略考察20世纪初叶私塾在中国乡村社区的社会地位,以期能为更全面地认识当时的乡村社会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
清末民初,私塾在乡间很普遍,几乎无村不有,大的村庄更有四五处之多,其分布之广,数目之众,在所有乡村社会教育机构中占绝对多数。以河北省为例,据1907年直隶提学司的调查,“各府州县官私两等小学虽已设立,而与私塾比较尚不敌其十分之一”[1](p.515)。1928年,河北82县共计有私塾6277所,男女塾生72144人,平均每县有私塾76所,塾生880人。1930年,河南郑县“全县公私立学校共有94处,而私塾则有285处”。江苏省苏属地区宣统元年(1909)底,共有新式小学校200余所,学生37000余人,而私塾则达7000余所,改良者仅千余所。时至1936年,江苏扬州私塾与学校数量比例大概10:1 [2](p.165)。1908年,山东省有官私两等小学105处,初等小学2644处,两种合计2709处,而私塾则有7405处,是全省新式小学的2倍以上(注:详见《抚院札据提学司逐件答复折行局文并折》,载《山东咨议局会议第一期报告书:下册·学务》。转引自郑起东《近代华北的乡村教育》,载王先明、郭卫民主编的《乡村社会文化与权利结构的变迁》,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9页。)。1910年,山东提学司曾下令“私塾一律改为学堂”,但到年底,仅山东寿光县尚有私塾599处,塾生7626人[3](p.380)。清末临淄县境有私塾400余处,至1916年,该县境内尚有私塾217处,1920年仍有180余处[4](p.419)。1921年,广东省私塾约2100处,生徒数约40万人,广州市内私塾共1100有奇,就学于私塾者,数倍于学校[5](p.269)。1929年,黑龙江省富锦县小学校仅35处,而私塾却有52处。1933年,江西省南昌、新建、进贤、清江等26县共有私塾6670所,学童101813人[6](p.262),平均每县有私塾257所,学童3916人。湖北省1935年人小学读书的儿童有24万余人,而入私塾者高达30万人[6](p.264)。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1935年公布的数字,当时私塾总数约占全国小学校总数的1/3,塾师数约占全国小学教职员数的1/6,塾生数约占全国小学生数的1/8(见表1)。
从教育部的统计数字来看,当时全国范围内私塾与新式小学比例为1:3,但是,我们绝对不能据此就认为,在广阔的乡村社会新式学校已经占有绝对优势,原因有三:
表1 1935年全国私塾概况表
省市 私塾数
塾师数
学生数
江苏省
24259
24299 436647
浙江省4609 4639
88360
江西省2652
2658 38957
福建省3018 3167
55944
广东省6109
6440
143703
广西省651
651
13047
湖北省6656 6680 134418
四川省
13924
14044
246874
贵州省1480
1481 24673
云南省869
872
10585
河北省4287 4313 65520
河南省8952
8952
152219
山东省3588 3588
40211
山西省628 628
9111
甘肃省1411
1411
34305
宁夏省11
11206
绥远省333
333
5663
察哈尔省
127
127
2016
青海省8
8
203
安徽省
14388
14422 188935
陕西省1348
1355
25118
南京市577
580
14645
上海市235
239
5669
北平市481
488
10527
青岛市40
41491
天津市386
386
8967
合计
101027 101813
1757014
*资料来源:乔启明《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298页。
其一,虽然在清末民初的教育改革中受益最大的是普通教育,特别是小学教育[7],新学教育推行之后,废科举、兴学堂的近代文明新风也吹入了广大的乡村腹地,单就乡村新学教育机构的数量来说,增加颇为迅速。但是,还应该明确一点,清末民初新式学校在城乡间的分布是极不平衡的,新式学堂主要集中在城市社区,在乡村社会只是零星点缀而已。以民国19年(1930)为例,全国34省市小学幼稚园的平均密度为每一千平方里9.6所,密度最大者为上海、北平、青岛、威海、南京这几座大城市,内陆省份只有几分之一、几十分之一甚至几百分之一(见表2)。
表2 1930年全国各省市小学幼稚园密度比较表
面积 平均每一千平方里
省市 小学幼稚园数
等级
(平方米)内之学校数
上海市
2680
792
295.5
1
北平市
2100
261
124.2
2
青岛市
1600
153
95.6
3
威海卫
2200
209
95.0
4
南京市
1800
155
86.1
5
山东省
540619
19932
55.3
6
河北省
538894 27420
50.9
7
山西省
470000
22959
48.8
8
浙江省
328140 12424
37.1
9
湖南省
622853
23112
35.6
10
河南省
520640 18652
35.1
11
广东省
665905
18085 27.1
12
江苏省
366574
8346
22.7
13
四川省
1177930 22597
19.2
14
广西省
655797
10702 16.3
15
陕西省
564865
8481
15.0
16
江西省
603447
6755
11.0
17
安徽省
405171
4385
10.7
18
辽宁省
970000
9228 9.5 19
湖北省
589116
4080
6.9 20
云南省
1137000
7410
6.5 21
福建省
478340
3080
6.4 22
贵州省 556800
1983
3.5 23
察哈尔
652630
2027 3.2 24
吉林省
1010500
2037
2.0 25
热河省
400000
808
2.0 26
甘肃省
1325836
1899 1.4 27
黑龙江省 1355200
1649 1.2 28
宁夏省
400000
208
0.5 29
绥远省
663700
243
0.3 30
青海省
2500000
550
0.2 31
西康省
1120031
70 0.06
32
新疆省 5364800
148
0.02
33
总计
25995168 2508409.6
*资料来源:[日]多贺科五郎《近人中国教育史料:民国编(中)》,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年版,第868页。
由上表可见,学校呈城市密集、内陆乡村稀疏的分布状态。另外,从一些零星的统计数字也能看出,广大乡村社会小学教育仍未普及,许多村庄甚至尚未设立学校。以河北省为例,有学者统计,到1928年为止,大约有1/4的村社尚未设立小学,有些县份如南皮、易县、东明、长垣等甚至高达70%以上[8](P.179)1932年,保定地区“全境四五百村,而未设立学校之村庄,竟达十分之三四,女学尤寥若晨星”[9]。如山东禹城,“村庄九百九十余处,学校只有一百八十余处,合五个村庄有一学校”[10]。山东泰安为一等县治,“面积辽阔,土质肥沃,平津铁路纵贯县境,交通极便,人口八十万有余,村庄一千七百三十三,民俗开通,得各县先,教育事业,向颇发达”,然而该县在1931年只有学校575处,合3村才有一处学校[11](p.375)。有人估计,清末民初中国共有乡村10万,村落100万(注:据世界著名农业经济学家白德菲博士(Dr L.Butterfield)1922年来华调查所得,中国当时至少有乡村10万,村落100万。陶行知先生估计,中国当时有一百万个乡村(见陶行知《中国教育改造(重版)》,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1页)。梁漱溟先生估计全国有“九数十万农村”(见《梁漱溟全集(四)》,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7页)。),以此计算,时至1922年,全国中小学校共178847所,平均每6村才有一所学校。至1931年,全国中小学校共262889所,平均每4村才有一所学校(注: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1922年,全国国民学校及小学校共177751所,中等学校1096所;1931年,全国国民学校及小学校共259863所,中等学校3026所。)。可见,在中国广大乡村,新式学校远未普及。与此不同的是,私塾却星罗棋布,遍及城乡,尤其在没有新式学校的地方更为活跃。以此算来,乡村社会私塾之数要比新式学堂超出几倍之遥。
其二,兴学以来,许多地方为谋求新学教育的快速发展,往往把推行新学教育作为县知事的考绩。于是,不免有将半私塾、半小学的冒牌货充数的事发生。如河北省兴学初期,“各处办理高等小学切实者固多,敷衍者亦正不少,至于乡村初等小学,往往有徒悬匾额,虽有若无者”[12]。创设小学堂五六年后,“其中设备合宜、教授得法者不过十之一二,而因陋就简,敷衍塞责则居十之八九,间有徒挂学堂牌额,并无学生,反不及私塾尚得按时上课”[13](pp.330-331)。冀南乡下,“小学都非常之小,即使有小学也是敷衍了事”[14](p.96)。邯郸县“全境学务仅只城中高等学堂一处,至于初等学堂,城乡虽有十余处,然皆从前义塾旧习,无一合乎奏定章程者”[15]。山西阳泉“许多村部办起了国民小学堂,由于受师资、教学条件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因此和私塾差不多,学校的地址也只是从私人家中搬到寺庙中”。山西阳高县“名虽改为学校,实际仍搞私塾那一套,所以我给它起名叫私塾式的学校,所不同的是除了教师由国家委派,学生上学不给老师束脩(学费)外,其他一切活动几乎和私塾没有区别”。豫北济源、沁阳一带,20世纪30年代各级学校“无一可人意者,乡村初级小学无论矣,即县立师范与完全小学,其设备之简单,亦等于昔日之私塾”。20世纪30年代初,河南唐河“学校虽多,除城市稍有可观外,余皆有名无实”。宣统末年,张相文游山东,“自登州起陆入内地,行数千里,所过城邑村镇,固已多矣,而不见一学校,舟车邂逅,不遇一学生,间有诵声琅琅出于棘篱茅舍之中者,率皆旧时之家塾也”,那些号称新式学堂的学校,其规模不过教师1人,生徒十余人,“教育内容不离《学》、《庸》、《论》,实与私塾无异”[16]。东平州“州境初等(小学)十二处,半多私塾就家,查学下属,方作临场救穷之计”。1931年,山东省督学马汝梅视察禹城教育状况时发现,“该县学校,除县立第一小学办理尚称完好外,其余学校多类似私塾,设备既不完善,教员亦类似冬烘”[17](p.14)。从这些零碎的资料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当时乡村学校之简陋与粗劣,几与私塾无二。
其三,清末民初,政府对私塾的态度不是严令取缔就是进行改良,目的就是最终以新式学校完全取代私塾,完成旧学的彻底改造。于是,在生存危机的压力下,为对付来自政府的软硬措施,许多私塾既不向官署备案,也不自行闭馆,而是转入地下进行秘密活动。因此,私塾的实际数量要远远多于任何官方的统计数字。如1913年春夏间,广东教育司在香山县进行私塾学务调查与登记注册工作时,谷都乡的劣绅煽动塾师逃避填表注册,致使该地私塾遵令改良者甚少[18]。义务教育的模范省山西亦有这种秘密开办的私塾,且深得百姓的信赖。1932年,刘容亭对山西太原附近阳曲县狄村、西流村、享堂村三村进行社会调查时,发现西流村有一所对外守秘密的私塾,有学生四十余人,且并非全是该村学生,亦有附近各村前往者,学生皆背诵四书五经,学习作文写字,其清洁与秩序,实优于该村之学校[19]。由此可知,其他地方秘办私塾而不报官府备案者肯定不在少数。
由上可以断定,清末民初乡村社会在数量上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私塾。俞于夷曾在19世纪20年代末说:“忽忽十六年大家也不好算没有努力,办小学的成绩也不好算完全失败,不过离开普及的程度却是很远很远。并且一到乡僻,私塾要比小学多;有时私塾的成绩还可以在小学之上。”[20](pp.230-232)1937年,《四川省内江县视察报告》称,“各乡村小学设备简陋,学生很少”,“私塾太多,亟应调训塾师,改良私塾”[21]。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的调查也证明了私塾在乡村教育领域内的地位:直到抗日战争前,我国农村教育属于旧式的占65.1%,属于新式的仅占29.7%,属于新旧式学校,即改良私塾的占5.2%;华北旧式教育占53.9%,新式教育占44.0%,改良教育占2.1%;华南农村私塾发达,旧式教育占75.6%,新式教育占19.1%,改良私塾占5.3%[22](p.292)。
二
乡村社会的私塾不仅数量多,遍设全国,而且势众,其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社会功能尤显突出。传统社会中,绅士为四民之首,乡民所仰望。由于对文化和教育的占有,绅士阶层“集教化、治安、司法、田赋、税收、礼仪诸功能于一身,成为地方权力的实际代表”[23](p.61)。乡间应用文字的地方很少,一切对外的交涉、田地的冲突、田赋经济的组织、集市、对付官府等运用文字的场合,常常是乡绅们大显身手的时候。“就是在满月酒、结婚酒以及丧事酒中,都得有绅士在场,他们指挥着仪式的进行,要如此才不致发生失礼和错乱。在吃饭的时候他们坐着首席,还得接受主人家的特殊款待。”[24](p.120)可以说,在乡民日常生活和观念里,乡绅是乡民文化的代言人。同时,又因为在传统社会教师受人尊重,被认为是荣耀的职业,所以众多绅士的处事态度是:得中功名后就应踏上仕途;如果未能在官府中任职,就应该从事教学。事实上,很多的乡绅都有任教于私塾的经历(注:据张仲礼先生估计,在19世纪后期,全国1500个州县共有正途绅士910597名,一个州县平均有1000名绅士,其中,正途绅士略多于600名。全国有60余万名有绅士身份的塾师,平均每个州县略多于400人。张仲礼收集到的5473份资料中,有2780份资料包含一些绅士经济状况的信息。在这2780份传记中,有859个传主明显是有绅士身份的塾师,约占总数的1/3。详见张仲礼《中国绅士的收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第106-107页。),大约1/3的塾师同时在从事经理地方事务中获得更高的社会威望和丰厚的收入[25](p.250)。因此,私塾作为基层社会的主要教育组织、传统的识字中心和学而优则仕的台阶,已然成为社区文化活动的中心。
尤其是学制改革以来,私塾作为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社会功能更显突出。这主要是因为:第一,新学教育制度中断了千年以来传统乡绅阶层的常规继替,堵塞了由绅而官的便捷桥梁,乡间精英为寻找新的出路不断外流。随着有文化、能适应社会变化的精英向城市的滞留,以及留在乡间的传统士绅的隐退,乡绅阶层出现了社会性、结构性的分化组合,并且在整体素质上出现了史无前例的蜕化。民国年间,土豪劣绅几乎成为乡绅的代名词,他们已经不像从前那样深得人们的信仰,反而成为人们痛恨甚至痛打的对象。因此,新的乡绅阶层已经基本无法扮演文化领导人的角色。第二,此时的新式学校在数量上还未能遍设各乡村,且学校和小学教师多不被乡民信仰,文化活动能力极为有限(注:关于这一点,笔者将在另文中作详细论述。)。第三,私塾组织具备成为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条件。首先,乡间的私塾无疑是文字栽培的大本营,新式学校敌不过私塾;其次,塾东多是地方有权有势之人,说不定就是乡镇长本人,地方组织的行政权都在这些人身上,紧握着老百姓的命脉;再次,塾师是地方上数一数二的才子,外头罢官回来当塾师的,那简直成了土霸王,他懂得官场的规矩,懂得社会的情形,见的事物多,也就有较大的眼光,遇到什么非常的事件,除塾师外似乎是无人可求了。这样,私塾文化活动中心的社会功能也就更加明显,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它以灵活的办学方式,较低的学费,严格且适合乡间生活的教学和管理方式得到乡民的信赖,成为乡民子弟读书识字的大本营,孩子们能够以最低的学费学到最实用的知识。
其二,对付上官和县府。在乡村生活里,最叫老百姓提心吊胆的就是对付上官、县府。若把这些人物和他们发出的官样文章对付好了,江山就算大定了。对付这些人物要靠交际手段,要能言善辩,会看风使舵;对他们发下来的分账、指令、告示、批驳、训令之类,又该懂得一些等因奉此,在文字上会敷衍,了解一些上下行文的步骤。在乡间,能说会道和识字的人同样贫乏,乡长本身也许就目不识丁。渠桂萍考察的晋西北83个掌握基层权力的乡绅中,就有4个文盲(注:详见《晋西区名人传略》,现存山西档案馆,档案号:A-22-1-4-1。)。结果有些地方就将这种工作移到塾师身上来了。此外,关乎全村利益的,如呈请、反对增税摊工、水利、防灾等,老百姓全认为是塾师的本分工作,也只有塾师才配办这些事。一部分塾师借此抬高身价,把持着这种重大的任务,活动中心渐渐移到他们开设的私塾,由此,塾师们直接间接地在当地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其三,“包揽”诉讼。塾师是写状子的能手,在行老练,笔墨纸张又方便。这样,一些超越一点范围的塾师,就走到包揽诉讼的道路上,找塾师写状子成为打官司必经的门径。假如一个村子内有几个塾师的话,谁的状子写得好谁吃香,谁就占着重要的位置。
其四,行所谓的“礼”。像给小孩子起个高雅显达的名字,给在外头混事的丈夫年终写封信,说句平安、报个喜,立张契约,检读由单(内写完粮的数目),填张借单,订张合同,起篇讣文,看个好日子,合合婚,择个时辰,写张表文,还个愿……这些最平常的事都得请塾师来帮忙;过年时节门前贴张“抬头见喜”、“出入平安”、“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对联,孩子半夜三更哭哭叫叫,要写张“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啼郎,行路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亮”的帖子,都是塾师的分内活。此外,比较少见的如庙文、祭文等也得请教塾师。凡此种种,老百姓都认为是塾师的工作,因为在乡间,除了塾师外别无合适的人选了,这也使得塾师顺理成章地成为乡村社会的重要角色。
其五,商议、决策村中大事。乡村社会尤其是北方,同姓的不一定住在一个村里,祠堂这种东西并不多见,村中遇到什么非常大事,要开会问问公意,免不了找到私塾。塾师是参谋,是当然会员,是设计策划者。因此,“在地方上,有以塾师、塾址为中心而形成一个近乎参议院雏形的说法,并不是过其词,一个私塾或许不是直接干预地方行政,间接活动的力量却是值得惊异的。”
由上可以看出,兴学以来,在乡村精英离乡的步伐日益加速的情况下,私塾先生便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充当起乡民的文化代言人,对付一切日常或非常的事态,并间接掌握了若干政治经济的力量,私塾的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社会功能也就更显突出。这也正是私塾深得人心、风雨无阻、地位稳固的原因所在。
当然,以上这些事务并非每个私塾先生都有能力去办,条件不适合的私塾,只得停留在教管塾生的工作上,而且大部分的私塾也只能做到这个程度。另外,从活动能力上来讲,塾师势力较之昔日的士绅已大大减弱,几乎不可同日而语。科举制度下的乡绅作为政府官员的后备人员,是官民之中介,是一个居于地方领袖地位和享有特权的社会集团,是基层社区系统中最主要的力量,各地兴革大事或地方事务均由其把持,甚至在一些绅士势力张扬的地方,地方官仅仅成为绅士的“监印”,而无法直接插手地方公务[23](pp.52-53)。塾师则没有帝制国家所赋予传统乡绅的法理权威和各种有别于平民百姓的特权,他们从事的社会工作往往仅限于一乡一村之内处理和运用文字的事务,在以往被认为是乡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的工作,乡间的私塾先生则不愿也没有能力插手其间。如建立与维持地方上的一些公益事务和机构——学校、社仓和各种慈善机构;修建与维护桥梁、道路和各种水利设施;维持社会治安,控制像团练之类具有一定的军事性质的组织,当社会发生动乱时,自行建立一些武力组织以保卫乡里等等,都是塾师力所不能及的。
在近代中国,传统文化尽管遭到西方文化的强劲冲击,但其顽强的生命力仍然在文化革新的历史过程中不断展示着[26](p.21)。表现在教育领域内,乡村旧式私塾以其极强的乡土适应性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教育现代化并不单纯是一个新式学校取代旧式私塾,科学知识征服八股科举的过程。现代化不能用新式学校的数字、教育法令以及引进西式学制和西式课程来表示,现代化不应被看成一个西化的过程,一个外来文化取代和征服地方文化的过程,而应看成是一个传统与现代互动的过程,一个妥协与创造并存的过程。尽管在新旧教育之争中,乡间新学始终没能战胜强大的私塾组织,但是传统私塾在新学教育制度的冲击和熏陶下已渐渐流露出了趋新的气象,私塾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按以前的面貌按部就班地工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