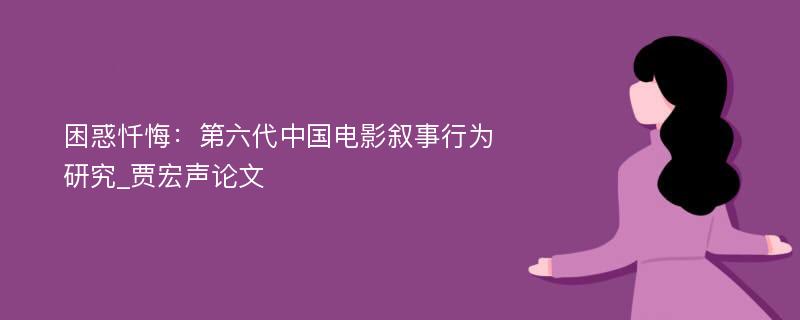
迷茫的告白——中国第六代电影的叙述行为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告白论文,第六代论文,迷茫论文,电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300(2008)05-0065-05
一、第一人称叙述者与客观视点
“电影叙事理论的最令人畏惧的问题,集中在叙事者的身份上。”[1] 罗·佰戈因如是说。的确,从叙事学的角度来看,“叙述”一个故事,构筑一个本文,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谁来讲故事?
1957年,刚刚25岁的特吕弗在《作家的政策》一文中指出:“在我看来,明天的电影较之小说更具有个性,像忏悔,像日记,是属于个人的和自传性质。年轻的导演们将用第一人称表达自己,叙述他们的经历。比如说,可以是他们的初恋,也可以是刚经历的感情,或者他们政治觉悟的转变,他们的婚姻、病痛、假日等。”[2] 就好像是对特吕弗的呼应,作为第六代电影人的精神自传,第六代电影非常钟情于使用第一人称结构影片,这种通过“我”来回忆和叙述故事的方式,第六代导演们使用起来驾轻就熟,真情流露。
第六代电影通过采用第一人称叙事,使叙述者“我”可以抒发感情,袒露心迹,这就使整部影片带有非常强烈的个人色彩。如《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的第一人称画外独白就是对画面未能传达的“我”的情绪和感觉的补充,“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太阳总是有空伴随着我,阳光充足,太亮了,使我眼前一阵阵发黑……”“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记忆中总有一种烧荒草的味道……”这是第六代电影最具代际色彩的地方,也是第六代电影广受非议的地方。
其实,只要我们详加分析就会发现:第六代电影的第一人称叙述者与他们叙述的故事和人物保持着相当的距离,“我”与“我”所叙述的世界并不认同,或者说并不完全认同。《扁担·姑娘》的第一人称叙述者东子,谈到高平的故事时说:“高平说这就是大城市里的爱情,可高平却为这爱情送了命……我只知道人应该靠干活挣钱,不应该干犯法的事情”;《周末情人》中的“我”——李欣,更是以回忆的口吻反省曾经的年少轻狂。最典型的是《苏州河》,“我”对于马达和牡丹的故事的态度是:“我知道一切不会永远,我想只要我退回阳台上去,我的这个爱情故事就可能延续下去;可是我宁愿闭上眼睛,等待下一次的爱情”。第一人称叙述者的思想和心态与所叙故事内涵的差异使电影产生了一种张力,而影片中又没有设置一个更高层次的叙事者,所以观众无法知道导演或者说影片更支持哪一种态度,影片因此具有多义性、开放性。由此可以看出,在第六代的影片中,第一人称叙事者的存在,恰恰反映了导演/作者对自我的怀疑和距离感。不是自恋而是自省;不是发泄,至少不是完全的发泄,而是迷茫的告白。在一个骤然到来的个人时代,在一切宏大叙事都受到置疑和解构的社会语境下,什么是我们应该坚守的?什么是值得记忆和诉说的?个人单纯的生命体验是我们所能够把握的唯一真实吗?第六代电影对第一人称叙事的偏爱及其疏离,既反映了他们对个体生命价值进行理性反思的努力,又表现出他们对个人、对自我亦难有坚定的认同,从而陷入一种困境。随着第六代电影的发展,第一人称叙事又出现了新的表现形式:以轻松的游戏姿态“超越”曾经的困境,从而逃避回答的艰难。
由于影片的故事情节都来自于第一人称叙述者,缺少旁证,这就很容易使整个影像世界不再是完全可靠的。这一点早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就已经初现端倪。例如影片中有这样的旁白:“北京,变得这么快!20年的工夫她已经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城市,我几乎从中找不到任何记忆里的东西。事实上这种变化已经破坏了我的记忆,使我分不清幻觉和真实”;“我发誓要老老实实讲故事,可是说真话的愿望有多么强烈,受到的干扰就有多么大。我悲哀地发现,根本就无法还原真实,记忆总是被我的情感改头换面,并随时捉弄我,背叛我,把我搞得头脑混乱,真伪难辨”。第一人称叙述者的存在使《阳光灿烂的日子》颇有《去年在马里昂巴德》的神韵。《苏州河》是另外一部更加典型的不可靠叙述的电影。“我”在影片中是一个重要的角色,并参与了剧情,但“我”从未在镜头中露面,我们只能看到他的一只手,听到他的声音,以及通过他晃动的镜头去看一些人和事,而这些人和事也不知是真实的还是仅仅出于“我”的想象。而且在影片中,“我”的旁白一直在提醒着观众这一叙述的不可靠性。诸如此类的第一人称叙述,使《苏州河》中的“我”好像不再是事件的经历者或旁观者,而根本变成了故事的“创造者”。“我”不仅拥有全知视点,通晓马达在认识牡丹以前的所有生活细节,了解他从外地归来之后寻找牡丹的一切行为,而且还可以左右故事的发展。叙述痕迹的外露使《苏州河》有一种“元电影”的意味,完全拒绝观众参与到影像世界中,彻底打破了经典电影的“镜式本文”禁忌,从而使电影变为可以随意拼贴的游戏。有研究者指出,在后现代叙事观念中,“电影不再是现实的镜子,也不再是现实的一面窗户,而是对现实本质一个无限深的推测与无限远的遐想,并是对现实图景的多种想象性的虚拟传达”。[3] 《苏州河》的存在使第六代的电影世界成为中国电影中最具后现代色彩的。
如果说“人称”主要是从叙述主体与所叙之事的主客体关系上来考察和区分叙述主体的介入程度与聚焦方法,那么“视点”则主要从“叙述层”分析具体的影像来源。在第六代影片中,贾樟柯和王超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他们常常在整部影片中完全使用纯客观视点镜头。放弃使用主观视点,也就等于放弃主观视点带来的对观众的控制(主观视点即观众通过占有角色的视点从而与角色同化,失去自我)。第六代电影中纯客观视点的使用意味着导演放弃权威地位,和观众站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审视和思考身边的现实世界。事实上,在观看贾樟柯和王超的电影的时候,我们似乎正在跟随一双因震撼而吃惊的眼睛,这是绝对平等的一种注视和关怀。被称为“贾樟柯故乡三部曲”的《小武》、《任逍遥》、《站台》,除了一个镜头之外,完全由客观视点镜头组成。这仅有的一个主观镜头是《小武》中小武听说昔日的伙伴小勇要结婚了,自己却未收到请帖。他去小勇家却最终没有进门,镜头略带摇晃模仿小武的主观视点走到门口,然后停下来摇到门边的墙上。这个唯一的主观镜头的使用在全片显得十分突出,不过它的作用不在于梦幻机制的营造,而是用于抒发导演难以抑制的情感。以客观视点镜头贯穿影片始终并不是导演故意哗众取宠,它反映了贾樟柯自觉的美学追求和对生活的态度。“我当然是一个旁观者,自然区别于主观的讲述,也区别于那种凌驾于一切之上、指手画脚充满优越感的视点。”[4] “包括为什么不动,老是站在那儿看,包括为什么镜头跟着人在那儿慢慢摇,这种电影的方法都是一个我自己对待事实的态度。包括我很排斥前后运动,我希望在一个距离里面来了解对方,这些形式上的运用都是跟自己的经验有关。”[5](P357) 客观视点贯穿影片始终,这就使观众再也无法自居为剧中的任何一个人,无法占据剧中人的视点,只能隔着一定的距离注视面前的影像世界。
青春是有激情的,但是在第六代电影中,这份激情却无处安置,所以只能选择试图面对自我的真实或者现实的真实。要么是个人经验的犹疑表达或者游戏拼贴,要么是对现实世界的审视和距离感,第六代电影的第一人称叙事和客观视点的大量使用,意味着生命个体与外部世界的疏离和参与其中的艰难。
二、夸大的时间与开放的空间
在中国第五代电影中,时间经常暧昧不明,我们只能根据人物的穿着打扮大致判断其表现的年代,从而形成第五代特有的“空间对于时间的获胜”的表达方式。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在特定的意义上,‘黄土地’的故事超越了具体的历史过程成为某种‘寓言’和‘神话’——‘寓言’和‘神话’正是以非历史性或非时间性的表达方式表现历史和未来。”[6](P197)
与第五代电影使时间模糊化、平面化的处理不同,第六代电影通常都有极清晰的时间标识。《周末情人》用字幕明确指出“那好像是1985年的一个周末”,《卡拉是条狗》发生在1994年11月30日北京市十届人大代表会议提出的关于养狗的规定之后,《昨天》讲述的是贾宏声在1993年至1996年之间的经历,《小武》、《站台》、《任逍遥》中用具有时代意义的歌曲和声音提示着故事发生的时间。清晰的时间标识显示着影片与当下社会现实的血肉联系,是第六代直面现实人生的最醒目的标志,是对当代形象在第五代电影中缺失的反拨。第五代的电影风格突出表现为对影像的精雕细琢,对被凝固于历史时空的生命化石的冥想。第六代电影却热衷于历史的变迁,热衷于表现人与历史的竞逐,拷问人在历史变迁中究竟有多大力量,是历史超越人类,还是人类穿透历史。这或许与第六代导演自身的成长经历有关。他们大多生于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成长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正是中国社会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革的年代。此时,人的社会归属感以及人生观、价值观都在经受着严峻的考验。时代的飞速发展、社会面貌的日新月异使人们的时间感特别强烈,与时间赛跑,不能被时代抛在后面是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的紧迫现实。所以,虽然第六代电影人还是那么年轻,他们表现的也大多是青春世界,但是却有那么多的回忆和感慨。影片中年轻的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无不是伤痕累累、沧海桑田。阮红的今生是浓妆艳抹地在乌烟瘴气的歌厅里唱歌陪舞的小姐,而在她的住处,在床边的桌上,那张清纯脱俗的照片却表明她并非生来就是舞小姐,但是对阮红来说,那已经是遥不可及的前生,虽然也许相差只有几年(《扁担·姑娘》);马小军青涩的少年时代用明朗的彩色呈现,成年后的马小军再次与昔日的伙伴聚首时却是黑白的世界,傻子也变了,不仅走起路来雄赳赳、气昂昂,连少年时马小军和他对过的暗语也变了,相隔也就十年左右的少年时代竟已渺茫难寻,恍如隔世了(《阳光灿烂的日子》);当张弛、李欣他们重新回到曾经年少轻狂的地方,迎接出狱的拉拉的时候,不仅背景音乐完全变了,从他们一度视为生命的摇滚变成了带有搞笑色彩的世俗音乐,影片的色调也由清冷沉郁变成鲜艳明亮,而且李欣还带着一个叫拉拉的孩子,一个时代已经完全过去,今天迥异于昨天(《周末情人》)。
如果说第五代的时间是凝滞的、压缩的,那么第六代的时间则是夸大的。在第六代影片中,实际的时间间隔远远小于影片所传达出来的时间感觉。与其说他们展示的是实际时间,不如说更像是第六代电影人的心理时间,是一个人成长所经历的不同阶段的隐喻。第五代电影使时间平面化,讲述一个“神话”或者“寓言”,第六代电影则使时间阶段化、历史化,讲述一个生命个体的懵懂、躁动以及最终的返璞归真。在第六代的影片中,以婴儿或婴儿的哭声作结几乎成为一个模式。《北京杂种》毛毛最终生下了孩子,卡子听见孩子长长的哭声;《昨天》贾宏声回到了焕然一新的家里,夜晚他放了一盘磁带,第一声就是婴儿的啼哭;《周末情人》李欣带着小拉拉迎接获得新生的拉拉;甚至商业色彩浓厚的《危情少女》片尾也是孩子们稚嫩的儿歌“树上的叶子哗啦啦,小明在家等妈妈,姐姐说,不要怕,老虎来了我打它”。总之,时间在第六代影片中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角色,时间的夸大使第六代电影总是弥漫着一股强烈的身世之感和幻灭之感,“婴儿哭声”这一细节设置表达了主人公、创作者对时间循环带来重新诞生的强烈渴望。
在空间的处理上,第六代电影总是力图打破封闭性。例如,在一个固定画框的镜头中,它允许人物随意进出画面,尤其是处于画面前景和后景的次要人物经常是流动的。这种镜头设计显示了第六代电影打破封闭的画面空间、提示画外空间存在的强烈愿望。尤其是在电影整体的形象空间的设计上,第六代电影通过各种方式突破镜头画面所展示的空间,提示一个更加遥远、更加广阔的空间的存在。
首先是通过剧中人物的言语。第六代电影中的人物经常是去过另外一个地方或者正在向往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可以是确实存在的、明确的,也可以是模糊的。与其说它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空间,不如说它是对影片主人公、导演内心世界期待改变、期待全新的生命境界的一种隐喻。其次是心理时空与现实时空的交织。在第六代影片中,心理时空的出现没有任何提示,与现实时空直接剪辑在一起,突破了现实空间的局限。《月蚀》中佳娘的故事是雅男通过胡小兵了解到的,但在影片中佳娘的故事是与雅男的经历交织在一起、片片断断地呈现出来的,观众完全可以把这些有关佳娘的故事情节看做是雅男内心世界的想象。尤其是影片结尾,雅男和佳娘两个人在不同的时空中互相凝视,时空随着镜头变幻,信息量之大,冲击性之强都是前所未有的。再次是象征时空与现实时空的交织。张元的《东宫西宫》是一部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称得上是精雕细琢的影片。从时空上看,影片的主要情节发生在一个小公园的派出所办公室里,时间只有一夜。在如此局促的时空中展开故事无疑有很大的局限性,很容易使影片沉闷枯燥。但导演在处理的时候,除了设计阿兰对往事的回忆时空以及小史听了阿兰的讲述以后产生意志上对其施暴的心理时空之外,还设计了一个极具象征色彩的女贼与衙役的时空。几重时空的交叉、叠加,使这部讲述权力与隐私、主题极其隐晦的电影始终扣人心弦。
强烈的身世之感和外面世界的召唤,使第六代电影充斥着一种出发的躁动和对个人的脆弱命运的敏感。他们并不知道未来或者外面是什么样子,但是他们已经别无选择,而他们除了审视这个世界的目光和脆弱的自我之外,一无所有,只能在想象中经历沧桑劫难,然后欣喜地迎接朦胧的新生。与第一人称叙事和客观视点所表达的犹疑与旁观相结合,开放的空间和夸大的时间的设置使第六代电影在犹疑与旁观的同时又充满了对外面世界的想象和对自我的感伤情绪,他们似乎仍然是思考大于行动的一代。郭连贵、老二、雷海洋、马达等人物形象的行动无不带有一种疯狂和偏执的色彩,与其说是行动,还不如说是情绪的宣泄。
三、复调叙事与开放性结尾
一部电影的结构并非单纯的技巧和形式,它关系到影片主题意念的表达与深化,包含着创作者对生活的认识和理解。结构主义对文艺作品进行普遍的、深层结构的研究对我们不无启迪的意义。“对于普遍的叙事模式的确认看来可以告诉我们的不仅仅是文学,而且是心灵的本质与(或者)文化的普遍特点。”[7](P102)
第六代电影很少专注于一个人、讲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而是基本上同时讲几个人物的几个故事。几个故事互相参照、互相影响,共同推进叙事的发展。除了像《谈情说爱》、《巫山云雨》这种分成明显的三段式来分别结构故事的影片以外,大多数第六代电影喜爱将几个人物、几个故事穿插起来讲述,形成一种复调结构、和弦效果。比如《周末情人》中就设计了李欣与阿西、拉拉的故事,张弛与陈晨的故事以及张弛办乐队的故事,在影片中几个故事同时展开,共同走向尾声;《十七岁的单车》中郭连贵的故事、小坚的故事、小保姆的故事交织在一起;《蔓延》涉及的面更广、人物更多,有大学艺术系的女教师,卖盗版光碟的小王、生明,爱看碟的妓女、下岗工人,还有身患绝症的音乐家。第六代电影铺陈多个故事、牵涉多个人物,形成复调结构的叙事,一方面是源于第六代对好莱坞经典电影形态的拒绝,对线性故事虚幻性的拒绝,另一方面更是源于第六代力图清醒、全面地把握世界的渴望。
《昨天》是导演张杨根据演员贾宏声的一段真实的生活经历改编而成。影片在形式上融纪实采访、影像内容与戏剧舞台三种方式于一体,在结构上采取了自述与他述相结合、众口纷纭说贾宏声的组织方式。影片对众人的采访按照其采访内容组接在一起,但是在同一内容框架下,不同人物的陈述又产生了撞击,彼此之间形成不同的关系。第一,互为印证、互相呼应的关系。例如,围绕吸毒这件事进行采访的影片片段,先是朋友说:“他吸毒是早晚的事,对他来说,那是一种虚荣……”接下来是贾宏声父母:“对,他就是虚荣,老说我们土,是农民……”第二,有时候,采访内容也互相抵触。比如就贾宏声这个人采访他的朋友,朋友们说,“他这个人很极端,特事”,后面插入贾宏声的自述:“我知道他们都笑话我,但是我有我的目标,比他们强”。第三,有时候,采访的内容又互为顺序。如就贾宏声迷恋音乐这个阶段进行采访的影片片段,李杰(贾宏声的朋友):“觉得我们越来越难以交流,有一天我走了”。紧接着是贾宏声的自述:“李杰走了,我不知道该干什么……”第四,有时候,采访内容又是一种递进关系。如贾宏声的父亲陪他出去散步,他躺在草地上,因克制毒瘾身体微微颤抖,父亲看着他,画外音中父亲说:“这孩子得遭多大罪!……”紧接着是贾宏声的自述:“我仿佛回到了93年……我看到了这个世界上最蓝的一片天……纯洁而又残忍……”内容与内容之间、形式与形式之间的撞击,使《昨天》这部电影既充满张力、发人深思,又产生了多声部合唱的韵味。
第六代电影在叙事上的另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开放式结尾。经典好莱坞电影总是喜欢给故事一个最终的结局,相应的镜头语言是:镜头拉开,由特写或近景变成全景或远景。而在第六代影片中,以特写或中景镜头结尾几乎成为惯例。小武在影片结尾被铐在路边,行人停下来看着他(《小武》);斌斌被抓到派出所,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是中景唱歌的斌斌,然后渐隐(《任逍遥》);郭连贵最后扛着已经摔坏的自行车走过北京的街头(《十七岁的单车》);麦强游过江去找陈青,又回到了信号台(《巫山云雨》)……观众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如果说“叙事始于世界发生混乱之时,或有必要说明世界的起源和结构之时。它结束于初始需要或欲望获得相应满足之际”,那么,第六代电影的开放式结尾、未终结的叙事则一方面反映了第六代电影人对于秩序的某种拒绝,它预防了叙事的封闭以及随之而来的意义的确定;另一方面,开放式的结尾也反映了他们尚未拥有赋予世界秩序和结构的能力,或者说他们所生活、所认知的世界本来就是变动不居、尚未定型的。
中国自近代以来一直都处于社会和文化的激烈变革状态,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道路和自身道路的探求从未终止。经过了“五四”和20世纪80年代的两次大规模的学习西方和对自身文化的反思,当下中国社会和文化渐趋多元化,既不唯西方独尊,也不故步自封,而是努力探询一种新的文化发展道路,追求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第六代电影的意义就在于对这种精神探求的继承性,它从20世纪90年代发展到今天恰好处于中国社会和文化探询新的发展道路的转型期,价值观的犹疑,意义的难以界定,自我把握的艰难,个人的迷茫和脆弱,所有这些转型期的特点在第六代电影中都得以委婉地呈现。多条叙事线索的交织是第六代电影为主人公寻找同路人、克服孤独情绪精心设计的策略之一,而开放性的结尾则彻底表明第六代的叙述仍然只能是一份迷茫的告白。
收稿日期:2008-06-11
标签:贾宏声论文; 电影叙事结构论文; 阳光灿烂的日子论文; 第六代导演论文; 苏州河论文; 小武论文; 周末情人论文; 任逍遥论文; 第一人称论文; 剧情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