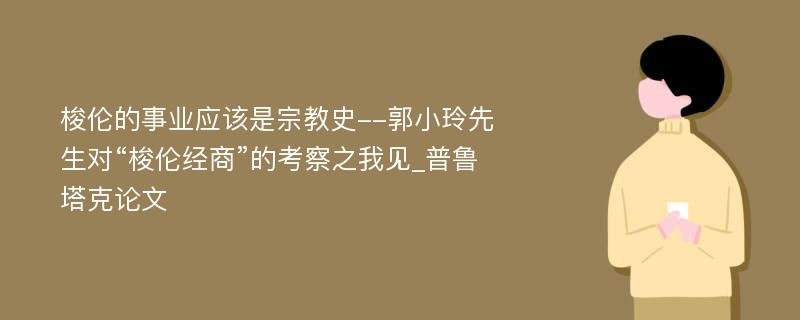
梭伦经商应为信史——对郭小凌先生《“梭伦经商”考》的不同意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信史论文,意见论文,凌先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89年,郭小凌先生在《世界历史》上发表了《“梭伦经商”考》(注:确切地说,该文是郭小凌先生的读史札记《梭伦改革辨析》的一部分。见《世界历史》,1989年,第6期。)一文, 否定了梭伦曾经经商的“定论”。说来令人难以置信,笔者孤陋寡闻竟至这等程度,十年间对如此重大的学术问题竟然一无所知(注:笔者所在单位偏处一隅,规模很小,图书资料奇缺,学术信息闭塞,连《世界历史》都读不到。再者,笔者一直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很少注意世界古代史领域的一些具体问题。)。所幸最近笔者到曲师大本部参评职称,利用闲暇时间去图书馆翻阅资料,才得以拜读郭先生的大作,可谓受益匪浅,启迪良多。
郭先生认为,关于梭伦经商的有关史料“并非可靠”,因此,梭伦经商说“不足凭信”。其论据是:梭伦的诗及其法律残篇作为史料,虽具可靠性,但从中“绝对看不到梭伦经商的痕迹”;古代作家中与梭伦时代最近的是希罗多德,他是“第一位成文史”的作者,是在亚里斯多德之前惟一对梭伦作过记载的,但他却对梭伦“经商一事只字未提”;亚里斯多德和普鲁塔克是古代作家中惟一记载梭伦曾经经过商的人,但他们的梭伦经商说“完全是对希罗多德作品及梭伦诗中有关内容的演绎”;亚里斯多德“关于梭伦的材料来自和他几乎是同代人的安德罗提昂,由于两人均远离梭伦时代,完全有可能获得一些走样的传闻或对其所获材料做符合自己需要的加工”;普鲁塔克引用某个晚期传记作者赫尔米布斯关于梭伦经商的材料,而赫尔米布斯是位“精心伪造历史”的作者;梭伦的心态也难以使梭伦经商说成立,等等。
笔者认为,上述问题作为论据是否能够成立,值得重新讨论。众所周知,梭伦是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人物,无论从哪个角度说,关于他的问题的任何争议,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其理论的和现实的意义都不容忽视。因此,笔者不揣冒昧,谈一谈对于郭先生的大作的一点不同意见。不妥之处,敬请郭先生及关心这个问题的学者批评指正。
1
笔者认为,所谓梭伦残篇无痕迹,不足为据。因为,既然是残篇,就难以反映全貌。退一步说,即使“全篇”中没有梭伦经商的经历,也不能就此下结论说,梭伦的一生没有经商的经历。因为,人一生之经历,有时候会通过自己的著作反映出来,有时候又确实反映不出来——这还不包括那些没有写作能力的人——这不仅取决于自己传世的作品的性质,还取决于其他各种因素。譬如,“梭伦写诗主要是为了表达其政治观点,传说他经常来到市场上朗诵诗歌以教育人民,激发其民主意识。诗风严肃、宁静,充满了强烈的感情和对公众利益的忠诚。”(注:飞白:《世界诗库》,第一卷。花城出版社,1994年版,第63页。)写这种政治性很强的诗,就很难叙及个人或经商、或务农、或做工、或求学、或娶妻生子之类的琐事。但不涉及,并不等于自己没有这些经历。就以普鲁塔克为例,“普鲁塔克以历史传记垂名于世,但他却没有给后世留下本人的传记或详细的自述材料”,“关于普鲁塔克的生平事迹,我们今天所了解的一鳞半爪大都是从散见在他本人著作中的絮谈插话推断而来,再就是参照各种版本和译本的序跋,从其中撷取点滴可用的材料编录而成的。”(注: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中译者序。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再以斯韦托尼阿为例,他“是罗马帝国早期的著名传记体历史作家,和许多古代学者一样,……详细地记载了许多别人的故事,却没有留下关于他自己的事迹。”(注:斯韦托尼阿:《罗马十二帝王传》,中译者序。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可见,有时候,作者自己的生平经历会在自己的作品中有所反映,有时候又不会得到反映,除非自己写下的是内容比较详尽的自传,否则,很难保证事事有痕迹。因此,我们不能因为梭伦传世的残篇中没有留下经商的痕迹就断定他没有从商的经历。
关于希罗多德对梭伦经商只字未提一事,笔者同样认为不足为据。无论在梭伦时代,还是希罗多德的时代,在希腊人那里,去经商做生意,就如同去从事农业或手工业劳动一样,是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小事,既不会引人注目,更不会引起轰动。只有在极度轻商的国度里,才会因人而宜引起某种程度的轰动。作为政治家的梭伦,刚刚完成各项改革措施,改革事业如日中天,此时却从政治舞台上倏忽退下,悄然而去,外出旅行,这是引起轰动、众人瞩目的大事。至于出游时顺便干了些什么,那就是不为人们所注意的小事了。由于出游是具有轰动性的大事,出游时捎带着做点生意是不起眼的小事,更由于二者有一个主从关系,所以史家记事,只记其出游,而未记其经商,是很正常的。更重要的是,希罗多德涉及梭伦的这段文字,(注:希罗多德:《历史》,Ⅰ,29-34。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其写作目的不在记其出游, 而在记其与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的著名会晤,目的在于传述梭伦那一番关于幸福问题的高论。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以及为行文的需要,即交待故事的来龙去脉,希罗多德才提到其出游及交待了出游的原因,文字非常简略。至于出游时干了哪些琐事,是经商了,还是没有经商,就略而不及了。只要稍懂逻辑常识,只要读希罗多德的书,这个问题就会很清楚。希罗多德的着眼点完全不在出游,而在会晤,所以才会出现“只字不提经商”这种现象,如果他的着眼点在出游,则肯定要比较详细地交待出游的过程及其有关细节内容,从而也就有可能为我们回答梭伦是否经商这个问题。
这还可以从希罗多德交待梭伦出游的原因是“为了避免自己被迫取消他应雅典人之请而为他们制订的任何法律”,而对梭伦法律的具体内容却只字未提的现象得到旁证。我们不能因为希罗多德此处没有提到梭伦的“解负令”;没有提到梭伦按财产多寡划分社会成员等级,按不同等级分配相应的政治权力;没有提到梭伦如何采取措施鼓励发展工商业等具体的立法措施,而断然否定这些措施的客观存在。根据“出游”与“经商”这种主与从的逻辑关系,我们可以认为,当希罗多德提到梭伦“出游”这一概念时,是完全有可能蕴含着“经商”的内容的。“出游”蕴含着“经商”,作为一种抽象的可能性,已经由普鲁塔克的一段文字证明为现实。普鲁塔克在梭伦传中谈到梭伦经商时说,“他出外旅行,主要是为获取经验和学问,不是为了赚钱。”(注: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梭伦传”,2。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这里,直接把出外旅行与赚钱(即经商)联系起来。试想,如果出外旅行不蕴含着经商的内容的话,或者说,梭伦的出外旅行仅仅是一种纯粹意义上的旅游活动的话,他这样说,不是既突兀,又荒唐可笑吗?
史家写史,有自己的着眼点,提到了某一件事,没有提到某一件事,都有很大的偶然性,提到了固然很好,证明有这么回事,没有提到,但也并不等于没有这回事。因为文献作品与现实是有距离的,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既反映现实,又不可能“复制”现实。所以,用希罗多德只字未提梭伦经商一事来论证梭伦没有从商的经历,是没有说服力的。这里,我们还可以再以普鲁塔克为例。与普鲁塔克“同时代和比他稍后的作者如塔西陀、小普林尼、斯韦托尼阿在传世的史籍、书简中,从未引用过普鲁塔克的著作,甚至没有提到他的名字”(注: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中译者序。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但我们却不能据此否认普鲁塔克其人其著的客观存在。按郭先生的观点,希罗多德早于亚里斯多德百年左右,离梭伦的时代比较近,(亦为百年左右),因此希罗多德只字未提梭伦经商,就意味着梭伦没有从商经历更接近真实,那么,塔西陀(约55-120)、小普林尼(约62-113)、斯韦托尼阿(约69-160)等人离普鲁塔克(约46-120)的时代更近,或者说,是同一时代的人,然而他们却没有提到普鲁塔克的生平及其著作,这能说普鲁塔克这个人的不存在更接近真实吗?
关于亚里斯多德和普鲁塔克演绎希罗多德及梭伦一说,笔者认为也不能成立。郭文中说,据著名史家哈蒙德考证,亚里斯多德所掌握的关于梭伦的材料来自于和他几乎是同时代人的安得罗提昂(前410-340),并断言,“由于两人远离梭伦时代,完全有可能获得一些走样的传闻或对所获材料做符合自己需要的加工。”“考虑到希罗多德较亚氏和安氏早生100年左右, 且梭伦改革时雅典以及整个希腊无任何有意识的历史记录,我们有理由认为第一位成文史的作者希罗多德的说法更接近真实,亚氏等人的说法则完全是对希罗多德作品及梭伦诗中有关内容的演绎。”这一番话,自相矛盾,先是说亚里斯多德的材料来自于安德罗提昂,又说亚氏、安氏是根据走样的传闻或对所获材料做符合自己需要的加工,又说亚氏、普氏演绎了希罗多德的作品及梭伦的诗,到底是哪一种情况?实际上,上述诸说,都是既无事实依据,又无严密论证的主观臆测。譬如说安德罗提昂,公元前376-346年,一直活跃在雅典的政治生活中,在晚年和流放中写成《阿提卡史》,广为人们阅读,而郭先生并没有指出安氏的哪些材料是据传闻写成,哪些材料做了符合自己需要的加工。即使对所谓“精心伪造历史”的赫尔米布斯,也没有举出确切的证据,尤其是没有举出他如何伪造梭伦经商的证据。赫尔米布斯是小亚西部沿岸的土麦那人,活跃于公元前3世纪后期,据有的研究者称, 他是杰出的哲学家和传记作家。这里我们暂且承认他伪造历史,但是否每一个他所记的历史细节,譬如梭伦的事迹,都是伪造的呢?很明显,这就像在法庭上指控一样,既举不出证据,又想让对方认输,那是很难奏效的。
2
笔者认为,梭伦经商,可为信史。根据在于,关于梭伦经商,有明确的历史记载,而且迄今为止,尚无确切的材料和完全的理由能够予以证伪。所谓明确的历史记载,是指亚里斯多德和普鲁塔克分别在《雅典政制》和《希腊罗马名人传》中留下了关于梭伦经商的文字记录。
亚里斯多德说,梭伦“按照上述方式,组织其政体后,人们接连去他那里以有关其法律的事情烦扰他,责备一些地方或追问另一些地方;他既不愿意改动这些法规又不想留在这里招人嫉恨,于是便去了埃及,既为贸易也为观光,声言在10年内不会返回,因为他不认为留下来阐释这些法律是公平的,倒是人人应该恪守这些业已成文的法规。与此同时发生的是,许多显贵之人由于债务的废除变得同他疏远了,而且双方派别由于其造成的格局不合他们的心意也转变了态度。因为平民们原以为他会重新分配一切财产,而显贵者以为他要么会恢复到与先前相同的秩序,要么仅作微小的偏离;但是梭伦违反了双方的心愿,在无论迎合哪一派意愿都可以实现僭政的情况下,他却宁愿选择拯救母邦和订立最完美法律而招致双方的仇恨。”“其他所有人众口一辞地承认以上这些便是实际的情况,而且他本人在诗中也就此作了记述……”,“由于这些原因,梭伦决定远走他乡,当他远走之后,城邦仍然处于纷乱状态,……”(注:《雅典政制》,11,12,13。见《亚里斯多德全集》,第10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从这一段文字及《雅典政制》的其他地方,我们可以看出,亚里斯多德关于梭伦改革及梭伦远游“既为贸易也为观光”的记载,既不是取材和演绎了希罗多德的著作,也不是仅仅来源于安德罗提昂,而是有众多的历史家或传记作家关于梭伦其人其事的材料摆在他面前,甚至在一些问题上“所有人众口一辞”。由此可见,亚里斯多德关于梭伦经商的记载必定是言之有据的。
美国学者J.W.汤普森在谈到亚里斯多德对史学的影响和贡献时说,《雅典政制》的内容结构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历史。亚里斯多德在其中记载了雅典所有的革命和体制变革,以及直到他本人的时代雅典所有十一部宪法的摘要;第二部分是关于雅典实际政治体制的描述,细致地研究了政府各机构和各类官员的职责。古代史以政治史为主要内容。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两人的著作都是这样,政治和战争占首要地位。但他们二位都很少谈到国内政治制度史。这个情况使亚里斯多德这本书在史学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珍品。”“但是,像亚里斯多德这样的哲学家能够成为优秀的史学家吗?他对史料的批判达到了什么程度呢?他很少引用史料,只在第十四章中提到希罗多德的名字。但这一段文字证明他确曾深入阅读其他历史家的著作。”“从他对这些文献的分析上看来,……事情很明显,他进行工作时有条不紊,而且表现出很大的批判能力。”“亚里斯多德并非一位历史学家,而是政治学家。对他说来,历史只是为了查明事实真实。”“一般来说,亚里斯多德最令人钦佩的地方是他那种永远不会走上虚幻道德的扎扎实实的思想。”“在亚里斯多德看来,一切事物的本质在于仔细研究直接间接与这个题目有关的一切类似的事实。他搜集希腊全境138 个城邦各种不同的典章制度就是一个例证。”(注: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一分册。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52-54页。)“他是考证学(criticism )的创始人。”(注: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一分册。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51页。)汤普森对亚里斯多德的这一大段评论,一方面揭示了亚里斯多德著述材料的广泛性,同时揭示了亚里斯多德治学和著述的特点,这就是严谨,不尚玄谈,富于批判精神。事实上,在学术界,对亚里斯多德的这一治学特点,是大家公认的。从这一角度看,梭伦经商说即使是演绎,也不会是毫无根据的。
在《雅典政制》一书中,亚里斯多德谈与梭伦有关的内容,重点是其改革和政制,而不是介绍其生平经历,所以对其经商一事也就一带而过。亚里斯多德之后,作为传记作家的普鲁塔克,由于其任务是为梭伦立传,所以对梭伦经商一事也就谈得多了一点,不但倾注了较多的笔墨,而且还带有一点考辨的味道。这也是古代作家中描述梭伦身世和经历的最为详尽的材料。
关于梭伦经商问题,普鲁塔克这样写道:“梭伦在他的父亲因为种种慈善事业而致家道衰败之后,像赫尔波斯(又译赫尔米布斯)所说,本来可以找到不少愿意帮助他的朋友,可是他以取之于人为耻,因为他出身于一个总是帮助别人的家庭。因此,还在年轻的时候,他就出外经商。有人说,他出外旅行,在他已经很老的时候,他还说‘愈老愈学到很多东西’。”(注: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梭伦传”,2。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这一段话不仅告诉人们梭伦年青时经过商,而且印证了梭伦执政官卸任后远游时顺便经商的现实。“有人说,他出外旅行,主要是为了获取经验和学问,不是为了赚钱”,显然,他是一边出外旅行,一边顺便经商。否则,人们怎么会将他的出外旅行同赚钱扯在一起呢?如果没有经商的行为,只是一种纯粹的旅游,是不会引发人们这样的议论的。这一点,上文已经谈到过了。通过普鲁塔克的话,我们还可以知道,在普鲁塔克的时代或其以前,确有人在谈论梭伦经商的事,并且就梭伦出游的动机问题还有争议。按普鲁塔克的观点,“一个好的政治家不应当过分把自己的心思用于获取多余的财富,但也没有理由过分地轻视享用那些必需的使生活安适的东西。”(注: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梭伦传”,2。商务印书馆,1990 年版。)普鲁塔克不但为梭伦的经商行为即赚钱行为辩护,而且还鼓吹经商光荣:“借用赫西俄德的话,‘工作不是不体面的’,没有一种行业会降低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而商人的行业实际上是被人认为光荣的,因为它使人熟悉外国的地方,使人能够和外国国王交朋友,并且使人获得很多世务的经验。”(注: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梭伦传”,2。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这里,普鲁塔克关于经商光荣的原因, 显然是从梭伦身上概括出来的,这同样,印证了梭伦的从商经历。
通过普鲁塔克的著作,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1、 普鲁塔克记载梭伦及其经商,既不是演绎希罗多德的结果,也不是仅仅取材于赫尔米布斯,而是有着相当广泛的资料来源。因为普鲁塔克在写梭伦传的时候,阅读了“许多作家”(注: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梭伦传”,10。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的作品。2、梭伦经商一事, 在古代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也是定伦。即使是属于历代相沿的“传闻”,也不是虚妄之说,当属口碑史学。不同的是,人们对其经商的动机有所争议,是为了获取经验和学问?还是为了赚钱?而这种争议本身,只能证明梭伦确实是经过商的。
郭小凌先生还断言,“从心态上讲,梭伦为商说也难以成立”。笔者则认为,梭论的心态恰恰证明了他是一个曾经经过商的人。众所周知,梭伦是古希腊七贤之一。所谓七贤,是指七个被认为最有智慧的人。梭伦能够入选七贤,除了他享有改革家、立法家的盛名,富有智慧,同时也因为他是一个道德境界很高的人。譬如他的财富观念就堪称卓越:“我想有财富,但用不正当的方法取得它,我不愿意,正当的方法虽然慢,可是稳当。”(注: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梭伦传”,2。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另一处地方, 梭伦的这两句诗被浓缩为:“我愿拥有财富,但不愿非法谋取。”(注: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普布利科拉传”,24。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让我们想一想,到底什么样的人最容易说出这样的话?是一个农民?还是一个渔民?还是一个手工业者?还是一个商人?……还是一个不务俗事的文化人?或政界要人?当然,人人都可以有这样的想法,但相对而言,只能是商人。作为政界要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有“非法谋取”财富的条件,但在伯里克利时代之前,公民参政无薪给,一个人从政,多为事业心、爱国心所驱使,非为谋一己之私利,亦即重名轻利,从政不是为发财。其他几种情况,一般也都不具备“非法谋取”的条件(除非是劫掠之类)。试想,一个务农的,或一个打鱼的,或一个从事手工业的,怎么去发不义之财?因此,最容易说出这话的既不是文化人、政界人,也不是农民、渔民、手艺人,……而是商人,是思想境界较高,有道德,曾经经过商,但又没有发财的人。就一般从商的人来说,拥有财富的欲望都会有的,这是很正常的。经商赚钱,谁不想发财?在古风时代,人们已经认识到经商是脱贫致富的关键。(注:拙文《论古代希腊人的重农思想——兼与古代中国重农思想比较》,《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4期。 )赫西俄德劝诫其弟不失时机地去经商以获得“充足的生活来源”,(注: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神谱》。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9页。)就是例证。到古典时代,经商行为被亚里斯多德概括为致富的“最便捷的方式”(注:亚里斯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30页。),这是很有道理的。 这与两个半世纪之后中国汉代司马迁“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注: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的思想是一致的。因为经商相对容易致富,所以对头脑清醒的人来说,要想拥有财富,最好是去经商。然而,通过经商赚钱达到发财的目的,又有两种途径,即文明经商和非文明经商。所以在商人队伍里,自古以来,就有奸商和非奸商之分。奸商不择手段,谋取暴利,发不义之财,这自然为那些有道德的人所不耻。亚里斯多德甚至不分奸商与否,将以谋取利润为目的的商业活动一概视为“不合乎自然的”(注:亚里斯多德:《政治学》。 商务印书馆, 1983年版,第25页。)应该受到谴责的致富方式。梭伦经过商,自然有过发财的念头,或者与能发财沾上一点边儿,但由于他又是一个有高尚道德的人,所以他又认为应取之有道,不能发不义之财。在我们中国,文明经商的人谈论经商之道,有一句老话,这句老话也体现了文明经商的人的心态,叫作“有利无利常在行”(音hang)。这句话有如下含义:经商应该持平常心态,不能过分计较利多利少;虽然利薄,但只能持之以恒,不懈怠,即使惨淡经营,也能积少成多,也能赚到钱;只有这样,才是正义的生财之道。中国商人的这句格言与梭伦所说的“正当的方法虽然慢,可是稳当”,含义相同。保持这种心态的经商人,就属于身上没有铜臭气的人,这种人在商海中不是没有,只是很少罢了。正因为很少,所以中国人又说“无商不奸”,甚至马克思也说商业利润“不仅表现为侵占和欺诈,而且大部分是从侵占和欺诈中产生的。”(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369页。)而奇怪的是, 郭先生把梭伦身上毫无铜臭气作为他没有从商的证据,这显然忽视了梭伦是一个“贤人”的现实,混淆了一个重要问题,即,经商就必有铜臭气吗?而且,还颠倒了俊伦远游与经商两件事的主从关系。把梭伦当成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商人看待了。梭伦经商,仅仅是远游的副产品,如同当年孔子一行周游列国是夹带着做生意一样。(注:朱活:《孔夫子货币观初探》,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史》,1988年,第7期。 )梭伦有船只,有仆从,远游夹带着做点生意,既不丢人现眼,又能维持一些开销,还能增一番情趣,何乐而不为?话说回来,即使一个纯粹的商人,也未必都沾染了铜臭气。既然如此,怎么能将梭伦身上没有铜臭气作为他没有从商经历的论据呢?梭伦在诗中还说过:“作恶的人每每致富,而好人往往贫穷;但是,我们不愿把我们的道德和他们的财富交换,因为道德是永远存在的,而财富每天在更换主人。”(注: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梭伦传”,3。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这里展示的思想无疑也是商品经济条件下的产物。有些人确实靠发不义之财而致富了,而老实巴交的人却一贫如洗。至于“财富每天在更换主人”的认识更是一个只有在商海里活动过的人才能最容易体会到的。
3
读郭先生的考证文章,发现有两个明显的特点:
一、通篇文章的基点主要建立在西方个别学者的三个观点之上。为了说明问题,笔者不厌其烦,再予以征引:其一,“古代作家……关于梭伦的论述大多是在改革200多年以后所作, 除了从梭伦诗和若干立法取材外,还根据世代相传的有关传说,(此处郭先生注曰:见《牛津古典辞书》,1970年版,“梭伦条”。)这就难免给梭伦蒙上一层传奇色彩,使记述打有明显的后代人的烙印。”其二,“据著名史家哈蒙德考证,亚氏掌握的关于梭伦的材料来自和他几乎同代人的安德罗提昂。(此处郭先生注曰:哈蒙德:《希腊史研究》,牛津1973年版,第152 页)由于两人均远离梭伦时代,完全有可能获得一些走样的传闻或对所获材料做符合自己需要的加工。”其三,“普鲁塔克……在谈及梭伦早年历史时,却引用某个晚期传记作者赫尔米布斯的记述,……现代史学业已确认赫尔米布斯是位‘精心伪造历史’的作者。”(此处郭先生注曰:《牛津古典辞书》,第504页)
郭先生的逻辑论证非常清楚。大前提,古代作家关于梭伦经商的记载,材料来源是有问题的。1、十分狭窄,或仅仅根据传说, 或仅仅根据某个人的。2、且又有假。结论:所以是不可信的。实际上, 我们只要认真读一读亚里斯多德和普鲁塔克的著作,就可以知道,他们所面对的,决不仅仅是“传说”,也不仅仅是某个人的,而是“许多作家”的材料。至于这些材料后来失传,我们今天看不到,那是另一回事。但可以肯定的是,古代作家关于梭伦事迹的记载,是在有丰富材料来源的基础上作出的,也就是说,是有一定史料根据的。我们如果不去仔细读古代作家的作品,或者读了没有留心,只把西方个别学者的个别观点即第二手的东西拿来,作为自己的论据,从而推导出自己预先设定的结论,单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也是不合适的。
二、根据不肯定的前提推出肯定的结论。这样,使“有可能……”变成了现实的,使“接近真实”就成了真实。实际上,不肯定的前提,只能推出不肯定的结论,否则,就很难令人信服。
总起来看,《“梭化经商”考》一文,缺乏第一手可靠资料和周全严密的逻辑论证,因此,得出的结论是似是而非的。笔者认为,由于我们面对的是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人和事,无论是肯定他(它)哪一点,还是否定他(它)哪一点,都应该十分慎重,否则的话,势必会造成人们思想上的以及理论上的混乱。因为,在现实中,能有几个人,愿意耗时费力,再去考考你考的是对,还是不对?这样一来,“地中海的水”势必就要浑了。
标签:普鲁塔克论文; 希罗多德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梭伦论文; 希腊历史论文; 雅典政制论文; 名人传论文; 雅典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