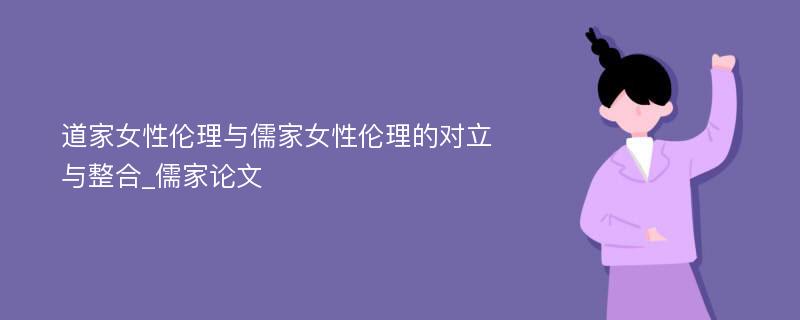
道学女性伦理观与儒家女性伦理观的对立及融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儒家论文,女性论文,道学论文,对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633(2012)04—025—06
道学是指以老子的道的学说为理论支柱的文化系统,包括道家的哲学文化、道教的宗教文化以及丹道的生命科学文化。[1]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历程中,道学原本是作为儒家的对立补充面而出现的,有着与儒家截然不同的思想主旨,这就决定了道学与儒家在女性伦理观上必然存在各种歧异。与此同时,在儒、佛、道“三教合一”的过程中,道学为了扩大其影响力而不断吸取儒家纲常伦理思想,这又使得道学与儒家在女性伦理观上出现会通之处。本文即对这两种女性伦理观的对立及融合之处逐一分析,以期全面揭示两者的思想内涵、相互关系及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作用。
一、道学女性伦理观与儒家女性伦理观的歧异及对立
(一)对于女性的地位和价值定位不同
道学与儒家在女性伦理上的首要对立在于如何看待女性的地位及价值问题,这一问题是女性伦理中最为基本的问题,对此,儒家根据《周易》的乾坤阴阳学说强调“男尊女卑”。乾坤阴阳是《周易》的基本范畴和卦辞。《周易》作者根据其对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和人事的观察,将乾坤阴阳分别赋予尊卑、贵贱、刚柔、动静等特定的性质,并认为这些特性具有先验性质且凝固不变,因而也是形而上学的。[2]如“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周易·系辞上传》)“乾,阳物也。坤,阴物也。……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周易·系辞下传》)根据“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周易·系辞上传》)的原理,儒家从“乾尊坤卑”、“阳贵阴贱”中合乎逻辑地推出了“男尊女卑”的观点,由此贬低女性的地位和价值。儒家认为,男子在社会、宗族、家族中应享有尊贵的地位,女子则处于卑贱的地位,他们的地位从出生开始就注定了。《诗经·小雅·斯干》云:“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诒罹。”在古代,“璋”本是一种长条形的玉器,是贵族行礼时手中所执的礼器;“瓦”本是“纺砖”,是女子纺线的工具。“璋”、“瓦”相对,男女之间的高低贵贱不言而喻。这种卑贱地位决定了女子必须终生依附男子而活,她们的价值就是为男子生儿育女和操持家务。在儒家看来,“妇无公事,休其蚕职”(《诗经·大雅·瞻卬》),他们反对女性参与任何社会政治生活。为了维护这种“男尊女卑”的等级秩序以及“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周易·家人卦》)的分工格局,儒家提出了“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三从”之道以及“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道德观。在男权的束缚和统治下,女性丧失一切自主权利,其地位和价值遭到了最大程度的践踏。
道学却主张“阴阳并重”,它以“道”为形而上根据而赋予了女性与男性等同的地位。“道”是道学的最高范畴。道家与道教一致认为,包括世间男女在内的天地万物都由“道”而生。《老子》第四十二章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太平经》亦云:“六极之中,无道不能变化。元气行道,以生万物,天地大小,无不由道而生者也。”“道”在派生万物之后,就会遍布于万物之中(老子将内在于万物之中的“道”称为“德”),成为万物各自的本性,呵护万物成长,此即老子所言“道生之,德畜之”(《老子》第五十一章)。既然男女都由“道”而生并都具备道性,那么,这两者在根本上应该具有同一的原理及价值根据,其社会地位是平等的,享有同等生存发展之权利。道学还指出,男女两性的价值同等重要,这又为男女平等提供了事实依据。例如,《老子》第四十二章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太平经》亦云:“男子,阳也,主生;女子,阴也,主养万物。……天下凡事,皆一阴一阳,乃能相生,乃能相养。”阴阳或男女两性在生命缔造过程中缺一不可,这表明他们具有同等的自然价值。从“阴阳并重”的思想出发,道学并没有将女性的价值仅限定在为男性生儿育女和操持家务,而是同时给女性指引了一条走向社会、实现自我的解放之路,那就是修道成仙以实现精神上的超越。在道教中,女性不仅能够享有与男性同等的修道成仙之权利,甚至能够担任教派首领。既然道教认为女性在精神价值层面上的追求拥有与男性同等的机会和成就,甚至是超越男性,那么,它就不会像儒家那样强调“女子无才便是德”。事实上,道教鼓励女性识字读书甚至是赋诗作词,因为道教要求修道者必须读道书和写道经,诸如《黄庭经》、《周易参同契》、《悟真篇》等道书都是用诗歌的形式写就的,《真诰》中的不少女仙也是用诗歌点化众生和开启世人的,这必然对女性的才华提出更高的要求。受此思想影响,在道教发展历程中,涌现了以卢氏、魏华存为代表的教派首领以及以薛涛、鱼玄机为代表的女冠诗人等大批杰出女性修道者,她们的存在对儒家“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道德观念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二)对于女性人格的要求和评价不同
为了维护“男尊女卑”的等级秩序,儒家否定女性的独立人格,强调女子须以柔顺服从为其至德。《周易》云:“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周易·坤卦》)这样一来,女性没有属于自己的独立人格,而必须以男性的人格为其人格,“阴卑不得自专,就阳而成之”。(《白虎通·嫁娶》)不仅如此,儒家还在人格上将女子和小人相提并论,认为她们具有先天的道德瑕疵。孔子云:“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论语·阳货》)朱熹在《论语集注》中将这句话注解为:“此小人,亦谓仆隶下人也。”女子的人格之所以被儒家归入小人一类,一是因为儒家认为女性的欲望难以满足,且“阴性主杀,惨刻少恩”;二是因为儒家认为“妇人心性不可信恃”,在性道德的问题上,女人是靠不住的。[3]从这种女子具有先天道德瑕疵的荒谬前提出发,儒家合乎逻辑地推出了“女人祸水论”的观点。《诗经·大雅·瞻卬》云:“哲夫成城,哲妇倾城。懿厥哲妇,为枭为鸱。妇有长舌,维厉之阶。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匪教匪诲,时维妇寺。”在此,作者指出了女祸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女色生祸和长舌生祸。受儒家“女祸论”的影响,人们多把亡国之祸或败家之祸的灾难性后果归罪于女子。儒家对女性人格的贬低和污蔑,不过是为男权社会顺利实现其对女性的统治与压迫寻找辩词而已。
倡导“阴阳并重”思想的道学不像儒家那样一味强调女性对男性的依附。虽然道学并没有明确提出女性应具备独立人格的主张,但其表达了对于女性具有主体意识的赞赏。如道书《云笈七签》记载,一位名叫张丽英的女子面有奇光,长沙王吴芮闻之领兵来聘娶,张丽英坚决不从,随后上了金精山,在石鼓处舍生取义并留诗一首:“石鼓石鼓,悲哉下土。自我来观,民生实苦。哀哉世事!悠悠我意。我意不可辱兮!王威不可夺余志。……父兮母兮!无伤我怀!”[4]其中的“悠悠我意。我意不可辱兮!王威不可夺余志”充分表达了女性的自主自由之精神。倡导“阴阳并重”的道学也不会像儒家那样贬低女性的人格。相反,道学高度评价女性的人格。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就运用类比推理的论证方式,使用“牝”、“雌”、“母”等阴性词汇来喻“道”,通过对“道”的基本特性和精神的赞美表达其对女性品格的欣赏之情。例如,《老子》第五十一章云:“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玄德”,即最深远的德。老子在此歌颂了母亲生而不有的博大宽容。《老子》第四十三章云:“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老子在此表达了其对女性柔韧品格的赞赏。《老子》第六十七章云:“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这三大美德都是女性在长期的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形成的,老子对其极力赞颂,并将其升华为人生的法则而默默恪守。道教同样讴歌女性人格,其塑造的女仙皆是真、善、美的化身,如蚕女“食桑叶,吐线成茧,用织罗绮衾被,以衣被于人间”(《墉城集仙录》卷六第六),昌容“能致紫草卖于染家,得之者色加倍好,得钱以救贫病者”(《墉城集仙录》卷六第九)。道学的“女性崇高论”与儒家的“女人祸水论”形成鲜明的对比。
(三)对于女性“贞节”及两性交往的态度不同
建立在男权中心主义基础上的儒家文化处处强调和维护男性的利益。为了保证继嗣血统的纯正性和满足男性的占有欲,儒家单方面要求女性贞、节、烈。所谓贞,是指女子应为丈夫守住贞操;所谓节,是指丈夫死了。女子决不再嫁,丈夫死得愈早,家里愈穷,女子便节得愈好;烈有两义,一是指无论女子已嫁未嫁,只要丈夫死了,她也跟着自尽;二是指女子遭遇强暴污辱时,设法自戕或抗拒被杀。[5]为了守住贞节,女子必须严格遵循“男女之大防”的道德准则,处处以“礼”自持,以免瓜田李下之嫌。《女论语》云:“内外各处,男女异群。”“女处闺门,少令出户。”《女儿经》也要求女子“莫与男人同席坐,莫与外来女人行。兄弟叔伯皆避忌,惟有娘亲步步从。”儒家的贞节观对传统社会的女子影响深远,尤其是宋明理学家提出“天理存则人欲亡”(《朱子语类》卷十三)及“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二)的观念之后,更是上演了无数贞妇烈女的悲剧。如清代姚元之的《竹叶亭杂记》卷七记载了一女子落水时为了守住所谓的贞节宁死不愿为男子伸手救助的事迹:“道光十一年辛卯,海口潮涌,江水因之泛滥。……大水时,一女子避未及,水几没腰。有一人急援手救之,女子乃呼号大哭曰:‘吾乃数十年贞节,何男子污我左臂。’遂将同被灾者菜刀自断其臂,仍赴水而死。”儒家过于强调女性“贞节”的畸形伦理观可谓对人性的摧残与扼杀,而其“男女之大防”的道德准则更是严重束缚了女性的智力进步和个性完善,其本质是虚伪的、野蛮的。
尊崇女性的道学却对处在封建礼教束缚下的女性持包容同情和慈悯怜爱之情,《庄子·天运》云:“嘉孺子而哀妇人”,因而,在女性“贞节”问题上道学比儒家要宽容些。例如,《太平广记》记载未婚女子褒女有所感而孕,这在封建礼教社会是要受到道德舆论的谴责和人们的唾弃的,但道教却让她升天成仙并让乡人立祀祭奠。谓:“褒女者,汉中人也。褒君之后,因以为姓。居汉、淝二水之间。幼而好道,冲静无营。既笄,浣纱于浕水上,云雨晦冥,若有所感而孕。父母责之,忧患而疾。……家人追之,但见五云如盖,天乐骇空,幢节导从,见女升天而去。及视车中,空棺而已。邑人立祠祭之。”(《太平广记》卷第六十一《女仙六·褒女》)既然道学对女性的“贞节”问题持宽容态度,那么,它就不会像儒家那样在男女之间层层设防。例如,道教从不把女冠幽禁在道观里,使其整天只知吃斋念经或闭关修炼,而是鼓励女冠四处宣传教义、教理,积极拓展传道的途径,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途径就是女冠与文人墨客之间的酬唱交游,诸如唐朝的李白、白居易等很多名家都曾写下了与女冠唱和的诗作。[6]较之于儒家,道学对于男女两性问题的态度更为开明,它倡导的是自然、健康的两性关系。
(四)对于女性生育伦理的看法不同
在奉行“男尊女卑”的儒家文化中,女性始终被物化,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儒家的两性伦理思想中,同时也体现在儒家的生育伦理思想中。儒家认为,婚姻最重要的目的是“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礼记·婚义》),因此,儒家非常看重女性的生育功能及宗族繁衍,孟子直接宣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儒家甚至将“无子”作为“七出”之一。这样一来,一是导致“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女性需要通过多生儿女来促使宗族兴旺并体现自己的价值,她们因此沦为生育工具;二是导致“重男轻女”的生育行为,女性需要为宗族生出男孩以延续香火,人们因此普遍歧视女婴,甚至出现溺杀女婴的陋习和现象。儒家以“多子多福”和“重男轻女”为主要内容的生育伦理思想既不利于女性的生存和发展,同时也引发了诸多严重的人口社会问题。
注重养生之道的道学反对多生多育而主张节制生育,因为无节制地生育会损耗元精、伤人元气、伐人年命,从根本上不利于人体养生。老子云:“益生曰祥”(《老子》第十五章),亦即贪生纵欲就会灾殃[7]。陶弘景亦曰:“道以精为宝,施人则生人,留之则生身。”(《养性延命录》)按照道学这一主张,女性不必以多子多福作为自己生育活动的道德规范,也不必以无节制地生儿育女作为自己的道德责任。与此同时,道学也坚决反对重男轻女的生育行为,尤其是溺杀女婴的现象,如《太平经》就对该陋习多次予以反对和谴责,认为虐杀女子“乃断绝地统,令使不得复相传生,其后多出绝灭无后世,其罪何重也”,并用宗教伦理鼓励人们制止这种丑恶现象,如果谁能“救冤女之命”,谁就能“得益天算”,“司命易子(行此善者)籍益”[8]。在道学文化中,女性不再是听凭宗族和丈夫摆布的生育机器,而是值得尊敬的神圣的生命缔造者;女婴也并非遭人歧视和任人处置的生命,而是和男婴一样成为值得尊重和爱惜的生命。
(五)对于女性所循人伦礼节的主张不同
道学原本是在批判儒家仁义礼法等思想基础上形成的,这就决定了它们在人伦礼节问题上的分歧。对于人伦礼节,儒家强调礼节之周全及形式之完备,有着重文轻质之倾向。为了培养封建社会和宗族家庭所希冀的理想女性,以汉代女教家班昭所著《女诫》以及唐代宋若华所著《女论语》为代表的各种儒家女书,对女性的待人接物、言谈举止、家务操持、衣食起居等问题予以非常详尽的规定,并要求女性无条件遵循。例如,在妇德问题上,《女论语》不仅要求女性行为要端正,即:“行莫回头,语莫掀唇。坐莫动膝,立莫摇裙。喜莫大笑,怒莫高声”(《女论语·立身第一》),而且要求女性做到循礼有节,即:“凡为女子,当知礼数。女客相过,安排坐具。整顿衣裳,轻行缓步。敛手低声,请过庭户。问候通时,从头称叙。答问殷勤,轻言细语。……如到人家,当知女务。相见传茶,即通事故。说罢起身,再三辞去。主人相留,相筵待遇。酒略沾唇,食无义箸。退盏辞壶,过承推拒。”(《女论语·学礼第三》)这些繁琐的规定不仅容易让人们变得虚伪而致使其人格异化,而且很难为人们所遵守而流于形式主义。
道学在人伦礼节问题上主张重质轻文。道家代表人物庄子极其反对孔孟的“性服忠信,身行仁义,饰礼乐、造人伦,上以忠于世主,下以化于齐民”(《庄子·渔父》)的矫揉造作之作法,在他看来,儒家所谓的仁义礼法都是流于表面形式,它们严重束缚和摧残了人的真性。《庄子·庚桑楚》载老聃弟子庚桑楚对于他的侍女持不同态度的事迹,凡是矜持仁义者都为其疏远,只有淳朴者才能和其一起生活,即:“其妾之挈然仁者远之;拥肿之与居”。庄子借助庚桑楚对侍女的不同态度,表明其对女性遵循人伦礼节问题的看法,他认为,女性应该追求发乎自然真情的忠贞孝慈,实现心灵的自由和个性的解放。道教亦秉承了《周易》的尚简精神,反对儒家的繁文缛节。葛洪就直接批判了儒家伦理失于繁复的弊端:“人伦虽以有礼为贵,但当令足以叙等威而表情敬,何在乎升降揖让之繁重,拜起俯伏之无已邪?”(《抱朴子外篇·省烦》)重质轻文的道教也是要求女性摒弃虚伪的流于表面的形式主义,实现心灵上的情敬。事实上,道教的这种思想结构更有利于伦理规范的贯彻,它将在人们灵魂上打上价值和审美烙印,其深度、强度和持久程度都是不可估量的。[9]
(六)对于女性道德监督机制的设计不同
包括女性伦理在内的整个儒家伦理思想体系具有明显的主体自觉性特征。在伦理道德的实施过程中,儒家主要强调“慎独”之类的主观修身功夫和自我控制方式,因此,它所设计和提供的道德监督机制就是人,这种道德监督机制具有浓郁的理性化特征。基于此,对于女性道德规范的实施和监督,儒家主要诉诸女性的自觉意识,如晋时王廙撰《妇德箴》曰:“团团明月,魄满则缺;亭亭阳晖,曜过则逝。天地犹有盈亏,况华艳之浮孽?是以淑女鉴之,战战乾乾。相彼七出,顺此话言;惧兹屋漏,畏斯新垣。在昧无愧,幽不改虔。”这里显然要求女性在守贞问题上要具备“慎独”之精神。除此之外,儒家还诉诸封建朝廷的奖惩、外在舆论的压力和风俗习惯的约束,如汉代皇帝就采取法令的形式来奖励女性的忠贞节孝行为。据《汉书·宣帝本记》记载,公元前58年(汉神爵四年),诏赐“贞妇顺女”以帛。[10]无论儒家采取哪一种道德监督措施,其实施者都是人。儒家强调人的道德主体性作用固然没错,但是在政治动乱、纲纪松弛、道德沦丧的封建社会变革时期,这种道德监督机制就会显得软弱无力。
相对于儒家道德监督机制的理性色彩,道学尤其是道教设计和提供的道德监督机制充满神学色彩,它是一个“无时不在运转着的从地(地祇)到人(身神)到天(神灵)相通的庞大的鬼神系统”[11]。为了督促女性践行道德规范及加强道德修养,除了诉诸女性自身的努力以及外在的人为奖惩措施之外,道教还专门构造了“神明监督”之说,让天地神明也承担起监管女性履行道德的作用,如《太上感应篇》云:“女不柔顺,不和其室,不敬其夫,每好矜夸,常行妒忌,无行于妻子,失礼于舅姑……如是等罪,司命随其轻重,夺其纪算。”此处“司命”即为掌管人的寿天之神灵。道教的这种道德监督机制不仅在结构上比儒家道德监督机制更为完备和庞大,而且在精神威慑力方面强于儒家道德监督机制。
二、道学女性伦理观与儒家女性伦理观的会通及融合
(一)奉行尊卑等级观念
道学与儒家在女性伦理观上不仅存在对立的一面,而且存在融合的一面,这种融合首先体现在它们都奉行尊卑等级观念。被封建统治阶级奉为正统的儒家文化大力宣扬封建等级观念,极力维护社会尊卑关系。这种尊卑等级观念体现在儒家女性伦理观中不仅是强调“男尊女卑”,要求女性遵循“三从”之道;对于女性之间的关系,儒家也是要求尊卑有序。例如,儒家对于婆媳关系奉行尊母贬妻和重姑贱妇的原则,认为婆婆的地位高于媳妇,要求媳妇曲从婆婆。《女诫·曲从第六》云:“姑云不尔而是,固宜从令;姑云尔而非,犹宜顺命。勿得违戾是非,争分曲直。”儒家对于妻妾关系则奉行贵妻贬妾的原则,认为妻子的地位远高于妾,要求妾尊重嫡妻。《白虎通·嫁娶》云:“妾事夫人如事舅姑,尊嫡绝妒嫉之原。”在儒家看来,封建社会中的各种尊卑等级秩序是天经地义、不可动摇的,这为封建统治者顺利实现其统治提供了最好的理由和辩词。
为了得到官方的认可而实现自身的顺利发展,道学尤其是道教不得不吸取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纲常伦理思想,其中之一即为尊卑等级思想。例如,对于男女关系,《庄子·天道》篇认为夫妇尊卑关系神圣而不可改变:“君先而臣从,父先而子从,兄先而弟从,长先而少从,男先而女从,夫先而妇从。夫尊卑先后,天地之行也,故圣人取象焉。”《太平经》则从男女之间特点的差异以及男女施受地位的不同出发,论证了“男尊女卑”的思想:“故男所以受命者,盈满而有余,其下左右尚各有一实。上者盈满而有余,向常施于下阴,有余积聚而常有实。上施者,应太阳天行也,无不能生,无不能成。下有积聚,应太阴,应地,而有文理应阡陌。左实者应人,右实者应万物。实者核实也,则仁好施,又有核实也,故阳得称尊而贵也。……阴为女,所以卑而贱者,其所受命处,户空而虚,无盈余,又无实,故见卑且贱也。”对于女性之间的关系,道学亦有尊卑之分,如道教的女仙世界就实行西王母统率之下的等级社会秩序,强调“得仙者亦有九品……各有差降,不可超越”(《墉城集仙录》卷四第七)。诸如此类都是道学吸取儒家尊卑等级思想的结果,它们显然违背了道学追求人际平等的思想主旨,成为道学女性伦理思想的一大瑕疵。
(二)倡导“贞顺”之德
儒家非常重视夫妇之伦,认为夫妇是“人伦之始,王化之基”(《毛诗大序》)。为了维护以“夫尊妻卑”为特征的夫妇之伦,儒家极力倡导“贞顺”之德,它不仅要求女性应为自己的丈夫守住贞节,而且要求女性应顺从自己的丈夫及公婆。贞节问题上文已论及,此处仅以女性的柔顺问题为例,对此历代儒者甚为强调。孟子云:“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孟子·藤文公下》)汉儒董仲舒说:“妻不奉夫之命,则绝,夫不言‘及’是也。曰:不奉顺于天者,其罪如此。”(《春秋繁露·顺命》)宋儒邵雍亦曰:“妻不从夫,其妻必孽。”(《击壤集》卷一六《治乱吟》之四)通过宣扬“贞顺”思想,儒家为封建宗法家庭打造出理想妻子。儒家的这种“贞顺”思想显然是其根据男性的需要而提出的,它们充分体现了封建传统社会男子的自私自利。
诞生在封建宗法社会中的道学亦重视夫妇之伦。道教中除了全真道之外,其余教派都允许修道者有着婚姻家庭生活。在夫妇人伦关系问题上,道学尤其是道教吸纳儒家的“贞顺”思想。如道教善书《赤松子中诫经》云:“妇人孝顺翁婆,敬顺夫婿,清贞洁行,饮气吞声,叁省晨昏,和颜悦色,无私奉上”。后期道教尤为重视“妇贞”思想,并将其作为能否修道成仙的先决条件之一。如道经《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云:“诸欲修道者,务必臣忠、子孝、夫信、妇贞、兄敬、弟顺,内无二心”。《上方灵宝无极至道开化真经》还专门设置“女贞章”,其文云:“良臣弗事二主,烈女匪聘再夫。女之尚者贞烈而已,女之道者洁操而已。……贞孝弗违,善弗怠,若能犹是,可谓节妇矣。”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道教吸取儒家的“妇贞”思想并对其予以重视,但是道教对于女性的贞节要求并没有儒家那么苛刻,道教中女性丧偶或离异后是可以再嫁的,前文中也论及了道教对于女性贞节的宽容态度。
(三)重视“孝亲”思想
出于对生命创造者的感恩之情与敬畏之心,儒家极为重视“孝亲”思想。《论语·学而》云:“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孝经》亦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儒家反复强调子女应该孝顺自己的父母,要求儿女对父母履行敬养、无违、服从等孝道,甚至鼓励人们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以尽孝。如《后汉书》就记载了孝女曹娥舍命尽孝的事迹:“父盱,能弦歌,为巫祝。汉安二年五月五日,于县江溯涛迎婆娑神,溺死,不得尸骸。娥年十四,乃沿江号哭,昼夜不绝声,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至元嘉元年,县长度尚改葬娥于江南道傍,为立碑焉。”(《后汉书·烈女传》)此类孝女在儒家经典中时有记载。虽然儒家“孝亲”思想难免有偏激之处,这些偏激之处束缚了个体自由,导致封建家长专制现象,甚至造成伦理价值观念的倒错,但其对于家庭和睦及社会稳定确实起到了重妻作用。
道学在其发展过程中融摄了儒家的“孝亲”思想。《太平经》、《文帝孝经》、《坤元经》等多部道教经典、劝善书、丹书都不遗余力地宣扬儒家的“孝亲”思想,并把“孝亲”作为女性修道者修炼性命的重要外功。如《太平经》云:“父母者,生之根也……寿孝者,神灵所爱好也。不寿孝者,百祸所趋也。”《坤元经·玄贞五皇姑女丹法言秘诀》亦曰:“直论世上女子,易得修为,不至不以孝善仁慈为根本。”为了督促女性修道者履行“孝道”,道教还运用因果报应论、构造“神灵监督”之说以及诉诸戒律的强制作用,如《赤松子中诫经》云:“妇人违背父母,不孝翁婆……皆夺福寿,恶病缠身,生遭人憎,死坠地狱。”《女丹十则》规定:“第一戒:要孝养翁姑。”这些作法非常有利于儒家“孝亲”思想的贯彻和执行,道教由此成为推广儒家“孝亲”思想的得力帮手。
(四)推行“五常”之道
在女性伦理观上,道学不仅吸取了上述三个方面的儒家思想,而且直接把儒家的“五常”之道纳入其伦理范畴。所谓“五常”,“谓仁、义、礼、智、信也。仁者不忍也,施生爱人也。义者宜也,断决得中也。礼者履也,履道成文也。智者知也,独见前闻,不惑于事,见微知著也。信者诚也,专一不移也”。(《白虎通·情性》)作为调控“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及“五伦”(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项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儒家的“五常”之道无疑适用于女性,是其女性伦理中的重要原则与规范之一。事实上,儒家对女性所实行的以“三从四德”为主要内容的各种礼教和德教无不体现了“五常”之道。虽然推行“五常”之道使得女性注重气节和品德,这对于女性塑造良好的性格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也对女性起到奴役与束缚的消极作用。
道教吸取了儒家的“五常”之道,并在原有内涵的基础上予以新的诠释和补充:所谓“仁”,是要人们慈悲不杀,放生度化,养护自身;所谓“义”,是要赏善罚恶,谦让戒盗;所谓“礼”,是要敬老恭少,贞正无淫;所谓“智”,是要化愚学圣,节酒无昏;所谓“信”,是要守忠抱一,不怀疑惑。[12]这种“五常”之道体现在道学女性伦理中,则是要求女性恪守封建礼教,忠孝、和顺、仁信,与人为善,爱护生命,道教以此作为女性修道成仙的重要条件,即如葛洪所言:“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抱朴子内篇·对俗》)为了促使其教徒恪守“五常”之道,道教还把“五常”与人体的肝、肺、心、肾、脾“五脏”相附会,赋予其相互制约的关系,使得道教伦理形成独特的表现形式。这样一来,儒家“五常”之道的推行得到更有力的保障。
三、结语
总体而言,道学女性伦理思想比儒家女性伦理思想更为积极,尤其从这两者的冲突中,可看出前者在很多方面对后者起到一定的弥补作用。例如,道学对女性地位和价值的肯定在一定程度上制衡了儒家“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等语言霸权地位的无限扩张;道学对女性人格的赞美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儒家贬低女性人格的缺陷,使人们重新认识女性品质及其宝贵价值;道学对女性“贞节”的宽容态度及其对男女交往的开明态度,对于儒家过于强调女性“贞节”及严防男女的偏激态度起到重要的矫正作用;道学的“节制生育”和“男女一样”的生育伦理,无疑是对儒家“多子多福”和“重男轻女”的生育伦理的一种纠正;道学女性伦理思想的重质轻文之特质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儒家女性伦理失于繁复之弊端;道学女性伦理思想以神学为强大后盾,则对高理论性、低操作性的儒家纲常伦理起到纠偏救弊之作用。
然而,在儒家一统天下的封建宗法社会中,道学女性伦理思想的积极性因素难以凸显,它对儒家女性伦理思想的弥补作用并不能充分发挥。相反,由于儒家女性伦理思想在封建社会的正统地位及强大影响力,使得处于边缘地位的道学女性伦理思想不断向儒家女性伦理思想靠拢,尤其是随着三教合一潮流的发展,这两者的相通相融趋势愈发严重。虽然道学女性伦理的儒学化可以扩大其影响力,但它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道学女性伦理思想的个性发展,使得其特异性逐渐淡化模糊,最终蜕变为维护封建纲常伦理秩序的御用工具。
[收稿日期]2012-03-28
标签:儒家论文; 易经论文; 国学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墉城集仙录论文; 老子论文; 太平经论文; 女论语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