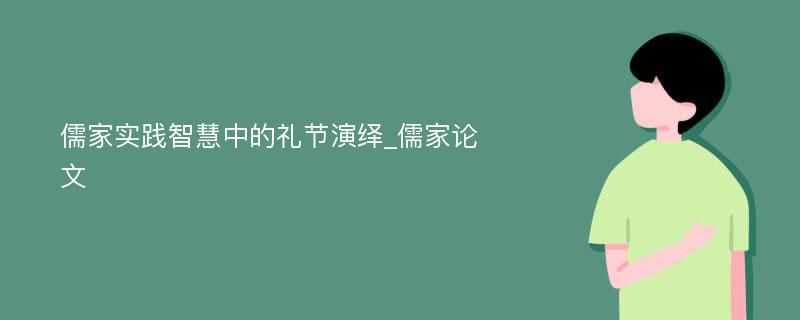
儒家实践智慧的礼学演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智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44.7 一、朱子对礼的实践性的认识 儒家的礼学可以说是实践智慧的集中体现。礼起源于中国上古先民的日常生产与生活实践,同时也在后世的日常生活中逐步得到发展与革新,因此,礼本身就是一种实践性很强的专门之学。朱熹不仅是北宋以来理学的集大成者,也是两宋经学尤其是礼经学领域的翘楚,在礼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他对礼的实践性特质同样有着深刻的认识,这从他在《论语集注》中对《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一句的注释即可看出:“雅,常也。执,守也。诗以理情性,书以道政事,礼以谨节文,皆切于日用之实,故常言之。礼独言执者,以人所执守而言,非徒诵说而已也。”(《朱子全书》第6册,第125页)他认为,诗、书与礼都“切于日用之实”,即与实践紧密相关。其中唯有礼强调“执”,则是因为礼尤重实践,这便明确指出了礼与其他诸经的区别所在。因此,他强调说:“礼者,履也。谓昔之诵而说者,至是可践而履也。”又道:“所谓礼之实者,皆践而履之矣。”(《朱子全书》第24册,第3585页)由此可见,在朱熹那里,礼的实践性实为礼的根本特征之一,礼是诗、书等诸经之微言大义在日常生活中的贯彻与实践。 与此同时,朱熹也以儒家的实践工夫作为儒学与佛老之学的区别之一,并以之为针对二氏的主要批判武器,而这一实践工夫的核心便是礼。如他曾批评佛教的“克己”之说道:“所以不可行者,却无‘复礼’一段事。既克己,若不复礼,如何得?”(《朱子全书》第15册,第1460页)当时,许多理学家一方面抵拒佛老之学,另一方面却又“忽视了作为理的具体外化与落实的礼文,失去了下学的功夫,这样也就无法真正与佛道划清界限”。(牟坚)即使是朱熹至为推崇的二程(尤其是程颢),也难免于这方面的问题。朱熹曾指出:“明道谓:‘克己则私心去,自能复礼;虽不学文,而礼意已得。’如此等语,也说忒高了。孔子说‘克己复礼’,便都是实。”(《朱子全书》第15册,第1453页)朱熹强调,孔子的“克己复礼”重在落于实处,将高妙之理贯通于具体的礼文的实践,即“下学”的工夫。而他对二程的弟子如谢良佐、范祖禹、游酢、杨时等人更是于此多有批评,如曰:“大抵谢与范,只管就见处,却不若行上做功夫。只管扛,扛得大,下稍直是没着处”。(同上,第1476页)认为他们只顾讲论与求索“上达”之“理”,缺乏贯通上达与下学的践履精神。 在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的鹅湖之会上,朱熹与陆九渊兄弟就“道问学”与“尊德性”的路径展开论辩。据陆九渊门人记载:“鹅湖之会,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陆九渊集》,第491页)陆九渊认为“圣人教人,只是就人日用处开端”(同上,第432页),强调于日常实践中“切己自反,改过迁善”(同上,第400页),故以朱熹的为教与为学乃“支离事业”,有流于空谈而轻忽道德践履之虞。朱熹则认为陆氏兄弟的主张过于“易简”,“似闻有脱略文字、直趋本根之意”(《朱子全书》第22册,第2190页),会导致为学者疏于学问、不求穷尽义理之微,恐沦入佛禅。但朱熹此后也由陆九渊的批评而对自己的教学主张作了反思,他在与学者论学时说道:“陆子静专以尊德性诲人,故游其门者多践履之士,然于道问学处欠了。某教人岂不是道问学处多了些子?故游某之门者践履多不及之。”(见《陆九渊集》,第400页)因此,朱熹中年以后格外强调礼的“下学”实践工夫,这除了他对儒家礼学一以贯之的实践精神与实践智慧的抉发之外,恐怕也是受到了陆九渊重视日常践履的思想的影响。 二、“因人之情”:朱子礼学实践的情感原则 人类生活中的情感因素是礼乐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如《礼记·乐记》道:“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礼记·坊记》也说:“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朱熹与其弟子吕焘有过一段讨论,就谈及了情感作为“人心之用”对于礼的实践的影响: 问:“‘林放问礼之本’一章,某看来,奢、易是务饰于外,俭、质是由中。”曰:“也如此说不得。天下事,那一件不由心做。但俭、戚底发未尽,在奢、易底发过去了,然都由心发。譬之于花,只是一个花心,却有开而未全开底,有开而将离披底。那俭、质底便犹花之未全开,奢、易底便犹花之离披者。且如人之居丧,其初岂无些哀心,外面装点得来过当,便埋没了那哀心。人之行礼,其初岂无些恭敬之心,亦缘他装点得来过当,便埋没了那恭敬之心……”(《朱子全书》第14册,第886页) 《论语·八佾》里,林放问礼之本,孔子赞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朱熹对这一段格外重视。吕焘认为:俭、戚作为礼之本,显然是由人心所发,然后体现于礼的实践;而奢、易则是“务饰于外”,只是人的外部行为,并非人心的发显。朱熹却指出吕焘的说法有问题——“天下事那一件不由心做?”认为在礼的实践中人所体现出的或俭、戚或奢、易的态度均源于“心”,即“人心之用”,亦即“情”,只是如同花开那样有“未全开”与“离披”的不同。 朱熹认为人的主观情感在礼的日常践履中有着重要的依据作用,尤其是在古礼今用时,“人情”更是一个主导性因素。如他指出:“某尝说,古者之礼,今只是存他一个大概,令勿散失,使人知其意义,要之,必不可尽行。如始丧一段,必若欲尽行,则必无哀戚哭泣之情。何者?方哀苦荒迷之际,有何心情一一如古礼之繁细委曲。”(《朱子全书》第17册,第3013页)他主张古礼只可行个大概,不能尽行,主要是因为古礼繁缛,如若完全依其行事,则人内心的真实情感就难以完整表达。所以,他强调礼的施行最重要的是使情感得以完整与合理地表达出来:“但使哀戚之情尽耳”(同上,第3014页),而不仅仅是关注礼的外在形式。 然而,朱熹又说:“感于物者心也,其动者情也,情根乎性而宰乎心,心为之宰,则其动也无不中节矣。”(《朱子全书》第21册,第1395页)情为心之发动,而心则为情的主宰,他此处的“心”似乎主要是指认知、思辨之心,“心为之宰”强调的是道德理性对于情感的控制。针对心与性、情的关系,朱熹曾有过详尽的解说,如曰:“性者,心之理也;情者,心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朱子全书》第23册,第3254页)陈来解释朱熹“性为心之理”的观点道:“性之为理不仅在于它是心所禀受的一种实体(天地之理),而且在于性就是人的内心原则、本质和规律。”(陈来,2000年,第185页)由此看来,性是人心的“原则、本质和规律”,情显然就是其外在表现与运用。朱熹道:“及其发而用,则仁者为恻隐,义者为羞恶,礼者为恭敬,智者为是非。随事发见,各有苗脉,不相淆乱,所谓情也。”(《朱子全书》第24册,第3589页)情作为性的发用,应该是井然有序的,但这只是一种理想的境界,现实生活中的情感表现有时是无序的,无序则有害于情感的正常表达,而这又正是礼得以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动因。如《礼记·问丧》就说:“礼义之经也,非从天降也,非从地出也,人情而已矣。”礼以合理安排情感的表达方式为首要功能,我们或可称之为“情感原则”,它是指在礼的实践中充分尊重和重视人的主观情感与心理体验,同时又以道德理性引导和规范人之情感的实践原则。 具体而言,朱熹关于礼之实践的情感原则主要有以下两点: 1.“敬” “敬”作为一种重要的道德心理与道德情感元素,被朱熹视为礼之实践的主要伦理与心理原则之一。朱熹的门人叶贺孙曾问祭礼的实践问题:“祭礼,古今事体不同,行之多窒碍,如何?”朱熹答曰:“有何难行?但以诚敬为主,其它仪则,随家丰约”。(同上,第3048页)朱熹指出,祭礼的实践以“敬”为主,只要心存“诚敬”,具体仪则可以依照家庭的贫富情况量力而行。这说明礼的实践主要取决于主体情感与态度的“敬”,而非尽在外在的仪节形式。 又如朱熹在《家礼序》中言:“凡礼有本有文。自其施于家者言之,则名分之守、爱敬之实,其本也;冠昏丧祭仪章度数者,其文也。……大抵谨名分、崇敬爱以为之本,至其施行之际,则又略浮文、务本实,以窃自附于孔子从先进之遗意。”(《朱子全书》第7册,第873页)告诫人们在具体实践中必须认真把握礼的文、质关系,不得因礼之“浮文”而忽略了其“崇敬爱”之“本实”。 可见,无论是祭礼中的“诚敬”还是日常人际交往礼仪中的“爱敬”,其核心都在于“敬”,“敬”构成了朱熹礼学实践的情感原则的核心要素。 2.“礼宜从厚” “礼宜从厚”是朱熹在日常讲论与实践礼的过程中,面对一时无法考证其源流而难以决断是非的具体仪则时,依据礼“出于人情”的发生论所提出来的实践原则,它充分体现出了朱熹的礼学实践观中所蕴含的充满温情与善意的情感因素,是另一种典型的情感原则。如其弟子叶贺孙问“改葬,缌”之礼道:“‘改葬,缌。’郑玄以为终缌之月数而除服,王肃以为葬毕便除,如何?”朱熹答曰:“如今不可考。礼宜从厚,当如郑氏。”(《朱子全书》第17册,第2097页)“缌”指缌麻,乃五种丧服(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中最低的一等,服期三个月。所谓“改葬,缌”,原文出自《礼记·丧服》,是指为已故亲人改葬之后所服之丧。改葬的情况发生于坟墓因自然力等原因而崩坏之时,按郑玄所说,此时必须为死者服缌的有三种情况:臣为君,子为父,妻为夫,而且需要服满三个月。但魏晋学者王肃却认为改葬之礼毕即可除缌服。针对前代学者间的上述分歧,叶贺孙有些无所适从。朱熹在难以准确考证双方论据的情况下,便强调“礼宜从厚”的情感原则,坚持以郑说为准。 从朱熹上述以情释礼的解经与实践的方法论来看,在丧祭礼的制订和施行中采取“从厚”的原则,可以更充分地表达在世亲人对死者的悼念哀思之情,这就体现出了一种温厚质朴的情感伦理。当然,朱熹“礼宜从厚”的主张也并非没有节制,而是必须“无嫌于僭”,只能在礼制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不得违背礼义。如李继善在书信中指出,《礼记·檀弓》说在举行祔祭之后只须于每天的早、晚两个时段哭祭,并行朔奠之礼;而张载认为三年丧期之内都不能撤除祭奠用的供桌,因此有每日祭的要求;司马光则主张三年中每日早晚都应当行馈食礼。张载与司马光的看法均与礼经不相吻合,故而李继善问朱熹该如何处置。朱熹回信说:“此等处,今世见行之礼,不害其为厚,而又无嫌于僭,且当从之。”(《朱子全书》第23册,第3048页)他认为两者所言都是当今比较通行的礼制,只要不妨害“礼宜从厚”的原则,又没有僭越礼制的嫌疑,姑且遵照施行,并无不妥。 三、经权“相济”:朱子礼学实践的辩证智慧 “敬”与“礼宜从厚”等是朱熹在礼的实践中提出来的情感原则,而针对礼的具体实践,朱熹又提出了经权“相济”的辩证法则,体现出了较高的理论思辨水平。综合朱熹对经、权之含义及关系的阐述,我们大致可以归纳如下: 首先,经是大经大法,为事物的根本之理;而权则是对“道”在某些复杂的“精微曲折处”作出的变通和补充,并非常态,但二者均为“道”在日常实践中的运用。如他说:“经者,道之常也;权者,道之变也。道是个统体,贯乎经与权。”(《朱子全书》第15册,第1378页)又道:“盖经者只是存得个大法,正当底道理而已。至精微曲折处,固非经之所能尽也。所谓权者,于精微曲折处曲尽其宜,以济经之所不及耳。”(同上,第1381页) 其次,经与权既“自是两物”,又“相干涉”,体现为一种辩证关系。朱熹说:“若说权自权,经自经,不相干涉,固不可。若说事须用权,经须权而行,权只是经,则权与经又全无分别。观孔子曰‘可与立,未可与权’,孟子曰‘嫂溺援之以手’,则权与经须有异处。虽有异,而权实不离乎经也。”(同上)朱熹认为,经、权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二者之间又必须“有个界分”,因为权毕竟只是偶一为之,并非经的所有实践运用都须借助于权才行,因此,“伊川所谓‘权便是经’,亦少分别。”(同上,第1378页) 朱熹强调经、权不相离,经为纲,权为经之变,同时也是对经在实践中的补充,此即经权“相济”的思想。那么在具体的礼的实践中,经权“相济”的思想又是如何体现的呢?笔者认为它主要体现在“中”与“时”两个方面。 1.“中” 在《孟子·离娄章句上》中,孟子针对淳于髡“嫂溺,则援之以手乎?”作了精妙的回答:“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朱熹对此一句中的经权之辨十分重视,曾在多种场合予以反复讨论。在《孟子集注》中,他对“权”的解释则很明确地提及了“中”之于礼学经权之辨的关键性地位:“权,称锤也,称物轻重而往来以取中者也。权而得中,是乃礼也。”(《朱子全书》第6册,第346页)朱熹于此强调“权而得中”便是礼之经。那么,何谓“中”?他解释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同上,第32页)“中”强调的是事物的发展不仅完全合乎规律,而且恰到好处,处于最理想的状态。在中国传统哲学里,“中”既是一种高妙的思辨与实践智慧,同时也是一种至高的道德境界,“中庸”与“中和”是其集中体现。“中庸”一词最早出现于《论语·雍也》:“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但孔子对于中庸之道的直接论述并不多。到了子思,其《中庸》一篇则对孔子的“中庸”说作了系统发挥,然其核心思想却是“中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与“中和”同源于“中”,但两者之间仍有着区别:前者更多的是倾向于一种方法论,常被人们作为思辨与实践智慧运用于具体实践之中;后者更侧重为一种理想的道德境界,它是由个体的情感与行为的中正和谐推衍至人类社会与自然万物间的合理与有序的状态。 朱熹对此有着深刻认识,他对“中庸”与“中和”的区别与联系作了细致的分梳:“以性情言之,谓之中和;以礼义言之,谓之中庸,其实一也。以中对和而言,则中者体,和者用,此是指已发、未发而言。以中对庸而言,则又折转来,庸是体,中是用。如伊川云‘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是也。此‘中’却是‘时中’‘执中’之中。以中和对中庸而言,则中和又是体,中庸又是用。”(《朱子全书》第16册,第2056页)按朱熹的说法,对于个体而言,“中和”主人之性情,“中庸”则关涉礼义,二者本为一物,即都是“中”的运用,只是所涉层面和范围不同。而“中和”与“中庸”之间又是体用关系,“中和”谓人之性情的实质,“中庸”乃礼义(在朱熹处亦即天理)在生活中的具体实践,二者的体用关系也就体现出了朱熹礼学实践观中作为道德实践主体的人的道德品性与情感的本体意义。同时,也正由于这一层体用关系的认识,在礼的实践原则的讨论中,朱熹所常言之“礼贵得中”之“中”就多是指“中庸”。而《礼记·丧服四制》说“贤者不得过,不肖者不得不及,此丧之中庸也”,可见“中庸”作为礼的实践原则,在早期礼学中就已得到了明确运用。到了朱熹这里,则对之作了进一步的肯定和理学化的形上升华,如他对“中庸之中”的“已发”“未发”问题的解释便是如此: 至之问:“‘中’含二义:有未发之中,有随时之中。”曰:“《中庸》一书,本只是说随时之中。然本其所以有此随时之中,缘是有那未发之中,后面方说‘时中’去。” “‘中庸’之‘中’,本是无过无不及之中,大旨在时中上。若推其中,则自喜怒哀乐未发之中,而为‘时中’之中。未发之中是体,‘时中’之中是用。中字兼中和言之。”(同上,第2004-2005页) 朱熹的“已发”“未发”其实质乃是一种直觉式的心理体验,描述的是道德心理的不同阶段或状态。陈来曾指出:“理学家因出入于佛教禅宗,也注意到这一心理体验,然而与佛教不同,他们企图把这种内心体验作为提高人的品格境界和心性修养的手段。”(陈来,2000年,第158页)对于中庸之“中”而言,朱熹将之分为“未发之中”和“时中之中”,“时中之中”显然便是“已发之中”了。而前者是体,后者是用,由“未发之中”生发出“时中之中”。他讲“中字兼中和言之”,“中和”当是指“未发之中”,“中庸”更多的时候则落脚于“时中之中”。所以,朱熹主张“礼贵得中”,在具体运用当中关注最多的仍是“时中之中”,即“中庸”的方法论意义。 而朱熹之所以反复强调“中”的“已发”“未发”,其主旨就在于提醒人们在具体的道德涵养和礼的实践活动中必须注意解决好“未发之中”和“时中之中”的关系。譬如他在《答刘平甫》的书信里指出:“古礼庙无二主”,祭祀先祖必须由宗子于庙中主持进行。春秋战国时代,国别较多,常有宗子身处国外而不得不由庶子代祭的情况,然庶子不得入庙,只能对着祖宗墓地筑坛而祭。但在宋代,宗子或奉仕于朝,或游宦四方,通常不出一国之内,因此不得不主祭,有时却又离家庙甚远。这时即可施行俗礼中的“二主”之法——“今有祠版,又有影,是有二主矣”,而“别宗子所在,奉二主以从之,于事为宜”;同时,“支子所得自主之祭,则当留以奉祀,不得随宗子而徙也。”目的就是要“上不失萃聚祖考精神之义,二主常相依,则精神不分矣。下使宗子得以田禄荐享,祖宗宜亦歆之”。让仕宦在外的宗子和留守在家的庶子(支子)各有所祭,以使先祖“精神不分”并从而“歆之”。这样做的依据和原则就是“中”,“处礼之变,而不失其中”,在古今异礼之两端取一折中方式,以“酌其中制,适古今之宜”。(《朱子全书》第22册,第1795-1796页) 从方法论来看,朱熹在此强调于“古礼庙无二主”和“奉二主以从之”之间“酌其中制”,则是“时中之中”;就本体论而言,若要“适古今之宜”,就必须坚守礼之本义,既能安顿萃聚祖考的精气与魂魄,也抚慰和满足了宗子荐享祖宗的孝敬之情,确保宗法伦理之大本,这一番周详细密的思虑显然又是出于“未发之中”。在此,礼的实践中“未发之中”和“时中之中”有机结合在一起,即完美地展现了朱熹经权“相济”的实践智慧。 2.“时” 朱熹认为“中”有“未发之中”和“时中之中”两义,“中”便蕴含了“时”的意涵在其间。实际上,“礼贵得中”,“时”也是得“中”的一个必要条件。“时”乃中国哲学里十分重要的概念,古人无论是从事生产实践,还是在具体的日常生活中都有着很强的“时”的观念。《尚书·尧典》中说:“(帝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作者认为人类的“时”由尧命羲和所定,人类生活中的一切事务都要依时而行,即所谓“百揆时叙”。具体而言,又如舜在给禹、后稷等人分配任务时所说:“禹,汝平水土,惟时懋哉!”“汝后稷,播时百谷”(《尚书·舜典》),等等,都强调了“时”在生产与生活中的重要性。《左传·文公十八年》道:“舜臣尧,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地平天成。”显然作者在《尚书》所论的基础上也是认为遵守“时序”是使得天地安泰、人事顺遂的基础。此外,对于个人情感的表达来说,同样也有着“时”的规定。郑伯会见虢叔时便指出:“寡人闻之:哀乐失时,殃咎必至。”(《左传·庄公二十年》)而在《左传·隐公十一年》中,作者则直接将“时”与礼结合起来:“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相时而动,无累后人,可谓知礼矣。”“相时而动”成为了“知礼”的重要表现。到了《易传》,作者在总结前人对“时”的哲学与伦理的种种思考之后,进一步引申并提炼出了“与时偕行”的概念,成为了“时”在中国哲学范畴里最基本和最典型的内涵。“与时偕行”,实际上应当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1)指的是天地自然以及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即都是随“时”而变,这也是《易经》之“易”的本义;(2)人当顺“时”而变,顺应自然与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相时而动”,“量力而行”。这两层含义中,前者是对规律的揭示,具理论价值;后者是对人类社会实践的指导,更具实践意义。《左传》将懂得“时”的观念视为“知礼”,可见古人早已熟知“与时偕行”的实践智慧在礼的实践活动中有着重要的价值。到了《礼记·礼器》,就更是十分明确地指出:“礼,时为大”,将“时”看成了礼的重要实践原则。“时”的观点在朱熹礼学实践观中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如他说:“是圣人固用古礼,亦有随时之义”(《朱子全书》第17册,第2947页),便强调古礼在现实生活里的具体实践应当坚持“时”的原则。 朱熹向来强调《仪礼》中的丧葬制度难以尽行,理由便是在未殡之前逝者的亲人往往悲痛难抑,无法按照仪节规定一一施礼。这也是朱熹缘情释礼的一个典型例证。其缘情说礼的解经方式又是和他强调“时”的礼学实践论一脉相承的,二者都以宋人疑经改经的学术风气为背景。在礼的具体实践活动中,他认为即使是圣人也会依循当世风俗来重新诠释与制定礼法,而礼的发展本身也就是“逐时增添”起来的,这就体现出了“与时偕行”的理念。又正因为礼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增添内容,有愈发烦琐的趋势,学者必须参酌古今时势对之加以修订和简化,使之易于施行。如他在和弟子关于“丧礼制度节目”的讨论中就说:“礼,时为大。某尝谓,衣冠本以便身,古人亦未必一一有义。又是逐时增添,名物愈繁。若要可行,须是酌古之制,去其重复,使之简易,然后可。”(《朱子全书》第17册,第3002页)不过,其底线则是“不碍理”,即以“理”为最基本的标准。《孟子·离娄下》说:“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朱熹解释道:“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则随事而顺理,因时而处宜,岂为是哉?”(《朱子全书》第6册,第355页)他认为孟子所谓的“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即源于人们对“理”的辨识不清,这个“理”便是经或经之根本,乃行礼时的大本大原。所以人们必须“顺理”“处宜”,其原则就是“随事”与“因时”,这正是“时”的观念的两个方面。而“时”所体现的则是权,其与“理”(或曰经)的有机结合即充分体现出了朱熹经权“相济”的礼学实践智慧。 经权“相济”是朱子礼学运用于实践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它所体现出的是儒家以其德性主义本质为基础的辩证的实践智慧,它与前文所述的“因人之情”的情感原则一起,共同构成了朱熹的礼学实践哲学体系。礼的产生与发展本就有一个从人类生活体验上升到生命体验的过程,朱熹礼学实践论的成熟,更是体现出了他对礼学之于生活体验与生命体验的总结与认识,并为儒家的实践智慧提供了一个可靠的理论样本。 关于儒家的实践智慧,陈来在肯定“儒家哲学思想的特点是:突出人的实践智慧,而不突出思辨的理论智慧”的基础上,总结出了这样几个特征:“儒家的实践智慧始终是强调以道德为基础,从不脱离德性;同时,儒家的实践智慧又突出体现在重视修身成己的向度,亦即个人内心的全面自我转化;最后,儒家哲学思想总是强调实践智慧必须化为实践的行动,达到知行合一的境界。”(陈来,2014年)而从朱熹的礼学实践观来看,儒家的实践智慧也还有着重视实践主体的情感与心理体验的情感性特征,以及较强烈的思辨理性色彩,可谓情理并重。当然,朱熹礼学实践观所具备的思辨理性特征并非出于完全自觉的体系性的理论建构,同样未能“突出思辨的理论智慧”,但他对礼学的传承与推广的贡献则是有史可鉴的。而其情理并重的礼学实践智慧,无论是在他《仪礼经传通解》《家礼》等礼学撰著还是礼学的日常讲论与实践活动中,都有着淋漓尽致的展现,是朱子礼学成就的方法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