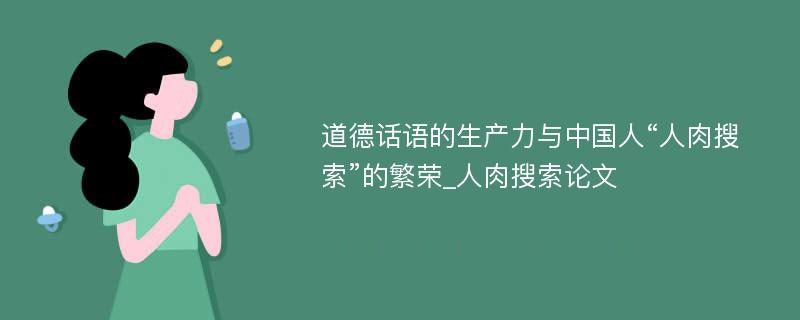
道德话语的生产性力量及中国式“人肉搜索”的勃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肉论文,话语论文,道德论文,力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2009-08-03
一、中国式“人肉搜索”的缘起及发展
2008年中国网络十大关键词中,“人肉搜索”榜上有名。虽然是非权威机构的排行榜,但由此可见“人肉搜索”在中国网络媒体及社会中产生的广泛影响。从技术角度来讲,“人肉搜索”是搜索引擎的一种,类似于“爱问”、“知道”一类的提问、回答模式。提问者提出问题,感兴趣的网民跟帖来回答、评价提问者的问题。“人肉搜索”引擎是基于优化传统搜索引擎的搜索结果、使信息定位更加准确而产生的一种行为模式。具体来说,“人肉搜索”就是运用人际关系,借助于网络的匿名平台,一人发动搜索,众网民从不同途径进行挖掘,从而获得某人的具体信息,并将其公布于网络的搜索方式。“人肉搜索”主要通过发帖、回帖的方式,在网络中形成一个匿名而广泛的对话空间。这一行为不仅完成了搜索过程,而且通过网民的个人话语及对某人、某事进行的评价,形成了相对一致的意见和情绪空间,推动了现实生活中被“搜索”事件的发展。
“人肉搜索”引擎的尝试最初源于猫扑网,是猫扑论坛中某网民求助于其他网民以搜寻信息的一种行为方式,使用之初并没有产生太大的效果。2001年的“陈自瑶事件”开创了“人肉搜索”的先例,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人肉搜索”事件,但并未引起轰动。“人肉搜索”引擎真正产生广泛影响的是2006年轰动网络的“虐猫”事件。2006年2月26日,某网民在网上公布了一组一名女子用高跟鞋踩踏一只小猫致死的视频截图,激起了网友的愤怒。很快就有网友将“虐猫女”的头像制成了“宇宙A级通缉令”并发动“人肉搜索”。不到六天,参与虐猫的人被网友们从茫茫人海中如剥茧抽丝般揪了出来,并将他们的身份信息暴露在网上,参与虐猫的几个人在舆论的重压之下有的丢了工作,有的作出检讨,现实生活也因此发生了巨大变故。在此事件中,“人肉搜索”引擎第一次显示了它的巨大威力。此后的“铜须门”事件再次掀起了网络“人肉搜索”的高潮;一年后的“死亡日记”事件更是催生了中国反对“人肉搜索”的第一案;2008年汶川地震后,发生了辽宁女辱骂地震事件,以及“Die豹”(网名)事件,还有“很黄很暴力”事件、“海淀艺校”事件、“彭宇案”、“菊花香香”事件、林稼祥案以及南京房产局局长周久耕案等等,都曾掀起了“人肉搜索”的高潮,并证实了“人肉搜索”对现实社会带来的影响。
虽然有人认为“人肉搜索”“成为中国转型期公民社会与政府体制‘双重不规范’条件下公民生活的一种替代性机制,具有公益性和互助性的特征”[1]6,并在公共领域确实发挥了网络舆论监督的作用,但这类现象毕竟是“中国特色”的替代性机制。正如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和英国《卫报》所指出的,“人肉搜索”引擎是中国网络出现的一种独特现象,也是中国的一种奇特现象①。
除了依托网络平台外,“人肉搜索”发挥作用主要是依靠“道德话语”及其所产生的生产性力量,这是“人肉搜索”最基本的话语特征。道德话语借助于网络媒体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酵下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量,影响着现实生活中具体事件的发展及涉入事件的个体的生活。
二、“人肉搜索”中的道德话语
虽然“人肉搜索”是一种搜索机制,但其与传统的搜索引擎和现实生活中的“寻找”行为有着本质的不同。“人肉搜索”之所以能够实现,其前提是人们享受用道德话语建构事件的过程,参与其中会使参与者得到“维护正义”和“道德审判”的快感。事件披露依托于网络媒介,传播过程不断得到网民的认同和参与,因此,无论是参与搜索的网民,还是社会公众,对“人肉搜索”事件的认知、判断也是在用话语生产新的意义。
通过对“虐猫”事件、“铜须门”事件、“死亡日记”事件和“Die豹”事件的梳理,我们发现这些“人肉搜索”事件的一个共同特征是:道德话语在“人肉搜索”事件中起着重要作用,即网民运用道德标准对搜索对象的行为作出判断后,便会用以价值判断为主的道德话语对搜索对象(不仅是某个人的某个行为,而且是对其整个人)作出整体性评价(这种评价常常是完全肯定或者完全否定的),从而将其构建成一个网络话语事件。因此,道德话语成为“人肉搜索”事件主要的建构话语,并具有不同于其他媒介话语的特征。道德话语的特征主要通过道德语言的使用表现出来。
从词汇角度来看,道德语言的基本特征是评价性词汇的使用。道德语言的“主要形式是价值判断……它既具有‘描述性意义’,也具有‘评价性意义’,因此,在某种意义上,道德语言既能陈述事实,也能规定或引导人们的行为,指导人们作出各种行为选择和原则决定(decisions of principles)……道德语言的评价性意义是基本的、第一位的,描述性意义则是从属的、第二位的,其评价性功能是通过各种价值词来履行的”[2]5。比如,在“铜须门”事件中,网民们对“幽月儿”和“铜须”的行为进行描述和评价时使用的多是评价性词汇。如用“骚货”、“垃圾”、“无耻”、“下贱”、“放荡”、“不要脸”、“败类”、“破鞋”、“不可饶恕”、“婊子”等词汇来评价“幽月儿”;用“败类”、“恶心”、“不可饶恕”等词汇来评价“铜须”。网民对这种“不道德”行为作出相对一致的判断,用极具情感煽动性的评价性词汇唤起更多网民的参与和公众的关注。
从句子角度来看,道德语言多是运用确定的、结论式的判断句。“人类使用道德语言的用意,在于进行道德判断,而人类进行道德判断的基本前提是某种特定的标准或准则。它们是在人类时代更迭的过程中历史地形成和固定下来的……而且,某种标准或者原则保持越持久,越有连贯性和一致性,其所显示的描述力量就越大,也就越有权威性的评价力量。”[2]5因此,道德语言在人们评价某事以及采取的行动中起着重要作用,这种作用的发挥在句子的使用方面表现为陈述句或结论式的判断句。比如在“铜须门”事件中网民跟帖②:“她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她不是一个好女人”;“兄弟,这样的女人没必要这么注重她,一脚踹开为好”;“这女人不要也好”;“放弃吧,兄弟,这样的贱货,要来何用!”网民用这些语义确定的陈述句来表达对“铜须门”事件中卷入者的判断。
从篇章角度来看,道德话语的文本是封闭的,语义明确的,这一确定语义应该表达某种价值判断,这样才能赋予由道德语言构建的文本语义以某种真理性。“人类历史地赋予它们(道德标准或原则)以既定的事实性意义,仿佛它们确实无疑,因而也就使它们获得了某种表示事实的真理性。”[2]6这种真理性就是福柯所讲的话语/权力,这种权力虽然没有赋予道德以某种法律上的强制效力,但它通过规训和惩罚机制获取了社会的普遍认同,从而成为某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话语,并以此来认同那些符合道德话语约束的行为,谴责那些不符合道德话语的行为。以“铜须门”事件为例,笔者以“锋刃透骨寒”在“魔兽世界”网站发表的题为“2区麦维影歌的丑闻”一文后的64条网民跟帖为样本,对每一条回帖的语义进行分析,力图从整体上把握网民对此事的认知和态度。在此事件中,有近60%的回帖对事件中的人物进行了评价,看来对于此类事件,网民关注的重点并不在于事件本身,而在于卷入其中的人物。具体来看,在38条人物性评价的帖子中,有高达90%的比例是针对女主角“幽月儿”的,并且一致认为她的行为是“淫妇”行为,是违背道德的,对其进行了强烈谴责甚至谩骂;只有2条帖子谴责了男主人公“铜须”乘人之危,做人不厚道等;还有2条帖子对发帖人“锋刃透骨寒”也提出了批评,认为是他对家庭的忽略造成了妻子的出轨。网民回帖的每个文本的语义都是明确的、评价性的,网民不仅将关注点落在人物上,而且在对人物的评价中显然运用了中国传统的道德标准,比如“男尊女卑”的性别观念以及“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不仅将女性的地位降低为从属,也对女性的道德品质提出了特殊的要求,如“三从四德”、“相夫教子”、“从一而终”等。正因为有这样的标准,才激起了更多网民心中道德律的认同,对女主角“幽月儿”进行了“人肉搜索”和谴责。
通过微观的话语分析,我们发现,“铜须门”事件不仅依靠话语来表达,更是被话语所建构,道德话语成为建构这一事件的主要话语类型,它为整个事件定了基调,也为事件中的每一个角色定了性。“人肉搜索”从搜索引擎到被话语建构的话语事件,道德话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成为主要的话语类型,也使“人肉搜索”事件兼具了道德话语的特征:评价性、判断性以及强大的生产性力量,推动着事件的发展。
三、“人肉搜索”中道德话语的生产性力量
“人肉搜索”之所以能够引起人们的关注,不仅因为它是网络媒体中出现的新事物,更是因为这种搜索方式、评价方式、审判方式远远超出了网络空间而作用于人们的现实生活。难怪有人评价“人肉搜索”时说:“如果你爱他,把他放到人肉引擎上去,你很快就会知道他的一切;如果你恨他,把他放到人肉引擎上去,因为那里是地狱……”“人肉搜索”之所以具有如此威力,其能量并非来自于某种至高无上的权力,而是来自于话语及其生产性力量。
“话语”是语言学的重要概念,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推动下,对“话语”的研究从纯粹的语言学范畴扩展到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范畴。巴赫金在更广阔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来理解“话语”,他认为话语作为一种言说或“表述”,是“活”的而不是“死”的,它的范围小到一个符号、一个词或单独一句话,大到一篇文章、一部作品(即文本),甚至无形的舆论等等,而某种话语的真实含义只能通过社会“交往”与“对话”实践才能获得③。法国哲学家福柯认为,“话语”不仅是一种言说的“表述”或对社会事务的“描述”,更是对各种社会事物与社会关系的“建构”(construct)。在这种“建构”的过程中,话语始终与权力保持着互相依赖和互相生产的关系。权力的运作必须进入特定的话语并且受特定的话语控制才能发挥其力量,没有话语,权力就缺少运行的载体。任何话语的形成及其实践都是权力运作的结果,同时也是权力运作的方式,权力能够让一部分话语成为主流话语,拥有更大的权力从而压制和规训其他话语。英国语言学家诺曼·费尔克拉夫将福柯的话语权力观引入到话语分析当中,提出话语建构作用的三个方面:建构“社会身份”、建构“社会关系”以及建构“知识和信仰体系”[3]60。可见,在哲学、社会科学的语言学转向中,人们已达成的共识是话语不仅反映社会现实,更重要的是它具有某种生产性的力量,建构着社会现实,推动着社会事件的发展。
“人肉搜索”中道德话语的生产性力量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对事件的建构作用。在搜索过程中,网民的跟帖建构了一个社会事件,其中包括某种“社会关系”、某些人的“社会身份”以及某种“知识和信仰体系”。比如在“铜须门”事件中,网民把“铜须门”事件建构成为一个已婚无业的家庭主妇背叛自己的丈夫与网友偷情的故事,在这样的故事基调中,女主角“幽月儿”被建构成一个背叛家庭的“贱妇”身份,不值得同情和理解;“铜须”则被建构成一个乘虚而入的“奸夫”身份,应该遭到唾弃;而“锋刃透骨寒”则被建构成一个辛苦工作养家糊口,在得知妻子出轨时不离不弃的丈夫身份。现实生活中复杂的社会关系和事件,被网民简化建构成与人们心目中的道德标准相冲突的故事后,遂再度建构了关于此事件的“信仰体系”,即同情“锋刃透骨寒”,谴责“幽月儿”,惩罚“铜须”。
其次,是对现实世界的影响作用。这种影响作用的发挥主要来自于网民在道德话语力量的激励下,对事件评价形成的所谓道德“舆论”。“人肉搜索”被搜索者奉为执行道义的有力工具,之所以让被搜索者生畏,主要是因为由道德话语建构起来的“舆论”具有某种权力,这种权力压制了其他话语(在“人肉搜索”中,当网民形成近乎一致的意见后,如果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会被认为与被搜索者同盟,也会遭遇斥责或搜索),反过来又强化了道德话语的“真理性”,不仅会让人们自觉检视自己的行为,还会对违背话语要求的行为进行规训和惩罚。比如,“虐猫”事件中当事人不仅向公众道歉,而且还丢掉了工作;“铜须门”事件中“铜须”迫于舆论压力,被迫休学来躲避网友的谩骂和骚扰;“死亡日记”事件中,被搜索者及所谓“第三者”的照片、工作单位、家庭人员状况及其个人电话号码等信息被网友披露在网上,还有网友到被搜索者父母家中进行声讨,在其门前写恐吓标语,所谓的“第三者”也迫于压力辞职;在“Die豹”事件中,重庆某学院大三女生“Die豹”被网民指责“没人性”,当其个人资料被“人肉搜索”后,也被迫选择了休学等等。
四、“人肉搜索”中道德话语力量发挥的条件
道德话语早有存在,并存在于多种文化中,却从未在网络媒体之前、儒家文化之外掀起这样大的波澜。如此看来,道德话语规训力量的发挥要依托于特定的条件,这种条件就是“人肉搜索”存在的技术平台和中国特定的文化环境。
(一)泛道德主义文化:中国式“人肉搜索”力量发挥的文化土壤
网友吉四六说,“人肉搜索”是一种“自然灾害”,一旦卷入其中,谁能真正保持冷静和超然的态度?在越来越强烈的情绪纷争之中,一旦走向极端的谩骂和发泄,“自然灾害”就变为一种无可逃避的结局[4]。这里用“自然灾害”来比喻“人肉搜索”对当事人造成的影响,是指“人肉搜索”的发生和发展往往是无法预料、无可防范、无人负责的。然而“人肉搜索”又并非真正的自然灾害,一方面,它确实是由人为原因造成的,是由许许多多匿名的网友搜索并传播出来的;另外,它并非像“自然灾害”一样作用于任何文化而导致同样的后果,它只有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对生长在其中的文化个体才会产生作用。
首先,“道德、文化与传播交织在文化的拼图中,它们既不可分割,又是每个社会的显著因素”[5]493。因此,道德话语绝不仅仅是一个语言学问题,更是一个关涉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文化习俗的问题。“人肉搜索”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掀起波澜,与中国特有的耻感文化是分不开的。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从根本上说是一种“道德主义”文化,道德的重要性被置于法律之上,不论在公共领域还是在私人领域都强调道德律,从而形成了传统儒家文化中的“泛道德主义”。泛道德主义就是用道德准则处理一切关系,以道德标准衡量一切价值,使之具有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和全面的社会影响。“在中国文化中,有‘一本万殊’的信念,于是坚信一切文化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这基础就是道德。”[6]61泛道德主义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典型特征,是传统儒家文化的内核。韦政通先生评价儒家道德思想的特点是“先验的道德原理”、“道德判断诉诸直觉”、“道德理性与本能相对反”、“道德为一切文化的基础”[6]55-58。
在道德至上的文化大环境中审视“人肉搜索”现象,我们找到了这种现象产生的文化根源。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是弥漫在社会一切领域的,比如,中国的政治理想是“德治”,文学理想是“文以载道”,经济理想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今天,中国文化由“重德”而流于“泛德”的主要原因,一是传统文化使然,二是现代社会普遍出现的道德缺失感。“重德”强调个人修身养性,“泛德”侧重评价他人、他事。因此,我们看到网民的评价语虽然正义凛然,但语言也不免粗俗和暴力。
从以上的话语分析来看,网民对搜索对象及其行为进行评价时,往往从直觉上来判断“好”“坏”,这一直觉判断的标准就是道德,这种判断是先验的、直观的、没有理性的。人们所运用的道德标准,往往依靠内化于其脑中的道德观念,无须证明其是否正确,只运用一种不言自明的“真”来作出判断,常常会造成人们对事物的评价过于绝对和简单化。如在“铜须门”事件中,对男女主角的无情批判,对“锋刃透骨寒”的同情;在“死亡日记”事件中,对自杀者的同情,对死者丈夫及“第三者”的痛斥;在“很黄很暴力”事件中,对尚未成年的小主人公的恶搞;在“Die豹”事件中,对出言不慎的大三女生的口诛笔伐等等。
其次,道德是人们在实际生活中根据需求而逐步形成的一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范,它是一种心灵契约,不具有强制力,只能靠社会舆论和自我约束来实现;道德形成了人们对事物的基本判断,它是一种思想观念、一种内在凝聚力和精神支柱,也是一种文化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社会通过道德将文化共同体中的个体黏合在一起。然而,道德也有其自身的缺陷,它本身是去差异化、求同存异的整体化过程。为了一个文化共同体的团结和凝聚,它往往需要打磨掉每一个个体的个性,赋予其共同的社会认知,将其纳入到一个文化团体之中。“在道德文化中,表达的语言,以‘规约语句(prescriptor)’为主。”所谓规约语句,主要是“教诲人一种固定的行为方式,或促使人去实现一种人格价值。在这里,只讲善恶(或好坏),不讲真假”[2]16。这样的特点必定导致道德话语的价值判断性(比如判断句以及大量价值判断的词汇的使用)、整体性、武断性和一定程度的暴力性。而正是这样诉诸判断性和情感的道德语言产生了“口号”和“大字报”的效果,才引起了人们视觉上的注意力和情感的共鸣,从而激起更多网民加入搜索行列。
儒家文化将道德标准上升为判断任何事情的普遍标准,而道德的约束力在日常生活中表现为舆论的压力,也就是所谓的“人言可畏”。在儒家的文化土壤中,“人言”常常会成为一种社会压力,从而扮演着社会法庭的角色。“人言可畏”的传统在中国则由来已久,从《诗经·郑风·将仲子》中“人之多言,亦可畏也”的记载,到今天被“人肉搜索”出来的当事人因无法承受“人言”的压力而被迫选择隐藏、逃避或保持缄默的困境,从根本上表明,“人肉搜索”带给被搜索者的“惩罚”或伤害仍然是一种话语惩戒,只是这种话语是在道德文化中产生,并在特定的道德文化中发挥作用的。
(二)网络媒体是“人肉搜索”话语力量产生的技术平台
“人肉搜索”不仅是中国“泛德”文化土壤中的特殊现象,更是网络媒体中的特有现象,网络媒体传播的便捷性、广泛性和匿名性的特点,为“人肉搜索”提供了特殊的技术平台,使“人肉搜索”现象能够在网络媒体中兴盛起来。
1.网络环境中言说者“身份”的缺失
网络环境是虚拟的,任何在网络中发言的人最终显示的身份只是一个虚拟的网名和一个网络ID,这些网络中的身份标志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身份相脱离,由此造成了人们在网络中的表达不具有身份特征,从而也就缺乏了身份“约束”。话语责任与言说者真实身份的断裂是导致网络言行失当或畸形发展的主要原因。而身份的缺失,使参与“人肉搜索”网民的目的和表现也有不同。
(1)发泄(压力、私愤)及娱乐。通过对“铜须门”、“死亡日记”、“Die豹”等典型的“人肉搜索”事件的分析发现,大多数网民在发帖时处于一种非理智的状态,言辞过激,并非理智地说话、发表意见,不少人是抱着发泄私愤、搅浑水或娱乐的态度。小K坦言:“在现实里我没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我愤怒但是我得压抑着自己。在这里没人认识我,我完成一次搜索,别人就叫我‘高手’,我不高兴了,还可以发起一次‘道德讨伐’,我觉得挺好。”“‘人肉搜索’里的确存在双重人格,而且是挺分裂的。”曾经参加过搜索的AT说:“搜索者本身就是一种不认真的态度,其实,不管你是文艺青年也好文艺流氓也罢,骂人是大环境,是在随波逐流。如果你搜索,而你又不骂人,那就不好玩儿了,‘不够娱乐’了。”[4]可见,在“人肉搜索”事件中,参与搜索的网民并非都是真的在惩恶扬善,也有不少人是高举道德主义大旗,运用网络媒体进行情感宣泄。
(2)在假想的身份中寻求快感。“人们对不同的身份及其行为有不同的评价……而不同的身份及其行为又是通过言语表现出来的……一个人的言语帮助他建构自己的身份,而其所言又是与其所处的社会位置有关。”[7]13而在网络的虚拟环境里,人们的真实身份被隐去了,他们可以以任何假想的或者幻想的身份进入网络,参与事件的评价。在“人肉搜索”事件中,很多网民扮演的是“审判者”的角色,对别人的行为发表看法,作出评价,甚至是“判决”,从而在网络中体验到了不同身份带来的快感。一位“人肉搜索”的参与者毫不避讳地对记者说:“让不道德的人接受道德的审判,我们何罪之有?”“当看到当事人的生活被打乱时,一种成就感油然而生。”[4]
身份的缺失使人们在网络中的表达更贴近于人的本性(甚至兽性),而非社会身份限制状态下的“社会人”。因此,人心中各种隐藏的欲望和快感会在这样的状态下体现出来,从而也就造成了人们在这种“无身份”状态下言语的非规约性、暴力性和非理性。
2.网络言说中说话“语境”的模糊
话语分析中对某个具体话语的分析不能离开说话者的语境。而网络的特点是扭曲了自然的时间和空间,人们在网络中言谈语境的模糊,也就造成说话人所针对的确切谈话对象的丧失。在“人肉搜索”中,网民所谈论和评价的对象并非直接针对生活中的真人、真事,而常常是基于出现在网络中的某网民的叙述,或者某些网民评价的片断言语,是通过描述、转述等话语方式建构出来的人物或事件。这些人物和事件一开始是以一种虚拟形式出现于网络中的,没有人对其真实性负责,真实说话“语境”缺失。当“人肉搜索”介入时,这些网络中的虚拟故事和人物迅速与现实中的某人某事发生了联系,从而使人们以网络虚拟故事或者人物为依据,开始对现实人物进行话语声讨。由此造成了人们不关心事情真伪,常常不假思索、不作考证地迅速放大、扩散、去差异化地进行“好的”或“坏的”整体评价。这种简单的、整体性的价值评价,又极易唤起人们情感上的认同,类似于“口号”一样具有很强的煽动力,依托于网络这样迅速、快捷的传播媒介,会在短时间内蔓延开去。
3.作为“乌合之众”的交流主体
网络的匿名性会造成匿名群体的产生,而在一个匿名群体中极易造成的是情绪的感染而非理性的传播。这与舆论的产生机制类似。当人们受到一种信息刺激时,人们的反应并非是理性的,大多数情况是情绪性的。“如果在公众聚集的场合或电视屏幕上出现相对强烈的同一方向的刺激性言论、举动、画面,会迅速造成一种耸动心理,从而发生较为广泛的情绪感染。”[8]54而受感染的人们的情绪又会在相互影响中经历多次强化。
法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认为,个人在群体中会丧失理性,没有推理能力,思想情感易受到旁人的暗示和影响,变得容易极端、狂热,也会因为人多势众产生的力量感而失去理性自控,甚至变得肆无忌惮④。艾略特也认为:“一旦人们被聚集在一起,并融为一个群体,他们就失去了各自的鉴别力。”[9]42一个人“当他独处时,他服从对真理的尊重,知道什么是理智和道德,而当他作为群体的一员时,其所作所为就完全背道而驰了”[9]24。网络环境中的交流主体是在对某件事情的关注中自发形成并匿名存在的,这种群体更像是勒庞提出的“乌合之众”或者莫斯科维奇所谓的“群氓”。对于群氓来说,在恐惧和兴奋、“……万岁”与“打倒……”的口号之间没有任何中庸之道。
在“人肉搜索”中,参与搜索的网民就像是一群“乌合之众”或者“群氓”,在一种虚拟的环境中,运用虚拟的身份,参与一种以情绪渲染为支撑的事件。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在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时并非一种自然状态,而常常受到现实各种因素的影响,比如身份的限制、社会利益团体的压力、文化的影响、刻板印象等等。这些外在的因素常常导致人们不敢或者不愿表达自己的意愿。而网络的虚拟性不仅隐去了说话人的各种文化身份,而且隐去了压力团体,尤其在“道德”的掩护下,在用道德语言进行“正义”表达时显得更加义正词严。
五、结语
话语是权力运作的结果,而权力的运作必须通过话语来实现,一旦某种话语得以形成就拥有了一定的权力实施审判和压制。正是由于话语拥有一定的权力,所以才具有生产性的力量。话语不仅反映世界,更可以建构世界。道德话语将“人肉搜索”建构成了一种特殊的话语事件,这类事件的特点是诉诸价值判断和情感宣泄。当某事件被道德话语建构起来并实施“人肉搜索”行动时,道德话语就不再停留在描述、反映事件的层面,而是在生产着事件和社会关系,从而影响人们的行动——新一轮的“人肉搜索”又开始了。
然而,“人肉搜索”中道德话语生产性力量的发挥并非纯粹的、天然的,而是需要其他条件的,中国“泛道德主义”的儒家文化土壤以及网络环境的匿名性提供了生产和传播空间,“人肉搜索”是中国“泛德”文化与网络媒体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中国网民发起的一浪高过一浪的“搜索”运动中,网民所使用的“贱人”、“奸杀”、“拉出去砍了”等等不道德的话语以及对被搜者生活的骚扰,透露出比被搜索者行为更强烈的“反道德”性。在“德治”强于“法治”的社会里,对话语建构起来的不道德行为所运用的惩罚措施,常常源于人们最原初的情感判断和动物性冲动。道德话语就是如此,强大的规约性和去差异性将属于某一文化中的个体黏合在一起,在维护了这一文化共同体的稳定时,也暴露出某种暴力和强权逻辑的“非人性”一面。面对这种现象,我们必须提出如下问题:什么样的行为可以被定义为“不道德”,可以被纳入道德话语的审判当中?而网民所谓的道德行为又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对等的效力来惩戒这些所谓的不道德行为呢?
“人肉搜索”中的不道德行为始终在道德大旗的掩盖下,被大量道德话语的反道德行为所讨伐。“人肉搜索”原本是维护社会道德的行为,但却用了“反道德”的行为加以实施;其目的本来是为了捍卫道德,却给被搜索者造成了最不道德的伤害。网络正义也在盲动和跟风的口水中,在歇斯底里的所谓“追杀”中异化成了一个幌子,借机发泄参与者的阴暗情绪和不良欲望似乎成了这一行为的目的和本质,而这更需要反思。
注释:
①本段引文译自P.Ford,"China's Virtual Vigilantes:Civic Action or Cyber Mobs?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2008-11-28; A.X.Li," Human Flesh Search Engines? Niu!" The Guardian,2008-11-02,并在英文基础上有所修改。
②有关此事件的资料均来自“魔兽世界”网站:http://wow.duowan.com/0711/58964630815.html。
③有关巴赫金的“话语”理论可参见《巴赫金访谈录》,见巴赫金《巴赫金全集》,钱中文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16页。
④转引自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第5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