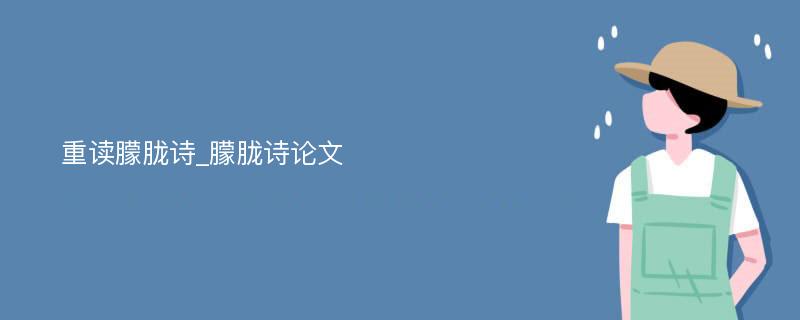
重读“朦胧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朦胧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整个朦胧诗,不仅仅是一种抗衡性的写作,同时兼具美学上的开发。
一、情感的美学力量不可低估
——读食指“北京”
40年前,一场史无前例的“上山下乡”,把几千万中国知青投放到“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多次目睹送行场面,最终也难逃“法网”,所以当我一口气打下这首诗的读后感时,我的眼睛湿润了。
触发这首诗的情感按钮是“离开北京”,离开我亲爱的故乡。离开家乡,意味着吊销户口、改变身份,可能永生永世回不了家。对未来恐惧、前途渺茫的忧虑,失落感与对城市眷恋,尽管有强大信念支撑,有光辉思想指引,然而在人心深处,那些最真实、最本能的柔软部位,在最后时刻,必定要冲破“面具”,撕开假象,回归到人之常情的本然面目上来。
反映这样的心理真实,在当时实在太难了。因为“假大空”风气,覆盖所有的话语空间,革命的宏大叙事,主宰了所有惯性思维。是朦胧诗的先驱者食指,冒着极大风险,对抗威权主义意志,第一个站出来,以个人化身份撩开普遍的人性真相,释放出一代知青心灵的重压。一个特定的出发时刻:凌晨四点零八分;在最牵动人心的地点:火车站——一个隐含着“集体无意识”的生死精神场域,举行悲怆的“告别仪式”。真切的情感仪式,真实的幻觉,伸手可触的细节,一起合成令人唏嘘、震荡久远的心灵图景。如泣如诉的真情,毫发毕现的场面,鲜明的节奏感、音乐性,拨动着普遍人心的和弦。所以直到今天,那些现场感特强的诗句,并不会因时代变迁,而失去打动人心的力量。
有论者把这首诗看作是“年轻一代的觉醒”标记,用哭声与权力者对抗,抵制了“假大空”。从实际文本出发,我是一直把它当作一次离别体验的出色抒发:真切的情感与真实幻觉的有机融汇,抓住典型场景,完成一次优美的悲剧性传达。毫无疑问,情感的美学力量,占据轴心位置,不可低估。
二、强力型主观投射
——读芒克“向日葵”
提到向日葵,立刻想到梵高,想到大英博物馆那幅举世瞩目的油画:15朵火焰,飘扬、燃烧,滋滋作响,简直要灼穿每一双注视它的眼睛。那是激情的喷溅,炽热的生命象征。1973年芒克写作此诗,我不知道他是否受到梵高的影响,如果有,那都是属于强力意志的主观喷射。不同的是,后者带有更多时代的鲜明烙痕。
众所周知,那年头正是“造神”运动的巅峰。太阳就是上帝、神明,稍有亵渎,是要掉脑袋的。偏偏就有一个叫“毛头”的瘦猴,不信邪不拜鬼,以大无畏的精神进行顶撞(要知道,即使这样一首不算是太煽动性的“反”诗,至少也得判刑)。这就是早期朦胧诗的勇气。作者激愤而丰沛的意绪,借助移情物化,将情感投注对象,以此来塑造具有先知先觉的“向日葵”,那种对王者“太阳”——的挣脱、反叛形象,这在当时,是相当超前的了。
向日葵,一向以对阳光的向往、亲和的自然属性而获得“忠诚”定型。芒克反其道而行之,大胆瓦解这一典型,不但锐气可嘉,具有深刻的思想启蒙意义,艺术上也体现了娴熟的投射型构。
芒克的投射是基于奥尔逊有关诗人主体性是一种“高能放射器”的说法,但又与其有所不同。奥尔逊的投射侧重“通过呼吸,到达诗行”,那是放松的、流动的、轻浅的。而芒克的投射则是强烈情感的外化“移情”,人为的暴力往往使对象变形。
整首诗在相对齐整的咏叹中,用强力型的主观投射方式,(或曰“以我观物”的方式),打造出抗争专制王国的斗士品格与形象。
三、言志载道,并非过时皇历
——读严力“还给我”
写于1985年的《还给我》,是严力早期代表作。近年影响不小的《齐人物语》,对该诗这样评价道:“我还没有见过一首呼吁回归自然的诗,如此简洁而诙谐,有力而优美。”我觉得这段评语,只说对了一半。我的意思是,这首诗的重心,是在对“异己”力量抗争的基础上,包含了更多对人性复归、人文复归、真善美复归的吁请、呼告。其社会性干预远远大于对“自然生态性”的表达。在那黑白交接、百废待兴的特殊历史时期,诗人以充沛的激情,喊出了时代强音。
这首诗的最大艺术特色,是一方面采用“请还给我……还给我”12个排比句,将强烈的思想情感做排山倒海的并列推进。分别指涉了被封闭的居所、被管制的时间、被束缚的歌声、被扭曲的人际、被污染的爱情、被毁坏的环境、被分裂的和平。针对当代各种领域的缺失,从个人到群类,从国家到种族,从本土到全球,它几乎无所不包,大气磅礴,高屋建瓴,咄咄逼人,给人喘不过气来的压迫感、危机感。另一方面,它又机智采用“连锁”方式,以“哪怕……”这样不断减低要求的“请求”,使其“言志”的抱负,达到最大化:没有房间的门已然没有意义,被吃剩的雄鸡已然成为空架子,录上磁带的牧歌不再稀有,亲情关系只留一丝半缕,爱的空间已被污染,地球百孔千疮……这一切早失去原本的美好和谐,即使这样,“我”也要求在最低限度中一一“返还”。最高期盼与最低限度“返还”,这二者本身的落差,就构成反讽。在愤忿与反讽中,诗歌具有了某种笃定的诙谐感。这也就使得“返还”的吁请,在连续的排比中,不至于那么呆板,一览无余。
这是一首写于20多年前的政治抒情诗,本来事过境迁,生命力有限。但因作者站在时代思想的制高点,充满对社会、人类、生命的忧患关切,由此能对时代做出巨大概括,即使多年过去了,时代语境发生很大变化,它还具有旗帜与炸弹的威力。
四、回旋曲:单纯的丰蕴深入的透明
——读梁小斌“墙”
经历“文革”的人,一定深有体会墙的分量。墙作为一种典型符码,如同“麦地”,承载着许多值得深究的信息。诗中反复出现墙——“雪白的”和“肮脏的”的衬托,毫不费力地指向文明与野蛮,理智与蒙昧的意蕴。儿童的视角、由视角派生的天真语言,经由对墙的叙述、倾吐(或借墙的载体)传达出典型的“伤痕”意识,及“伤痕”下的美好意愿。“伤痕”,可以说是“文革”最重要的心理症候,时时引起社会强烈共鸣,墙出示和回应了这一普遍情感,写得平易自然,亲切动人。
本诗形式上有一突出特点,就是运用钢琴曲式结构(呈示部、展开部、对比部、再现部)来传达诗人情思,具体体现为回旋曲式,即A-B-A-C-A式。第一节可视为A,作为呈示部:妈妈,我看见了雪白的墙,是诗歌的第一句,也是全诗核心句,全诗所有情感的生发、变奏、高潮,皆由它“掌控”,堪称该诗“主旋律”。这一“主旋律”又在第四节、第八节出现两次,使这一呈示部成为全诗轴心,经此反复吟述,不断强化,起到一咏三叹的效果。
可是,2008年我在网上读到梁小斌悔其少作,对同是自己的代表作《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进行忏悔,理由是:它的基本模式是控诉,只是控诉主义骗局的变种;虚伪地毒化后人,违背说真话原则,所以建议将这首诗从所谓的经典系列中永远抹去。
我认为梁小斌犯糊涂了。我们知道任何一件艺术作品,它一旦产生,就已经跟艺术家本身没有多大关系。“钥匙”所代表的特定历史时期,民意对“失落”(时间、青春、理想、财富失落)的寻找,完全是真实反映时代多数人的心声,何谓虚假?用历史主义眼光看,诗歌的意识形态化是不可逃避的职责,无需自戕。
五、光的静心
——读王小妮的“月光”
古今中外写月光的诗如恒河沙数。看看我们女诗人写出什么特别来:“月亮在深夜照出了一切的骨头。”单挑一行,放在最前面,成为金鸡独立的首句,是对夜光做出总体抽象裁决:在深夜,月光使“一切的骨头”现身、显影,无从遮匿。“骨头”作为皮肉的内里,可视为坚硬的事物、或事物的本相,在此,骨头直接“转喻”为城市物象。对于这样反自然的坚硬的城市物象,赋予月色以“火眼金睛”——“照出”,即看穿看透城市(亦可引申为存在的虚象、表象、假象。有如X光式的穿透力——穿透一切,简直就是神迹哪。
神迹的辉光弥漫在四周,仿佛空气一样的气息,一旦吸入这样的“青白”,那么人世间的许多“琐碎”——烦恼、杂念、喧嚣,便会化作“下坠的萤火虫”。在这里,我,可以与自然、与宇宙自由进出,互相交通,形成精神上的一场涤荡、净化的“洗礼”。而号称现代文明进程中结下的最大硕果——城市,此时该已露出原形,在神迹的照耀下,变成了一具没有血色温度的“木乃伊”:那些钢筋混凝土、水泥汀、玻璃幕墙,在如此感性和绝美氛围笼罩下,难道不是成了一堆“死骨架”?……
王小妮的表现增强了我的基本判断:整个朦胧诗,不仅仅是一种抗衡性的写作,同时兼具美学上的开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