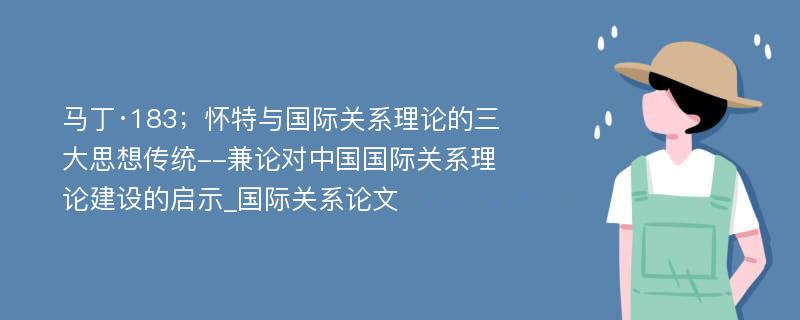
马丁#183;怀特与国际关系理论三大思想传统——兼论对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怀特论文,马丁论文,理论论文,三大论文,国际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1)05-0004-14
一 引言
将国际关系思想划分为彼此间既有联系但又时常冲突的传统,是采用经典方法从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学者的显著标志之一。尽管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史上出现过许多不同的分类方式,但英国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马丁·怀特(Martin Wight)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现实主义”、“理性主义”和“革命主义”三大传统却以独到的见解和深邃的思考为此后历代国际关系研究者(尤其是英国学派的学者)所重视。作为国际关系学科中著名的英国学派主要的创始人和组织者之一,怀特构建的三大思想传统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史上的重要性概括地说主要有三方面:首先,怀特提出的三大传统是迄今为止国际关系研究者对历史上的经典国际关系思想进行的最杰出、最重要的原创性研究之一,其学术成就几乎无人望其项背。其次,怀特提出的三分法非常明显地贯穿于英国学派代表性人物的几乎所有主要著作,因此对三大传统的系统研究很大程度上也是研究英国学派特有的国际社会理论的逻辑起点。最后,怀特提出的三大传统非常典型地体现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之“经典方法”的若干基本特征,这种方法对构建当代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同样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① 尽管怀特构建的三大传统在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迄今为止,有关怀特三大传统分析模式的本体研究却较罕见,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怀特构建的三大思想传统是他于20世纪50年代在伦敦经济学院的讲座中提出的,但他的讲稿却一直到1991年才得以出版。在他生前和去世后的相当长时间内,人们只有通过他人介绍才能够领略其概貌,而这点无疑是限制了怀特思想的影响。其二,怀特是二战后历史上少数几位始终坚持以经典方法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之一,他的思想与现代国际关系学科中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美国学派格格不入,因此现代国际关系学科特有的美国属性很大程度上也限制了人们对怀特思想的认识和把握。② 鉴于怀特所构建的三大传统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史上的重要性,本文将着重从四个方面(即怀特构建的思想传统的内涵与本质、三大传统的主要分野、思想传统与经典方法、三大思想传统对中国研究者的启示)来分析和阐述三大传统的思想风貌及其蕴藏的哲理内涵,而这点不仅对理解英国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及国际关系研究的“经典方法”有重要价值,而且对构建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 “历史传统”与“分析传统”
通过对经典国际关系思想的系统研究从而发现或构建不同类型的思想传统,是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经常采用的研究方式之一,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乃是英国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爱德华·卡尔(Edward H.Carr)首先提出,并且由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和约翰·赫兹(John Herz)随后又加以明确界定的“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两大思想传统。③ 从严格意义上讲,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发现或构建的思想传统大致可服务于两类不同性质的目的,即学术史研究和理论的构建:前者是指通过对经典国际关系思想进行系统梳理,从而勾勒出国际关系思想的发展轨迹和智识渊源;后者则指研究者基于特定视角对经典国际关系思想进行系统梳理,以此来阐述自己对国际关系的某种特定认识。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研究目的所导致的主要后果就是使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实际上存在有两类不同性质的“传统”,即历史传统(historical tradition)和分析传统(analytical tradition),而混淆两类不同性质传统间的界限和分歧,不仅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面临的重大障碍,且很大程度上是导致人们对各类思想传统进行诟病的主要诱因之一。④ 在理论上,历史传统就是指一种由“前人构建或自我构建的、各种观念能够通过它在一种可以辨识的确定且具体的话语性框架中得以传播的常规性实践模式”,无论是何人或何时构建的历史传统,其目的都是为了要还原和追溯特定的观念或思想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本来面目,即是为还原历史而研究历史,而不是为任何其他目的而研究历史。与此相反,分析传统则是指一种由研究者根据“当下的标准和关切以追溯性方式构建起来的思想产物”,即分析传统是研究者根据其特定的标准和关切从而认定某些观念、主题或文本存在有本质上的相似性而得以形成的,分析传统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还原思想发展的实际历史,而是为研究者特定的学术目标(即立论或反驳)服务的。⑤ 怀特构建的三大思想传统本质上是一种分析传统而不是历史传统,即现实主义、理性主义和革命主义并不是代表历史上经典国际关系思想发展的真实轨迹,而是怀特根据自己的标准和关切构建起来的产物,怀特三大传统的“分析”特征主要是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怀特构建其三大传统的根本目的,二是怀特本人对传统的特定理解。
怀特构建三大传统的首要目的是反对卡尔在20世纪30年代对国际关系思想所做的“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这种简单划分。怀特认为,卡尔对国际关系思想传统的这种划分乃是一种“病态局势”的反映,这种局势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英国绥靖政策鼎盛时期及20世纪50年代美国冷战政策初始阶段,虽然这种简单划分不失为一种对“病态局势”的有效诊断,但如果真正以此作为我们理解国际关系思想的理论基础则显得过于狭隘,因为这种简单划分根本无助于正确地把握国际关系思想的丰富内涵和结构特征。⑥ 与卡尔的看法相反,怀特认为“纵观马基雅维利以来曾经探讨过国际关系理论的最卓越学者以及在这个领域中曾经广为流传的主要思想,我们显然可以将这些学者划分为三大派别并且将这些思想划分为三大传统”。⑦ 怀特对卡尔思想的最大修正是他在现实主义和革命主义两种极端间提出了一个中间派别,即理性主义,怀特界定的“理性主义”思想传统的核心是所谓“国际社会”的理念,这也是怀特对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首要贡献。⑧ 怀特构建三大传统的另一目的是展示国际关系思想的内在延续性,即每个时代的问题不过是某些同样核心议题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怀特在讲座的导论中曾经引用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的话来阐述他对国际关系思想本质的认识:“很难相信,有多少道德和政治的思想体系一直在不断地经历被发现、被忘却、被重新发现、再次被忘却、过了不久后又重新出现的过程,它们每次出现总会带给世界以魅力和惊奇,仿佛它们是全新的,这种情况真正见证的并不是人类精神的多产而恰是人类自身的无知。”⑨ 正是秉承与托克维尔相同的理念,怀特认为,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最佳方式是研究历史上那些从事过类似研究的最杰出学者,“以重新发现一直在人类中广为流传的这些领域中的主要思想——并且将它们简化为少数几种思想体系——以便对它们进行比较和做出判断”。⑩ 怀特对国际关系思想内在延续性的认识意味着他构建传统的根本动机之一,是以此来反对那种将当今世界的问题看作是独一无二的企图以及那种将无穷的选择当作是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的倾向,即思想传统在怀特的眼中也是他用来克服生活在当今的人们固有的那种傲慢自大的有效工具。(11)
怀特构建的三大传统的“分析”特征,既体现在他构建传统的目的上,同时也体现在他对“传统”本身的理解上。自20世纪50年代在伦敦经济学院开设讲座以来,怀特构建的三大传统在产生广泛影响的同时,一直都不断地遭受到各种质疑,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批评是认为怀特构建的三大传统过于僵硬,这种划分掩盖了经典国际关系思想家内在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但这种意见很大程度上乃是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传统间的界限。(12) 怀特构建三大传统的根本目的并不是还原历史上经典国际关系思想发展的实际历史,而是服务于他本人特定的学术目标,而这点也就意味着,怀特提出的三大思想传统并不是实际存在的,而是他从自己特定的标准和关切出发,通过对经典国际关系思想的系统梳理,以追溯性的方式构建起来的思想产物。(13) 也正是因为如此,怀特在他的讲座中从来也没有将任何单个的思想家固定在某个传统中,他明确强调,“在人文研究中,只有在进行区分的那些点上,分类才是有价值的。国际关系理论中最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几乎都跨越了那些将两类不同传统区分开的界限,而且其中绝大多数思想家也超越了他们自己创立的思想体系”。(14) 从严格意义上说,怀特构建的三大传统并不是人们可以用以来辨识某位经典思想家之理论属性的标签,而只是用以来展示历史上各类不同国际关系思想彼此间存在的同质性或一致性的分析框架,而这点同样意味着,怀特构建的三大传统只能够用来辨识某种类型的思想而无法用来辨识某位特定的思想家。怀特指出,三大传统并非是三条完全平行并且通往无限尽头的永不交汇的铁轨,“它们是三条不断有漩涡和逆流的小河,时而交汇在一起,但从来不会长时间拘泥于自己的河床”;三大传统彼此间“既相互影响又相互滋润,我认为,虽然它们从没有丧失过自己内在的一致性,但它们却是在不断发生变化”。(15)
三 三大传统间的主要分野
在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史上,怀特构建的三大思想传统做出的首要理论贡献,就是在现实主义和革命主义两种极端间提出了理性主义这一中间性派别,而正是这点使怀特成为英国学派国际社会理论的首要奠基者。怀特界定的理性主义思想传统的最重要特征就是摆脱了现实主义和革命主义两大传统赖以立论的根本前提,即国际政治的“国内类比(the domestic analogy)”,而后者也正是区分现实主义、理性主义和革命主义三种不同思想传统的首要标准。
按照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的界定,“国内类比”是一种将个人在国内无政府状态中的经验应用到国家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中的经验得出的类比性论断。(16) 这种论断的核心是,由于在无政府状态下的个人间需要有某种公共权威才能够实现秩序,因而在无政府状态的国家间也需要建立某种公共权威才能够实现和平与稳定;而这点也就意味着,国家间有序社会与国内有序社会的条件是相同的,而消除国际无政府状态之效应的根本途径就在于建立一个世界政府或是将国内社会中的制度和原则应用来处理国家间关系。(17) 布尔界定的国际政治之“国内类比”的理论基础是17世纪英国政治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提出的“自然状态论”。霍布斯“自然状态论”的根本目的乃是强调建立一个拥有绝对主权的君主专制政体的必要性,即生活在自然状态中的人为寻求自我保护而创造和服从了“利维坦”,从而结束人与人之间险恶无比的战争状态;但个人间战争状态的结束造成的一大后果就是使主权国家成为国际层次上的个人,而这点势必将导致个人间的自然状态在主权国家间的重现,由此得出的逻辑结论是,消除国家间自然状态的根本路径同样有赖于创造某种国际层次上的“利维坦”。(18) 布尔界定的“国内类比”理论包含了两个核心要素:一是有关国际政治本质的描述性论断,即国家间的无政府状态必然是一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二是有关如何消除这种状态的规范性论断,即消除国家间战争状态的根本途径,要么是在国家间建立起类似个人间的公共权威,要么就是将国内社会的制度和原则应用来处理国家间的关系。(19) “国内类比”虽然是由布尔首先提出并加以界定的概念,但这个概念本身却贯穿于怀特有关三大思想传统的论述,尽管怀特界定的三大传统的思想内容各不相同,但它们在形式上却有着一个共同特征,即每个传统不仅描述了国际政治的本质,且同时也规定了人们在其中应当如何行事的一整套原则,而怀特用以界定其三大思想传统的首要标准也正是“国内类比”的两个核心要素。(20)
在怀特的思想分类中,现实主义和革命主义虽是两类不同性质的极端,但它们赖以立论的根本前提却都是国际政治的“国内类比”。(21) 这两大传统的主要不同点就在于:现实主义传统只接受“国内类比”包含的第一要素,即主权国家间无政府状态必然将是一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但同时却排斥了第二要素,即现实主义者从来没有认为消除国家间战争状态的根本路径在于创造某种国际层次上的“利维坦”或是用某种以个人为基础的普世性社会秩序取而代之,现实主义者渴望建立的国际秩序主要依赖两种机制:一是均势,二是大国协调;(22) 革命主义传统一般只认同“国内类比”包含的第二要素,即消除国家间战争状态的根本途径是国家间建立某种公共权威或是将国内社会中的某些根本的制度和原则应用来处理国家间关系,但却间接排斥了第一要素,即革命主义者虽然也认为国家间的无政府状态是一种战争状态,但他们的重点却是在否认主权国家存在的合理性,革命主义者设想的世界秩序乃是以个人而不是国家为核心的。(23) 革命主义者虽然认同现实主义者对国际关系本质的判断,但革命主义者却要比现实主义者更激进,即他们根本否认国家存在的合理性,革命主义者的根本目标是要将国际社会转变为国内社会,即他们本质上是“世界主义者”而不是“国际主义者”,革命主义者的国际理论与国际政策都具有明显的“救世性质”。(24)
正因为现实主义和革命主义都依赖“国内类比”,因此两者都否认了国际社会的存在:现实主义者的眼中只有国内社会而没有国际社会,革命主义者的眼中只有世界社会也没有国际社会。与现实主义和革命主义形成对比的是,怀特界定的理性主义传统的核心特征则是摆脱了两者赖以立论的前提,即理性主义传统根本否认“国内类比”的适用性。(25) 与现实主义相比,理性主义承认主权国家的合理性,但同时承认国际社会的存在。理性主义者认为,由国家构成的国际社会本质上是一个不同于国内社会的特殊社会,国家间的无政府状态并非一种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或“战争状态”;理性主义承认个人的权利,但同时认为国家是实现个人权利的主要载体;实现国家间和平与秩序的根本途径并不是建立一个世界政府或是用普世秩序取而代之,而是应当改进国际社会的各项制度。(26) 按照怀特的看法,理性主义思想传统与17世纪荷兰法学家格劳秀斯的思想是联系在一起的,而他正是以这个传统来说明国家间关系的社会基础和制度基础,从而使国际社会具有了实质性的含义。怀特界定的理性主义思想传统的核心是强调国家间有共同利益,且认为国家间为共同利益能够进行合作,即国际社会虽不够完善,但却真实存在;国际关系是一种自然状态,但绝非一种赤裸裸的战争状态,理性主义者正是基于这点才完全排斥了“国内类比”的适用性。(27) 理性主义者认为,由国家构成的国际社会是一种“真正的社会,尽管制度上不够完善,且缺乏一个共同的最高领导者或最高仲裁者”,但国家间合作仍然存在,并具体表现为如外交、均势和国际法之类的国际社会机制,甚至战争也是国际社会的一种机制,因为国际法的首要功能是规范而不是取消国家间的战争。与现实主义者不同,理性主义者认定的实现国际秩序的根本路径乃是尊重国际社会赖以运行的法理准则和社会准则,与革命主义者相反,理性主义者不认为推翻现有的国际秩序是可行或可取的,因为实现国家间及个人间之秩序和正义的最佳路径是完善现有的国际社会。(28)
四 思想传统与经典方法
怀特构建的三大传统对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贡献是双重的:一是他在现实主义和革命主义两种极端间提出了理性主义这一中间派别,从而为英国学派独具特色的国际社会理论的创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二是他构建的三大传统集中体现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之“经典方法”的若干基本特征,而这点对理解英国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同样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经典方法(classical approach)”与“科学方法(scientific approach)”确切地说是现代国际关系学科中两种不同的构建理论的路径,这两种路径间的分歧也正是构成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史上“第二次大论战”的核心内容。(29) 经典方法乃是一种“源自历史学、哲学和法学的构筑理论的方法,这种方法的核心特征是明确依赖判断力的实施并且假定:如果我们拘泥于严格的验证或检验的标准,那么对国际关系便很难能够提出多少有意义的见解;有关国际关系的一般命题因此也必定来自一种在科学上并不完善的感知或直觉的过程;与其来源上的不确定性相对应,这些命题充其量只能是尝试性和非结论性的”。与经典方法相比,那些采用科学方法构建的理论,“其命题要么基于逻辑或数学上的证据,要么基于严格的经验性检验程序”,而采用科学方法的研究者,要么认为“国际关系经典理论毫无价值,且明确认为自己是一门全新科学的创立者”,要么是勉强承认“采用经典方法构建的产品聊胜于无,甚至可能怀着某种感情来对待它们”,但这两种人都相信自己的理论将取代过去的理论。(30) “经典方法”与“科学方法”间的分歧根本上涉及的乃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性质,即我们究竟应该构建什么样的国际关系理论或国际关系理论究竟应该向我们提供什么样的知识?“科学方法”构建的是由一系列有内在联系且旨在解释变量间关系的命题或假设构成的理论,“经典方法”构建的则是一种有思辨性质的旨在对现象的意义进行诠释或理解的理论。(31) 这两种理论构建路径间的核心分歧主要源于两者对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之本质有不同的看法:由于科学方法的实践者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本质相同且可以用同样方法进行研究,因此科学方法的实践者衡量理论品质的终极标准是理论的解释力,这点实际上也正是科学方法最杰出的实践者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强调的重点;(32) 但正如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所言,华尔兹最大的错误之处在于他将理论的解释力缺少进步的根源主要“归咎于理论家自身,而不是问一问这种失败是否源自于这个领域(国际关系)的本质。即我们是否可能构建一种有关不确定行为的理论”。(33)
与科学方法实践者的认识正相反,经典方法实践者一般都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因而两者需要以不同方法进行研究,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布尔才认为,“科学理论遇到的困难似乎并非源自国际关系研究被普遍假定具有的性质,即国际关系研究是一门‘落后’或是被忽视的科学,而是源自人们已予以足够经常之界定的研究对象(国际关系)本身固有的特性:对国家行为进行的任何一种概括都必须考虑的变量数目不胜枚举;素材与可控性试验相抵触;甚至在我们要进行把握时,其性质也会在我们眼前发生变化并且从我们指缝中悄然流逝;我们提出的理论与那些需要被理论化的事务间不仅是因果关系而且是主客体关系,这个事实必然使我们的那些即便是最无害的想法也会影响到它们自身的证实或证伪”。(34) 布尔的立场实际上也代表了怀特对国际关系理论本质的看法:对怀特而言,由于对国际关系的理论探究必定是有关道德性或规范性问题的探究,因此有关国际关系的理论性著作只能是哲学性的,它无法按照自然科学的方式导致知识的累积增长;判断国务家遵循的道义原则的有效性,“绝对不是一种科学分析的过程;它更类似于文学批评。它要求我们必须发展出一种对所有政治局势的不可驾驭性及所有国务活动在其中运行的道德困境的敏感意识”。(35) 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怀特指出:“国际关系史著作,无论宽广的编年史,还是资料详尽的研究,都要比新近的那些以新方法为基础的理论著作更好地揭示了外交政策的本质和国际体系的运行。这不仅是因为历史著作在做着不同于系统分析的事,历史著作也做了许多同样的工作:即不仅提出了对现象做出解释的前后一致的一整套命题,而且解释得更深刻、更中肯,更加密切地关注于国际实践的历史。”(36) 怀特对国际关系理论本质的认识同样体现在他构建的理论中,而这点也使他构建的三大思想传统集中体现了经典方法的若干基本特征,这些特征大致有三方面具体内涵:一是强调对规范性问题的研究,二是对思想传统的重视,三是有关理论发展模式的认定。
科学方法的本质是排除人的判断力的作用,因而以此构建的理论总是会突出理论的经验性而排斥规范性的内涵;经典方法则强调国际关系理论应当包括经验性和规范性两方面内涵,即在对“政治问题的学术探究中,重要的不是排斥充斥着价值观的前提,而是对这些前提进行的研究和批判,并且将政治问题和道德问题的提出看作学术探究的一部分”,而这也是怀特理论最根本的特征。(37) 怀特眼中的国际政治理论本质上乃是一种与国内政治理论相对应的理论,即有关“国际关系的政治哲学探究”,而这点也就意味着“对国际关系的任何理论探究也必定是有关道德性或规范性问题的探究”,与这种认识相对应,怀特构建的三大思想传统虽然内容上各不相同,但形式上却有着一个共同特征,即它们不仅描述了国际政治的本质,且规定了人们在其中如何行事的一整套原则。(38) 科学方法与经典方法的另一个重要区别在于,科学方法实践者力图构建的是具有终极解释力的理论,但经典方法实践者认为,由于国际政治理论根本无法以自然科学的方式实现累积性增长,因此国际政治理论始终将停留在一种就某些根本问题不断进行争论的哲学阶段,即国际关系领域的性质决定了我们无法创造出终极理论,而我们对国际政治的理论探究也必须依赖不同思想传统间的争论。(39) 与这种认识相对应,怀特界定的国际关系理论也正是建立在三种不同思想传统间竞争与对话的基础上,这其中没有任何一种思想传统能够涵盖国际关系的全貌,尽管怀特相信可以将这些探究分为有共同特征的类别,但分类的前提是,“国际政治真相的探求,并非只在于其中的任何一种思想模式,而是在于各种思想模式间的争论”,而这点也正是怀特在他的讲座中力图传达出来的基本看法。(40) 与两者对思想传统作用的认识相对应,经典方法与科学方法的另一个核心分歧在于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模式有截然不同的认定,科学方法认定的发展模式是替代性而不是累积性的,即新理论必定能够在解释力上取代旧理论,但怀特认为,对国际关系的理论性探究乃是一种持续不断的传统,因而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模式也是累积性而不是替代性的,这点也是经典方法有别于科学方法的一个重要特征。(41) 在怀特看来,自马基雅维利以来,有关对国际关系的理论性探讨主要是围绕着为数不多的几个规范性问题展开的,这些问题是借助不断发展的思想传统而得到说明的,尽管这些传统的思想内容上各不相同,但却都是在分析和探讨同一类相互联系问题的方方面面,研究思想传统不仅是可以帮助我们辨别经久存在的规范取向,而且还是一种运用各时代的集体智慧来探讨某些根本性问题的工具。(42)
五 思想史视野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
怀特构建的三大思想传统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为英国学派国际社会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并在此过程中详尽展示了经典方法特有的价值和魅力,而且在于怀特的理论及方法论取向对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具有很大的启发性,这点也正是我们研究怀特思想的现实意义。
要理解怀特提出的三大传统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价值,首先必须明确的就是“反向格义”在现代中国学术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格义(analogical interpretation)”是指以本土经典中的术语或概念(它们一般都广为人知)来解释那些尚没有得到普及的外来文化中的思想或理论。“格义”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并不重要,这不仅由于西方文化中许多内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本找不到对应成分,因此国人只能另造新词来翻译新说,更是由于近代西方的许多思想往往由日本学者首先用汉字翻译出来再传到中国。“反向格义(reverse analogical interpretation)”则指以西方文化的概念体系或理论框架来研究和分析中国传统的经典或思想,这是近代中国学术传统的主流。“反向格义”对近代中国学术研究的作用不仅在于有利于中西方文化间的对话和交流,且更是许多中国学者用来发掘和改造传统的文化资源以使之走向现代化和国际化的重要渠道之一。“反向格义”虽然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造就过大批杰出的学者和著作,但若就国际关系研究而言,迄今为止这种方法起到的作用似乎并不明显,其中的主要原因,既是因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时间相对而言非常短暂,因此还来不及拥有较为深厚的学术积淀,但同时也是因为当代中国学者用以来“整理国故”的参照系主要是二战后出现的经过科学化改造的美国国际关系理论,这种理论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是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相去甚远,因而单纯以此来观照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似乎有缘木求鱼之嫌。
与现代国际关系学科中占统治地位的美国学派相比,怀特构建的三大思想传统是基于对经典国际关系思想的梳理和发掘而形成的理论,这种理论对中国研究者至少提供了两方面启发性:一是思想史研究的意义,二是经典方法的价值与作用。这里的思想史主要指“国际关系思想史”,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性在于,思想本身与广义上的理论是相通的,思想史研究虽不一定能取代严格意义上的理论研究,但却能够提供后者所必需的思想资源和价值基础。理论与知识的关系(即知识必须先于理论,但知识只能从理论出发)意味着,任何理论构建都须具备某种“创造性想法”,这点也决定了思想史研究对国际关系理论构建的意义,由于当代许多重大问题同样是经典思想家们关注的主题,因此人们从考察他们的思想中将获益匪浅。(43) 怀特理论对中国研究者的启发性同时也体现在具体研究路径上。怀特展示的经典方法的最根本特征,是强调理论应具有经验性和规范性两方面内涵,而这点特别适用于我们对传统政治思想的发掘,因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显著特征之一是经验性与规范性的内涵同时并存且彼此密不可分,因此如果单纯以“科学理论”作为整理国故的参照,则不仅将导致对经典政治思想的歪曲,而且将会人为构建出某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怀特展示的经典方法的第二个特征就是对思想传统的重视,而这点同样为构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指出了一条较切实可行的道路,由于自春秋战国以来的中国经典政治思想源远流长,且在此期间除去那些对传统思想的诠释外还不断有新思想和新学说的诞生,因此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必经之路,就是对中国经典政治思想进行合乎现代标准的发掘和诠释。怀特展示的经典方法的另一特征是强调理论发展的累积性而不是替代性,这点也特别值得中国研究者的重视,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国,任何形式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都离不开对传统与现代的政治思想及政治实践的诠释和发掘,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也必然将会是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即我们只能够追求缓慢的进步而不要奢望任何一蹴而就的突破。
怀特构建的三大传统对中国研究者的启发性不仅是在于思想内容和研究路径上,同时也在于某些具体的问题领域。英国学派国际社会理论的重要议程之一是有关历史上西方民族与非西方民族的交往与互动,与英国学派这一特有的研究议程相对应,怀特构建的三大传统虽然主要是源于对西方经典国际关系思想的梳理和发掘,但怀特讲座中包含的篇幅最长且内容最丰富的一章(第四章)却是有关历史上西方民族如何看待自己与非西方民族间关系的详细探讨,而这点对我们构建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启发性。(44) 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以汉民族为主体且包括众多其他民族在内的政治实体,而这点很大程度上也就意味着中华文明的历史发展应该是包含了两个彼此间密切联系的进程:一是历史上汉民族与汉文化的生成、巩固与发展,二是历史上的汉民族和汉文化与众多的其他民族和其他文化的交往与融合。中华文明史从根本上说正是这两种进程共同缔造的,即中华文明就具体历史形态而言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进程,与这种进程相对应,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也不是只包含汉民族及汉文化自身的生成与扩散,而是包含了汉民族及汉文化与其他的民族及文化间的碰撞与融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怀特在有关历史上的西方民族如何看待自己与非西方民族间关系的探讨中,专门辟出一小节探讨了历史上以汉民族和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华帝国是如何看待自己与其他民族关系的。他认为,历史上中华帝国对自己与其他民族的看法也可以分为三大派别,即现实主义(法家)、理性主义(儒家)和革命主义(道家),他根据自己对中华帝国历史的理解与认识得出的最终结论是,中华帝国处理与其他民族关系时主要以法家思想为主,而儒家思想不过是一种总的姿态,怀特得出的这一结论简单地说也就是中国学者常常提到的所谓“外儒内法”。(45) 作为一个精通西方经典思想且持有西方中心观的学者,怀特的知识结构当然不足以使得他对汉民族及汉文化与其他民族及其他文化的交往进程得出正确的判断,但他在讲座中提示并进行了初步研究的这一领域(即历史上以汉民族和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华帝国如何看待自己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却正是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者在整理和发掘中国经典政治思想时应当要予以特别重视的领域之一,即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应当特别重视中国政治历史发展的特有形态,并且据此找到对中国经典政治思想进行符合现代标准的富有成效的整理和发掘的突破点。
[收稿日期:2010-12-18]
[修回日期:2011-02-13]
注释:
① 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对经典国际关系思想的研究大多是“编年式的”,很少有怀特这种几乎纯粹是“分析式的”研究路径,只要将怀特的研究与其他几种研究进行对比即可看出前者的哲学深度和逻辑力量。参见David Yost,“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the Theory of IR,”International Affairs,Vol.70,No.2,1994,p.277。怀特的著作对“英国学派”主要代表人物赫德利·布尔、约翰·文森特的思想和著作都有很大影响,从这点即可以明显看出怀特构建的三大传统对“英国学派”独具特色的国际社会理论的影响力。参见Hedley Bull,The Anarchical Society: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5。目前对怀特的三大传统分析模式的本体研究都是集中在怀特构建的三大传统的描述性及规范性的特征上,几乎无人注意到怀特采用的分析模式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方法论价值,本文将会在最后部分对此予以详细阐述。
② 目前唯一一本有关怀特国际关系思想的专著对他的三大传统仅做了“描述性”而不是“分析性”的评判,参见Ian Hall,The International Thought of Martin Wight,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06。现有有关怀特三大传统分析模式的本体研究主要体现在相关学者(尤其是赫德利·布尔)撰写的论文中,参见Hedley Bull,“Martin Wight and the Theory of IR,”Britis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2,No.2,1976,pp.101-116; David Yost,“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the Theory of IR,”pp.263-290; Jens Bartelson,“Short Circuits:Society and Tradition in IR,”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22,No.4,1996,pp.339-360。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时殷弘教授是中国最早对怀特构建的国际关系三大思想传统进行评述的学者,参见时殷弘、叶凤丽:《现实主义·理性主义·革命主义》,载《欧洲》,1995年第3期,第1-6页。
③ 有关“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两大思想传统的划分及其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要意义,参见Edward H.Carr,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New York:Palgrave,2001; Hans J.Morgenthau,Scientific Manvs.Power Politics,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2; John Herz,Political Realism and Political Idealis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6。
④ 有关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思想传统的作用及历史传统与分析传统两者间的分歧,参见Renee Jeffery,“Tradition as Invention,” Millennium,Vol.34,No.1,2005,pp.57-84; Gerard Holden,“Who Contextualizes the Contextualizer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28,No.2,2002,pp.253-270 ; Brian C.Schmidt,“The Historiography of Academic IR,” Review of lnternational Studies,Vol.20,No.4,1994,pp.349-367。
⑤ Brian C.Schmidt,The Political Discourse of Anarchy,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8,p.25.
⑥ Martin Wight,International Theory:The Three Traditions,Leicester: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1,p.267.
⑦ Martin Wight,International Theory:The Three Traditions,p.7.
⑧ Ian Hall,The International Thought of Martin Wight,p.143.
⑨ Martin Wight,International Theory:The Three Traditions,p.5.
⑩ Martin Wight,International Theory:The Three Traditions,p.268.
(11) Ian Hall,The International Thought of Martin Wight,p.142.
(12) R.B.J.Walker,“History and Structure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illennum,Vol.18,No.2,1989,p.182.
(13) Renee Jeffery,“Tradition as Invention,” Millennium,Vol.34,No.1,2005,p.75.
(14) Martin Wight,International Theory:The Three Traditions,p.259.
(15) Martin Wight,International Theory:The Three Traditions,p.260.
(16) Hedley Bull,“Society and An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Herbert Butterfield and Martin Wight,eds.,Domestic Investigation:Essay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London:Allen and Unwin,1966,p.35.
(17) Hidemi Suganami,The Domestic Analogy and World Order Proposals,p.24.
(18) Hedley Bull,“Society and An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40.
(19) Hidemi Suganami,The Domestic Analogy and World Order Proposals,p.24.
(20) Ian Clark,“Traditions of Thought and Classical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Ian Clark and Iver B.Neumann,eds.,Classical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1996,pp.4-5.
(21) Hedley Bull,The Anarchical Society: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p.23.
(22) Martin Wight,International Theory:The Three Traditions,pp.17,32.
(23) Hedley Bull,“Society and An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37-38.
(24) Martin Wight,International Theory:The Three Traditions,pp.8,41.
(25) Hidemi Suganami,The Domestic Analogy and World Order Proposal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14.
(26) Hedley Bull,The Anarchical Society: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p.25.
(27) Hedley Bull,“Society and An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38.
(28) Ian Clark,“Traditions of Thought and Classical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Ian Clark and Iver B.Neumann,eds.,Classical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5.
(29) Emmanuel Navon,“The Third Debate Revisited,”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27,No.4,2001,p.614.
(30) Hedley Bull,“International Theory:The Case for a Classical Approach,” World Politics,Vol.18,No.3,1966,p.362.
(31) Stephen George,“The Reconciliation of the Classical and Scientific Approaches to IR?” Millennum,Vol.5,No.1,1976,p.29.
(32) 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McGraw-Hill,1979,p.12.
(33) Stanley Hoffmann,“A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aedalus,Vol.106,No.3,1977,p.52.
(34) Hedley Bull,“International Theory:The Case for a Classical Approach,” World Politics,Vol.18,No.3,1966,p.369.
(35) Martin Wight,International Theory:The Three Traditions,p.258.
(36) Martin Wight,“Why is There No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Herbert Butterfield and Martin Wight,eds.,Domestic Investigation :Essay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32.
(37) Hedley Bull,The Anarchical Society: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p.75.
(38) Martin Wight,International Theory:The Three Traditions,p.1.
(39) Robert Jackson,The Global Covenant,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71.
(40) Martin Wight,International Theory:The Three Traditions,p.259.
(41) Hedley Bull,“Martin Wight and the Theory of IR,” p.104.
(42) Martin Wight,International Theory:The Three Traditions,p.47.
(43) Martin Wight,International Theory:The Three Traditions,p.6.
(44) David Yost,“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the Theory of IR,” p.282.
(45) Martin Wight,International Theory:The Three Traditions,p.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