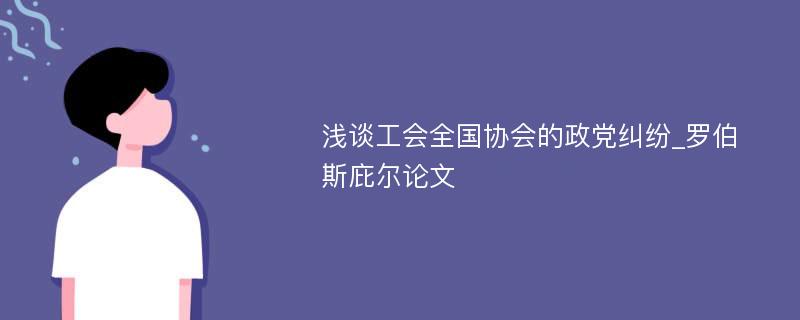
简论吉伦特国民公会的党派之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派论文,之争论文,公会论文,国民论文,简论吉伦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法国大革命中,吉伦特派的统治最为短暂,却不乏引人注目之处。史学家们已对其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但关于这段历史的一个重大问题:吉伦特派与山岳派争斗的实质,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本文拟以此作为论述的主题。
一
关于吉伦特派的由来与组成,英国的大革命史专家西登汉姆已作过详尽考证。他认为,被称作吉伦特派的只是几个政见大致相同而组织松散的小集团,其成员也只有二三十名,包括一些来自吉伦特郡的国民代表。这一判断是符合大革命中党派存在的实情的。大革命中涌现的众多党派并不是有特定政治纲领、组织严密、有纪律的政党,而是政见或志趣大致相同的人所结成的一些松散的小集团。吉伦特派的主要代表有布里索、孔多塞、罗兰、韦尼奥、巴巴鲁、卢韦、比佐等。山岳派最初是对立法议会中极左翼代表的称呼,国民公会中的山岳派指的是以罗伯斯庇尔为代表的小集团,其主要成员有圣茹斯特、科洛·德布瓦、丹东、德穆兰等。
就其成员的社会身份和基本主张而言,吉伦特派和山岳派的一致性是主流。布鲁瓦佐对此作了这样的概括:“两个派别的人是同行,受过相似的教育,其主要观点和生活方式也相类似。这些相视如寇仇的兄弟都具备正直、勇敢、克己的品质,而且同样地威严和坚忍不拔,奉行同一套处世哲学。”(注:布鲁瓦佐:《雅各宾共和国,1792~1794》,49页,剑桥大学出版社,1983。)他们曾亲密无间地推动着革命向前发展,但在国民公会时期二者却唇枪舌剑地要争个你死我活,最终演出了一幕自相残杀的悲剧。
大革命史的研究者已从不同角度对两派争斗的实质作出了解释。我认为,吉伦特派与山岳派之间的争斗既非阶级斗争,亦非阶层间对抗性的原则之争,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两个资产阶级派别间爆发的权势之争;决定这场争斗结局的力量主要来自于激进的下层群众运动。
二
吉伦特派与山岳派分裂的根源可上溯到布里索和罗伯斯庇尔关于战争问题的争论。
1791年6月国王出逃事件之后,外国武装干涉的危险日益增大。吉伦特派坚决主战。罗伯斯庇尔认为对外战争隐含着危险,因而独树一帜公开反对战争。他攻击吉伦特派,指责布里索勾结宫廷,策划阴谋。这些指责虽措辞激烈,却含混不清,缺乏使人信服的证据。被激怒的吉伦特派如法炮制,指控罗伯斯庇尔是阴谋的参与者。虽然这场争论的权势争夺色彩不甚鲜明,却初步展示了两派在以后的权势之争中所使用的主要手段和进行方式。
吉伦特派和山岳派在国民公会中的激烈较量直接起源于二者关于建立共和国的道路问题的争执。就大革命发展的内在逻辑而言,1792年夏季的共和运动目的在于清除行政权日益明显的反革命性质,重新调整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体制的变更实际上是对权力的重新分配。共和主义者在反封建方面步调一致,在建立共和国的道路问题上却存在着明显的分歧。
吉伦特派在议会占有优势,所缺少的只是行政权。这一权力似乎可以利用群众运动的压力迫使国王屈服而获得,“国王”这一称号则可以暂存。同时,立法议会应予保留,共和国应当通过法律程序,诞生在立法议会的决议中。为此,7月20日韦尼奥、让·索内等人通过与王室有联系的画家博兹致信国王,(注:哈德曼:《法国大革命》,142页,圣马丁出版社,1982。)26日布里索公开反对废黜国王。
罗伯斯庇尔等人的影响力主要不在议会而在群众中,只有一场广泛的群众运动才可能把他们推上权力顶峰。因此,他们选择了一条相对激进的、议会外的革命道路,而且视议会为通向权力之路的最大障碍。此时,罗伯斯庇尔在废黜国王问题上的表现并不突出,甚至有些保守;但在反对立法议会问题上,他却十分坚决。7月29日他指责“行政权想搞垮国家,而立法机关则不能或不想拯救国家”。(注:王养冲、陈崇武编:《罗伯斯庇尔选集》,88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两天后,他又提出了一个排挤吉伦特派的议会改造方案。
8月10日革命结束了两条道路之争,使双方暂时妥协,但这并没能平息争斗。革命壮大了罗伯斯庇尔等人的势力,他们所控制的巴黎公社获得了相对于议会的独立性。在法国政治舞台上出现了最高权力被立法议会和巴黎公社分享的特殊现象。吉伦特派与罗伯斯庇尔等人间的权势之争便表现为两个机构间的争斗,这样就形成了国民公会时期派别之争的基本格局。吉伦特派鼓动立法议会不断通过限制或摧毁巴黎公社权力的决议,一向谨慎的孔多塞也公开攻击巴黎公社“采取专横的行动,损害了国家的最高权力”。(注:伊丽莎白·巴丹特尔、罗贝尔·巴丹特尔:《孔多塞传》,308页,商务印书馆,1995。)罗伯斯庇尔等人则针锋相对,最终使吉伦特派在巴黎的选举中全军覆没。
三
9月21日国民议会开幕,吉伦特派与山岳派的权势之争由序曲转入了主题阶段。
此时,山岳派主要由来自巴黎的国民代表组成,他们以公社的真正代言人自居。吉伦特派在外省的选举中获胜,他们再度控制了议会。这样,共和国形成过程中出现的分裂和对峙延展到了国民公会中,从而也使两派的权势之争呈现出外省与巴黎冲突的表象。
根据吉伦特派、山岳派以及群众运动三种力量的消长和相互关系变化,吉伦特派与山岳派在国民公会时期的争斗以1793年4月1日为界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两派激烈争斗,同时又都敌视激进群众运动,共同反对限价;第二阶段山岳派转而联合群众,支持限价。
在第一阶段中,两派争斗主要限于议会内部。双方首先在对革命形势的认识上发生了冲突。马拉等人认为革命远未结束,仍鼓吹革命。吉伦特派则只要求巩固维护私有制的法律秩序。显然,这种对革命形势认识的分歧是两条道路之争的变相延续。两派在第一阶段的争斗还表现在以下三件事上:联邦主义问题、卢韦与罗伯斯庇尔的争执、关于处置路易十六的斗争。(注:国民公会初期国民公会与公社对抗的详情可参见汤普森《法国大革命史》,289~356页,牛津,1966。)
在以往的大革命史论著中,吉伦特派多受到推行联邦主义的指责。这种论断与实情存在着差异。事实上,吉伦特派内部对联邦制的认识存在着很大的分歧。真正的联邦主义者大概只有比佐一人,深受美国共和制影响的孔多塞却极力反对在法国实行联邦制,主张在宪法中增设防止地方权力膨胀的条款。(注:王令愉:《孔多塞与法兰西第一共和国》,载楼均信主编《法兰西第一至第五共和国论文集》,55~56页,东方出版社,1994。)同时,关于在罗兰夫人的沙龙中讨论联邦主义的说法也被证明是一种误传。(注:西登汉姆:《吉伦特派》,12~18页,格林伍德出版社,1972。)乔治·勒费弗尔曾指出:“吉伦特派鼓动自1789年以来广泛发展的地方自治情绪。他们中间虽然有些人对联邦制感兴趣,但整个吉伦特派却从未有过在法国实行联邦制的打算。”(注:乔治·勒费弗尔:《法国革命史》,240页,商务印书馆,1989。)这一判断是合理的。
此外,1792年9月25日拉索斯的发言和罗兰在9月23日关于郡卫军的提议,也常被视为吉伦特派推行联邦主义的证据。拉索斯的发言:“我不愿这个受阴谋家指挥的巴黎对于法国变得象罗马城对于罗马帝国那样。巴黎的势力必须和其他各郡一样,应缩小到八十三分之一”,是和勒贝基攻击罗伯斯庇尔搞独裁的发言前后呼应的。(注:马迪厄:《法国革命史》,284页,商务印书馆,1973。)这正体现了国民公会与巴黎公社、吉伦特派与山岳派之间的权势争斗。吉伦特派建立郡卫军的用意亦在于掌握武装力量对抗巴黎公社和山岳派的挑战。(注:西登汉姆:《吉伦特派》,90、195页,格林伍德出版社,1972。)
有关卢韦与罗伯斯庇尔争辩的详情,史学家们已有不少论述。(注:陈崇武:《罗伯斯庇尔评传》,112~125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纵观整场冲突,双方并未真正就原则性问题进行论战,而主要是围绕“篡权”、“独裁”这两个字眼,即围绕着权力归属问题展开争吵的。
如何处置国王的争论是吉伦特派与山岳派之间更全面、更直接的一场冲突。这场争论与其说是原则之争,不如说是策略分歧的产物,因为两派在最根本的问题——国王是否有罪——上意见完全一致。吉伦特派确实在处置国王的问题上实行了拖延政策,他们担心处死国王会成为大规模反法战争的导火线。山岳派则把这种策略上的考虑视为阴谋,在他们看来,“对国王的赦免便是对8月10日起义和雅各宾主义的亵渎与否定”。(注:布鲁瓦佐《雅各宾共和国,1792~1794》,53页,剑桥大学出版社,1983。)国王的死便成了他们权力合理性的证据。因此,圣茹斯特指出,处置国王已“不是一个法律案件,而是一个政治案件”。策略分歧依然源于对权势的争夺,“国王的脑袋成了党派斗争的赌注”。(注:乔治·勒费弗尔:《法国革命史》,297页,商务印书馆,1989。)
国王被处死后,全面战争、叛乱、叛变接踵而至,革命形势空前危急。群众的爱国热情再度高涨,同时他们强烈要求限定物价。由埃贝尔分子控制的巴黎公社在4月初决定支持最高限价要求,一向反对限价的山岳派与公社的关系处在转折点上。
4月10日罗伯斯庇尔最终决定向激进的群众靠拢。从此,山岳派就以激进群众运动代言人的面目出现在国民公会。群众运动作为一支外部力量更直接地介入了派别之争。
大革命中的群众运动按其社会构成和目标的不同,可大致分为城市下层群众运动和农民运动。城市下层群众运动主要是无套裤汉运动,运动的兴起一方面基于无套裤汉的反封建意识,另一方面也是出于生活危机的压力。乔治·鲁德有这样的论断:“大革命时期人民起义最经常的原因就是下层人民经常要求得到足够的廉价面包和其它产品,以及渴求对此采取必要的行政措施保证。”(注:G.鲁德:《法国大革命时期巴黎人民暴动的动因》,转引自M.扎赫尔《忿激派运动》,27页,吉林大学出版社,1986。)随着粮食供应日趋紧张,无套裤汉们便“想建立一种制度,生产与交换的制度,用以限制企业自由和利润自由,以一种社会价格来制约它”。(注:布罗代尔、拉布鲁斯:《法国经济和社会史》第3卷,36页,法兰西大学出版社,1976。)农民运动也在1792年发生了转变。绝大多数永佃田的拥有者在吉伦特派执政初期获得了所期望的所有权,从此退出了农民运动。余下的人“首先他们或是在寻求完全废除私人财产,或是希望把这些财产严格限制在平均主义的范围内;其次,他们采取了很多措施去控制市场”。(注: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政的社会起源》,65页,华夏出版社,1987。)
无论是城市的限价要求(当然,限价运动在农村也有众多支持者),还是乡村的平均土地主张,都和吉伦特派遵奉的原则相去甚远。吉伦特派崇信启蒙思想家的人权学说,虽然他们从整体上把所有权视为一种社会权利,但又倾向于把这种社会权利视为与社会共生的、源于建立社会的原始契约的权利;虽然他们反对社会中的极端贫富差距,但更强烈地反对任何要求社会平等的主张。因此,作为资产阶级的忠实代表,吉伦特派成为群众运动首当其冲的攻击目标。
山岳派与下层群众的关系比较密切,并且善于从群众运动中获取声威和势力。但是二者间的联系并非一直都那么紧密、直接。山岳派与吉伦特派一方面在审判国王等问题上吵得难分难解,不共戴天;另一方面在对群众运动的态度上保持一致。他们不仅支持吉伦特派的反限价运动法令,而且二者攻击限价要求的言论如出一辙,就连一向十分激进的马拉也在二、三月间对力主限价的忿激派大加斥责。
但是,到了4月初,形势发生了急转,吉伦特派的统治摇摇欲坠,与无套裤汉关系密切的埃贝尔派在巴黎的声威扶摇直上,山岳派面临着被挤垮的危险。山岳派决定步埃贝尔派的后尘。所以,“从4月10日起已昭然若揭,以公社和各区为一方,以山岳派为另一方,双方之间达成妥协。公社和各区帮助山岳派战胜吉伦特派,山岳派为报答这种帮助而支持‘忿激派’的社会纲领”。(注:马迪厄:《恐怖时期的物价高涨和社会运动》第1卷,137页,巴黎,1973。)吉伦特派为摆脱这种困境,希望赶紧颁布宪法,通过新宪法生效后的选举排斥山岳派。他们的提议因罗伯斯庇尔的反对而未能通过。
4月24日罗伯斯庇尔对刚刚确立的人权定义提出异议:“人的主要权利是保证维持生存和自由的权力”,并要求对所有权定义作如下修正:“所有权是每个公民按自己的裁夺使用和支配法律保障他的那部分财产的权利。”(注:波普朗:《罗伯斯庇尔文选》第二卷,132~140页,巴黎,1957。)罗伯斯庇尔对人权、所有权的定义与资产阶级奉为圭臬的“八九年原则”和“九三年宪法”中的相关定义存在很大歧异,吉伦特派随即予以反击。
的确,两派的主张泾渭分明,只需稍加对比,很容易就会使人得出“原则之争”或“阶级之争”一类的结论。其实,将罗伯斯庇尔前后的言行加以对照,并结合革命所处的实际情况稍作分析,罗伯斯庇尔表里如一的真实性便要大打折扣。所谓的原则之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表象,它分明掩盖着权势争夺的实情。
罗伯斯庇尔早在1792年12月2日就提出“第一位的人权就是生存权”,这一原则是忿激派论证其限价要求的理论前提。不过,罗伯斯庇尔的结论却正好与忿激派的限价要求截然对立,他和吉伦特派一道喊出了“巩固粮食自由贸易”的口号。(注:波普朗:《罗伯斯庇尔文选》第二卷,85~86页,巴黎,1957。)此刻,罗伯斯庇尔又从这一理论出发要求对所有权进行严格限制,把曾被视为自然权利的所有权降为第二性的社会权利。这一改变是与山岳派决定接近无套裤汉、支持限价的事实密切相关的。这实际上是“以含蓄的方式为经济统治进行辩解”。(注:乔治·勒费弗尔:《法国革命史》,302页,商务印书馆,1989。)索布尔也认为:“我们不能掩饰罗伯斯庇尔这种态度的策略性质:为了战胜吉伦特派,必须给无套裤汉一种社会民主的希望,好让他们关心这种胜利。”(注: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23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策略只是暂时性的手段,与相对持久的原则确实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当两个月后,所有权以“一切公民享受和随意支配自己的财产和收入以及劳动和产业成果的权利”的新面目出现于“1793年宪法”时,我们也就完全用不着惊讶、惶然了!但是,勒费弗尔还是忍不住要发出一声感叹:“罗伯斯庇尔对他以前提出的可能使资产阶级害怕的几项条款从此不再吭声!”(注:乔治·勒费弗尔:《法国革命史》,302页,商务印书馆,1989。)
6月初,山岳派与无套裤汉联合行动,推翻了吉伦特派的统治,吉伦特国民公会时期就此完结。
四
吉伦特派与山岳派的权势之争贯穿整个吉伦特国民公会时期。在两派争斗中,争斗的激烈程度和各自实力的消长呈现出非规则的波动。这些变动在一定程度上是随着革命形势演变而发生的,缺乏内在的独立发展的逻辑。双方的争吵并没有呈现多少原则之争或阶级之争的色彩。考察两派人物的社会地位和财产状况,也找不出更多的证据来支持原则之争的论断。
当我们把注意力移向党争中相互攻讦的言辞,就不难发现,随时随处均可听到或看到“阴谋”、“野心家”、“同谋者”、“独裁”之类的字句,这正展示了双方的头脑里都充溢着一种与危机感和惩戒决心相伴随的“阴谋意识”。这一意识在争斗中发挥的作用十分显著。罗伯斯庇尔和布里索就战争问题发生争执时,都指控对手大搞阴谋。“九月屠杀”中,罗伯斯庇尔再次指控布里索等人涉及阴谋案,使布里索险遭杀身之祸。国民公会成立伊始,吉伦特派便揭露罗伯斯庇尔等人搞独裁,这种指控一直发展到卢韦对罗伯斯庇尔的猛烈攻击。在审判国王时,双方都把对方骂作“王党”。在1793年4月15日公社提交国民公会的请愿书中,吉伦特派以往的言行均被斥为阴谋活动。(注:《巴黎市府要求国民大会逐出吉伦特党领袖的请愿书》,见吴绪、杨人梗选译《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86~90页,商务印书馆,1989。)对阴谋的恐惧和警觉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大革命中阴谋意识的出现是和法国民众的阴谋思维定式、革命群众在国内外反动势力进攻下萌生的强烈危机感以及阴谋事件大量存在的现实紧密相关的。这种阴谋意识一旦渗入党派之争,便衍生出一种“反党派意识”,从而形成以党派斗争的形式反党派存在的怪圈:“即使最反对党派政治的革命者(一般说来,政治态度越是激进,反党派倾向就越是强烈),他们的活动也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党派行为的性质。”(注:高毅:《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272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吉伦特派和山岳派均陷入了这一怪圈,都患上了这种“议会政治的早期幼稚病”。他们一方面齐力推进政治透明、政治公开化,对拉帮结派极度鄙夷;另一方面却在社会政治资源的分配中不自觉地结成派别,谋取优势。温文尔雅、口若悬河的吉伦特派在共和运动中最先成为统治者,他们力图使自己的统治有序,取得完全的合法性。而山岳派并不甘心只作在野的批评者。在受阴谋意识毒化的政治空气中,他们一方面拼命地维护小集团的权势,一方面把对自己的挑战视为反革命阴谋。随着党争的激化,他们越来越把阴谋指控当成争斗的手段,时常毫无依据地给对手加上“阴谋者”的罪名,大肆攻击,以此来确保或扩大自己的权势。党争离原则之争的距离也愈来愈远。群众运动的介入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党争的内容与演化方向,而且在党争的最后阶段成了决定党争结局的关键因素,并最终使本已激化的党争跃出了非对抗性矛盾的边界走向对抗。
吉伦特派与山岳派的权势之争削弱了资产阶级自身的力量,使整个统治机器缺乏应有的效率和威力,变得低能、软弱。同时,这些争斗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革命形势的恶化,积极好战的不妥协政策在一定意义上是党争的恶果。党争也阻延了统治阶层解决社会问题的步伐,从而激化了资产阶级和下层群众的矛盾。这使得革命政府不得不求助极端措施来拯救革命。
这场权势之争的悲剧性还不止于此。影响更为深远的是,这场争斗为革命内部的派别之争提供了一个不好的先例。后来者对权势之争的恶果多视若无睹,反而承袭了先行者所使用的党争手段,相互倾轧,严重地破坏了资产阶级内部的团结。这种内耗式的争斗无疑是导致法国政局长期不宁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正是在这场争斗中,在那些宗奉民主自由原则的革命者的意识里,反民主的倾向正在潜行暗长。党争刺激下日益强烈的反党派意识促使罗伯斯庇尔在为吉伦特派敲响丧钟的时刻,给自己立下了这样的原则:“只能有一个意志,无论它是共和国的或者是王权的。”共和二年恐怖专政的轮廓已隐约可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