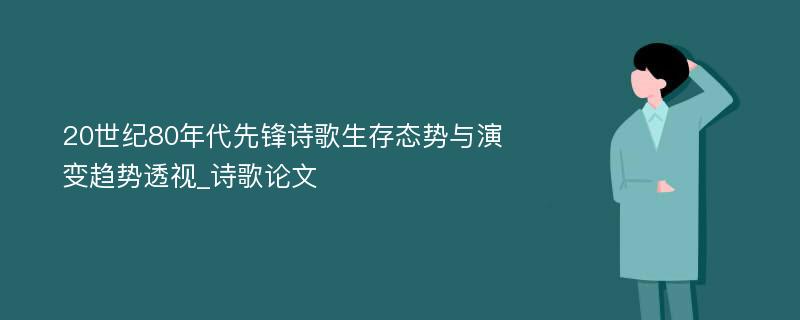
八十年代先锋诗的生存境遇及演变态势透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锋论文,境遇论文,态势论文,透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02)03-0086-06
艺术“要是表现了一种风格上或技巧上的根本变革,它可能就是革命的。这种变革可 能是一个真正先锋派的成就,它预示了或反映了整个社会的实际变革。”[1](P2)诗的 “先锋”本质是指诗艺(诗歌艺术上)的变革而不是指诗意(诗的内容及诗人的思想)上的 变革。先锋的动力主要有三点:人追求自由的本能、喜新厌旧的天性、文体本身具有的 革命的政治潜能;即人和文体天生具有先锋性,人和艺术虽然都在自由与法则的对抗与 和解中生存,都具有强烈的秩序感,但也有强烈的破坏欲。特别是人和艺术的自由本能 受到法则的压迫时,由破坏欲引发的“先锋”更是激进。诗是最高的语言艺术,正如心 理学家加登纳认为人天生具有语言智能,诗歌是人的语言智能的典型范例。古今中外, 诗在小说、散文、戏剧等文学体裁中都具有强烈的“先锋性”,至今在语言和文体的求 新求异上更容易出现“先锋性”。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革命和改革重于一切的破旧立新 的时代,诗更是常常成为革命的前驱和工具,政治运动常常以诗歌运动开始,如世纪初 的新诗革命和70年代的“四五”天安门运动,80年代的思想大解放也与诗歌改革,如朦 胧诗运动直接相关。因此,20世纪的汉语诗歌更是具有“先锋性”的文体。这里的先锋 性不仅指语言革命及文体革命,即怎么写上的先锋性,更指“写什么”的先锋性。
“文革”以后,中国进入大规模的改革开放时代,新诗也进入大变革时代,各种流派 异彩纷呈,新潮叠出。80年代的新诗诗坛始终或弱或强地出现“先锋”浪潮,正是此起 彼伏的“先锋诗”推动了新诗的巨大发展和国人的思想解放,同时也给新诗的文体建设 和国人的思想带来了一定的混乱。尽管80年代先锋诗从诗的语言、文体等诗歌艺术方面 给新诗带来了巨大的进步,但是受中国“诗言志”、“达则兼济天下”的入世的诗教传 统和“立意高远,境界自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重内容轻形式的作诗传统的 巨大影响,加上80年代又是各种观念大碰撞、新旧势力强烈对抗的特殊时期。尽管作为 现代艺术的重要特征之一的“先锋”精神本来应该具有敢破敢立的“前卫”品格,却不 得不向现实妥协,不再那么锋芒必露。本来先锋诗人大可不必“直而温,宽而栗,刚而 无虐,简而无傲”[2](P2)地做“温柔敦厚”的谦谦君子,应该义无反顾地勇往直前当 改革的前驱,真正成为“先锋”,却不得不从重视诗的语言文体的极端走向重视诗的内 容思想的极端,“媚俗”地由诗艺的高空飞翔变成诗意的低空巡行。不难发现80年代先 锋诗的特征:重视“写什么”的内容的先锋常常压迫甚至取代了本应重视“怎么写”的 形式的先锋,即诗意的先锋远远大于诗艺的先锋,先思想家后诗人的现象普遍存在。
朦胧诗:负载现实重任的先锋诗
当代诗歌的先锋首推称为“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的朦胧诗,不仅以更自由的形体、 更富有弹性的诗歌语言打破了垄断诗坛近数十年的新格律诗的一元格局,甚至使很多在 六七十代流行的诗人“下岗”,更是以“先锋思想”的启蒙独步神州的。在为朦胧诗辩 护的3篇经典性诗论中(人称“三崛起”)便能发现朦胧诗诗人思大于诗,更多地致力于 思想改革,试图当民众的启蒙者和代言人的非诗倾向。谢冕在《在新的崛起面前》第一 段就指出:“一些老诗人试图作出从内容到形式的新的突破,一批新诗人在崛起,他们 不拘一格,大胆吸收西方诗歌的某些表现方式,写出了一些‘古怪’的诗篇。越来越‘ 背离’诗歌传统的迹象的出现,迫使我们作出切乎实际的判断和抉择。”这里的“古怪 ”、“背离”是先锋的求异求变的特质。在此,他没有对表现方式的“古怪”(诗艺的 先锋)和对诗歌传统的“背离”(诗意的先锋,汉诗的传统一向是内容大于形式,诗言志 大于抒情,“思无邪”的伦理化情感大于人的自然情感)作出孰多孰少的评判,在文中 却说:“的确,有的诗写得很朦胧,有的诗有过多的哀愁(不仅仅是淡淡的),有的诗有 不无偏颇的激愤,有的诗则让人不懂。”这段话道出了朦胧诗当时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 “围攻”的实质性原因,并不是朦胧诗人不能当把诗写得朦胧些的表现手法的先锋,而 是因为不愿意当“歌德派”,反而让诗有“过多的哀愁”和“偏颇的激愤”,这样的思 想先锋在一些强调稳定高于一切,甚至不相信“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语)眼中是不 利于“社会稳定”的,当然会受到阻击。其实当时参与反对朦胧诗的很多人,特别是诗 论家完全有能力读懂朦胧诗,他们借读不懂向朦胧诗发难只是一个借口。有的确实是出 于艺术目的反对“崛起派”的不顾中国国情的激进,害怕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就无法 关上,特别是针对新诗60年来多破少立的实际,想用改良的手段取代革命,如“上园派 ”的诗论家提出要中庸地稳健地发展。有的是出于对朦胧诗醉翁之意不在“诗”而在“ 思”的反感,认为有害于纯诗艺术的发展而反对的。还有的确实是因为诗歌观念落后保 守,文化水平太低真的“读不懂”,害怕诗歌背离为工农兵服务的大众文艺方针而反对 的。反对朦胧诗最严厉者是害怕偏激的诗歌运动带来思想运动最后导致政治革命者。准 确地说,正是因为读懂了朦胧诗的“思想先锋”的本质,才出现了“围剿”诗歌先锋的 运动。值得庆幸的是,由于已是改革开放年代,政治较为开明,“朦胧诗论争”才没有 沦落为“政治运动”。
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的副题是《评我国诗歌的现代倾向》,没有使用先锋一词, 此处的“现代”一词可以与“先锋”互换,如同世纪之交的“先锋”一词在大众传媒中 被“另类”一词形象地取代。文中结论“中国的诗人们不仅开始对诗进行政治观念上的 思考,也开始对诗的自身规律进行认真的回想”[3](P432)。尽管他认为朦胧诗具有文 体的先锋性:“这些诗,角度新颖,语言奇警,结构不凡。”但他列举的《回答》、《 致橡树》、《这也是一切》、《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不满》都是思想先锋的诗 作。他在此文中也以此为自豪:“一个平淡、然而发光的字出现了,诗中总是或隐或现 地走出了一个‘我’!”
当时海外华语诗人都认为朦胧诗并不朦胧。1982年郑树森曾在纽约一个现代文学讨论 会上宣读一篇题为《朦胧诗究竟多朦胧?》的英文学术报告。叶维廉在《危机文学的出 路——大陆朦胧诗的生变》一文中评介此文:“该文着重他们的短诗(大陆的诗向来是 单调而长,偏于叙事而少抒情;这次的诗有些是奇短,如北岛的《生活》只有一个字: ‘网’),并将之与英美的意象派和台湾着重意象的现代诗人比较,有些相似,并非难 懂。”[4](P273)然后结论:“所谓‘朦胧’,所谓‘难懂’,对大陆以外的一般的作 者而言,根本不存在。这些诗被批判的主要原因是:他们用了多重意义多重指涉的意象 和隐喻。但在1949年以前所承袭的阅读训练的读者,在他们读中国古典诗或西洋诗的习 惯里,多重暗示性,意义不限指,是诗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诗本来就有隐有秀,秘向 旁通,含蓄而丰富。除了一些专写个人私有象征那类诗之外,有放射性的指涉作用的意 象,一向被视为优点而非缺点。显然,对朦胧诗提出来的难懂问题,不是‘表达策略’ 上的问题,而是‘阅读与诠释习惯’上的问题。因为,在大陆,长久以来,作者、读者 一再走向一种观察现实的方式,走向一种表达现实的方式。”[4](P273-274)正是作者 、读者具有重现实轻理想,重直觉轻想象,重客观描写重主观抒情的创作和欣赏习惯, 使朦胧诗诗人不得不从诗艺的先锋高度下降到诗意的地平线上,直接关注大众生活,重 视诗的思想内容,做时代精神的代言人和民主自由思想的启蒙者。即中国诗歌长期形成 的现实主义传统同样严重地妨碍着朦胧诗人进行重大的诗艺探索,残酷的现实使他们不 可能进行象牙塔中的文体实验。由于所受的文化教育和所处的特殊的生存境遇。朦胧诗 的代表诗人绝大多数都不是生活在校园中的诗人,特别是有影响的几位主将全都是社会 青年,生活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从事着非知识分子性的职业,更不是作家协会养起来的 专业诗人,即使为数极少的几位当时就读于大学,也都是一直在社会中早就成长起来的 社会型诗人,大多是当过知青,特别是“老三届”的学生,学生不仅年龄大,而且有丰 富的社会经验和写作经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二届大学生诗人大多得益于生活阅历丰 富而不是知识丰富。尽管他们有生活,甚至还有较长的创作经历,但他们的写作技巧, 特别是语言文体的创造能力并不强。由于特殊的生活经历和创作经历,他们太重视现实 生活,太想过早地干预现实,太重视实践,不愿意奢谈理论,更不愿意为艺术逃避生活 。当时的诗坛被比朦胧诗诗人文化水平和作诗技能更低的“工农兵”诗人垄断着。特别 是在六七十年代,中国的专业诗人极少有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在各个作家协会任专业 诗人的大多是闲职的老干部和没多少文化却根红苗正的工农兵出身的中年人,他们常常 只具有写豆腐块式的顺口溜、打油诗的水平。尽管有的专业诗人每年由国家出版数本诗 集,却没有写出几首真正具有艺术性的好诗。朦胧诗诗人向如此水平的中老年诗人发起 “冲锋”,自然不需要多少诗艺。相对而言,朦胧诗对新的作诗技法的学习热情和接受 能力都要远远高于他们想“造反”的前辈诗人。因此,在国家级诗歌培训班上,发生了 本是学生的青年诗人群起“哗变”不愿听前辈诗人讲课的事件。
时代造成朦胧诗的几位主将的文化水平都不高,没有一位是通晓中外诗歌的知识型诗 人,如舒婷只有中学毕业,杨炼、顾城甚至没有接受到完整的中小学教育,在80年代初 写出组诗《失传的国度》、《礼魂》、《西藏》、《逝者》的杨炼是朦胧诗人中最具有 实验精神的诗人,“因‘文革’原因,总共只上过小、中学六年。”[5](扉页)这样的 知识实力较难在诗的语言文体上进行巨大而有成效的“实验”。因此,人们重视的是朦 胧诗的先锋精神,如北岛的“我不相信”的怀疑品格和民主精神。甚至舒婷《致橡树》 的女性自强自立的爱情观以及《神女峰》一诗中“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 肩上痛哭一晚”的实用性、人性化的爱情观等诗的“内容”远远比诗的形式更引起了人 们的重视,诗艺粗糙的《致橡树》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中正是因为此诗有利于对青年学 生进行思想教育,培养正确的恋爱观。
如顾城的诗所言:“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朦胧诗诗人进行 的更多是思想的先锋,思想的“求索”,缪斯只是他们寻找光明的工具。“朦胧诗诗人 在文化无政府主义的歧路上,……像古代被放逐的诗人们,不但对时间与存在的压力极 其敏感(如他们走向自我和走向古代那种近乎发热发狂的‘行程’所呈现的),而且对他 们所处的空间位置亦极其敏感。”[4](P282)从他们的诗名(如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 匙丢了》、杨炼的《自由》、舒婷的《一代人的呼声》、《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等 )和诗的意象(如杨炼的大雁塔、长江,江河的天安门、长城、黄土高原,鸿荒的汨罗江 、天坛、黄花岗,舒婷的祖国、老水车等)便可以看出他们的大我情感远远大于小我情 感。舒婷写于1980年2月的《一代人的呼声》总结出了朦胧诗人的不由自主地充当时代 和人民甚至真理的代言人的非我的创作目的:“我决不申诉/我个人的遭遇。”“为了 百年后的天真的孩子/不用面对我们留下的历史猜谜;为了祖国的这份空白,/为了同民 族的这段崎岖,/为了天空的纯洁/和道路的正直/我要求真理!”这样的创作目的很难相 信诗人会把诗作为个人情感,特别是个体的隐私性情感宣泄的艺术,很难让人相信诗人 如雪莱在《诗辩》中所言:“诗人是一只夜莺,栖息在黑暗中,用美妙的声音唱歌,以 安慰自己的寂寞。”[6](P53)即使是写于1977年3月27日的爱情诗《致橡树》,也很容 易理解为不是写给自己的情感上的爱人,而是如同她1979年4月创作的《祖国呵,我亲 爱的祖国》一样的赤子爱国的诗篇。
第三代诗:重视诗艺更重视诗意的先锋诗
正是因为朦胧诗诗人文化水平和作诗技巧不高,他们的诗作又过于重内容轻形式。才 使大多从小受到正规教育,较长期间生活在校园中的第三代诗人的不满。他们喊出了“ PASS北岛”、“诗到语言为止”等试图从诗艺上超越朦胧诗的“先锋”口号。第三代诗 人所受的诗歌教育比朦胧诗诗人正规很多,他们正处在80年代初中期大规模的外国现代 诗歌理论和诗作的译介和对中国现代诗歌的重新发掘的时代。他们发现,尽管朦胧诗比 六七十年代的诗在诗艺上有了巨大的进步,把朦胧诗与现代文学史上的意象派、现代派 等相比,或者与外国的现代诗相比,其“朦胧”及诗艺完全是小巫见大巫,甚至可以说 诗艺是很粗浅的。特别是第三代诗人生活在如卞之琳所言的“当时由于方向不明,小处 敏感,大处茫然,面对历史事件、时代风云,我总不知要表达或如何表达自己的悲喜反 应”[7](P3)的校园中时,有条件书生意气般地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进行主要是语言实 验和文体实验的“实验诗”创作,进行真正的“先锋诗”创作。80年代中期是校园诗歌 最繁荣和校园诗人进行诗歌实验最疯狂的时期。几乎所有的校园都有诗社诗刊,北京大 学、吉林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西北师范学院、西南师范学院、华东 师范大学等都培养出大批诗人。著名的大学生诗歌刊物有《大学生诗报》(重庆以西南 师范大学、重庆师范学院、重庆大学、第三军医大学、四川外语学院等高校大学生联办 ,是全国第一家多家大学联办的诗报,80年代中期轰动一时,后因意识形态和某些大学 生诗人的做人和作文方式都被认为有悖时尚,从而受到社会,特别是成人社会的阻扰等 多种原因停办,在全国产生影响的诗人有尚仲敏、胡万俊、邱正伦、邵薇等)、《我们 》(西北师范大学大学生办,20年不间断,走出了张子选、彭金山、高尚、唐欣、桑子 、阿信、叶舟、扎西才让等数代优秀诗人)。北京大学的《启明星》从80年代初创刊出 刊了25期。北大在近20年涌现骆一禾、海子、西川、臧棣、西渡、戈麦等优秀诗人。全 国各校都有处处宣称“为诗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校园诗人。
尽管仍以朦胧诗为主流诗歌,朦胧诗人与唱着“归来的歌”的中老年诗人的诗作占据 了公开刊物的版面。但是在比朦胧诗人更年轻的校园诗人和刚毕业离开校园的民间诗人 中,以实验诗为代名词的先锋诗几乎成了主流诗歌,自编的诗刊诗报成了他们的实验地 。不久,少数公开的刊物也开辟了实验诗歌专栏,成为很多民间诗人、诗派大显身手的 舞台,当时也是他们唯一能够展示其创作的先锋性的地方。因为当时的主流刊物和大众 读者都不接受他们。如阿红主编的《当代诗歌》1987年第1期以该刊,更是其他诗刊前 所未有的魄力推出了民间诗歌的代表团体“非非主义”的诗作,开设了“非非主义诗作 选”专栏,并标明是“新潮诗”。同期刊发的诗作有周伦佑的《埃及的麦子》、《鱼形 花瓶》,蓝马的《巧克力游戏》、《降旗仪式》,陈小蘩的《月亮高度》、《盗警“11 0”》,杨黎的《看水去》、《中国鱼》,刘涛的《对视》、《阴天》。《当代诗歌》1 987年第5期还发表了司徒闵的《非非主义简介》,使该诗派的极具先锋性的诗歌主张在 公开诗歌刊物上亮相。80年代中期无论是民间或是校园先锋诗歌大多经历了同样的历程 :先是相信个体的力量,单枪独马地写诗,后来发现中国是一个“一个好汉三人帮”、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群体意识强烈垄断的社会,于是便拉帮结派,发动群体冲锋 ,便形成诗派。很多诗派开始时只是诗歌创作,寄希望于诗坛已成名的理论家的支持。 但是,由于80年代前期的朦胧诗论争由于多种原因不幸演变为政治权力、意识形态论争 ,很多诗论家开始对先锋诗保持沉默。而且当时很多诗论家出于诗坛稳定、权力划分等 艺术和非艺术因素,对先锋诗持保守反对态度。民间诗派便不得不推出自己的理论家和 与主流诗歌对抗的极端理论。这就更导致了主流诗歌的反感甚至反击。但是,这并不意 味着民间诗人有自己的诗歌刊物(当时的民间诗歌刊物的印刷发行并不自由,甚至多次 出现因为是“非法出版物”刊物被查禁收缴、编者被治安处罚的事件)和写作自由就意 味着他们没有想与官方诗歌合流的“招安心理”,特别是那些试图借诗歌出名和得到社 会认同的诗人,这种心理更为严重。很多诗人都是先在自己编的民间报刊上刊发自己的 诗作,再把这些诗作寄给公开的诗歌刊物,标明“请选载”;寄给主流诗歌的名诗人和 理论家,美其名曰“请指正”,本意却是请“广告”式评论。绝大多数诗人就是这样进 入主流诗坛的。所以《当代诗歌》不但发表“非非”的诗作,还发表了理论文章,最重 要的是,其后还刊发了针对“非非主义”的讨论。1987年第5期发表了当时的名诗人叶 延滨的极有见解的反对文章《一只没有壳的气球——读<当代诗歌>1987年1月号的“新 潮诗”随想,兼议“非非主义”的主张》,认为“非非主义旗号下发的所有的诗,包括 我举的《埃及的麦子》在内,没有一首是按‘非非主义’的理论写成的。原因很简单, 把一切文化和传统语言因素都清除掉了,那么诗人连一个字也无法书写,因为连诗人的 署名都是一个按‘非非主义’应该清除的‘抽象概念’。非非主义只会取消诗的存在” [8](P327)。1988年第3期发表了“非非”主帅,理论家周伦佑的《语言的奴隶与诗的自 觉——谈非非主义的语言意识兼答一位批评者》。周伦佑一开笔就写了一段相信“酒香 也怕巷子深”的八九十年代的民间诗人惯用的广告文字:“继‘朦胧诗’之后,‘第三 代诗歌’正在成为当代诗坛上引起争议的热点,作为‘第三代’诗歌前卫的非非主义, 一出现便受到了海内外诗界和理论界的广泛注意,10多家刊物(包括《当代诗歌》)转载 和介绍了非非主义的作品。当然也有批评,叶延滨刊登于《当代诗歌》1987年第5期上 的文章便是一例。”[9](P328)尽管这段由非非主帅给自己的诗派的价值评判——颇受 主流诗歌欢迎的“先锋的先锋”有广告嫌疑,但是这篇极有才气的文章却是当时极富有 “先锋意识”的诗论,文中谈论的“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和“语义的确定性问题”等问 题确实是先锋诗歌最应该关注的,尽管他的理论资源来自于阿恩海姆、燕卜逊等西方理 论家,这篇文章及非非的理论对当时先锋诗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这种影响不在于非非理 论的本身,而在于非非诗人及诗论的“先锋”意识和关注语言的独特视角,当时很多诗 人都还死抱着“体验”美学不放,决无向语言美学转向的充当诗艺的先锋的意识。尽管 写诗要重视语言,甚至“诗歌艺术是能够超语义”的这些观点绝非非非诗派的独创,但 是非非、他们等诗派在某种程度上唤醒或者强化了当时诗人的语言及诗艺甚至文体意识 ,是对朦胧诗“诗意的先锋”远远大于“诗艺的先锋”的巨大反拨。因此,80年代中后 期大陆风起云涌的民间先锋诗歌运动的最大意义在于对旧的有与政治意识形态合谋的主 流诗歌意识形态的巨大解构,有意无意地充当了“诗意的先锋”或“思想的先锋”甚至 “政治革命的先锋”,第三代诗人在诗艺的探索的功绩也是不可磨灭的。
民间先锋诗人的成功与《当代诗歌》的“新潮诗”这类栏目的大力举荐休戚相关,这 些栏目更是校园诗人显求诗艺的先锋的最佳阵地,使毕业了的大学诗人也能继续进行诗 歌实验。由于不再受到校园较为严格的政治检查和校园诗人没钱自己出刊物、出诗集的 压力,进入社会的诗人们更能随心所欲地“先锋”,民间诗歌刊物因此风起云涌。《深 圳青年报》、《诗歌报》等报刊都为先锋诗作出了巨大贡献。最值得一提的是《飞天》 的《大学生诗苑》对先锋诗作出的杰出贡献。尽管它发表的诗并不都是先锋诗,更没有 打出先锋诗的旗号。却成了朦胧诗后具有先锋品质的诗人的“黄埔军校”,特别80年代 中后期校园诗人施展才华与以前朦胧诗人为代表的,已成垄断之势的社会诗人对抗的主 要舞台。王若冰、伊沙等很多先锋诗人都撰文感谢过此栏的诗编张书绅老师。伊沙在《 大家的张老师》一文中说:“在80年代各大学诗爱者的心目中,《飞天》是最具权威性 而又有亲切感的刊物,因为它的《大学生诗苑》,因为张老师。全国各地高校中的诗歌 创作的佼佼者纷纷在此亮相并相认相识,形成一支庞大而富有生机的诗坛后备军。继‘ 朦胧诗’之后成为诗坛中坚力量的那批诗人,几乎都是当年在《大学生诗苑》上崭露头 角的……《大学生诗苑》对现代诗在民间的发展也起过重要的推动作用,为一个诗歌时 代的结束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大学生诗派’就是在《大学生诗苑》的基础上创立的…… 而真正的‘黄埔’,非《大学生诗苑》莫属。”[10](P319)“诗人”伊沙的成长经历和 当年的很多大学生诗人相同:“我第一次在《诗苑》上发表的是张老师删改后的一首4 行的小诗,那是我大学时代所发表的第一首诗,给了我莫大的信心和鼓舞!张老师的改 动使我感到满意。我在对‘朦胧诗’的模仿中徘徊了两三年之后,在1988年渐渐找到了 自己的路子,那批诗寄给张老师之后很快得到了他的回信。于是在当年的10月号的《诗 苑》上以《伊沙诗抄》为总题刊出了我10首诗,近400行,占了当期的《诗苑》一半的 页码——那是《诗苑》有史以来个人一次性发诗的最高纪录,而以《××诗抄》的形式 刊出也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这样发表对一位中文系的大学生刺激有多大是不言自明 的,这使我在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年变得异乎寻常的勤奋,好像正是从那时开始我变成了 一个认真的人,一个时刻保持工作状态的人。”[10](P319-320)伊沙还道出了张老师支 持先锋诗的事例:“听说王寅的那首《想起一部捷克电影想不起片名》是兰州的一帮大 学生抄给张老师的,起初张老师并不喜欢,但看到大家喜爱就把它编发了,发表后王寅 还获了奖,那首诗日后还成为‘第三代诗歌’最具代表性的篇目之一……于坚的口语诗 ,最初连他同住的‘尚义街6号’的朋友都认为没什么前途,后来他便遇上了张老师, 不但连获发表还得了奖,后来于坚这路诗一度成为诗坛主流。80年代的大学生基本上都 是在对‘朦胧诗’的模仿状态中写诗的,张老师和他的《大学生诗苑》为他们展示了另 一可能性,为‘第三代’——‘后朦胧诗’的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0](P320)虽 然这段话有些溢美之处,却道出了先锋诗发展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如果没有受到 较为正规的诗歌教育,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的大学生诗人纷纷通过《当代诗歌》、《飞 天》等不歧视文化人和年轻人(中国诗坛长期形成重社会阅历轻文化修养,重名家轻新 人的不良倾向)的刊物走上诗坛,就不可能有新生代诗人打破朦胧诗人先到为君式的垄 断。
尽管80年代中后期是先锋诗重视诗艺的先锋品格的鼎盛时期,先锋诗人主要是从校园 中走出的第三代诗人,由于80年代中后期校园生活的特殊性,特别是时局时时影响着那 个时代的浪漫青年,此期的大学生生活并非完全能够做到“大处茫然”。当时从小受“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教育和“解放全人类”舍己为公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又 被社会大众视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们更是以兼济天下为己任。因此他们更容易走出 “小我”而选择“大我”,更带有强烈的堂·吉诃德式的革命的英雄主义和积极的浪漫 主义思想。更早一点的80年代初的校园诗人虽然不像70年代后期在社会生活中成长起来 的朦胧诗诗人那样“思大于诗”,争当生活的、大众的“代言人”,但也绝不愿意遁入 象牙塔当纯诗诗人。80年代中期成名的先锋诗人程光炜回忆说:“80年代初,77、78级 的大学生都有过一段既贫困又奢侈的思想生活……这代人思想的强烈渴求,恐怕超过了 建国后的任何一代人。”[11](P236)
在80年代中后期席卷全国的“先锋诗潮”虽然比朦胧诗更注重以诗的语言为中心的“ 怎么写”,甚至提出了“诗到语言为止”的口号。他们也是以诗家语的改革者登场的, 却越来越偏重诗的启蒙职能,当思想的先锋。但更强调当代中国人的个体意识是一种抽 象的个体而不是传统的一种集体类型,重视诗的思想启蒙,当时最流行术语是“生命意 识”和“使命意识”。以第三代诗人最积极的理论家,自身也是先锋诗人的陈超为例, 尽管他算得上是博识的学者,深知语言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性,他却强调:“诗歌作为 一种独立自足的存在,源始于诗人生命深层的冲动……隐去诗人的面目,让生命的活力 让给诗歌本身吧。”[12](P139)他不但把宣传这种诗观的一篇随笔命名为《诗即思》, 还把此文作为唯一一文放入《中国当代先锋诗人随笔选》中。80年代中期先锋诗人的代 表作——李亚伟的《中文系》也是思想的先锋大于诗艺的先锋的典型,欧阳江河、周伦 佑、廖亦武、翟永明(80年代的诗作)等先锋诗人充满了关注个体生命和现实社会的思想 ,他们甚至成了女权运动、民主政治改革的精神先锋。诗即思,思大于诗,诗应该有高 度的严肃性,先锋诗人更应该是先锋思想家,这样的先锋诗观在80年代中后期渐渐流行 。即使是求学和求职都在外语学院,受外来诗歌,特别是意象派诗歌影响,在后朦胧诗 诗人中少有的高度重视诗艺技巧的诗人柏桦,也没有放弃抒情传统,成为纯粹的诗艺先 锋。1987年他在第一本诗集《表达》中说:“23岁时,读了波德莱尔的《露台》后开始 认真写诗。受梁宗岱教授的影响至深,恪守‘技巧是对一个人真诚的考验’这一名言并 坚持‘一首好诗应该有百分之三十的独创性,百分之七十的传统’这一信条,为提高诗 艺不懈地努力着。”[13](P307)1993年,他在自传体长篇随笔《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 情诗人》里的《去见梁宗岱》一文中总结说:“1981年5月一个凉快的夜晚,我揣着我 早期的一首象征派习作《夜》以及对波德莱尔的一鳞半爪去见一位老人——诗人梁宗岱 ”,“我读小学时就在鲜宅沐浴了旧时代的朝霞,读初中时又在山洞、林园聆听到旧时 代的残余正在一天天消失的挽歌。这一幕幕旧时的图书像一个迷朦的古都或一个‘同此 凉热’的老人正在慢慢地破碎。从那时起,我就有了一种难以描绘的模糊感觉——新旧 时代的血液将毕生在我的内心循环。这也是为什么我的诗歌在走向最先锋的时刻仍保持 着对歌唱的抒情传统,并形成我后来带有总结性诗观,‘一首好诗应该只有百分之三十 的独创性,百分之七十的传统。’(其实这是一句反语)”[12](P307)
结语
正如林以亮在70年代所言:“老实说,五四以来,中国新诗走的可以说是一条没有前 途的狭路,……中国旧诗在形式上限制虽然很严,可是对题材的选择却很宽:赠答、应 制、唱和、咏物、送别,甚至讽刺和议论都可以入诗,如果从19世纪的浪漫派的眼光看 来,这种诗当然是无聊、内容空洞和言之无物,应该在打倒之列。可是现代诗早已扬弃 了19世纪诗的传统而走上了一条康庄大道。”[14]80年代是中国史无前例的大改革时期 ,尽管出于对过去长期诗歌政治化的强烈反拨,出现了朦胧诗后持续多年的回避政治, 抒写个人小我情感等在诗的题材上的“轻化”现象。但很多先锋诗人还是不由自主地选 择了当思想的、精神的“诗意的先锋”,有意识地压抑自己的艺术天性,少当或者不愿 意当语言的、文体的“诗艺的先锋”。因此,即使是于坚的“口语诗”及“生活流”诗 歌,不仅没有在语言和文体上有多大的建树,如果说有只是把意象化的“诗家语”变成 了直白式的“口语”,改变了“诗出侧面”的古典汉诗传统,把20世纪初的“白话诗” 运动在20世纪末重新“演变”了一次。第三代诗人追求平民化生存方式的思想改革和解
构已有生活和艺术秩序的“革命精神”远远大于他们的艺术独创精神。为了当精神上的 先锋,他们甚至以牺牲诗歌艺术为代价:19世纪末“诗界革命”的先锋黄遵宪的“我手 写吾口”和20世纪初“白话诗运动”的先锋胡适的“作诗如作文”两个口号的负面结果 是造成了汉语诗歌在诗艺及文体建设上的停滞不前甚至倒退,80年代中后期流行诗坛的 口语化自白诗给人的感觉是人人都能写,人人都能独创,加剧尚未完善的新诗文体的混 乱,造成了新诗本应该有的艺术标准和审美尺度的沦丧。当思想的先锋而少当诗艺的先 锋的另一大害处是:很多诗人在“思想先锋”的诱惑下,让青年诗人好走极端的天性极 度膨胀,不是靠语言能力和诗歌功力写诗,而是过分迷恋思想观念的独创性和激情的力 量,进行“弑父”般写作。不仅严重影响了先锋诗人自己在诗艺上的精益求精,也被读 者和研究者视为先锋诗人非艺术功利的独有的“炒作”行为,被仍以谦逊为国人的美德 ,崇尚“温柔敦厚”的做人风格的大众不齿。因此,“先锋”在80年代经历了由早期的 褒义、中期的中性到后期的贬义的变化,特别是在后期“先锋”常常成为“浮躁”的同 义词。这种“自绝于人民”和“自绝于诗歌传统”的反艺术进化原则的“思想先锋”诗 对新诗文体的成熟和诗艺的进展的害处是显而易见的。正如郑敏所言:“对文学艺术采 取后一代淘汰前一代的错误价值观,以致争当‘先锋’,往往宣称自己是超过前一代的 最新诗歌大师,并有文学每五年换一代的荒谬理论,造成青年创作队伍浮躁与追逐新潮 的风气,未能潜心钻研,坚持‘根深树大’的文学艺术信念,只求以最短的时间争取最 大的名声与商业利益。长此以往只能是遍野闲花小草,而无松柏。”[15](P103-104)
收稿日期:2001-11-05
标签:诗歌论文; 朦胧诗论文; 先锋艺术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致橡树论文; 中国当代文学论文; 现代诗论文; 张老师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