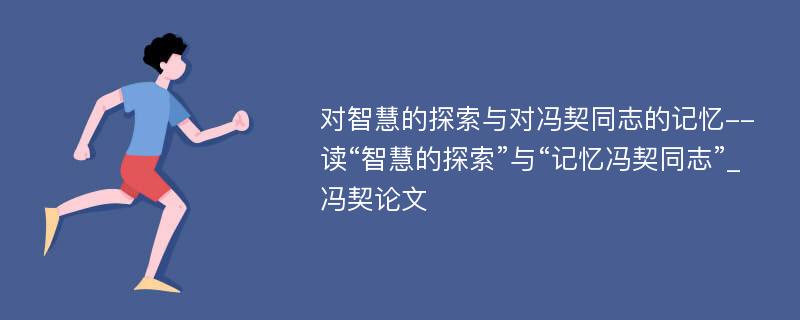
神思慧境两嵚崎——读《智慧的探索》,缅怀冯契同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神思论文,同志论文,智慧论文,慧境两嵚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冯契同志未尽天年而遽然长逝,离开我们已经一个多月了。三月初,在北海突闻冯契同志遽逝的噩耗,野祭怆怀,曾给华东师大传去一唁电:
“惊闻冯契同志翛然弃世,震悼不已!
冯契同志一生追求真理,耿介不阿,立德立言,有为有守。佩纫秋兰,襟怀霁月,传道育人,教泽广远。他长期瘁力于学术耕耘,辨章新旧,融贯中西;而智慧探索,更独辟蹊径,妙启玄门。晚年会心之作《智慧》三书,自成体系,巍然卓立,实神州慧命之绵延,当代学林之楷模。惜书尚未刊,而哲人其萎,玄圃星沉,曷胜悲惋!谨此致唁,并祈代致候冯师母及家属,伏望节哀保重是祷!”旋返汉皋,再次捧读不久前为庆祝冯契同志八十诞辰而新出的论文集《智慧的探索》一书,许多文章,以往曾断续读过,一些思路,曾当面听他娓娓谈过。捧读中,边体会边回忆,浮想联翩,冯契同志的音容笑貌,宛在目前,可是,一些读后的感发和疑点,已无法再向他问难请教了。
一
去年三月,我因赴东南大学一会过沪,住华东师大,特去看望冯契同志和师母,一见面,他就高兴地送我新发表在《学术月刊》上一篇关于“超名言之域”问题的文章,并郑重表示,这是专为纪念金岳霖先生百年诞辰而写的,其中凭记忆演述了金先生40年代在昆明的一次讲演和一篇题为“名言世界与非名言世界”的重要论文。由于金先生论文已佚,故只能靠记忆和参照金先生已发表的其他著作写成此文,简要论述了金先生关于哲学领域“说不得的东西如何能说”的深刻思想和他对金先生思想的发挥;他又说,这是他接着金先生思路,几十年来一直在探索着的哲学理论问题,并因而简述了他正整理定稿的三部书稿(即《智慧说三篇》)的书名和大体结构。当晚,我认真读了这篇理邃情真的文章,深受启发,并使我略窥冯契同志多次谈到的他关于知识向智慧发展的认识辩证法以及重新诠释“转识成智”的用心和理论上建构的系统性,因而感到一种“闻风坐相悦”的衷心高兴。次日,冯契同志来招待所,我向他表示了心中激起的这种“法喜”,他也莞尔一笑;接着苏渊雷老先生、王元化、邓伟志同志和师大哲学系几位师友同来招待所一聚。当日饮谈甚欢。我在纪行诗中遂有“三年华盖终无悔,此日清歌有解人。海上欢呼蜃雾散,东南淑气正氤氲”之句。但却未想到,此次沪上行,竟是与冯契同志最后的一次握晤。
去年冬,冯契同志八十诞辰,闻华东师大及沪上师友相知将集会庆祝,我曾寄去颂诗一首,略表微忱:
“劫后沉吟一笑通,
探珠蓄艾此心同。
圆圈逻辑灵台史,
霁月襟怀长者风。
慧境含弘真、善、美,
神思融贯印、西、中。
芳林争羡楩柟秀,
愿鼓幽兰祝寿翁。”
并附一《后记》:
“60年代与冯契同志初识于北京;旋经浩劫,华盖略同。80年代,幸得重逢,多次握晤于学术讨论会中,探珠有志,蓄艾多情,目击道存,率多心契。每向他请教学术疑难问题,都得到言简意赅的深刻启示;他每有论著,辄先惠寄,俾得早读。教泽学风,濡染良深。至于他的会心新作,融会中、西、印思想之菁华,证成真、善、美统一之理想,胜义时闻,仰慕久矣。近年几次被召赴沪参加研究生论文答辩,亲见冯门学脉,英才辈出,桃李芬芳,楩柟挺秀,令人感奋。欣值冯契同志八十华诞,汉皋飞觥,衷心遥祝。《幽兰操》,古琴曲,颂君子之德也。甲戌初冬,祝于汉皋。”
颂诗及后记中,试图对冯契同志的为人治学风范表示个人敬慕之情,力求对他的丰美学术成就作出诗意的概括,如“慧境含弘……,神思融贯……”等,虽颇费沉吟,实际辞难达意。因为我还停留在耳食肤受的知性理解,未能达到深入慧境的思辨综合和切身体证。后来,收到华东师大同志寄来《智慧的探索》一书,曾先选读了最后一篇未发表过的《智慧说三篇·导论》,自己似乎被提升到一个新的思想境界,急向周围同志推荐此文;直到最近,在对冯契同志的深切悼念中,重新细读全书,并回溯以往读《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时的许多感受,才似乎憬然有悟,才觉识到他有关哲学史的大量论著,仅是他从事哲学智慧创作的某种准备——知识积累与历史铺垫的准备,而他晚年琢磨出的《智慧》三书,乃是作为思想家个人独创的会心之作,以其哲学视野的深广程度和反映时代脉搏的真切程度,可以历史地说,这样的哲学智慧创作乃是神州慧命的延续。正如冯契同志自述的,他从王国维、金岳霖的心中发现了“可爱与可信”的哲学矛盾,他把这种矛盾诠释为正是近代哲学史上“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实证论与非理性主义的对立,是近代西方科学与人生脱节,理智和情感不相协调的集中表现”,反映在中国,“五四”时期的中西文化论战、科学与玄学论战也正是这两种时代思潮的冲突。他自觉到,沿着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的道路前进,正确发扬中国哲学的民族特色,进而会通中西,从理论上阐明知识和智慧的关系,解决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立以及“可信与可爱”的矛盾等,就能反映时代精神而达到一种新的哲理境界。他努力这样做了,并取得某种成功。可以说,他的《智慧说三篇》,作为神州慧命之绵延,实现了哲理境界上一个大的飞跃。
二
如何正确估计和恰当评价冯契同志的学术成就,还需具体研究他尚未刊印的《智慧》三书,尚需经过历史的过滤,经过纵向和横向的比较,才会得出准确结论。但缅怀冯契同志一生,至少可以体会到,他已取得的学术成就绝非偶然,而有其实践的基础,有其内在的动力。从青年时代投身革命激流而坚持理论探讨的《智慧》一文(1947年发表于《哲学评论》),到近年完成的《智慧》三书,中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征程,而他追求真理的初心不改,勇攀高峰的志向不移,无论什么样的处境(包括十年浩劫中的种种遭遇),他都能不断檠括自己,“磨而不磷,涅而不缁”,“出入于险阻而自靖”,始终保持着心灵的自由思考,始终保持着耿介不阿的独立人格。神思慧境,磊落嵚崎。这中间,起支撑作用的是一种内在的“至诚无息”的精神力量。他自订座右铭:“化理论为方法与化理论为德性”,成为自觉自愿遵循的律令,在这双重实践的磨炼中,真正把为学与做人、敬业与修德、穷理与尽性二者统一起来,真正做到学用一致,言行相掩,心口如一。特别是他身体力行地把哲学理论化为个人德性的实践中,对于真善美统一的自由理想的执着追求,对于独立人格的自我塑造,对于社会异化现象的高度警惕,具有一种非凡的自觉性。这是他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精神遗产。
这种自觉性,表现为具有历史感的理性自觉,如他明确指出的:
“德性的自证首要的是真诚。这也是中国哲学史上儒学和道家所贡献的重要思想。儒家着重讲‘诚’,……道家崇尚自然,着重讲‘真’。儒道两家说法虽不同,但都以为真正的德性出自真诚,而最后要复归于真诚。”“对从事哲学的人来说,从真诚出发,拒斥异化,警惕虚伪,解蔽去私,提高学养,与人为善,在心口如一、言行一致的活动中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坚定的操守,也就是凝道而成德、显性以弘道的过程。……‘德性之智’就是在德性的自证中体认了道(天道、人道、认识过程之道),这种自证,是精神的‘自明、自主、自得’,即主体在返观中自知其明觉的理性,同时有自主的坚定意志,而且还因情感的升华而有自得的情操。这样便有了知、情、意等本质力量的全面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真、善、美的统一,这就是自由的德性。”①
这些话,掷地有声,只有亲身体悟,才能如此鞭辟近里,笃实可行。中国传统哲学讲“希贤希圣”、“知性知天”之类的道德体验或理想人格追求,往往失之空泛迂阔或高不可攀,而他把“理想人格如何培养”等价值论问题,也纳入“广义认识论”的范畴,认定“认识的辩证法贯彻于价值论领域,表现为在使理想成为现实以创造真、善、美的活动中,培养了自由人格的德性”。(第648页)“我们讲的理想人格不是高不可攀的圣人,而是平民化的,是多数人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第652页)他一再强调“平民化的自由人格”具有时代特征,在当代“出于自由意志,积极投身人民的事业”,坚定地为实现“个性解放与大同团结相统一的理想而奋斗”,“就是当前便能达到的自由人格”;引用鲁迅的话来说,这种自由人格,“内心有理想的光”,“既有清新的理智,又有坚毅的意志”,完全清除了“寇盗心”和“奴才气”,既自尊,又尊重别人,始终是大众中的一员。在论证中,他一方面从正面指出个性解放和大同团结相统一的新时代的价值观和平民化的自由人格理想形成和实现的机制;另一方面,联系十年浩劫及社会现实中某些阴影,又从负面揭露,中国文化中还有天命论、独断论与怀疑论、虚无主义等互补而成的腐朽传统,在现实生活还有流毒。他极为深刻地指出:
“由于数千年封建统治中儒学独尊,经学独断论和权威主义根深蒂固。……这些东西似乎已成为死鬼,但由于理论上的盲目性,死鬼又披着革命的外衣出来作祟。十年动乱中,变相的权威主义和经学独断论泛滥全国,造成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而一旦个人迷信冷却下来,那些‘居阴而为阳’的野心家面目被揭穿,独断论和权威主义就走向反面,怀疑论和虚无主义俘虏了人们,造成严重的信仰危机。近十多年作出了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经济上取得较快的发展。但就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来说,盲目性仍然很大。……鲁迅所痛斥的‘做戏的虚无党’仍然很活跃。”(第624-625页)
“要保持真诚就要警惕异化现象。自然经济条件下人对人的依赖不可避免,商品经济条件下人对物的依赖不可避免,在这种依赖关系基础上,因人的无知而产生权力迷信和拜金主义,以致权力、金钱成了异化力量反过来支配了人,人成了奴隶,甚至成了‘奴才’。而且在中国,这种异化力量还特别善于伪装,披上了正人君子的外衣,成了鲁迅所痛斥的‘做戏的虚无党’。要保持真诚,必须警惕这种异化力量,警惕伪君子假道学的欺骗。”(第638页)
具有理论深度的解剖刀,锋芒所向,入木三分。冯契同志平时淡泊自甘,宁静致远,对于朋友、学生更是薰然慈仁的长者,待人接物,和颜悦色,使人如坐春风。但他真诚地把哲理内化为德性,内化为有血有肉的人格,则性格上必然有光风霁月的一面,又有“金刚怒目式”的一面。他在著作中一再引述陶渊明的“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诗句,并一再赞扬“不平则鸣”的“风雷之文”。他的这些对腐朽传统与现实社会阴影的揭露批判,正是“风雷之文”。语重心长,燃犀烛怪,发人深省!
三
冯契同志真诚地实践了做人和做学问的统一,又不断地开展以智慧问题为中心的多层面探索,堪称自觉的“爱智者”、名实相符的哲学家。他明确声称他的学术兴趣主要在哲学理论的本身,而不仅在哲学发展的历史,并清楚地认定:“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两者密不可分。因而,在大学读书时,就已博览群书,广泛涉足于中、西、印三系的哲学史籍,时而随金岳霖先生精读休谟,时而自学《庄子》和斯宾诺莎而着了迷,时而在汤用彤先生指导下阅读龙树《三论》和《大般若经》;……与此同时,在投身革命洪流的实践基础上,消化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经过长期反复琢磨,经过心灵的自由思考,他对实践唯物主义的辩证法的哲学路线和理论取向,作了自觉自愿的肯定选择;并进一步思考着这一哲学理论的中国化形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如何得到丰富、发展,如何进一步“会通古今中西,推陈出新,达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
冯契同志沿着他自己自由选择的学术道路,奋力开拓,在哲学和哲学史的创造性研究方面,已经作出了流誉海内外学林的许多卓越贡献。这许多贡献中,我感到最突出、最具有个性特征的理论贡献,似乎可以例举如下,略见一斑:
首先,冯契同志在其把理论化为方法、由一般回到特殊的中国古代哲学史的研究中,着力于一系列哲学史方法论原则的阐述和运用。诸如,运用哲学发展既有其“普遍根据”与又有其“特殊根据”的两重根据的观点,较全面地阐明了哲学发展的特殊矛盾和客观动力,坚持历史和逻辑一致的方法论原则,通过去粗取精的剖析,较准确地把握了中国古代哲学发展圆圈的逻辑起点和终点;运用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对比中西哲学史,辩同异,别共殊,重新诠释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澄清了关于中国哲学只重伦理学、缺乏认识论的流行观点,从而充分揭示了中国传统哲学中关于辩证逻辑思想及各门自然科学方法论的丰富和关于自由人格理想学说的高明。至于“广义认识论”的提出,把“感觉能否给予客观实在”、“思维能否达到科学真理”、“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具体真理(世界统一原理和宇宙发展法则)”、“人能否获得自由”(或“理想人格如何培养”)等问题,都纳入认识论范畴,把认识全过程看作是从不知到知、从知识到智慧的辩证发展。这正是从中西哲学史的比较研究中得出的理论成果,对西方近代实证论思潮的狭隘观点是一个突破,并提供了解除、沟通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之间两极对立的致思途径,这就具有了更重大的时代意义。
其次,冯契同志十分重视中国近现代的哲学运动,注意总结其革命进程和积极成果,同时揭露其局限性和严重的理论思维教训。其目的,都在于确切地认识和把握中国近代哲学是如何从古代传统中蜕变而来,中国现代哲学如何在进一步会通中外古今中找到自己的生长点而得以继续发展。他一再强调“通古今之变”,而把历史、文化、哲学都看作是“不断推陈出新,不断变通而持续发展的运动。”(第550页)他对厚今薄古,别有会心,认为:
“古代文化中那些在当代仍然有生命力的东西,大多是经过近代历史的筛选,并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形了的东西。所以,批判继承民族文化传统的问题,首先应注意的是自1840年以来一百多年间(主要是20世纪)形成的近代传统。”(第557页)他写了《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专著,并深情表示:“我的前半生是在民主革命时期度过的,在那如火如荼的革命岁月中,许多进步思想家用鲜血、用生命写下了哲学的诗篇,曾使我深受感动和鼓舞。在这时期从事哲学的知名学者中,还包括有我曾亲聆教诲的老师。我对这一逝去的历史时代的思想家们是精神相通、血脉相连,有着特别的亲密关系和亲切之感的。”②正因如此,他对近现代哲学传统的清理,用心深细,创见尤多。
对于以西学东渐为杠杆的中国近代哲学,特重逻辑和方法论方面的探索和进展,这是冯契同志的独见。他认为,“只有找到中西哲学在逻辑方法上的交接点,才能促进中国哲学的近代化,才可能进而使中国哲学成为统一的世界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第254页)他把严复引进培根的经验归纳法;章太炎对比《墨经》、印度因明和亚里士多德的三段式,又推崇演绎法;胡适提倡“科学实验的态度”和“历史的态度”,偏向归纳法而忽视数学方法;金岳霖引进罗素的数理逻辑,对科学方法的认识论基础和逻辑根据作了深层次的探讨;都作为重要的环节,而归结到马克思主义者介绍和发挥的辩证逻辑,注意到了分析与综合的结合以及归纳与演绎、历史与逻辑的结合,这是重大成就,并指出对阶级分析方法绝对化和对传统经学方法清算不力,及对近代方法论成果未加以系统总结,则又是重要教训。
同时,他也认真清理了近代中国自由学说和价值观的变革发展,突出从谭嗣同的“冲决网罗”、梁启超的“道德革命”到鲁迅的“国民性”改造等为挣脱封建主义“囚缚”的批判意义,又把李大钊提出的“理想的自由社会”即“科学的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个性解放与大同团结的统一”,和鲁迅提出的“理想的自由人格”即自觉与自愿相统一的“平民化的自由人格”,视为最新成果;但又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比较和会通中西的工作并未成功”,“‘五四’为哲学革命提出的任务——反对天命论、独断论与虚无主义互相补充的腐朽传统,用科学思维取代经学方法,用自由原则取代权威主义——至今尚没有完成。”(第354页)他还饶有兴趣地清理了中国近代美学方面的历史成果,对王国维、梁启超、朱光潜、宗白华、鲁迅的艺术意境理论等,一一作了析论。(第265-280页)
这一切,都旨在找到中国近代哲学在中西汇合、古今通变中形成了什么新成果、新特点,和现代哲学得以进一步发展的新起点、生长点。如他所肯定的:“到了中国近代,哲学家很重视逻辑和方法论的探索,特别是从西方学到的形式逻辑、实验科学方法,需要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找到结合点,才能生根发育,……所谓找到结合点,那就是经过中西比较而达到会通,有了生长点了。”(第526-527页)他在这方面,身体力行,锲而不舍,为西方传入的逻辑学和科学方法论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找寻生根发芽的结合点,做出了很大的成绩。
四
冯契同志以其特殊的因缘走向学术道路。他在抗日战争的风雷中投身时代洪流而自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启蒙;同时,他又曾在清华研究所亲受金岳霖、汤用彤、冯友兰等先生的长期学术熏陶,通过他自己德业日新的奋发努力,终于找到一条弘扬学脉、重道尊师、在学术承转上继往以开来、推故而致新的特殊途径,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形态对哲学遗产的总结、继承和发展,并在其近代传统中找到直接的结合点、生长点,提供了可贵的实践经验。
在《智慧的探索》文集中,有多篇文章深情而生动地叙述了他与金岳霖、汤用彤先生等的亲密关系,尤其是他与金先生的学术交往和心灵感通,数十年如一日,师生的友情那么纯、那么真,讨论的哲学问题那么细、那么深,读后特别感人。冯契同志以半个多世纪的实践所完成的学术任务,给我们留下的是可资广泛借鉴的典型经验。
就这些实践经验的典型性而言,至少以下数端,具有普遍的启迪意义:
必须具有充分的同情和理解,这是尊师、重道、求学的前提。冯契同志说:“我早就认为金先生是热爱祖国、热爱真理的学者,在感情上和他比较接近”。金先生为他这一个学生单独开课,严格要求;他也对金先生衷心敬佩,无话不谈。这样,才可能真从学术思想上进入师门。
必须“能入、能出”。冯契同志回忆在汤用彤先生指导下读《大般若经》和《肇论》时,如何经汤先生指点而体会到学习哲学家名著,不能浅尝辄止,必须“能入、能出”。“能入”难,“能出”更难。后来,他读金先生的巨著《知识论》的手稿时,逐章做笔记,决心钻进去;又经与金先生不断讨论,而能够向金先生深入提问,终于触摸到了金先生内心深处的哲学矛盾,并敢于对《论道·绪论》把“知识论的态度”与“元学(形而上学)的态度”区分为二提出质疑,得到金先生的鼓励“循着自己的思路去探索”。因而,40年代在昆明,能够听懂金先生关于“名言世界与非名言世界”或“说不得的东西如何能说”的讲演,给予高度评价,但又跳出来,试图突破金先生认识理论的某些局限,开始了来自金先生而又超越金先生的关于智慧问题的深入探索。
必须从前辈哲学体系中找到哲学进一步发展的生长点,即把前代哲人“先我而得者已竭其思”所达到的终点或极限,当作自己哲学致思的起点或突破口。冯契同志经过博学、慎思,作出明断:
“金先生无疑是中国近代最有成就的专业哲学家之一,他会通中西,建立了自己独特的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在认识论、本体论、逻辑哲学等领域都作出了创造性贡献。诚如金先生所说:‘哲学既不会终止,也不会至当不移。哲学总是继续地尝试,继续地探讨’。但后继者只有通过对先行者的认真研究,才可能作出真正的新的尝试。金岳霖哲学不自封为‘至当不移’,它期待着后继者将通过它来超过它,所以是富有生命力的。金先生在哲学上作出的贡献和对若干重大问题的探讨(如本文所说的超名言之域问题),将如薪传火,随着后继者将不断增多而产生深远的影响”。(第583-584页)
这些论断如此精审,表明他确实在金岳霖哲学体系中找到了自己哲学致思的突破口和生长点。只有通过对先行者的认真研究,才可能作出真正的新的探索,才可能“通过它来超过它”,“如薪传火”,这是承先启后的发展规律。冯契同志50年AI写作《怎样认识世界》一书时,已明确运用一些金先生的认识论观点而加以引伸;1957年赴京专访金先生,就如何研究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问题作了长夜之谈,他事后回忆:“正是那次讨论,使我明确了一点,为要把认识论的研讨引向深入,我应该从老师自己肯定为‘讲对了’的地方出发,沿着辩证唯物主义的路子前进。所以我后来对金先生的某些论点又作了进一步的引伸和发挥。这些发挥当然不一定是金先生自己的主张,但我以为,如果我的发挥中有某些合理成份,那便可以说明金先生著作是富于生命力的。”(第233页)具体地说,金先生“用概念具有摹写和规范双重作用来说明知识经验就是以得自所与(经过抽象)来还治所与,便克服了休谟、康德的缺点,比较辩证地解决了感觉和概念的关系问题,这在认识论上是个重要贡献”,但这也就是金先生哲学的终点和极限,所以他“只承认抽象概念,不承认具体概念,不承认科学可以而且应该把握具体真理,而认为具体(全体与个体)非名言所能表达,非抽象概念所能把握。他看不到科学的抽象是一个不断深化、不断扩展而趋于具体的辩证运动”。(第224-225页)这也就是金先生哲学视野的局限或其内蕴的不能自解的科玄矛盾。冯契同志正是从这里出发,把金先生的静态分析引伸到动态考察,把金先生的抽象概念引伸到具体概念(即“由抽象再上升为具体”的“理性具体”),并全面总结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高扬从《易传》、荀子直到王夫之的辩证逻辑和从庄子、中国化的佛学直到宋明儒学的理性直觉、转识成智与德性自证等,依据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为圭臬,来阐明从无知到知、从知识到智慧的辩证发展的全过程,从而构建为自成体系的《智慧说三篇》。
冯契同志一生笃实光辉的学术实践,提供了这些具体经验,不是很值得我们咀嚼么?
五
在完成了《智慧》三书之后,近年来冯契同志一再语重心长地提醒人们:“在本世纪中,中国进步确实很大,自作孽的事也干了不少。社会经历了巨大动荡,一次又一次的狂热浪潮席卷全国,使得人们难以定下心来对历史进程作反思和自我批判。”由于缺乏自我批判和系统反思,理论上的盲目性曾在实践上造成民族的巨大劫难。为了克服理论上的盲目性,必须进行自我批判和反思,这种反思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客观的历史过程的反思,即对20世纪中国社会的演变,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作批判的总结;二是对反映现实生活的社会意识、理论认识等各个领域包括20世纪中国哲学的演变作批判的总结。”他预期,“到世纪之交,中国可能进入一个自我批判阶段”。而“中国哲学能达到自我批判阶段,进行系统的反思,克服种种盲目性,那就可能在总体上经过‘批判、会通、创新’的环节而取得崭新的面貌,成为当代世界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第561页)
同时,他又高瞻远瞩,一再强调:“从世界范围看,我们正处于东西文化互相影响、趋于合流的时代。为此需要全面系统地了解西方文化和哲学,也需全面系统地了解东方文化和哲学,并深入地作比较研究,以求融会贯通。这种研究和会通当然会见仁见智,产生不同学说,形成不同学派。所以,应该说,我们正面临着世界性的百家争鸣。海内外中国哲学各学派,都将在国际范围的百家争鸣中接受考验。为了参与争鸣和自由讨论,那就需要有民主作风和宽容精神。”(第562页)“要以平等的自由讨论的态度,而不能以定于一尊的态度来对待各家,……通过争鸣、自由讨论,必然会促进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自信。”③
冯契同志这些呼唤和期待,反映了不少人的心声。我相信,他的预期,在即将到来的世纪之交,定能变为现实。
1995.4.10.稿于东湖
注释:
①《智慧的探索》,华东师大出版社1994年版,第638-639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
②《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第59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③《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第59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