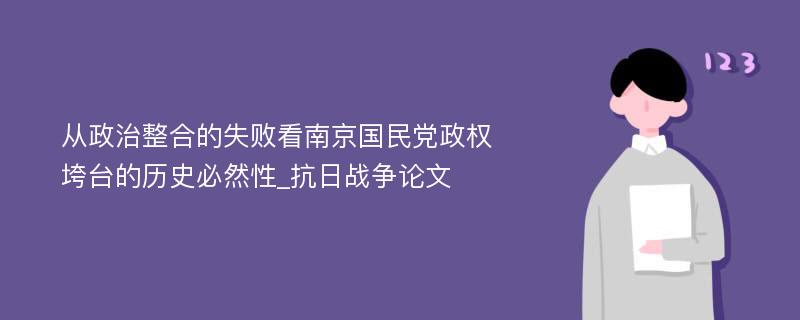
从政治整合的失败看南京国民党政权崩溃的历史必然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必然性论文,南京论文,国民党论文,政权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2003)01-0043-06
按照现代化理论和政治学原理,一个观代化政权必须实现政治整合过程,即由单一的、世俗化的、全国性的政治权威,取代各种传统的、宗教的、家族的或地域性的政权,实现中央政权的集中统一、把权力集中于公认的公共机构手中的政治整合过程,形成一个统一集中而有效运行的中央权威,政权才具有其合理性或称之为理性化[1](P35)。按此标准考察南京国民党政权,可以发现,这是一个始终没能实现真正统一的形统实分的政权体系。
南京政权从建立那天起,就一直伴随着内部各种势力和派系的纷攘争夺,其中既包括各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国民党中央政权的矛盾和斗争,也包括国民党内各种政治派别的争夺,同时又包括基层政权与中央政权的抵制和抗衡。这些派系横向间的矛盾虽时有发生,但往往是局部的或短期的,而他们与国民党中央政权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却是长期的、普遍的,贯穿了南京政权的始终,南京政权直到崩溃,也没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统一。本文试从三个层面分析南京国民党政权政治整合的失败从而导致其崩溃的历史必然性。
—、地方实力派与中央政权的抗衡——中央权威资源的流失
经过北伐战争,到1927年南京政权建立时,大部分旧军阀势力被消灭或削弱,但打着国民党旗号的新军阀却在北伐过程中乘机崛起,国内出现了各派国民党新军阀林立的格局,如冯玉祥在陕西、河南一带,阎锡山盘踞山西,北方的张作霖仍控制着东北、京津和山东等地,孙传芳的残余占据着苏北,经过纵横捭阖的政治、军事争斗,到1928年,南京政府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
蒋介石统一中国后,国民党政权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获得了国际承认,并在统一币制、取消厘金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仍无法实质性地消灭地方割据势力,如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被分别任命为广州、武汉、开封、太原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四个分会的主席,就是对国民党各派军阀割据现状的实际上的承认,各地军阀拥兵自重,甚至觊觎中央政府。
二期北伐后,围绕地盘分配和军事编遣问题,蒋、冯、阎、李四派间的矛盾尖锐起来。从1929年开始,蒋介石发动了对地方军阀的军事征剿。军事编遣会议后,蒋桂、蒋冯、蒋唐战争相继爆发,均以蒋胜利告终;1930年,蒋又借国民政府名义征剿阎冯联军,双方投入大量兵力开始了中原大战,冯、阎败北,此后,阎、冯失去了问鼎中原的实力;至此,蒋介石在东征西讨、南征北战中削弱了国民党各派军阀,在军事上显然处于优势地位。但这种对异己力量的打击只能说是削弱,而不是消灭,各地军阀仍在重新积聚力量,寻找时机,对抗国民党中央政权的统治。
与武装斗争相联系的是地盘,实力派有没有巩固的地盘,往往决定其与蒋介石把持的中央能否持久对抗。凡是具有较巩固地盘者,即使战败,也有可能凭借地盘东山再起。如龙云多年经营云南,地盘巩固,后龙云本人虽被蒋介石软禁于南京,而龙云手下的卢汉等人还能凭借地盘与蒋周旋。反之,凡失去地盘的地方实力派却难以持久,如中原大战中,冯玉祥将西北军“倾巢”调入前线,未能巩固后方地盘,兵败之后,无立足之地,失去了与蒋武装对抗的依托。可见,派系斗争的胜负决定于武装力量,而没有地盘作依托的武装力量是不能长久生存的。与蒋介石武力较量失利后的各地军阀,与蒋的争斗从此由公开的分庭抗礼转为以地盘为依托的较为隐蔽的权术斗争,如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势力挟西南以抗中央与蒋的国民政府斗争长达20多年,不仅在军事上对蒋处处掣肘,促成了蒋军的最终失败,而且在政治上处处给蒋施加压力。解放战争后期,借美国政府对蒋失望与不满之机,推出李宗仁,对蒋“逼宫”,再次迫蒋下野,这对蒋家王朝的最后覆亡无疑起了推动作用;阎锡山表面上皈依中央,却在山西经营“独立王国”,龙云在云南,刘湘、刘文辉在川康,马步芳在青海,盛世才在新疆,陈济棠在广东……他们各自占地为王,以国民党委任统治之名,行营私之实,相对独立于中央之外,可以自行发行货币,自立税目,私设关卡,人为地搞地区经济、文化壁垒,形同大大小小的“土皇帝”。“他们名为国民党员,却抵制国民党中央派到其统辖区内的代表和设立的机构,国民党地方组织机构,往往为地方实力派所控制,成为他们的统治工具,地方实力派的实权凌驾于地方党和政府之上,在地方实力派统辖区内的军民,只服从当地的‘土皇帝’,无视中央的政令、军令、法令。”[2](P7)直到1937年,国民政府也只能对大约25%的全国土地上的66%的人口建立有效的统治,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西迁四川,其控御机能更加危机了:
在它所偏安的地盘里,只有全国4%的发电量和6%的工厂。对农业社会更谈不上控制,战前10年中,政府收入的83.1%来自关税、盐税和统税,就地方来说又有46%来自江、浙、皖三省,抗战时这些收入中的绝大部分都丧失了。抗战中期,它的年收入只及战前的37%,但费用却上升33%,军队集中在大后方,四川一地供应了所有军粮的1/4至1/2[3](P57)。这就不能不严重影响了南京政府军令政令的统一和有效行使,给敌对政权的发展壮大造成可乘之机,这一点在抗战爆发前的剿共战争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抗日战争爆发后,全民抗战,全国各派政治力量都在民族矛盾当前的情势下重新集合在南京政权周围,一切敌对集团都捐弃前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形成了一个真正的统一战线,应该说,民族战争给国民党政权实现政治整合创造了一个绝好的机遇。但蒋介石却采取了一套令国人大失所望的做法——在党外,顽固坚持“一个党、一个领袖”的立场,企图借抗战之机“收编”共军,消灭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在国民党内,则一面部署抗战,一面处心积虑地欲借抗战之机削弱所谓“杂牌”军即地方实力派的力量,如在对待桂系的态度上表现得非常明显:白崇禧被授予副参谋长和军训部长的较高职务调离广西,李宗仁被任命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派往北方抗日的最前线,这样,作为桂系核心的两个领导人物离开了其政治基地,而且被分割开来;在抗日最前沿的桂系军队又得不到象“嫡系”部队一样的给养和装备,致使军队士气低落,军心涣散,连吃败仗后损失惨重;1945年2月,败军之将李宗仁被免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职,“晋升”为委员长汉中行辕主任,一个形式上辖几个战区而实际上不直接指挥任何部队的有职无权的虚衔;与此同时,取消了广西农民自卫军,切断了桂系补充兵力的重要渠道,企图控制桂系的政治基地。
表面上看,蒋介石巧妙地利用“分而治之”的手法瓦解了一个强大的地方集团,进一步推进了“团结”。然而,“这种政策的代价是巨大的,全国不可能在这种基础上真心实意地团结起来……这对抗战造成的后果是,它使地方集团确信,只有傻瓜才会在对日作战中去牺牲他们的部队和放弃他们的政治基地”[4](P287)。这种做法更激起了人民和士兵的愤慨和反抗,李济深继续组织反蒋运动,最终走上了与蒋公开决裂的道路,而桂系也最终成为蒋介石政权崩溃的助力器。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随着人民革命力量的不断壮大,许多长期受蒋压制的地方实力派及其军队,开始纷纷脱离国民党统治营垒,投向人民,从而大大削弱了国民党的统治力量,扩大了新民主主义统一战线,加速了蒋家王朝的覆亡和新中国的建立。在蒋介石的军队中,许多是在北伐和以后的“统一”过程中未经战斗就来归顺,或稍经接触就告投降的军阀部队,蒋介石只是把他们简单地收编过来,编成自己的部队,但他的实际控制力却要打一个极大的折扣。在与解放军的交战过程中,这些被视为“杂牌”的军队纷纷倒戈,到1946年10月,起义军队已达国民党总兵力的2%,三大战役后,起义人数更是成倍增加。与蒋矛盾斗争由来已久的桂系,在淮海战役中“一再对蒋介石集团的军事部署进行掣肘,在作战关键时刻,桂系再度发难,拖延黄维兵团的调动,从而贻误战机,且隔岸观火,故意造成蒋军失利,以便同蒋争夺天下。结果我军集中兵力对黄伯韬、黄维兵团及杜聿明直接率领的李、邱、孙三兵团分割包围,各个击破,从而获得以60万兵力挫败蒋军80万人,歼灭55.5万多人的巨大战果”[4](P287)。此役可谓新中国建立的奠基礼,蒋家王朝的覆灭已成定局。
由此可见,国民政府东征西讨的军事征战并没能达到收集中央权威的目的,而各地方实力派的存在则使蒋政权没能有效行使中央权威,中共领导的革命力量才得以发展壮大,最终成长为蒋介石政权的掘墓人。
二、国民党内部各派系纷争——政府内部权威资源的丧失
派系政治是国民党政权体系的一个显著特点,这首先有其历史的渊源。
在国民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历来组织涣散,纪律松懈,成分复杂,军阀、官僚、政客充塞其中。1924年改组后的国民党吸收了新的成分,以三民主义为党的思想基础,国民党获得了新生。但即便如此,国民党的组织纲领和纪律约束仍谈不上严密统一,加之1926年北阀开始后国民党半年之内席卷半个中国,使得本来成分已经鱼龙混杂的国民党,经过北阀期间蒋介石的“廉价取胜”,就更为泥沙俱下了。许多地方势力和军事势力未经改造便被整合进国民党,在国民党内形成错综复杂的派系关系:军事上有蒋、冯、阎、桂四系,政治上则有蒋、胡、汪三巨头。经过几年惊心动魄的军事、政治较量,最终确立了以蒋介石为中心的军事政治格局,但派系斗争并没因此而结束,而是以新的或更隐蔽的方式继续与蒋记政权抗争,而蒋系内部又衍生出的新派系则是国民党政治机体上的又一致命的恶瘤,这些新生的派别有政学系、CC派、黄埔系、改组派、再造派、三青团等,而在蒋介石的嫡系和亲信中又有派别斗争,可谓派中有派。各派之间互相攻击,实力此消彼长,彼此欲置政敌死地而后快,甚至闹出命案,其中,政学系、黄埔系、CC派以及三青团之间的争夺尤为典型。随着抗战的结束,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就愈演愈烈,这在国民党六大上已初露端倪,到六届二中全会时矛盾冲突便完全公开化了。
在国民党六大的中委选举问题上,政学系和黄埔系联手反对CC派的操纵把持。六大开会之初初步决定中央执监委员名额共为250人,候选人经各方协调后瓜分完毕,但陈果夫认为还有CC中委20人没列入名单,于是陈签呈蒋追加,蒋批可。张群等政学系政要不甘示弱,也急起直追向蒋要了一些名额补充政学系骨干,陈果夫闻讯又追加了一批,这样,六届中委候选人名单在数日间就超出300人以上,而且涨势未已,最后经蒋的“裁决”,中委名额增至480人,以双方大体平分而告终。
六届二中全会上,黄埔系、CC系联手与政学系之争更趋尖锐化。
政学系在组织上虽不成为一个严密的体系,但它在蒋介石的身边能量很大,他们中的不少人是知识精英或技术专家出身,且长期从事党派联系工作或实际行政工作,以温和和识势见长。在抗战胜利后的国共战和问题上,他们希望国民党能够改变党治体制,与各党派合作,重建一个开明的政治共同体。在促成重庆谈判、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及与各党派协商签订政协决议等问题上起了积极的作用。到1947年4月国民政府改组时,政学系的权力达到了顶峰,这引起了黄埔系、CC系的不安和不满。六届二中全会上,黄埔、CC一起发难,指责政学系出卖党国、政治“走私”,并发起政治“革新运动”。革新运动虽然无疾而终,但CC派与政学系的裂痕从此开始,矛盾冲突的结果最终形成巨大的政治破坏力——蒋介石表现出政治动摇,从政协会议全面倒退,由此构成国共两军四平决战的政治背景。
黄埔系、三青团与CC系的矛盾在1946年9月的三青团二大上达到白热化。
蒋介石最初组建三青团的目的,是在对国民党失望的同时,为了建立一个新的“革命组织”,取代国民党政治领导力量的地位,吸纳国民党内不同的派系,割除派系这一政治恶瘤。从蒋经国在重庆任三青团组织训练处长起,三青团为蒋太子所控制,而蒋经国系认为国民党太腐败,已不能担负起领导重任,企图别树一帜,以团代党,将原国民党变为在野党,这立即遭到了国民党内其他派系的围攻。围绕党团关系问题,把持国民党党务的CC系与三青团展开了激烈的较量,到三青团成立一年后的1939年,蒋不得不改变对三青团的期望;1946年三青团二大上,黄埔系及蒋经国系设想将三青团组建成一个新党与国民党轮流执政,新党交由蒋经国全权领导,由蒋介石一人兼国民党和新党两党领袖,以削弱CC系的力量,重振三民主义事业,这项改革措施最初深合蒋意,但遭到CC系的强烈反对,蒋介石只得改变原意,改为党团分离,以避免CC系与蒋太子系和黄埔系的火拼。党团分离后问题并没有因此解决,党团间争夺势力范围的冲突有增无减,1947年9月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党团合并的决议案,三青团并入国民党,蒋太子系和黄埔系的势力渗入了原由CC系一手包办的国民党上层,从此党团纠纷演化为党内纷争,黄埔系和蒋经国系的改革志向也被政治上的欲求所淹没。这样,党团合并不仅未能拯救国民党,反而使三青团仅存的一点“革命朝气”化为乌有。
总之,派系斗争的纷争攘夺,淹没了国民党内的一切变革努力和举措,使得国民党丧失了一切励精图治、融入现代化变革洪流的机遇,这种纷繁复杂的派系斗争在国民党肌体中普遍存在,而且贯穿了南京国民党政权的始终,最终成为导致国民党政权失败的致命伤。很难想象,一个派系林立、互相掣肘的离散政府能成功地整合各种社会力量,一道迎接由传统向现代国家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挑战。
三、对基层政权的控制乏力——收集民间权威资源的失败
为了把散落在民间的权威资源收归中央,国民党政府采取了包括保甲运动、新县制建设、土地改革等革新举措,但均无疾而终。
其中新县制建设开始后,由于地方与中央政权不可调和的矛盾,始终效果甚微。如国民政府规定在1943年内完成新县制建设,但到了1943年,实行县制的16省1106县中,召开县政会议的有358县,占总数的32%,召开县临时参议会的有321县,占29%,召开乡镇代表大会的有203县,占18%,召开保民大会的507县,占45%。基层组织建到底层尚不足半数,新县制推行的效果可见一斑。
至于土地改革运动,尽管国民政府制定各项土地法规,准备进行土地改革,其中较重要的如1930年6月公布的《土地法》等,应该说,这些法令法规基本体现了孙中山“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思想,试图借以打破封建地主对农村的把持,强化农村社会对中央权威的认可,并在局部地区试行了土地改革。但由于国民党土地改革政策本身就充斥着矛盾和被动,国民政府上层官僚地主阶层的抗拒,最重要的是把持乡村政权的土豪劣绅的激烈抵制和反对等政治因素,国民政府拿不出大量资金进行土地赎买等经济原因,土地改革失败。抗战爆发后,该运动被迫停下来,而紧随其后的大后方“扶植自耕农运动”也不了了之。农村的旧式结构依存,恶绅把持的底层政权仍未被中央所渗透[5](P78)。
旨在收集民间权威的三项改革运动的无疾而终,使得这些乡村的土豪劣绅,在地方财政、税收、土地等一系列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同国民党中央政权展开了剧烈的抗争。土豪劣绅在乡村社会中的无法无天,迫使南京政权在乡村建设中只能从事一些纯粹的农业技术改良工作,但合作社、农业银行发放贷款等事项还要经由这些土豪劣绅,又给他们提供了大发横财的机会,基层政权完全被地方豪强所控制,割断了南京政权同农民的联系,其结果是:政治上,国民党政权与土豪劣绅、地主的联合,本身就意味着对农民的背离,依靠前者作为自己的统治基础,其统治的对象自然也就是广大农民,结果是前者不能同自己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却又完全丧失了后者的支持;经济上,支撑政权生存的大部分财政来源流失,因此,虽然“农业在30年代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60-70%,”但由于土豪劣绅、地方官吏从中作梗,“从土地上所得的总收入还不到1936年国家和地方总收入的10%”[6](P76)。30年代中期,江苏“素不纳粮之荒熟地竟达9000余万亩”,浙江省“无税之土地,占75%”[7],在国民党中央政权控制严密的江、浙两省尚且如此,其他地区的情况便可想而知了。抗战时期的大后方,有1/3以上的土地是政府无法收取地租的。
总之,南京国民党政权建立后,以军事征战收集地方权威,以领袖个人独裁收集政府内部权威,以推行保甲制度、土地改革运动和新县制运动等形式收集民间权威的努力,均因政府的逆动行为而收效甚微或完全失败,直到灭亡,南京政权一直处于这样一个怪圈:一方面,政府对外部权威资源吸收不足,而内部却领袖集权,权威紧缩,由此导致政府貌似强大而实则弱小;另一方面,政府内部的权威紧缩必然诱发其权威扩张动机,进而招致多方抵抗,当政府无力消解这些抗争时,社会将失稳定,在无序的社会秩序中,政府权威必再次流失,合理性受到削弱,最终又必然导致政府内部的权威紧缩。恶性循环的最终结果是政府权威的极度虚弱,其崩溃也就成为必然。
收稿日期:2002-10-11
标签:抗日战争论文; 国民政府论文; 历史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蒋介石论文; 南京国民政府论文; 国民党论文; 黄埔论文; 世界大战论文; 太平洋战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