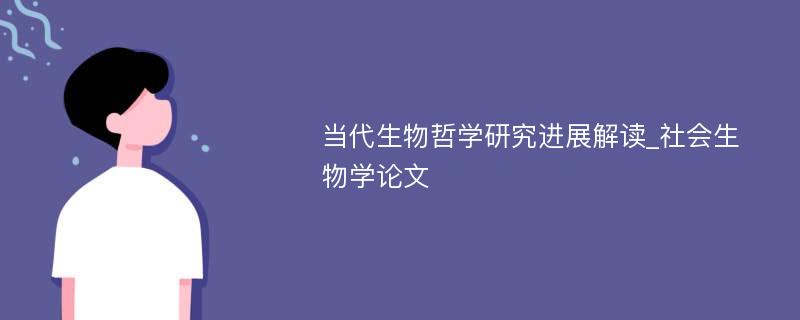
当代生物学哲学研究进展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研究进展论文,当代论文,生物论文,学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2012)01-0038-05
在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科学哲学家们一直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物理学的理论和发展上面。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生物学和社会科学就远不那么重要了。如果在回顾之中这一注意之焦点显得不太公平的话,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无的放矢。
在过去九十年之中,物理学的革命性进展提出了一些基本的哲学问题并且向科学性质的既存概念提出了挑战。正如埃利奥特·索伯(Elliott Sober)所记录的那样:“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理论之所以占据了科学哲学的中心地位是有充分理由的。作为哲学家,我们关心先验知识、约定主义的问题和那些能够允许根本不同的科学理论进行比较和评价的普遍原则。”(1984,第6页)
然而现在人们已经达成共识,认为对物理学的过分着迷已经对科学哲学产生了扭曲性的影响。这一倾向导致假定物理学的某些性质——如其易于导向数学公理化的特性是科学理论的普遍特征,以至于到了这种程度:其他领域不具备这种性质的理论,就被看作不完全的、不充分的,需要加以发展以适应从物理学中所得出的这种模式。
本卷前半部分所选的文章已显示出:由逻辑经验主义者自1920年代至1950年代期间系统表述的关于科学理论的“公认观点”陷入了严重的内部困难的包围之中。换言之,这种科学理论的、居主导地位的模式甚至在显示其特征的最重要的领域中都是不充分的。近年来,越来越明显地显示出这一模式对物理学之外的科学领域是更不合适的。
在过去的至少四十年的时间里,生物学一直是一个极其活跃的科学研究领域。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成熟的、极为成功的研究领域,就生物学现象提出了若干复杂的问题,并且对之给出了复杂的、富有成果的答案。实际上,生物学是我们所拥有的成功的、非物理科学的最好例子。然而,生物学理论的结构、生物学说明的标准、生物学理论的检验方式,都不太符合物理科学的标准模式。这是怀疑该模式的适当性、至少是作为科学性质的总体表述的适当性的进一步理由。
在科学理论的公认观点处于危机的情况下,生物学研究所取得的连续的成功使得生物学哲学大概成了同时代的科学哲学中最令人兴奋的研究领域。生物哲学家们已经对我们关于科学理论的性质、说明、因果关系、推动力、自然种类及其他许多问题的理解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一部分所选的文章主要集中在生物科学中最具重要性的一个问题的诸方面:还原。
关于还原的问题在所有非物理学的科学中(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科学)都时隐时现,这有其明显的原因。由各门特殊的科学所讨论的现象,其最终的组成部分在本性上都是物理的,这点是得到了各方公认的。例如,生物有机体是由细胞组成的,细胞又是由复杂的分子组成的,复杂分子又可由简单分子组成,依次类推一直可达到作为物理学的解释对象的现象层面。但即便这一本体论上的还原主义是没有争议的,是否就意味着特定科学的理论也将最终还原为物理学的理论?是否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利用物理学的概念和方法为像生物学这方面的现象寻求说明?换言之,我们是否应该接受解释性的或方法论的还原主义的某些说法?无论我们是否应当如此,都要弄清楚有关“高层次”领域的理论和关乎“低层次”领域的理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在第一部分的第三节中,对理论还原的一些重要概念进行过细致的讨论。从理论还原的传统观点来看,理论被看成命题的集合,当一个理论的命题可以从另一个理论的命题中得出时,前一个理论就可以大致地还原为后一个理论。一些能干的哲学家(例如,可参见Schaffner 1967,1976; Ruse 1973,1976)已经试图将这一模式应用于古典生物学的理论(细胞学,古典基因学)与分子生物学理论之间的关系上。
在这一部分的第一篇文章中,菲利普·凯切尔(Philip Kitcher)提出了几个须加以考虑的、反对这一做法的重要因素。他认为,还原的标准典型没有把握住不同层次的生物学理论之间的确切关系,并且只有通过对分子基因学、古典基因学领域的实质性进展进行仔细的检查,才能理解二者的相关性;试图将细胞学还原为分子生物学,将无法识别那些具有因果关系的性质。他还主张,说明应当是双向的,有时“高层的”现象说明“低层的”现象,反之亦然。
这一部分另外两篇文章讨论在进化论背景下的解释性的或方法论的还原。达尔文理论的基本观点是:进化是通过自然选择的过程发生的。达尔文最初是以下面这种方式表达这一观点的:生物在生存与繁殖方面的特性彼此不同,因此具有某些性质的生物将会比其他的生物留下更多的后代。既然很多有益的特性是可以继承的,生物体的连续的后代将不同于它们的祖辈,因为某些特征变得更加普遍了。这种发展的模式重复多代以后,进化就发生了。
达尔文认为选择作用于个体生物之上,但近年来生物体是否总是或曾经是选择的基本单位已成为一件颇有争议的事情。自然选择的基本思想可以完全不提及生物体来加以表述。任何一群实体只要显示出在适应方面的可继承的变异(当适应是对实体的生存和繁殖能力的衡量时),在原则上就可能成为进化的主体。对达尔文来说,选择作用于个体的生物之上,但原则上并没有生物群体为什么不能成为选择的单位的原因。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选择可以发生在个体基因的水平上,如果能够指出个体基因的适应程度的话。
选择的压力只能直接作用于表现型的水平上而不是基因型的水平上,因此有人反对基因可以作为选择单位的可能性(例如,可参见Mayr 1963,Gould 1980)。某一特定基因能否保存并在下一代中得到复制,取决于由它构成一个组成部分的生物体的形态学、行为及其他的表现型特征。但当这一主张正确的时候(至少在多数情况下),这一反对就是不适当的。既然是生物体的基因型产生了其表现型,那么任何能够直接作用于后者的力量都能间接作用于前者。如果不同的单个基因对表现型的影响能够被区别开来,那么特定的基因便会间接地成为选择的对象。
几位有影响的生物学家主张不应当仅把基因当做选择的一个单元,而应将之当做选择的唯一单元。例如,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其广为传阅的著作《自私的基因》中主张自然选择的每一实例都可以看作基因选择的例子,同时将较高层次的选择看成仅仅是派生的,基于节约的考虑使得将基因选择视为基本的是合乎情理的。
在本部分的第二篇选文中,埃利奥特·索伯和理查德·列万廷(Richard Lewontin)认为,道金斯的处理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他们认为在很多例子中,对某一基因的适合度的衡量是纯粹人为的。进化生物学正在努力辨别出来的真正的因果过程并不总发生在基因的水平上。
索伯和列万廷试图指出一个以个体基因为依据的说明甚至在种群遗传学的领域内都是不充分的。任何选择过程的结果都可以由不同的基因在该种群的整个基因库中的相对出现频率来表现,这点是没有争议的。然而索伯和列万廷认为这种结果不能总以基因水平的选择来作为解释的依据。在他们看来,道金斯结果的基本问题是个体基因的效果对环境很敏感,例如,很依赖于将其包含于其中的整个基因组的性质。但是,“如果我们希望讨论单个基因的选择,那么必须存在有某一事物作为拥有该基因的因果性的结局。一个在某些情况下有益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有害的基因将会有很多有机体的作用。但在种群的水平上,将不存在支持或反对该基因的选择”。索伯和列万廷并没有排除基因选择,但他们主张选择过程作用于若干个水平之上,从基因到有机体的整个种群。最后,他们引出他们关于特征和力量的性质等问题的答案的哲学含义。
正如在本部分最后一篇论文中,金·史特瑞尼(Kim Sterelny)和菲利普·凯切尔所阐明的那样:是否所有由自然选择而起的进化都可以被视为发生在基因水平上,仍然是个不断争议的话题。史特瑞尼和菲利普对列万廷和索伯的结论提出异议,认为若能对道金斯的建议作合适的解释,则仍可作为对自然选择的活动方式的一种合理的表述(尽管可能不是唯一的)。
在生物学哲学领域,还有其他一些有争议的重要领域,限于篇幅,在此不能一一述及。这其中的两个至少是值得一提的。这些领域中的第一个与建立人类社会生物学的尝试所引起的一组论题有关。“社会生物学”是给对社会行为的生物学的(尤其是进化论的)基础的研究所起的名字。近年来,这一领域的研究已吸引了很多研究(非人类)动物行为的学者,对他们的研究成果的强烈兴趣导致了将相关技巧运用于研究人类行为的尝试。
人类社会学的研究可以粗略地、但很有用地分为专业人类社会生物学和大众社会生物学(见凯切尔1985,1987)。专业人类社会生物学一直主要是、但不完全是为在部落或其他传统社会(可以被看做近似于人类的社会特性及其他特性演化时的社会条件下的社会生活)中的人类社会行为的特点提供进化论的说明。
大众社会生物学则与之相反,其特点在于致力于获得有关现代社会中实际的及可能的人类行为的进化论的认识。这种研究几乎总是试图将进化生物学的方法应用于评价人类行为的社会、政治、道德方面的重要特点的柔韧性这类问题。更广泛的目标几乎总是评价不同种类的社会改革的成功的可行性或可能性(对种族主义、排外主义的消灭,更为公平的社会秩序的建立,等等)。结论几乎总是悲观的:进化理论被用来预言那些被改革者们批判的行为特点的与生俱来的僵化性。
另外一个论题贯穿了人类社会生物学的普及文献的大部分及一些专业文献。它是这样一个想法:人类社会生物学的纲领为把社会科学乃至道德理论还原为生物学提供了希望。这点非常有趣:这种提议中的还原与科学中其他种作为目标或已经达到的还原有实质上的不同。总体说来,在还原看来是一种似乎可能的策略的情形下,处在还原之中的科学就成了一种构成被还原科学之主题的实质或结构的组成部分的理论。就社会生物学的情形而论,据称是被还原的科学,所研究的就是作为人类进化世系之组成部分的人类和人类社会,即正在还原的科学的主题。
很多批评家(例如Allen以及其他人的1975,列万廷以及其他人的1984)已经在大众生物学的主流中看到了标志着19世纪社会达尔文主义特征的社会意识形态的某种影响。大众社会生物学的实践者们(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几乎都是职业的社会生物学家)认为,他们的工作是因进化理论的新进展(例如亲缘选择理论;凯切尔的1985对这些进展作了一个很好的说明)而非意识形态才活跃起来的,他们以此来作出反应。很多人论证说,那些批评家们自己就是受左翼或有改革意识的意识形态的因素所驱使的(例如,可以看看Wilson的1976)。
作为回答,大众社会生物学的批评者们就社会生物学家们应用进化理论研究人类行为的方式提出了若干科学上的及方法论上的批评。例如,他们论证说,社会生物学的假说常常建立在人与非人的动物这二者之行为的不适当的类比的基础之上,这样的假说依赖于成问题的“适者”假设,该假设的大意是,所有意义重大的行为特点都已经被选择了,早期人类的社会行为对于繁殖来说是最适宜的,等等;总之,社会生物学家低估了由早期原始人类的行为的论断外推到关于现代社会人类行为的论断的难度。当然,社会生物学家们已经试过反驳所有这些批评了。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查阅本引言末尾所列之参考书目(凯切尔的1987是一场在人类社会生物学的辩护者与批评者之间的特别有用的争论)。
本文选未加讨论的第二个领域包括了由系统论所引起的问题。系统论是关系到为有机体的分类发展起一个合适的体系的这部分生物学。系统论内部的争论提出了与自然种类及科学方法的理论依赖有关的重要问题。一场重要的争论关系到物种的性质问题。物种似乎是自然种类的典型例子——是某些事物的并非臆断的集合,这些事物的界限代表着世界上客观存在着的区分。但是,是什么使得一个特定的事物是或不是某一些自然种类的成员?决定成员身份的很显然的办法就是看它是否具有能够明确说明讨论中的物种的性质(或一定数量的性质)。然而,批评这一方法的人却说,同一生物种内部成员间的变异实在太大,这一方法是无法奏效的(Ghiselin 1974,1981,1987; Hull 1976)。他们提出了替代的建议,说物种应被视为个体。物种的成员被用以显示与物种的同一性,恰如有机体的细胞之于有机体那种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这样一种观点很自然地暗示着,是物种而非有机体,作为选择的基本单位,而这确实是其捍卫者所主张的。在这里无法讨论这一观点是否合适。但如果它是正确的,那么主张物种是自然的种类这一观点是否应当被放弃呢?或者是否应当保留这个观点并对我们关于自然种类的概念作相应的修正?这将是个很有趣的问题。
争议中的第二个领域关系到将应用于物种分类的合适的框架应用到更广泛的种类或更高的类群中去(在标准的等级制度中的种类是界、门或部、纲、目、科、属)的问题。一些生物学家已主张这种分类的进行不应与进化论有关。取而代之作为分类的基础的应当是不同物种的典型成员间的表现型的相似与差异(例如,Sneath和Sokal 1973)。这些“表型分类学家”们已经为他们的方案提出了两点理由:首先,客观的判断要求独立于理论;其次,如果进化论被用作分类的基础,那么作为其结果的分类就不能用来推进我们关于进化过程自身的认识。然而这些主张都不能给人以深刻印象。现在,没有几个科学哲学家会怀疑科学方法的所有方面,包括分类方法依赖于理论。但是正如在文集第一部分中的几篇论文所主张的那样,这并不妨碍这些方法产生客观的结果。物种间的关系建立在理论的考虑基础之上这一事实,也并未排除运用这一关系为背景理论提供进一步的确证的可能性。
关于分类的一个可选方案使得生物进化史的因素具有了极大的重要性。我们可以通过考虑可能的、可供选择的生物进化史来决定现存种群的进化历史,并且就像我们从任何竞争的科学假说中选择那样从其中进行选择(Sober 1983、1988)。生物进化史可以用图解来表示,即系谱树,它显示出最早的种群是如何在经历了漫长的时间之后分化成了不同的互有区别的后代种群的。一个很有影响的生物学家小组、系统分支学学派,已经主张分类的问题可以直接从系谱树中获得答案。物种存在于这种图表的诸分支点之间,每次现存种群分枝的出现,都会形成两个新的物种,同时老的物种消失。系统分支学学派坚持认为更高的种群应当是严格地属于一个原种,即一个种群的全部成员都应该是一个共同祖先的后代,并且所有的后代都应该是该种群的成员。据称,作为结果的分类,将最为精确地反映生物进化史。这种分类是通过分析物种的特征以试图区别是否从祖先继承下来而建立起来的(见Hennig 1966,Eldredge和Cracraft 1980)。
然而,进化系统论者们认为,系统分支学学派的分类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例如Mayr,1969)。他们指出,一个共同祖先的后代可以彼此差异非常之大,在很多情形下使得将同一祖先的所有后代划入一个种群是误导性的或不自然的。例如,鳄鱼和其他爬行动物有很多共同的特征,可能是从同一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但是如果我们要把鳄鱼和其他爬行动物划入同一更高的种群,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把鸟类也划进去,因为它们也是同一祖先的后代,尽管它们已经产生了大量的新特征(Mayr 1981)。如果我们要把鳄鱼和其他的爬行动物划入一个范畴,将鸟类划为一个独立的同型的种群,那么,我们就得放弃严格地同种发生的要求。进化系统论者们就是这么做的,只要求同一个种群的成员拥有一个共同的祖先,而不要求这个祖先的所有后代都作为该种群的成员。哪些后代是这个种群的成员将部分地取决于其特殊的性质。
尽管进化系统论者所运用的分类方法导致了明显的自然种群集合,但这种方法的生物学上的理由却不够明显。进化系统论者可以允许两栖动物组成一个种群(虽然所有两栖动物的共同祖先有很多非两栖动物的后代),其理由是,它们的共同特征使得它们在将来面对相似的选择压力时可能会经受相似的进化的变化,但这一主张至多是纯粹的玄想,因此对于生物学分类方法来说将是一个脆弱的基础。
此外,任何一个根据自然进化关系分类的系统都将面对一个困难:证据太少使得分类学的进展非常困难。一部分是出于对此困难的反应,一部分是对上文提到的与表型性的分类相关的哲学考虑的反应。一些系统分支学学派即“纯形式的系统分支学学派”现在主张,他们所建构的系谱树根本不应被看做进化的模式,使得系统分支学学派的分类独树一帜的仅仅是其特征分析的方法。这种分析是否真的是分类的全部仍是一个争论中的问题(见Beatty 1982; Patterson 1978,1982; Ridley 1986)。
(原文出自《科学哲学》[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由Richard Boyd、Philip Gasper、J.D.Trout三人联合主编,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二部分,第545-550页。标题和摘要为译者所加。鞍山师范学院安金辉博士译,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桂起权校。)
收稿日期:2011-1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