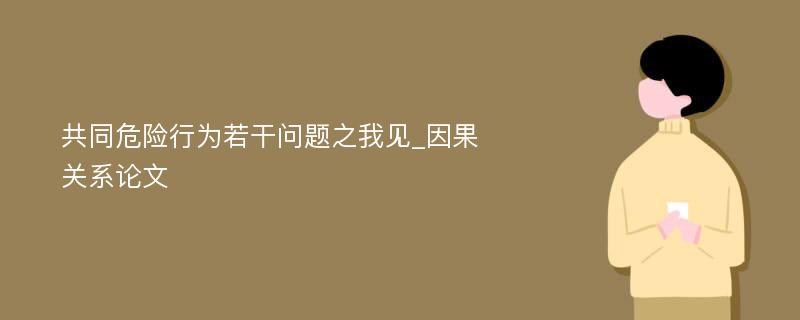
共同危险行为若干问题之我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见论文,若干问题论文,危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 0964(2000)02—0042—05
传统民法理论把共同侵权行为分为三种形态:一是狭义共同侵权行为,又叫共同加害行为;二是准共同侵权行为,指数人实施的行为均有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危险性,其中一人或部分人的行为致人损害而又不知谁为加害人的侵权行为,这种行为又称共同危险行为;三是视为共同侵权行为,即有教唆人、帮助人参加的共同侵权行为[1]。 关于共同侵权行为,我国《民法通则》第130 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侵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除此条之外,无其他规定。可见,我国民法对共同侵权行为的种类未作区分。根据王利明教授的观点,共同侵权行为分为狭义的共同侵权行为(共同过错)、共同危险行为和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2]。这一观点, 避免了传统民法理论分类的不周延,成为现今关于共同侵权行为分类的权威说法。
关于上述分类中的共同危险行为,我国学者不乏理论探索,在司法实践中也已开始承认和运用共同危险行为理论处理案件。然而,由于共同危险行为理论甚为复杂,学者们的认识不尽相同。本文拟就上述几个问题进行分析。
一、关于共同危险行为的主观方面
在共同危险行为中,虽然各行为人的行为都有造成损害后果发生的可能性,但是其损害后果并非由行为人全体共同造成的,至于何人造成,不能得知。这样,共同危险行为的行为人就有致害人与非致害人之分。致害人与非致害人之间,主观方面如何,学者有不同见解,分歧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非致害人是否有过错;二是倘若非致害人亦有过错,致害人过错与非致害人过错之间有无意思联络。
1.关于非致害人是否有过错
有学者认为,非致害人主观上并不存在过失。过失的成立须以损害后果的发生为前提,没有损害的发生也就无所谓过失。而危险行为人中非致害人的行为尽管共同造成危险状态,但并未实际致害,这些行为人也就不存在过失[3]。
另一些学者认为,非致害人主观上存在过失。从主观上看,行为人没有致人损害的故意,在数人中,既没有共同的故意,也没有单独的故意,只存在疏于注意义务的共同过失。因为共同故意可以构成共同侵权行为,单独故意构成一般侵权行为[3]。
笔者认为,认为非致害人并无过错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所谓过错,是一个主观和客观要素相结合的概念,它是指支配行为人从事在法律上和道德上应受非难的行为的故意和过失状态[2]。的确, 过错的存在须表现为受行为人主观意志支配的外在行为,行为人的意志必须外在化时,才具有法律上的意义。但是,损害事实的存在并非构成过错的必要条件。当然,行为人的过错大多致人遭受损害,从而有损害事实发生,但实践中行为人有过错却并未致人损害的例子并不罕见。例如,开枪打人未中,他人并无伤亡,却不能认为行为人主观上并无过错。倘若只有损害事实发生,行为人才有过错,则一般侵权行为损害事实要件的存在实无必要。因此,损害事实和过错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就共同危险行为而言,危险行为的存在本身即是以表明行为人主观上的过错。因为行为人致人损害的可能性的存在必然伴随着其主观上的故意或者过失。
就过错内容而言,共同危险行为人的主观过错是否像有学者主张的那样,仅包括过失?笔者认为,危险状态能否形成和存在,并不因行为人主观上的过失与故意之不同而有所区别。诚然,在共同危险行为中,行为人的过错大多是过失状态,但也不可否认,在一方故意他方过失,甚至在行为人均有故意的情况下,行为人致人损害的可能性仍能并存。例如,二人素不相识,均于某日晚找甲复仇。二人同时向某甲开枪后,以为被人发觉仓皇逃走,某甲身中一弹,不知何人所为。二人虽因触犯刑律须承担刑事责任,但在民法上,仍构成共同危险行为。
2.关于行为人之间有无意思联络
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共同危险行为人之间须具备意思联络,否则不构成共同危险行为。德国著名学者拉伦茨(Larrenz ),日本学者冈松参太郎、矶谷幸次郎、野田孝明[4]等持这种观点。 第二种观点认为,共同危险行为人之间,不以意思联络为必需,行为人之间,或有意思联络,或无意思联络。我国学者张瑞明先生持这种观点[5]。第三种观点认为,共同危险行为人主观上并无意思联络。
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因为意思联络,即行为人主观上的关联,使行为人的客观行为联结成一个整体,具有不可分性。而受害人所受损害,理当认为是行为人全体所致。或许有时直接致害人并不明确,但决不能认为此时致害人不明。就上述三种观点而言,第一种观点使得共同危险行为与共同侵权行为(狭义)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从而使二者的区别毫无实际意义;第二种观点认为共同危险行为人之间可以有意思联络,也可以无意思联络,显然不适当地扩大了共同危险行为的适用范围,从而有排挤共同侵权行为(狭义)适用范围之嫌。
应当指出的是,既然共同危险行为人之间不存在意思联络,那么,行为人之间有无共同过错?笔者认为,行为人的过错之间没有意思联络,只是个别的过错或者相同的过错,并不构成共同过错。共同侵权行为(狭义)之共同,即是指行为人之间具有共同过错而言。在共同危险行为中,行为人虽然都具有主观上的过错,有时甚至具有相同的过错,但因行为人主观上并无意思联络,他们之间的过错仍未联结在一起,不能称为“共同过错”。至于共同危险行为的“共同”,不是行为人过错的共同,而应解释为行为人之间造成损害可能性的共同,即危险的共同。
二、关于共同危险行为的客观方面
关于共同危险行为的客观方面,我国学者普遍认为要构成共同危险行为,行为人的行为之间须具有客观的关联,且具备行为之一体性。但在国外及我国台湾省,共同危险行为是否必须具备行为之共同性,引发过诸多争论。其中主要有两种不同的学说[4]。 一种学说认为行为人的行为须具有共同的一体性,才能构成共同危险行为。这种学说在理论上称“行为之共同说”。持此说者以德国的拉伦茨(Larrenz)、 日本的梅谦次郎、饭岛乔平等为代表。另一种学说认为构成共同危险行为,不须具有行为共同性的要件。行为人的行动,虽不在同时、同地发生,只要均具有造成损害的可能性,仍构成共同危险行为。这种学说在理论上称为“致害人的不能确知说”。持此说者以德国的埃赛尔(Esser)、 日本的我妻荣、几代通等为代表。
笔者认为,上述两种学说的分歧主要在于,共同危险行为之客观方面是重在行为之共同性,还是重在致害人的不能确知性。如果重在行为之共同性,则行为人的行为须构成共同行为,否则不构成共同危险行为;如果重在致害人之不能确知性,则只需致害人不明,不须有共同行为,仍可构成共同危险行为。
从立法史来看,共同危险行为起源于罗马法。其原始的构想在于解决致害人不明时,扩张赔偿责任人的问题,以使无辜的受害人得到赔偿。在罗马共和国末期,罗马市街道狭隘,住宅密集,屡见投下物、流下物造成损害。为了确保公众集会场所和交通道路的安全,乃创设了“流出投下物诉权”,规定在共同住宅(无论是自有、租赁、借住)内的居民,不知何人,有物体从窗户投下、坠落或有物流出,到达道路或者其他场所,造成行人或他人受损害,究竟投下物或流出物为何人所为,无法确知时,应科以共同住宅全体居民负连带责任[4]。可见, 在罗马法中,成立“流出投下物诉权”,无须具备行为的共同性,而仅以实际致害人的不可确知性为要件。后世德国民法典第830 条即源于罗马法“流出投下物诉权”,而日本及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中关于共同危险行为的规定,则源于德国法。因此,可以说,共同危险行为创始之初,并不重在行为人行为的共同性,而重在解决致害人不明时受害人无法举证求偿的问题。
就国外学说判例的发展而言,“行为之共同说”主导了大陆法系国家共同危险行为理论界很长一段时间。但近些年来,法、德、日等国理论界均倾向于强调行为共同性的要件并不必要。许多学者认为,所谓“时间的、场所的关联”要件,不为必需。共同危险行为人之赔偿义务,是由于各人对于导致结果具有可能性,即他们均做出具体的危险状态,此即由于不能确知致害人所做的危险行为,而科以共同危险行为人责任的根据所在。所谓“时间的、场所的关联”的基准即救济范围限制,应该予以否定[4]。
综上所述,无论是其立法起源,还是其发展趋势,共同危险行为都是重在致害人的不能确知性。因此,笔者认为,共同危险行为的客观方面,无须表现为行为的共同性,而是只要受害人遭受损害,行为人均具有致害可能性。
那么,在共同危险行为中,行为人致人损害的危险在造成实际损害时是否都已实际存在呢?有学者认为是肯定的,并且都有造成实际损害的可能性[5]。笔者认为, 既然共同危险行为不以行为的共同性为要件,则异地、异时、异质的危险行为也能构成共同危险行为。从这个角度看,在实际造成损害时,可能行为人的危险行为都已实际存在,也可能部分行为人的危险行为已经存在而其他行为人的危险行为尚未实际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强调共同危险行为重在加害人的不能确知性,难免有时会不当地扩大无辜被告人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应根据社会公共的价值观、伦理观对“危险行为”的概念作出合理的界定,使不具有致害可能性的无辜被告人免除责任。例如火车车厢内有人丢出物体,致路人受伤;开架式图书馆闭馆时,发现当日有书被窃,不宜认定车厢内的所有乘客或所有当日进入图书倌的读者构成共同危险行为。
三、关于共同危险行为的因果关系
与共同危险行为有关的因果关系不外两种:一种是择一的因果关系,另一种是累积的因果关系。择一的因果关系,是指数个人的行为均有可能导致结果的发生,但究竟何人的行为与结果有因果关系,并不明确。累积的因果关系,是指数个人行为的结合导致了结果的发生,数个原因对结果的发生之作用比例不明。
笔者认为,对择一的因果关系,因其只有一个行为人的行为与结果有关,且行为人不明,这正是共同危险行为因果关系的特征。毫无疑问,共同危险行为之因果关系应当包括择一的因果关系。国内外学者对此亦无不同看法。而对累积的因果关系,数个行为人的行为之结合导致了结果的发生,这就表明,整个行为人的行为与结果之间都有因果联系。具体到共同侵权行为实践,数个行为人都是致害人,即致害人已经明确,虽然各致害人之致害比例不能确定,却不存在“致害人不明”的情形。因此,累积的因果关系不构成共同危险行为。至于在累积的因果关系中,致害人之间无主观的意思联络时,则是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的一种情形。
四、共同危险行为承担连带责任的基础
在侵权行为法领域,一般地,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是以其主观上有共同过错为基础的。行为人主观上的共同过错,表明其实施侵权行为时有意思联络,行为人之间同心协力,其损害必较单一的行为较重,故应使数人就因数行为所生的损害,各负全部责任,即连带责任。
在共同危险行为,数行为人就损害事实承担连带责任,其基础为何?有学者认为,共同危险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基础在于他们具有共同过错[2][3]。如前所述,在共同危险行为中,虽然行为人都具有过错,但主观上并无意思联络,因此,共同危险行为的数个行为人之间并不存在共同过错。所以,认为共同危险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基础在于共同过失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笔者认为,共同危险行为人就损害事实承担连带责任基于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共同危险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在于“无辜的受害人”与“无辜的被告人”利益的取舍。在共同危险行为中,一方面,因为致害人不明,若要由受害人举证证明致害人的致害行为与受害人的损害事实之因果关系,必然会因举证困难而使受害人不能请求致害人赔偿,这对无辜的受害人是十分不利的,有违民法的公平原则;另一方面,因为受害人的损害事实只是共同危险行为人中的一人或几个所致,而致害人并不明确,则不能由某人或某些人对受害人负责,更不能使全部行为人均被免除责任,只能由危险行为人全体对受害人负责,但此时又因受害人的损害事实并非由危险行为人全体所致,对非致害行为人即无辜的被告人难免过苛。这样,就产生了“无辜的受害人”与“无辜的被告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法律必须在二者之间进行细微考量,做出取舍。综合判断,非致害行为人的危险行为虽与受害人的损害事实无因果关系,但因其在造成危险行为方面仍有过错,为惩戒危险行为人,权衡轻重,法律仍应保护无辜受害人的利益,推定各危险行为均与受害人损害事实有因果关系,从而要求危险行为人全体对受害人负赔偿责任。
其次,共同危险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基础在于危险行为的客观关联性。法律在“无辜的受害人”与“无辜的被告人”之间做出利益取舍,只是说明了共同危险行为人何以均应对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而共同危险行为人为什么应对受害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呢?笔者认为,在共同危险行为中,行为人之间虽不具有主观的意思联络,并无共同过错和主观的关联性,从而行为人的行为也不因其主观的意思联络而联结成一个整体,但是,由于各危险行为人都有造成受害人损害后果发生的可能性,而致害人又不明,那么各危险行为人的行为或因时间场所之共同,或因时间之连续,或因场所之毗邻都会联结成为一体,从而具有客观的关联性。危险行为的客观关联性,正是共同危险行为人对受害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基础。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可以将共同侵权行为(狭义)、共同危险行为和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区分开。
从主观方面看,无论是共同侵权行为(狭义),还是共同危险行为,还是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其行为人均具有主观上的过错;所不同的是,在共同侵权行为(狭义)中,行为人之间主观上有意思联络,具有共同过错,而在共同危险行为和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中,行为人之间主观上并无意思联络,只有个别的过错,而不具有共同过错。
从客观方面看,在共同侵权行为(狭义)和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中,致害人是明确的,而在共同危险行为中,孰为致害人,并不确定。就客观行为的关联性而言,共同侵权行为(狭义)基于行为人主观上的共同过错和客观行为的共同性,共同危险行为基于各行为人造成损害后果发生的可能性和致害人的不可能确知性,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则基于各行为人的行为的相互作用与结合。
从因果关系看,对共同侵权行为(狭义)和无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行为人的行为和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都是认定的;而共同危险行为则属于推定的因果关系。由此衍生出,在共同侵权行为(狭义)和无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行为中,不存在行为人之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因欠缺因果关系而免责的问题;而对共同危险行为,行为人可以其行为与损害后果欠缺因果关系为由,主张免责。
从责任的承担看,三者有不同类型的责任,在共同侵权行为(狭义)中,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在共同危险行为中,各行为人承担可以免责的连带责任;而在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行为中,各行为人分别承担赔偿责任。
收稿日期:1999—12—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