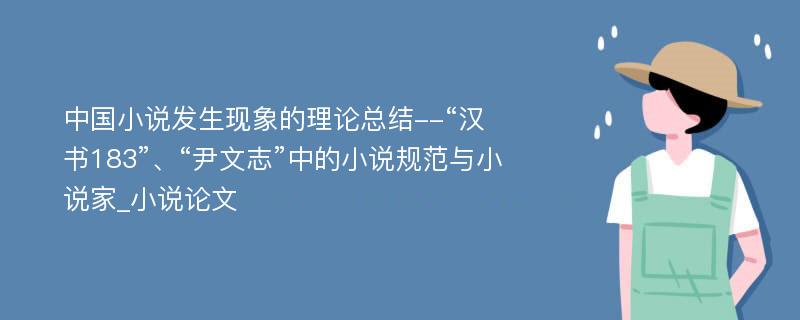
中国小说发生期现象的理论总结——《汉书#183;艺文志》中的小说标准与小说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书论文,小说论文,小说家论文,中国论文,现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术界一般认为魏晋时代以前是中国小说的发生期①。事实上,发生期的上限从理论上可追溯至很远,但从具有小说因素的存世文本来看,实际发生的上限当从史官文化和诸子之学的出现而开始;发生期的下限从理论上可推至汉末,但汉代文化,西汉和东汉有较大差异,西汉与先秦有关,而东汉则与魏晋联系多一些,发生期的下限应在西汉末。因此,中国小说的发生期,实际而论,主要在先秦至西汉末。《汉书·艺文志》由刘向《别录》、刘歆《七略》而来,它所体现的,可说是二刘与班固三人对先秦至西汉末学术文化成果的基本认识。《汉志·诸子略·小说》以其所著录的作品篇名、篇名所附的注言和《诸子略·小说序》,对中国小说发生期现象作出了理论总结,标志着中国小说理论批评的正式出现。《汉志》小说理论,在给我们构筑出一幅小说起于民间口语的历史场景的基础上,提供了关于小说三条标准和小说家情况的看法。这些看法,奠定了中国正统的小说观,对小说的历史发展意义重大,至清代仍为四库馆臣遵循不二。
一、小说的民间性标准
《诸子略·小说》著录了十五家(部)一千三百九十篇作品,其中汉以前九部,西汉六部。这诚然是作者所认定的具体的小说文本,是其立名“小说”的基础。但是,有种种迹象显示,这十五部小说并非是先秦至西汉末的所有小说,而只是被收藏于“延阁、广内、秘室之府”②,即其时的国家图书馆和为刘、班诸人的小说标准所认可的先秦到西汉末的部分作品而已,但是,这些毕竟是被正史所认可并被堂皇地载入史志的首批小说作品,它们对中国小说史研究尤其是发生期小说诸方面的研究无疑具有充分的代表性价值。
探讨《汉志》的小说标准,应当立足于这样三个方面:一、《诸子略·小说序》;二、班固根据《别录》和《七略》对作品所作的简短注言;三、学术界对十五部作品所作的辑佚和探讨。在这些基础上所得出的小说标准,才有可能臻于全面和准确之境,并可进一步去把握他们的小说观念。
在小说标准中,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作品的民间性。这种民间性,在刘、班那里,是就小说内容的来源而不是就小说的最后定型而言的,对此,《诸子略·小说序》有明确的论断: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小说“出于稗官”,这个问题容待最后一节再议。上引序言中,“道听途说者”和“闾里小知者”是就小说创作主体而言的;“造”和“缀而不忘”是就小说创作过程而言的;“街谈巷语”和“刍荛狂夫之议”是就小说内容而言的。从这三个角度,作者勾勒了一个小说民间化发生、流传和在民间得以初步整理的轮廓。
为使这一轮廓更加清晰,我们对上面有关词语作些解释。一是“闾里小知者”,这指的是民间粗通文墨的人,其文化程度比“道听途说者”稍高,但绝不是中上阶层的人,甚至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所谓“士”。作者在《诸子略·杂家》的《吕氏春秋》下有个注言“秦相吕不韦辑智略士作”,这里的“智略士”可拿来与“闾里小知者”作比较,就可见所谓“闾里小知者”实隐含着两层意思:一是知识和见识并不高,所以他们对“小说”只能做些“缀而不忘”的工作,即把流传于民间口头上的作品进行连缀加工,以书写的形式保存下来以免散失遗忘;二是针对其社会身份而言,确认其居于社会下层的民间身份。因此,从“道听途说者”所“造”到“闾里小知者”初步整理得以“缀而不忘”,小说就这样在民间形成并一直在民间流传和得到整理保存。
二是“刍荛狂夫之议”。句中以此作比,喻指在民间创作并在民间得以初步整理后的小说的内容。“刍荛”一词,割草为刍,打柴叫荛,合指割草打柴的人即草野之人;“狂夫”一词,泛指愚钝者,古代“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劳心者”统治下的“劳力者”往往被视为愚钝和不开化的人,这与前面的“闾里小知者”似乎有类似之处,不仅指其知识程度之低下,更指其所处社会地位之低。以“刍荛狂夫之议”来比喻小说的内容,是进一步强化了小说的民间性。但是,“狂夫”尚有特指之义,指那些驱疫逐邪的人,在汉代即为类似于方士身份的人。《左传·闵公二年》:“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孔颖达疏曰:“方相之士,蒙玄衣朱裳,主索室中殴疫,号之为狂夫。”③
这里的“方相之士”即“狂夫”,乔妆执鬼,属于方术范围。如果将“刍荛狂夫”理解为草野之人和方士一流的人,那么,则说明在早期的小说中另含有方士书的内容,而且正与《汉志》所著录的小说篇目情况相吻合④。同时,刘、班将“刍荛”与特指之义的“狂夫”相并置,是否也表明“狂夫”之议即方士书的内容同样出自民间?经过了汉武帝时重用和轻信方士的闹剧以后,在刘向、歆父子所生活的西汉后期与班固所生活的东汉,有可能对鼓吹仙鬼混杂、长生不老的方术作出理性的判断,而表明其内容渊源自民间,正是这种理性判断的标志之一。
《诸子略·小说序》为我们构筑了小说发生的民间空间和民间状貌,确立了小说内容源自民间的性质,这与所著录的大部分小说的内容互有照应。
《汉志》十五部小说,到梁朝已仅存《青史子》,至隋则全佚。前人包括鲁迅《古小说钩沉》对这些小说做过辑佚工作,但收效甚微。但在古代典籍中,有明引或暗用这些小说的痕迹,借助于这些材料以及吉光片羽式的作品注言,我们还是可以对这些小说的内容有个大致的了解。
《伊尹说》讲述了伊尹出身及其事迹,主体是伊尹向汤述说天下之至味,铺陈一些如水火之齐、鱼肉菜饭之美等言辞。这些言辞的最终指向虽与政教有关,但其内容却不乏民间风物,并且“其语浅薄”,使用了某些民间语言,作品的民间风格是相当明显的。如果我们再进而考虑到现在所据以分析的这段佚文保存在《吕氏春秋·本味篇》,而《吕氏春秋》是杂家的代表作,以说理形式阐释王道治化为其主要倾向,在由“智略士”对各家书抽删缩编之时,某些书包括《伊尹说》的民间况味和故事性自然要受到损伤。鉴于此,我们对原作内容的民间性和小说样式就会有一个合理的想象与推测了。
出自《大戴礼记·保傅》、贾谊《新书·胎教十事》和应劭《风俗通义》中的《青史子》佚文,讲胎教之道、巾车教之道和鸡祀,由于佚文有两条辑自《礼记》,故而有明显的礼教色彩,但尽管如此,其内容的主体还是民间风俗和习俗的记载。在梁代尚存的《青史子》,刘勰曾见到过,故而在《文心雕龙·诸子》中说“《青史》曲缀于街谈”,突出其内容的“街谈”即民间性质。
《师旷》篇,《汉志》作者自注曰:“见《春秋》,其言浅薄,本与此同,似因托之。”历史传闻中的师旷,能辨音以知吉凶,他在各种典籍中的事迹,虽多出入于王宫,但其正是民间所喜闻乐道的、赋有异秉神技的那一类人物,所以注言中不仅指出了作品所使用的浅薄的民间语言,而且揭示了作品正是汇聚众多有关师旷其人其事的民间传说而成的文本原貌。袁行霈从《吕氏春秋·长见篇》辑得了有关小说《师旷》的一则佚文,并进而认为“其他如《韩非子》所载师旷奏清徵而有玄鹤从南方来一段,也很像是街谈巷语的小说家言”⑤,这正是其民间性的表征。
《黄帝说》从保存在《风俗通义》中的佚文来看,使素女鼓瑟、荼与昆弟于桃树下以苇执鬼,其记载与《山海经》中的片断相类似,采自民间传说而附益于黄帝其人,并启后世方术之源,故而《汉志》注言斥其为“迂诞依托”,表明了这种民间传说的记载荒唐怪异而不可征信的特点。
《封禅方说》和《待诏臣安成未央术》被明确指认为方士小说。前者是有关武帝时封禅的方术,从《史记·封禅书》的记载来看,方士关于封禅的议论多围绕着黄帝和神仙,对其流弊,《方技略·神仙序》说:“然而或者专以(神仙)为务,则诞欺怪迂之文弥以益多,非圣王之所以教也。”大概《封禅方说》一类就是被指责的诞欺怪迂之文吧。方士所依借的各种方外之谈和方术,其来源无外乎收集和自创,收集成分多而自创成分少,这些被收集的基本资料和技能大约一直在民间社会流传,诞妄怪异的色彩自不可免。大凡方士书,取材多源自民间传说。至于《待诏臣安成未央术》,则是求长生的方术,应劭注曰“道家也,好养生事,为未央之事”,《史记·封禅书》载有武帝时燕齐方士献长生不死药的事情。关于长生不死的话题及其所敷演出来的一系列荒诞之术包括房中术的谈说,可能自民间传说创造了黄帝这个人物就开始流传了,如医药之制,如素女陈五女之法。这篇供汉武帝择采的《未央术》当为此类传说的汇集或解说。
《虞初周说》,《汉志》作者注言:“河南人,武帝时以方士侍郎号黄车使者。”若以此为据,则虞初则为伴驾出巡的方士,其《周说》则是备武帝顾问的方士书,其性质与前两书相类。然而,应劭注曰“其说以《周书》为本”,则又似史书。其实这两者并不矛盾。在晋唐人所引的《周书》中,不乏祯祥怪异之谈,可见早期的史书,必不可免地染有神怪色彩。人智不足以破解自然之奇而后神怪出,这是原始思维特性所决定的。因此,将《虞初周说》视同于方士书还是有根据的。这部小说有九百四十三篇,不可能纯出于虞初创制,而只能解释为汇集众多传说并且主要是民间传说而成,因为伴驾出行的“黄车使者”主要的职责是告知人主“地事”和“地俗”以及“四方所识久远之事”⑥,而这种材料只能是源自民间。由此,我们确认:一、方士小说的内容非常广泛;二、其原始材料大多依赖于民间所出。
《百家》,据刘向《说苑·叙录》而知,此书是他在校书过程中汇集各家书中“浅薄不中义理”的片断而成,由这些“浅薄不中义理”的片断汇集而成的《百家》,其小说况味当比《列女传》、《说苑》和《新序》等书更足,故而班固将《百家》增入于“小说”,而将其他作品增入于“儒”。据保存在《风俗通义》的佚文来看,当由流传于民间的历史掌故和寓言故事汇聚而成,是典型的“街谈巷语”。
在十五部小说中,其余七部,《周考》、《天乙》和《臣寿周纪》,被学界认为是“近史”之小说;《鬻子说》、《务成子》、《宋子》和《待诏臣饶心术》被认为是“似子”之小说。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惟据班固注,则诸书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者也。”此论断既成为后世对《汉志》小说分类的依据,也在作品注言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这些小说的特征。这些作品的佚文虽不可考,但我们从《诸子略·小说序》对小说起于民间的发生机制的阐述以及对这些作品所加的注言,其民间性质还是隐然可辨。尤其是“近史”小说,缘于口头传述的历史传说而为史官所不采,有着更多的好事作奇的民间痕迹。此外,《汉志》的“近史”小说,多围绕着周代历史,可作对照的是,《六艺略·〈尚书〉》著录了《周书》,注言为“周史记”;《六艺略·〈春秋〉》著录了《世本》,注言为“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讫春秋时诸侯大夫”。可见,同样是记载历史的书籍,有的归入《六艺略》中的《尚书》和《春秋》类,有的却退置于《诸子略·小说》类,原因不外乎“一是庙堂经典、诚信有据的史书,一是出于民间、充满神话传说的野史纪闻,如同后世既有绵延不断的官修正史和编年通鉴,又有真假相参、种类繁多的历史演义和传记小说”⑦。说到底,正像我们上面通过《诸子略·小说序》和小说内容所作出的判断一样,其根源在于作者所持的小说民间性标准。
有学者认为,“就《汉志》所著录的小说来看,很难看得出是得自民间”⑧,其依据是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的一个判断:“然审察名目,乃殊不似有采自民间,如《诗》之《国风》者。”以我们不成熟的眼光来看,《黄帝说》之类的篇目像不像得自民间且不去说它,但根据《汉志》所著录的篇名来判断这些小说不具备民间性,似乎过于简单和草率。现在保存下来的古小说,除单篇如《穆天子传》和《燕丹子》等之外,结集的小说,若为整理品,则其篇名均由整理者后加;若为创作品,则其篇名亦仅取大略而已。两者之篇名,均有游离于具体故事之本体的倾向。《汉志》小说,除《待诏臣安成未央术》标明为单篇以外,余皆为多篇甚至多达九百多篇的集子,从后人所加的一个笼统的篇名中怎能否定其民间性呢?而古诗如《诗经》之标目,是以单篇为单位取诗行头几字,庶几可把握其诗之状貌,与小说的标目方式并不一致,结论也无法类推。
二、小说的叙事性标准
如果我们从叙事性的角度来考察《诸子略·小说序》,则可同时感觉作者给我们呈现了一个小说起于口语叙事的历史场景。在小说发生之初,“街谈巷语”的材料构成了小说的基本内容。换言之,“街谈巷语”即为小说内容的主体,呈现为口语传述的状态。而创作“街谈巷语”的主体,却是生活在民间的“道听途说者”。他们创作的基础和素材来源是“道听”,创作的方式和形态是“途说”,而这适与他们的创作成果“街谈巷语”相一致。《汉志》作者以“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这几字,告诉了我们一个小说发生的基本事实:在文字已经产生但书写工具和材料极为不便的先秦乃至远古,口语腾兴于田陌广野、街头巷角。在这一基本事实下,作者又以“缀而不忘”和“刍荛狂夫之议”进一步让后人加深对这一历史事实的印象。所谓“缀而不忘”,在这一背景下进行解释,说明口语成果即“街谈巷语”如果不用文字记载下来,则有可能被遗忘或散佚,因此,这里的“缀”字,可能不仅具有对零乱的片断性材料进行编次和整理的意思,同时还有用文字予以记载和保存的意思。所谓“刍荛狂夫之议”,则进一步突出了“街谈巷语”类乎于此的特点。这一特点在“议”字上被做了必要的强调,即其与“谈说”、“议论”相仿佛的口语性。
盛兴于民间的口语传述成果,如果不以事件或故事作为载体,是无法想象的。它既不可能大规模产生,也不可能使众人津津乐道而踵事增华,更不可能在口语状态中被长久保存。片断性的言说或叙述,如果没有一条明确而且易使人理解的线索,则无法在口语状态中被有效地组织和贯穿起来,同样不利于记忆。而事件或故事,尤其是产生于上古时代的事件或故事,都有明确的时间线索以及与之相呼应的事件或故事内部的其他线索。在这些线索中,呈现为纵状的、直线的、由头至尾的时间线索是最重要的,而且与先民们的生活直觉和得自于随时间的流逝而兴衰繁枯的自然现象的印象相吻合。可以说,时间线索,是最原始最根本的记忆基础。由此角度,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最先出现的史体是强调时间线索的编年体,同样,为什么小说尤其是早期的小说大多追求以时间进程为线索的有头有尾的叙述。在众多口语载体中,言论的、义理的、学说的、事件的或故事的,能使时间线索发挥最大作用和最易融进组织有机体之中的,莫过于后者。
然而,不可否认,言论的、义理的、学说的口语片断也有可能被产生出来。这些片断,最易滋生的社会环境在哪里呢?在士人集聚之处,如孔子聚徒讲学与策士们纵横捭阖的各种场所。而在民间,除了一小部分先民们感兴趣的生活知识和自然知识的口说片断之外,大规模产生并流行的口语片断则应是叙事性片断。简言之,民间的口语主体是叙事品。因此,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一文中,就中国小说的发生问题作过小说起于百姓休息时讲述故事的论断,这与《汉志》作者所勾勒的小说起于口语叙事的历史场景几无二致。小说之发生,与口语叙述事件或故事这一根本要素,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构成了小说发生机制的基础。若验之以相关事实,则我们可以看到保存至今的中国少数民族的史诗如《格萨尔王》、《江格尔》之类也是缘于口语并在口语状态中传闻叙事、代代相传的。西方小说的最初形成若可以追溯到荷马两大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那么同样也不难发现其与民间长久流传的口语叙事素材有着直接的联系。如果允许我们将口语叙事的作用范围稍稍从小说领域向外拓展一点的话,那么,中国历史著作的形成也与小说的发生有着共通的状貌。但是,史书和小说的根本分野之点,在下述的第三条标准,而在这里,以叙事性标准来衡量,这两者并无明显之分。
《诸子略·小说》所著录的十五部小说,学术界已明确认定的四部“近史”小说即《周考》、《青史子》、《天乙》和《臣寿周纪》,自然具有叙事性。值得我们作出重点说明的是“似子”小说和方士小说这两类,是否具有明显的叙事倾向。
我们得首先承认这样一个前提,即“似子”小说和方士小说不能排除含有一定的言论和介绍性成分,这是由它们的类别倾向和用途所决定的。严格意义上的诸子书是为了表明一家的立场和言论而作的,说理是其基本的言语方式,有些故事形态如神话、传说、寓言和民间故事的出现,是为说理而服务的,在篇幅、文字上并不占多数;而方士书则以介绍神技仙界为目的,即使偶或用些故事,也只不过是为了渲染和说服之用,同样不占多数。但是,与被著录在《汉志·诸子略》其他九家、《汉志·数术略》和《汉志·方技略》中的这些严格意义上的诸子书和方士书所不同的是,这些被《汉志》作者视作为“小说”的作品,除了在民间性标准上可与前者划出界限之外,在叙事性标准上是否也同样如此呢?
“似子”小说七部,即《伊尹说》、《鬻子说》、《师旷》、《务成子》、《宋子》、《待诏臣饶心术》和《百家》;方士小说四部,即《黄帝说》、《封禅方说》、《待诏臣安成未央术》和《虞初周说》。在这些作品下,《汉志》作者所加的注言,确实没有类似于对“近史”小说作品所作出的“考周事也”、“古史官纪事也”等明确的叙事性提示。尽管如此,作者仍然在这些注言和篇名上给我们留下了讨论的线索。一是关于语言方面的三条“浅薄”和“非古语”的提示,对此,我们认为这些提示不仅表明作品使用了无法与古雅的士人语言相提并论的民间语言,而且更重要的是,作品使用的是在民间语言中占主导倾向的口语,而口语与叙事的直接联系则已如上述;二是关于内容方面的“似依托也”、“后世所加”、“似因托之”、“迂诞依托”几个注言。这里所谓的“托”、“加”等字,表明小说作者依托古代有名的人物黄帝、伊尹、鬻子、师旷等人而对其言其事有所附会增生,以致模糊了古人对他们的原有印象或古书对他们的实录式记载,表现出小说化的塑造人物的倾向。但是,我们知道,无论是“托”、“加”也好,还是对人物的初步塑造必须具备的基础也好,事件或故事总是比言论或情况介绍在倾向上更占优势;三是在全部《汉志》小说中,以“说”来命篇的只有五篇,而这五篇全部出现在这两类小说之中,而小说之“说”与叙事性有直接的联系⑨。上述三条来自作品注言中的证据,若为孤证,则难以充分说明《汉志》小说的叙事性,尤其是后两条,恐怕连确认这些作品是否为小说都很困难。但是,这三条证据集而互证,再加上我们在下面所要讨论到的关于这两类小说佚文情况的说明,则论证的结论必然导出《汉志》小说的叙事性特征。
这两类小说,有的存有佚文,有的已全佚。从分散于各篇作品中的佚文情况来看,叙事性、言论性和介绍性文字兼或有之。由于是佚文,我们就无法依据这些文字哪怕是以叙事性为主的文字来得出这些小说在整体上具有叙事性的结论。然而,如果我们考虑到这样一个因素,就会对这些小说的叙事性有个恰如其分的估价了。这个因素就是:当小说被古书尤其是佚文所出的众多子书所采用之时,必然会对其内容有所节略和选择,而这种节略和选择必然出自古书尤其是子书自身的内容需要及其表达形式的要求,被删削不用的恰是最能体现小说本体特征的叙事性成分。在发生期小说中,《燕丹子》尚存,而其被众多古书所引用的文字也随同这些书籍本身被保存了下来,两相对照,我们就能发现,古小说被他书所采用或引用之时,小说性受到了严重斫伤,在被节略而用的文字里,小说的叙事况味被减低至微而又微的地步。这种情况,也同样体现在类似于典故、成语、格言、谚语和语录等对其所出之神话、传说、寓言、民间故事等“母体”的大幅度“缩水”。一般而言,古书互用时,小说往往对来自于他书所选用的部分作踵事增华式的铺写,而他书则往往对来自于小说所选用的部分作删繁就简的处理以至于仅存轮廓。因此,当我们在考察《汉志》中的“似子”小说和方士小说的叙事性时,若考虑到这种古书互用的情况,那么,不以佚文为主要依据但又不弃佚文,就是一种较为可取的方法了。
三、小说的一定程度的虚构性标准
对小说的一定程度的虚构性标准的认定,也同样体现在《诸子略·小说序》之中。作者引孔子的话⑩,认为小说“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又认为“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这些话语在持有保留意见的前提下,对小说的作用作了某种程度的肯定,但保留性意见还是占了主体,故而在《诸子略序》中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将小说正式排除于诸子中“可观者”之列。分析《汉志》作者对小说的这一认识倾向,一般认为,其依据可能有这样三点:一是语言方面的问题即“浅薄”,二是思想倾向的问题,三是内容不真实的问题即虚构性。
对于第一点即语言“浅薄”,我们通过对《汉志》所有著录篇目下的注言的考察,发现专门指出语言问题的,《诸子略·小说》有三条,《诸子略·杂家》有一条,此外则均无。可见,小说中的语言“浅薄”和“非古语”确实引起了作者的注意,这源于儒家的尚文传统。《说苑·敬慎》载:孔子读《黄帝金人铭》曰“此言虽鄙,而中事情”(11)。由此见出孔子尚文,故鄙此铭。持坚定的儒家经学立场的刘、班诸人,是不会不注意到小说中的语言问题的。然而,尽管存在着这一问题,而且显然引起了作者的反感,但若仅此一点,料尚不会将小说排除于“可观者”之列。这一推测,从孔子对《黄帝金人铭》尚持肯定的态度中就能推演出来。因此,语言问题还不是最主要的。
对于第二点即思想倾向的问题,依笔者的看法,这是不能成立的,其根据在于《汉志》作者在尊崇儒家“六经”的前提下,对别的诸子八家(除“小说家”)在思想倾向方面所持的宽容态度。《诸子略序》有言:“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于此可见作者对各有“蔽短”的诸子所持之基本态度。
对于第三点即内容虚构性问题,这才是最为主要的。刘向把自己所整理的“浅薄不中义理者”命名为《百家》,而班固则将此增入于《诸子略·小说》,但将刘向另外的著作和整理品增入于《诸子略·儒家》,就可见其小说标准。在此,源于民间性的内容“浅薄”是一条理由,而另外一条则是“不中义理”。这个“义理”是什么呢?我们认为,这指的是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特别发达的一种表现形式即历史所具有的真实性原则。虽说从后人来看,史籍不乏诗心和文心,但在古人那里,史学最讲究信实有据,其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刘歆《七略》曰:“尚书,直言也。”《六艺略·〈春秋〉序》曰:“(孔子)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六艺略序》曰:“《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上述引文中,刘、班诸人针对《尚书》和《春秋》发表了对史书本质特征和史书写作要求的看法,这种看法就是“直言”、“据行事”、“仍人道”、“论本事”而不“失其真”,只有达到了这种标准和要求,史书才会立于不朽的“信之符也”的地位。史书是叙事体,对史书的这种看法会直接影响到同样为叙事体的小说。故而,小说“违实”的虚构性才会导致《汉志》排除小说于诸子中“可观者”之列。这表明了作者轻视小说的态度,但似乎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他们对小说特性和小说标准的一种明确认识。此外,作者在《诗赋略序》中针对乐府歌谣而下的基本评价“感于哀乐,缘事而发”,隐含着对于内容真实性的要求,可从另一侧面引申至他们对于小说内容虚构性的体认。
在《汉志》所著录的十五部小说的注言中,标有“依托”、“后世所加”、“迂诞”等评价的作品有五部,它们是《伊尹说》、《鬻子说》、《师旷》、《天乙》和《黄帝说》。这些用于评价的注言,明确指出了文本的虚构性。此外,《务成子》所注“称尧问,非古语”,从语言角度指出其依托性质。“近史”小说中的《周考》、《青史子》和《臣寿周纪》,作者不收入历史类的《六艺略·〈书〉》和《六艺略·〈春秋〉》,显见在刘、班眼里,这些作品有违史书据实而作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说明其虚构性。另外,《百家》已如上述。余下五部,《宋子》和《待诏臣饶心术》为“似子”小说,前者注言曰“其言黄老意”,可见其思想倾向属于道家或阴阳家;后者以其书名之意推测,其思想倾向当为演绎,如《诸子略·道家序》所说的“君人南面之术”。这两篇不被著录于《诸子略·道家》或《诸子略·阴阳家》,可见不同程度地存有如《诸子略·阴阳序》所说的“舍人事而任鬼神”,以及如《诸子略序》所说的“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的倾向,必在其原属思想学术体系之上有所增事衍说。它们的佚文虽不可考,但以此分析,其虚构性还是存在的。另外三部《封禅方说》、《待诏臣安成未央术》和《虞初周说》为方士小说,它们的虚构性从两个角度可据以分析:一是有两部以“说”命篇,而“说”义在具有叙事性前提下绝有可能导向于主观性较强的杜撰和虚构(12);二是方士书依其思想倾向当入于《方技略·神仙》,而这些方士小说不入于此,盖因其有着《方技略·神仙序》所指出的“或者专以为务,则诞欺怪迂之文弥以益多,非圣王之所以教也”的倾向,其虚构性是较为灼然鲜明的。
以上立足于《诸子略·小说序》和十五部小说的大体情况,较为全面地论证了《汉志》的三条小说标准,即民间性、叙事性和一定程度的虚构性,它们同时也是发生期小说的内在规定即小说性的完整体现。在确认某部作品是否为小说之时,三者缺一不可,都是必然条件。至于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简单地说,在中国小说发生期之内,是民间性决定了叙事性和虚构性,但是,在决定与被决定之间,存在着一个中介环节,这就是口语传述。在文字尚未大量出现并且书写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民间作品主要依靠口语来产生和传播,具有虚构性的故事是寄生于口语传述基础之上的。用口语来传述故事,其时代下限离我们现在较近,而其上限则离我们非常遥远。讲述故事尤其是讲述作意好奇的故事,当出于人的天性。在古人能够用口头语言来表情达意之时,可能就会产生最原始的故事,而这些故事,长久地滋生和流传于民间。因此,如果我们把口语传述作为小说发生的最主要因素来看,或者视之为在民间环境下的小说发生机制,可能离事实真相不会太远。口语传述的故事是小说形成的前提,它本身不是小说,只有当用文字载之于楮墨,小说才渐渐形成,因此《汉志》作者才会提示我们注意“缀而不忘”这一由口语走向文字的最后环节。
《汉志》的三条小说标准构成了其小说观念的主要基础。民间性标准,相当程度地隐含了刘、班诸人对小说发生的认识;叙事性标准和一定程度的虚构性标准,则体现了对小说本体以及小说不同于其他文化表现形式的认识。
四、小说家的人员构成
《诸子略·小说序》所谓“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云云,这一“小说家”,从其字面意思来理解,指的是在古代从事小说活动的人员,它不是内涵较为狭窄的“小说创作者”所能代替的。《诸子略·小说序》明确指出在先秦至西汉末即小说发生期,小说家是由三类人员构成的一个集体。
第一类人,是小说活动中的口语创作者和传播者,即作者所言之“道听途说者”。他们的社会身份是生活在民间的普通百姓,通过社会活动和劳动实践,出于各种需要和天性,包括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一文中所言之“到休息时,亦必要寻一种事情以消遣闲暇”,广泛吸取了世代相沿和累积渐成的神话、传说、寓言和各种民间故事,根据他们的理解,凭借着他们所要表达的想法,搬用、附会或新创各类口说故事即“街谈巷语”,从而形成了小说发生的文本基础和小说状貌的民间色彩。这类人往往既是口说故事的创作者,又是这些故事的传播者。在传播过程中,同样是出于各种需要包括出于作意好奇的天性,对所接受的即“道听”的故事做不同程度的增删和改变,以至于一个故事母本在实际流传过程中出现和形成几个面目似是而非的口说版本。从这意义上说,传播活动其实也是创作活动中的一部分,最初民间的创作者和传播者的身份很有可能是混而为一的,只不过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
第二类人,是小说活动中的初步整理者兼文字记录者,即作者所言之“闾里小知者”。他们的社会身份也是民间人士,与《诸子略·小说序》所说的“君子弗为”之“君子”即“士”有着较为明显的身份之别。他们能识文断字,有一定的知识和见解,但水平都不高。然而,他们对流传在自己身边周围的各种口说故事,有着浓烈的兴趣和高昂的热情并且怀有珍惜之心,故而能在当时书写虽已出现但书写条件仍然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用文字将这些口说故事记录和整理下来,以免时光的流水冲走了这些令他们感慨沉迷的不定型的口说故事。这些过程,即《汉志》作者所谓的“缀而不忘”。在记录和整理活动中,他们既是鉴赏者,同时必不可免地又是小说的创作者之一。他们根据对远古年代的理解和对现实境况的感受,加进了对故事的改编成分。对小说由口语状态转化为文字状态,这些整理者和记录者作出了积极而有效的贡献,并且他们从事这种小说活动的目的性比起下面所分析之“稗官”,可能要纯粹一些,可能更不知自己在从事的是一种“小说”活动。一般来说,经过文字记录和整理的小说文本,比起其原型即口说故事,在长度、篇幅和生动性上会受到削减和影响。
第三类人,是小说活动中的官方参与者,即作者所言之“稗官”,行使了对民间流传小说的采集和拣选工作。出现在《汉志》中的“稗官”一词,因语意过于模糊,因而自《隋书·经籍志》则弃而不用。但在中国小说史研究界,稗官问题一直是争议的焦点和中心,现当代学者如余嘉锡、袁行霈和潘建国,皆有辨析其义的文章(13)。诸说或有不同,但均是从某一角度依据史料来理解“稗官”语义,不妨共存。稗官在周代王官系统和汉代官员阶层中的确指身份虽较为模糊,但在小说活动中的角色和作用,却还是相对清晰的,诸说对此亦有一致之处。稗官在民间收集各种载体的小说,口语和文字兼或有之。虽说《诸子略·小说序》的意思倾向于他们所收集的是经过“闾里小知者”记录和整理过后的文字稿,但根据春秋时采诗官员收集口语诗歌的沿例,也有可能收集仍存留于口语状态的故事,这样,他们也就肩负了部分文字记录的职责。然而他们是官家所派,采集的目的是使“王者欲知闾巷风俗”(14),有着较为明显的政治教化色彩,因而,采集的过程其实就是拣选的过程。在这过程中,各种口说故事和文字小说,或黜而不采,或采而改动,于小说的整体和原貌是会带来相当程度的损伤的。另外,在中国小说发生期所出现的小说,绝非仅仅是被稗官所采而保存在官家书库中的那一部分,汉代结束战争后,自民间几次大规模收集书籍就是一个例证。《汉志》所著录自先秦迄西汉末的十五部小说,何啻冰山之一角!然而,正因稗官的采集和官家的保存,在某个相对历史时期内,使一部分民间小说得以暂时流传下来。
在小说发生期内,上述对这三类参与小说家的人员的分析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在某个历史时期,或在某种特殊情况下,都有可能出现超出于这种一般情况之下的特殊情形。比如杜贵晨就根据《庄子·逍遥游》和《孟子·万章上》的记载,推测“西周以后就出现了普通士人写作小说的情况”(15);又如李剑国于民间小说之外,把历史遗闻逸事之类作为小说的另一源头,从而把史官也归入到小说家之中(16)。诸如此类,均有超出于《汉志》所提供给我们的原生历史场景之外的合理想象和坚实论证,构成了中国小说史研究向前发展的一层又一层台阶。
通过对小说家中三类人员的情况分析,也大致表达了我们对中国小说发生期内的小说创作、小说传播、小说整理和小说采集等一系列活动的看法。出现明确的小说创作者和整理者,从《诸子略·小说》所著录的情况看,是始于汉武帝时(17);而在此之前,均未载作者,其实这些作者就是我们已经提到的三类人。他们不自觉地围绕着某些文本,跨地域、跨时段地以集体性的劳动,共同促成了这些被史志所载的最早一批小说的出现。
注释:
① 另一说认为是在唐以前。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参阅拙文《中国小说史的起点问题——小说发生期研究举要》,载《文学遗产》2004年第4期。文章在列举代表性观点时,错误地将王齐洲的观点归于“魏晋说”,实际上应归于“汉代说”,特此致歉。
② 《汉志·总序》如淳引用刘歆《七略》所作的注言。见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02页。
③ 《春秋左传正义·闵公二年》,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88—1789页。
④⑤ 袁行霈:《〈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考辨》,载中华书局《文史》第七辑(1979年)。
⑥ 潘建国:《“稗官”说》,载《文学遗产》1999年第2期。
⑦ 汪祚民:《〈汉书·艺文志〉之“小说”与中国小说文体确立》,载《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6期。
⑧(16) 李剑国:《小说的起源与小说独立文体的形成》,载《锦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⑨(12) 拙文《〈汉志〉“小说”考》,载《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
⑩ 在《论语》中,这是孔子的弟子子夏的话,但能代表孔子的思想。
(11) 刘向:《说苑》,见向宗鲁《说苑校证》,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59页。
(13) 余嘉锡:《小说家出于稗官说》,载《余嘉锡论学杂著》(上册),中华书局1997年版;袁行霈:《〈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考辨》;潘建国:《“稗官”说》。
(14) 《汉志·诸子略·小说序》如淳注言,载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45页。
(15) 杜贵晨:《中国小说起源于民间故事说》,载《传统文化与古典小说》,河北大学出版2001年版,第108—109页。
(17) 《待诏臣饶心术》、《待诏臣安成未央术》、《臣寿周纪》和《虞初周说》,这四篇标明了作者或收集整理者。这些小说篇名,也可写成《心术》、《未央术》、《周纪》和《周说》。另外,《百家》的整理者为刘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