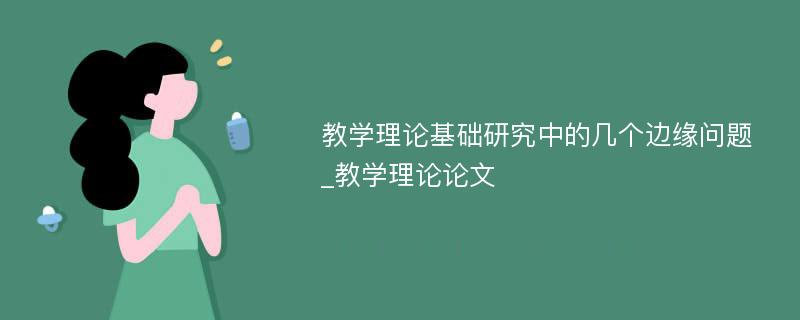
教学论基础研究的几个边缘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边缘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出教学论基础研究的边缘问题,不是要讨论重修教学论的学科边界,也不是要讨论借鉴边缘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教学论。这里说的“边缘”,是指学科边界的边缘,研究关注的边缘,这里提出的“问题”,是指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还值得研究的问题。我认为在教学论范畴中或教学论学科边界内,还有些基础性的问题没有引起研究者的充分关注,或者是被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它们是被边缘化了的教学论基础研究的问题。
一、教学论比较研究中谁与谁比较的问题
教学论研究必然涉及域外教学论和中国教学论(在教学论没有明确地称为教学论的时候,泛指中国教学思想),这之间必然存在某种形式的比较,比较研究因此是种常见的基础研究。但谁与谁比较,以谁为基准比较,不是认识层面的问题,而是评价层面的问题,这就会关系到价值判断与选择。如果价值判断与选择失衡,就可能造成评价失衡。
我们译介域外教学论,或者从教育史的角度研究它们的发展,这都很有意义。但要解决如何借鉴的问题,还需要进行域外教学论与中国教学思想的比较。但时下有些比较的办法值得商榷:一种办法是撇开中国教学思想,直接移植域外教学论。它用一句“中国起步较晚”代替比较,就把近现代以来在中国出现的借鉴了域外教学论的教学理论,认定为中国的教学论,中国教学论的发展,也就失了根基,呈现出天生幼稚的样态。未读《学记》就说中国自古重教轻学,不问《师说》就批中国的师道尊严,这可能是种文化虚无主义的办法。还有一种办法是把域外教学论与中国教学思想进行跨时空比较。它用一句“中国传统教学”涵盖几千年传承延续的中国教学,它拿中国的先秦与外国的近现代比较,拿孔夫子的思想与杜威比较,与现当代、后现代的教育教学思想比较。让孔夫子担当中国教学的一切过失,就像把江河污染的问题,统统归咎于三江源头,这样的比较,也不是尊重历史的办法。
这两种比较的办法有个共同特点,这就是以域外教学论为基准,把中国的教学思想拿来比较,而不是以中国的教学思想为基准,把域外教学论拿来比较。这是失衡的比较,失衡的比较有失公正,譬如人们讨论“教学责任”,就可以说“关于责任的研究中国起步较晚”,而中国先贤论“责”、论“任”的文献,没说“责任”就可以被虚无。孔子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难道可以因为没说“启发”被虚无?所以谁与谁比较,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我们研究域外教学论,如果把相同历史时期的中国教学思想,拿来进行比较,或许会比较出差距,但也能比较出差异。差异未必都是差距,还可能是种文化特色,这有益于我们有的放矢地借鉴域外教学论。譬如近年来人们提出一个问题:20世纪上半叶,中国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大师?我认为这个让人困惑的问题,尽管可以有多种解释,但从教育和教学的角度看,可能就与缺乏这样的比较相关。那时候出现的大师,人人学贯中西,这就绝不只是因为他们的觉醒与觉悟、进新学堂与赴海外留学,还可能有中国传统教学思想的原因。他们拥有的深厚的国学功底,是否也让他们获益呢?换句话说,他们之成为大师,是否也曾受惠于中国传统教学?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可以让我检讨个人曾经的研究,20年前我写《困惑与抉择——20世纪的新教学论》,[1]起初是想把20世纪的中国教学论拿来比较的,后来还是把它删掉了。那时我认为研究域外教学论,不宜把同时期的中国教学思想拿来比较,我顾忌这样比较会比出差距,没考虑到比较出文化差异和文化特色,低估了这些特色对借鉴域外教学论的不可替代的价值,现在想来,就有些许的遗憾了。
我们是否可以换一种思考路径来比较?陶愚川先生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中国教育史,他写的《中国教育史比较研究》,[2]不只是在中国教育范围内比较,而是也与相同历史时期的外国教育比较,他跨越空间,但不跨越时间地进行比较,不是要比较出差距,而是比较出了文化差异。我们是否可以不以域外教学论为基准,直接研究中国的教学思想、教学论?研究中把域外教学论拿来进行比较,无须关注是否能比较出差距,只要公正对待文化差异,尊重自己的文化。我认为域外教学论之于我们自己的教学思想、教学论,应该有个本与末的正常关系,它得“化为本土的”才能存活、才能被应用。无本之木很难存活更妄论长久,因为“本土”的价值不只是根本,而是它赖以存活的厚重的土壤。
我们是否还可以换一种思想方法来比较?我研读古典儒学的时候,曾接触过一些当代学者研究儒学的文献,文献中诠释的儒学,读起来很新也很深刻,隐约有一种译自西方的哲学的艰涩。显然,它们是用西方哲学或思想方法诠释儒学,而不是用中国哲学或思想方法诠释儒学,这虽然很新也很深刻,但淡化了文化特色。时下的教育学、教学论研究中,也有类似的情况,这就是用外国的哲学或者思想方法,诠释中国的教育和教学,还用以指导中国的教育教学实践,这种研究,用研究者们自己的话来说,称得上是种研究“范式”了,它让教育学、教学论很新也很深刻了,但也淡化了文化特色。许多实践者说他们读不懂这样的理论,这固然可以敬而远之,但许多这样的理论也说不清实践,乍读起来它们像是把简单问题说复杂了,读懂之后才知道,它们是把复杂问题说简单了,这如何可能指导实践?
读许嘉璐先生的《卸下镣铐跳舞——中国哲学需要一场革命》,[3]很受触动,甚至感到有些震撼,因为许先生主张的革命,就是要换一种思想方法。中国的学者们如果不再“戴着镣铐跳舞”,用外国的哲学或思想方法,把中国的传统文化研究得很深刻,而是“卸下镣铐跳舞”,用中国的传统哲学或者思想方法,解读自己的文化,推而论之,也用这样的思想方法,试着解读外国的传统文化、外国的教学论,来进行域外教学论与中国教学思想的比较研究,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谁与谁比的问题。
二、教学论的生存环境与适应人群问题
任何教学论都有其得以生存、生存其中的文化环境,也都有个为着哪些人适应哪些人的问题,生存环境和适应人群,这是个基础性的问题。在教学论借鉴、移植过程中,环境变了、适应人群也变了,这个问题就会百倍复杂起来。不同的域外教学论在中国的遭遇不同就与生存环境相关,而它们究竟适合哪些人,就更是个与生存攸关的问题。提出这个问题,主要缘于对文化差异比较的思考,也感念于弱势群体的“人”的被漠视。
我们在中国教育史、教学史中读到的域外教学论,主要是有关译介、传播、学习域外教学论的史实,但要解决如何借鉴的问题,还需要研究它们“转化为本土的”的事实,这就是它们何以存活,以何存活?所以必须弄清它们的生存环境与适应人群。这是个历史问题,也是个当下的问题,我们无论从哪个国家或地区引进教学论,都存在同样的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较多关注理论自身的先进性,甚至只是新颖、前沿,也会关注意物质性教育资源环境差异,但对政治经济制度差异、文化差异缺乏关注。譬如20世纪二十年代引进杜威的教育教学思想,它的生存环境与彼时的中国有哪些差异?而时下人们把世界范围内的课程与教学理论、模式、方法甚至课程标准、教材简单地移植过来,也很少见到有关其生存环境的审慎研究。还有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我们也不同程度地忽视了适应性人群的研究。20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多数学龄儿童与学校教育无缘,我们引进杜威的教育教学思想,是否考虑了与学校教育无缘的人?当下我们借鉴域外教学论,拿来改革基础教育,也有类似问题,如今已经很少与学校教育无缘的人了,但基础教育要均衡,学校教育有差异,是否从弱势群体学校、教师和学生的立场来讨论问题,就成了必须关注的新问题。
这两个问题的共同特点,是借鉴或引进域外教学论忽视了社会适应和学生适应,这是从域外理论出发改造中国实践,而不是从中国实践出发借鉴域外理论。所谓水土不服的困扰,从来就是双向的,既是理论能不能存活的问题,也是实践能不能接纳它的问题。引进一款外国新车,都需要审慎地研究中国路况、中国人驾车习惯、中国受众的承受能力等,更何况课程或者教学?所以域外教学论的生存环境与适应人群,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研究域外教学论的生存环境,我们欠缺的是文化差异比较研究,这就要研究它们的文化土壤,也研究我们的文化土壤,在比较中寻求文化契合,这是它得以存活的根本。从历史的角度看,我们该知道,域外教学论在中国的生存与发展,文化差异让它遇到过什么样的艰难?譬如杜威、凯洛夫的教育教学思想在中国,它们的遭遇不一样,这就不只是人们肤浅认定的政治原因,还有个中美文化差异、中苏文化契合的原因。朱小蔓先生谈师范教育改革,曾提到她与俄国学者交流,俄国学者对我们借鉴美国的作法不以为然,他说:你们可以不学习俄国,但还可以借鉴法国。显然,这位俄国学者知道中美文化有差异,而中俄、中法文化能契合的道理。从当下情况看,域外教学论在中国,也不是说句“地球村”或者“与国际接轨”就能生存与发展的,这不是个简单的谁落后谁先进的问题,文化土壤合适,不像用“洋快餐”吸引青少年那么简单,何况“洋快餐”为了生存与发展,也懂得开发中式新款。这更不是个简单的物质性教育资源配置问题,我们有些豪华的薄弱学校、只知道炫耀应试“状元”或成绩排名的“优质教育”学校,它们的物质性教育资源配置一流,为什么还把许多域外教学论思想,弄得像是一件“皇帝的新衣”?这些教学论思想在中国生存与发展,为什么会遭遇到如此的尴尬,是否还有些深层问题值得研究?
研究域外教学论的适应性人群,我们重视打造名校或优质教育学校,名师或优秀资质教师,也重视它们或他们的适应性,但有关弱势群体的适应性研究还相对欠缺,这在基础教育、义务教育中,无疑是个误区。国际公认的优质教育,关注的是教育公平、无歧视、培养负责公民,所以更关注弱势群体的适应性。从历史的角度看,我们该知道,哪些学校哪些儿童曾受惠于域外教学论,而那些与学校教育无缘的学龄儿童,彼时的生存境遇怎样?撇开他们讨论基础教育、义务教育问题,是一种根本性的缺失。有些学者研究民国教育,研究课程、教材与教学,却不研究与学校教育无缘的学龄儿童,这样的研究撇开了它的普适性,是舍弃了它是否适合基础教育、义务教育的根本特征。从当下情况看,域外教学论在中国,不研究它的适应性人群的差异,或者只关注优势群体的适应性,它也不可能有生命力。譬如我们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从国外译介进来许多课程与教学新理论、新思想、新模式,甚至还有移植的教材,但我们也能感受到,许多弱势群体学校中的教学实践,与它们不相关,离它们很遥远,甚至根本就够不着它们。对此,说几句理论脱离实际的空话,解决不了问题,批评实践者落后,也无济于事,因为这未能触及问题的实质,未能摆正适应性人群的位置,遮蔽了教育不公正、有歧视的问题。在学龄儿童100%拥有了接受公平教育的权力的情况下,域外教学论在中国的生存与发展,它是否具有普适性,它是否适合弱势群体学校、教师和学生?这是不能回避的问题。而他们在学习、实践、评价这些理论的问题上,是否拥有平等的话语权,同样是不能回避的问题。在基础教育、义务教育中,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究竟该依据哪些适应性人群,借鉴从国外译介进来的课程与教学的新理论?
三、社会教育机构、家庭中的学校教学延伸问题
学校教学与非学校教学,这是两种不同的教学环境。所以有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的教育类分。如果不同教学环境中的教学职责不清楚,泾渭不分明,清浊也就不容易分辨了。我提出这个问题,缘于对存在于非学校教学环境中的学校教学的思考,也就是存在于社会教育机构、家庭中的学校教学,我用“延伸”这个词,是把它置于学校教学论的边缘来研究,它也可以说是非学校教学论的边缘。
我十年前写过几篇有关家教的文章,其中第一篇就是以《家教:一个教学论边缘的实际问题》[4]为题。我说的家教,特指在家庭中发生的学校教学延伸行为,不是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并列意义上的家庭教育。同样,这里说的“社会教育机构”中的教学,指的是在社会教育机构中发生的学校教学延伸行为,不是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并列意义上的社会教育。从教学论的角度看,这种教学行为存在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它从总体上看不健康。我十年前就认为家教是学校教学的病态延伸,如今在社会教育机构、家庭中发生的学校教学延伸行为,比十年前更有发展,它们多数以助推“应试教育”为目标,鲜有以实施素质教育为目标的,所以还是病态延伸行为,只是功利性更赤裸、对学校教学的负面影响也更大。诚然,我不是要完全否认社会教育机构、家庭中发生的学校教育、教学延伸行为,那些不以推助“应试教育”为目标的教育行为,如拓展训练、艺体特长培养、生存生活教育、劳动教育等就是积极健康的。另一个问题是,它被教学论研究边缘化了。它是在社会教育机构、家庭中发生的学校教学延伸行为,它不是理论意义上的社会教育、家庭教育,所以不属于它们的研究范畴,它也不是理论意义上的学校教学,也不为学校教学研究所关注,更少有人从教学论的角度研究它,所以是被边缘化了。这种边缘化是一种普泛意义上的不作为,这种不作为让它得以宽松,这种宽松释放了教育的选择性,也酿成了许多教育问题。
这都是学校教学问题,都是以学校教学为研究对象的教学论问题,但它们又是发生在学校之外、学校教学研究之外的问题。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可以问责,但也可以推诿责任,可能增进健康,但也可能延伸病态,具有很突出的或然性。时下的社会教育机构适用市场需求而盛况不衰,家庭教育则为满足个人愿望而不遗余力,教学论该如何有所作为?至少它可以就或然性提供些解释,解释它的健康,也解释它的病态。
社会教育机构、家庭中的学校教学延伸,如何才能健康?我认为,它如果要支持学校教学,成为学校教学有益的补充、学校课程与教学改革积极的推助,可能需要有个颠覆性的改变。教育要全面实施素质教育,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社会教育机构如果是健康延伸学校教学,就该更多关注弱势群体、学业困难或后进的学生,更多关注弱势的课业、学校教学不能充分满足学生的课业。日前媒体报道,有贫困大学生组织志愿者群体,为弱势群体的学习困难生义务辅导,也有艺体专业大学生志愿者,到偏远的农村学校辅导小学生足球、合唱,这就值得倡导。而有些社会教育机构,组织拓展训练、举办中国武术、跆拳道训练班、举办不以助推“应试教育”为目标的音乐、美术训练班等,这也积极健康。家庭教育如果健康延伸学校教学,就该更多关注合适的家校合作,关注集体教学不能满足的个别教学、辅导子女在学校教学中的弱势课业。尤其是关注孩子诚实守信的品质、勤俭节约的习惯,培养其生活自理能力、掌握生存生活必需的劳动技能等。诚然,这样的问题与解释,这样的建设性研究,在当下看来或许有些苍白,因为在社会教育机构中、家庭中,学校教学的病态延伸行为依然强势,而健康延伸的教学依然单薄,这甚至还只能是一种期待。
所以我们更迫切需要研究的,是社会教育机构、家庭中的学校教学病态延伸问题,这里的延伸是种存在的事实,但病态是个隐蔽范畴。因为说一句市场需求,社会教育机构就可以理直气壮,说一句可怜天下父母心,家庭就仿佛合情合理。但我坚持认为,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正在成为我们的基础教育、义务教育健康发展的隐蔽的结症。
其一,它可能阻滞基础教育、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它从总体上趋势上看是支持优势群体、强化优势课业、助推恶性考试竞争的,这就势必让贫困地区和薄弱学校的学生更加弱势,因为无论从物质性教育资源还是精神性教育资源来看,这些学生在获得学校教学延伸行为方面,通常也是处境不利的弱势群体。其二,它可能助长唯考试科目的教学,弱化学校全面课业的质量,弱化人的全面发展,因为它可以不受学校教学规矩约束,以家庭或学生的自愿选择为借口,加重所谓的课业负担,这种负担的实质只是“考业”负担。其三,它可能建立起一种社会教育机构与家庭之间的功利性教学交换关系,异化学校教学的价值。许多高价辅导班,就是利用家长的善良和不智谋取暴利,它可能不择手段地追逐评价符号,甚至把学校教学也导向隐性舞弊(帮助学生获得与实际水平不符的考试成绩)的歧途。其四,从教学变革和规范办学来看这种学校教学延伸行为,它可能是学校教学健康发展的顽固障碍。如学校教学三令五申想要控制的各种补课,往往正是这种教学的优势特色。而各级各类教育主管部门都在倡导规范办学,但谁来研究社会教育机构、家庭中的教学规范?人们说教育问题不只是学校和教师的问题,那么,谁来研究并且解决其他问题?
四、教学论研究中的儿童理解与学科理解问题
教学要理解不同的对象,区别不同的学科,这几乎是种常识。研究高校教学论的不懂中小学教学,研究语文教学论的不清楚数学教学,它们都有自己的学科范畴,这几乎也无可厚非。但如果模糊了学科范畴,无视不懂或者不清楚,就把大中小学的学生、文理艺体的课程混为一谈,这样的研究就让人觉得有些扑朔迷离了。而这样的研究,如今在许多著作论文中都能看到,只是它们的标题往往都有清楚的学科范畴,人们又不多用心考量它的内容,就把这个问题边缘化了,这也就成了一个被遮蔽的问题。
我们的高等教育、基础教育、学前教育都各有各的教学论,我们也有与学校课程相应的各学科的教学论。人们单知道过细的学科分化,有可能造成学科壁垒,但忽视了各学科鸡犬之声相闻,还可能造成学科“混搭”。如今是个信息时代,混搭或许也是一种时尚,但如果望文生义不求甚解,就可能造成理论的不和谐或实践的尴尬。一个问题是,许多研究不注意区分不同的教学对象,把中小学教学与高校教学混淆了。有些中小学教学改革,定位就像大学,精英人才、创新人才,这些大学也够不到的教学目标,竟然走进中小学了。而有些高等教学论研究,又毫不顾忌地引用普通教学论文献,并不考虑它们用在高校教学中究竟是否适应、如何变通才能适应?这不能不让人疑问,这样的研究如何处置教学实践?另一个问题是,有些教学论研究,忽视不同学科教学的特殊性,它们甚至让文科和理科共享同一种教学模式或方法,在基础教育改革中,就有研究者把外国的理科课程改革模式,移植过来改革中国语文教学,毫不关心它在实践中是否行得通?或者,研究者压根儿就没考虑教学实践?
这两个问题的共同特点,是模糊了教学论下位学科的学科边界,前者混淆了针对不同教学对象的教学,后者混淆了针对不同学科的教学。与其说这是个边缘问题,毋宁说这是个模糊了边缘的问题。这样的研究不被理论拒绝,显然是个理论脱离实践的问题,而这样的研究不被实践拒绝,就很可能是个实践以理论为装饰或巧饰的问题了。这让人深感忧虑,时下教学理论繁荣的形式,是否遮蔽了它实质的贫困?而有些黏附在教学改革或创新实践上的理论基础、理论依据、理论解释,是否只是些自欺欺人的标签、符号?
教学论研究如何尊重不同的学生?区别不同的教学对象?众所周知的因材施教,就是要区别对待不同的教学对象。而心理学者的研究,就更让教学论研究者汗颜,他们研究教育与发展,或者儿童发展,甚至以0~1岁半、0~3岁、4岁半之墙等,严格限定不同的研究对象。但我们有些教学研究,竟可以坦然漠视中小学生与大学生的区别,有位教授给博士生上课,就发现有些研究者主张的中小学教学改革新方法,应用于博士生似乎很适切。
譬如时下有关教学对话、话语权力的研究很多,就有研究者随意拿中小学生或者大学生的教学来举证。从教学实践来看,教学关系(不是泛指师生关系)中的教学对话,这在中小学生与大学生必然有区别。而话语权力与教学责任密切关联,中小学生与大学生能承担的教学责任不同,在教学实践中的话语权力因此也不同,这可能都要审慎的研究。再譬如研究教学中的书本知识间接经验、教学回归生活,这在中小学生与大学生也必然有区别,我们为什么帮助失学儿童回归课堂,鼓励大学生深入基层生活实践,这里的不同教学对象有何不同,是否需要审慎的研究?让人百思不解的是,有些教育学、教学论专业的年轻学者,热衷于凭借书本知识间接经验(尤其是译自外国的所谓理论前沿的)作研究,乐此不疲地用这种脱离教学生活实践的办法,写教学回归生活的文章,写批判书本知识间接经验的文章,就是不肯回归生活到田野里作研究。这是否也需要审慎的研究?
教学论研究如何尊重不同的学科?区别不同学科的教学?不同学科的教学论,原先叫学科教学法,研究者分散在不同学科群体里,从来就缺乏相互沟通,而教学论的基础研究,也不关注它们,这就把问题边缘化了。结果是有一种新教学模式或新方法,各学科都可以拿来用,也就避免不了牵强附会。当年布鲁纳提出发现法教学,就曾解释说它主要适合理科或科学,还说它不适合历史等人文学科,我们有些研究者偏要把发现法教学、探究教学拿来实践中国语文教学,这如何能够行得通?这里应该有些深层问题值得研究。
有记载说,钱伟长先生1930年考清华,唯有国语、历史两科考了满分。这不只是让我们疑问这两科考满分的学科与这位科学家研究的科学有何关系,还让我们疑问他的这两种学问分别是通过何种教学获得的,这两种让他获得不同学问的教学究竟有什么不同的奥妙?这里的奥妙是否值得比较教学实践研究?毋庸讳言,近几年的课程与教学变革中,中国语文教学可能是个最活跃也最让人不踏实的学科,在我看来,中国语文、历史教学与外国的同样学科就有根本性的文化差异,而与他们的理科或科学教学更有天壤之别。前文提及的民国大师们的国学功底深厚,是否与此相关?记得曾见过梁启超、胡适推荐的必读书目,相信它必定让今天的学者望洋兴叹,我们何必疑问当代为什么出不了大师?
注:
[1]杨启亮.困惑与抉择——20世纪的新教学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
[2]陶愚川.中国教育史比较研究[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
[3]许嘉璐.卸下镣铐跳舞——中国哲学需要一场革命[J].文史哲,2009(5).
[4]杨启亮.家教:一个教学论边缘的实际问题[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