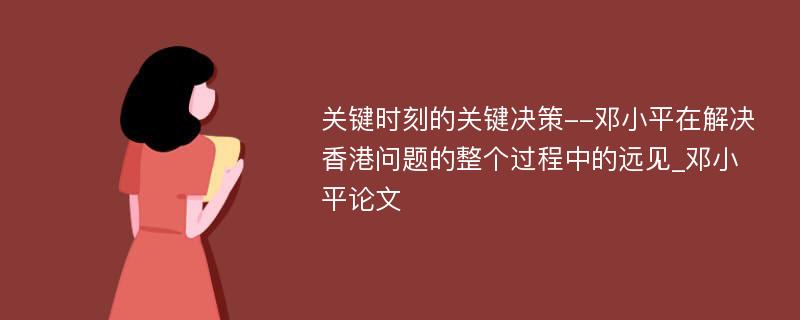
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的关键决策——邓小平在解决香港问题全过程中的远见卓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关键论文,远见卓识论文,香港论文,关键时刻论文,过程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4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674(2005)04-0000-04
众所周知,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战略构想原本是用于解决台湾问题的,但由于它体现了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原则[1] 第3卷(P87),当解决香港问题的条件成熟时,它也就顺理成章地被实施于解决香港问题上了。但要使英国人接受“一国两制”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就意味着解决香港问题的谈判必将是艰巨的和曲折的。但在邓小平的领导下,特别是他在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的关键决策使得谈判朝着中方的既定目标前进。
一、“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邓小平在香港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从一定意义上说,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主权被践踏、内政被干涉的屈辱历史。从历史中走来的邓小平对此有着切肤之痛后的刻骨铭心。因而,他对捍卫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极为敏感,尤其是在解决香港问题上表现十分突出。
(一)明确收回香港的时间
1982年9月,“铁娘子”撒切尔夫人挟着马岛(马尔维纳斯群岛)胜利的余威来到了中国,满心以为可以用同样的强硬态度来对付中国人,也可以马到成功。柯立达在其回忆录中说:“她(撒切尔夫人)是摆开一种好斗的和不合作的(combative and uncooperative)姿态来处理香港问题的。她刚刚取得了福克兰群岛(即马尔维纳斯群岛)的经验,……而香港从表面上看同福克兰群岛又具有某些相似之处:英国的另一处远方的殖民地[2] 又受到了威胁,英国根据法律和条约所享有的权利至少在香港的一部分领土上仍然有效,我们的外交官员又在鼓吹过早的投降……。”[3] (P174)但中国不是阿根廷,香港更不是马尔维纳斯群岛。[4] (P259,P489-490)同时令她意想不到的是,她的谈判对手却是被誉为“钢铁公司”的邓小平。
9月24日邓小平会见了撒切尔夫人,由于她有备而来,故会谈一开始就说,三个不平等条约在法律上是有效的,不能单方面废除;要保持香港的繁荣,就必须由英国来管治。如果中国宣布收回香港,就会给香港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和后果;中国如果要搞四个现代化,就离不开香港的繁荣,就离不开英国的统治等等。听完这些荒诞逻辑之后,邓小平说: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一九九七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中国和英国必须在这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方法。“如果中国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所以,现在,当然不是今天,但也不迟于一、二年的时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这个决策。我们可以再等一、二年宣布,但肯定不能拖延更长的时间了。”[1] 第3卷(P12-13)但谈判的时间不能超过两年,如果时过两年,还达不成协议,那么中方也将单方面宣布自己的决定和政策。此外他还说:“我们还考虑了我们不愿意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十五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怎么办?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1] 第3卷(P14)邓小平的这番话给本存在很高心理预期的撒切尔夫人迎头一击[5] (P148),同时也为后来的中英香港问题谈判定下了基调。
(二)明确中央要在香港驻军
根据中央政府的基本方针政策,未来的香港特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但外交和国防则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这就意味着中央政府将从1997年7月1日起,向香港特区派驻适当数量的部队,负责香港的防务。但驻军不干涉香港的内部事务,特区的治安由特区政府自行负责,驻军的费用由中央人民政府负责。但英方却进行抗拒。对此,邓小平说:“既然是中国领土,为什么不能驻军呢?这是起码的主权的象征。如果连这点权利都没有,还叫什么中国领土?”[5] (P166)后来他又一次说:“除了在香港驻军外,中国还有什么能够体现对香港行使主权呢?”[1] 第3卷(P75)但他同时也明确表示:“我们派军队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而不是去干涉香港的内部事务。”[1] 第3卷(P58)
(三)明确“以主权换治权”的路不通
尽管邓小平在会谈一开始就宣布:中国在主权问题上是没有回旋余地的。但在前四轮的谈判中,英方仍心存妄想,[4] (P259)并打出所谓的“经济牌”、“民意牌”、“信心牌”,图谋“以主权换治权”。对此邓小平在1983年9月会见来访的希思时说:“英国想用主权换治权是行不通的,劝告英方改变态度,以免出现到一九八四年九月中国不得不单方面公布解决香港问题方针政策的局面。”[1] 第3卷(P388)并要求希思把这番话转告撒切尔夫人。正是由于邓小平以及中国政府在主权问题上的坚定立场,使得英方坚持的“以主权换治权”的荒谬主张不得不有所收敛。这样在第五、六轮会谈中,英方确认不再坚持英国管治,也不谋求任何形式的共管,并理解中国的计划是建立在一九九七年后整个香港的主权和管治权应该归还中国这一前提的基础上。于是从第七轮会谈开始,谈判纳入了以中方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方针政策为基础的轨道。
二、“制造混乱是很容易的”——邓小平对香港回归过程中过渡时期的担心
早在1982年邓小平就说:“我担心的是今后十五年过渡时期如何过渡好,担心在这个时期中会出现很大的混乱,而且这些混乱是人为的。”[1] 第3卷(P14)为此,他多次警告大家不要以为声明签订以后就什么事都没有了,总有人是不想认真执行中英联合声明的。为了减少担心,保证平稳,邓小平适时地采取了一系列重要决策。这里既有在中英联合声明签订前所采取的关键决策,也有在过渡时期针对英国的变故而采取的应对策略。
(一)明确要求建立中英联合小组,保证过渡时期的稳定
为保证过渡时期的平稳,邓小平要求在联合声明中明确写进设立一个常设性的中英联合小组。对此提议英方感到十分紧张并坚决反对。1984年4月,邓小平在接见杰弗里·豪时说,在过渡时期内有很多事情要做,没有一个机构怎么行?并表示要常设在香港,但可以轮流在北京、伦敦、香港三地开会。但在此后三个多月的会谈中,英方仍反对。在这关键时刻,还是邓小平做出了指示。据周南介绍,最后经邓小平的同意,将联合联络小组的任务写得笼统一些,并在协议公布之后成立,可以先在三地轮流开会,但几年后必须进驻香港。经过努力,终于基本上按中方的设想达成了协议,设立联合联络小组,小组于1988年7月1日进驻香港,2000年1月1日撤销。
(二)明确要求按照“一国两制”的精神和中英联合声明的规定起草基本法
尽管起草基本法连英方也承认属于中国的内政,但英国仍通过各种手段对起草工作的进展施加影响。而其中最具有争议性的问题是界定中央和未来特区的关系和明确未来香港政治体制这两个问题。
第一、明确中央和特区的关系
在中央与未来的特区的关系地位上,有人主张把“高度自治”解释为“完全自治”或“最大限度自治”,企图使香港成为一个准独立的政治实体。针对这种态势,邓小平在1987年4月会见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说:“‘一国两制’也要讲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一些特殊地区搞资本主义,不是搞一段时间,而是搞几十年、成百年。另一方面,也要确定整个国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否则怎么能说是‘两制’呢?那就变成‘一制’了。”[1] 第3卷(P219)所以在邓小平看来,如果未来的特区与中央关系解释为“完全自治”或“最大限度自治”,那么就是在制造“两个中国”,而不是一个中国。如果中央把什么权力都放弃了,就可能会出现一些混乱,损害香港的利益。所以,邓小平说,保持中央的某些权力,对香港有利无害。大家可以冷静地想想,香港有时候会不会出现非北京出头就不能解决的问题呢?过去香港遇到问题总还有个英国出头嘛!总有一些事情没有中央出头你们是难以解决的。
第二、明确未来香港的政治体制
中英联合声明快要达成的时候,英国人便鼓吹要在香港搞“立法主导”和“三权分立”,妄图对以行政主导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造,其目的就是想给未来特区的政治体制设定一个既成的“构架”。对此邓小平说:“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现在如果完全照搬,比如搞三权分立,搞英美的议会制度,并以此来判断是否民主,恐怕不适宜。”[1] 第3卷(P220)至于普选,邓小平说:“对香港来说,普选就一定有利?我不相信。……即使搞普选,也要有一个逐步的过渡,要一步一步来。”[1] 第3卷(P220)“其实有些事情,在某些国家能实行的,不一定在其他国家也能实行。我们一定要切合实际,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1] 第3卷(P221)后来基本法中关于香港政治体制的部分,就是按照邓小平上述的指示精神写的。
(三)明确反对彭定康的“政改方案”
在中英联合声明签订以后,邓小平又一次告诫地说:“应该想到,总会有人不打算彻底执行《中英协议》。某种动乱的因素、捣乱的因素、不安定的因素是会有的。果然不出所料,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风云突变。因错误估计形势,英国在香港问题上蠢蠢欲动。尽管如此,中方在邓小平和中央的“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指示下,还是从保证过渡时期的稳定的大局出发,同英方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但英方却在背离联合声明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其突出表现就是1992年夏决定派遣“强硬”的彭定康出任新一任港督。这位“受命于危难时刻”的港督于同年10月就擅自抛出了“以加速民主进程”为招牌的“政改方案”。妄图把既定的“行政主导”的政治体制改为“立法主导”。面对英方利用国际局势的变化来违背联合声明,邓小平说:“香港的事我都很清楚。香港问题就是一句话,对英国人一点都软不得。对他们背信弃义的做法,必须坚决顶住,决不能让步。要质问他们,中英协议还算不算数?要揭露他们的言行。如果他们一意孤行,我们就另起炉灶。”[5] (P240)他还说:我在1982年同撒切尔夫人讲话中提到,必要时在另外的时间,采取另外的方式收回香港的讲话,今天仍然有效。为此,要做好各方面的工作。包括军事方面的准备。为此他对中方人员提出了要求,他说:“对待英国这个老牌殖民主义者,我们的同志切切不可过于天真,过于老实了。在香港问题上,我们已经让得够多了,不能够再让了。愈让愈复杂,要引起动乱。”[5] (P240)正是这些关键决策构成了这一时期中国对付英国政府和彭定康在香港问题上提出挑战的指导方针。
三、“我相信我们会制定出收回香港后应该实行的、能为各方面所接受的政策”——邓小平对香港回归后的信心
1997年7月1日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保持香港繁荣是邓小平关心的另一件大事。对此他通过明确1997年后香港所实行的制度和政策给予了回答。
(一)明确“一国两制”的政策和《基本法》的规定不会变
1982年邓小平就说:“我们在宣布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的同时,还要宣布一九九七年后香港所实行的制度和政策。”[1] 第3卷(P14)并充满信心地说:“我相信我们会制定出收回香港后应该实行的、能为各方面所接受的政策。”[1] 第3卷(P14)1984年6月邓小平就清晰地说:“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通过了这个政策。”[1] 第3卷(P59)同时邓小平又强调了基本法的不变。他说:“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回归到祖国以后五十年政策不变,包括我们写的基本法,至少要管五十年。……五十年以后更没有变的必要。”[1] 第3卷(P215)对此,邓小平从三方面进行了说明:
第一、从政策制定的出发点来看。邓小平说:“采用和平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就必须既考虑到香港的实际情况,也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和英国的实际情况,就是说,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使三方面都能接受。……三方面都能接受的只能是‘一国两制’,允许香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保留自由港和金融中心的地位,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办法。”[1] 第3卷(P101-102)但同时他又明确地说:中国的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这是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不行。在这个前提下,可以容许在自己身边,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我们相信,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更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从政策本身正确与否来看。邓小平说,“有人担心这个政策会不会变,我说不会变。核心的问题,决定的因素,是这个政策对不对。如果不对,就可能变。如果是对的,就变不了。”[1] 第3卷(P59)1984年10月邓小平又说:“现在有些人就是担心我们这些人不在了,政策会变。感谢大家对我们这些老头子的信任。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的政策不会变,谁也变不了。因为这些政策见效、对头,人民都拥护。既然是人民拥护,谁要变人民就会反对。”[1] 第3卷(P72)
第三、从中国国家利益的要求来看。邓小平在1984年说:“中国现在制定了一个宏伟的目标,就是国民生产总值在两个十年内,即到本世纪末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就是达到了这个目标,中国也不算富,还不是一个发达国家。所以这只能算是我们雄心壮志的第一个目标。中国要真正发达起来,接近而不是说超过发达国家,那还需要三十年到五十年的时间。如果说在本世纪内我们需要实行开放政策,那末在下个世纪的前五十年内中国要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也不能离开这个政策,离开了这个政策不行。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是符合中国的切身利益的。”[1] 第3卷(P102-103)所以“如果懂得了这点,知道我们的基本观点,知道我们从什么出发提出这个口号、制定这个政策,就会相信我们不会变。”[1] 第2卷(P103)
(二)明确联合声明确定的内容不会变
“我们在协议中说五十年不变,就是五十年不变。我们这一代不会变,下一代也不会变。…所以不要担心变,变不了。……如果有什么要变,一定是变得更好,更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发展。”[1] 第3卷(P73)所以对于中英联合声明,我们不仅相信我们自己会遵守,也相信英国人会遵守,更相信香港同胞会遵守。“人们担心中国在签署这个协议后,是否能始终如一地执行。我们不仅要告诉阁下和在座的英国朋友,也要告诉全世界的人:中国是信守自己的诺言的。”[1] 第3卷(P102)
(三)明确有些干预是必要的
邓小平说,中央确实是不干涉特别行政区的具体事物的,也不需要干预。但是,当特别行政区发生危害国家根本利益、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的时候,该怎么办?对此,他坚定地说:“那就非干预不行。”[1] 第3卷(P221)对于有些人的“担心”,他也明确说:“要看这些干预是有利于香港人的利益,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稳定,还是损害香港人的利益,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切不要以为没有破坏力量。……如果发生动乱,中央政府就要加以干预。由乱变治,这样的干预应该欢迎还是应该拒绝?应该欢迎。”[1] 第3卷(P74)所以,“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不行的,这种想法不实际。”[1] 第3卷(P221)
(四)明确“港人治港”的标准问题
邓小平多次讲过,北京除了派军队以外,不向香港特区政府派出干部。香港过去的繁荣,主要是以中国人为主体的香港人干出来的。要相信我们中国人自己是能干得好。香港人是能治理好香港,要有这个自信心。[1] 第3卷(P60)但港人治港有个界线和标准,也就是说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什么叫爱国者?邓小平说:“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只要具备这些条件,不管他们相信资本主义,还是相信封建主义,甚至相信奴隶主义,都是爱国者。我们不要求他们都赞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求他们爱祖国,爱香港。”[1] 第3卷(P61)
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之所以能够取得圆满的结果,从根本上是由于新中国这时已经是一个具有较强实力的大国。她早已结束了“弱国无外交”的可悲局面。同样重要的是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战略方针和他在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做出的关键决策。一个是国家的综合实力,一个是正确的策略方针。正如邓小平在协议草签后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指出的:“香港问题为什么能够谈成呢?并不是我们参加谈判的人有特殊的本领,主要是我们这个国家这几年发展起来了,是个兴旺发达的国家,有力量的国家,而且是个值得信任的国家,我们是讲信用的,我们说话是算数的。”[4] (P492)“当然香港问题能够解决好,还是由于‘一国两制’的根本方针或者说战略搞对了,也是中英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5] 第3卷(P85-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