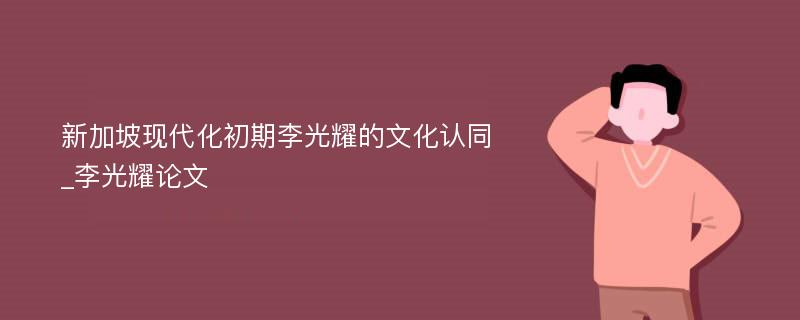
李光耀在新加坡现代化初期的文化认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加坡论文,初期论文,李光耀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以来,亚洲一些国家的政治活动家纷纷登上国际舞台,就亚洲与世界面临的问题发表意见。由于比较集中地涉及亚洲社会不同于西方的特点,并因此而强调亚洲人有自己的价值观或价值标准,故与此相关的观点便被统称为“亚洲价值观”。而公众舆论对于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所发表的言论,则每每给予特别关注,并誉之为“亚洲最雄辩的发言人”。概而言之,李光耀以历史渊源、现实功用、未来发展趋向的架构,紧紧把握住“亚洲价值观”的主体,使之成为有效而不乏严谨的抵抗西方文化霸权的理念。而在他的演绎过程中,又生发出对中华文明的强烈认同。
对于许多尚需进一步现代化的国家而言,“亚洲价值观”中的精华因素,无疑将成为社会发展的宝贵资源。但是,如果将李光耀近年的“亚洲价值观”及其文化倾向,视作新加坡现代化一贯的思想资源,便难免产生种种认识误区。因此,考察李光耀在新加坡现代化初期即六七十年代的文化认同,有助于我们客观地认识与评价东亚现代化的历史,并从中汲取值得借鉴的经验。
1.汉字与家族制度:现代化的障碍。李光耀“亚洲价值观”的文化认同,在历史的渊源方面多指向在东亚具有典型意义的中华文明。然而追溯新加坡现代化的早期历史,却很难搜寻其一以贯之的脉络。相反,他对于中华文明的载体——汉字的评价,对与儒家文化相关的传统的批判,似乎颇得中国新文化运动之真髓。李光耀认为汉字是一种贵族化的文字。70年代初,当香港大学授予李光耀名誉博士学位时,他在演讲中谈到香港与新加坡历史,其中涉及对汉字的评价,他说:“使用表意符号、不用拼音字母的汉字是世界最难的文字的一种,它是为学者式的高贵人物而发展的,存心使普通老百姓成为文盲而对官吏产生敬畏之心。”因此,汉字不能够适应现代化工业技术社会对于普及教育的要求:“一种对人民大众来说是神秘而艰深的字体,与工业技术社会是不相容的”〔1〕。这就是说,在以工业化为特征的现代社会中, 李光耀认为汉字的效用与价值是很低的。
李光耀对汉字的认识不能说毫无道理,现代化首先是从西方向全世界扩散的,而工业化传播的语言载体就是拼音文字。李光耀也深知,其实中国自1911年以来一直在进行简化汉字的努力。但是从现代化发展速度的视角出发,李光耀仍然将汉字看作是一种障碍,即如果不采用这一文字系统,发展将便捷得多。因而值得庆幸的是:“一个多世纪以前,由于采用英语,在香港和新加坡的华人已经把他们那副表意符号的眼罩给去掉了”〔2〕。
不仅如此,李光耀还为摆脱古典的汉文化传统而深感庆幸:“当你离开了你的祖国,并且不再受那些用《论语》培养出来的达官显贵们的支配而是接受‘总规则’(它教导行政官员要对所有生活在他们管辖下的人们公正地、诚实地主持公道)培养出来的英国行政官的管理时,那就非常容易摆脱过去那种无益的羁绊了”〔3〕。 姑且不论李光耀对《论语》、对中国古代选拔人才制度有多深刻的了解,至少他对汉文化传统影响下的政治文化或政治生活是反感的;而在另一方面,他对于英国文官制度“总规则”的强烈趋同,则表明了西方化的价值观念。
李光耀在探讨中国的科学技术大大落后于西方的原因时,指出了家族制度和宗法观念在其中的根本影响。李光耀以中医的发展为例:“就中医来说,本来拥有几千年的经验,但是由于有些人惯于利用祖传与秘传的办法来处置新的发明,以致不能帮助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父传子,子传孙,这个办法是否可以保持永远流传下去呢?”比照西方,他认为专利权在方法上更为有效,因为如西方国家,“今天有人发明一种新的药品,好象盘尼西林等,在起初的二十年里拥有专利权,但是过了这个时期以后,这种药品(发明)就完全属于大众的了。他们利用这种办法,对于他们的人民和国家是有很大帮助的”。于是他号召华人(中医)“看到人家这样的好办法”,也“应该随着改变”〔4〕。
与对汉字与家族制度的认识相关,传统的影响对一个社会越弱,李光耀对它的信心似乎越足。1968年,在新加坡优素福学院十周年纪念日的讲话中,他从妇女在亚洲家长制社会中的地位谈起,强调了新加坡社会的传统势力之弱:“我们的社会是一个传统势力很弱和历史的残渣很容易被清除的社会”。虽然就亚洲的情况(包括日本)而言,“工业化过程并没有改变他们男女之间的社会关系”,但新加坡“作为一个交通中心,通过报纸、电影、电视荧光屏,通过男男女女的来访和新思想的接触,我们受着几乎所有的现代思想的激荡,因此,人类文明各大中心所发生的或正在发生的事情,都使我们的社会受到了启发。所以说,我们是有较充分的准备去迎接现代世界的挑战的”〔5〕。 此番讲演的意蕴非常明显:亚洲社会是相对落后的;西方是现代社会的中心。而迎接世界的挑战则意味着摆脱旧传统(这里特指亚洲家长制社会)的束缚。
综览李光耀在新加坡早期现代化过程中对亚洲社会、特别是中华文化传统弊端的批判性思考,可见其焦点不可谓不准确,其剖析亦不可谓不深刻,甚至有相当一部分内容,还是延续至今的“东方问题”。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反传统和对西方文明强烈趋同的观念,作为新加坡建国的精神资源,则确确实实有力地推动了新加坡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成为决定新加坡成功的关键性因素。不过,另一个不同的结论也恰恰由此而得到证明:以李光耀当时的“非儒化”(笔者按)言论及对西方文化的强烈认同而言,新加坡的经济起飞或曰现代化的成功与儒家文化联系的环节便显得十分薄弱了。由于人们往往将新加坡经济起飞以后,李光耀针对西方现代化的弊病所提出的伦理方面的对策,等同于新加坡整个发展过程的精神资源,这样,便在认识上出现了时间错位。对于误读李光耀,也许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2.从“不再成为亚洲人”到“仍为亚洲人”:现代化的必要步骤。在现代化过程中,李光耀认为作为一个亚洲人,必将经历一种类似蜕变的磨砺。早在李光耀执政的1959年,他就曾这样说:“这是亚洲人历史发展的过程:先是受了西方教育,不再成为亚洲人,转到学会西方语言、技术和科学而仍为亚洲人,并以其为亚洲人感到自豪”〔6〕。 其实,这正是东亚现代化过程中多见的“脱亚入欧”发展特征,也是新加坡面对现实世界所采取的应对措施。所谓“不再成为亚洲人”,是具有丰富内涵的。李光耀将“受英语教育”定义为不仅仅是接受语言教育,“我所谓的受英语教育的人,不仅仅是指会说、会读、会写英国语言的人”,“他们不但会操英语,而且是经过进入英语学校后获得明显特征的人。”〔7〕在他看来,受过英语教育的人不仅仅具备语言知识, 而且应在行为标准、价值尺度方面具有西方特征,它们包括:具备科学、技术知识,富于理性精神;有独立自主的人格;接受了国家、民族的概念,饱含为自己祖国的进步而奋斗的热忱。而这些有利于推动现代化的特征,李光耀认为正是亚洲社会与中华文化传统所缺乏的。这就不难理解,何以六七十年代期间,李光耀在政界、商会、军队、学校等公众场合屡屡阐发上述观点,因为他要将独立不久的新加坡民众,培育成为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公民。
而“仍为亚洲人”的意蕴,当时李光耀有关言谈所反映的,基本只局限于人种方面的考虑。在他的观念里,亚洲人正由于社会的落后而普遍处于一种自卑的困境,特别是新加坡的华人,所以他反复强调,在种族的意义上,人们没有必要为上帝这样的安排而自卑,“承认华族后裔又有什么羞耻呢?我们是华族的后裔,他们一看我们的面孔就会知道了”〔8〕,问题的关键在于选择什么样的生存方式。对此, 李光耀的态度很鲜明,他将一种“亚洲的影响”,视之为新加坡站隐脚跟的障碍。1966年7月,李光耀在新加坡南洋大学的演讲中指出, 当时的新加坡“不时还受三个具有长远历史文明的亚洲大国家所影响”,所以,“这一点,有时就难免对我们这个年轻国家多少是一个问题了”〔9〕。
作为新加坡的领袖人物,李光耀采取如此文化策略动机显然如他所言:“在一切的理想主义之外,我和我的同僚也在‘功效至上’的基础上决定政策的。”〔10〕因为李光耀当时清醒地意识到:“没有哪个国家愿意奉送辛苦得来的技术秘密……电子计算技术、电子学、宇宙火箭和太空通讯的差距不断在扩大,欧洲的西方国家对此感到很大的不安……在美国、英国和一般的欧洲技术专家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情愿同非欧洲集团分享技术知识的同时,他们却比较容易同那些类似欧洲的集团扩大这样的合作,这些集团不见得成为无情的竞敌。这说明为什么战后澳大利亚的工业潜力得到了迅速的发展。”〔11〕
基此,虽然种族的天赋不能改变,但文化意义上的“不再成为亚洲人”,却成为新加坡现代化初期“人的现代化”之主旋律。
诚如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的研究,新加坡文化政策的调整,发生在70年代末以后,他指出:“看来促使李光耀以官方名义正式强调‘东方’价值观念的还是新加坡社会中伦理‘退化’的种种征象。”他还说:“受日本成功的影响,其领导层自70年代末开始日益省察到具有‘儒家’依据的日本发展模式是一种替代西方的选择。也就是这个时候,显然是因为中国1976年开始重新开放,提供了新的商业机会并且有可能导致东亚的转变,新加坡政府决定提倡教授汉语。”〔12〕由此看来,在新加坡文化政策调整前后,李光耀的文化认同内涵是很不一致的。分析李光耀的亚洲价值观和新加坡现代化的精神动力,需要有一种历史的眼光。
3.西方政治制度与社会理想:现代化的典范。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一种推动进步的参照系,渗透在李光耀关于新加坡现代化的早期思想构架中,使人感觉到他对于西方文明的汲取,有一种驾轻就熟的本领。表现在政治制度方面,当新加坡在1950年尚属马来亚一个省的时候,李光耀已经将英国人的制度作为建设一个独立国家的政治资源,他那时正以双重第一荣誉毕业于剑桥大学法科,归国前,在伦敦马来亚学生会组织的一个座谈会上,面对东南亚殖民统治的行将灭亡及马来亚的种族问题,他理性地认识到:“我们还得接受英国人统治一个时期,以期在这期间内,我们能够达致适当程度的社会聚结,提高马来亚各民族间的适当程度的公民及政治意识。”〔13〕他肯定了英国在殖民地遗留的政治特征,即“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效而诚实的行政管理”〔14〕的价值,并且在建国初期不断地向他所领导的政党人民行动党,以及国家机构的官员和公务员强调这样的原则。尽管因当代西方的一些学者将新加坡政治模式归纳为“威权主义”类型而难免有“家长制”之嫌,但新加坡因受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影响,其法理型社会的特征还是很鲜明的。
我们还可以发现,李光耀经常参加国际民主社会主义者的集会,在类似的讲坛上是个活跃人物。不仅如此,他在国内也不断向各社会阶层包括学生阐发他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涉及民主,他认为马来西亚共产党与种族主义集团这两种势力都是反民主的。1964年12月2日, 李光耀在远东童子军训练会议上有过这样一段发言:“我们在东南亚赖以生存和维护文明生活最高形式之一的机会就是要让宽容的民主标准胜利,在那里,人们承认多数派不仅将占优势,而且也将尊重适应大批持不同意见的少数派的需要。”〔15〕1965年,李光耀在国际社会主义青年联盟所组织的亚洲社会党领导人会议的开幕式上表述了他对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解,包括民主社会主义当时在世界上的地位、它的平等与公正的原则,以及“作为民主社会主义者,我们应当支持人类的一切个人自由”〔16〕的理想。李光耀所崇尚的,基本上是当时在西方占有优势的民主社会主义。
4.文化即命运:一个无法避免的历史必然。李光耀对东西方社会与文化的体认,带有微妙的双重标准:对东方文化(更确切地说是与东亚社会有着密切关系的中华文化)的认同,偏重于历史渊源,是对历史必然性的欣然接受,颇有黑格尔式的宿命意味,体现了“文化即命运”的思维轨迹;对西方文化的评价,除具有确认现存秩序的理性特征之外,似有更多情感倾向蕴含其中,从中使人感受到一种默契,反映他作为一个社会的、文化的人,与西方文明之间有着天然的、共生的关系。难怪早在60年代,英国外交大臣将他称之为苏伊士以东最典型的英国人。我认为,这就是李光耀的价值观中往往被人忽略的更为深厚的文化内涵。本文源自历史视角的考察清晰地再现了:西方的文化传统与治国实践的需求,在本世纪60—70年代,如何紧紧缠绕在李光耀关于新加坡现代化的思考中。
1996年5月,已经退居幕后的李光耀作为新加坡的内阁资政, 到威廉斯堡参加美国商业理事会议,会议期间,他接受了美全国广播公司晚间新闻主持人汤姆·布罗考的采访。耐人寻味的是,李光耀在谈话中曾经将自己说成是大英帝国的产物。当时布罗考请他对李登辉作一个评价,于是有了如下回答:“他的际遇与我相似,不过他生长在日本帝国里,我则是大英帝国的产物。我们俩年龄相近,他73岁,我72岁。我在新加坡的英国学校里受教育,之后到英国的大学去。因此他通过日本人的视野来建立世界观,就象我的是通过英国人的视野。”〔17〕
这就是文化对个人的根本性影响;这也是文化对历史进程的关键性作用。
注释:
〔1〕〔2〕〔3〕〔5〕〔6〕〔7〕〔11〕〔14〕〔15〕〔16〕[英]亚历克斯·乔西:《李光耀》,第481、481、481、369—370、122、122、306、477、212、235—236页。
〔4〕〔8〕〔9〕〔10〕〔13〕李光耀政论集:《新家坡之路》,新加坡国际出版公司1967年版,第164、251、265、124、275页。
〔12〕[美]阿里夫·德里克:《似是而非的孔夫子:全球资本主义与儒学重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5 年冬季卷, 第168页。
〔17〕《李资政谈美国在亚洲的角色及中台问题》,新加坡《联合早报》,1996年6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