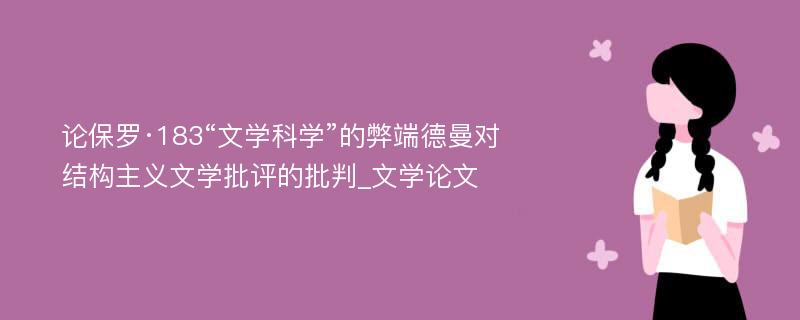
“文学科学”的弊端——论保尔#183;德曼对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的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保尔论文,结构主义论文,文学批评论文,弊端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保尔·德曼早在结构主义仍然风行欧洲和美国的时候就发现了它的许多致命弱点。他把罗兰·巴特等结构主义批评家视为极端化的形式主义者,对他们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但是,由于德曼本人一贯被认为是极端的虚无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代表,是所谓的“美国解构主义”的倡导者,所以,他对形式主义的批判似乎被人们有意识地忽视和遗忘了。因此,细致地分析德曼对于结构主义的批判,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结构主义文学批评,而且也有益于我们深入了解德曼的批评思想。
说起文学科学化,其实是结构主义从俄国形式主义那儿继承下来的东西。俄国形式主义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促使文学研究的科学化。什克洛夫斯基在其早年的著作中就对“诗歌语言的法则”感兴趣,而雅可布森则强调“文学学”必须成为一门科学。(注:参见佛克马和易布思《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三联书店,1988),第14页。)正因为要使文学研究成为一门科学,所以俄国形式主义者们就致力于寻找文学的一般的、普遍的特点或者文学的本质特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雅可布森宣告:文学科学的对象是“文学性”,(注:这里,雅克布森的“文学性”同德曼的“文学性”不一样,它主要指一些文学语言技巧。)而不是整体的文学或个别的文学文本。罗兰·巴特几乎是直接地从俄国形式主义那儿借鉴了“科学化”这个概念,他在几十年之后又重新提出了这个问题。只是,在罗兰·巴特这里,科学化不再是一种有待追求的理想,而是似乎转变成了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
我们具有文学的一种历史,而不具有文学的一种科学,因为我们无疑未能完全认出文学对象——一种写作的对象——的本质。从人们很想赞同作品是由写作构成(并很想获得其结果)之日起,文学的某种科学便成为可能了。……这将不是有关内容……的一种科学,而是有关内容的条件亦即形式的一种科学……(注:罗兰·巴特:《文学科学》,引自《罗兰·巴特随笔》(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第131页。)
罗兰·巴特等结构主义者不仅想当然地认为文学科学是注定要实现的,而且还非常具体地为实现科学化进行了种种努力。但是,结构主义对俄国形式主义在这些理论与批评实践上的发展和推进与其说是一种进步,还不如说是把后者的方法和错误都发展到了极致。从德曼对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的批评中,我们可以总结出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理论误区。
一、高度简约化代替了对单篇文本的“阅读”
从理论发展的角度来看,俄国形式主义虽然提出“科学化”的口号,并且把它视为某种理想和目标,但是,在具体的文学研究实践中,除了对文学语言的技巧和手法等进行了高度细致的研究,并且总结出“文学性”这个文学的特征之外,他们并没有在“科学化”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但是,结构主义文学批评作为20世纪兴起的结构主义大潮中的一个分支,第一次真正地努力把文学研究与科学研究等同起来。他们在追求文学科学化的过程中把俄国形式主义所尝试过的简约化方法运用到了极端的程度。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高度的简约化是自然科学的基本操作方法,在自然科学中,人们可以从研究对象身上抽象出许多普遍的和一般的客观规律来。结构主义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科学主义。结构主义的理论前提就是结构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也就是说,一切事物都具有某种程度上的整体性和系统性。而这种整体和系统在具体的现实中还体现为不同事物之间的一致性关系。例如,皮亚杰就曾经宣称:“物理的现实与用来描写这种现实的数学理论之间有着惊人和稳固的一致性”,而且,“……有肉体有精神的人这个具体的算子和自然界中不同级别上的物理客体这些数不胜数的算子之间(也)有一种和谐的关系”。(注:皮亚杰:《结构主义》(商务印书馆,1984),第28页。另参照罗伯特·休斯《文学结构主义》(三联书店,1988),第4页,译文略有变动。)列维-斯特劳斯也认为,“无论是原始的还是文明的思维法则都与表现在物理现实和社会现实之中的那些法则相同……”(注:列维-斯特劳斯:《亲属关系的基础结构》,转引自罗泊特·休斯《文学结构主义》,第4页。)这些论断表现出了明显的泛科学化倾向。
罗兰·巴特在结构主义提倡的泛科学化思潮的语境中,通过把科学的结构理论运用到文学研究之上,明确提出要创建一种同自然科学相似的、高度简约化的学科——“文学科学”,他声称:
不可能有一种关于但丁的科学,关于莎士比亚的科学或关于拉辛的科学,而只有一种关于话语的科学。……借助于文学的这种新的科学所获得的客观性,不再涉及到直接的作品(这种作品属于文学史或语文学),而是涉及到它的可理解性。(注:Roland Barthes,Criticism and Truth,trans.K.P.Keuneman(London:Athlone Press,1987),p.142.译文参见罗兰·巴特《文学科学》。)
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到,罗兰·巴特把关于单篇的文学作品的研究,甚至关于单个作家的研究,统统地排除到了文学科学之外。他的“文学科学”公开地成为一种关于所谓“总的话语”的研究,其目的是为了总结出似乎可以涵盖一切的“一种结构”。
结构主义批评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托多罗夫明确地反对把文本视为文学批评的主要对象,他认为这种“阐释”某个具体作品的含义的方法是不可取的。在他看来,真正的文学批评应该是对每一部作品中共同存在的某种抽象的结构的认识,即文学批评的目的“不再是描述某一个别作品,明确一部作品的含义,而在于建立一些普遍的规律……”(注:Tzvetan Todorov,Introduction to Poetics,trans.Richard Howard(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1981),p.18.)在托多罗夫看来,任何文学作品都仅仅是某种普遍的和抽象的结构的具体表现,而且,它只是这种结构可能实现的多种形式之一。由于托多罗夫的这部《诗学》是作为“何谓结构主义?”丛书中的一种,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它代表了当时人们关于结构主义的主要观点。
但是,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结构主义落入简约化的陷阱呢?结构主义又假定自己是科学的,于是,就像在自然科学中一样,结构主义评论家所使用的语言本身就必须被设定为“外在于”文学,“外在于”它的研究对象的。他们把文学语言与文学批评的语言截然区分开来,过分地强调语言的语法性质,而忽略了语言本质上的修辞性质,(注:关于文学语言的语法性质和修辞性质之间的关系,德曼也有很好的论述,拟另撰文介绍。)仅仅把语言的修辞性质视为文学的艺术技巧,而没有意识到它对于一切语言的本质规定性,从而假定了一个特殊的、能够脱离语言本身并被抽象化理解的文学性。但是,德曼认为:“文学性,就是那种更加突出语言的修辞功能,而不是它的逻辑功能和语法功能的运用语言的方法。”也就是说,“文学性”主要是文学的语言性和文学语言的修辞性。因此,对文学性的研究必然是一种语言学的研究,而且是不能够脱离具体文学文本的。然而,结构主义对于文学性产生了错误的理解。他们没有意识到文学性的语言学内涵,而把它视为某种能够脱离语言而独立存在的内在本质因素,某种可以采用科学的方式,由文学的外部出发,去从文学的内部发掘出来的、具有普遍性的和一般性的东西。许多具有结构主义倾向的文学批评家致力于寻找文学中的某种普遍原则,并且分别创立了各自的阐释系统。例如,曾经是俄国形式主义者的普洛普从神话中总结出了31种功能和7种“行动范围”;列维-斯特劳斯从神话叙述的结构中总结出许多“神话素”(就好比科学家从血液中分解出血色素);弗莱的神话原型理论和他的“词语秩序”;罗兰·巴特的文化的5种编码等等。
这种种努力的共同特点就是把文学研究等同于科学研究,忽略了文学的特殊性质——语言的修辞性。在德曼看来,文学语言的修辞性就是它的文学性,它无法独立于文学作品本身而独立存在,所以也无从被科学地抽象和提炼。此外,文学语言的修辞性对于文学批评的要求不是一种泛科学化的研究,而主要是阅读和体悟。从神话中分解出种种结构模式根本无助于人们欣赏神话的魅力。可以说,作为一种语言的艺术,在很大的程度上,文学是抵制任何形式的抽象化和简约化分析的。因此,结构主义者力图对作品中的一切做出明确的解释,力图对文学中的一切进行系统化和合理化处理,其结果就是不得不把一些不可明确解释的细节宣布为无意义。例如,罗兰·巴特、热奈特、卡勒等人对福楼拜作品的分析就为上述论点提供了例证。在他们看来,福楼拜的作品中有许多没有意义的细节,而这些细节之所以被认为是没有意义的,主要是它们不能够被科学化和系统化地进行解释。(注:王钦峰:《巴赫金与比较文学的方法》,见《中国比较文学》1998年3期。)
鉴于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人们对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最经常提出的批评就是:“它在单个文学文本这个层次上失败了。……结构主义不能代替我们阅读文本。”(注:罗泊特·休斯:《文学结构主义》(三联书店,1988)。)公平地说,结构主义的创始人之一雅可布森和列维-斯特劳斯(在其学术生涯的早期)并没有放弃对单篇作品的分析研究,相反,他们两人合著的《评夏尔·波德莱尔的〈猫〉》一文还曾经掀起过巨大的轰动效应。但是,从总体上看,结构主义忽视单篇文本,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因为结构主义批评家们的批评实践证明了,结构主义为了建立所谓的“文学科学”,确实把文学视为某种可以进行高度抽象的东西,而不是各具特色的众多文学文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曼严厉批评一些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家,在追求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热情中,基本上遗忘了对单篇的文学文本的阅读: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除了极少数非学院派的例外(指普鲁斯特对巴尔扎克和福楼拜的阅读),法国文学批评是通过回避任何关于阅读的问题而发展和繁荣起来的。直到如今,法国批评从来也不费心去阅读,或者认为阅读这个问题值得他们关注,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大量地写作关于他们从没有阅读过的作品的评论。(注:Paul de Man,The Resistance to Theory(Minneapolis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6),p.33.)
二、统一性与“作者之死”
德曼认为,新批评和结构主义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它们都否认了文学文本的意向性,但是,它们各自的否定是基于不同的理论基础的:在新批评,这是由于把文学作品等同于有机世界中的自然物体,从而使其获得某种本体性和整体性;而在结构主义这里是因为对一个建构性主体(constitutive subject)的压抑,其目的是为了获得叙述的可靠性,以及为了设置一个具有统一性的话语。而且他认为,这后一种对建构性主体的压抑所带来的后果比前者要严重得多:列维-斯特劳斯为了维护自己的科学的合理性,不得不总结出一个无作者的神话,而那些试图维护合理性的语言学家也不得不提出一种无说话人的元语言。(注:Paul de Man,Blindness and Insight(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Minneapolis,1983),pp.11—12.)
换言之,从文学中驱除“建构性的主体”,也是追求科学化(即合理、统一和系统性)的必然结果。把神话分解成无数类似于化学元素的、可以任意组合的“神话素”,然后再把文学简单地等同于神话,这一系列化繁为简的举动,说明结构主义者为了找到支配人类语言活动的客观规律,不惜摈弃文本的意义和它的建构性主体这些无法确定的因素。所以,在当时的泛科学思潮下,主张神话没有“说话人”的,并不仅仅是列维-斯特劳斯一个人。L·塞巴也认为:“神话是一种语言,这种语言似乎不具有承担内容和要求获得意思——当然是神秘的意思——的真正传播者。”(注:L·塞巴:《神话:编码与讯信》,载《现代》1965年3月。转引自《罗兰·巴特随笔》,第133页。)虽然列维-斯特劳斯等人在这里所试图否定的仅仅是神话的“建构性主体”,目的是在于追求一切神话所具有的统一性。但是,列维-斯特劳斯追求“元语言”,即对一种纯粹的语言的抽象思考,被通俗化成为对作者的某种抵制和反对。这种误解其实也有一定的客观原因,因为列维-斯特劳斯在研究神话的时候,完全忽略了神话虽然没有署名的作者,但是,它们在最初也是由某个人创作的(或许多人逐渐地创作的)。所以说,列维-斯特劳斯等人的观点客观上给人一种否定一切文学文本的作者的印象,这样一种否定,在某种程度上,比新批评对于文本的意向性和作者的意图的否定,具有更加严重的后果。
从最直接的影响来看,列维-斯特劳斯关于没有作者的神话的分析,似乎更加强了当时语言哲学研究中盛行的“语义自主论”观点,这种观点在美国评论家赫施看来,是极为错误的,因为它直接导致了人们对于文学文本的作者的否定。赫施对这种观点作了如下的批驳:
……语义学自主论……在排除作者时,忽视了这一事实,即意义是一种不带语词的意识状态,而几乎任何语词序列,除非某人要么用它来表示某物,要么借助它来理解某物,它什么也不表示。在人类意识之外,根本不存在意义的魔地。每当意义同语词发生关联时,总是有人在做这种联接。(注:Eric Donald Hirsch,Validity in Interpretation,转引自《二十世纪西方美学经典文本》卷三,(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第706页。)
应该承认,赫施的语言观与德曼的语言观其实是一致的,他的结论是正确的。但是,赫施从“保卫作者”出发,对语义自主论进行批判,这里面不仅暴露了他对作者作为文本的权威解释者地位的错误坚持,也隐含了他对于语言哲学理论的某种简化和误解,因为,现代语言哲学理论并没有简单地把语言和人对立起来,无论是列维-斯特劳斯,还是强调语言在人的生活中的重要性的海德格尔和卡西尔,他们都没有简单地否定作者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看,赫施对他们的批判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出于误解。德曼在批评列维-斯特劳斯时,使用的是“建构性主体”这个词。而所谓“建构性主体”,在这里类似于“作者”,但是,又不完全等同于个别的作家。它的含义颇接近于某种操纵语言的、抽象意义上的意向性。德曼之所以使用这个词语,一方面是因为“作者”这个词,在他看来携带了许多认识论方面的附加涵义:在传统解释学中,作者成了解释文本的权威者,同时也是某种对于文本的可理解性的保障;(注:参见Paul de Man,Allegories of Reading:Figural Language in Rousseau,Nietzsche,Rilke,and Proust,(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9),p.202.)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列维-斯特劳斯确实说的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作者”,而是某种语言哲学意义上的“话语传播者”。赫施之所以得出这样一个误解,主要是因为罗兰·巴特的夸张和误导。罗兰·巴特首先想当然地把列维-斯特劳斯的观点错误地阐发成对一切文本的作者的否定。
在《作者之死》一文中,罗兰·巴特宣布:“文本一旦从作者手中完成,文本的作者就死亡了,文本不再与作者有关。”所以,“谁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读”。罗兰巴特还曾经更加直接地把自己的观点同列维-斯特劳斯的观点联系起来声明:“科学又怎样可能谈论一位作者呢?文学的科学只能使文学作品——尽管已有署名——与神话结合,尽管神话没有署名。”(注:罗兰·巴特:《文学科学》,第133页。)
从文学批评史来看,对作者的轻视同样是来自俄国形式主义。在俄国形式主义那里,作者其实只相当于某种“工匠”,并无研究的价值。俄国形式主义者布里克居然得出如此谬论:“即使没有普希金,也会有人写出《叶·奥涅金》。即使没有哥伦布,也会照样发现新大陆。”(注:布里克:《所谓形式方法》,见《左翼战线》1923年第一期,第213页。转引自拉吉斯拉夫·斯托尔《从概括到美学的非人化》,波利亚科夫编《结构-符号学文艺学——方法论体系和论争》(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第311页。)显然,为了对文学进行“定量分析”,为了把文学研究改变成某种“精密科学”,俄国形式主义者已经从文学中铲除了作者的个性因素,而个性因素正是文学完全无法科学化的原因之一。因为,从文学的个性因素出发,我们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普希金、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那就绝对不会有与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完全相同的《奥涅金》、《战争与和平》和《人间喜剧》,可是如果没有哥伦布、牛顿和门捷列夫的话,美洲大陆、微积分和元素周期表这些客观存在的事物倒是确实照样会有人发现。
其次,受到艾略特和俄国形式主义的影响,英美新批评不仅旗帜鲜明地把作者排除在文学批评活动之外,而且力求避免所谓的“意图谬误”。而曾经被列维-斯特劳斯高度赞赏的结构主义叙事学所关心的也只是“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的关系”,因为他们认为,“真实作者与真实读者的关系存在于叙事学之外”。米歇尔·福柯在自己的学术生涯的前期也曾经断言,继续维护“作者的特权”已经是关于写作的过时的理论了,人们应该彻底地把自己从“作者这种概念化的、已成为累赘的结构中解放出来”。
所有这一切似乎说明了,罗兰·巴特提出“作者之死”是顺理成章的和理所当然的,因为否定作者似乎已经成为当时的一种时髦的风尚。但是,必须澄清的是,对于作者的抵制,在各个流派、各个不同的评论家那里具有不同的理论涵义,根本不能够被统一到“作者之死”的口号之下。例如,艾略特所反对的主要是作者的主观主义、新批评所反对的是作者的意图和它对文本意义的决定权、福柯所反对的也不完全是作为文本写作者的“作者”,而是“作者的特权”,等等。但是,在罗兰·巴特极具有轰动效应的口号“作者之死”中,所有这一切都混为一谈,彼此没有区别了。此外,罗兰·巴特在宣布他的“作者之死”时,并没有费心去解释这个概念里可能包含的哲学前提,它并没有被指明是一种对胡塞尔复兴笛卡儿的cogito的反对,(注:英国学者布克(Sean Burke)认为,罗兰·巴特、福柯和德里达等法国理论家提出作者死亡的观点是有非常复杂的哲学前提的,但是,他们的这些历史的和民族的环境被人们忽视了,作者之死的观点被进口到了美国,并没有经过必要的改造。在布克看来,作者之死问题的兴起,主要是因为法国当时的思想家们普遍地反对胡塞尔的现象学复兴笛卡儿的“思想的自我”(cogito)。因此,布克认为,只有被理解为一种特别有效的反现象学的方式,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才能够得到恰当的理解。而60年代的美国却大大不同。这也是这个理论传到美国就褪色了的原因。当时的美国人已经厌恶了新批评的意图谬误,而现象学则显得非常地异国情调、朝气蓬勃,它提供了最具有挑战性的走出现实主义的途径。布克认为,以乔治·普莱为代表的耶鲁先锋派提出了一种意识批评,而它就是基于现象学之上的。参见Sean Burke,The Death and Return of the Author(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92),p.163.)所以,这个概念在流传的过程中越来越遭到歪曲和简单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作者之死”这个概念,造成了上个世纪文学批评领域里最大的灾难之一。
三、无奈的结局——从科学走向游戏
由于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内在的缺陷和理论前提上的根本性错误,从狭义上看,这个批评流派实际存活的时间其实非常短暂。几乎所有的理论骨干都陆续背离了结构主义的主要观点。从上文的分析可以总结出,结构主义的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对文本的具体含义的某种简化和拒绝。托多罗夫曾经明确地宣布,结构主义不是对文本含义进行解释,而是对它的抽象结构进行归纳和总结。因此,可以说,从一开始,语言的所指或者说指称功能,就是结构主义为了科学化而不幸丢弃的东西之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的演变,之所以在很大的程度上表现为一种从科学走向游戏(注:这里的“游戏”概念不同于维特根斯坦的“游戏”概念,它强调的是嬉戏,而后者强调的是规律和法则,所以必须把两者区分开来。)的过程,根本的原因也就在于此。
结构主义的这个错误的策略,在罗兰·巴特这里最明显地体现了出来。罗兰·巴特在其思想的后期,批判自己曾经极力提倡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提出一种符号学,但是他的符号学其实同其早期的结构主义思想之间存在着某种逻辑上的连贯性。德曼甚至把罗兰·巴特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等同起来,并不认为这两者之间有本质上的区别。(注:德曼曾经应美国《纽约书评》的邀请,替罗兰·巴特的《神话研究》英译本写书评。由于德曼在自己的文章里批评了罗兰·巴特,对他所谓的符号学的“新颖”表示极大的怀疑,并且直截了当地指出:“罗兰·巴特对文学文本的分析性研究所提供的创新其实是很微不足道的。”德曼这篇序言因此被拒绝。德曼不仅认为罗兰·巴特的符号学在某种程度上是陈旧的,而且,他还认为,罗兰·巴特同美国新批评在许多方面也是相关联的。)德曼指出,罗兰·巴特的后期作品“必须被理解为一种智力冒险而不是对某种方法的科学化发展……一种欣快的、略带狂乱的语调贯穿了罗兰·巴特的写作……他总是好像处于某种重大发现的关头”。(注:Paul de Man,Romanticism and Contemporary Criticism,ed.E.S.Burt,kevin Newmark,Andrzej Warminski(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3),p.166.)例如,罗兰·巴特曾经明确地宣布:“一种具有无可置疑的特殊意义的新人类学或许正在诞生:人类实践的图景正在被重新绘制,而且这种巨大革新的形式……使我们不得不联想到文艺复兴。”德曼分析说,说这些话的是一个从过去的束缚中释放出来的人,只是,这一次并不是人从宗教和神学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而是“能指从指称意义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注:Ibid.,p.167.)在其理论发展的过程中,罗兰·巴特一再声称文本的意义(即其指称或者其所指)并不是文学研究的对象:
文学科学的对象,不是为什么一种意思是应该接受的,也不是为什么这种意思被接受了(这还是历史学家的事情),而是为什么这种意思根据象征符号的语言学规则但不根据文字的语文学规则是可以接受的。在此,我们再一次看到,现代语言学的任务——描写句子的合语法性而不是描写其意指——已经转移到话语的一种科学的高度。(注:《罗兰·巴特随笔》,第132页。)
德曼认为,罗兰·巴特的这个观点显然是对雅可布森的严重误解。雅可布森曾经提出文学语言具有自成目的这一特征,可是,罗兰·巴特虽然“对雅可布森的上述观点非常着迷,就好像一只飞蛾为闪动的火焰所吸引,但是他虽然围着它的周围转动着,却最终出于某种自我保护的目的而退却开来”。(注:Paul de Man,Romanticism and Contemporary Criticism,pp.173—174.)这里,德曼指出了罗兰·巴特在文学语言问题上的根本性错误:罗兰·巴特从雅可布森的观点出发,并没有走向对语言本质的质疑,没有对“(阅读)永远无法到达‘最终的’所指”这样一个哲学问题进行思考,(注:Paul de Man,Romanticism and Contemporary Criticism,p.176.)而是完全放弃对所指的研究。罗兰·巴特过分乐观地认为,我们可以把所指问题转让给历史学家。他主张“文学本身就是关于人类语言(而不是关于‘人的心灵’)的科学或知识”,(注:The Languages of Criticism and the Sciences of Man,ed.Richard Macksey and Eugenio Donato (The Johns Hopkins Press,1970),pp.144—145.)所以,他致力于创造一种符号学科学,力求摆脱作者和不能确定的所指等一切无法纳入他的科学体系之中的因素。但是,德曼指出,罗兰·巴特等符号学家的基本阅读方式还是传统式的,因为它是建立在设码和解码的模式上的。而德曼认定这种阅读过程无法进行,因为最重要的符码(the master code,在这里是指语言本身)于解读者本人也是未知的,这样一来这个解读者也就无法理解他自己的话语了。一种无法解读自身的科学就不再能够被称为科学了。一种符号学科学的可能性就这样受到了挑战,即它无法用纯粹的符号学术语来解释。(注:Paul de Man,Romanticism and Contemporary Criticism,p.174.)
德曼认为,罗兰·巴特所受到的挑战来自于哲学的一个出人意料的角落——语义学,而这个学科则是早期结构主义为了所谓人的科学(包括心理学、人类学和语言学)而抛弃的学科。
在德曼看来,罗兰·巴特在其理论发展的后期,显然已经意识到了这种来势越来越凶猛的挑战。但是,罗兰·巴特对付这一来自语义学的挑战的方法却非常令人吃惊,他只是简单地放弃了他本人曾经执著追求的文学科学(这种科学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其实恰恰就是假定语言具有确定的指称意义),走向了德曼所反对的那种对“形式和意义的调和”。也就是说,当罗兰·巴特等结构主义者从对语言的极度信任中醒悟过来之后,他们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不仅完全放弃了所指,而且从科学走向了游戏:
法国符号学吸取语言学的模式,……通过对符号的任意性(索绪尔)和文学作为一种自足的陈述(关注它自己的表述方式)(雅可布森)的认识,(法国符号学)把意义问题整个地悬置了起来,从而把批评话语从阐释的重负中解放了出来。……它还破除了语义学关于符号和指称之间的对应关系。……(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应该用一种“预防性的符号学卫生学”来对待它。(注:Paul de Man,Allegories of Reading:Figural Language in Rousseau,Nietzsche,Rilke,and Proust,pp.5—6.)
关于德曼的上述言论,粗心的读者似乎会把它解释为对符号学的某种赞赏,但是,德曼一贯具有的那种冷嘲热讽的语气,特别是他的最后一句话点明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罗兰·巴特等所提倡的这种“把意义问题整个地悬置起来的”的符号学,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病毒”,所以,尽管它具有如许“解神秘化”的力量,“我们仍然应该用一种‘预防性的符号学卫生学’来对待它”,以防止自己被“感染”。
罗兰·巴特晚年不仅“放弃阅读而去生产自己的自传小说”(这主要是指他的《S/Z》给人的感觉),(注:Sean Burke,The Death and Return of the Author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92),p.159.)而且还陷入了某种无以自拔的“文本的愉悦”当中,似乎他自己首先被这种危险的“病毒”感染了。在《文本的愉悦》里,罗兰·巴特把文本同肉体、阅读与色情享受联系了起来。在罗兰·巴特这里,似乎文本完全成为一种色情形式,而所谓“文本的断裂之处”居然成为最有挑逗性的诱惑。(注:Roland Barthes,The Pleasure of the Text (London:Jonathan Cape,1926),p.6.)
许多西方学者非常反感罗兰·巴特晚年的作为。伊·库兹韦尔认为,罗兰·巴特在其后期已经忘记了自己的结构主义原则和符号学原理,而一味地投身于“文本的愉悦”之中去了,(注:参见伊·库兹韦尔《结构主义时代——从莱维·斯特劳斯到福科》(上海译文出版社),第231页。)言辞之间充满了责备之意。罗伯特·休斯也认为:
罗兰·巴特是一位基本上无系统的但又喜欢系统的作家,一个厌恶结构的结构主义者、一位鄙视“文学”的文学工作者。他喜欢在任何问题上都持一种令人不能容忍的立场,并竭力为之辩护,直到它变得似乎有理……在《S/Z》中,罗兰·巴特比任何人都更加严厉地批评了结构主义……(注:罗泊特·休斯:《文学结构主义》,第233页。)
罗兰·巴特的善变,从某种角度证明了他的理论观点是没有根基的和肤浅的。鼓吹“文本的愉悦”的罗兰·巴特和《文学科学》里的罗兰·巴特相比,似乎已经脱胎换骨了。对于放弃了结构主义的科学化之后的罗兰·巴特来说,“文学成了一个语义偏差的零度领域”,写作本身成为作家工作的目的,成为一个“不及物动词”,文学文本丧失了一切可能的指称功能……罗兰·巴特的变化似乎令人费解,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又是一种必然,因为结构主义的文学科学至多只能算是某种神话,而从神话到游戏也就比较自然了。罗兰·巴特的错误从本质上说,是对文学语言的认识上的错误。具体说,它表现为,在看待文学语言的所指问题上,罗兰·巴特非常卤莽地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从“科学化”(相信所指的确定性)走向文本游戏(抛弃所指,否认其存在)。而德曼则认为:
阐释的语义学并没有认识论意义上的坚实基础,所以它不是科学的。但是这不同于声称批评家所说的和作品没有任何内在的联系,是一种任意的添加和削减,或者批评家的陈述和他的意思之间的差距可以被作为一种错误而抛弃。(注:Blindness and Insight,p.106.)
简而言之,文学批评虽然不是科学,但也不是文本游戏。
总之,结构主义虽然在许多方面把俄国形式主义所首创的文学科学化构想大大地改造和发展了,但是,这种改造和发展最终暴露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一科学化构想在被不顾一切付诸实施之后,被证明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正如德曼所指出的,“文学性的语言学只能够是一种叙述,一个寓言,一个故事,而不可能是一种科学”;(注:The Resistance to Theory,RT.)而且,“(关于文学的)科学化研究就好像卢梭所说的自然:‘不再存在,或许从未存在过,并且可能永远也不会出现’”。(注:Blindness and Insight,p.171.)
标签:文学论文; 文学批评论文; 结构主义论文; 科学论文; 艺术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读书论文; 符号学论文; 斯特劳斯论文; 神话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