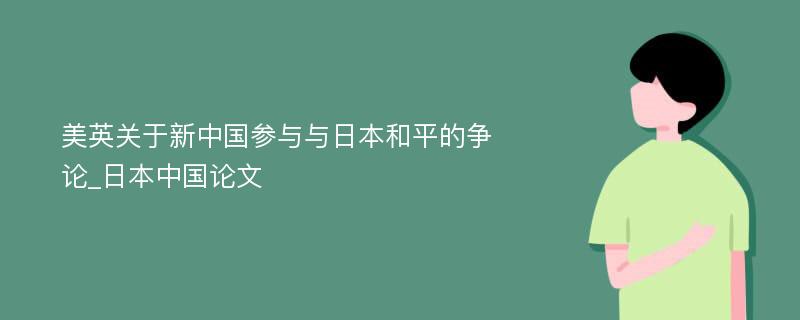
美英在新中国参与对日媾和问题上的争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中国论文,美英论文,对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51年9月4-8日旧金山对日和会召开,包括战败国日本在内的52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会议,而参战最早、付出牺牲最大的对日作战国家中国却被排除在外,最后竟由战败的日本“挑选”了台湾当局作为媾和对象,并与之签订了和约。对于这种被严重扭曲的局面的出现,美英作为旧金山和会的联合发起人当然难辞其咎。然而鲜为人知的是,美英在中国签约权问题上的立场一度严重对立,美国支持台湾当局而英国主张由新中国作为中国合法代表参与媾和谈判。美英之间为此长期争议,龃龉不断。尽管近年来出版的相关著述开始在不同程度上涉及这一问题,但总体上看,国内学术界对美英在中国签约权问题上的争议尚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本文试图对这一论题做初步探讨。
一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华政策走向全面敌视。在对日媾和这个牵动远东、太平洋地区和平与安全的重大问题上,美国更是从遏制中、苏的冷战需要出发,全力支持台湾当局的签约权而阻止新中国参与媾和。美国希望借此不仅斩断日本与中国大陆传统的经济、政治联系,达到既孤立、封锁新中国,防范日本的赤化倾向,又借机将日本的传统贸易对象由中国大陆转向台湾和东南亚地区,将日本纳入美国主导下的西方政治经济体制,同时也解决日本与中国大陆隔绝后的资源供给及商品与投资的市场问题,缓解美国振兴日本经济的后顾之优等多重目的。然而,美国要排斥新中国于对日和约之外难度很大。
首先是绝大多数对日作战国家都反对台湾当局的签约权。这其中不仅有在战后处理战败国问题的处长委员会和远东委员会中拥有否决权的苏联和英国,还有在远东委员会中占多数的其他英联邦成员国和一些西欧国家。所以不论是外长委员会的大国一致还是远东委员会的多数表决程序,对台湾当局都非常不利。对此,美国政府负责对日媾和事务的国务卿特使杜勒斯(John F.Dulles)有非常清醒的认识。早在西方国家尚未就中国签约权问题明确表态之前,他就多次对顾维钧说,尽管“迄今为止,它们还没有提,但我觉得,像英国和印度,它们已经承认了中共政权,肯定会在一定的时候这样做”(注:《顾维钧回忆录》第9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1页。)。实际上,除台湾当局外,远东委员会的12个国家中提出反对台湾当局签约的就有10国之多(注:《顾维钧回忆录》第9卷,第90页。)。然而对美国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英国的态度。因为美国的初衷是排斥中、苏的对日片面媾和,但决不是美日单独媾和。而英国尽管日趋衰落,但“在亚洲问题上,其他一些西欧国家常常指望英国来同美国打交道”(注:威廉·斯塔克:《影响的局限:英国的政策与美国扩大朝鲜战争》(William Stueck,"Limits of Influence:British Policy and American Expansion of the War in Korea"),《太平洋历史评论》(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第55卷,1986年第1期,第66页。),况且在远东委员会中,英联邦成员国就占6个。所以对美国来说,如果英国支持了和约,就意味着远东委员会多数国家支持了和约。
其次是强行中断中日间由来已久的经济联系可能使日本的经济发展受到影响,从而遭到日本的阻挠,美国也将不得不为之承担高额的援助费用。特别因为涉及到英国在东南亚和中国大陆的传统利益,势必招致英国的强烈反对。因此,尽管杜鲁门政府一直担心日本大规模的对华贸易可能最终使其接纳共产党中国,但迟迟未采取断然措施来限制中日间非战略物资的贸易(注:朝鲜战争以前美国对中日贸易的政策考虑在国家安全委员会41号文件(NSC41)中有多处论及,参见: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9)第9卷,华盛顿1974年版,第826-834页。)。
由此可见,美国要在中国签约权问题上贯彻自己的意图决非易事,而两大难题的解决又都与英国直接相关。为解决上述难题,杜勒斯决定在程序问题上做文章。他一方面极力撇开苏联拥有否决权的表决程序,坚决主张对日媾和将在远东委员会范围内,依据多数表决的形式进行并事先获得了英国和台湾当局的认可,同时为回避与远东委员会多数国家,特别是与英国的正面冲突,美国提出媾和谈判将采取与远东委员会成员国进行双边协议而不是所有对日作战国家的多边会议的形式。1950年9月7日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和国防部长约翰逊(Louis Johnson)联名提交给杜鲁门总统批准的备忘录指出,“将由国务院通过外交渠道与远东委员会友好国家进行私下的预备性磋商”(注:《美国对外关系1950年》第6卷,华盛顿1976年版,第1295页。)。杜鲁门总统在签署备忘录后于9月14日正式对外宣布,授权国务院首先开始与远东委员会成员国政府进行非正式磋商,并阐明“在有机会对那些非正式磋商的结果进行评估之前将不会采取正式的行动(注:杜鲁门总统9月14日的新闻发布会,参见《美国总统公共文件集:哈里·杜鲁门1950年》(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Harry S.Truman 1950),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务局1965年版,第637-640页。)。美国政府决定在正式和会之前先行非正式双边外交磋商的主要意图在于避免多边和会可能一开始就在北京中央人民政府还是台湾当局将出席和会的问题上陷于分裂,同时也为了便于美国施展外交手腕,防止联合对美施压局面的出现。更重要的是,美国采取的非正式外交谈判一开始就能起到将新中国排斥在外而将台湾当局延揽其中时效果。杜勒斯曾对顾维钧坦言:安排双边会谈就是为了避免这一棘手而又麻烦的问题(注:《顾维钧回忆录》第9卷,第41页。)。而英国外交部也根据迹象认为美国政府这样做“就能让俄国在他们所期望的范围内活动,并继续撇开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注:H.J.亚塞梅与K.A.汉密尔顿:《英国海外政策文件》(H.J.Yasamee and K.A.Homilton,eds.,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第2系列第4卷,伦敦1991年版,第316页。)。所以,美国官方虽未正式提出台湾当局的签约权问题,但其支持台湾当局的意图不言而喻。
与美国支持台湾当局政权、排斥新中国的立场不同,英国明确坚持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合法签约权。早在1950年5月,英联邦对日和约工作组伦敦会议即已形成共识:远东委员会有代表权的国家都将应邀参加和约起草工作。1951年1月2日英国各部大臣会议提出“在某些阶段,将给予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参与媾和的机会”(注:《英国海外政策文件》第2系列第4卷,第315页。)。这一立场得到了随后召开的英联邦首脑会议的认可(注:《英国海外政策文件》第2系列第4卷,第315页。)。
英国在新中国参与对日媾和问题上与美国所持的不同立场,主要缘于它在远东与美国不同的切身利益与外交思路。
首先,英国远东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是维护与其国内经济恢复和社会稳定至关重要的经济利益。一方面这是由于战后英国国力衰微,不得不进行战线收缩。如在战后英国防御政策与全球战略考虑中,西欧被放在第一位,随后是中东。至于远东,尽管它承认这里是西方全球冷战阵线中的薄弱环节,但英国的现实考虑是不使自己更深地卷入远东事务以免其注意力由西欧转向远东(注:《英国海外政策文件》第2系列第4卷,附录1《参谋部报告:英国防御与全球战略》,第411-43l页。)。这说明英国远东政策中政治与战略考虑的份量下降。另一方面对于以重振经济和实现充分就业为头等大事的工党政府来说,最大限度刺激出口,确保英国在远东的传统海外市场,特别是东南亚和中国的市场,无疑是远东政策的主要目标,因而远东的重要性也最直接地体现在经济方面。而从经济角度来看,如果台湾当局代表中国签订和约,日本将会中断其同中国大陆的贸易,其结果将是日本在美国的帮助下进入英国在东南亚的传统市场以弥补其对中国大陆的损失,日本将在东南亚地区再次同英国竞争。由于日本能向亚洲市场提供更廉价的纺织品和其他产品,英国在这一地区的贸易地位将受到削弱。所以为防止日本进入东南亚市场就需要维持日本与中国大陆的贸易联系。就像艾登所说的“为了贸易的原因……重要的是,不应该让日本跟着别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顽固的敌对态度而使它失去这一出路”(注:安东尼·艾登:《艾登回忆录》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23页。)。另外,英国也非常担心追随美国的反华立场将会使英国在华利益蒙受损失。因为亦如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1号文件(NSC41)所分析的,由于“英国在华有比美国大得多的投资,香港的经济地位也有赖于同中国大陆活跃的转口贸易”,英国的主要考虑将是“保护英国在华利益和香港的地位”(注: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1949》(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9)第9卷,华盛顿1974年版,第828页。)。现实的经济考虑决定了英国对中日关系发展走向的基本立场。
其次,远东对于英国特有的政治意义也迫使其在中日关系问题上必须务实。由于英国远东地位虚弱,英国认为香港地位的稳固,东南亚殖民地利益的维护,离不开强大的新中国政权的友好、合作。同时,英国还必须考虑亚洲新独立国家,特别是印度等已大多承认新中国、主张新中国签约的现实。
再者,尽管从意识形态来说,反苏反共是美英的共性,但英国对中国共产主义的威胁以及中苏关系有着与美国不同的理解。英国并不认为中国会危及其根本利益,即使反共人士如丘吉尔在1952年8月26日也说,“我并不认为中共是一个可怕的敌手,不管怎么说,在随后的四五年内,4亿中国人仍将呆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他们不能靠近我们,除了在东南亚和香港外。”(注:《丘吉尔备忘录》(Minutes by Churchill),1952年8月26日,首相档案:PREM 11/301,原件藏于伦敦公共档案馆(Public Record office London),以下简称“PRO”。)而且英国并不认同美国所坚持的共产主义铁板一块及中国是苏联的卫星国的说法,而坚持认为中国人具有仇外传统,不会更顺从于俄国人的干涉,加之英国一向视中、日为对抗俄国在远东扩张的平衡力量,现在同样希望通过保持中国与西方的接触来离间中苏关系。英国人还认为政治体制的选择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注:《英国海外政策文件集》第2系列第4卷,第424页。)。
最后,在务实的英国决策者看来,国民党已丧失对大陆的控制权,由其签订的和约将难以适用于大陆地区,因而没有实际意义(注:《顾维钧回忆录》第9卷,第81页。)。所有这些因素决定了英国在中国签约权问题上有着与美国不同的考虑。
二
1951年3-4月间,美英在中国签约权问题上的矛盾公开化。3月30日,英国正式提议邀请北京中央人民政府参加对日媾和谈判(注:《美国对外关系,1951年》第6卷,华盛顿1977年版,第952-953页。)。美国得知英国的立场大为恼火。4月6日,杜勒斯召见英国驻美大使弗兰克斯(Olive Franks),抱怨英国在媾和问题上设置障碍,并暗示说他在考虑抛开英国与日本单方面媾和的可能性(注:华盛顿致外交部(Washington to FO),1951年4月6日,外交部档案:FO371/92538/227,PRO。),借以向英国施加压力。4月10日英国还是将这一立场正式通知美国(注:《1951年4月11日,英国外交部关于英国已通知美国认为新中国必须参加对日和约谈判的声明》,《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419页。)。13日美国正式回复英国:美国承认台湾当局,无意与中共讨论对日和约(注:《顾维钧回忆录》第9卷,第66页。)。
面对英国的强硬态度,为打破僵局,杜勒斯决定以退为进,试图通过暂时搁置台湾当局的签约权以换取英国不支持新中国,并准备在6月初访问伦敦,说服英国。6月2日杜勒斯正式开始与英方代表、新任外交大臣莫里森(Herbert Morrison)和外交部国务大臣杨格(Kenneth Younger)等在伦敦进行会谈。双方一开始相持不下。后来英方提出一个折中方案,建议北京中央人民政府、台湾当局都不参与和会,由包括日本在内的2/3多数国家在究竟哪一方代表中国的问题上取得一致时中国再行签约。杜勒斯考虑到远东委员会中有6个英联邦国家,再加上苏联和一些亚洲国家,支持新中国的2/3多数很容易形成,因而表示不能同意该折中方案,并提出双方都参加和会的反建议。英方表示已正式承认新中国,无法接受台湾当局参加和约的提议。这时杜勒斯说出他的真实想法,即他认为惟一可行的是中国不出席9月初的旧金山和会,由日本政府来决定与哪一个中国政府签约(注:《下院会议记录》(Record of Meeting Held in House of Commons),1951年6月5日,外交部档案:FO371/9225/513,PRO。)。6月6日,莫里森最后同意了杜勒斯的建议。
然而莫里森与杜勒斯达成的妥协方案在6月7日提交英国内阁审议时未获通过。内阁认为美国监护下的日本只会屈从于美国的意志而与台湾当局谈判签约(注:《内阁备忘录》(Cabinet Minutes),1951年6月7日,CM41(51),PRO。)。8日,莫里森只得再见杜勒斯,向他解释内阁的态度,即英国接受杜勒斯提议的双方都不参加的立场,但要求附加一条,就是如果没有主要成员国2/3多数的同意,任何一个中国政府都不能参加和约。杜勒斯以这种附加条款会损害日本主权为由加以反对,并安抚英国人说日本不可能与台湾当局签约。同时也暗示他不愿接受超出美国国内政治容忍限度的提案(注:《外交部会议记录》(Record of Meeting Held in Foreign Office),1951年6月8日,外交部档案:FO371/92556/547,PRO。),之后杜勒斯终止伦敦之行前往巴黎,临行前对艾德礼表示,如果英国内阁不同意杜勒斯—莫里森协议,他将不再返回伦敦。迫于压力,11日的英国内阁会议投票通过了4天前被其否决的杜勒斯—莫里森协议。19日以英美联合备忘录的形式形成的杜勒斯—莫里森协议载明:任何一个中国政府都不参加多边和会,日本未来对华态度将由日本自己依据和约所赋予的主权和独立的地位来确定(注:《美国对外关系,1951年》第6卷,第1134页。)。美英围绕中国签约权问题的纷争暂时告一段落。
杜勒斯从伦敦返回后,紧急拜会了共和党加利福尼亚议员诺兰(William Knowland)及其他一些亲蒋人士,消除了因为置台湾当局于对日和会之外可能引起的美国国会内亲蒋人士的不满。然后频繁会见台湾当局“驻美大使”顾维钧,迫使台湾当局接受了被排斥于和会之外的现实而寄望于美国压服日本选择与台湾当局谈判。这样美国对日片面媾和的主要障碍得以排除。1951年9月4-8日,旧金山对日和会召开。中国大陆和台湾方面均未与会。尽管有苏联、东欧国家的强烈反对及一些亚洲国家的抵制,片面的旧金山对日和约还是按照美英等西方国家既定的程序顺利签署。
三
旧金山会议后,美英关于中国签约权问题的争议转向对杜勒斯—莫里森协议的理解和执行上。杜勒斯坚持认为旧金山和约一经签署,日本便成为“自主和独立”的国家,有权做出与哪一方签约的选择。由于他非常清楚,如果放手让日本选择,日本不会选择国民党政府,而且英国人还暗中寄希望能改变日本的态度,力促其与北京签约。如果得不到日本与台湾签约的保证,参议院的亲蒋势力不会让和约生效。所以杜勒斯希望日本与台湾立即开始媾和。而英国内阁接受杜勒斯—莫里森协议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的高压,另一方面也是心存侥幸,以为凭借英国的影响力,特别是日本与中国大陆的利益关系,可能会使日本至少与大陆和台湾保持等距离接触,而不是像美国所期望的那样,完全倒向台湾一边。所以杜勒斯—莫里森协议后,英国外交努力的重点是要求美国恪守杜勒斯—莫里森协议,即在和约生效之前,日本不得做出任何决定,直到它有充分的自由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与北京中央人民政府或台湾当局签约(注:《顾维钧回忆录》第9卷,第275页。)。实际上英国希望日本会自主选择与新中国签约。所以莫里森一再告诫杜勒斯,杜勒斯—莫里森协议意味着在和约生效以前不要有任何使日本对华政策明确化的行为(注: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1951年》第6卷,第1343-1344页。)。
9月12日,以诺兰为首的56个参议员写信给杜鲁门总统,宣称,“日本承认中共或与中共进行双边谈判即是对日本和美国人民利益的背叛。”(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1951年9月13日;《顾维钧回忆录》第9卷,第244页。)10月,英国外交部公认的日本问题专家,已长期参与媾和决策的埃斯勒·丹尼(Sir Esler Dening)前往东京,主持英国驻日本联络代表处的工作。丹尼此时赴任,旨在加强英国对日本的影响力。而此时日本政府的态度也捉摸不定。10-11月间,吉田茂相继发表了几次令美国人大为不安的演说(注:吉田茂告诉日本国会说,他正考虑在上海设立一个日本海外代理机构。他还几次宣布要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上采取“等着瞧”的政策。参见《美国对外关系,1951年》第6卷,第1389页。),而对与台湾当局的谈判则表现得相当冷淡。杜勒斯认为必须采取果断行动迫使日本对美国所期望的对中国政策做出正式、明确的承诺,以确保和约在参议院顺利通过,而日本态度的摇摆同英国的影响分不开。于是他双管齐下,一是着力于迫使已日益滑向等距离外交的吉田回到美国指定的路线,二是力争英国在对华问题上接受美国的立场。
11月13-14日,美英在伦敦举行了旨在协调日本对华政策的会议。代表美国出席会议的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麦钱特(Livingston Merchant)强调指出,如果日本不在几周内表明它将与台北建立某种合理关系的意图,和约将不能在参议院通过。他希望英国支持其关于杜勒斯—莫里森协议的灵活解释。会议形成的备忘录鉴于日本调整其与台湾当局关系的重要性,双方不反对日本为此在和约生效前与台湾当局进行预备性会谈(注:《1951年11月13-14日在外交部举行的关于日本与未来福摩萨关系的会议记要》(Summary Record of Meeting Held at Foreign Office on 13-4,Nov.1951 to Discuss Japan Future Relations with Formosa),外交部档案:FO371/92604,转引自细谷千博:《日本、中国、美国和英国和〈吉田书简〉的真相》,《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第60卷,1984年第2期,第253页。)。但英国驻日代表丹尼怀疑杜勒斯会随意解释调整与台湾当局的关系,并诱使日本同国民党签署一个实质性协议,于是将这种疑虑告诉了当时正出席巴黎外长会议的外交大臣艾登。艾登立即向艾奇逊表明他将继续遵循前工党内阁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反对日本在和约生效之前与台湾当局谈判。艾奇逊要求艾登重新考虑一下,艾登以议会将不会接受任何与杜勒斯—莫里森协议不符的动议为由加以拒绝。双方协商陷入僵局(注:转引自细谷千博:《日本、中国、美国和英国和〈吉田书简〉的真相》,《国际事务》第60卷,1984年第2期,第253页。)。
12月初,英国议会批准了对日和约。杜勒斯认为向英、日摊牌的时机成熟。13日杜勒斯和吉田茂会谈,要求日本尽快与台湾当局和谈,以便在对日多边条约生效时日台双边条约也能生效(注: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1951》第6卷,第1437-1438页。)。吉田茂没有公开反对,但表示,如果英国强烈反对,日本不愿采取这一举动,理由是“面对自由世界两大强国意见相左时,日本不知如何是好”,还说通过增加日本与大陆的贸易,可以促进中国松驰与苏联集团的关系(注: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1951》第6卷,第1438-1439页。)。然而杜勒斯不由分说,他明确告诉吉田,美国比英国更强有力,能给日本更多经济和安全的帮助。既然日本在缔约过程中已选择了与西方合作,就当接受美国关于台湾问题的安排(注:翟强:《龙、狮、鹰;1949-1958年的中、英、美关系》(Qiang Zhai,The Dragon,the Lion,the Eagle;Chinese/British/American Relations,1949-58),美国肯特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0-111页。)。在吉田—杜勒斯会谈的同时,杜勒斯和丹尼之间也在会谈。但此时双方谈拢的可能性很小,因为艾登已于12月8日明确指示丹尼,“坚决反对日本和蒋介石之间任何具有和约性质的东西”(注:转引自细谷千博:《日本、中国、美国和英国和〈吉田书简〉的真相》,《国际事务》第60卷,1984年第2期,第255页。)。而杜勒斯也不打算让步,他觉得“美国人能让日本人作美国人想让他们做的事情。因为他们有着比英国人手中更多的牌”(注:转引自细谷千博:《日本、中国、美国和英国和〈吉田书简〉的真相》,《国际事务》第60卷,1984年第2期,第256页。)。结果,17日的美英会谈不欢而散。
英、日的态度令杜勒斯非常恼火。他决定采取强制措施迫使日本就范。18日,杜勒斯再次会晤吉田茂,并将事先拟好的一份以日本首相的名义起草的备忘录交给吉田茂,要他签字后寄给杜勒斯。其主要内容是日本政府准备从法律意义上尽快依照多边协议所确定的原则与台湾当局签订双边条约。这个双边条约的条款将运用于那些现在或将来可能处于在日本和台湾当局实际控制之下的地域。日本政府保证无意与中国共产党政权缔结双边条约(注: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1951》第6卷,第1445-1466页。)。在美国的高压之下,吉田茂签署了这份出自杜勒斯之手的信件,并于12月24日将信寄到了华盛顿。这就是著名的“吉田书简”。
杜勒斯收到“吉田书简”后并未马上对外公布,意在等待1952年1月初美英首脑的华盛顿会晤能说服英国人改变立场。1月10日双方进行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会谈。当时以艾奇逊和杜勒斯为一方,艾登和弗兰克斯为另一方。尽管杜勒斯和艾奇逊轮番劝说英国接受美国的立场,并暗示美国已收到日本首相阐明日本政府意图的信息,但艾登始终坚持在多边协议生效之前,最好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说。一定要问他什么意见,他将不得不说他的观点没有改变,而且美国人也知道他的看法。他还提到他已得到日本在对日和约生效之前将不会采取一个最终的行动来与中国缔结条约保证。鉴于艾登不可动摇的立场,艾奇逊最后提出,如果吉田问及英国对日台谈判的立场时,他希望丹尼能够对吉田表示,尽管美英各自保留自己的看法,但对此没有异议。艾登表示为难,理由是艾奇逊提出的立场超过了艾登所打算迈出的步子(注:《艾登与艾奇逊1952年1月10日关于中日关系问题华盛顿会谈记录》("Conversation between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nd Mr.Acheson in Washington on 10 th Jan.1952"),《艾登私人文件》(The Private Papers of Sir Anthony Eden),FO800/781,FE/52/5,藏于英国伯明翰大学图书馆物特藏室(下略)。)。这样,美国希望华盛顿会谈能改变英国立场的希望落空。1月16日,在艾登离开华盛顿返抵伦敦的当日,美国对外公布了“吉田书简”。
“吉田书简”是在艾登既不知道信的内容,又不知道公布时间的情况下面世的,而这种时间上的选择给人的印象是艾登可能已认可美国对杜勒斯—莫里森协议的修改,这使艾登非常被动和气愤。尽管艾奇逊去信表示歉意,并说明他们这样做并非有意。但双方的芥蒂并未消除。1月17日艾登还念念不忘告诫丘吉尔在就中日关系问题发表演说时,“应考虑这一令人生厌的发展事态,避免造成任何这样的印象,就是我们认同了已经发生的事情”(注:《艾登1952年1月17日给丘吉尔的私人信件》("Personal for Prime Minister from Secretary of State"),《艾登私人文件》,FO800/781,FE/52/6。)。不过,事已至此,艾登已回天乏术,因为英国议会已审议通过旧金山和约;丘吉尔又建议英国政府接受日本承认台湾当局的事实,只要他们的声明不包括中国大陆(注:《丘吉尔致艾登1952年1月6日》("letter from Churchill to Eden"),《艾登私人文件》,FO800/781,FE/52/4。);而美国在对日媾和的问题上对英国做出了一定的让步使英国的立场也有所软化。2月20日,日台双边谈判在台北开始。3月20日,对日和约以66∶10的压倒多数在美国参议院获得通过而最终完成了它的法定程序。4月28日,在旧金山和约正式生效之前的7小时,日本政府与台湾签署了日台条约。这样,一直悬而未决的中日媾和问题终以非法的日台和约而收场。这种结局也表明英国在新中国签约权问题上试图影响美国的努力最终失败。
四
表面上看,美英两个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远东冷战正酣之际为新中国的签约权问题发生如此长期、激烈的争议,似乎不可思议。但前文的分析表明,围绕中国签约权问题的争议首先直接涉及美英在远东的利害冲突。美国希望通过排除新中国参与对日媾和,既切断日本与中国大陆的一切联系,并将日本纳入美国设计的对华遏制体制,又借此使台湾和东南亚地区成为日本廉价的原料供给地和商品倾销市场,从而有效贯彻自己的远东战略。而英国恰恰相反,它希望通过维持中国大陆与日本的传统联系,保住英国在远东的既得利益:确保英国在中国大陆的巨大商业利益及香港、马来亚等殖民地的稳定,防止日本的经济势力进入东南亚市场,同时也希望借此保持中国与西方世界的接触,以离间中苏和赢得亚洲新独立国家的好感。其二,这种争议也反映了美英对远东和世界政治的不同理解。有着均势传统并以务实见长的英国外交,在战后远东政治棋盘中,希望北京中央人民政府和日本之间关系的发展会鼓励中国独立于苏联之外。在对华问题上,日趋衰落的英国基于现实的态度,寄希望于与新政权的友好来保住既得利益。而有着强烈理想主义色彩的美国外交严格以冷战思维来对待中日关系。对于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财大气粗的头号资本主义国家企图凭借实力,通过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打压来强行贯彻自己的意志。所以美国信奉的是联合该地区非共产党国家来反对“铁板一块的中苏共产主义集团”的外交思路。围绕中国签约权问题的分歧实际上反映美英两国在远东的利害冲突及现实处境,也映射出两国外交的不同理念与方式。
关于英国在中国签约权问题上的立场,有学者认为,英国从来没有幻想美国会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对日和约,但这是“一个很好的讨价还价的筹码”(注:霍华德·舍恩伯格:《缔造亚洲和平:美、英与日本决定承认国民党中国,1951-1952》(Howard Schonberger,"Peacemaking in Asia:The United States,Great Britain and Japanese Decision to Recognize National China,1951-1952"),《外交史》(Diplomatic History)第10卷,1986年第1期,第64页。)。但笔者认为,英国有希望新中国参加对日和约的真实动机,一则这关系到英国在远东的根本利益,事实上英国也为新中国的签约权与美国进行过长期抗争;二则这与英国在承认新中国以后的一贯立场相符。尽管英国在新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台湾归还中国等问题上显得摇摆不定,但毕竟英国不像美国,它没有因为在中国内战问题上的过深卷入而出现的感情用事及受国内强烈反共因素的掣肘而严重敌视中共政权,所以英国对华政策基本务实。英国也的确在这些方面进行过一些积极的努力,尽管最终的结局都基本上屈从美国的立场;三则这种考虑也合乎英国外交的基本思路。尽管战后英国失去了在世界事务中的大部分实力和影响,但英国仍是除美苏之外的第三大强国,特别是英国曾支配世界达两个世纪,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与世界许多地区建立了联系。英国人非常看重他们的外交经验及其与海外的传统联系,并认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国家能够替代英国的作用:“苏联人太遭人恨,美国人仍不够成熟”(注:迈克尔·多克莱尔和约翰·W·扬:《1945-1956年的英国外交政策》(Michael Dockrill and John W.Young,British Foreign Policy:1945-1956),伦敦1989年版,第2-3页。)。而抑制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极端行为是战后英国外交的基本目标。如外交部常务次官斯特朗(William Strang)说过,“我们要不失时机地与美国讨论一些特别行动……只有通过我们的行动与他们的行动的合作,我们才能希望……去抑制美国方面的那些我们看来是过激的行动。”(注:转引自约翰·W·扬主编:《1951-1955年丘吉尔和平时期政府的外交》(John W.Young,Foreign Policy of Chuichill's Peacetime Administration:1951-1955)》,莱斯特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7页。)工党时期的外交“所应做的是对善意的但缺乏经验的巨人的政策施加有效的控制,我们的安全有赖于它的合作”(注:转引自里奇·奥文多:《20世纪英美关系》(Ritchie Ovendale,Anglo-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伦敦1998版,第61页。)。丘吉尔政府对美关系的基本目标也是尽可能充分地协商;抑制美国政策中的一些极端行为并指导美国外交朝向适宜于英国利益的方向发展(注:约翰·W·扬主编:《1951-1955年丘吉尔和平时期政府的外交》,第31页。)。由此可见,英国在支持中国的签约权问题上应该说是富有诚意的,并为此进行过抗争。
而在笔者看来,英国往往从一开始的坚决立场不断后退而最终屈从美国的根本原因除了人们通常提及的冷战环境的制约外,还在于美英特殊关系中英国地位的虚弱,在于英国务实外交的基本属性,同时也在于战后英国外交战略的基础与背景已同当初英国称雄世界时的情形殊异,等等。
其一,受制于有限的资源,英国急需借重美国来捍卫其安全、重振其经济和维护其在世界各地的利益和影响。这在战后英国重新审定全球战略中起过关键作用的斯特朗常务次官委员会的一份提案中得到充分反映。该提案指出,英联邦、西欧本身,甚至是英联邦加上西欧都不足以在经济或军事上强大到可以独立应对反对他们的力量,美国的全面参与对自由世界的生存至关重要。1949年底英国政府接受了斯特朗委员会的结论,即英美在世界事务中的密切合作将继续下去,这样一种合作将涉及英国实际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努力(注:里奇·奥文多:《20世纪英美关系》,第61页。)。此后,英美合作一直是英国外交的基础。而实际上,华盛顿企图把英国在亚洲事务中的作用减少到最低限度——只征求英国对美国政治策略的默许或支持,但不承认英国是独立的决策角色(注:唐耐心:《艰难的抉择——美国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的争论(1949-1950)》,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页。)。结果正如有的西方学者所说的40年代末以来发展起来的英美关系的基本特征,从根本上讲,就是“英国需要美国的保护,美国需要英国在遏制苏联的问题上充当一个基本的、级别较低的角色”(注:约翰·W·扬主编:《1951-1955年丘吉尔和平时期政府的外交》,第51页。)。这样一种处境极大地限制了英国独立决策能力及回旋的余地。
其二,对于以务实著称的英国外交来说,尽管中日关系的发展走向对英国有着特殊意义,但其重要性毕竟无法同美英关系相比。当发现不可能在中英关系和扭转美国的立场方面有所作为时,他们又很容易走向接受现实。如在1951年底,尽管外交大臣艾登强烈抵制美国的行为,但其上司和下属都主张迁就美国的立场。因为对丘吉尔来说,维持与华盛顿的密切关系是英国保守党外交政策的头等大事,因而在1952年1月的华盛顿会谈期间,当艾登试图说服丘吉尔,“如果我们不能在远东给美国更多的帮助,我想我们能在欧洲给美国一些安慰”(注:《艾登私人文件》,FO800/781,FE/52/3。)时,丘吉尔却主张:“在远东,由于美国承担了绝大部分(19/20)的负担和损失,当然会要求相应的领导地位,我们要让他们觉得我们接受这种事实。……我们将默认日本承认国民党政权,只要它表明这不包括中国大陆。……重要的是要让他们感觉到在远东我们真心追随他们。”(注:《艾登私人文件》,FO800/781,FE/52/4,P.M./52/3。)日本和太平洋部的负责人罗伯特·斯克特(Robert Scott)也建议英国支持非共产党的台湾可能会有助于美英关系的和谐(注:《斯克特备忘录》(Minute by R.Scott),1951年12月28日,外交部档案:FO371/99403/14,PRO。)。
其三,英国一开始态度坚定而后动摇的另一重要原因是英联邦在美国威逼利诱下立场的改变。美国重视英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英国在英联邦中的重要地位。但实际上自二战以后,英国对殖民地、自治领地的控制、影响力大为降低。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美国的影响下,老的自治领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等都在政治、军事关系方面各行其是。最明显的转变是1951年的美澳新条约,借此美国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防务方面接替了英国的地位。澳、新两国因之更加靠近美国。英联邦统一的外交难以为继。英联邦立场在1951年前后发生变化正是美国一开始不敢忽视英国的意见到后来公然藐视英国反对的原因之一。
最后,二战后英国的实力地位及其实施传统外交的背景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首先是英国与美苏距离的拉大。丘吉尔早在战争期间就曾自喻英国是夹在巨大的俄国熊和北美野牛之间的一头可怜的小毛驴。而在战后美苏势力急剧扩张后英国更显单薄。其二是战后世界发生了历史性巨变,如欧洲中心地位的衰落,民族主义的兴起,共产主义的壮大,这些注定了战后英国所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国际环境。实力的不足与国际社会具有独立意识的行为主体增多,矛盾冲突又前所未有的复杂多变,这些不仅使英国很难维持英联邦内部的统一,更不可能像原先在欧洲国家中起平衡作用那样在美苏两极尖锐对抗的情势下影响美、苏、中、日及其许多亚洲新独立国家的外交政策走向,从而使得曾经在欧洲中心体制下起主宰作用的英国外交力不从心;曾经屡试不爽的外交经验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已很难奏效。
总之,冷战大环境、英国全球地位的削弱及其对美国经济援助的依赖无疑是英国未能在中国签约权问题上坚持立场并无法阻止美国的一意孤行的根本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英国最终屈从于美国的压力在所难免。然而,美英在中国签约权问题上的分歧,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英美特殊关系的脆弱性。它也揭示出即使在冷战背景下,国家利益和历史传统在一国外交中仍发挥重要的影响,因而以意识形态划线或先入为主地评判一国外交难免失之偏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