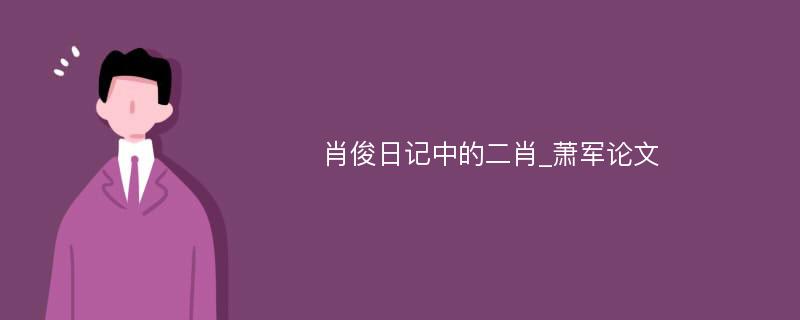
萧军日记里的二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记论文,萧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1932年7月至1938年4月,萧红和萧军共同生活了差不多六年时间。二萧“浪漫”的结合,富有传奇色彩的成名以及让人扼腕的劳燕分飞,至今仍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萧红的人生经历被一再叙述,初步统计,其传记多达60余种。拘囿于能够见到的材料,以往人们对于二萧分手前的情感状态,很大程度上充满想象与讹传。近年,《萧军全集》公布了1937年5月4日至1942年底的部分日记。1937年4月23日前后,萧红结束当年1月为抚平萧军1936年上半年的情感出轨而带来的情感创痛的东京之旅不久,因不堪再次面对对方更为严重的情感出轨,独自离沪北上,开始又一次疗治心灵之伤的旅行。在萧红传记研究上,二萧平沪间往还的书信(萧红自北平致上海七通,萧军上海致北平四通)素来被人忽视或误解,但却是了解萧红从日本归国后情感波动及思想变化的重要文献。参照此期及以后的萧军日记,则更有助于揭示二萧真实的情感世界,为今人理性认知二萧的最终分手,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无论东渡扶桑,还是北上北平,萧红作为女性之“弱”在于,萧军与陈涓、许粤华等的情感纠葛,不仅给她带来心灵巨创,更扰乱了她作为一个痴迷于创作的作家的生活方式。对她来说,这是非常无情的双重困扰和折磨。每一次逃离是追求“眼不见为净”的自我麻痹;而更主要的是为寻得一个安宁心境的处所,进入写作状态,以达到对现实的暂时忘记。因而,无论东京还是北平,对于萧红来说是逃离更是找寻,伤痛和焦虑始终伴随着她。1937年5月3日在致萧军的第三封信里,她自述,“心情又和在日本差不多,虽然有两个熟人,也还是差不多”,同时更加明确地意识到:“我一定应该工作的,工作起来,就一切充实了”。[1](P115)
收读前两信后,萧军于5月2日回信提及,送萧红北上当晚回家,日记里记下当时心情:“她走了!送她回来,我看着那空旷的床,我要哭,但是没有泪,我知道,世界上只有她才是真正爱我的人。但是她走了!”[1](P136)对比晚年萧军对萧红北上缘起的讳饰(如为了访友、怀旧),青年萧军当时的回信,坦率说出了其内心的愧疚,以及对萧红情感世界的真切感知。他也谈到自身心境烦乱,还有无法开始工作的焦虑。
也许,二萧同在上海期间,萧红无法当面向萧军直陈内心的伤痛。一旦时空间隔,萧红再次独自面对自我,终于有机会通过纸笔向对方倾诉。5月4日第四封信基本上没有了前三封信里的寒暄,直接表达内心苦痛的深巨。这在二萧往来书信中实属罕见:
我虽写信并不写什么痛苦字眼,说话也尽是欢乐的话语,但我的心就像被浸在毒汁里那么黑暗,浸得久了,或者我的心会被淹死的,我知道这是不对,我时时在批判着自己,但这是情感,我批判不了,我知道炎暑是并不长久的,过了炎暑大概就可以来了秋凉。但明明是知道,明明又做不到。正在口渴的那一刹,觉得口渴那个真理,就是世界上顶高的真理。
这回的心情还不比去日本的心情,什么能救了我呀!上帝!什么能救了我呀!我一定要用那只曾经把我建设起来的那只手把自己来打碎吗?[1](P116-118)
很显然,萧红让长久以来郁积的隐痛,有了一次痛快“说”出的机会,文字因情感起伏而错落有致,但是痛诉里亦充满理性,不再如此前组诗《苦杯》或《沙粒》那般哀怨。这封信是她与自身拉开距离之后的深刻观照。某种意义上,痛苦让萧红对自己甚至女性的命运有了更深切的认知。这封信似乎成为逼着晚年萧军无法回避萧红痛苦呼号的根源。1978年9月19日,他注释此信时坦承自己爱情上对萧红曾有“不忠实”发生:“那是她在日本期间,由于某种偶然的际遇,我曾经和某君有过一段短时期感情上的纠葛——所谓‘恋爱’……”[1](P119-120)他对因此给萧红带去的“刺痛”引为终身遗憾,但随即还是极力对几十年前的逝者,尽可能保持那份道德优胜:“除此以外,我对于她再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地方:——对于她凡属我能尽心尽力的全尽过所有的心和力了!”[1](P120)人之晚年,似乎恩怨早该平淡,但萧军却仍力图从有限的自责中,尽力找到对于萧红的道德优胜,从而达到心理平衡。
晚年萧军所谓与某君“恋爱”,虽发生于萧红旅日期间,但后续影响却持续于萧红返沪后很长时间之内。自东京返沪,二萧的生活、写作都陷于巨大混乱,萧红再次离沪其实是他们力图重新厘清头绪、调整生活的努力。作为无辜者,如果说萧红此时是独自品尝伤痛的话,那么,作为当事人的萧军,则再次陷于“失恋”的苦痛。1937年5月4日萧军日记载有,头天许广平劝其珍惜才华,“不要为了爱就害了自己”,应该“把失恋的痛苦放到工作方面去”。对于许的劝告,他亦坦率相告:“我但愿自己渐渐就会好起来的,不过,自己总是不能把握自己的热情……”[2](P8)为了让自己早日超离“失恋”的痛苦和人事纠缠,萧军5月5日日记载有其自创的摆脱痛苦的方法:每日晨起告诫自己要“健康”、“安宁”、“快乐”。而正在阅读《安娜·卡列尼娜》的他,次日更反省到自己“不适于做一个丈夫,却应该永久做个情人”[2](P10)。6日,他回复一封长信,将自己所认为的作为一个作家如何面对生活中的情感变故的态度,介绍给萧红:
我现在的感情虽然很不好,但是我们正应该珍惜它们,这是给与我们从事艺术的人很宝贵的贡献。从这里我们会理解人类心理变化真正的过程!我希望你也要在这时机好好分析它,承受它,获得它的给与,或是把它们逐日逐时地纪录下来。这是有用的。[1](P140)
这段规训意味浓郁的文字,居高临下地传达出一个极其怪异的逻辑:规训者的情感出轨,对于被规训者同时也是无辜受伤者及他自己这种“从事艺术的人”,都是一种很有益的经验,应该坦然接受并“好好分析”。命令的语气(“好好分析”、“逐日逐时”还带有着重号)和霸道的逻辑,自然让萧红难以接受。这一方面归之于萧军成名后的狂妄、自恋;另一方面,又源于二萧结合之初,他当年对张廼莹那“爱的哲学”的告知。
萧军此时的自恋之态常流露于日记:5月15日,他首先对萧红作出一种居高临下的判断,认为她“是一个不能创造自己生活环境的人,而自尊心很强,这样人将要痛苦一生”;接着更有一段对镜自怜:“我有真挚的深厚的诗人的热情,这使我欢喜,也是我苦痛的根源。晨间在镜子,看到自己的面容,很美丽,更是那两条迷人的唇……清澈的眼睛,不染半点俗气,那时我的心胸也正澄清。”[2](P13)所谓“真挚的深厚的诗人的热情”,应该是他常常情感出轨的根源所在。可见,青年萧军将自己的多情视为可炫耀的浪漫。渐近中年,其心态或许有所变化,1941年4月身在延安的萧军,听说黄源死于“皖南事变”,心有所感地在26日的日记里写道:“听说黄源在乱军中死了!不知道是否真确。我对他是抱着终身歉疚的。”[2](P417)正因狂妄与自恋,萧军无从体察自己给萧红带去的到底是什么。6日信中,在大段规训之后,还有类似“领导视察工作”般的指示:“注意,现在安下心好好工作罢,那时(指大约两个月后萧军自己也来北平——论者注)我要看您的成绩咧!”
5月9日在对萧军6日信进行回复之前,萧红述及收读对方两信哭了两回,6日自己也有一封信,只是因为流着眼泪写的没有寄出,怕自己的恶劣心绪影响对方。然而,等到情绪稍稍平复回复萧军,此信却是另番滋味。对方的规训、命令,令其大为反感。对于萧军所谓每天看天一小时变成美人的建议,她不无讥讽地回应道:“这个是办不到的,说起来很伤心,我自幼就喜欢看天,一直看到现在还是喜欢看,但我并没有变成美人,若是真是,我又何能东西奔波呢?可见美人自有美人在。”[1](P121)而对那即将视察其长篇创作计划的“命令”,萧红更是将新旧账算在一起反唇相讥道:
我的长篇并没有计划,但此时我并不过于自责。“为了恋爱,而忘掉了人民,女人的性格啊!自私啊!”从前,我也这样想,可是现在我不了,因为我看见男子为了并不值得爱的女子,不但忘了人民,而且忘了性命。何况我还没有忘了性命,就是忘性命也是值得呀!在人生的路上,总算有一个时期在我的脚迹旁边,也踏着他的脚迹。总算两个灵魂和两根琴弦似的互相调谐过。[1](P121)
据书信原件,萧红将最末一句划掉了,并在旁边注明:“这一句似乎有点特别高攀,故涂去。”[1](P122)在日本期间,萧红读到萧军小说《为了爱的缘故》引起不快。在那部关于二萧结合之初的自传性的小说里,萧军所传达的宏大而庄严的理想,让他自己即便卑怯的行为也变得无比冠冕;现如今,萧红似乎看穿了他那在革命、女色面前所表现出的空洞与虚伪。很显然,经历此前种种,萧红对萧军已然拥有另一层面的认知。这封信显然伤及萧军的骄傲,萧红的话真切戳到其痛处,令他不知如何回复。于是,13日日记载有:“昨晚吟有信来,语多哀怨,我即刻去信,要她回来。”[2](P13)萧军令萧红返沪的信只有寥寥数语,诸如“见信后,束装来沪”,原因是他“近几夜睡眠又不甚好,恐又要旧病复发”;并说“本欲拍电给你,怕你吃惊,故仍写信”。[1](P146)这显然是萧军急令萧红返沪而编造的借口,6日信中他还叮嘱萧红租房,两人准备在北平过冬。
萧军骄傲而难有自责并非偶然。这出于他对“情”与“欲”的认知。1937年5月11日,他在日记里认识到“获得‘性’是容易的,获得爱情是艰难的。我宁可做个失败的情人,占有她的灵魂,却不乐意做个胜利的丈夫……”[2](P12)正如前文他对自己所谓的“热情”的认知,可以肯定的是,当时,他对于自己的情感出轨给他人所带来的苦痛的认识,亦非常有限。这自然让他不可能从萧红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作为。正因如此,他回复萧红5月4日那封充满痛苦呼告的来信,更充斥居高临下的规训。信头由惯常的“吟”一变而为“孩子”。或许在他眼中,萧红永远只是一个需要庇护的“孩子”,眼下责任就是开出一个让她脱离痛苦的处方。在他,处方似乎早就有了,所以开头一段就自信地写道:“收到这封信——我想你的情绪一定会好一些。”[1](P142)而“处方”很简单,就是勇敢面对。相对于前信,此信的规训意味更加明显,满篇都是诸如“应该”、“不要”、“希望”、“要”之类带有命令语气的词汇,道理却极其宏大、空洞。收读这样的回信,萧红或许更加意识到在一个如此自恋的男人面前,已经无法达成真正的沟通。她所等待的,或许只是对方一声发自内心的道歉。但萧军此时没有这个意识,骄傲如他,“道歉”不在他的词典里。萧红也就觉得跟这样的男人说出更多真实所想也没有意义。5月15日,针对萧军的长信,她只作了一个极简短的回复,对萧军那热烈而庄严的规劝,冷淡回应道:“我很赞成,你说的是道理,我应该去照做。”[1](P125)不过,晚年萧军注释说,这不过是萧红的“反话”。
然而,多年来,在萧红传记研究中,人们往往自觉不自觉站在萧军立场上来理解萧红。即便对萧军此信的解读亦是如此,无视二萧平沪书信往还的大语境,甚至对萧军的注释也不在意。丁言昭认为萧军这封信“写得有情有理有节,任何人看了都会动心,因此萧红收到这封‘规劝的信’,说:‘我很赞成’,你说的是道理,我应该去照做”[3](P158)。季红真更认为:“萧军的这封信既诚恳地承认了自己的过失,也坦然地表达了对萧红情感的看法,重修旧好的愿望是明显的。萧红收到他的信以后,情绪有了好转:‘我很赞成,你说的是道理,我应该去照做’。”[4](P279)两位萧红传记作者之所以出现纰漏,除了对材料语境的疏忽之外,还与对萧红此时思想状态的认知不足有关。很显然,如此回应萧军,源于萧红独处东京的历练与女性意识的生成。某种意义上,萧军霸道的逻辑和居高临下的规训早已令其厌烦,她在寻求人格独立。或许,她由此看到在狂妄、自恋的萧军面前,与之心灵通约的不可能。一年后,二萧的分手自是必然。
一次别离确乎是二萧常常用以处理情感隔膜貌似有效的方式。萧军日记1937年5月22日开头载有:“吟回来了,我们将要开始了一个新的生活。”[2](P14)在日记里,萧军亦多有对自己待人接物的反省。6月2日悟出“思而后做,多是不悔”,“做而后思,多是后悔”,而他常犯第二种毛病,萧红与之却恰成对比。[2](P15)无论青年萧军在书信中、中年萧军在日记里,抑或晚年萧军在书信注释间,一向少有对萧红的正面评价。6月2日,认识到萧红在待人处事上优于自己,可能基于一种特殊情境令其激发出对萧红的爱意,以及在情感上的回归。随即,他还表达了对未来爱情的不渝:“我现在要和吟走着这一段路,我们不能分别。”[2](P16)可见,萧红自平返沪正如俗说“小别胜新婚”,二萧都有一段情感上的新鲜感,激发出彼此间的爱恋,企图抹平此前的情感裂痕。
从萧军日记来看,二萧间的“和谐”似乎只维持至6月12日左右。萧军曾将与萧红的关系,比喻成两个刺猬在一起:“太靠近了,就要彼此刺得发痛;远了又感到孤独。”[1](P25)这或许是晚年萧军事后对与萧红相处较为理性的看待。本质上,萧红、萧军都是个性鲜明、充分尊重自身人格取向的人。萧红骨子里极其不愿成为男性的附庸。当活着为生存第一要义的时候,这一切也许无从体现;而当他们各自追求自己的发展空间时,人格取向和艺术取向上的差异自然凸显。这或许就是二萧何以能够度过艰难的商市街岁月,恰恰成名之后劳燕分飞的深层原因。在我看来,成名后二萧间最为根本的矛盾,除萧军的情感出轨外,还在于他自认为对萧红的救赎,始终将她当作一个“孩子”,一如导师般指导其人生,而不知道这个“孩子”在拜其所赐的苦难中早已长大。
1937年6月13日萧军日记有一段对自己帮助他人心理的剖析:“一个人对旁人有过一下援助,如果被援助者反叛的时候,就要感到失望,伤心……接着就有一种‘再也不援助任何人’的心理决定。可是过了不久,这决定又破碎了,又形成了……我是在这矛盾里常常苦痛着。”[2](P20)这段话自然是有感而发,或许不只是针对萧红。但是毫无疑问,由一个落难旅馆险些被卖到妓院的潦倒女子到如今的知名女作家,在萧军看来,萧红自然是其援助的最大受益者,某种意义上是他创造的一个救赎“奇迹”。而“被援助者反叛”明显暗示萧红此期对其说教生出的叛逆与冲撞。联系二萧当时的关系,分析其语境,这段话分明有所指。更重要的是,萧军还是将自己与萧红很自然地放在援助者与被援助者的位置上进行道德衡量,其内心那份道德优胜实在太过分明。紧接着,当天日记便重新观照自己与萧红的关系:
我和吟的爱情如今是建筑在工作关系上了。她是透明的,而不是伟大的,无论人或文。
我应该尽可能使她按照她的长处长成,尽可能消灭她的缺点。[2](P20)
将爱情“建筑在工作关系上”,意指两人在情感上的淡漠。这意味着他们近20天的“蜜月期”即将终结,情感上趋于冷淡。萧军对萧红“人”和“文”的所谓“透明”的评价,实则还是想说萧红的“弱”。正因为有了如此认知,才有了他那在萧红面前导师角色的定位。由此可见,二萧之间,萧军此时以爱的名义力图指导萧红无论“人”或“文”的成长,而萧红却已然有了自己的取向与定位。因为在历经伤痛的基础上,她渐渐丧失了对萧军的感激和崇仰,分明认识到知名男作家荣光背后的虚伪与幼稚。
萧军日记6月25日记载其散文集《十月十五日》出版后,他将每篇文章重读一遍,自觉“运用文字的能力确是有了进步,无论文法或字句,全没有什么疵”,“内容也全很充实”。在稍有写作经验的人看来,萧军这些颇为自恋的自我评价,恰恰是缺乏写作自觉性的表现。他接着分析,萧红“全不喜欢”该书,“是她以为她的散文写得比我好些,而我的小说比她好些,所以她觉得我的散文不如她。这是自尊,也是自卑的心结吧”。他更谈到萧红“近来说话常常喜欢歪曲,拥护自己,或是故意拂乱论点,这是表现她无能力应付一场有条理的论争”。或许,萧军无从意识到,敢于批评,不附和,恰恰是萧红自主性增强的表征;而面对萧红这一悄然发生的变化,他仍以一个规训者和指导者自居:“我应该明白她的短处(女人共通的短处——躁急,反复,歪曲,狭小,拥护自己……)和长处,鼓励她的长处,删除她的短处,有时要听取她,有时也不可全听取她。只是用她作为一种参考而已(过去我常要陷于极端的错误),当你确实认清了一个人的时候,你会觉得过去有的地方实在愚蠢好笑。”[2](P24)当天日记接着还记载了两人为描述一个日常情景所运用的一个词句孰高孰低,发生有些动气的争执。两人都认为自己的表达优于对方,最终在友人鹿地亘的调和下平息。从这近乎孩子气的争执里,可以见出二萧当时见解的不能调和已是常态。
除了人事、文学见解上的差异之外,横亘在二萧之间的另一重因素是萧军与许粤华的后续交往,这是导致他们家庭冲突升级的导火索和心灵渐远的重要诱因。萧军日记6月30日记载了发生在两人之间的一场严重争吵,并说因此“决心分开”。起因似乎在于,许到来之后同萧红说话,遭到不搭理的冷遇,这让萧军很受伤害,于是故意上前对许说将要和萧红分开,并且说自己对于许的事情以后还要帮助,并让她明天十点再来。如此这般自然是故意刺激萧红,但萧军认为这是萧红逼他这么做。他还写到,眼见许流着眼泪无言走开,萧红也难过地哭了。稍后,当他们在友人池田幸子的调解下和好时,萧军坦言“我也哭了”。面对许粤华,萧红申辩“为了爱,那是不能讲同情的吧?”换来的却同样是萧军的一段规训:“X并不是你的情敌,即使是,她现在的一切处境不如你,你应该忍受一个时间,你不应这样再伤害她……这是根据了人类的基本同情……”并断言萧红“将永久受一个良心上的责打”,进而得出结论:“女人的感情领域是狭小的,更是在吃醋的时候,那是什么也没有了,男人有时还可以爱他的敌人,女人却不能。”[2](P25-26)
如果以人之常情看待,萧红面对萧军与许粤华的后续交往,所采取的态度似乎并没有过分之处。萧军对她的要求,对一个女人来说,虽然并非完全不能达到,但确乎是一种比较严厉的苛求。他那霸道的逻辑一仍其旧,似乎全然没有自责,更多只是责怪萧红做得不够。自此,他也感到与萧红不能达成沟通与理解,以致生成深深失望。后续日记不时出现与萧红争吵的自我告诫。7月21日写道:“少与吟作无必要争吵”[2](P28);24日更写道:“少和吟争吵,她如今很少能不带醋味说话了,为了吃醋,她可以毁灭了一切的同情。”[2](P29)1937年8月4日日记里,萧军将对于萧红的失望,阐释得非常清楚:
她,吟会为了嫉妒,自己的痛苦,捐弃了一切的同情(对X是一例),从此我对于她的公正和感情有了较确的估价了。原先我总以为她会超过于普通女人那样范围,于今我知道了自己的估计是错误的,她不独有着其他女人一般的性格,有时还甚些。总之,我们这是在为工作生活着了。[2](P30)
由此可见,至少沪战爆发前,二萧仍生活在萧军那“没有结果的恋爱”的后续影响下。萧军要求萧红做到给予给她带来巨大心灵创伤的丈夫绯闻女主角以同情和理解,而萧红做不到,这让萧军失望于她缺乏超离于普通女性的品格。或许萧军此时还怀着对许的牵念,不忍眼见许遭遇家庭困境和不堪的道德评价。在这方面,作为男性,萧军所承受的舆论压力自然比许小得多。而萧红或许能原谅丈夫的再次出轨,但无法原谅他那与“妻子的朋友、朋友的妻子”发生的不伦之恋的后续牵连。萧军夹在萧红的嫉妒还有许的无助之间,或许也是一种煎熬。他一天天感到与萧红之间爱情的死亡,只是出于工作需要生活在一起。
沪战爆发前,二萧的婚姻就这样走向名存实亡的边缘,分手只是时间长短问题,只是等待一个特定情境到来。以萧红的敏感,自然会感受到这一切,明了自己和萧军陷于婚姻的暗战。即便发生在眼前的民族战争,似乎也不能改变二萧日渐破裂的家庭。战争与离乱让他们这对本身就不存安稳感的作家夫妇,无望奢求更大的安稳。经历“八一三”淞沪抗战,萧军8月21日日记结尾平静写道:“对于吟在可能范围内极力帮助她获得一点成功,关于她一切不能改造的性格一任她存在,待她脱离自己时为止。”[2](P34)这显示出他在离沪前往武汉前夕,对萧红蓄有离意的冷静。两天后,他进一步表达了对爱情的灰颓与不信任,以及对萧红那份可怕的冷漠:“我此后也许不再需要女人们的爱情,爱情这东西是不存在的。吟,也是如此,她乐意存在这里就存在,乐意走就走。”[2](P35)
沪战爆发,如果二萧不能离开上海,战争或许能够转移他们基于彼此观照而生出的失望,分手也许不会来得如此之快。但是,战争促使他们转移,打破了两人那暗战僵持的格局,新的变数亦随即出现。
1937年9月,二萧转至武汉,住进武昌小金龙巷。不久,东北籍作家端木蕻良应萧军之邀来到武汉,与二萧生活在一起。一个屋檐下生活,一张大床上挤睡的三人日久悄然产生了情感格局的变化,由三人行渐至瓜田李下。更大的变动随即到来,1938年2月6日,萧红、萧军、端木蕻良、田间一行抵达临汾,任教于民族革命大学,旋即因为晋南战局变化,民大被迫转移,萧红、聂绀弩、端木蕻良等人决定跟随“西战团”前往运城,而萧军却执意留下打游击。萧军长篇散文《侧面》记录了二萧在临汾车站分手时萧红的缠绵、伤感与不舍。在萧军,这应该就是用一个冠冕的理由与萧红作出的心照不宣的分手。
见证人之一的聂绀弩,对萧军这蓄有离意的分手亦叙述详尽。当萧军坚持己见,在月台上将萧红托付给聂时,面对其诧异、不解,他说出了对萧红总结性的评价:“她单纯、淳厚、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5]并表达了与萧红分手的原则:“我说过,我爱她;就是说我可以迁就。不过还是痛苦的,她也会痛苦,但是如果她不先说和我分手,我们还永远是夫妻,我决不会抛弃她!”[5]可见,萧军只是不愿担负在战乱之中离弃女人的恶名,只等萧红将分手决定说出。临汾之别,亦可理解为萧军利用当时情势,一方面让自己仍然保持对萧红的道德优胜,另一方面,可以达到就此顺利离开萧红之目的。
临汾一别,萧军去五台山打游击不成,后转至延安;萧红则随“西战团”到了西安。在西安,萧红与端木的恋情逐渐明朗,而在与聂绀弩的交谈中,她同样也有对萧军的总结性评价:“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个同志,又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我不知道你们男子为什么那么大脾气,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气包,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妻子不忠实!忍受屈辱,已经太久了……”[5]
这些都明示二萧情感世界再也没有修复之可能。1938年4月初,当萧军跟随丁玲、聂绀弩一同回到西安的当天,萧红就当着众人面向萧军提出分手请求。以萧军的骄傲,自然是硬气答应,即便事后或许得知萧红怀有自己的孩子而有所反悔,但情势不可逆转,萧红与端木的恋情亦同时公之于众。萧红与萧军六年的共同生活从此彻底终结。不久,萧红与端木南下武汉,5月在汉口大同酒家正式举行婚礼。萧军与一班文化人结伴西去,途经兰州与王德芬相识,旋即堕入爱河。
对于二萧而言,西安一别遂成永诀。两人后续也有一些彼此间的间接关注。1939年5月16日,在成都的萧军,在当天日记里仍带着情绪写下:“他们说和我交友感到压迫,妨害了他们的伟大,红就是一例,她已经寻到了不妨害她伟大的人。”[2](P44)萧红此时已搬离重庆市区,住在嘉陵江畔的黄桷树镇。搬离前不久,她在胡风夫人梅志处了解到萧军、王德芬婚后的情形,脸上写满了痛苦、失望与伤感。梅志自述没想到萧红“对萧军还有这么深的余情!”[6](P38)
比较起来,王德芬也许并不比萧红具有更丰富的内心生活,从萧军日记来看,萧军与之一起生活不久,便产生了更为尖锐的矛盾,日记里一样记载着痛苦的呼告。此时,他也不时生出对萧红的怀念,以及对已然失去的那段爱情的痛惜。1939年9月20日,萧军深情写下:
夜间,偶然把红的信,抽出几页要看一看,但是我看不下去了,一种强烈的悲痛,击痛了我的心!我保存着它们,但又不敢好好地看它们一遍。不知她现在跑到哪里去了。我想无论怎样,大家全要怀着这个永久的悲剧的心,一直到灭亡
此后,萧军亦留意于从白朗等友人口中了解萧红的生活和创作的状况,关注其行踪。1940年2月24日,萧军日记记载,他从周围人口中获悉萧红去香港,便“有一种可悲的感觉,觉得这个人是一步一步向坟墓的路上走了!”[2](P236)萧红的最终命运,似乎被他不幸言中。
值得一提的是,1940年10月7日,萧军在延安与王德芬因看戏发生冲突,日记里他由此反思与王德芬以及此前与之生活过的女人的态度:“我的咄咄逼人的态度,命令的声调,这是一个人不能忍受的,可是芬她能忍受,这使我更不能离开她,更深地爱着她。这似乎近于感恩。我又记起红说过:‘一个男人爱女人,无非让她变成一个奴隶,这样他就更爱她了。’确的,不有奴隶忍受性的女人,是不容易得到爱了。”[2](P341)由此,似乎可以进一步地看出萧红与萧军在一起时的悲剧根源。萧红毕竟不是王德芬,所以她得不到萧军那近于“感恩”似的爱,因为她成不了他的“奴隶”。写下这些时,二萧分手已两年多,萧军也意识到自身强迫与自己生活在一起的女人所遵守的逻辑的怪异与霸道,不禁自问:“这是什么逻辑?!”[2](P341)
萧军也偶尔流露从作家这一维度对萧红的评价。1941年3月7日,他在延安与T(应该指丁玲——论者注)再次谈到萧红,当天日记载有:“我告诉她,萧红是常常鼓励我的,她是有正义和文艺气氛的人,她和我离开,原因不怨我”,并接着感慨道:“T和红是不能相比的,红是有晶莹崇高感情的……”[2](P387)此时,二萧分手快三年,萧红在香港埋首创作,已完成《呼兰河传》、《马伯乐》等巅峰之作。萧军是在作为家庭生活中的王德芬以及作为作家的丁玲与萧红的对比观照中,体察到萧红作为女性的卓异之处。但即便此时,他对自己与萧红分手中所应该担负的责任似乎难有一份平和而理性的心态,言下似乎更多简单归之于端木蕻良的出现以及萧红选择的草率。
1942年4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转载了萧红逝世的消息。萧军当天日记载有“下午听萧红死了的消息。芬哭了”。两天后的日记里,他在4月8日的剪报下面写道:
师我者死了!
知我者死了!
前文论及,无论为“人”还是为“文”,萧军在萧红面前总有一份无形的优越,直到萧红已死,他仍然将萧红看作他的效仿者和追随者,完全无视萧红离开他之后有诸多杰作问世。他自然不可能认识到,恰恰是离开让作为作家的萧红走向了成熟。而从萧军目前公布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部分日记来看,恰是二萧分手之后,他陷于更大的焦虑和纠缠中,创作上越发沉寂、平庸。写下这两句表明心志的话之后,萧军亦记下当日心情:“只是感到闷塞。我流了两次泪。对于她,我不是悲悼过去的恋情,只是伤怀她底命运。‘我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我不愿承担起这罪过和谴责。”[2](P599)
一个人写于当年的日记、书信,因为没有日后公之于世的预期而有所顾忌其功利性,很大程度上应该是彼时彼地最为真实的内心和思想情状的呈现。在萧红传记研究上,对于二萧情感世界的认知,几十年来一直过于依赖萧军晚年的自述。对当时事件的后续阐释毫无疑问大多带有有意无意的讳饰和自我同情。萧军20世纪三四十年代部分日记的面世,很显然对于理解二萧间情感裂隙生成直至分手的深层根源提供了全新的可能。在萧红传记研究上,这批文献将产生深远影响,某种意义上或许可能改变人们对于二萧形象的固有认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