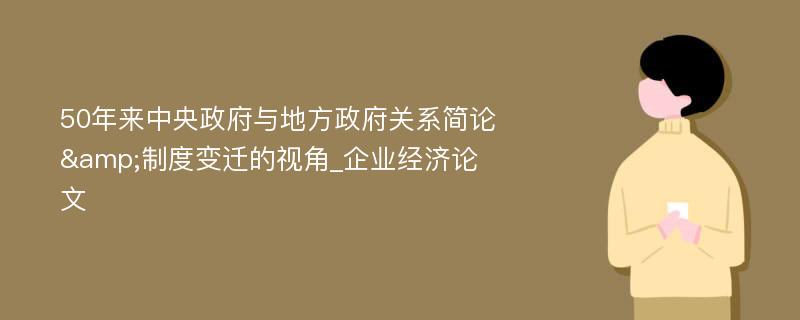
中央与地方关系50年略考:体制变迁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体制论文,中央论文,关系论文,地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央与地方关系根植于一个国家的社会体制之中,尤其是一国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状况直接决定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形态特征。可以说,中央与地方关系是一国政、经体制的结合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之间又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其构架,是变动不居的。这也决定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发展变化。正是从这个原理出发,本文把这一问题放在我国50年来社会体制、政经体制构架的历史变迁的视角之下进行研究。
一、前30年:政经一体化构架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在现实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决定作用与反作用原理,表现出丰富的特点。就经济与政治结合的密切程度而言,大体上表现为政经一体化与政经二元化两种模式。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结束后,就基本确立了苏联模式的“高度集权的官僚等级社会体制”,(注:王天生:《东欧昭示我们什么》,《读书》1997年第1期第36页。 )作为这种社会体制的核心是政经一体化的体制构架,它的基础是作为国民经济主体的企业的政企不分,企业事实上成了国家政权的附属与延伸。正是在上述体制背景下,我国头30年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从总体上表现出中央高度集权、地方缺乏必要的自主权和独立性的格局。当然,这种格局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更不是一成不变的。下面,让我们在政经体制构架视角参照之下,分三个阶段考察前30年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一)大区分权(1949年—1952年)
这一阶段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显著特征是大区分权。解放初期,各地差别极大,国家政权尚未完全建立和巩固。在此情形下,沿袭了革命战争年代各大部队和中共中央派出机关(中央局)在全国各大区域内实施管理的格局。全国被划分为东北、华北、西北、西南、中南、华东六大行政区。各行政区身兼二任:既是该区所辖省(市)高一级的地方政权机关,又是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工作的代表机关,享有广泛的立法、行政和人事权,在管理当地经济事务方面负有主要责任。中央对省级地方的领导要经过大区这一级。在中央这一层面,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党中央进行了多次的反对分散主义的斗争,并在随后强化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建立了请示报告制度。这些措施极大地提升了党中央的权威。建国以后,我国政治体制的确立正是以此为基础的。在经济上,过渡时期的统一财经工作,即统一财政收支、统一物资管理、统一资金管理,为此后中央的高度集权奠定了物质基础。
(二)中央集权(1953年—1957年)
从1953年起,我国进入了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在“一五”计划展开过程中,高度一体化的社会体制形成了,它直接决定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格局。
1952年底,为了强化统一与集中,中央决定改变大行政区的机构与任务。各大行政区不再作为一级地方政府,只是中央派驻各大区的代表机关,其机构大大精减,职能也相应缩小。1954年,为了便于中央直接领导省市,中央进一步决定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与此同时,中央政府机构的数量与职能快速增加、扩大。1953年底,政务院的部门由35个增加到42个,到了“一五”末期,国务院的部门增加到81个。各部门对各自所管辖事务实行垂直领导,“一杆子插到底”,一个地方、一个企事业单位要面对众多的“婆婆”,形成了所谓“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的“条条专政”模式。中央掌握了关系经济发展和行政管理命脉的产、供、销、人、财、物大权。从法律的角度看,由于1954年《宪法》没有给地方以立法权,地方人大也没有常务工作机构,本应对同级权力机关和上级政权机关负责的地方政府,实际上只对中央与上级负责,这就为中央的高度集权提供了方便。
与中央的权力日益膨胀和不断渗透相反,地方的独立性与自主权日渐萎缩。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之下,地方逐渐沦为中央政府机构的延伸,沦为中央计划的执行者与中央向企业发布指令的中介,丧失了作为一级地方政权必要的权力和地位。
这种中央与地方关系格局的形成不是偶然的。从根本上说,它是由在我国经济文化极端落后的国情下追求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所决定的。这个模式表现在体制上,就是政治、经济体制的高度集权与政企不分;表现在发展战略上则是走高积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前者直接决定了中央的高度集权,相应地就贬抑了地方的地位和作用;后者则表现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与极端落后的国情之间的矛盾,客观上要求中央高度集权,以便解决重点项目的资金、技术、人才、原材料不足问题。与此同时,一种无形的权威力量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人,在全国人民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们当中杰出的领袖、精英,尤其如此。随着大区的改制和撤销,原来各大区的主要领导人调往中央,担任重要职务,各地方的主要领导人,大多数是他们的原部下,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执行中央的意志,必定是毕恭毕敬,一丝不苟。
(三)统与放的循环(1958年—1978年)
很显然,中央高度集权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各地差别极大、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的大国的高效发展非常不利。对此,党中央在“一五”末期就向地方放权、提高地方的积极性问题进行探索。从1958年到1975年,中央有两次大规模地向地方放权的实践,但都以中央重新收权而告终。
1、50年代中后期的尝试。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指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根据这一讲话精神,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中,周恩来在“二·五”计划建议报告中,就此问题作了进一步布署。1957年底由陈云主持对上述探索进行具体落实,起草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商业管理体制、财政管理体制三个文件,正式规定了下放权力的原则、措施、步骤。(注:《陈云文选》(1956—1985),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8—96页。)可是,1958年“大跃进”方案的出笼,在狂热的政治气氛之下,分权改革也走向极端。在极短的时间内,企业管理权、计划权、基建投资权、物资分配权大幅度下放。各地方随意提高经济计划指标,层层加码;争相上马基建项目,投资极度升温。很快,恶果就出来了:国民经济比例下调,经济秩序混乱,物资匮乏,资金紧张,重复浪费严重,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面对这种局面,中央从1961年开始,不得不决定把所下放的各种权力重新收回,反对分散主义,强调全国一盘棋。
2、70年代初期的尝试。“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对经济建设造成严重冲击。1969年“九大”之后,局势趋于相对稳定。可是,由于错误地认为世界大战随时都会爆发,因而要求各地建立独立作战的工业体系,建立所谓“工业省”,展开对“条条专政”的批判,要求实行“块块专政”。在实践中,从1970年6月到9月短短的时间内,把包括鞍钢、大庆等超级大企业在内的2400多家中央直属企事业单位下放到地方,并对中央政府机构和人员进行大规模的撤并、裁减。同时,相应扩大了地方的财政、计划管理、物资分配、商品价格管理和人事管理方面的权限。这些措施无疑加大了地方的责任,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但同样造成了地区分割,管理混乱,地方无力管理大企业。对此,“文革”结束后两年,中央又开始收权:强调对铁路、民航、邮电等部门的统一管理,调整若干企业的隶属关系,把重点企业收归中央管理,上收了部分财政、税收、物资管理权。
(四)政经一体: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症结。
应当承认,在历次下放权力的尝试中,地方的职能在经济领域明显扩大。但是,也要看到,从总体上放权并没有突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框架,高度一体化的社会体制并没有受到冲击。另外,50年代末期之后,“纵向放权与横向分权总是异步进行,而最终却是纵向权力与横向权力的同步集中”,(注:韩钢:《“文革”前十年我国政治体制演变的主要特点》,《党史研究与教学》,1989年第2期,第2页。)高度集权的状况反而日益强化,不论是横向上的党政、党群、政企关系,还是纵向上的中央与地方、单位与个人关系,都是如此。在此背景下,企业首先面对的是政府,即要么是中央政府要么是地方政府,毫无独立性可言。当面对的是中央政府时,必定是“条条专政”,地方没有积极性,企业缺乏效率;当面对的是地方政府时,必然是“块块专政”,地区分割,重复建设,盲目投资,经济秩序混乱。由此造成“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可见,只要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还如此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企业就永远是插足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第三者”,中央与地方关系就永远无法走出“统——放”的怪圈。
二、后20年:政经分离过程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二十年的改革开放是一个市场化程度不断提升的过程。市场经济的内在品格与运作方式势必对传统模式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提出合理调适的客观要求。邓小平在1980年说:“过去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分过几次权,但每次都没有涉及到党同政府、经济组织、群众团体等等之间如何划分职权范围的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9页。 )这就为此后的分权改革奠定了基调:即分权不应局限于以往的行政性分权,更应当进行经济性分权。(注:刘吉瑞《论行政性分权和经济性分权》一文认为,“行政性分权是在保留行政协调机制本质特征的框架下,经济权力向较低层次的转移。经济性分权则是按照市场取向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原则在各类组织中分配决策权。”见《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8年第6期。)这一思想指导下的实践, 客观上促使我国的社会体制走上政治、经济日渐分离的这一符合世界历史潮流的轨道,(注:美国著名经济学者布坎南认为,现在人们公认:“第一:市场经济的绩效高于计划经济和管制经济;第二:在全世界范围内,有一个持续的制度变迁的过程,这一过程涉及到经济活动的非政治化。”见《公共论丛: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 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2—33页。)从而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健康发展提供日益广阔的空间。
(一)经济性分权与行政性分权(1979年—1991年)
改革从农村切入,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原来的政社合一、“一大二公”的社会体制被打破,确立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机制。这种彻底的政、经分离改革,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1984年后,城市改革沿着经济性分权与行政性分权相结合的路子展开,中央与地方关系发生了一系列变化。(1)在微观经济方面,逐步弱化“条条专政”, 放开大部分经济活动,国家指令性计划的范围大幅度缩小。流通领域国家调拨的产品、物资只占极小的比重,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政府定价部分到1992年仅有5%。中央直接管理的企业到1985年仅占企业总数的1%。(2 )财政体制改革总体上按“包干制”的思想展开,改“一灶吃饭”为“分灶吃饭”,实行了收入包干,致使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不断增加,1987年为51.2%,1990年为60%,1992年达到71.3%。( 3)基建投资方面,地方的审批权限大幅度提升。结果,在国内投资方面,地方投资成为主体。此外,在外贸、税收等领域,地方的权限也大幅提高。(注:王绍光,胡鞍钢:《中国国家能力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0页。)(4)针对一些地方的特殊优势, 建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沿边城市;同时,扩大城市政府的经济管理权限,实行市领导县体制,增加城市经济的幅射力度,消除城乡分割。(5 )在政治、法律体制上,进行党政职能分开,权力下放,给予地方以立法权,中央政府在地方政府人事上的权限随着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健全、选举法的完善,有所减小。这些措施极大地激发了企业的活力和地方的积极性、自主权。
作为其结果之一,我国的社会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高度一体化的官僚集权体制被打破,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开始走向分离,社会逐步趋于多元化。中央与地方关系也不例外,传统单一的中央高度集权的模式,让位于多元化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并存的新的格局。也许有人会产生疑问:同样是分权,前30年与后20年的结果为什么会迥然不同?答案恐怕只能从分权本身去寻找。前面讲过,此间的分权是经济性分权与行政性分权同时并举,而以前则只注重行政性分权。它由于忽视了企业和地方的独立性,分权只停留在调整企业的隶属权、管理权。即使地方拥有了对企业的统辖、管理权,但是计划权、财权、物权很大程度上仍然操之于中央,分权表现出不彻底性。而改革开放后分权的首要目标是经济性分权,让企业获得自主经营权;同时,地方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财权、计划权、基建投资审批权等等。在企业、地方双重积极性与独立性的作用之下,经济生产活跃,社会体制转轨,中央与地方关系发生变革,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但是,激流之中必有泥沙。在如此大国、如此短的时间、如此大规模地分权,不可能没有问题。主要的问题便是出现了所谓的地方主义、“诸侯经济”,其显著特征就是各“诸侯”彼此间的贸易封锁和资源争夺。一时间,各地关卡林立,障碍重重,“黄麻大战”、“茶叶大战”等烽烟四起,此起彼伏。在中央则是财政困难,政令不畅,“有令不从、有禁不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由此导致宏观调控乏力,许多措施每每半途而废。(注:赵夕方:《当代“诸侯经济”忧思录》,《人民日报》1989年8月6日第8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 我们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改革的不彻底性。我们已经知道,我国改革所面临的是高度一体化的社会体制背景。而这种体制本身的转型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更何况,改革所走的是局部的渐进的道路,主要集中于经济领域,并从体制外围进行攻坚。这决定了体制转型只能是自然的历史过程。因此,此间的分权仍然是在高度一体化的社会体制框架内进行,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局面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企业的自主权难以真正地落实。事实上,中央下放给企业的许多权力被地方截留了。这固然与计划经济观念的历史惯性有关,但更是利益驱动下的一种行为扭曲。因为在财政包干制下,控制了企业,就意味着地方财税的增加。另外,许多企业在体制转轨期,适应市场的能力很差,宁可“找市长”而不“找市场”。这样,分权化的改革客观上把高度统一的政经一体化分解成许多分散的政经一体化。各个地方在功能膨胀、责任加重的分权改革中,挟着中央所给予的投资决策权、物资调配权、金融控制权等大权,以扩大自身实力(利益)为依归(在现实政治运作中,这是获得提升必备的政绩),或自行其是,或“绕着红灯走”,遂产生了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它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企业改革难以真正到位;中央的权威下降;全国统一市场无法形成。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深化改革。但是,改革向何处去呢?
(二)政治、经济二元化(1992年至今)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使人们的思路清晰了,那就是:改革的取向只能是市场化,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此思想指导下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深入,从体制上,为中央与地方关系发生质的变革创造了条件。这些措施至少包括:(1)企业改革的目标已经确立。 那就是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立“产权明晰、责权分明、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现代企业制度。而这样的企业制度将摒弃非经济权力对于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从而使地方化的政治经济一体化体制失去依托; (2)1994年财税体制实行分税制,从而初步理顺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建立起规范的财政运行机制。财政的厘清,为中央与地方事权的划分创造了前提条件,从而为中央与地方关系实现规范化奠定了基础;(3)1998年11月,党中央、 国务院决定对中国人民银行管理体制实行改革,撤销省级分行,设立跨省区9家分行。这一改革, 将使我国货币政策决策和实施进一步统一,从而增加金融宏观调控的有效性,确立中央在货币金融领域的权威。同时,有利于摆脱各地方各方面的干预,使地方失去驾驶企业的一大法宝;(4)对政府的机构与职能进行改革, 精简机构与人员,减少专业部门,改变其职能,强化综合经济部门,以加强宏观调控。中央政府的改革已迈出决定性一步,地方的改革也将开始,这样,“婆婆”少了,政府过多干预微观经济活动的“手”,也就被“斩断”了。
显然,这些措施已经直接改变着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状况。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到位,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日,开始于20年前的政、经分离进程将会结束,从而建立起政治运作与经济运行相对独立的政经二元化体制。在这种社会体制之下,中央与地方关系将摆脱以往那种因经济政策、经济形势和政治局面的变化而不断受干扰的命运,实现相对独立稳定地运行;同时,中央和地方各自在政治、经济、立法等方面的职责权限将易于界定,更加明晰,从而为两者关系的规范化、法制化创造前提。
标签:企业经济论文; 分权管理论文; 社会管理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财政分权论文; 财政制度论文; 经济学论文; 时政论文; 统一企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