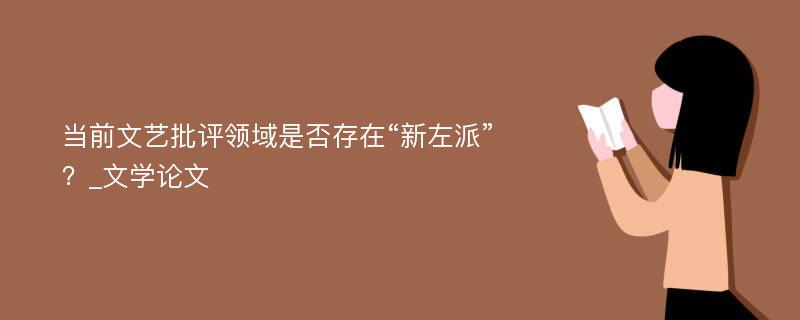
当前文艺批评界存在“新左派”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批评论文,左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当前文艺批评界存在“新左派”吗?似有还无。即使在肯定或者否定“新左派”的人那里,当前文艺批评界是否存在所谓的“新左派”也不很明确。支持“新左派”的人认为,中国当前“新左派”本身是一个尚未得到普遍认可,但是却被普遍使用的概念。反对“新左派”的人认为,21世纪初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规范受到“新左派”的真正挑战。“新左派”虽然队伍并不庞大,但影响日盛。“新左派”的领军人物离文学越来越远,影响却越来越大。但是,这个领军人物对这些封号却很不领情。而在我们已划分的当前文艺批评界的三大派别中,也很难说哪一个派别是“新左派”。
当前文艺批评界存在三大派别。一是粗鄙存在观。这种粗鄙存在观认为,“如果真的致力于人文精神的寻找与建设,恐怕应该从承认人的存在做起。”即既“承认人的差别而又承认人的平等,承认人的力量也承认人的弱点,尊重少数的‘巨人’,也尊重大多数的合理的与哪怕是平庸的要求”。这种粗鄙存在观认为,要求人人成为样板,其结果只能消失大部分作家。提出寻找或建立一种中国式的人文精神的前提是对于人的承认。从这个意义上说,“痞子”或被认为是痞子或自己做痞状的仍然是人。很明显,这种粗鄙存在观只承认人的存在,否认了人的发展和超越。这是一种满足现状、不求进取的庸人哲学。二是虚无存在观。这种虚无存在观从人类的某种完美理想状态出发,彻底否认了现实的存在。它只看到了现实和理想的差距,而没有看到它们之间的辩证联系,这实质上无异于取消了多样的存在。虚无存在观和粗鄙存在观虽然是两个极端,但是这些文艺批评派别却很难被认为是右的或者“左”的。况且,一些在过去具有“左”的倾向或右的倾向的人都同样表现了粗鄙存在观或虚无存在观的偏向。三是科学存在观。这种科学存在观既承认人的局限性,又承认人的超越性。它既不是完全认同现实,也不是彻底否定现实,而是要求既要看到现实和理想的差距,又要看到现实正是理想实现的一个必要阶段。也就是说,我们针对现实提出某种理想,与人们实现这种理想时达到了什么程度是两回事。我们绝不能因为人们没有完全达到这种要求,就全盘否定他们的努力。这种科学存在观就更不可能是“左”的或右的。
为了进一步把握当前文艺批评的发展趋势,我们还是很有必要认识人们所说的“新左派”。
在《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年第6期上,郑闯琦以“中国现代思想传统中的《北方的河》”为题,对“新左派”这个问题作了梳理。他说,在中国,“新左派”本身是一个尚未得到普遍认可,但是却被普遍使用的概念。被归于这一思想流派之下的代表人物有汪晖、崔之元、刘康、陈燕谷、韩毓海、李陀等。虽然这些学者的思想观点和学术水准参差不齐,但是在关于如何看待中国左翼思想、中国社会主义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上基本上具有一致的立场和看法。“新左派”思潮的理论资源主要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卢卡契的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等西方左派理论,并融合了解构主义、弗洛伊德理论、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新兴学说,成为一个具有相当理论深度并和时代保持着密切关系的世界性思潮,在20世纪晚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至今依然具有蓬勃的生命力。“新左派”在中国是伴随着经济改革的持续发展而逐渐引起人们注意的。在自由主义渐渐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潮并将“市场”推向神话境地的时候,它针对“消极”自由主义对社会公正的忽视而采取了尖锐的批判性立场,并逐渐在知识分子阶层中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郑闯琦的这种梳理和概括基本上符合人们所说的“新左派”的实际。不过,他没有突出人们所说的“新左派”的实质。
在2003年10月30日的《文学报》上,杨扬以“或前或后:文学批评的位置”为题和吴亮进行了一次对话。在这次对话中,他们严厉地批判了他们所说的“新左派”。杨扬认为那些“新左派”文学批评,高调得很,以底层代言人出场,抢占道德制高点。并说“新左派”不如老左派。“新左派”都是嘴上说说,抢个话语权,没有一个实地去做的;老左派倒是死心塌地冒死去做一些事,那倒是真正关心、帮助底层。吴亮则说,“新左派”是在玩话语权。“一个批评家提倡什么,就要做什么,你要做底层的代言人,那你真的深入到底层去,不要老对着外国人和公众表演:我是底层的代言人”。杨扬和吴亮虽然既没有明确界定他们所说的“新左派”,也没有指出他们所说的“新左派”包括什么代表人物,但是,他们却抓到了人们所说的“新左派”的实质,即成为基层民众的代言人,为基层民众说话。
然而,杨扬等人对“新左派”的批判是难以立住脚的。
首先,无论是“新左派”,还是“老左派”,既然都是“左派”,那么,他们一定在不少方面是一致的。为基层民众说话,捍卫和维护基层民众的根本利益可以说是他们的共同点。至于他们的分别,在于“老左派”在这方面既有理智上的需要,也有感情上的需要,而“新左派”则主要是理智上的需要。
其次,在复杂的历史环境中,有些人不是别林斯基所说的默尔而息,而是拍案而起。这本身就值得高度肯定。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进一步要求他们和基层民众相结合。虽然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但是,在还没有到武器的批判以前,批判的武器不但是必要的,而且相当宝贵。
最后,杨扬、吴亮批判“新左派”没有在实际中真正关心、帮助底层,这是对社会分工的取消。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的,“分工也以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的形式出现在统治阶级中间,因为在这个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而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思想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谋生的主要泉源),而另一些人对于这些思想和幻想则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他们准备接受这些思想和幻想,因为在实际中他们是该阶级的积极成员,他们很少有时间来编造关于自身的幻想和理想”。不但统治阶级存在两部分人,而且被统治阶级也有这样两部分人,“一定时代的革命思想的存在是以革命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我们提出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中国作家精神寻根的问题,不是形式上的,而是思想上的。我们要求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中国作家深入实际生活,深入基层民众,不是取消社会分工,而是以社会分工为前提。
人们所说的“新左派”是当前中国思想文化界历史分化的产物。当前中国思想文化界包括文艺批评界出现了历史分化时,人们将其中一种历史趋向概括为“新左派”。这是思想懒惰和简单的表现。其实,人们所说的当前文艺批评界的“新左派”,其人员构成相当复杂,有的是一以贯之,有的是从其它阵营中分化出来的;有的是自我调整,有的是被裹挟进来的;有的仍然在变化,有的只是部分表现……我们很难一锤定音地把握这种仍然在继续变化的历史趋向。所以,面对这种不可阻挡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新左派”这种概念是无法真正概括的。这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很快就被一些敏锐的知识分子包括作家所意识,我们很难认为这些知识分子包括作家是“新左派”。
一、这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发展的必然产物。
在《南方文坛》2003年第1期上,旷新年以“‘重写文学史’的终结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转型”为题,指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转向”。这种“转向”是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发展的必然产物,而不是极个别人所说的是“新左派”的造势。旷新年把握了这种历史发展的潮流。他说,“重写文学史”成为一个明确的口号和明显的潮流始于1988年7月《上海文论》第4期上陈思和、王晓明主持的“重写文学史”专栏。从根本上说,构成“重写文学史”运动的有力支撑的是两个中心的观念:“文学现代化”和“纯文学”的观念。“文学现代化”被理解为“纯文学”,最终又被理解为“现代主义”。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纯文学”的标准和“文学现代化”的标准几乎是同时产生和确立的。也就是说,将“文学现代性”理解为“文学现代化”,将“文学现代化”又理解为“纯文学”和“现代主义”的追求。旷新年在指出“重写文学史”逐渐生成了“纯文学”的意识形态和体制的同时,揭示了这种发展的悖论。一方面,“重写文学史”以“纯文学”作为旗帜;另一方面,最终却以所谓的政治正确性作为单纯的评价标准,以对“政治”距离的测量来确定文学史地位的高低。这同样是以政治性的评价代替了文学性的评价。“自由主义作家”由于“远离政治”而得到高度的评价;左翼作家因为强烈的政治意识而被取消了“艺术价值”。这种“重写文学史”走到了它的反面,“‘重写文学史’的‘洞见’最终变成了文学史的‘盲视’。更有甚者,‘重写文学史’以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开始,却以认同‘文艺黑线专政论’而终。不仅将‘文革’文学,而且甚至将‘十七年文学’视为文学史的空白”。
显然,以“文学现代化”和“纯文学”为中心观念的“重写文学史”的终结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李扬提出的“‘文学’的斗争从来就不只是‘文学’之间的斗争,而必然是——只能是文化与政治的斗争。因此,不应该把‘文学’剥离出具体的历史进程和权利关系,而应该把‘文学’历史化——或者说将‘文学’作为话语对待。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才不会再以是否与‘政治’有关作为判断‘好文学’的标准,而是转而追问这种文学表现的是‘何种政治’与‘谁的政治’。”(见《南方文坛》2003年第1期,《“好的文学”与“何种文学”、“谁的文学”》)这必然成为历史的潮流。至于这是谁提出的,谁先倡导的,就不是很重要了。
正如李扬以“‘好的文学’与‘何种文学’、‘谁的文学”’为题所指出的,成为20世纪90年代文学环境的社会生活的主要问题早已不是“过度政治化”的问题,而是“过度私人化”的问题,或者说,主要不是“个人”或“私人”受到“左翼”政治压抑的问题,而是“全球化”以“个人”为名压抑和排斥“公平”、“平等”等“集体叙事”和“宏大叙事”的问题。用甘阳的话来说,“当少数人正在疯狂掠夺多数人的财产并且日益威胁多数人的基本保障时,我们却听到许多人在那里摇头晃脑地谈什么‘多数人的暴政’”。20世纪80年代的那套文学话语已经无法有效应对和解释这个今非昔比的世界,20世纪80年代倡导和参与“重写文学史”的人早已感觉到了,他们应该进行较为深刻的反省。
王晓明在为《半张脸的神话》(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年4月)一书的自序中写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他认为他在20世纪80年代获得的那些认识生活、历史和社会性质的理论方法,已经开始丧失效力了。
陈思和虽然没有明确的反省,但也作了相应的调整。他说,21世纪已经过了几年了,全球化的阴影越来越浓郁,对敏感的中国人来说,这对文学创作不可能不带来某些影响。通过一部影片的分析也许能把一些文人的心思看得更加透彻些,对某些貌似正义的声音更加警惕。陈思和不但在他主编的《上海文学》2003年第7期上发表潘旭澜对张艺谋导演的影片《英雄》的批评,而且在2003年第10期上作了进一步的批判。潘旭澜认为:“那些正说、戏说的影视,基本上避开了这一点,满台辫子飞来飞去,马蹄袖甩个没完,‘皇上圣明’、‘奴才该死’之声不绝于耳,实际上是在对观众进行帝王崇拜和奴化教育。而《英雄》更有很大发展,它不是隐恶溢美,而是以虚幻的人物,不讲心理流程与行为逻辑的情节,从根本上倒说嬴政,将血腥的兼并和全无人性的暴政‘颠倒’为‘保国卫民’,值得英雄志士为之死的人间大义。要用一句话来说,这是宣扬强权与极权崇拜”。陈思和则说:“一般来说,中国的武侠总不能摆脱从流氓到鹰犬的堕落过程,但至多也只是黄天霸之流拍御马,没有一个像张艺谋那样把‘马’拍到了世界霸主的屁股上。《英雄》是劝说荆轲们千万不要去刺‘秦’,而应该反过来,为了秦始皇的‘天下’放弃生命和正义”。陈思和的这种调整是相当深入的。
蔡翔在《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6期上以“何谓文学本身”为题对“纯文学”这个概念作了清理。蔡翔认为,在某种意义上,“纯文学”概念正是当时“新启蒙”运动的产物。到了20世纪90年代,种种新的权力关系开始形成,社会重新分层,利益要求与权力要求也开始分散化,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同盟事实上已经不复存在,这个时候,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集团或者作为一个阶层,也已经很难代表弱势群体的利益要求。因此,当“纯文学”继续拒绝进入公共领域,在更多的时候,就演变成一种“自恋”式的文学游戏,同样,“怎么写比写什么更重要”这个20世纪80年代的著名口号,因其对传统的现实主义编码方式的破坏而发展出一种新的写作可能,虽然夸张仍不失为一个有效的文学主张,但是一旦失去其反抗前提,也就自然转化成为形式至上或者技术至上主义者,而其保守性也就明显地暴露出来。
早在《上海文学》2001年第3期上,李陀以“漫说‘纯文学’”为题就已经从反思进到拷问了。他指出,20世纪90年代在坚持“纯文学”这个问题上,固然作家们应该重新思考,有所批评和讨论,但是批评家们更需要反省。我们不能不想一想:面对这么复杂的社会现实,这么复杂的新的问题,面对这么多与老百姓的生命息息相关的事情,纯文学却把它们排除在视界之外,没有强有力的回响,没有表现出自己的抗议性和批判性,这到底有没有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
面对这种历史反省和历史潮流,我们能够简单地用“新左派”这个概念圈定吗?不能。与其说这些人的立场发生变化和自我调整,不如说他们对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有了清醒认识。
二、这种历史发展的潮流是中国当代现实生活发展的必然产物。
当然,当前文艺批评界的这种变化从根本上说不过是中国当代现实发展的历史变化在文艺批评界的反映。
在20世纪最后20年,人们对“重写文学史”的中心观念和文学发展的严重危机的批判可以说一直没有停止过。但是,当前文艺批评界的自我反思绝不是这种批判引起的。个中原因只有从现实生活的变化中去寻找。
李陀、王晓明等人就认为这种变化的原因是现实生活的巨变。李陀在《漫说“纯文学”》一文中指出,由于对“纯文学”的坚持,作家和批评家们没有及时调整自己的写作,没有和20世纪90年代急剧变化的社会找到一种更适应的关系。很多人看不到,随着社会和文学观念的变化与发展,“纯文学”这个概念原来所指向、所反对的那些对立物已经不存在了,因而使得“纯文学”观念产生意义的条件也不存在了,它不再具有抗议性和批判性,而这应当是文学最根本、最重要的一个性质。虽然“纯文学”在抵制商业化对文学的侵蚀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它使得文学很难适应今天社会环境的巨大变化,不能建立文学和社会的新的关系,以致20世纪90年代的严肃文学(或非商业性文学)越来越不能被社会所关注,更不必说在有效地抵抗商业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侵蚀同时,还能对社会发言,对百姓说话,以文学独有的方式对正在进行的巨大社会变革进行干预。
王晓明在《半张脸的神话》一书中较为真实地道出了自我调整的原因。他说他由于知识积累和思维训练上的偏颇,也由于个人性情的限制,现在还无力对那日渐膨胀的新的管制和掠夺,展开直接而持续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学分析。但是,对它的种种日渐膨胀的文化表现,却应该给予及时的揭露。王晓明认为那“成功人士”的神话,那新的主导意识形态,那由广告和传媒合力编造的共同富裕的幻觉,早已成为新的掠夺的吹鼓手和辩护士,成为哄骗被掠夺者的蒙眼布,而一一戳破这些神话和幻觉,也就仿佛砍断了新的压迫和掠夺的一根吸盘,给它的横行增加了障碍。“在即将来临的21世纪,如果那新的压迫和掠夺竟然继续通行无阻,社会的前景就势必不堪设想。所以,尽管明知力弱,也总得奋身出言,那新的意识形态早已四面联络,我又岂能自限于文学的世界之内?”
当前文艺批评界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纯文学”在20世纪90年代逐渐丧失了关注现实和把握现实的能力。李陀指出,在这么剧烈的社会变迁中,当中国改革出现新的非常复杂和尖锐的社会问题的时候,当社会各个阶层在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都在进行激烈的、充满激情的思考的时候,20世纪90年代的大多数作家并没有把自己的写作介入到这些思考和激动当中,反而是陷入到“纯文学”这样一个固定的观念里,越来越拒绝了解社会,越来越拒绝以文学的方式与社会进行互动,更不必说以文学的方式参与当前的社会变革。蔡翔在《何谓文学本身》一文认为,“纯文学”日渐轻视我们直接置身其中的现实的日常生活,而把想象力更多地投注于内心,这样,不仅在某种程度上加快了“纯文学”和社会存在的疏离,同时也使“纯文学”逐渐丧失了关注现实和把握现实的能力。在文学退出社会拒绝现实的背后,可能还隐藏着一种对世界的建构愿望,这种愿望来自于人性是静止的、永恒不变的本质。当文学沉迷于这个世界并且认定它就是真实的存在本身时,实际就压制了“关于历史的思想的作用”,也就此失去了把握永恒变化着的历史和现实的能力。
在《文艺理论与批评》2002年第5期上韩毓海以《当代中国的启蒙主义遗产》为题尖锐地指出,随着私有化进程造成的社会分化的加剧,对广大的社会阶层来说,现代化不再是一个共同的目标,相反,“什么样的现代化”和它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则成为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人的解放也不再具有道德的感召力,代之而起的是“哪一部分人的自由”、“谁的解放”和哪一部分“主体性”的实现的追问。新启蒙的抽象、乐观的现代化叙事逐渐被具体的社会分化进程所瓦解,被社会所质疑和抛弃,从而逐渐丧失了社会的支援。因此,韩毓海提出:“在新启蒙主义在当代世界丧失了其存在条件的时刻,我们应该竭尽全力去阻止这一思潮向右翼的、保守的方面转化”。
李杨反对把“文学”剥离出具体的历史进程和权利关系,要求把“文学”历史化。他提出我们不要以是否与“政治”有关作为判断“好文学”的标准,而是追问这种文学表现的是“何种政治”与“谁的政治”。
蔡翔深刻地提出:“如何使‘被压迫者’的知识成为可能,并且进入文学的叙述范畴,就成为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他认为,阶层分化早已开始,“穷人”和“富人”的概念也早已在消费时代变得日渐明晰,大多数人重新“沉默”,他们的声音不仅难以得到“再现”,而且我们几乎无法听见。不仅仅是当下的媒体,即使当下的知识,也在拒绝这个“大多数”,以至于他们显得更加(或者强迫他们)“沉默”。但是,正是这个新的“大多数”的产生或者存在,才促使我们反省现代性,反省资本化的过程,反省“历史终结”或者“意识形态终结”的神话。因此,关注这个“沉默的大多数”,实际上是我们更深地切入现实,寻找问题所在,以及一种新的乌托邦的可能,而不仅仅是简单地持一种道义的立场。
我们曾在《关于中国作家精神寻根的问题》、《现存冲突与文学批判》、《鲁迅的方向》等文中相继提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中国作家经历了两次社会分化。第一次是20世纪初期,第二次是20世纪末期。不过,第一次是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中国作家从统治阶级阵营里分化出来,成为革命阶级的有机组成部分。鲁迅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正如瞿秋白所说:“鲁迅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他终于宣言:‘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消灭,后来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有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第二次是有些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中国作家从社会基层民众中分化出来,跻身社会上层,有的甚至蜕变成为西方霸权主义的附庸。针对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中国作家的第二次社会分化,我们提出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中国作家直面现实,感受基层,超越局限,精神寻根。现在,有些知识分子包括作家所进行的反思和寻找,这是返朴归真,回归本源,是对历史发展的真正趋向的有力把握。
当前文艺批评界的这种发展趋向,绝不是“新左派”这个概念所能圈限的。
标签:文学论文; 纯文学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艺论文; 文化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读书论文; 英雄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陈思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