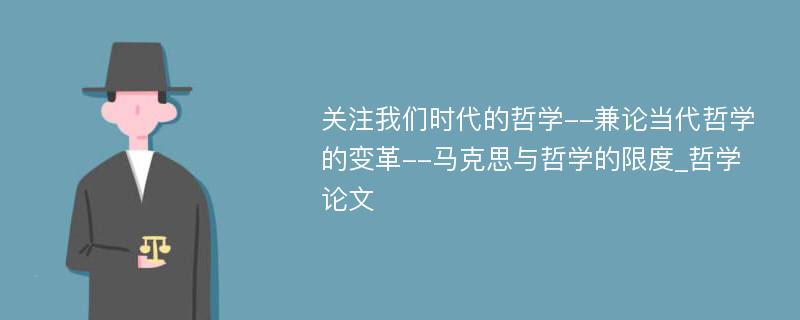
关注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当代哲学观变革笔谈——马克思和哲学的极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马克思论文,笔谈论文,这个时代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2)06-0005-22
随着后现代思潮的播撒,“故事”一词流行和普及开来,文学是故事,人类学、社会 学是故事,甚至物理学、化学也是故事,哲学当然更不例外了。如果认同这种时尚,我 们就可以说,所谓马克思的哲学,也就是马克思讲给我们的故事。
马克思的故事,是在欧洲思想文化传统中生成的,其情节直接传承了德国古典哲学, 特别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故事。我们知道,黑格尔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在他的演绎 中,自然、社会和人类精神一脉相承,犹如汪洋大海,滚滚滔滔。但仔细追踪起来,无 非是一种思维,一种思路,历经磨难,最后抵达绝对的、惟一的真理。这种真理是任何 人都不能不承认的,是超越时代、地域、种族、性别和一切差异的。这个故事,构成绝 对的圆满,听众或许可以走进它,但却很难走出;构成绝对的高峰,读者或许可以登上 去,感觉“高处不胜寒”,但却难以找到下山的路。后来者摒弃黑格尔的故事,拒绝接 着他的故事往下讲,原因之一就是,按照黑格尔的套路,人们无法讲出更新更有诱惑力 的故事。后黑格尔的人们当然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听众,哲学故事不甘心就此打住。怎 么办?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提出,哲学已经达到这样一个“关节点”,它将它之前的全 部哲学原则都融进了一个庞大的体系之中,在此之后,思想只能在一个崭新的方向上产 生出来。也就是说,黑格尔的哲学由于其完整性和普适性,使自身变得不现实,并与不 断分化着的世界形成对立,因而它“能动性地表现得支离破碎,自相矛盾”。在这样一 个时期,摆在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或者软弱无力地模仿过去,或者进行一场真正的根 本性的变革。这样一种状况,非常类似于亚里士多德之后的状况。后亚里士多德学派的 哲学特征就是“自我意识的一切环节都得到充分表达”。马克思喜欢伊壁鸠鲁,主要就 是基于两点:第一,尽管他承认所有的现象都具有客观实在性,但却同时希望保留意志 自由,否认世界是被永恒不变的法则所控制的;第二,他强调“自由的个体自我意识” ,提示了一条超越“整体哲学”体系的出路:“这些个别的自我意识永远具有一个双刃 的要求:其中一面针对着世界,另一面针对着哲学本身”;“哲学体系同世界的关系就 是一种反映的关系”;“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哲学的实现同时也就 是它的丧失”[1](P258-259)。
费尔巴哈作为后黑格尔时代的人物,也在讲述自己的故事。马克思对他的故事予以充 分的重视,并提出批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对于这一经典表述,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真正值得重视的,是反馈性模式(the feedback model of interaction with the world)和同步性模式(the simultaneity model of interaction with the world)。在反馈性模式中,为了行之有效,人们需要 理论分析,但是人活动的根本目的是现实变革而非知识;而且,理论分析也需要依据实 践经验不断提炼和修改。在同步性模式中,人并非外在于世界、仅仅从理智上把握世界 ,对人与世界关系的正确理解也不可能由此获得;相反,人与世界的基础性关系是不断 变革世界并为世界所变革的过程,对这一事实的正确理解也源于这一变革过程。与反馈 性模式不同,这里的正确理解不是分析(理解)、实践活动、依据实践活动再理解的“三 步曲”,理解正是寄存于活动之中,不存在独立的理论立场,改造世界是解释世界的合 法途径。相比较而言,反馈性模式关心如何达到目标,但不关心这个目标是自我中心的 还是无私的,是个人的还是公共的,同步性模式则不是单单指向目标,而是聚焦于我们 与世界的基础性关系。美国学者Daniel Brudney认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八 条中上述两种模式是可以共存的,第二条倾向于反馈性模式,第一条、第五条和第十条 倾向于同步性模式。
费尔巴哈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是因为他只是在个人支配自然以满 足自我需要的意义上理解实践活动,这也就是市民社会的态度。他正确地看到当时针对 自然的实践态度是成问题的,但他没有意识到这并非惟一的对待自然的态度,也不是真 正的人的实践态度,他没有把握“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由此不难理 解,费尔巴哈反对抽象思维而喜欢直观,马克思则既反对抽象思维,也反对直观,认为 二者都是成问题的:前者从不触及现实世界,后者则把自身视作仅仅为世界所触及;前 者缺乏物质性,后者缺乏主动性。抽象思维和直观正是反馈性模式的特点。反馈性模式 不考虑人与世界的关系,即使它含蓄地涉及这个问题,也只是把世界视作一种“物”, 它已经形成,静止地呆在那里,等待人去观摩和支配。反馈性模式仅仅把感性视作实践 活动的场所,而马克思要求我们把感性视作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这显然是反馈性 模式所无法达到的。马克思反对抽象思维和直观的态度,要求实践的思维。
依据Daniel Brudney的观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单薄和含混的,如果必须给 它一个定论,说它倾向于同步性模式可能比较合适[2](P236-240)。也许只是Daniel Brudney感觉含混罢了,但我们却不能不考虑这样一个问题:面对马克思的文本,我们 为什么几乎不曾感觉含混和失语?我们惯于自圆其说,惯于把马克思“体系”化,而且 无论历史情景发生什么样的变迁,都能游刃有余地把马克思“体系”化,然后心安理得 地用它来解释生活的变迁。这与其说是一种理论上的自信,不如说是一种惰性十足的表 现。
如果说哲学史是故事不断改头换面的历史,那么,就同一时代而言,这种改头换面是 修饰重心的改变,而不同的时代之间,则是不断扩大外延,把既有故事包容自身的关系 。也就是说,后来的故事不是简单地把以前的故事弃之不顾,而是讲一个更大的故事, 可以解释以前故事的故事。应当承认,马克思最初的故事也只不过是从黑格尔的故事大 全中抽取了一个材料,把它放大,而此后的故事,则越来越有包容性了。这种包容性, 一方面使得它获得了充分的解释力量,另一方面,也使得后人或褒或贬地把它视做有待 解构的新的宏大叙事。
黑格尔的故事,归根到底,还是一个关于人类思维和精神演变的故事。虽然此过程中 不乏“恶”,但借助于三段论的演绎,最终的结局是大写的真、善、美。在马克思看来 ,未来的乌托邦与其说是一种期冀中的世界,不如说是一种反观现实的视界。这种视界 本身,始终是不断游移和调整的;没有惟一的真理,只有诸多的话语。这种话语是受到 具体的时代、境遇和个人的处境限制的。任何一种理论话语,与其说是对现实生活的反 映,不如说是对现实生活的规划。现实总是“制造”出来的,本质总是被“赋予”的。 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哲学的意义,不在于它发动了怎么样的本体论变革,而在于它引起 了怎么样的世界变革;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不在于它是否能够解释世纪之交的种种变迁 ,而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引导了这种变迁。马克思的故事是很复杂的,后来的人们为了 便于复述它,把它弄得很简单。不管把复杂的故事ABC有什么样的便利,其后果之一肯 定是断章取义、各取所需。事实上,这样的断章取义已经太多太多。例如,马克思往往 被视作“线性进步论者”。其实,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发展图景中,“他者”始终具有 必要的地位,“他者”的叙事构成一种必要的补充,马克思并没有把所有民族国家的发 展都纳入统一的轨道。虽然马克思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探讨值得商榷,但马克思对这一 问题的明确意识本身就值得赞赏。又如,马克思往往被视作“经济决定论者”。事实上 ,马克思认为,社会历史发展中,贯穿着种种不同的线索。虽然他看重经济线索的重要 性,但除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外,他还谈到了军事、暴力、迁 徙等因素的巨大影响。这样,所谓的经济叙事本身就受到内在的消解。运用目前比较时 髦的话语,甚至可以说,马克思在建构经济叙事的同时,又在不断消解它。
西方哲学史一直到黑格尔,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条理清楚,系统连贯。但黑格尔 之后,尼采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孔德等等其他的人也讲述了各自的故事。很难说哪一个 人的故事是惟一合法的后续故事。马克思讲述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有很大的弹性空间 ,喜欢这个故事的人们,可以在其中自由地嬉戏;这个故事自觉地留有豁口,听完它后 感觉不满足的人们,可以走出去,听听其他的故事。喜欢这个故事的人很多,他们在它 的弹性空间和邻近地带,讲述了许多“家族相似”的故事,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正如伊 格尔顿所说:“马克思主义一词的作用似乎是表示一系列的家族相似之处,而不是指某 种不变的本质。”[3](P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