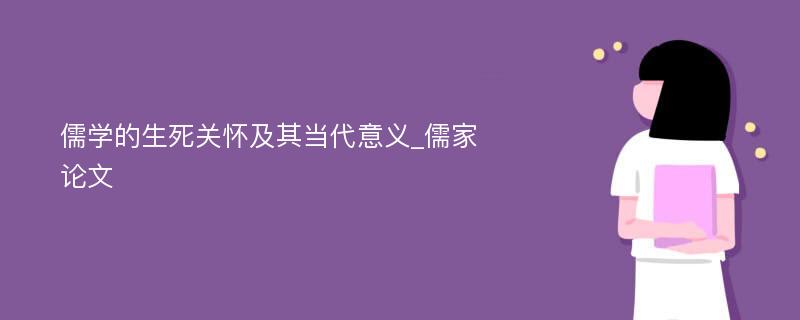
儒学的生死关怀及其当代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学论文,生死论文,当代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科技文明的飞速发展和高龄化社会的出现,人类的精神安顿与终极关怀的问题将愈来愈凸显。在21世纪,人们对于生命的意义与死亡的意义的探索,将变得愈来愈重要。儒释道的生死智慧是当代人反思自身的宝贵精神资源,值得认真地发掘与推进。本文旨在论述儒家的生死智慧、终极关怀及其当代价值。
1.尊生重生
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在生与死之间,孔子重视人生,珍视生命。儒家高扬生命意识,把生命提到本体的高度,从生生不息的“一体之仁”之自我肯定出发,就在人生即世间生活的当下,直接地进入本体的境界。
儒家的生命意识和人生态度根源于天地宇宙。人是宇宙家族中的一员。宇宙精神就是生命创造精神。《周易·系辞传》说:“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天(乾元)地(坤元)有“大生”“广生”之德,并把这种广大悉备的生命创造精神和“元、亨、利、贞”等生成长养、流衍创化的能力,统统赋予人类,使之成为人的本性。儒家认为,人的创造可以与天地的创造相配合,相媲美。人效法天地、德配天地、弘大天性,全面发挥人的禀赋与潜能,具有一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这是儒家“尊生”“主动”的传统。“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礼记·中庸》)这就是说,人类理性所能设想的“天”“道”,是宇宙万物、人类生命的本原,亦是一切价值之源。一旦人能充分地护持自己的生命理性或道德理性,也就能全面发挥其本性,并以平等精神体察宇宙间一切存在的价值,尊重他人及他物的生存,使之“各遂其性”,这样就能回应天地的生命精神,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与天地相协调、相鼎立,最终通过“正德、利用、厚生”、“立德、立功、立言”,积极入世,奋勇拼搏,在实际行动中实现人的价值和意义。
儒家的“仁”学,以“仁”来界定“人”。“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故曰“仁者,人也”(同上)。其实“仁”就是生命的相互感通,是天(终极信念)、地(自然生态)、人(社会与他人)、我(内在自我意识与情感)之间的普遍联系与相互滋养润泽,否则就叫做“麻木不仁”。“仁”也是生命的潜能与种子,是生命创造精神,有如桃仁、杏仁,可以长成参天的大树。“仁”又是自己决定自己的道德自律,所以孔子说:“为仁由己”(《论语·颜渊》);“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仁”又是博施济众、利济天下、推己及人、宽容忠恕的精神。
儒家哲学是生命哲学和人生哲学。《易》学经传的精髓是“生生”二字。所谓“尊生”“重生”,就是要明了宇宙与人生的本然状态、本质属性是生生不已、变动不居、不守故常、日新又新。儒家主张以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特别是道德实践精神来回应天地乾坤父母的生生之德。就个体人生来说,必须把守与创、动与静、性与欲、生与死统一起来。易道、仁体既有创化的一面,又有寂静的一面。只有深刻地理解了宇宙生命的刚健创造精神,才能在生活中,在变动中,在“开物成务”的实践活动中保持己性,保持寂静,不至沉溺物欲、心有挂碍。儒家以存仁立乎其大,即于天地万物一体处认识大生命,体悟自性,护持大我,使人格向上发展,不离开现实世界又能超越现实世界的种种限制,把人的精神提扬到超脱寻常的人与己、物与我相分离的境界。如此,则“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
在生与死之间,儒家与佛学和某些西方哲学不同,它不倚重于死亡意识,不是从生命意识的自我否定出发,通过建构死亡意识的曲折周章来接近形而上的世界。相反,它是通过正视生命来正视死亡,以强烈的生命意识来通透死亡意识。“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这都是以生来界定死,以积极热烈的人生实践,省视生命的有限性,赋予有限人生以无限的价值和意义。
2.死而不朽
追求生命的不朽,是儒家生死观的重要内涵。立德、立功、立言,谓之“三不朽”。儒家坚持独立人格,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决不苟且偷生,决不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儒者在道德价值与其他价值冲突时,能作出正确的选择,因为他们有自觉的道德需求,崇高的人格理想,热忱的救世情怀,坚定的生活信念。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孟子·告子上》)荀子说:“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恶,死甚矣;然而人有从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荀子·正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坚持气节和操守,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文天祥的“时穷节乃现”,“生死安足论”,“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为何事”,更是广为民众所传颂。
在道义和个人利益之间,儒学的价值取向从来都是十分鲜明的。儒家认为,生命是可贵的,但有比生命更宝贵的道义、节操、品格、民族精神和民族利益。为了后者,所有的祸患都决不躲避。如此,生命的价值转化为死亡的价值,生命的承担转化为死亡的当担。不因害怕死亡而偷生,不因威胁利诱而苟活,生命通过死亡得以延续,人生由有限变为无限,个体自由和人格独立得到最大的发挥。正因为死亡的意义和价值的问题根本上是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的问题,因此,《左传》中多次提到的“死而不朽”、“死且不朽”、“死又何求”,《论语》中所说的“死而无悔”、“死而后已”,《孝经》中所说的“死生之义”,以及普遍流行的一句话“士可杀而不可辱”,在儒家属于生命哲学、人生意义的范畴。儒者决不逃避死亡,以自己的价值方式追求“死而不亡”。
3.存顺没宁
张载提出的这一著名命题,实际上包含了儒释道的生死智慧。张载说:“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正蒙·乾称》)意思是说,富贵福泽与贫贱忧戚,都是天赐予你、宝贵着你、使你有所成就的手段。活着的时候,我们真诚地爱别人,这就是事奉宇宙乾坤父母,因为我与他人都是宇宙乾坤父母的孩子;死了,我们就得到了安宁,因为我们活着的时候,仰无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张载又说:“《易》谓‘原始返终,故知死生之说’者,谓原始而知生,则求其终而知死必矣。此夫子所以直季路之问而不隐也。”(同上)张载在这里集中阐述了儒家生死观的两条材料,一是《周易·系辞传》关于生死之终极根据的求索,意思是,只有明了天地之道,才能考察生命的起源、归宿与究竟,而死亡只是对生命终极地的复归;二是《论语·先进》中孔子关于“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的回答。这两条材料是互为补充的。
“存顺没宁”是一种平宁的生死态度,又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境界。儒家在“尊生”“重生”的前提下,在价值冲突与紧张的场合,追求“死而不朽”,以一种“猛志固常在”的心态,抗拒生命的被窒压和被扭曲。但是在平凡生活中,儒学通常主张“存顺没宁”的恬淡、平静。这里当然吸取了佛家和道家的解脱与达观。佛家主张“了生死”,既然生死能了,还有什么不能放下?庄子说,应当“外天下”、“外物”,“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庄子·大宗师》)这里,“外天下”是遗世独立;“外物”是超然于利害、毁誉、荣辱、是非之外;“外生”是无虑生死;“朝彻”指死生一观,物我兼忘,惠照豁然,如朝阳初启;“见独”指体悟绝对的道;然后进入不知“悦生”“恶死”,无古今、成毁、将迎的“撄宁”状态,即万物齐一的本体境界。
王阳明《传习录》指出:“学问功夫,于一切声利嗜好,俱能脱落殆尽,尚有一种生死念头,毫发挂带,便于全体有未融释处。人于生死念头,本从生身命根上带来,故不易去。若于此处见得破,透得过,此心全体方是流行无碍,方是尽性至命之学。”一个人的声色利欲已难脱落殆尽,而从生身命根上带来的生死念头,则更不易“见破”“透过”。“见得破”、“透得过”在王阳明这里不是“寄世浮生”“譬如朝露”的咏叹,而是尽性至命的学问功夫。尽性至命,不惟面对生命,而且面对死亡,从体认生命与死亡的意义的高度,脱落利欲的系缚,因而才能更加积极地思考和筹划人生(参见段德智:《死亡哲学》,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总之,儒学生死观把个体生命与人类生命、宇宙生命贯通了起来。
儒家的“存顺没宁”模式以一种宇宙家族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的情怀,强调生命意识的自觉,以生界定死;同时又直面死亡,借死反观生;把生命的个体性和有限性与宇宙家族生命的群体性和无限性联系起来。按照这一模式,儒家的人生设计,既生气勃勃、轰轰烈烈、奋发有为,又毫无牵挂粘滞而做到达观自如,正所谓“以出世的精神干入世的事业”。儒家的生死态度,既有壮怀激越、视死如归的一面,又有恬淡无欲、安静平宁的一面,既与那种惧怕死亡、不敢直面死亡的恐惧心态不同,也与那种耽于声色、及时行乐的游世心态不同,既与那种消极无为、惰怠保生的逃世心态不同,又与那种斤斤计较于功名利禄的执著心态不同。因此,在生存与死亡、有限与无限的关系上,儒学克服了二元对峙的局限性,从而把二者统一了起来。在这一辩证统一过程中,物欲的解脱是一个关键。面对死亡,必须有这一解脱精神。
4.慎终追远
《左传》中有“慎始而敬终”之说,《尚书》中有“慎终于始”“慎厥终惟其始”之说。“始终”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生死”之意。儒家慎于生敬于死的生死态度已如前说。
与人类思想史上其他的精神资源不同,儒家尤其强调“慎终追远”。《论语·学而》:“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意思是说,谨慎地对待父母的死亡,追念远代祖先,自然会导致老百姓归于忠厚老实了。这一思想具有很深的文化意蕴。
首先,它反映了农业文明基础上宗法血缘纽带的强韧。在一定意义上,儒家的重视孝道,即是肯定了生死转化、代谢中“死而不亡”的问题,通过血亲的、宗族的、种族的延续来延续和光大其事业、文化、生命。因此,它包含有死亡意识向生命意识、道德意识和文化意识的转化,有限的个体人生向无限的群体人生的转化的思想,并指示了转化的途径。
其次,它表明了谨慎地对待先人的临终关怀、保持死亡的尊严的态度。尊重死亡也就是尊重生命。后人应当帮助先人自然安宁地接受死亡,并获得临终的尊严,而且祭奠追念死者的德业,体悟生死的终极意义。孔子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这反映了一种宗教信念,同时也昭示了人的归属感,强调以人性化的方式料理后事。
5.天道性命一体
儒家的终极关怀具有天命根据与冥悟体认的宗教性格,其天命之道是生命与死亡意义的价值源头。儒者彻悟生死和在精神上超越死亡的根据是天道、天命及其对人之所以为人的规定——道德心性。天道与人道、天道与心性的贯通,表明儒者的世间肯定与世间关怀之中仍有其超越的形而上学的要求,即终极的最后的关怀。中国古代儒者“以天下为己任”、“救民于水火”的信念目标和救世献身的热诚,尤其是至诚不息虔敬无欺地尽心知性、存心养性以事奉天地的精神和“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的安身立命之道,都表明了他们的宗教品格。儒者的使命感、责任感、“舍生取义”、“死而不朽”、“死而后已”、“朝闻夕死”的忧患意识和力行实践精神,都有其宗教性的超越的“天道”“天命”源头。儒者个体有其信念信仰上的终极承担,能发现和发掘自身生存与死亡的终极意义。惟其如此,才能获得安身立命,以使有限的生命达致无限的意义之境。儒者彻底解决生死问题的真正理据不仅在天道,而且在源于天命而有的心性。这是儒者“天命论”和“心性论”的枢纽。儒者的人生态度和生死关怀都有超越世间的意义。
前面所说的“原始反终”“慎终追远”“抱始返本”,都是要追溯到这里。有人说儒学缺乏宗教性,只有世间关怀;也有人说儒学缺乏个体性,只讲群体伦理。看来这都是一些似是而非之论。儒学的生命意识、救世热忱、生死关怀及其超越理据,即是它具有宗教性的铁证。儒学的道德体验与实践,特别是直面人生、直面死亡的承担,绝对是不可替代、不可让渡的个体性使然。也就是说,儒家“天命论”和“心性论”省视了生命与死亡的根源性和个体性,使个体不脱离生生不已的宇宙仁体,同时又从日常共在的沉沦状态中超拔出来。儒家体证了生的超越根据,突显了生的本己性和个体性,同时也涵盖了死的超越根据和死的个体自由。
6.儒学生死观的当代价值
生死及其意义的问题是一个永恒的问题,是世界上各种宗教、哲学探讨不休的问题。随着现代工商科技的日新月异和高龄化社会的出现,天、地、人、我之间更加疏离,迫使现代人远较古人更加感受到孤独无依。现代人的精神安顿已成了问题,生活的无意义感笼罩着新生的一代,他们面对的是无信仰、无本根的生活。在人文淡泊、道德危机和“文化工业”、痞子盛行的世界性氛围中,人们的心灵缺乏滋养,生命缺乏寄托。而人寿的延长,使得迫近死亡的负面心理的纠葛更加严峻。大量的退休之后的准老人、健康老人、衰弱老人或绝症患者的物质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成了问题。临终物质与精神关怀的缺乏及料理后事的非人性化方式,更使人们惶恐不安,使得临终者不能从容不迫而又具有人性尊严地承担死亡。
现代化的科技文明不能代替现代人思考人生与人死的意义与价值问题。儒释道耶等思想资源中具有丰富的破除世俗迷执的生死智慧。借助人类古老文明的精华,凭藉宗教的、道德的高度精神力量发现生死的终极意义,从而在信念信仰上具有某种终极承担精神,是提高现代人生活品质和人格境界的重要途径(参见傅伟勋:《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台北正中书局1993年版)。
儒学,特别是它的形上本体论及生死观是我们走向21世纪的重要的精神依据之一。它可以扩阔我们的精神空间,避免价值的单元化和平面化,避免现代化所预设的价值片面夸大,并批判其负面,批判工具理性的恶性膨胀。儒学的安身立命之道可以丰富我们的人生,提升我们的人格,活化性灵,解脱烦恼,缓冲内心的紧张,超越生死的执著,复活人文理想的追求,使人真正过着人的生活。儒家的精神对21世纪社会和人生负面的治疗和拯救,尤其是对人性和人心的安立,肯定会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儒学根本上是教人如何做人,明了生活的意义。儒学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主干。儒学在现代社会的创造性转化有助于促进人们的理想人格追求,克服人文精神的失落、民族素质的弱化和民族性的消解。
一个人、一个族类必然有自己终极的信念信仰。它超越了世俗人伦的实践意义。儒学的超越性和内在性的和合,肯定人本乎自己的(又是天赋的)心性从事道德实践的工夫,可以知天、事天、上达于天,即达到一究极的、为天所知的境界。“天”“天命”“天道”及其对这一终极真实的主体性体认,是儒家在精神上超越俗世的真正根据。儒学资源仍然是现代人生的源头活水,是21世纪中国与世界的重要精神食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