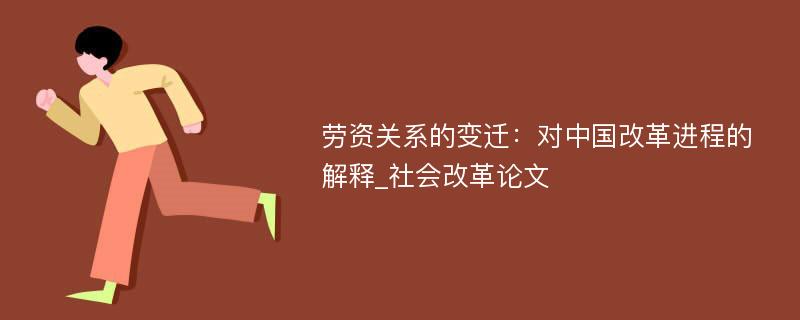
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变迁:对我国改革历程的一种解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程论文,资本论文,关系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劳动和资本分别是劳动者和资本所有者获取收入的两种方式。劳动必须依附于资本才能获得劳动力价值,而资本必须依靠劳动才能赚取利润,因此,在劳动与资本之间构成一组相互依存和对抗的关系。然而,如果我们从经济全球化的视野来看的话,马克思的这种论述可能需要增加一些新的内容。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在马克思时代之后又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历史,而今,全球资本更多是依托于全球范围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而流动和增殖,并且已经在全球空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治外法权。这样,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就有了新的变化。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复杂而重要的课题。我们仅从资本的扩展逻辑中简单绘制出二者的关系变迁图景:作为经济力量的资本在形成的早期主要得益于市场化的劳动力,当资本成功地取代宗教和政治而成为主导社会变迁的力量时,劳动者就被剥削成为无产者;当资本局限于一国之内并由国家来主导时,无产者还可以组织成为马克思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来与资产阶级抗衡以维护自身利益;当资本不受民族国家的经济政策羁绊并且能够在全球空间自由流动时,它就直接与全球的消费者结合起来,就与仍然处于固定地域的生产者相分离,其结果是,不利于资本流动的劳动大军陷于无力反抗的绝对贫困状态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的历史才呈现出劳动与资本之间的这种关系变迁图景。我国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到目前成为世界资本市场不可忽视的经济力量。我国没有改变社会主义体制而取得这一成就的确是奇迹。然而,尽管如此,我国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变迁却浓缩在这二十多年的改革历程中。本文试图在中国语境下展现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变迁轨迹,从而揭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三次改革之争的一个内生变量。
一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得以正常运转的基础条件在于,劳动力可以像商品一样自由流动和交易,并与资本紧密结合在一起。没有劳动力的自由买卖也就没有资本的原始积累。一方面,工人依赖于工厂的雇佣来维持生计,而资本则依赖于工厂的雇佣工人以求得再生产和进一步积累。另一方面,工人是通过工会和国家法律的权利保障来反抗资本家的过度剥削。正是劳动与资本之间存在的这种依附和对峙关系刺激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中国,劳动与资本的这种矛盾关系是在社会主义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指导下分两个步骤来实现的。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推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政策,使劳动力自由买卖与资本原始积累的正相关性在我国成为现实。首先,是意识形态的转变。马克思的劳资关系理论是用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但这不适用于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因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性质决定了所有资源都归属于以无产者为主人的国家或集体,从而决定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不具备劳动与资本发生勾连的前提。然而,在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改革使我国这种意识形态开始发生变化。邓小平根据国情提出的“中国式的现代化”使劳动与资本的关联性开始在国家意识形态上获得了支持。其次,是政策的调整。在八十年代前期,我国一系列的改革使劳动与资本的依存关系获得了制度的支撑,并在实践中开始产生积极作用。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获得劳动和经营的自主权,农民的劳动成果与资本运作直接挂钩。在城市推行经济责任制的改革,大力发展城镇集体企业,支持和扶植个体经济。这样,农村和城市的许多劳动者都自主开发资本,并从商品交易中直接获益。如果说我国改革起步于让劳动者直接掌握资本的话,那么,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的创办就标志着资本运行逐渐具备规模效应,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变迁也从此开始正式接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轨道。在整个八十年代,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政策的指引下,资本从一个襁褓婴儿开始孕育,在劳动者的积极参与中茁壮成长,从此逐渐成为一种主导社会变迁的力量,同时我国逐步融入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很显然,在八十年代初改革之争的焦点可以视为,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可以存在劳动与资本的关联性。
在九十年代初,坚定不移地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策,进一步使资本开始真正成为主导社会变迁的力量。1989年的政治风波引发出一场关于我国姓“资”还是姓“社”改革的大争论,其焦点在于:经济发展是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这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是让资本成为社会变迁的主导性力量,还是继续使资本为所有劳动者支配。显然,这一次争论终结于邓小平九十年代初的南巡讲话。他指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1]。这表明我国的改革,不能把社会拉回到计划经济时代,而是要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来化解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开始出现的紧张关系。随后几年的市场化改革基本上打破了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加速了资本多元化的进程。在改革的浪潮中,资本的势力持续扩张,而劳工的地位和劳动的价值却在持续弱化。这表现在,国有企业的改革逐渐把终身雇佣制改变成为全员合同制,所有职工的合同期限开始变得不固定和不稳定;逃避缴纳“三金”和其它劳动保障责任;对下岗职工、离岗退养(内退)人员、长期病休人员等,不签订劳动合同,形成模糊的劳动关系;把原来属于企业加工的程序转移到乡镇企业或民营企业,以此降低劳动成本;把工程层层转包给没有与工人签订劳动合同的包工头。同时在企业中也引发了各种对抗性的矛盾。
然而,劳动本身意义的弱化不止如此,因为九十年代是“断裂的年代”,是“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消费”向“耐用消费品生产和消费”过渡的年代。[2]这表明,资本已在社会变迁中已取得了权力支持的主导地位,资本的运行形成了多元化的社会结构,而且,资本已经开始直接与消费相结合。其结果是,迅速贬值的劳动不再可能成为与资本相抗衡的力量,而且主要由劳动者所组成的社会弱势群体愈发不能影响社会舆论和公共政策。从此,加快资本循环和推动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已不是劳动者的生产能力而是消费者的购买能力。
二
在新世纪之后,尤其是以加入世贸组织为标志,我国以成员国的身份正式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表明,我国的资本市场已难以完全通过政府来主导和控制,而是溢出于国家的经济政策,并成为全球资本运作的一个重要场域。这样,我国不仅不可避免全球资本的治外法权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而且在八九十年代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基础上,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变迁已经具有“中国特色”。
首先,经济全球化使资本与劳动相分离成为当今世界的一个普遍现象。在全球化时代,资本愈发强化自由流动的速度,要求高效便捷地穿越空间的限制,但劳动力仍然停留在局部的空间,这种背反关系促使资本与劳动的分离。这是因为,资本的再生产和增长在信息化的电子时代都已经很大程度地变得自主独立,不再依赖于与生产者签订任何特殊的、长期的契约关系,而是依赖于消费者。资本为了它的竞争力、有效性和获利性,逐渐与消费者联姻,而且,资本预期的流动方向和规模都受消费者的偏好、时间和规模所决定,而劳动力的影响已经成为第二位的考虑因素。其结果是,劳动力的地位和劳动的性质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主要是“灵活”的劳动力市场。短期合同、滚动合同或没有合同的劳资关系,致使任何职位都没有内在的稳定性,从而导致稳定和有保障的前景变成了短期的行为。这样,短期雇佣的思维方式最终取代了长期雇佣的思维方式。同时,随着劳动者的知识层次和技术含量要求不断提高,“劳动已经成为一种‘高层次的’或‘高成就的’体育运动,它超出了大多数求职者的实际能力之所及。”[3]这种精英化的劳动方式使多数劳动者无力参与社会劳动;技术化的劳动方式不仅使所有劳动者的劳动寿命缩短,而且使他们对生活前景充满不确定性意识。这种全球性现象的后果已造成了资本与劳动的马太效应:资本拥有者愈发居于社会的强势地位,控制社会变迁的话语霸权,从而掩盖或抹煞严重的社会危机;劳动者愈发陷入贫穷而丧失社会主人的地位,但却又难以通过马克思意义上的阶级斗争来争取社会权利。
其次,我国的改革无法阻挡反而催化了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变迁,从而出现资本抛弃劳动之后所遗留的许多社会政治问题,如贫穷问题、失业问题、医疗与社会保险问题、教育问题,等等。在当前法律缺位、市场规则不健全,各种暗箱操作、寻租行为大量存在的情况下,一些强势群体巧妙地利用现有的法律和制度,合法地使自己掌控的资本流动高效化、收益最大化。不仅如此,国家政策的公正性也面临着新的问题。因为各种强势资本集团通过集聚资本的方式来影响公共政策,甚至政府官员利用权力直接参与资本运作,从而导致许多公共政策和法律的制定和执行都向富人倾斜。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多年无法解决房地价上涨所导致的住房问题。这是因为,资本总是流向利润更高的领域,在人多地少的中国,资本增值最多最快的必然是房地产市场,又因为只有国家才拥有土地所有权,只有政府才拥有征收和买卖土地的权力。其结果必然是,资本极力与政府权力结盟,把风险和不确定性转嫁给了庞大的弱势群体。然而,遭受资本流动所蹂躏的劳动者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更不用说,“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意味着人们会温顺地接受资本的驯化,以至于不能也不愿意对资本的流动实施任何有组织的反抗。面对与资本保持暧昧关系的国家权力难以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经济精英控制社会舆论,工会的功能弱化,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都只能“以个人传记的方式来解决系统性的矛盾”。[4]这样,劳动者成为穷人就不言而喻了;而且,他们无法通过自身的能力来摆脱绝对贫穷,也无法通过既定的教育体制和经济发展来确保下一代不再贫穷。因此,第三次改革之争的内容就是,劳动意义在资本运作中的逐渐消逝对已成为穷人的劳动者产生无以复加的后果时,政府权力如何缓解少数资本拥有者与多数已成为穷人的劳动者这两个极端之间的紧张关系,如何在社会财富明显分配不公的困境中发挥积极作用。
三
从以上我们勾勒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变迁轨迹在中国的生长过程来看,我国资本市场从二十多年前“星星之火”已经形成了“燎原”之势,主导社会变迁的资本运行不仅重铸了多元化的、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而且还与全球资本对接起来。这样,在全球空间中自由运作的资本不仅与中国广大的劳动大军相分离,而且还不断吞噬原只属于国家和政府的权力;从劳动方面来看,劳动在八十年代是作为创造财富的主体来开发资本,但当资本在九十年代可以自主运转之后,劳动的价值和意义则被逐渐贬低,在新世纪进而变为资本自由流动的绊脚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关系变迁中的劳动与资本可以比喻成为伊索寓言中的“农夫与蛇”。如果说,我国改革之初的商品经济脱胎于农民“穷则思变”而发明的联产承包制,那么,为什么我国资本经过二十多年的培育却给劳动者带来贫穷呢?我们当然可以把其中的原因归咎于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变迁这个自变量,但除此之外,我们也不得不深思在其中起到推波助澜作用的中国改革。我国二十多年来的改革方向是,通过经济政策的调整和政府职能的转换,国家权力逐渐疏远于劳动者,转而积极支持资本在中国的茁壮成长。然而,政府在推崇市场化的经济改革的进程中,社会保障体系、法律制度框架、医疗卫生机构、伦理价值观念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其后果是,劳动与资本的严重失衡以及由此导致的各种社会问题。
如何缓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变迁中的张力呢?政府在其中应该如何发挥积极的主导作用呢?我们先来看看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在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历程中是如何平衡的。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上,劳动与资本的紧张关系在两个阶段体现得比较明显:一是19世纪后期。其解决的途径有二:一方面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所号召那样,所有无产者都联合起来,形成共同的阶级意识,通过无产阶级的力量来对抗甚至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这起码可以迫使资本家在工资和福利待遇方面做出让步;另一方面是政府采取积极的福利国家政策,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来确保所有劳动者的基本生存需求。可以说,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这两种途径对后来缓解劳动与资本的张力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二是20世纪后期,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当资本在全球空间流动而与劳动相分离时,劳动者又开始陷入贫困中。尽管处于“后福利国家时代”的西方国家至今还未找到有效办法来解除全球化带来的社会贫穷,但毕竟可以继续延用已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福利国家政策。所以,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当政治权力不断被资本吞噬,劳动者不断被抛弃到穷人群体中时,我国改革的总体方向不是使政府的权力继续单向度地助长资本的支配地位,也不可能使国家退回到计划经济时代,重建与劳动结盟来对抗资本,而是要走“第三条道路”:充当社会总体资源再分配的执行者和社会系统动态平衡的监护人。一方面继续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支持中国资本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博弈,以此维护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大国地位;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是,运用劳动者给予的公共权力,通过架构宏观的再分配体制和稳定的福利政策来维护社会正义,使最不受惠者也能够有生存保障和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否则,政府的权力将丧失其人民认同和支持的合法性基础,也就难以维系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