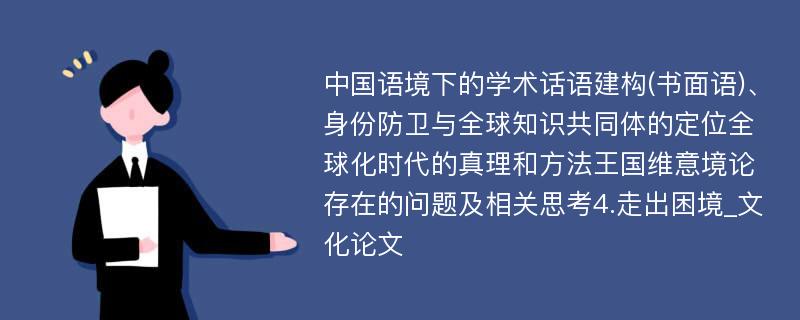
中国语境中的学术话语建构问题(笔谈)——1.身份防御与全球知识共同体的面向——2.全球化时代的真理与方法——3.王国维“意境说”的问题及相关思考——4.走出“失语”焦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语境论文,共同体论文,中国论文,意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602(2014)04-0143-14 身份防御与全球知识共同体的面向 黄卓越 中国在对待差异性知识的态度上,一直是双重的,即开放与抵制并存,也由此引起过大量剧烈的辩说。就单独的一方面,即对差异性知识的抵御来看,也是常态性地存在于中国历史周期中的,并与中国历史文化的特点及由此引起的身份解读方式等有密切的关系,需要对此做点分析。大致而言,可以分成两种情况:一是作为较为单纯的知识与文化输入,比如魏晋以后的佛教与16世纪末以来一段时期的耶教引入;二是与强势性政治、经济等入侵相伴随的知识与文化的输入,比如19世纪初西方各种新学(包括基督新教)在中国的泊岸,两种类型的输入均遭到了中国知识社会的强烈抵制,而背景却是有所不同的。很显然,后者所呈示与带来的问题更为复杂,由此也造成了对不同层次效果分辨的困难,与前者面遇的情势很不一样。但是这些抵御方式及其推论逻辑则有一些共同之处,即往往会将知识与信仰置于一个不加区分的“同构体”之中,为此而将对差异性信仰的排斥同时转化为对差异性知识形态的排斥。其次是即便从知识输入本身来看,也会被抵御者们视为是对自我身份(同时也是“老大”身份)的一种挑战,从而使原来确定不变、清晰自足的主语身份,或说是“中国性”、“中国特征”变得模糊难辨。尽管这种论证有时是在知识学层面上展开的,但仍可以归属到族性身份确认的范畴之中。 20世纪80年代,随着新一轮的向外部世界的开放,知识领域的抵御意识也被再次唤起。仅从人文科学或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这一分支领域看,诸如现代主义文学、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等被引入之时,抵御的意识均显示与释放出了强大的能量。而最近这些年来,曾经被激烈抵制并被视作“有害之物”的差异性知识,有些已经被我们看平淡了,或习以为常了,有些则被我们积极地吸纳,顺利地融入到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之中,有时甚至难以区分哪些是“我们”的,哪些是“他们的”。然而在若干交流的区域,比如在对待海外汉学的态度上,抵御者依然表现出了不弃不让的姿态,甚至于通过冠以某种谑号如“汉学主义”,使对象在命名上即处于一种十分不利的局面,这也是知识界在抗拒差异性知识时惯常使用的一套言说策略。与前两轮,尤其是19世纪以来于历史进程中出现的知识揽入有所不同的是,80年代后对各种外部知识的引进既不是在某些附带性外力的陪衬下发生的,而是中国学人自觉地面向国际知识世界所做出的选择,又大致能够将知识与信仰做出适当的区分,更多注重的是一些工具性的目标,其次也会对一些知识形态的思想取向(意识形态)加以辨析,这自然与“科学主义”对我们思维的长期洗涤有一定的关系。 在这样一种历史梳理的前提下,就今天的情况来看,对有些在抵御性话语中习惯性出现的立论或提法,也需要再做澄清。 其一是所谓的“中国特征”的提法。就我们看来,这一提法可能存在着的问题是,首先,中国特征的内涵是什么?其次,中国特征将由谁来定义,即谁掌握这一下定义的权力?可以举些通常的例证,如以一般思想史为例,难道儒道释是中国特征吗?佛学最初属于异域性知识,但自出现第一个汉语翻译文本之后,事实上就已纳入到了“被中国化”的历程之中,后来又不断地被中土的高僧、学者与民众社会所重构并成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然而我们又不能将佛学视为中国性的知识,而是更为合适地将之视为与亚洲其他地区与民族交叉共享的一种知识与思想模块。儒家虽然源出于中土,但除了这一点是确定的之外,就很难确认其“本真”的面貌,而是在历史的移位中已不断地被改写为新的文本,在宋明之后,又大量地吸纳了佛学与道学的致思方式,使得这一体系变得愈益繁复与庞杂,更不用说在20世纪以后出现的“新儒学”,也是在大量地掺入西学概念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可以说,几乎所有我们现在仍拥有的概念都是处在移位与重释的过程中的,而像“意境”这样一种被视为颇具中国特征的概念,事实上也是在至少经历了两次由外域知识补入(唐以后的佛教与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之后才传递至今日的。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也无法寻找到一种固化的身份界义,且不说血统上的,在知识的领域中,随着各种不同地域性知识(中土与外域)的不断植入,知识身份也会处在经常性的变动、转型与扩容之中。因此,即便我们能够在“某一时刻”给出一个界定的坐标,但是却无法阻挡随之而来的扩张性活动对新的知识身份的重塑。从意义的存量上看,这种连续性的解释活动,即便是以逆向的方式展开的,也不是减除式的,而是通过不停地往里“添加”,使我们的知识身份变得愈趋“混杂“,同时也愈趋丰富与多义。从而也使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身份焦虑,在很多情况下,也只是建立在一个假定性地以为有一种本真、无染或固定的身份谱系的前提之下的。 其二,即关于“本土性”的提法。本土性的提法在不同的表述中,有“提醒”与“批评”两种含义,但无论在哪一种含义里,都含有着明显的防御性焦虑意识,并在暗中托付着某种话语霸权实施的策略。当“普遍性”的概念为西方中心主义话语所污染而声名狼藉之后,“本土性”事实上已在当今成为知识公正与“政治正确”的一个代名词,因此,使用这样的言述便永远也不会出错。难道我们的学术最终不是要导向一种本土性知识系统的建立吗?谁不承认这样的命题,就至少会有一种去民族性的嫌疑存在,而且,如果不是这样,岂不等于将一个民族的学术置于虚无的地步?然而究竟什么是本土性,却在这样的表述中始终是阙如的,因为如同无法精确地界说我们的知识身份一样,同样也很难界定这个所谓的本土性。就方法论来看,难道可以将朴学的实证主义作为本土性的标本吗?很显然,这种朴学实证主义不仅与西方现代的实证方法有重叠之处,而且在用于治理当代的社会与人文科学时也是远远不够用的,因此,即便像被誉为“国学”大师的陈寅恪也在半个世纪以前即对之表示出不意,而更愿意通过熔铸东西的路径而开拓自己的学术新境。 当然,我们还是可以一般性地同意本土性这样的提法的。但不是将本土性看做是对传统学术路径与理念的一种复制,也不是以之作为对传统内容或乡土内容单纯展示的一个代称,即便是有这样的本土性存在,其在当代学术认定的系统中也还属于低层次上的定位,并易将“文化”误等同于“学术”。那么什么是“更高一级”意义上理解的本土性呢?这就是相对于国际的知识场域,或在国际的知识场域中建树起来的知识特征,这也许可看做是对从防御性角度理解的所谓“本土性”的一种递进性解释。也就是说,本土性概念的含义,不应当是在与世界隔绝的意义上,而是在与世界关联的意义上能够成立的一个表义。这种关联,既指可对比性,也指可交涉性、可传递性等。就以上的一些分辨来看,“低层次”意义上的本土性其实是很容易做到的一件事(只是我们的学科框架与论述框架早已经被国际化了一遍,也很难有纯净意义上的本土性),这难道还值得挂齿一谈吗?真正的难度还是出现在当我们被置放于一个更大的对比系统中,即一个可互涉与可传递的场域中,同时也是一个国际知识生产日益更新的场域中时,如何确立与构建自己的学术面向的问题。在这个场域中,当所有区域的学者都在其中添加自己的差异性、工具性智慧的时候,任何一个民族的单方面智力都已显得十分的单薄、有限。 作为整体的中国人文与社会科学(而不是某些单一个人的学术),一直处在两种价值判断的交汇处,一是如何有用于中国社会,二是如何能够在国际知识体系中确立自己的地位,并对之有理念、概念、学理等等方面的贡献。这两个序列的评判标准在具体贯彻时会有一些重叠,但不是都能够通约的。对于前一个问题,恐怕没有哪个学者可以轻松地给出结论。对于后一个问题,或许可以相信,我们还是做得相当不够的。这有很多方面的原因,有些来自于客观的方面,比如身处于现代学术进程的后发性位置、语言流通上的局限、学科划分与科研评估体制的束缚等,但不可忽视的一点,也在于我们还缺乏更为开放一些的情愫与怀抱,大多数的学者在科研中所用以对比、参照的总是“本土”圈内的学术,而并未将自己作为全球知识共同体中的一员,与之同时,防御性意识的惯力也会如在历史轴轮上堆积起来的渣垢,于意识的深处制约着创新能量的大幅喷发。要想使中国从一个后发性现代知识的位置走向国际学术的前沿,并从目前已经成形的学术大国(从学者人口比率上看),转型为一个学术强国(在全球知识共同体中占有一席地位),仍是一个“道阻且长”并需要“细密商量”的事儿。或许,只有当中国不仅在研究单个国家,同时也能在全球共同关注的理论问题上,甚至在对中国以外诸地区与国家的研究中,均能有独特的建树与被公认的实力的时候(这当也是作为学术强国的基本标准吧),我们才能摆脱学术滞后的身份位置。在过去,我们有过过多的因防御性意识产生的身份焦虑,但到了今天,我们是否也该怀有一种在开放性视野下激发的身份焦虑呢? 全球化时代的真理与方法 金惠敏 李春青教授在给我的约稿函中写道:“在我们这样所谓‘后发现代性’语境中究竟应该如何做学术研究?我们借用了西方理论观点或方法进行研究,我们的研究成果是否就成了西方理论的‘翻版’?比如王国维的‘意境’说,究竟应该如何定位?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对待西方理论?”①李教授的这些问题可以归结为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学界基本上一直都在纠结着的一个重大问题,即中国和西方的关系问题,它因各种不同的机缘、话题而被不断地激起、被不断地重新质询。我所谓“被不断地重新质询”是说,似乎每一次讨论都要从头来过,然后争吵一阵子便归于沉寂,等待下一次的机缘,如此的循环往复,而问题本身却依旧在那儿晾着。 这个问题“本身”,如果从哲学上说,就是真理与方法的关系。以为真理会自己呈现是一种十分幼稚的想象。真理之自行“解蔽”(aletheia)、“自生”(Ereignis)是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现象学的革故鼎新,也是海德格尔存在论的软肋,因为任何显现均先已假定了意识的存在,换言之,显现均为在意识中的显现,它无法脱离与主体的干系。具体于真理与方法的关系问题,这也就是说,真理难脱与方法的干系。那么,真理与方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许多思想家认为,方法即真理。尼采早就声言:“没有事实,只有阐释!”②尼采的意思是没有赤裸的真理,只有被阐释的真理。在此“阐释”即是“方法”。在电子传媒时代,麦克卢汉发布了一则读若天书的格言:“媒介即信息。”③对此,波兹曼形象地解释说:“在手握榔头的人看来,任什么都像是钉子。……在端着相机的人看来,任什么都像是图像。在拥有计算机的人看来,任什么都像是数据。”④这是说,工具即视角,媒介作为工具也是一种视角;通过何种媒介看世界便会有该媒介视角所给予的那种世界。在这一意义上,麦克卢汉和人类学家卡彭特都喜欢援引诗人布莱克在其《耶路撒冷》中反复吟诵的一个名句:“他们成为他们之所见。”⑤根据布莱克,一是看的方式,二是以此方式所看到的内容,构成了人的基本存在。单纯的自然界不是人的存在,人的理性能力也不是人的存在,只有人与自然的关系才是人的存在,而此关系是由一定的媒介来承担的。由此,我们不妨说,媒介即真理。 如果说以上思想太过人文气的话,那么量子物理学家海森伯则从科学实验方面证明方法即真理。他发现:“想以任何一种事先规定的精确度来同时描述一个原子粒子的位置和速度,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做到要么十分精确地测出原子的位置,这时观测工具的作用模糊了我们对速度的认识,要么精确地测定速度而放弃对其位置的知识。”⑥这就是被后现代主义者哈桑所津津乐道的那一著名的测不准原理。⑦从此原理出发,海森伯断言:“即使在科学中,研究的对象也不再是自然本身,而是人对自然的探索。这里,人所面对着的又仅仅是他自己。”⑧“换言之,方法与对象不再能够分开。”⑨海森伯虽然不是主观唯心主义者,但其测不准原理无疑是突显了方法对于真理的决定性意义。真理诚然不同于方法,但方法则是真理之呈现于人类意识的限度。我们能够接触到的真理就是我们的方法允许我们接触到的真理,简言之,方法即真理。 我们不能不经方法而达到真理;然而一旦经由方法,真理便不再是真理,而成为方法,这都是常识了。不提德里达流传甚广的“文本之外无一物”了,就说我们的老祖宗公孙龙吧,他早就教导我们说:“物莫非指,而指非指。”这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凡物莫不呈现于我们的指称之中,而在指称中的物却并非我们所意指的那个物。此物非彼物啊! 记住这一点,我们就不会简单地抱怨王国维之使用方法这件事本身了。我们甚至也不能抱怨王国维的方法是西方的,外在于中国对象、中国经验,因为所有的方法对于对象而言都是外在的。事物本身与方法无关。方法是人的宿命,包括使用方法的人和反对方法的人。反对方法的人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使用方法,因为其方法经习得而来,方法淹没在其对世界的认知和表达之中。这就像牙牙学语的幼儿,尽管没有语法意识,但他在学话中便掌握了语法。伊格尔顿说得好:“敌视理论通常意味着对他人理论的反对和对自己理论的健忘。”⑩如此说来,即使中国文论家如王国维不使用德国理论,那他也会使用别的理论如中国自身的理论资源,只要他尝试去认识,去概括中国文学这个对象。认识从来是带着方法的认识,甚至也可以说,认识本身就是方法。 于是,问题当只在于理论或方法与对象之间的切合程度。伽达默尔的“效果史”(Wirkungsgeschichte)概念试图在真理与方法之间做调和:它首先肯定了方法之必然,这根本上取决于任何认识必然带着“前见”,或明或暗的“前见”。理解必须是有能力去理解,而“有能力”则是说具备理解所需要的知识,且这种知识多半会转化为一种不自觉的习惯。举例说,你要读懂《红楼梦》,你必须有关于《红楼梦》的历史知识,一定的文学素养,一定的鉴赏能力,等等。这就是说,你已经具备阅读《红楼梦》的方法了。你的理解可能带有主观偏见,而“效果史”概念则强调理解必须是文本的自性展开、自性发生作用,你的理解因而便是你的“前见”与文本自性的对话、协商。伽达默尔要求:“一种实事求是的解释学应当在理解本身中揭示出历史的真实性(Wirklichkeit)。”(11)此话是要求在方法中让真理如其本身地呈现出来。在伽达默尔,完美的理解就是方法与真理的合二为一,这时方法便不再是那种他所深恶痛绝的科学主义的方法。但我们要警惕,真理与方法的完美切合永远是一个解释学的梦想;不存在完美的切合,裂缝从来都存在,也永远不会全部弥合,而这也恰恰是继续阐释的动力。我们要学会接受争论,接受歧见。争论和歧见将显露出各自方法或视角的局限,从而扩大各自的视野。何乐而不为呢? 不存在内在的方法,一切方法都是外在的。以为中国传统的理论内在于中国文学不过是一种错觉。在此意义上,西方的方法与中国本土的方法在作用上、价值上是可以等而视之的。这里或许更需要为西方的方法做一些辩解,因为方法的反对者既反对西方的方法,也反对中国本土的方法;而西方的方法还会遭到另一重的反对,即中国方法守持者的反对。 第一,中国的文学尽管有其独特的存在,我们不会把《诗经》混同于荷马史诗,把关汉卿混同于莎士比亚,把曹雪芹混同于托尔斯泰,等等,但就其文学的基本要素如抒情、叙事、虚构、陌生化等等而言,他们之间又是有一些共同之处的。这涉及共同的人性、共同的需求、共同的审美经验。这种共同性既存在于显性的话语层面,也存在于隐性的本体层面。否认这种共同性将无法解释古往今来实际发生着的各民族(或部落)之间的交往和对话,无法解释文学作品何以被跨界阅读和接受。最近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西方诺贝尔文学奖即是一个明证:通过西方的眼睛是可以阅读并欣赏中国文学作品的。 第二,使用方法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如王国维并非一纯粹的西方学者,当其使用西方之方法时,他先已是有意无意地做过中西方法之间的对话了的,因为王国维作为一位训练有素的中国文学专家有对中国文学的“前见”。在本质上,西方汉学家与王国维并无不同,只是他们是从自己的西方“前见”与中国方法(他们或者学习过中国文论,或者已在对中国文学作品的研习中产生了一些抽象)进行对话的,出发点不同而已。因此我们可以断言,王国维的“境界”概念绝非仅仅一个西方视角之所见,完全与中国传统理论无关。学界早已举证,在对“境界”概念(或与之相通的“意境”概念)的使用上,王国维并非开天辟地第一人。(12)王国维的文学“前见”应该是既有来自西方的,也有上承中国传统的,两种方法在对话中协同作用于中国文学实际,而后“境界”出矣。 第三,文化从来是复合结构的。一种文化固然有一种文化的特色,如说西方文化是理性的文化,中国文化是德性的文化,但这只是就其突出特色或主导性力量而言的,那些不突出的、被抑制的、在冰上之下的要素也共存于一种文化的结构之中。我们不能认为中国文化没有理性,西方文化没有德性,其区别只在于理性或德性在两种文化各自的结构中位置不同而已。这于是就根本上决定了方法的普适性,即是说,任何一种方法都会在任何一种对象中发现它能够发现或发掘的东西。不是只有西方作为研究中国的方法,中国也可以作为研究西方的方法。每一种方法都能照亮在一种文化中被其突出特色所掩盖着的方面。就此而言,方法是促使一种文化发生变革甚至于革命的力量。 第四,在历史上,我们有异域方法与本土经验成功对接和融合的范例。近年季羡林和汤一介等学者鼓吹“大国学”,欲将佛学这种西来之学纳入“国学”范畴。这听来似乎有些荒诞,但案之于中国历史实际,还确乎是有道理的。在中国这个“地方”的思想学术不是单一的儒学,单一的汉学,而是儒释道共存,各民族思想文化共存。而在这样一个“大国学”的形成过程中,不言而喻,是一定存在着儒释道互释、各民族思想文化互释的。所谓“互释”意味着各以其方法丈量对方之真理。在中国文论发展史上,以佛学这种泰西之学、泰西之方法来阐释中国文学经验的例子不胜枚举,且硕果累累,成为中国文论一笔弥足珍贵的遗产。非经特别提示,有谁会意识到今日我们许多学术用语与佛学的渊源关系呢,诸如“悲观”、“本性”、“本体”、“意识”、“顿悟”、“观照”、“因果”、“不即不离”、“不立文字”等等?它们已进入“国学”的基藏书库,没有谁目其为“非我族类”。 由此说来,未来某一天,柏拉图或柏拉图的汉译也不是没有可能加盟我们“国学”大家庭的,不过那时将不再有中学西学之分,人们只是谈“古”论“今”,其心中只有古今之分。在全球化时代,人们将不再谈论“国学”,因为严格地说,“国学”是建立在中西二元划分基础上的一个概念。相对于历史长河而言,“国学”,甚至“大国学”,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仿照一个马克思的说法,民族的“国学”终将为“世界文学”所取代。 我们早已进入一个全球化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是对话,是彼此的方法基于彼此的真理的对话。对话将改写各自的“真理”,如果我们不是把“真理”理解为纯粹的物理性存在,而是社会性存在的话。一切社会性存在都是话语与实在——也可以说是方法与真理——的动态对话的结果。海德格尔把“争辩”称为“实事”,阿尔都塞把“意识形态”落实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威廉斯把“文化”下沉到“日常生活”,古英语以“思”(think)为“事”(thing),等等。依照这样的思想,任何对话都将在方法和真理两个层面上同时展开。 在自我与他者的相互对话中,伽达默尔提醒我们,切记避开一种“危险”,即“在理解中‘占有’他者并由此而无视其他者性。”(13)也许对那些认真的阐释者,这提醒是多余的,因为他们知道应该对对象的陌生和差异抱着谨慎而谦虚的态度,否则对象在主体性逼视的目光中恐惧地遁迹无形。 一个研究者如果具备了这种虚席以待他者出现的态度,那么对他来说便是不再有错误的解释而只有不同的解释了。“不同”在此没有正误之分,它只是意味着在方法与真理之间所建立的一种真实的历史性关系。这种关系向变化开放,但这变化绝不意味着今是而昨非,而是在新的存在处境中与阐释对象之间的关系调整。如果不变化,那倒真是一个错误了。 王国维“意境说”的问题及相关思考 彭亚非 王国维的“意境说”在中国文论学界影响很大,这是个不争的事实。同样的事实是,一个世纪以来,对这一影响巨大的王氏“意境说”一直缺乏深入的反思。就此而言,我很赞同春青教授的观点:罗钢教授做了一件很重要的、具有开拓性的工作。另外,对于春青教授在文章中就罗钢教授的观点所谈的一些意见,我也基本认同——其中有些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不过,有些问题我觉得或许还有进一步斟酌商讨的需要。因此不揣浅陋,在此谈谈我的一些相关想法,以就教于两位教授和学界同仁。 首先,我想我们在讨论王国维的“意境说”之前,还是有必要先区别一下中国传统诗学中的意境观和王氏的意境说。这是两个层面上的问题,它们在性质上和意义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意境说是中国传统诗学中固有的一种诗学观,我觉得这一点应该是毋庸置疑的。在王国维张扬这一概念之前,它可能没有处于中国诗学的核心地位,但是我们也应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意境之说在中国诗学史上有一个不断生成、形成和集成的过程。即它不仅为不同时期的诗论家以自己的方式理解、追问和运用,而且中国传统诗学的核心精神也在通过不同的维度不断地指向它和接近它。 意境者,诗意之境象、境界、境地也。所以在诗学批评中也常常单言“境”或“境界”、“境象”。唐人首开以“境”论诗先河。王昌龄《诗格》云:“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情。”“久用精思,未契意象……心偶照境,率然而生。……搜求于象,心入于境,神会于物,因心而得。”僧皎然《秋日遥和卢使君游何山寺宿敭上人房论涅槃经义》中说:“诗情缘境发。”司空图《与王驾评诗书》云:“长于思与境偕,乃诗家之所尚者。”明人已有“意境”之说:“作诗之妙,全在意境融彻。”(朱承爵《存余堂诗话》)清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一则云:“神理意境者何?有关系寄托,一也;直抒己见,二也;纯任天机,三也;言有尽而意无穷,四也。”但大部分情况下,明清人还是多以“境”论诗。如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三有言:“遇境即际,兴穷即止。”卷四中说:“才情所发,偶与境会。”清叶燮《原诗》“内篇下”中说:“故有境必能造,有造必能成。”“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至晚清况周颐的《蕙风词话》,才开始大量使用“意境”一词评诗论词。这一事实已是学界常识。 当然,仅有这一事实还不足以说明它在中国诗学中逐渐形成的重要价值和地位。真正重要的是,中国传统诗学的核心精神中,至少有三个重要维度的指向,对于意境概念的最终成型和价值定位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的。这三个重要维度就是:对无穷诗意的追求,对最高诗意形态的追求,和对超越性诗格境界的追求。限于篇幅,我不能在这里对这三条线索一一进行梳理。简言之,对无穷诗意的追求,使中国诗学中对蕴藉难言的、余味曲包的虚涵诗意要更为重视。在中国诗学史上,人们用了不同的概念去描述这样的诗意对象,如滋味、象外、兴趣、神韵等等,以意境论诗,同样是为了更有效地意会和悟解这样的诗意涵蕴。如僧皎然《诗议》云:“夫境象非一,虚实难明。”清魏源《诗比兴笺序》说:“古今诗境之奥阼,固有深微于可解不可解者乎!”等等。其次,对最高诗意形态的追求,同样经由天然、冲淡、空灵、虚静,而归结于无穷诗意之境象。唐权德舆《送灵澈上人庐山回归沃洲序》中云:“心不待境静而静”;“深入空寂,万虑洗然……”诗意之境的虚静性质唐人已经有所直觉。苏轼《送参寥师》中说:“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空且静方有境可言。至清金圣叹,则这样总结道:“境字与景字不同:景字闹,境字静;景字近,境字远;景字在浅人面前,境字在深人眼底。”(《杜诗解》卷一“游龙门奉先寺”)所以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二中说:“词境以深静为至。”复次,意境概念也更好地契合了中国传统诗学对诗意中超越性人格境界的追求。正如王世贞所谓:“调即思之境,格即调之界。”(《艺苑卮言》卷一)或况周颐所谓:“胸次无一点尘。”(《蕙风词话》卷三)不用说,传统意境说的这三条殊途同归的诗学线索,不仅显示了中国诗学中孕育出意境说的某种必然性,也明确显示了传统意境概念的诗学局限性与特指性。因此,它不宜也不应予以不受限定的、过度的诗学运用与解释。 因此,王国维以意境为说,不光是他的学术素养与学术敏感所致,也是中国传统诗学旨趣本身的自然传承与发扬。就是说,意境成为中国诗学的经典概念,自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并非只是“被经典”。王从中国传统诗学资源中“拈”出一个意境概念来概括、总结和说明中国诗学的核心美学精神,这和中国传统诗论家的做法并无区别:滋味、意象、兴趣、神韵等概念,出现有先后,往往也是中国古代诗学史上某个时代有代表性的诗学家特意“拈”出的一个术语,以说明中国诗学所一直追求的一种诗意深长之美,因此也都并非是贯穿诗学史始终的核心概念。之所以不断有新概念提出,而又不断被更新的概念所取代,就是因为不论哪个概念,都不足以概括中国诗学那足堪意会却难以言传的最高追求,所以也都不足以成为真正的核心概念。王国维不过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认为后起的意境概念较之以前的诸多概念要更能准确地表达这一诗学追求的本质与核心,因此才大力张扬之,并非只是想以某一德国美学观念来取代中国传统诗学追求。否则他就完全没必要用意境这一术语,而直接翻译一个德国美学术语就行了。 这就涉及第二个层面的问题,即王国维如何“说”意境的问题了。对于这个问题,我在很大程度上是赞同罗钢教授的考述与分析的:王国维确实是运用德国古典哲学美学的理论,对意境概念进行了有别于传统诗学的义项诠释与理论解说,从而提供了一套“新”的诗学话语。这才是我们今天应该重点反思的问题。但是即便如此,对此也还可以具体分析。 首先,王国维运用德国古典美学理论来阐释意境概念,也许造成了对中国诗学精神的某种程度上的误读和曲解,但主要还是由此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意境学说。王的意境说并非借用中国传统术语、用语来翻译德国古典美学理论,而是借用德国古典美学理论来解读和阐释中国传统审美经验及其诗学概念。他对意境的推崇之所以影响巨大,恰恰不是因为这是一个来自德国美学的全新概念,而是因为这一传统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标示了中国诗学追求的特定文化精神与思维方式。因此,他对意境的理解与论说,依然有着中国传统诗学资源的有力支撑。所谓有我无我、隔与不隔,基本上也还是一种中国式的说明。即使有所误读与曲解,也并不能因此就真正改变了意境概念固有的诗学美学内涵。因此,将王国维独特的意境学说与他借以思考与分析的德国古典美学理论完全等同起来,恐怕也还是有欠妥当的。 其次,王国维的意境说影响极大,与其开创与张扬之功有关,但也远未成为定论。王对意境的阐释虽然常被奉为权威,但也并未真正成为理解意境本义的不二法宝。换言之,王对意境的解说本身,并未成为中国诗学的核心观念。一百年来,对王说意境的异议与超越一直在进行,关于意境的新的解说与阐释,可说是汗牛充栋,言人人殊。诚如春青教授所说,“中国近现代建构起来的‘意境说’其实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具有内在一致性的理论学说”。只是宗白华之外,鲜有独出心裁、别开生面且深中肯綮的论说就是了。换言之,王在意境说上的最大贡献与其说是运用西学进行了新的解说,不如说是“拈出”意境为说之举。这正如清王士祯首倡“神韵说”的影响要远过于清翁方纲著《神韵论》的影响一样。 复次,王国维、宗白华等的意境说受德国古典美学理论的影响,并不意味着中国诗学传统中的意境说没有在他们的理解与阐释中得到一定程度的总结与发展。阐释有是否到位、是否符合原意的问题,但意境说本身是中国传统诗学的一个重要结晶,因此,它自身的美学特质与诗学精神,还是会在种种深入探讨的阐说中不断显现出来。事实上,不光是意境说,滋味说、传神说、气韵生动说、神韵说、性灵说……均无不在现代以来被予以了种种现代理论化的解说。这些解说的理论资源与方法论也同样无不来自西学。但这并不影响这些概念、范畴及其观念、学说是中国诗学传统在现代的某种总结与发展。真正的问题应该是,近现代以来,以不同的西学理论为解释资源与分析方法解说中国传统文论与诗学概念,在多大程度上偏离了、曲解了、误读了和遮蔽了这些传统概念的文化特性与美学本义。就此而言,相对于王、宗以来的种种对意境说的解释,王、宗的解释也许还是更为接近意境说的中国诗学原意的。他们对意境说的认识与解说,迄今以来一直有着巨大的不可忽视的影响,可能与此不无关系。 当然问题确实是存在的。其中最根本的问题是,王国维以来,中国学界运用西方理论对中国传统文学诗学观念进行现代诠释,其学术目的往往是要将其纳入“普遍性”的理论框架之中去。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回避了中国传统观念的种种“特异性”。这是一种普遍现象。这可以说是一种面对西方的“求同”的追求,是中国学界自王国维以来一直在努力的方向。而在我看来,我们今天研究中国传统观念时,真正要做的工作应该是“求异”。即通过对其文化的、人文的特异性的研究,揭示中国种种传统观念中所包含、所具有、所指向、所追问的“特殊的普遍性”。而其中的一项工作,就是要对以往的“权威”解说进行不同程度的纠偏矫枉。 因此,罗钢教授对王国维意境说的批评和反思的重要意义就凸现了出来。它同时也提示了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即我们现在应该如何解读、阐释中国传统的文论与诗学观念,或者说,我们今天应该如何将中国传统的文论与诗学观念正确地、准确地表述为当代理论话语形态,以及如何使其在当代的理论成果与文学经验的基础上得到新的发扬与发展。 显然,我们现在既不能一味以古释古,又不能如以往那样以西释中或以中证西,而是要尽可能用普适性的现代理论表述方式,将中国传统文论的概念、命题、观念中特有的、具有文化及诗学异质性的本义、原义展示出来、阐释出来。这里有两点我想我们是应该有所自觉的:一是我们不能、也不可能在今天的学术研究与理论思考中完全排除或弃用普适性的、世界通行的现代理论思维方式与表述方式,而这和以往的、几乎已形成惯例的以西释中或以中证西在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上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本质上,这只是使中国传统文论的问题意识、思维过程、逻辑环节和思想内涵获得现代理论话语的表述方式。二是我们要尽可能再现和还原中国传统文论固有的具有文化异质性与美学、诗学异质性的理论内涵,尽可能将这些传统观念再现和还原为本文化语境中特有的问题,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特有的追问与解答。这里的重点是与西学相比的本原性、异质性和另类的普遍性。不应再用西学中固有的理论模式与理论术语来硬套或简单标注中国的文论范畴与观念。比如说西方是再现的,中国是表现的之类。这种对中国文论诗学思想的简单化处理,正是今天最应该得到深刻反省和彻底摒弃的。 事实上,相较于王国维的意境说,宗白华对意境概念的理解要比王更到位。这并非因为宗更现代,而是因为宗更中国。相较于王,宗更加试图呈现中国自身所具有的东西,也就是宗先生自己所强调的“特殊”。或者说,“中国的艺术与美学理论也自有它伟大独立的精神意义”。这才是我们真正要追求的。 走出“失语”焦虑 李春青 在西方学术话语处于强势地位的当下学界,中国人究竟应该如何做学问才能保持自己独特的学术品格——这是不是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明眼人不难看出,其实这也就是所谓“失语”问题的另一种说法。有人说,学术是天下公器,哪里分什么“东方”“西方”?学术只有对错是非,没有什么地域与民族的差异,所以也就无所谓“独立品格”,也就无所谓“失语”。如此来看,上面这个问题是典型的伪问题了。是不是真的如此呢?在我看来对这个问题简单的肯定或否定都是有问题的。要对这一问题做出恰当回答,至少需要做下面几个层次的辨析。 首先,对于当下中国学者来说究竟应该如何处理中国文化学术传统和西方学术的关系是需要辨析的。我们的学术研究,从理论观念、学术术语到论证方式、研究方法,究竟是从何而来的?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难,只要分析一下中国学界通用的书面汉语的构成成分就可以明了。作为现代以来中国学术之呈现方式的书面汉语既不是自古有之,也不是从外面照搬而来,它是清末民初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人创造出来的,是他们对各种因素进行组合重构的结果。它以现实生活中通行口语为基础,融汇了传统文言文因素和外来语因素。因此不能小看现代书面汉语,它是古代与现代、高雅与通俗、中国与西方多种文化传统交融互渗的产物。既负载着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艰巨任务,又承担着实现中国文化现代性的伟大使命。蔡元培、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胡适为代表的一代学人开创的现代书面汉语经过了一个世纪的丰富与完善,最终成为当下中国学者们共同操练的书写方式,我们这代学人对这套现代书面汉语应该礼敬有加,应该大加赞美,更应该爱护与维护,而绝不应该对其价值熟视无睹、妄自菲薄,镇日做“失语”之叹!好像我们不用文言文写作就算不得中国人了似的。现代汉语的多元构成这一特点实际上已经提供了现代中国学术形成独特品格的可能性:较之古代,其有现代因素,较之西方,其有中国因素,较之精英,其有民间因素,这是一种独特的中国现代学术传统,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学人对人类文化所做出的独特贡献。对于这一独特学术传统文明应该自觉维护与传承,应该发扬光大。因此,从现代汉语构成的角度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建立有独特性的中国学术是可能的。 其次,从另一角度看,当今中国学界对世界文化学术的贡献确实是比较小的,与现代汉语所能够释放的能量相比可谓微不足道。即如文学理论这一学术门类来说,20世纪以来的外来理论,俄苏的、欧陆的、英美的,相继占据了中国文学理论言说的主导地位。我们自己的理论或方法,无论是来自古老传统的,还是来自当下文学实践的,都渺无踪迹,丝毫构不成世界性影响,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之一,就世界范围来看,现代学术的评价体系、研究范式、术语系统等等都是从西方文化学术传统中生成的,中国作为“后发现代性”的国家,在学术上融入国际体系时日尚短,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特别是某些学术领域,至今依然没有真正融入国际体系之中。这就使得中国学术不在西方学者视野中,因而根本不被关注。原因之二,作为中国学术主要书写方式的现代汉语虽然包含着来自西方的诸多因素,但毕竟是与英语等西方语言有巨大差异的、有鲜明特性的语言体系,这就使得除了专门的汉学家之外,能阅读汉语文献的西方学者几乎没有。从比例上看,懂英语的中国学者比懂汉语的西方学者不知道要多多少倍。这样一来,由于语言的隔阂,中国学术就很难被西方学界所关注了。原因之三,当下中国学术确实存在问题,我们的学术体制、教育体制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造成学人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少有沉潜于学术之途探赜索隐者。整体来看,论文、著作的数量很多,真正有价值的,特别是具有原创性的学术缺少,学术刊物与出版物中充斥着毫无价值的学术垃圾,这样的“学术”当然不会受到别人的关注了。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如何理解学术的独特性。就学术研究而言基于意识形态或者民族主义(当然民族主义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我们的”、“他们的”之分显然是有问题的。巴赫金作为前苏联的理论家之所以对西方学术产生重大影响,首先就在于他的研究是超越了意识形态与民族主义立场的,是从世界学术史的角度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中国学者心目中似乎都有一个“中国”与“西方”的二元对立模式,好像在“中”与“西”之间横亘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这对于我们学术研究的国际化是极为不利的。所谓学术的独特性不在于确立一套与别人完全不同的言说方式与话语系统,不在于形成自己不同于别人的概念与逻辑体系,而在于为人类学术文化的发展提供新的成果。这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一是研究具有独特性的问题与现象。用国内外学界能够理解的理论资源与方法研究新的问题,从而丰富学术传统。王国维借鉴康德、叔本华等德国美学家的思想和观点,转而研究中国古典诗词的审美特征,标举“境界”之说,这就是学术创新,就是为人类美学和文学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因素。这是借鉴外国理论分析、命名中国传统审美经验的成功尝试。“境界说”的理论资源多来自德国古典美学,但它所指涉的具体内容却是中国传统审美经验,从而构成了一种“非中非西”、“亦中亦西”新型文论形态。可以说,中国现代学术传统大抵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二是形成新的研究方法。一般说来,任何研究方法都是针对具体研究对象和基于必需的理论资源而形成的,因此都只具有有限的适用范围。面对新的研究对象就应该对已有研究方法进行改造,如此便形成新的研究方法。汤用彤先生曾说:“新学术之兴起,虽因于时风环境,然无新眼光新方法,则亦只有支离片段之言论,而不能有组织完备之新学。故学术,新时代之托始,恒依赖新方法之发现。”(《魏晋玄学论稿·言意之辨》)可见新方法之于学术创新的重要价值。在汤用彤先生看来,“言意之辨”实为魏晋玄学所操练之“新方法”,然这一方法并非玄学名士们凭空创造出来,而是对先秦《庄子》、《易传》中相关论述的继承与改造。可以说没有哪种方法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为了证明某种方法的普遍有效性而“改造”研究对象,那就真成了削足适履了,其研究结果也必然毫无学术意义。三是通过具体研究总结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观点与方法。在学术研究中,任何新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都应该是通过具体研究实践总结升华出来,而不应该是凭空想象出来。巴赫金的文学研究方法,所谓“社会学诗学”很大程度上是他通过研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等人的作品总结升华出来的。在这方面中国学者应该大有所为,因为中国文学,从古至今,有大量极具特色的经典作品,文学理论家们理应通过总结中国文学审美经验而产生具有独特性的文学理论观点与文学研究方法。可惜的是,我们用中国文学经典印证西方文学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有余,而生发出自己的理论观点与研究方法严重不足。 中国有着悠久而辉煌的历史文化,长期处于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这自然会养成中国学人的某种优越感与自豪感,然而中国又是后发现代性国家,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我们融入世界发展潮流的时日尚短,在许多方面至今还远远落在发达国家后面,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这种历史与现实的错位状态必然给当下中国学人造成文化心理冲突:自尊与自卑交织。文学理论界的“失语”焦虑正是这种文化心理冲突的显现。如果没有文化上的优越感和自尊意识也就无所谓“失语”,别人的东西比自己的好,全心全意地学就是了,管他说的是谁的话呢!倘若没有文化上的自卑感,也就不必对外来的东西感到压力,为我所用就是,如果真的有强大的自我,是不会失去的。所以说,尽管中国的学术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那种根深蒂固的“失语”焦虑却依然是随处可见、挥之不去的。如何才能走出“失语”焦虑呢?下列几个方面似乎是值得注意的: 首先,以开放心态对待外来学术。面对外来学术中国学界一直存在三种不恰当的态度:一是预设了外国学术高于或优于中国学术的立场,认为凡是外来的理论与方法必然比中国的高明。比较突出的例子是研究中国传统学问的学者常常无视中国学界的研究成果,而对于海外汉学家的研究却津津乐道,即使有些海外汉学家的见解很肤浅、有偏颇。二是盲目抵制,认为凡是借用外来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学术的,都是追新求异,是哗众取宠,一概靠不住。有人甚至认为只要是用现代理论的视角阐释古代学术问题的都是毫无意义。这类人自以为是坚守中国固有的学术传统,但究竟是什么样的传统?汉学的还是宋学的?章句之学还是义理之学?玄学还是实学?其中任何一项都是真正的中国传统学术,遗憾的是,其中任何一项都不见有多少当下学者真正继承了。所以,他们所坚守的所谓“传统”也是靠不住的。三是所谓“鸵鸟战术”,蒙起头来做自己的学问,对外来学术既不推崇,也不拒斥,而是假装其压根儿就不存在。这类学问如果是某类特别专门的考据也还无可厚非,如果也是理解、分析、阐释,那它的学术意义就大可怀疑了。东海西海,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在当今文化全球化,至少是国际化成为大势所趋的语境中,对别人的研究成果视而不见,师心自用,以为老子天下第一,只有自己生有一颗能够思考的大脑,这样的人的学问究竟有几斤几两,不问也知。 以开放的心态对待外来学术就意味着从心里消除彼疆此界的思维方式,在学问上没有什么中外的分野,无新旧、无中外,只有深与浅、对与错、是与非。无论欧陆还是英美,是日本还是印度,是俄国还是韩国,只要有独到之见,我们都兼收并蓄,视为我们共同的学术领域的新成绩。只有秉持这样的心态,我们的学术研究才可能获得世界性影响。 其次,对外来学术要善于“化用”而不是照搬。尽管我们追求开放的心态,力求打破学术研究的“中外”界限,但是国与国之间、地域与地域之间,特别是有着不同文化传统的民族之间,在学术研究上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这就有个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的问题。如何学习外来的理论与方法?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如果以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学界借鉴外来文化学术的历史经验为基础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觉得,“化用”而不是照搬似乎是真正可行之路。任何理论与方法都是面对具体问题或现象而提出的,或者是对某些具体研究实践的归纳与总结,因此都只是具有有限的适用性。对于不同的问题与现象来说,这种理论与方法只是具有启发意义而非直接的指导意义。这就意味着,当我们面对这些外来的理论与方法时首先要考虑的是它们对我们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有哪些启发意义,而不是考虑如何把它们直接运用到我们的研究中去。例如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都有具体的适用性,不能简单照搬使用,但是它们都可以启发我们在研究中国文化现象,例如古代文学思想时,可以关注文人士大夫阶层的交往方式、文学评价机制、文人们建立并活动于其中的文化空间等,把这些现象当做研究文学思想的视角,如此我们就可以发现一系列有价值的学术问题。“化用”之后我们就不必标榜是用了什么什么理论和方法,但实际上是借用了或借鉴了,这样就可以既避免生搬硬套之弊,又无故步自封、无视国际学术发展新成果之嫌。在文学研究领域,除了场域和公共领域之外,诸如陌生化、狂欢化、复调、隐喻、反讽、结构、解构、身份、互文性、性情倾向、情感结构等概念和理论,在用于研究中国文学现象时,一般都应该多“化用”而不宜直接运用。 所谓“化用”最主要的是受这一感念或理论的启发,发现我们研究对象中的一些以前没有发现的问题,并通过解决这些问题而丰富和推进我们的研究。“化用”的结果是形成一种新的思路,是学术研究产生某种突破效应。在我看来,王国维、宗白华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与艺术特征时对于德国古典美学的借鉴就是一种成功的“化用“,丝毫不露痕迹,却突破了传统诗文评的理论视界,二人这方面的研究之所以产生持续不断,甚至历久弥新的影响,不是没有原因的。 第三,“激活”中国传统学术思想资源。我们身后矗立着三千多年学术思想传统,极为丰富灿烂。这些资源对于我们今日的学术研究是不是应该发挥某种作用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然而究竟应该如何利用这些资源呢?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有学者曾主张用传统文论的概念、范畴建构一种“中国式”的文学理论体系,以此解决“失语”问题,在下期期以为不可。那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制造假古董,丝毫无补于事。也有人主张选择若干古代文论的概念、范畴加入到今天的文学理论建设和文学批评实践中,虽然可行,但除了增加一些“中国的”色彩之外,也没有真正实际的意义。对于传统的学术思想资源,我们不能简单“拿来”,必须重新加以“激活”才行。所谓“激活”,最根本之点就是对传统学术思想资源加入一定的现代学术因素,使之发生“脱胎换骨”般的变化,成为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学术话语。显然,这里暗含着“古今融合”的意味。王国维、宗白华的“意境”理论正是现成的范例。“意境”和“境界”等语词中国古已有之,王国维、宗白华汲取德国古典美学家的思想,如叔本华的“直观说”等,对其进行重新解释,从而为这古老的中国诗文评术语注入了现代因素,使之成为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重要学术概念。其他许多中国古代重要的学术语词,诸如体认、涵泳、自得、活法、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吟咏情性、气韵生动等等,都可作如是观。只要阐释得合理,古代学术资源是可以被“激活”的。 注释: ①也见李春青:《略论“意境说”的理论定位问题——兼谈中国文论话语建构的可能路径》,《文学评论》2013年第5期。 ②尼采:《权力意志》,(原编)第481节。 ③Marshall McLuhan,Understanding Media:The Extensions of Man,New York:McGraw-Hill Book Company,1965[1964],p.7. ④Neil Postman,Technology:The Surrender of Culture to Technology,New York:Vantages Books,1993[1992],pp.13-14. ⑤William Blake,The Complete Poetry and Prose of William Blake,ed.by David V.Erdman,Berk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8,pp.177ff.卡彭特将这句话用作他一本著作的名字。 ⑥海森伯:《物理学家的自然观》,吴忠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0页。凡出自该书的引文均核校过其英文底本(Werner Heisenberg,The Physicist's Conception of Nature,trans.by Arnold J.Pomerans,New York:Harcourt,Brace,and Company,1958)。除特殊情况外,改动处不做说明。 ⑦See Ihab Hassen,The Postmodern Turn:Essays in Postmodern Theory and Culture,Columbus,Ohio: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7,pp.55-63. ⑧海森伯:《物理学家的自然观》,第11页。 ⑨海森伯:《物理学家的自然观》,第13-14页。 ⑩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序”第2页。 (11)Hans-Georg Gadamer,Gesammelte Werke,Band 1,Tübingen:J.C.B.Mohr(Paul Siebeck),1986,S.305.请注意:德国人总是在“效果”中理解“真实性”(Wirklichkeit)。 (12)见周锡山:《人间词话汇编汇校汇评》,北岳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13)Hans-Georg Gadamer,Gesammelte Werke,Band 1,S.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