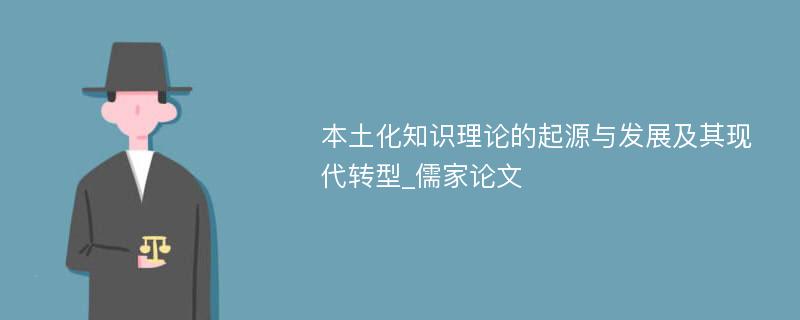
格物致知论的源流及其近代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格物致知论文,源流论文,近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000-0763(2012)01-0094-06
当西方的科学技术传入中国时,我国学者称之为“格致”之学。可见,当时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中的“格致”概念与西方科学技术的概念最为贴近。我国古代所说的“格致”之学究竟是指什么学问?它最终又如何成了西方科学技术的代称?对“格致”概念的源流及其近代转型进行梳理,将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一、格物致知论的起源与道德化的诠释
所谓的“格致”,是“格物”与“致知”两个概念的简称。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这两个概念密切相关,故常常放在一起作为一个概念使用。简略说来,格物致知论就是中国文化与哲学中关于认识世界的方法或方式的理论。仅从字面上进行初步解释:所谓格,即推究之义;所谓致,即求得之义。格物致知即穷究事物原理,从而获得知识。当然,这种解释较倾向于现代认识论与知识论的角度。其实同其它很多中国哲学的概念一样,它还含摄着价值论、工夫论等多方面的内涵。应当说,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国传统概念,把真、善、美融合为一体。古人对这一概念的诠释往往侧重不同,不同时期的不同学者之间也呈现出一定的差异。
格物与致知这对范畴,最早见于《礼记·大学》。《大学》是儒家的一篇重要的著作。它重点阐发了儒家关于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其中有一段说道: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1],pp.3-4)
这一段概括起来即所谓的“三纲领”与“八条目”的儒家修养理论。三纲领是指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它制定的是儒者应该达到的理想境界。八条目是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制定的则是要达到这一理想境界的具体步骤和方法。“格物”与“致知”是八条目之中的前两个步骤,可以看出,格物与致知是修身的基础,也正是因为它们的这种基础性地位,故被视为“儒者第一要义”,逐渐成了儒学的核心概念。当然,关于格物与致知的准确含义,《大学》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以后的思想家们纷纷尝试为其注解,并各执一说,居然成了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大公案!明末刘宗周就说:“格物之说,古今聚讼有七十二家!”([2],p.771)
最早对格物和致知进行解释的是汉代经学家郑玄,他说:
“知,谓知善恶吉凶所终始也。格,来也;物,犹事也。其知于善深,则来善物;其知于恶深,则来恶物。言事缘人所好来也。”[3]
在郑玄看来,所谓的“知”,是指善恶吉凶所起始与所终结的知识,这显然与现代哲学中把知识只看作是关于世界的客观知识的观点是不同的。在汉代,主要的哲学意识形态是天人感应论,其实,郑玄解格物致知所本的也正是这一理论。郑氏认为,你对善与吉的知识深切不疑者,则“来到”或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也必定是善和吉的;若你对恶与凶的知识念念不移者,则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也必定是恶与凶的事情。人对善恶吉凶的信仰与偏好将决定发生于他身上事情的好坏(言事缘人所好来也),即道德信仰将决定人的生活样态。这不正是典型的“天人感应”式的理论诠释吗?!但从逻辑顺序来看,郑氏所解的更像是“致知格物”论,即你信仰什么样的知识,就应验什么样的事情。
唐代孔颖达基本沿袭郑玄的观点解释格物致知:
“致知在格物者,言若能学习招致所知。格,来也……缘人所好也。物格而后知至者,物既来则知其善恶所至。善事来则知其至于善,若恶事来则知其至于恶,既能知至则行善不行恶也。”[4]
本段释义前半部分基本就是对郑注的详细发挥,不过在后半部分孔颖达又把道理倒过来说了一遍,大概是有意在对郑注做补充。他说,事情到来了知也就至了,因为事情之善恶吉凶也就明了了。人既然善事来则知善,恶事来则知恶,故人知行善而不行恶也。孔颖达此部分的解读顺序才是“格物致知”顺序,也表明了格物与致知并非必定是由此及彼的单向逻辑,是相互可逆的。
而唐儒李翱对格物致知的理解则与郑玄和孔颖达有较大不同,他说:
“物者,万物也。格者,来也,至也。物至之时,其心昭昭然,明辨焉而不应于物者,是致知也,是知之至也。知至故意诚,意诚故心正,心正故身修,身修而家齐,家齐而国理,国理而天下平,此所以能参天下者也。”[5]
李翱训物为“万物”,格亦是“来”或“至”。他认为,物呈现于眼前时,人心便昭昭然明晓此物,此谓之格物。但是,心虽能明辨万物,却不应于物,不为外物所牵,此谓之致知。可见,致知并非只是对万物知识的简单把握,还是认识主体(人心)对万物明晓后的一种心理把持。他认为这才是掌握知识的最高境界(是知之至也)。因此,按照这种逻辑,李翱就顺理成章地推理出“知至故意诚,意诚故心正”等其它条目来,而意诚与心正等也即是李翱所说的“复性”。可见,在李翱看来,格物不只是认识客观事物的方法与手段,重要的是对本性的恢复。这就解决了格物致知何以能够与意诚心正联系在一起的问题,保证了前两个条目向后面条目推演的逻辑严密性。李翱这种格物致知可使人意诚心正的观点,启发了宋代的儒学家们,从而开启了宋明理学从心性修养角度来解释格物致知的先河。
总体看来,唐代及以前的时期,先哲对格物致知基本是单纯作为道德修养理论对待的。郑玄直接把“知”定义为关于善恶吉凶的知识,格致之事到了神奇而应验的程度,这几乎如宗教般“强迫”人们去进行道德修养实践。李翱虽然不似汉儒做得如此玄乎,但其论证格物致知乃是复归本性的修养方法,所关注的也无非道德修养这一事。《大学》中虽然没有对其内涵做准确解释,但把它作为修身的根本是毋庸置疑的,另外,“八条目”的终极追求还是为了达到“三纲领”。因此,可以说,此前形成的关于格物的知识不过都是“明明德”的知识。所以,唐代之前思想家大多只训格物致知为修养的工夫应当是比较接近其原义的,格物的目的并非只是要格尽具体的形下之物,而是为了“尽人性”,进而获得诚明之知,而能意诚心正也,格物致知即是在行事接物上求至善之知而入正道也。应该可以说,这一时期,格致说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关系不会太大。
二、格物致知论的心学与理学的诠释之争
在宋代,二程沿袭李翱等先驱开启的理论路线,注重心性(主体)在认识与修养问题上的研究。但是,由于二人的理论倾向不同,由此也开创了宋明理学的两条不同理论路向。他们对格物致知的诠释也各具心学与理学的特征。相对而言,程颢的格致说,更具心学特征,他说:
“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当处便认取,更不可外求。”([6],p.15)
“‘致知在格物’,物来则知起,物各付物,不役其知,则意诚不动。意诚自定,则心正,始学之事也。”([6],p.84)
程颢认为,一切知识尽在心中,知识之获得,只向心上求索即可,不必向外找寻。物来时心中固有之知自然应起,不必将迎,然后,识得此物之后也不必我心之知役系其上,物归于物,心归于心,如此,我之意志方可诚静不动(此处应该是继承了李翱的“明辨焉而不应于物者”的理论)。意诚自定,则心必然得正,因此,格物之工夫乃是人的初学之事也。
而程颐的格致说则是理学的特点。他认为,格物即穷致事物之理,穷理自然就能致知。他说:
“凡一物上有一理,须是穷致其理。”([6],p.188)
“格犹穷也,物犹理也,若曰穷理云尔。穷理然后足以致知,不穷则不能致也。”([6],p.1197)
程颐训“格”为“穷”,训“物”为“理”,格物即是穷理。穷理的工夫做足了,知也就至了。如果说程颢的格致论是只从心中找寻的话,程颐则认为先通过在外物上穷尽其理,再复归本心。虽然,要先从外物上穷理,但是,程颐也是认为此理先在地存在于自己的心中的。他说:“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则不能得之,而致之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6],p.316)即知识为我心中所固有,但如不做格物的工夫亦不可得之,因此说致知在于格物。
程颐的格致说被南宋时期的朱熹继承,并且进行了深入的发挥: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1],pp.5-6)
朱熹认为,之所以说致知在格物,是因为欲致我之知,必须通过即外物而穷理方可。这是因为,虚灵不昧之人心本来就有知的,同时天下万物也各具其理。只要外在之物理没有穷尽,心中之知也无法全部被“唤醒”。故此,《大学》所教,是要使学者先格尽天下之物,其实格物所穷之理亦不过是其已知之理,只不过是力求心外之理与心中之知完全相合而已。如此,格物之功用力日久,到某一刻必能豁然开朗,内外贯通,此时再看众物,其表里精粗则一览无余也。而我心中本具之知也就得到了印证,本心具有众理的全体也得以彰明与显扬。则自己便可以应万事之大用,能举一反三,一通百通,则世间无论大小之事没有不明白的。这就是物格即是知之至也的大义矣。由朱熹的阐释看来,他基本上承袭的是程颐格物即穷理的基本观点,不过发挥的更加精致一些而已。但总体看来,向外物穷理的工夫是程朱理学派所强调的重点。
而由程颢开启的心学路线后至陆九渊正式确立,陆九渊也强调“心即理也”和“心外无理”,格致的工夫也是要在心上求索。心学派至王阳明时乃集大成,王阳明把心学派的理论发挥到了极致。在格致论问题上,王阳明则反对朱熹的理论。他说:
“所谓格物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7],p.45)
在王阳明看来,所谓格物致知,就是把自己内心的良知“发挥”到事事物物上去。我心具有之良知即是所谓的天理,致我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事事物物才获得各自存在之理。所谓的致知,就是把我心之良知发挥到事事物物上去。所谓的格物,即是事事物物都得到了各自之理,格物致知就是合心与理为一的过程。王阳明批评朱子的观点道:“朱子所谓格物云者,在即物而穷其理也。即物穷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谓定理者也。是以吾心而求理于事事物物之中,析心与理而为二矣。”([7],pp.44-45)也就是说,他认为朱子是在事事物物上寻求天理,这样心与理即为二端,是“析心与理而为二”的做法。既然,万事万物的理都是由“我心”赋予,那么,“我心”是否端正成为天理是否昭明的关键,故王阳明训“格”为“正”,说:“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7],p.972)这样,正其不正就是“去恶”,归于正者,即是“为善”,格物就成了为善去恶的自我修养活动。
从上述论证可以看出,程颢下启陆九渊至王阳明为心学一系,程颐与朱熹为理学一系,两派理论特点鲜明。从整体上来说,心学派对格致论的诠释基本上沿袭了早期道德化诠释的方向。程颢认为知识之获得只须在心上求索即可,心不随外物迁迷,自然可以诚静不动。王阳明训“格物”即为“正心”,是去恶存善的工夫。可见,心学派格致论于外物求真的意味极为淡薄,而求心为善为正的倾向成为终极关怀的事情。这与早期论证格致不过是求“明明德”的理论取向是基本一致的。而理学派则强调格致是在外物上穷尽事物之理,进而获得众理之全体的“最高知识”。这种重视客观、富有理性精神的理论路线,显然与自早期以来一直到宋代心学派所坚持的重视主观(心)、强调德性精神的诠释路线不同,因此,有学者就批评程朱理学派是“别子为宗”,并未继承起古代先哲们的理论路线。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牟宗三先生说道:“北宋自伊川开始转向不与濂溪、横渠、明道为一组,朱子严格遵守之,此为伊川、朱子系。伊川是《礼记》所谓‘别子’,朱子是继别子为宗者。”([8],p.47)即牟先生认为自程颐开始,其理论的转向就与周敦颐、张载、程颢等人不一致了,程颐不继承传统即所谓“别子”(非嫡传也),而朱熹又继承程颐的系统而为其宗,也偏离了儒家的传统。而牟先生认为象山(陆九渊)、阳明才是“宋明儒之大宗,亦是先秦儒家之正宗也。”([8],p.47)因为,程朱理学所说的理,“于道德实践(成德之教)根本为歧出,为转向;就其所隐涵之对于经验知识之重视言,此处之‘致知’即可视为道德实践之补充与助缘。”([8],p.44)即程朱理学所说的理的知识,由于隐含着对客观经验知识的重视,因此他们通过格物致知获得的知识只能视为道德实践的补充而已。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即便理学派格致论没有获得儒家所谓正统的延续的肯定,可是他们对于传统格致论的内涵有所拓展却是无疑的,这种拓展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意义重大。因为,科学知识最重要的特质就是向事物求索的理性精神,而在之前的中国传统的知识论体系中,基本都是关于道德的知识,理性的知识一直没有获得独立的地位,程朱理学在格致论上重视客观与强调理性精神无疑给理性知识以一席之地。因此,宋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当时达到了世界科学中心的高度,与程朱理学在格致论上提供的思想方法不无关系。李约瑟在其名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曾论证过宋代理学对成就当时自然科学的“黄金时代”的作用,他说:“宋代理学本质是科学性的,伴随而来的是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本身的各种活动的史无前例的繁盛。”([9],p.527)还有学者说道:“自然物理知识虽然处于儒家知识体系的边缘,但也构成了儒家话语的一部分……到了宋元时期,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到高峰,与程朱发挥格物致知的思想有很大关系。”([10],p.9)宋明时期的科学家把格致之学应用于各个学科,强调对外物的仔细探究,这已经带有了较为浓郁的近代实证主义精神。葛荣晋先生也认为:“程朱学派的格物说所蕴含的科学理性精神,不但是宋明古典科学发展的理论基础,而且也是明清古典科学与西方近代科学的衔接点,是中国古典科学走向近代化的重要突破口。”([11],p.88)确实,进入明清之后,中国科学发展的近代化倾向更加明显了。
三、实证化的理论取向与格物致知论的转向
到明清之际,由于理学逐渐走向僵化,而心学由于过于注重心(主体)的能动作用,容易导致主观自大,王门后学也逐渐流入狂禅的弊病之中。再加上受“天崩地解”的时代的刺激,以反对程朱陆王道学(包括理学与心学两派)空谈性理学风的实证化思潮兴起了。这股思潮认为道学空疏不实,故提倡“力行致知”、“经世致用”等重视实用和实践新学风。明清时期的思想家们对格物致知的诠释赋予了更多的时代特征,格致论发生着重大的理论转向,实证化取向日益突出。
明末清初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方以智,他的格致之学与宋明理学注重心性修养的理论特征已有明显的不同,他更加注重对客观物理世界的探究,具有浓郁的实证化特征和西方科学精神的意蕴。首先,他认为前人在“物理时制”方面比较欠缺:“汉儒解经,类多臆说;宋儒惟守宰理,至于考索物理时制,不达其实,半依前人。”[12]方以智把知识分为三类:质测、宰理和通几。他所谓的质测,即相当于实证自然科学的学问。方以智认为,“格物”之学即是他所说的探究外在“物理”世界的“质测之学”,而且,这种质测之学具有基础性的作用。他说,“舍物则理无所得,又何格哉!”[13]方以智的“质测之学”有别于传统学者的研究取向,可以说,他第一次把具有近代意义上的科学从传统格物说中独立出来。这标志着明末清初的中国学者已经开始对传统格致论的内涵与功能进行反思,对格致论进行符合时代要求的重构。这种反思和重构为中国古代科学向近代科学转型,提供了理论基础。
与方以智基本是同时代的思想家王夫之,也指责王阳明后学“废实学,崇空疏”。他对格致论的解释上也具有了一定的实证精神和近代哲学与科学的意蕴。他说:
“夫知之方有二,二者相济也,而抑各有所从。博取之象数,远征之古今,以求尽乎理,所谓格物也。虚以生其明,思以穷其隐,所谓致知也。”([14],p.312)
王夫之认为,获得知识的方式有两种,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其一即格物,它的方式是,在空间上博取万物之现象与数理,在时间上征验事理于古今,以在时空全部维度上求尽事物之理;其二即致知,它的方式是,虚静以生显明之神智,从而可以深思以穷尽事理之隐微。二者是认识的不同层次,不同阶段,它们又是联系的,一体的。这颇有些像现代哲学中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二阶段论,感性认识广泛地搜集资料,并进行一定的整理与加工,而理性认识则通过分析、推理、判断等抽象的思维方式对事物进行更高一层的认识。而感性与理性的二阶认识法无疑是近代科学最为重要的认识方法论之一。因此,王夫之的格致说为中国理解与接纳西方的科学技术理论做了进一步的铺垫。
由上述可知,以方以智和王夫之为代表的思想家的格致说,在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到清代时,对格物致知的解释更加趋向实证化,黄宗羲批评道学“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他解“致良知”之“致”为“行”:“致字即行字,以救空空穷理”;([15],p.178)颜元则训“格”为“手格杀之格”,([16],p.491)更加强调“习行”(动手实践);对程朱理学颇具批判精神的戴震训“理”为“在物之质”的“分理”,一反朱熹形上意义的“天理”,格物的过程则是带有科学意义的“察分理”。([17],p.1)于是,格致论变成了强调“经世致用”的“实学”学问。这与宋儒强调格致为心性穷理的理论显然是背道而驰的。但这无疑有助于去除之前格致说“厚重”的道德教化的包袱,使其更加靠近西方科学的理论特质,为中国近代科学与西方科学接轨铺设了一个桥梁。
西方科学思想最早的输送者主要是西方的传教士。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带来的科学理念,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中国学人的思维方式,最初借用“格致论”来谈论科学技术理论的可能正是利玛窦。他在《几何原本序》中说道:“夫儒者之学,亟致其知,致其知当由明达物理耳……吾西陬国虽褊小,而其庠校所业,格物穷理之法,视诸列邦为独备焉”。[18]《几何原本》的译者徐光启也开始采用此说法。在饱受西方列强欺凌的近代中国,不少学者为救亡图存,开始更加主动地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干脆直接以“格致学”来称谓西方的自然科学,并把自然科学家称为“格致家”。如严复提出:“救亡之道……又非明西学格致必不可。”([19],p.48)就直接以“格致”代称西方的自然科学。洋务派在上海、广州等地开设教授西方科学知识的学校即称其为“格致书院”。至此,格致几乎成为近代科学的代名词,其中的道德形上意义也被消解殆尽了。“十九世纪中期,随着国门的重新打开,经过经典化的西方科学技术传入我国,格物致知便渐渐演化为‘格致’学,而其中的道德形上学意义最终被消解。”([20],p.193)
四、格物致知论与西方科技理论的比较及其现代意义
从对格致论历史考察来看,在明清时期,格致论所具有的道德形上意义才逐渐被消解的,而正是消解了道德形上意义的格致论才能够与西方的科技理论进行对接。如果要把中国传统的格致论与西方的科技理论进行比较研究的话,显然,在近代,二者的内涵是基本对应的,当时的中国学者也基本是直接拿“格致学”来指称西方的科学技术理论。究竟,中国的格物致知的概念与西方科学技术的概念存在着哪些同异呢?近代洋务派的科学家徐寿说:“中国之所谓格致,所以诚正治平也;外国之所谓格致,所以变化制造也。中国之格致功近于虚,虚则常伪;外国之格致功征诸实,实则皆真也。”[21]说中国的格致之学重道德教化,近虚;西方重变化制造,则近实。这种区分还算中允,但说中国格致之学虚则伪,似有贬低之义,不过作为那个时代的科学家,救亡之心切,也可理解了。钱穆先生说:“西方人求通于物,中国人求通于心。”他认为大学的八条目,首先说格物与致知,而致知又首贵明德。“儒家知识从德性起。德性中即有情感”。知识从德性中来,故知识是德性的知识,知识之生成,最终还是为了完成其德性。而西方“不言修身”,“皆重向外发展”。([22],pp.509-514)应该说,近代科学在西方兴起,进而发展为现代科学体系,也非偶然,中西方所侧重不同而已。中国重道德心性,西方重变化制造;中国重向内修身,西方重对外发展。
细察中国先哲们对格致论的解释所表现出的共性,我们不难发现,对德性的重视是其共同特点。关于“道问学”与“尊德性”的关系问题也是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话题,古代学者基本倾向于尊德性为主,道问学为辅,人人可通过道问学而至尊德性,尊德性处于神圣、崇高且不可动摇的位置。而科技之学至多算是道问学之中的一小部分,古代学者自然不会把它放置到最高的地位上去。自北宋兴起的“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分辨也属此类问题,宋儒多注重德性之知的获得而轻见闻之知,“见闻所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23],p.24)见闻之知是与物交接而产生的知识,不是德性之知,德性之知不产生于见闻之知。可见,他们对见闻之知不但有贬低之义,甚至还否定了它成为德性之知的可能性。这种如此注重德性的知识传统,与西方的知识传统是不同的。西方的知识是客观知识,所谓的“客观”,自然是要求主观的因素越少越好,极端客观的知识即所谓的真理。而在近代,西方认为最具真理性的知识是科学的知识,因为科学的知识是依靠于实验得来的,实验的最大特点就是客观性。即使在科技高度发达的宋代,格致论也没有发展出近代西方科学意义上的实验方法。即便在学习西方科学的热情高涨的近代,中国的学人们虽然在努力消除格致论中的道德意义,也肯定无法彻底根除心中对于科学活动的道德关怀。
历史表明,中国传统的格致说内涵之中虽然不缺乏西方科学最重要的品质——求真精神,但由于它始终没有像西方那样如此强烈地执着于求真精神,故而近代科学没产生于中国也就不足为怪了。唐君毅先生说:“然由清末凭格物之一名,以引入西方科学之新知,使科学渐成为独立知识之领域,虽为中国文化之发展,不得不有之一端;然依中国文化之传统,又素以德性之知为本。”([24],p.216)从这个意义讲,所谓的“李约瑟难题”(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于中国)也并非一个难解的谜题,各自侧重不同而已。当然,这也并非要为近代中国进行辩护,世界文明史已经表明,各民族的发展需要取长补短、互通有无,止到今天,现代中国仍没有放慢自己向西方科技学习的步伐。因此,一方面,我们要继续学习西方“求实求真”的科学精神;另一方面,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也不能完全摒弃自己传统思想中的一些优秀的观念,比如,格致论中的道德形上意义在新的时代似乎又将重获用武之地。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单纯求真的科技确实为人类带来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但也带来了以道德问题为主的诸多问题。为此,他们呼吁要“科技返魅”,这不就是要补现代科技缺少善与美的问题吗?因此,对中国传统的格物致知学说的历史考察具有强烈的现代意义。由上面论述可知,一方面,对于中国科技的发展我们将获得一种新的认识,中国传统的格致说一直为其提供着理论支撑;另一方面,格致说丰富而思辨的理论成果,或许可以为现代科技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提供一些借鉴作用。
[收稿日期]2008年4月2日;修回:2011年11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