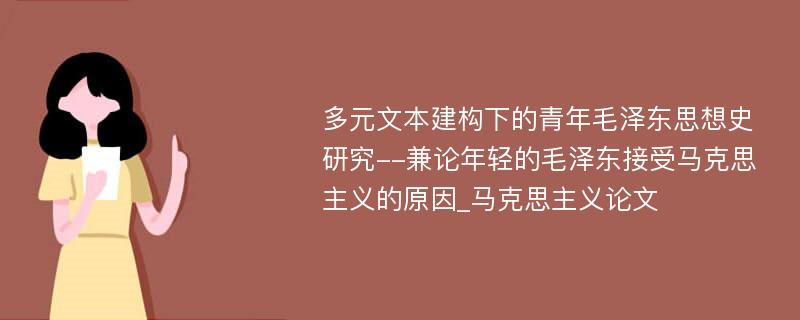
多重文本构筑下的青年毛泽东思想史研究——兼论青年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青年论文,毛泽东思想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史研究论文,文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3)01-0006-05
一、思想史潜蕴的历史文本
青年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是青年毛泽东思想史的主要线索之一。揭示青年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原因,就是循着这条线索对青年毛泽东思想史进行文本重构。思想史是思想文本的现实构筑。任何思想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也总是在一定的历史场域中演进,这些表征历史条件和建构历史场域的事件构成了思想史潜蕴的历史文本。只有通过对历史文本的深掘,才能澄清思想文本的建基所在,才能呈现思想史的基底。
青年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文本,就是围绕青年毛泽东发生的历史事件,也即其所处的政治环境、思想环境和国际环境。环境既包括历史问题的提出与回应,也包括物质条件和思想材料的具备与整合。历史问题的提出与回应以及当时物质条件和思想材料构成了历史文本的内容。青年毛泽东所处的政治环境,既呈现了亡国灭种的危机,也提出了救亡图存的革命任务;思想环境既表明了空虚迷信的国民精神危机,也指明了启蒙民智的未来路向;国际环境既凸显了中国落后于世界发展的危险,也打开了中国学习先进思想和实践的窗口。而政治环境、思想环境和国际环境则同时提供了可资利用的物质条件和思想材料。
政治环境被表达为由一系列政治关系和政治事件所构成的政治话语。政治话语总是寻求表达的路径。并显示为差异性政治活动。政治话语是错综复杂的,所以从差异性政治话语出发,就可以发现差异性政治活动的线索。革命话语也是一种政治话语,革命活动就是政治话语表达。青年毛泽东的时代是辛亥革命失败、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时代。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辛亥革命之后,中国仍然处于新旧时代的断裂期。这种断裂保留着过去和未来之间的张力,既使得帝国主义和封建因素依然顽固,又使得新的民主自由的时代喷薄欲出。被推翻的只是已经沦为封建时代符号的清王朝,而以封建军阀和地主为首的封建残余势力却依然顽固地盘踞在各个区域。被更换的只是帝国主义的代言人,而帝国主义势力依然有增无减。但是,封建主义因其落后于时代进程而产生了时间滞后;帝国主义因其异质文化而产生了空间裂隙,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境遇下,封建主义为消弭其时间滞后,帝国主义为弥补自身的空间裂隙,两者勾结起来,产生了异质文化和落后时代的混合物——官僚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等。官僚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表征了身份的混杂、时代的断裂和文化的交融。他们既有封建权力,又有大量产业;既是旧时代的达官贵人,又是新时代的资产者;既保留严重的封建传统文化特征,又渴望新的资产阶级文化生活。所以,他们是断裂时代的承载者,是中国古代社会和近现代社会之间的断裂本身。半殖民地半封建语境下的革命话语就是对这种断裂的一种回应,试图弥补新旧时代语境的断裂。作为必然表达方式的革命活动本身,天然地孕育在这种时代断裂的内部,时刻等待着最强有力的唤醒。
思想环境是围绕主体产生的时代思想氛围。根据不同的线索,可以把思想环境划分为不同的范畴。在革命的政治话语之下,思想环境必然被划分为表征新旧时代断裂乃至对立的不同范畴及其关系,即传统文化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反叛。青年毛泽东所处时代的思想状况就呈现为落后与先进相互对立的革命话语的范畴:一方面是封建、殖民地特征的客观思想条件;一方面是新兴的资产阶级的科学、民主、自由思想的传播。这两者是时代断裂在公共思想层面的展现。时代思想一般以公共理性的方式存在,所以一定的时代思想就是一定时代的公共理性。而公众作为代表社会的显性共同体,则总是对应着一般以隐性的方式潜藏于时代语境之中的反公众。反公众一般表现为革命者和启蒙者,而公众则一般表现为旧时代的顽固守护者。因此长期以来,公众都是处于被启蒙的地位。在这种意义上,梁启超将“启蒙民智”作为当时知识分子的任务。青年毛泽东所处的时代,毒害民智的主要是迷信、空虚、自大和根深蒂固的奴性意识。这些思想都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必然形成的意识形态。半封建体制为维护皇权崩溃之后的仍未分崩离析的封建势力,借助宿命论的强大传统力量论证自身的合法性。为泯灭民间的反抗动机,封建势力用传统文化中最为保守和虚无的力量,使得民众的反抗神经成为空场。帝国主义为维持半殖民地制度,也要用经济占领、政治控制、军事恐吓和文化输出的方法,取消民众的“排异反应”——即反侵略意识。在这一点上,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达成了一致。
但同时,反公众的态度却永远存在于公众意见之中。作为对时代断裂的积极反应,反公众意识往往充当觉醒者的角色,是革命话语的代言人。革命时期,反公众就会由隐性转为显性。在中国,这群角色的扮演者就是五四时期的新兴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不止传播资产阶级科学、民主、自由的思想,而其也传播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南陈北李”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人物。青年毛泽东在五四时期深受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影响。陈独秀是促使他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关键人物。毛泽东回忆说,“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1]107再者,五四运动时期涌现的大量的新思想为毛泽东提供了可资比较和选择的材料,除马克思主义之外,包括无政府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实用主义等等,使他掌握了时代的话语权。五四运动为青年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文化氛围和土壤,准备了思想条件。
十月革命给中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最为重要的就是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界的变化是现实运动的反映,反过来也影响现实运动的发展。思想文化的觉醒为革命培养了新的力量,而新的革命作为历史趋势已经不可抑止了。十月革命是时代的革命话语和反映时代断裂的哲学的结合体。革命的活动必然内含伟大的时代革命意义,在传向中国的时候,把时代的伟大革命意义也一并带了过来。第一位公开宣传十月革命的人是李大钊。李大钊认为布尔什维主义必定在世界范围内获得胜利,主张全国上下翘首以待十月革命所带来的新文明的曙光,接受马克思主义,顺应历史潮流。十月革命之所以能够带给中国如此巨大的影响,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面临时代断裂的不仅是中国,还有俄国等许多国家。共同的时代境遇,使得不同国家分享了共同的政治话语。地理上的毗邻使得十月革命能够很快引起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注意。再者,近代中俄两国相似的内外交困的历史,使得两国的历史传统具有家族相似性。因此,俄国容易被中国的知识分子拿来比较。十月革命之后的俄国不仅推翻资产阶级专制,建立工农联合专政,而且抵御住了敌对势力的围剿,使俄国完全摆脱了内外交困的局面,这给处在相似困境中的中国带来了一线希望。最后,俄国与中国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清朝末期,俄国侵占了东北的大片领土,与中国签订了一次又一次的不平等条约。苏维埃政府建立之后,列宁主张废除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这使得中国人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有着不一样的好感,因此也更容易受其感染。
历史环境所构筑的历史文本,是勾画思想史的底板。但是历史文本并不直接是思想史,因为思想史需要一个内核,一个本体,使得思想史围绕这个内核构筑和呈现为一个有机的总体。这个思想本体,就是青年毛泽东的哲学思想。
二、寄寓于哲学的思想本体
任何思想的发展都是围绕一定的基本思想进行的锻造和雕琢,这种基本思想就可以称为某一思想文本的思想本体。虽然两者都是思想,但作为思想本体的基本内容却决定了思想文本的结构、特征和趋势,而且也是后来思想发展的基础。这种思想本体往往由一个人的基本观念体系所构成,代表了一个人基本的性格特征和价值取向。思想本体实质上是个人的文化心理特征,主要以个人的哲学思想为表征。青年毛泽东也不例外。他的哲学思想构成了他后来思想建构的基质,决定了他后来思想发展的结构和特征。
总起来说,青年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主要是实践哲学。简单来说,实践哲学是主要围绕实践为核心进行探讨的哲学。他将身心关系和知行关系的哲学思想与“立志”和“树立主义”结合起来,由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转向追寻社会的改造。
身心关系是青年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的重要范畴。他结合了19世纪德国哲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把西方的伦理学思想和中国传统的身心观交织构造了起来,提出了自己的身心观。他提出,“筋骨者,吾人之身;知识,感情,意志者,吾人之心”。[2]72在青年毛泽东看来,身心完善就是自我完善;自我完善是改造社会的必要条件。完善身体就需要体育,完善心灵则需要学习知识和修养道德。青年毛泽东以心物关系的本体论哲学说明了“身”是“心”的根本。他说:“一人生死之言,本精神不灭、物质不灭为基础(精神物质非绝对相离之二物,其实即一物也,二者乃共存者也)。”[2]199其中,精神和物质并非完全相离,而是“一物”,故有一元论倾向;然而“二者共存”,又有二元论特征。精神与物质的关系在心智哲学中反应为身心关系,因此青年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有“身心二元论”的特点。身体是知识、道德、感情、意志的载体,“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2]67。但是,身心又要并完,既要“文明其精神”,又要“野蛮其体魄”[2]70。
知行关系是青年毛泽东实践哲学的核心范畴。实践哲学原本探讨的就是道德行为和政治活动的哲学原理,并进而扩展到关于一切实践活动的哲学原理,研究“知”与“行”关系。对青年毛泽东来说,就是研究思想如何能够变为实践,影响现实。在他看来,首先,“行”是“知”的根本归宿,有“知”就有“行”的义务。他说:“凡吾思想所及者,吾皆有实行之义务,即凡吾所知者,吾皆有行之义务”[2]235。而道德知识的目的,也在于道德实践:“伦理学之正鹄在实践,非在讲求。……伦理学示人生之正鹄所在,有裨于躬行”[2]133。其次,“知”又是“行”的前提。他提出“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2]67,意志是人生事业的先决条件。另外,“知”也是“行”的原因。他说:“外部之事,结果之事也……内部之事,原因之事也”[2]65。因此,受梁启超“新民说”的影响,他认为改造社会就必先要变革人心、启蒙民智[3]38,以对公共意识的改造达到对社会的改造的目的。因此,他认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如此大一挥,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噎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2]86知行关系一直是毛泽东的实践哲学的重要范畴。后来他在革命实践中对知行关系进一步思考,结合了马克思主义写下了光辉的哲学著作《实践论——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
“立志”也属于青年毛泽东的实践哲学的重要范畴。“立志”并非青年毛泽东的独创,而是与他的老师杨昌济的思想交织的产物。“杨昌济是一位融通中外,学贯古今的学者,也是一位爱国心切,道德高尚,思想进步,诲人不倦的教育家。”[3]80他的思想融合了中国传统的修身、治国理想和西方现代的独立、现实精神,为青年毛泽东与时代话语的结合提供了条件。通过他,青年毛泽东才能在中西融合的语境中重构出传统理想与现代文化的混合物。他打开了一扇青年毛泽东与西方文化交流的窗户。由于现代化运动主要从西方社会发起,因此,现代性话语权实际上把握在西方文化手中。如果不能把握现代性的话语权,青年毛泽东就很难把握时代的政治话语,更不要说革命话语了。杨昌济将“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3]80奉为圭臬,主张广泛地教化青年,作为国家的栋梁。毛泽东在回忆杨昌济时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教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着强烈的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1]98在他的鼓励下,毛泽东立志改造社会,希望成为“奇杰”,以达“庶几震竦天下之耳目,而扫绝风霾腥秽之气”的目的[2]51。
在关于知行关系的实践哲学所构筑的思想领域内,“知”始终是“行”的根源,“知”得真切才能“行”得有效。而对于青年毛泽东来说,“立志”就是寻求行动的根本方向,因为“心之所之谓之志”[2]589。所以,只有真“知”才能树立真“志”。否则,“只可谓有求善之倾向,或求真求美之倾向,不过一种之冲动耳,非真正之志也。”[2]87所以,毛泽东说:“志者,吾有见夫宇宙之真理,照此以定吾心之所至之谓也。”[2]86认识与真理的关系问题是认识论的根本问题,而认识论又是近代哲学的核心问题。所以,“立志”思想也是毛泽东与近代哲学的交汇点。对青年毛泽东来说,真理就是“大本大源”。他说:“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2]85这是典型的“知本体”特征的哲学思想,即真正的知识——真理——就是宇宙的根源,是宇宙的一体性的基础。融合中国传统的“道”居留于人心,是人心和万物的根源的思想,毛泽东又把宇宙真理转化为公共理性的本质。
青年毛泽东将公共理性作为改造社会的根本力量。他寄希望于改造公共意识,进而鼓动民众运动,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因此,他认为必须要大举改造社会的伦理学、哲学,以摧毁旧的公共语境,构建新的公共语境。只有在新的公共语境中,革命话语才是可能的。青年毛泽东将改造社会的根本目标称为“主义”。他说:“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2]544“主义”就是在公共理性中构筑的社会蓝图,是革命话语的想象表征。“主义”标志着青年毛泽东走出了个体意识的樊笼,进入了公共意识的舞台,是他掌握时代革命话语的重要步骤。“立志”和树立“主义”的本质都在于“大本大源”,这是前者得以升华为后者的根本依据。但是,无论是志向,还是“主义”,都还只是思想文本的本体,并未生长扩充为思想文本本身;二者还都未在历史文本上铺陈,还未被编织到历史网络当中去。而这必须要在思想与现实的交汇即实践中才能实现。
三、思想与实践的交互验证
如果将历史事件看作思想史的历史文本,那么历史文本与思想文本的交融就要通过思想与现实的交汇,而思想与现实就交汇于实践中。通过实践,思想本体只有被编织入历史文本才能融合、生长成思想文本,思想文本的重叠与联结才能构成思想史。思想与现实的交汇,是通过思想与实践的交互验证而实现的。思想与实践的交互验证,就是不断地规范实践的目标、方式和路径以达到思想的预期,但又不断地修正思想以剔除思想预期中与现实不相符合和不能实现的部分。因此,通过思想与实践的交互验证,思想文本就不再是原来的文本,而是将史实潜植在自身的根基处的文本;实践也不再与思想处于相分离的状态,而达到与思想的直接合一。也只有在这个阶段,思想史才达到了自身的完满状态。发展到这个阶段的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才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融会。
不惟物质性的行动是实践,围绕实践具体过程展开的思考,也是实践的一种方式,包括对行动的目标、途径、方式的选择。不惟围绕自己实践展开的思考属于实践,对别人的实践展开的思考,如学习经验和教训,也属于实践。青年毛泽东首先就在解决中国问题的目标选择上,展开了实践探索。他认为,“今日变法,具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破碎,幸则与本源略近,不幸则背道而驰。”[2]85相较之下,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应主张大规模改造。”[4]1因此,“社会的腐朽,民族的颓败,非有绝大的努力,给他个连根拔起,不足言摧陷廓清。”[2]486中国问题的解决必须要动摇旧社会的根本。在青年毛泽东看来,必须要发动所有民众的力量来实现这种变革。而之所以要依靠民众,是因为社会的“大本大源”具于民众心中,是公共理性的本质。因此,“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2]85,而“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2]85因此,“今吾以大本大原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2]85青年毛泽东专门以“民众的大联合”为主题写了三篇文章,来论述民众革命的道路。他提倡平民联合,反对强权者联合,以小联合为基础组成大联合,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民众大联合,而“民众的大联合”是改造社会的“根本的一个方法”[2]388。这种思想成为后来的“群众路线”的思想渊源。
通过真理来把握公共意识,启蒙公共理性使之成为革命力量,青年毛泽东的这种思想与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一段话有着惊人的一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上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上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5]9两者都表达了真理的公共理性本质,追寻真理就是公共理性的天然趋向的思想。而公众一旦掌握了真理,就会自觉地充当实现真理的工具。因为真理就包含着真实的、完善的、合理的社会图景,只有实现了的真理才是真理的全体。而真理必须拥有全体的形式才是纯粹的真理。对青年毛泽东和马克思来说,完善、合理的社会图景就是社会革命的目标。两位伟人这种思想上的默契是青年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潜在契机。
“主义”是一种话语体系,以对社会根本特征、根本问题的判断以及改造社会的根本办法的制定为内容。只有对社会的根本特征、根本问题判断准确,制定了正确的改造社会的根本办法,才是树立了真正的“主义”。一言以蔽之,抓住了真理,才是树立真正的“主义”。为索求真正的“主义”,青年毛泽东展开了对社会上流行的一切“主义”的研究。他说,起初,“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1]101后来,他剥离了掩盖在这些“主义”上的杂芜外表,将这些“主义”概括为不同层次、不同系统的几个方面:“哲学上之主义,伦理上之主义,教育上之主义,宗教上之主义,文学上之主义,美术上之主义,政治上之主义,经济上之主义,法律上之主义”[2]401。
青年毛泽东依据这些纲目进行了研究之后,逐渐转向无政府主义。他起初并不赞同马克思的“激烈的共产主义”,而是倾向于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他说:“联合以后的行动,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这一派的音〈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的,叫做马克斯。一派是较为温和的,不想急于见效,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互助的道德和自愿工作。贵族资本家,只要他回心向善能够工作,能够助人和不害人,也不必杀他。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这派的首领,为一个生于俄国的,叫做克鲁泡特金。”[2]341在他看来,“革命非兵戎相见之谓,乃除旧布新之谓”[2]639,只要是温和的革命能够解决的问题,就不需要暴力流血的革命。
此时青年毛泽东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至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2]293。为实现自己的这种主张,他先从湖南入手,领导和参与了驱张运动、废督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但是,驱张运动和废督运动只是更迭了湖南省的统治权,并未改变湖南省受压迫的根本面貌;湖南自治运动则根本未能统一分裂的局面,最终沦为知识分子的“独角戏”。“无血革命”,或者“呼声革命”,是在现代资本主义语境下的一种革命话语的表达方式。这种话语的背景中低吟着道德感化和教育手段的声音,其中的潜台词是对既有财产的保护和对暴力的排斥。因此,采取这种“主义”的人不是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就是资产者或者其代言人。此时的青年毛泽东并没有认识到道德话语向来从属于政治话语,而社会结构中经济向来处于比道德更为根本的地位。因此,道德呼声必将被政治环境所压制,也绝对不可能战胜私有者的私欲。对他来说,必须要重构新的话语体系,包括新的革命逻辑,新的目标、方式、手段和革命道路。因此,最终他认为“自治问题发生,空气至为黯淡。……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2]548至此他总结道: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民主主义,都属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6]6改造社会的办法,只剩下“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4]2
青年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是思想与实践交织的过程。但是,青年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毕竟是一种思想的变革,而不是实践的变革。在思想变革的场域中,实践只是一种参照系,而不是思想变革的主线本身。因此,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历程本身构成了青年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主体文本,伴随着的革命实践则在思想史的场域中充当了比对文本。思想与实践的交织,成为了文本的交织。交织的文本,构成了阐释青年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原因的解释场域。唯有在此场域中,青年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各环节才能统一为有机整体,青年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原因才能得到完整、真实的揭示。
青年毛泽东所接受马克思主义,是思想文本和历史文本的完整构筑,是在青年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本体上建构的有机整体。马克思主义是对时代断裂的回应,是新时代的政治话语体系,拥有全新的哲学基础和理论体系。因此,这也尤其能满足青年毛泽东寻找新的革命话语的需要。他说:“我看俄国的革命,是无论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6]4因此,马克思主义是他选择的革命话语的理论表达。青年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只是他的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融合的开始。在交互影响中,他的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彼此融合。直至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这种融合表征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诞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伟大成果——毛泽东思想。
*收稿日期:2012-09-26
标签:马克思主义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思想史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