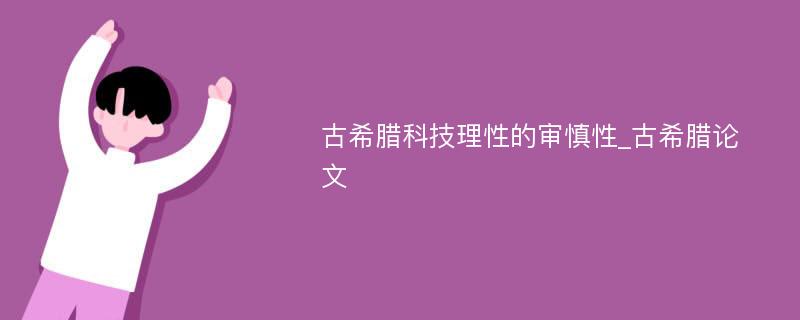
古希腊理性对技术的审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希腊论文,审慎论文,理性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在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时代,技术的发展远没有达到今天的水平,可以说是技术的蒙昧时期,现今,人们对此的普遍认知是:古希腊哲人重理性(科学、哲学),轻技术,几乎不谈或很少谈到技术。事实上在这些先哲的思想体系中,他们并不是对技术或技艺没有思考,反而对技艺充满哲理性的认识,在技术与人的关系上往往表现出对技术的渴望同时伴随着对技术的不安,以至不信任。今天的技术批判思想可以在古希腊技术怀疑论中寻找到根源,这种怀疑的理性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1 古希腊哲人眼中的“技术”
在古希腊时期,有关技术的用词是技艺“techne(复数形式technai)”,在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中,虽然没有明确地表达技艺的定义,但他们在使用技艺一词时,倾向于在“技艺是支配对象的技能”意义上使用,这个对象可以是自然的,如,苏格拉底说在“当你用刀来整枝的时候,花匠的技艺就更有用了”,“利用它们(指盾和琴)的时候,军人和琴师的技艺更有用了”[1]。这个对象还可以是人,技艺也指支配人这个对象时的管理甚至统治手段,在苏格拉底那里,也往往是从自然的技艺谈起,向统治人的技艺过度,“我们不用管他是不是正在水上行船,我们并不是因为他在行船叫他水手的,我们叫他舵手,并不是因为他在船上实行航行,而是因为他有自己的技艺,能领导水手们”[2]。总的来说,古希腊时代的技艺倾向于在自然技艺的意义上来使用。
对此,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7.7)、《物理学》(2.1)和《家政学》(1.1)中主张,要把这种技艺分为培植性技艺和建造性或支配性技艺。培植性技艺(即苏格拉底所称的“补偿性技艺”),如医疗,教育,农业等,它们旨在帮助自然更加丰富地生产出她本身就能够生产的东西;建造性或支配性技艺,如驾船,造房等,它们所产生的东西不能在自然本身中自然地产生。
从中可以看出,这种技术分类所依据的标准,就在于技术的目的是直接指向技术自身的完善,还是指向技术对象的利益。这里所说的技术目的是指技术的直接指向,不理解为技术的间接对象。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如果床能生长,那长出的就不会是床而是树木”[3]。造床的技术是建造或支配性技术,木工的技术是建造出自然不能产生的东西,其结果之一是木工的技艺在建造中得到提高,直接目的是指向技术本身的完善。而培植性技术力求实现形式和质料方式最紧密的统一,需要对与之交往的材料给予尊重和遵从,这种技术的目的是指向技术对象的利益,如农业生产的技术是帮助自然更加丰富地生产出它本身就能生产的东西,只要技艺的确模仿自然,其结果就将产生一种不可模仿的个性,这种个体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是第一位的。而在建造性技术中,对象(或材料)有必要被忽略或降低到一种听任摆布的无差别的底层地位。
对此,苏格拉底也有自己的阐释,每种技艺都有自己的利益,如舵手驾船技术,每一种技艺的天然目的就在于寻求和提供这种利益。这实际上就是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建造或支配性技术,比如说造房子、驾船技术。他认为有另一种技术,就是补充性技术,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培植性技术,“技艺的利益除了它本身的尽善尽美而外,还有别的,……任何技艺都缺某种德性或功能,这种补充性技艺本身是不是有缺陷,又需要别种技艺来补充,补充的技艺又需要另外的技艺补充,依次推展以至无穷呢?是每种技艺各求自己的利益呢?还是并不需要本身或其他技艺去寻求自己的利益加以补救呢?实际上技艺本身是完美无缺的。技艺除了寻求对象的利益以外,不应该去寻求对其他任何事物的利益。严格意义上的技艺,是完全符合自己本质的,完全正确的”[4]。这种技术的分类方法,直接反映出古希腊哲人对技术的态度。
2 关于技术的态度
在古希腊人眼里,哲学和神话是一对孪生姊妹,关于技术和人的关系,许多古代西方神话中都有所暗示——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赫菲斯托斯、依卡洛斯、潘多拉盒子等。这些神话一方面寓示了技术能满足人的需要,对人类来说技术是必要的、有用的,但另一方面技术也极易背离人——这种分离在古希腊人看来,可以表现为对上帝或众神的不敬,而遭到惩罚。这种态度基本可以概括为:技术是必要的(或好的)但是危险的。
从技术的产生看,苏格拉底认为“当你用刀来整枝的时候,花匠的技艺就更有用了”。“每种技艺都有自己的利益……每一种技艺的天然目的就在于寻求和提供这种利益”。他又说“无论任何技艺都不是为它本身的,而只是为它的对象服务的。技艺是支配它的对象,统治它的对象的……技艺除了寻求对象的利益以外,不应该去寻求对其他任何事物的利益”[5]。从这里会看出,无论哪种情况,苏格拉底都认为技艺是有用的,表达出对技术向往的意愿,但对技术又有所怀疑,担心技术会为寻求另外的目的而被它用,明确表现出对技术活动的不信任或不安。
亚里士多德也认为,虽然地球“极其丰富地提供着物产,但是耕作并不是在软弱无力地产出作物而是……生产出了一类人……此外,地球,作为神,也在把公正教给那些能够学习的人”[6]。关于是否要做以及如何来做某事的区别,色诺芬引用了苏格拉底的观点,人必须独立决定如何执行某项活动——他们可以学习“建筑、铸造金属、农业、统治人类以及……计算、经济以及军事策略”[7],因而不需要依赖上帝帮助他们“记数、丈量或测重”[8];然而他们的技术活动的最终结果却是隐性的。他最初举的例子还是农业:知道如何种地的人不知道他是否能获得丰收。因此我们是否应该动用技艺的力量是一个需要依靠神的指引而决定的主题[9][10],表现出对农业技艺的不信任。
苏格拉底认为,人应该关心人事,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忠诚之类的道德问题,而想了解自然规律并进行制造生产,关心上天的命运的人,苏格拉底“把那些认为这些事并不随神意而转移,而是一切都凭人的智力决定的人称为疯子”[11],自以为似乎“当他们掌握了所有事物产生时所依据的法则,如果选择的话,他们就能制造风、水、季节和任何他们所需要的诸如此类的东西”[12],这种制造能力会使人变得失去理智,作出更多的邪恶。其实“苏格拉底并不是急于要求他的从者口才流利,有办事能力和心思巧妙,而是认为对他们来说,首先必须的是自制,因为他认为,如果只有这些才能而没有自制,那就只能多行不义和多做恶事罢了”[13]。表现出对技艺的不安甚至恐惧,害怕驾驭不了这种技能,为此苏格拉底要求技术知识的系统追求要服从于道德规范和政治所关注的问题,对技术有所约束。
3 技术对个体人和社会稳定的影响
在苏格拉底眼里,人的根本的追求是最完满的“善”,美德就是关于善的知识和概念。而技术的富足和变化往往能破坏个体对卓越和社会稳定的追求。“财富和贫困,其中一个是奢侈和懒惰的专利,另一个是可鄙和恶性的专利,两者都是不满的专利。”[14]面对技术力量本身固有的无节制的发展,他认为可能会产生各种不安,柏拉图为此做了更为深入的阐述。在《理想国》第二卷中,当描述了原始国家的轮廓,反而遭到格劳孔的反对,把这一切说成是“蠢猪之城”的时候,苏格拉底回答说:“真正的国家在我的心目中就像是我所描述过的那样——可以说是一个健康的国度。不过你需要的话,我们也可以研究一种狂热的国度……因为着起来有些人对已有的东西和生活方式不太满意;但是,床、桌子和其他家具等还不得不加进去,当然还应该有调味品、香料、熏香、妓女和甜品——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先前提到的要求条件可以不再限于必须有房屋、衣服和鞋子等,但是(各行各业的技艺)也必须同时调动起来……健康的国家也不再嫌大,但是有太多的活动超出了满足必须条件的范围必将使它的规模膨胀。”[15]
这段话表明,面对技术无限制的膨胀后产生的富足财富,人们对此仍然缺乏信心,其结果还要追求更多的财富,但是有太多的活动超出了满足必须条件的范围,一方面引起人物欲的膨胀,“而邻居如果不以所得为满足,也无限制地追求财富的话,他们势必也要夺一块我们的土地。下一步,我们就要走向战争了,战争使城邦在公私两方面遭到极大的灾难”[16],从而破坏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古希腊的文化受到了伤害,因为在古人看来,技术膨胀后而获得财富让人们习惯于适应于(局限于)财富提供的安逸生活,把财富当作主要的追求目标,忽略人之为人的其他各方面追求,实现美好或完美的东西(即苏格拉底的理想境界)就困难了,因为任何事物的完美,包括人本性的完美,都与温和安逸相对立,因而无论是为自己还是为他人都选择了不太完美而不是更加完美,选择了较低水平而不是更高水平的生存状态,不再去追求个性的卓越,这就是对苏格拉底式古文化可能造成的伤害。
米切姆认为这样的情况在医学方面表现得比任何其他方面的技术都普遍。例如,当有了麻醉药物可用作缓解药的时候,许多人便选择麻醉药物来缓解痛症,而放弃了自然科学的卫生学疗法或心理启迪疗法。在《理想国》第三卷中苏格拉底在回答格劳孔时继续主张,目前医学的技能属于“延缓死亡”驯服疾病的教育;与提高健康水平不同,取而代之的是它允许非健康的人过着“长时间痛苦的生活”并“繁衍像他们一样的后代”[17]。米切姆认为与苏格拉底那时所描述的情况相对照,当今的现代医学技术甚至比当时雅典的情况更加相符。从苏格拉底式看来,现实的生活方式不是追求完美,而是在技术提供可能的条件下选择了较低水平而不是更高水平的生存。正如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所揭示的技术使人丧失了审视社会的能力,在“病态”的技术下“病态”地生存。
柏拉图进一步说明技术的变化所带来的危险。用阿第曼图斯(Adeimantus)的话来说,“它一点点地渗透,悄悄地流入人的性格和习惯,再以渐大的力量由此流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再由人与人的关系肆无忌惮地流向法律和政治制度,它终于破坏了公私方面的一切”[18],也就是说一旦技术发生的变化在技艺中被确立了正常的地位,它将影响到人的本性和活动,继而冲击到商业活动,并进而发展到违背法律和政治秩序。对法律的遵循从理想状态来看主要应该建立在习惯或自愿的基础上而不是出于被动。从如今的现实来看,技术上的变化的确逐步向习俗和习惯的权威发起挑战,其结果是逐渐降低习俗的权威,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倾向于强化强制性法律并把暴力引入国家及国际事务。这种情况的确可能促使我们严肃地考量一下20世纪的历史和21世纪的今天,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暴力和战乱的时期之一。哈贝马斯在《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与技术》中指出:随着现代技术的诞生,出现了技术力量的倒置,变成了一种政治统治的手段。古希腊在道德和政治的阐释中表现出对待技术活动的小心谨慎和不安、怀疑在今天持续地得到印证。
4 技术及人工自然的地位
在古希腊,一种哲学传统就是走向形而上学,轻视形而下世界,无论通过对苏格拉底还是对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层面的分析都可看出轻视技术形而下的倾向。这种轻视有足够的理性根据,进一步确证古希腊对待技术活动的不信任态度。
苏格拉底在认识论层面上对技术知识进行批判时,将技术置于次要地位。在《理想国》第七卷中关于“哲学王”教育的讨论中,苏格拉底考虑的是什么样的教育内容才能最有效地把“学生”领引到最崇高或最重要事物的“真理”之中,得到的一个结论是,肯定不是那些“其他的技术科学则完全或是为了人的意见和欲望,或是为了事物的产生和制造,或是为了在这些事物产生出来或制造出来之后照料它们”[19]的技艺。由于技术无法从对世界的关怀和关心中转达或释放出这样的思想,因而它不应该成为人类生活的首要关注点。由于技术关心的是弥补世界的缺点,所以技术的定位总是朝着更低微或更软弱。医生见到的有病的人总比健康的人多,相比之下,爱或爱情的朝向则总是指向更崇高或更强烈,它力求卓越;在柏拉图的《会饮篇》中,狄俄提玛(Diotima)对苏格拉底说,“精通此类事情的人是有灵性的人,而有其他智慧,例如各种技术和手艺的人则是庸俗的,平常的”[20],“手工技艺似乎又全都是有点低贱的”[21]。在苏格拉底那里典型地反映出古希腊哲学的显著特点,追求形而上学境界,轻视技术,把技术置于道德和政治之下。
对此亚里士多德表示赞同,其理由是一种更加适度地形而上学的理由。亚里士多德在形式质料因中,提出实体由四因生成,所有物质实体的实在性完全依赖于形式和质料表现方式、样式的紧密统一,以及由此而确定的目的或目标。而人工自然的问题是它不能够在极其深入的水平上达到这种形式和表现样式的统一,这种分离,使得它们具有种种用途或被强加上外在目标,而失去对人工自然的把握和控制,使人工自然在一定程度上脱离其本性所为(本质因)存在而为它用。亚里士多德认为实体是以个体的形式存在,具体的个体被他称之为“第一实体”,即说它们是第一性的,主要的,基本的,决定性的实体;把它们的种、属称为“第二实体”,即第二性的,不是像个体事物那样根本的实体。用这种观点考察对比手工制作的陶制盘子和机器加工的塑料盘子,可看出“陶制盘子有着厚重的分量,丰富的纹路,并与它的周边环境有着清晰的联系,这点和石头没有什么两样,而塑料盘子所展示是盘体的光亮,以及只是抽象地牵扯到它的生产和使用环境的千篇一律的表面”[22]。手工的陶制盘子清晰地体现形式和质料的统一,体现个体性,是第一实体;机器加工产生的塑料盘子,是以大规模生产,以功能为导向的聚合技术的产物,是第二实体,它们是第一实体的种和属。这种对突出实体(个体)的手工技术的青睐和对千人一面的机械技术的轻视的不同态度在现实社会仍然有所反映,如中国现代的手工云锦技术,它逐花异色,任何机器化千篇一律的生产都不能替代,现代最高级的计算机也模拟或实现不了这种技术,每一个技艺的产品都是独一无二,是独特的个体。这种逐花异色的技术地位无论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世界还是在现实世界都明显地高于机械化技术生产的产品,所以在米切姆眼里以亚里士多德的从形而上学实体论的角度看现代技术,“塑料盘子所展示的是盘体的光亮,以及只能抽象地牵扯到它的生产和使用环境的千篇一律的表面,应该把它取消”[23]。然而这样的论点是否正确,完全取决于此前对于什么是最初的现实东西的理解。以亚里士多德实体观来看,有一种现实只能在个体中找到,它是超出了大规模生产,以功能为导向的聚合技术的范围的独特的个体。
从中可以看出,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体系分析技术的地位,尤其是具有抽象性千篇一律的技术及人工自然,它是居次要地位。古希腊时代从理性层面上置技术及技术活动为第二位。
5 人工自然和自然存在的真实性问题
《理想国》第六卷,从认识论的角度明确提出自然存在比人工自然更真实,苏格拉底认为“要把辩证法所研究的可知的实在和那些把假设当作原理的所谓技艺的对象区别开来,认为前者比后者更实在。”[24]
在《理想国》第十卷中讨论到了由神或自然、木匠以及画家或艺术家所制造的床。制造床或桌子的工匠注视着理念或形式分别地制造出我们使用的桌子或床来。造床的木匠造的不是真正的床或床的本质的形式或理念,而只是一张具体特殊的床而已。如果他不能制造事物的本质,那么他就不能制造实在,而只能制造一种像实在(并不真是实在)的东西,理念或形式本身则不是任何匠人能制造得出的,画家制作不是真的制作,他是制作床的影子。因此,有人说这种东西(指床)也不过是一种和真实比较起来的暗淡的阴影。自然比人工自然更真实,模仿术和真实距离是很远的。而这似乎也正是它之所以在只把握了事物的一小部分(而且还是表象的一小部分)时就能制造任何事物的原因,这也正是技术与人的意愿分离的原因所在。在柏拉图《理想国》中,从他的理念概念出发技工只是模仿理念而产生具体事物,在这个过程中,技工只把握了理念的部分,然后就去模仿制造,事实上他根本没有把握对象的联系,就利用这种部分的表面东西来进行技术活动,因此,造出来的技术产品就远离真实世界,它就可以异化为不受技工支配的东西。亚里士多德认为,“当某种器具只是为了某一种用处而非多种功能,这种器具才是一切器具中最完美的器具”[25],以防止它用。
苏格拉底的观点是,自然的床,由上帝制造的床是第一现实,技工模仿制造出的许许多多的床,是第二现实,而艺术家所画的床的图片是第三现实。因此,在第二或第三现实的意义上技术才具有创造性,第二现实、第三现实对第一现实的模仿远离第一现实——所以通过技艺而形成的现实(人工自然)应服从于道德的和形而上学的指导。
总之,古希腊理性一是依据道德来判断技艺,认为人工自然是由它的有益或有用性得以判断而产生;二是依据形而上学,判定的标准应该是正确的程度或美。关系到制造的这种层面,柏拉图派和亚里士多德派之间一种可能有的分岐就在于,有益和美,道德规范和审美是否应该是指导技艺的恰当标准。然而,这种分歧的存在不掩盖这样一个更为基本的共识:有必要让生产和技术服从于某种严格定义了的限制。技术是好的,但如果技术对象或活动不能服从自然的内在指导,自然必将被人类有意拿来从外部对它们施加压力。“当代的技术创造带来环境问题和生态混乱的倾向从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前现代的观点。”[26]。综上所述,技术与人共在,古希腊理性对技术的怀疑的态度表明对技术的不信任,蕴涵着深刻的技术批判思想,如同恩格斯所说现代科学许多思想都可以从古希腊找到根源,似乎也可以这样说,当代人们对技术的反思与批判的观点都可以从古希腊哲人那里看到原初的萌芽。
收稿日期:2003-04-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