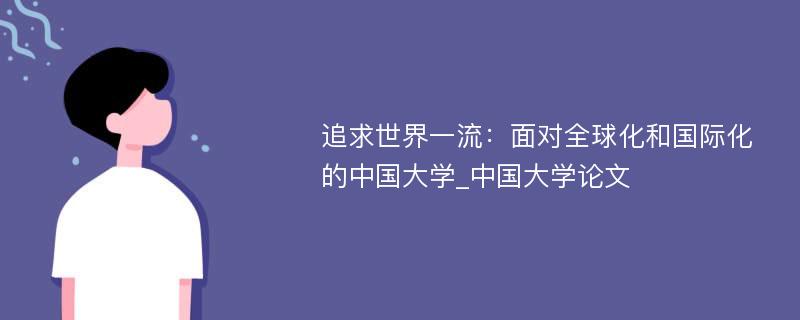
追求世界一流:面对全球化和国际化的中国大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一流论文,中国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全球化的现象往往被看作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动全球经济的日益融合,是通讯技术的不断推广使得世界范围存在即时的信息联系。尖端科学知识的同质化现象,竞争实力日益通过实行同行评审的国际刊物加以衡量,再加上跨国顾问公司和国际组织的咨询建议,所有这些形成压力使得大学不得不被引入一种全球文化的氛围之中。人力资本理论的浪潮导致在世界各地高等教育领域里对“效率”和“责任”日益高涨的呼声,大众化、多样化和分权化的高等教育正在通过共同的模式涌现。与此同时,这种被一位学者指称为“全球性技术文化”(Franklin,2001:247)所产生的源源不断的压力已经导致在某些地方的强烈反应,其形式就是维护当地和本土的知识,这些知识可以提供根基和一种认同感(Friedman,2000)。人们也同样期待着来自中国的这种反应,因为中国拥有极其丰富的传统文化遗产;在过去的千百年中,它已经孕育出众多杰出的科学和艺术成就。
国际化通常被认为是大学积极充当媒体,促进具有国际指向的科研、教学和课程变革,接纳越来越多的外国留学生(Knight,1997)。大学国际化往往通过民族国家政府的支持以及与民族文化和教育机构相关的方式加以实现。因此,民族国家政府的作用及其国际政治关系,对大学的国际化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尽管民族国家政府的作用方式要受到全球化各种力量的制约(Knight,1997;Lingard and Rizvi,1998)。就中国而言,我们把国际化理解成是对全球化压力的一种反应,而且我们有意探索这样一种可能性,亦即中国大学的国际化是否可能对全球学术界形成独特的文化、认识和制度作出贡献。
面对全球化的中国大学
在上世纪80年代早期,中国领导人决定要迈向市场经济,这最终导致中国于2001年被世界贸易组织接纳为正式成员。在此期间,中国经济的发展引人注目,其GDP平均增长率连续20多年保持8%,而且中国在2003年已经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CreadersNet,06/11/2003)。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在2002年达到7,400亿美元,同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三大进口国(Ibid)。虽然中国经济仅占世界总量的4%,但是对2002年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却达到17.5%,而且有望对未来的世界经济做出越来越大的贡献(Ibid)。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领导人越来越认识到,高等教育对确保国家劳动力的素质和发展尖端领域的研究具有极端重要的作用。最近几年,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扩张迅速,已经建立起了大众化的高等教育体系,这对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而言,的确是巨大的成就。在1990年,全国18到22岁年龄段的人口当中,只有3.4%的人接受了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到1995年,这一比例上升到7.2%,到2000年,该比例达到12.5%(《中国教育统计年鉴》,1999、2002)。最近发生的跨跃式发展特别引人注目,高等教育的招生人数从1998年的115万人增长到2001年的284万人。在2002年,中国已经跨过了国际公认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最低门槛,即入学人数占同年龄段人口的15%,接受各种形式高等教育的在校生总人数达到1,600万人(《中国教育部(a),2003》)。这一数字与美国规划的2002年在校生人数1,560万人相当(NCES,2002)。
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在前苏联的帮助下也曾经历过一次快速发展阶段,但那是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限制条件下,通过发展高度专门化的院校来为各个经济部门培养人才。整个高等教育体系自上而下实行严格管理,高等院校或地方教育当局几乎没有什么自主权(Hayhoe,1999:73-90)。今天,中国领导人认识到给予大学一定程度的自由以使其形成自己的定位和作出自己的选择,它们能够更好地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作出贡献。因此,他们采取了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方法来规划高等教育的扩张。国家颁发的一系列政策已逐渐扩大了大学的自主权,并且终于在1998年颁布了《高等教育法》,其条款规定大学能够规划自己未来的发展(Law,1999)。
中国政府在1993年首次宣布一项重大计划,即给予100所大学显著增加财政资助,其目的是它们能够在21世纪跻身世界一流行列。这一大规模的资助项目,被冠名为“211工程”(Program,1993)。与过去从上面决定“重点”大学并给予其高水平资助的做法不同,在这个项目上政府鼓励大学通过竞争获得精英地位。这种获得认可和重大财政支持的机会,在全国引起极大的震憾,大学竞相根据其在关键领域的特定优势进行战略规划,展示它们能对国家发展做出独特的贡献。在许多情况下,它们特别珍惜过去同各国已经建立起来的历史联系,以及自1978年开放以来建立起来的各种伙伴关系。
在1994年举行的一次全国性会议上,出台了若干鼓励性措施,旨在提高教育质量和更好地利用教育资源。这些措施包括:省级和中央政府共同支持高等教育、把部属专门院校下放给地方管理以及高等院校之间的合并等(Zhou,2001)。大量的合并随之发生,而且几乎所有的合并都导致产生更趋综合化的大学,使其拥有从基本的文理学科到大多数专门领域的知识范围(Yang,2001)。这些合并有效地改变了上世纪50年代在苏联影响下建立起来的过于专门化的高等教育体系。当时的体系由十多种截然不同类型的大学构成,包括集中文理学科的综合性大学、理工科大学、培养师资的师范大学以及一系列工、农、医、财、法、艺术和体育等学科领域的专门院校。
位于杭州的浙江大学可能是大学合并的一个典范。浙江大学在上世纪30和40年代已经是中国顶尖的综合性大学之一,但是在1952年遭致分解并变成一所工科大学(Zhejiang daxue bianxiezu,1997)。1997年,它进行了一次大合并,即把当地的一所医科大学、农业大学和政法大学合并过来,而所有这些大学都是在1952年从浙江大学中分离出去的(Chen & Xu,1998)。另一所被合并到浙江大学的是浙江省属综合性大学——杭州大学,其在历史、文学和教育学等学科领域具有很高的水准。这所大学建立于1952年,是在原浙江大学文学系和教育系与一所建立于19世纪早期的著名基督教教会大学合并的基础上组建起来的(Hangzhou daxue xiaoshi bianji weiyuanhui,1997)。如今,浙江大学在中国顶尖大学中排名第五,仅次于南京大学(第四)、复旦大学(第三)、清华大学(第二)和北京大学(第一)。它们是1998年5月被挑选出来的九所精英大学中的五所,而这九所精英大学获得了比“211工程”中其它90所大学高得多的财政资助。1998年5月,中国最顶尖大学——北京大学举行100周年校庆活动,这一活动直接导致了所谓的“985工程”的诞生,这一项目就是专门为资助这九所顶尖大学而设立的(China Education Daily,8/102002:2)。
总的说来,除了前面已提到的规模大扩张之外,这次席卷全国的院校合并浪潮,已经使中国高等教育拥有了引人注目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可从两个维度来看,一是横向,一是纵向。在横向维度上,综合性大学越来越多,专业侧重各有不同。而且中国大学的平均规模已大为增长。从表1可以看出,大学平均规模在扩张和合并前后的变化情况,即在校生规模为3,000以上的大学,从1990年的170所(占全部大学总数的15.8%)增加到2000年的603所(占全部大学总数的57.9%)。
表1 中国高等院校按招生规模分类表
年份 总学 1000人
1001到
3001到
5001人
校数 及以下
3000人
5000人
及以上
1990 1075358 547 99 71
1993 1065236 568 163 98
1998 1020122 535 193170
2000 104186
312 247356
资料来源:中国教育统计年鉴1990,1993,1998,2000年
位于中国高等教育体系顶端的100所大学从“211工程”中获得额外资助,在经费来源方面享有明显的优势,而且它们承担着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中绝大部分的研究生教育和研究活动。这在表2所提供的统计数据中是显而易见的。
表2 “211工程”大学主要资源占全国高校的比重(%)
资源项目名称 “211工程”大学所占比重
图书馆藏书量 25.65
科研仪器设备 38.70
本专科在校生数18.33
硕士生在校生数69.14
博士生在校生数86.01
外国留学生在校生数58.19
正教授占师资比例 18.85(全国平均为9.77)
科研经费 70.10
国家重点实验室100.0
国家重点学科 83.61
专利登记数72.81
资料来源:中国高等教育,Vol.24,No.19:p.16
在纵向维度上,现在实际上存在四个等级的高等院校。由“211工程”资助的100所大学构成最高等级,负责教育从全国各地选拔来的最有才华的学生,并承担主要的研究活动。第二等级由省级公立大学组成,主要满足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和不同类型学生的各种需要。第三等级由主要提供2-3年短期课程的公立学院组成,它们通常由市级政府部门管理。这些学院原先被称作职业大学,但现在有时也被称为社区学院。第四等级由正在迅速增长的私立高等院校组成。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允许私立院校存在,以满足社会对高等教育的巨大需求,如今私立高等院校已经如雨后春笋般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群体(Mok,1997)。私立高等院校有意识地专注发展职业教育,以此与国家资助院校相区别。除了国家规定的学习内容,这些私立院校所开设的课程以外语、商贸、信息技术及其它实用科目为主,这些都是就业市场所需要的。只有一小部分私立高等院校获得政府的正式认可——在差不多1,300所私立院校中,只有167所获得这种认可。其中,只有九所获得国家批准而拥有学位授予权(Ministry of Education [b],2003)。毫不奇怪,在这些私立高等院校就读的学生中,绝大部分都是没有获得进入公立高等学校资格者。因此,中国私立高等院校都集聚在国家高等教育体系的最底层(zha,2003)。
因此,全球化压力所产生的结果之一,就是高等院校之间的等级分化日益显著,即处于顶端的高校与处于较低等级的高校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种现象在世界其它地方也是随处可见的。对中国大学而言,这种等级分化的积极意义在于,赋予一批顶级大学以机会和资源,使他们主动评价自己的强势和弱项,并且在全球范围找到自己的定位。他们除了获得更多的来自政府的经费外,也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国内外募集资金。这主要是通过遍布世界各地的校友网络,通过提供咨询服务以及在某些情况下通过经营销售其高新技术成果的跨国公司来实现的。以北京大学为例,它的跨国公司“方正集团”已经给学校带来了可观的收入。在2000年,该集团已实现超过100亿元人民币的销售收入和44,554万元人民币的利润(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China[c][d],2003)。
在20世纪的许多时间里,中国大学都在努力“追赶”世界其它地方的所谓先进。在21世纪初叶,它们终于接近或达到一个拥有优势的层次,能够被看成与世界其它国家大学平等合作的伙伴,而且人们也期待着它们能够凭藉中国近几十年来所取得的杰出成就以及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对全球性问题贡献出自己的才智和力量。目前,中国大学校长们对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津津乐道,而且他们也的确正在朝着这一目标努力奋斗着。然而,人们还不清楚的是,一所世界一流的中国大学与世界其它地方的同类学校——尤其是北美和欧洲的大学——有何区别,其标准也有待确立。
为了形成一种中国大学精神并使其为世界学术界带来一股活力,中国大学领导人必须加强对中国历史、哲学、医学及其它相关领域的研究,从而把自己无与伦比的学术遗产与在西方模式下进行的自然和社会科学前沿研究联系起来。近年来的大学合并应该使得跨学科领域的文化理解得到显著增加,这将有利于形成一种新的大学精神。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讲,这就要求对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学术历史进行全面的重新审视,因为自那时起儒家文化传统就被当作封建糟粕而抛弃,而且还被认为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主要障碍。最近几十年里,世界哲学界对儒家思想的兴趣开始回潮(Tu Weiming,1993,1998),这的确是对当代中国大学提出了严肃挑战。我们不禁要问,如果抛弃了历史遗产,它们能够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吗?
最近的改革使得中国大学获得了比1949年革命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大的自主权(Zhong and Hayhoe,2001:275-278)。大学自治通常被认为是保护学术自由的重要条件之一,而且毫无疑问,中国的学术自由在最近几年里已经得到极大的改善。然而,在经济快速转型期,中国政府依然高度强调社会“稳定”,依然对中国的新闻界和出版界施加一定的控制。由于这种原因,中国学者发现要专注于本专业领域的批判研究并不容易,反而学术批判容易流向直接相关的政治和社会领域。因此,中国大学要想取得高度的学术自由还需要进行长期的和渐进的不懈努力,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特质,而且还因为大学里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具有高度的社会和政治责任感。
尽管存在这些局限性,但是毫无疑问中国大学已经积极参与全球化历程,已经能够在许多自然科学领域以及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和专业学科知识领域跻身国际研究界和学术界。它们通过培养学生和双边计划,已经建立起向非洲国家提供帮助的良好模式(Gillespie,2001),而且最近它们已经开始同印度杰出科学家和知识分子进行一系列的对话,以分享有关亚洲如何承担全球发展责任的思想和观点(根据2002年10月31日在多伦多同印度技术教育委员会主席Ramamurthy Natarajan教授的个人谈话记录)。什么时候中国大学会被欧洲和北美的大学真正接受为平等的合作伙伴呢?什么时候它们能够利用自己丰富知识遗产所产生的真知灼见来解决西方世界面临的问题和困扰呢?这些令人着迷的问题尚有待回答。
中国大学与国际化
与欧洲和北美相比,国际化对中国具有相当不同的含义。对西方大学来说,课程的国际化就是把越来越多的国际内容结合进其学科领域和课程结构,这些学科领域和课程结构深深植根于欧洲历史、尤其是19世纪史。对中国而言,在1905年废除传统的科举考试制度之后,随着西方模式的现代大学的创立,现代学科的整个结构才从国外逐步引进(Hayhoe,1999:35-36)。一个多世纪以来,大学知识分子努力把这种结构与中国自身的学术遗产和发展需要结合起来。在上世纪50年代早期,中国强制实行苏联学术模式;然而,尽管政治意识形态不同,苏联模式是植根于欧洲传统的,这就保证了欧洲传统得以与1949年之前一样在相当程度上延续下来。这种一边倒地通过一种西方社会主义模式来尽快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的急迫心情在当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最终悲剧性地导致“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知识模式在激进的“文革”十年遭到全盘否定。
相比之下,1978年以后发生的课程和研究的国际化带有折衷主义的特征,亦即是课程内容取自不同的西方国家,再下功夫使之适应中国自身的发展需要。中国留学生被派往世界各地学习,中国与许多国家建立起学术交流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合作伙伴关系,这就允许在知识转让和改造方面进行各种有趣的实验。尽管世界银行支持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项目带有浓厚的美国影响,但是它们也为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创造了机会,使之能够参与中国的课程改革、科研及其相关领域的发展(Hayhoe,1989,Chapter 7)。
数以万计的中国学生利用改革开放之机到国外留学,他们主要集中在北美地区,但在欧洲、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其它国家也为数众多。中国的官方政策一直有些摇摆,介乎于输送年轻学生到国外取得高学位与派出有前途的学者到国外了解本学科领域的最新进展、争取合作研究机会之间。尽管在过去20年里中国政府支持留学的力度很大,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和学者也常常能够有机会获得私人赞助到国外留学。中国官方发表的统计数据表明,从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已有46万人留学海外,并有15万人已学成回国(Si,2003)。从这些数据也可看出这一留学运动的范围和规模之大。
人才流失已经成为中国政府的一大困扰。在上世纪80年代早期,中国政府相信大多数留学人员将回国参加国家建设。然而,他们当中许多人后来选择在欧洲、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地长期居留,得益于这些地方积极配合他们取得永久居留权的政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留学生开始看到在高等教育和其他产业领域奉献其专业知识的机会。因此,在最近五年里,回国人员的数量以每年13%的速度增长(Wei,2003)。
其结果,现在中国名牌大学教师在观念和经验的国际化程度上与西方主要大学的教师相差无几,抑或更甚。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北京大学70%的教授和80%的副教授是从西方学成归来的(Xinhua News Agency,05/10/2003)。同一研究也表明,中国科学院85%的研究所负责人和81%的院士是留学归国人员。
这个留学运动的另一个有趣现象是,那些永久定居海外的大量学生和学者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已经在世界各地的大学取得事业上的成功。这批人员中大量的就职于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然而正是那些从事人文和社会科学工作的人可以肩负起有关中华文化的研究和诠释,因而可以发挥特别有意义的作用。这些学者的研究方法和效率能够达到西方标准,他们的知识储备又深深浸淫着自己的文化传统,他们因而能够以内外结合的理解方式来诠释中华文明以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最近的学术研究成果反映出他们正在起着这种作用。
这里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新近出版的一本关于当代中国哲学的书。这本书介绍了20世纪16位中国主要哲学家的成就及其对当代全球性问题的思考。参加编写此书的学者多半来自中国大陆,但现在美国大学任教(Cheng and Bunnin,2002)。另一个可以说明定居海外中国学者重要作用的例子是《中国季刊》。这是西方研究中国首屈一指的学术刊物,其中发表的大量文章为目前在北美和欧洲大学任教的中国大陆学者所撰写(Edmonds,2003:322)。这些学者能够以国内学者所不能的方式,向全球社会反映和阐释中国在社会和文化知识领域所取得的成就。
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这对中国大学意味着什么?它们将来会发挥什么样的影响?
随着“211工程”和“985工程”的设立,中国将全力以赴地创建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211工程”的100所大学可以获得大量的额外资助,“985工程”的九所大学所获得的资助更是惊人。最近,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分别获得18亿元人民币(折合美元22,500万)的资助,而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和南京大学则分别获得12亿元人民币(折合美元15,000万)。这些资金被计划用于资助高水平的研究工作,同时用于改善师生的报酬和居住条件。更重要的是,这些中国顶尖大学的校长们正在积极热烈地讨论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和质量问题。
最近在清华大学举行了一次有关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理论和实践的研讨会,十几位与会大学校长们达成如下四点共识:第一,一所世界一流大学必须具有独特的大学精神和明确的基本原则。这种精神特质必须渗透到学校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在校园内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第二,一所世界一流大学需要一种独特的管理风格,这种管理风格能够确保上述基本原则在大学运作的方方面面都能得到贯彻和实施。第三,最重要的是,一所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拥有高质量和高标准。最后,一所世界一流大学应该对人类的文明和福祉、对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Tsinghua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Studies,2003)。
这最后一点可能会把中国大学带回到世界大学的大家庭中,并分享其理念。再早一些,一位中国大学校长在其文章中提及孔子“和而不同”的观点。他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可以成为人类在新的千年里追求“和而不同”的精神力量(Hu,2001)。把这种观点应用到中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时,他认为“和”意味着一所世界一流大学要善于吸收其它大学的优秀传统和成果,同时又要善于创立植根于本民族文化的独特大学文化。这样的一所大学将特别强调在教学和科研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把世界历史、地理、国际金融和贸易等领域的内容整合进自己的课程体系之中。它将力争成为一条明晰的渠道,招贤纳才,并且从世界不同文化当中汲取精华。如果说“和”的观念可以服务于国家发展的近期目标的话,那么“不同”的观念,因其具备创造和创新的意味,可以在某种意义上很好地表达中国大学在人类发展过程中未来可以发挥的长远作用。
尽管这些观念还只是在萌芽阶段,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大学领导人已经在切实思考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本质的问题。为了获得更为具体的认识,这里有必要提及两位北京大学资深学者1997年在考察美国的本科教育之后,对中国传统文化优势的反思。他们指出,本科生教育应该能够使学生具备社会责任感,并且善于构建良好的人际关系。这是中国教育取得成功的一个方面,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倡导集体精神,这种文化鼓励学生在学习方面互相帮助(Minarid Chen,1997)。从这一意义上讲,中国传统文化可能有助于全球范围内的大学生,因为它鼓励学生在竞争日趋激烈和个人主义倾向日益显著的全球社会中,培育坚实的道德责任感,并倡导人文关怀。
综上所述,可能是今后几十年中国大学会对全球社会产生影响的几个方面。我们正期待着中国大学精神的进一步发扬,也期待着中国学者和大学领导人与国外学术界进行更为广泛的交流和沟通,因为国外学术界对儒家思想在解决全球发展问题方面的潜在作用日益发生兴趣。我们在此要特别提及一些美国哲学家的著作(如Robert Neville(2000),David Hall and Roger Ames(1999))。他们在最近发表的这些著作中,都探讨了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与儒家思想的某些共同点,指出了这两种传统文化的交融,可能对欧洲理性主义的实质,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众所周知,自从启蒙运动以来,欧洲理性主义就一直处于支配性地位。在少数中国大学获得特别资助以追求世界一流地位的时候,我们希望这是在把新的活力和新的文化资源注入到整个世界大家庭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