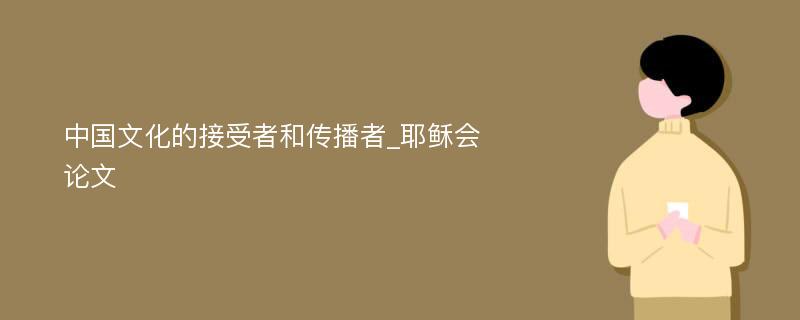
中国文化的接受者和传播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接受者论文,传播者论文,中国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十六—十六世纪来华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有其特殊的作用,他们既充当了西方文化的传播者,又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中国文化的接受者,继而他们又成为向欧洲传播中国文化的传播者。他们被称为“近代文明的哥伦布”,因为他们发现了文化意义上的新大陆。
来华耶稣会士都是博学之士,他们以异域人的敏锐眼光吸取了中国文化的精华,同时,他们又以文化比较的目光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保守、自封的一面,至今仍能发人深思。
一、耶稣会士脱胎换骨接受中国文化
地理大发现启发了天主教会向海外寻求发展的天地。天主教的传教事业也顺应了时代的潮流,推动了海外殖民地的建立和发展,成为欧洲各国殖民政策的一部分。天主教耶稣会士来华也是受时代潮流的裹挟而来。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曾预言:“我认为这个传教会(指在华耶稣会)对于上帝的荣耀、人类的普遍利益、科学和艺术的发展,无论在我们这里还是在中国人那里,都是我们时代最大的事情,这是一次互相的启蒙,这使我们一下子了解了他们几千年来做的工作,也使他们了解了我们做的工作,其中的伟大意义超越了我们所能想象的。”
耶稣会来华后,他们身兼两职,既充当西方文化的发射者又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中国文化的接受者,继而他们又成了向欧洲传播中国文化的传播者。十七—十八世纪,天主教士开创了欧洲的汉学研究,被十九世纪法国历史学家米什莱称为“近代文明的哥伦布”。
我们从初期来华的耶稣会士们的叙述回忆中可以看到他们在中国传教时,在接受中国文化的过程中经受的文化震惊和文化融合。
中国和欧洲相隔万里,地理历史、文化礼俗都绝然不同。耶稣会士进入中国后必然有一个艰难的文化适应过程,甚至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沙守信神父一七○一年十二月三十日从北京给巴黎的信中以他的切身体会谈到传教士来华前应做的思想文化准备。他说:“首先,到中国来的人们必须热爱耶稣,决心在各方面约束自己,让自己脱胎换骨。不仅因为气候、穿着、吃食发生了变化,而且生活方式和法兰西民族的性格和风俗都迥然不同了。没有这方面的能力,或者不愿意接受这种变化都不用想到中国来。本性难移的人这里是不需要的,某种太冲动的情绪会很奇怪地导致某些灾难。中国人要求人们能够控制自己的感情,尤其要能控制自己不要为所欲为。”
语言和文化是不能隔开的,对于不同文化背景的异族人交谈不是那么一点而通的,需要作一番详尽的文化历史的交代。沙守信说:“一个法国人一小时内能够给他们讲完的事情,中国人听上一个月也仍然不知所云。……如果您不具备某种柔和,某种温厚,某种坚韧不拔的品质,您每时每刻都会觉得难以忍受。”众所周知,开创耶稣会中国传教会的利玛窦神父的成功的奥秘正在于他谦虚谨慎地接受中国文化,适应中国文化,然后用中国人能接受的语言和方式来传播他的教义。学汉语、穿儒服、结交中国朋友,既是他为了传播基督教采取的必要途径,也是他逐渐中国化的过程。他成了后来耶稣会士们仿效的榜样。
初期来华的耶稣会士们的确是以利玛窦为榜样,在踏上中国土地前后都把接受中国文化作为传教是否成功的关键。雅克神父一七二二年十一月一日信中这样自我描绘:“如果您现在看到这位被派来的人的话,我怀疑您是否还能轻易地认出来。蓄了两年的胡子,光头只剩下一块地方有头发,那是欧洲神职人员通常剪发的地方,他穿的衣服也是不可想象的,这一切使得一个人的形象完全改变了。”“我们在这里的服装是这里的体面的服装,一件白布长袍,外面罩了一件同样长的丝棉袍,通常是蓝色的,束一条腰带,上身穿一件黑色或紫色长到膝盖的宽大的小外衣,袖子又宽又短,一顶如缩短的圆锥形的小软帽子的四周挂满了丝穗和红色的花翎,脚蹬一双布靴,手上拿一把扇子。这就是每次出门前或者有客来访时要认真打扮起来的装束。在家里,可以脱掉一部分这些物品,但是做弥撒时别忘了戴上那种特别的软帽和穿上靴子……”。这种自我形象改变的认可正是接受中国文化的过程。
穿儒服还只是需要传教士们心理上承受自我形象的改变,学习汉语却要他们付出千百倍的努力。晁俊秀神父一七六九年十月十五日从北京给巴黎的信中把中文和法文作了比较:“汉语真难。我向您保证它和任何我们知道的语言都不相同。同一个词从来只有一个结尾(词干),我们以性数来区别的讲的东西的种类和数量,而汉语没有性数变化。汉语的动词也不表明是谁在作为,怎样做的,什么时候做的,是单独做的,还是和别人一起做的。总之,中国人说话同一个词可以当名词、形容词、动词、副词、单数、复数、阳性、阴性,等等。您必须听仔细,琢磨揣度说话的场合。”“更有甚者,这些所说单音节的组合排列,好象没有任何规律可循。因此,为了学会这种语言,学了所有词汇以后,还必须学会特定的每一句话。稍一些改动,你说的话就有四分之三的中国人听不懂了。”
“对于一个欧洲人来说,汉语的发音尤其困难,永远是个障碍。简直是不可逾越的障碍。首先,每一个词有五个不同的声调,不要以为每个声调都是清晰可辨的。这些单音节在耳边一晃而过,好象就怕被人抓住似的。中国人还省掉不知多少元音,几乎听不到双音节的词。从一个送气发音的词接着就是一个连音词;一个嘘音接着是一个被吃掉的音;一会儿气流通过嗓子,一会儿气流通过上腭,几乎总是有鼻音。我在公开布道前,先对我的仆人至少练了五十遍。我让他听不懂就要我重复,我得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重复。他就象我的中国听众一样,只听懂十分之三。还好,中国人很有耐心,他们很惊奇,一个可怜的外国人竟会说两句他们的话。”“难懂的语言文学要求我们勤奋学习,尽管这种学习毫不痛快,我们只希望有一天能成功地掌握这种语言文字来为上帝服务。唯有这种希望支撑着我们。由于在语言文学方面,我们总有许多东西要学习,研究,我们必须养成习惯不断地把学到的东西进行操练,并且在对外交涉中付之实践。”
对于一个法国人来说,要学会汉语确实不容易,需要坚韧不拔、刻苦学习。无论传播文化还是接受文化,都必须首先闯过语言关。语言通了,还必须学习、理解对方的文化,与对方作思想交流。洪若翰神父一七○三年二月十五日给路易十四的听神功神师拉歇兹神父的信中叙述了熟喑中国经书的法国耶稣会士刘应获得康熙的皇太子的好感:
“……他(皇太子)熟读中国经书,对于以熟悉中国经书著名的刘应神父表现出特别的好感。谈了一会儿话,皇太子命人取出古书来给刘应神父看。一打开书,刘应神父的解释简易明了。皇太子非常惊讶,对周围的大臣们说:‘大懂’(他理解得非常好)。然后皇太子问他对中国这些书怎么看,它们是否和我们的教理一致。刘应神父思忖了一会儿对他说我们的教理和中国古书里写的能够一致,但是和别人写的对这些书的注释不相一致。‘应该承认’,皇太子接口道,‘新的注释不一定符合我们古代作者的意思。’这次谈话以后,皇太子特别尊敬刘应神父,他甚至毫不掩饰这一点,我们希望我们的教会能够大大得益于此。”皇太子在帛卷上写了一段赞词送给刘应:“这位来自西方的学者,我们感到他对我国的文学和文字上的研究已登峰造极,上彻云霄,深及九渊。(译文)”刘应神父以其丰富的汉学知识为其教会在中国得到认可作出了贡献。他有许多著译,如:《关于易经的解释》、《论老子的道教》、《中国四书的年代背景》,还有《中庸》和《书经》的拉丁文译本。他是法国第一代汉学家。他接受了中国文化的精髓,又向欧洲作了传播。
沙守信神父说:“对于一个法国人来说,这个国家的礼节是最繁琐的,最令人难受的。”可见法国神父们在接受中国礼节的问题上,也有一番痛苦的过程。可是他们深入中国大地,潜移默化,耳濡目染,有意无意地把中国的礼节融合进他们的生活中去了。从洪若翰神父叙述南怀仁神父的葬礼的一七○三年的信中,我们可略见一斑。他说:“主持神父带着所有在北京的耶稣会士跪在大街中央灵柩前。我们深深拜了三下,头一直碰到地上。”西方人初来中国,最不习惯的就是磕头。可是久而久之,他们却对着自己的主持神父的灵柩也磕起头了。他信上说:“我们穿着白色丧服紧跟其后。我们已经说过,中国的丧服是白色的;我们按中国的习惯一路行进一路号哭,我们实在也伤心至极。”西方人的丧服是黑色的,白色是礼服。而在此,他们也按中国人习惯穿上了白色的丧服。他信上继续说:“到了墓地门口,我们在路中央向着遗体跪下,拜了三下,哭丧的人又开始了。人们把遗体抬到落葬的墓地;那里已经设了一个祭台,上面已经放好了十字架和蜡烛。主持神父穿上白色法衣,背诵了祷文,按照礼仪常规点香。我们又向着棺材拜了三下,人们把棺材从车上抬下放进墓穴里。哭丧的人又号哭起来,他们哭得那么厉害,真叫人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这是一个很奇特的景象。祭台上的十字架表明这是一个天主教神父的葬礼,却又有中国式的礼仪——点香、磕头,甚至还有专人哭丧。神父们听着哭丧人的号哭也情不自禁地“眼泪夺眶而出”。一般来说,神父为死者祈祷时是不会伤心落泪的,因为死者是回到上帝的怀抱里去,是走向了永恒。可见,耶稣会的神父们接受了中国礼节的同时,思想感情也渐趋中国化了。
耶稣会士进入中国宫廷以后,以其精深的学问,为中国皇帝服务,如绘画艺术。他们把逼真写实的西洋绘画传统带进了中国宫廷;同时他们又不得不适应中国皇帝的趣味,把中国艺术观揉和进自己的创作之中。受过良好的意大利和法国艺术传统教育的王致诚教士不无遗憾地说:“说到绘画,除了给皇帝的兄弟,他的妃子,其他皇子公主,亲信大臣们的画像以外,我几乎没有按欧洲方式作过画。我必须忘掉我所学过的东西,用一种新的方式作画来适应中国人的趣味。因此,我要用四分之三的时间来画树木,果实,飞鸟,游鱼,走兽。有时在玻璃上作油画,有时在丝绸上作水彩画,很少画人物。”渐渐地,他的目光、趣味也发生了变化。他说:“自从我来到中国后,我的目光,我的趣味都有点中国化了。”他也接受了中国的艺术观。他向欧洲极力介绍中国园林的不规则的自然美。他说:“我很欣赏中国人在这方面(园林)及他们的建筑上表现出来的丰富想象力,相比之下,我真觉得我们在这方面太贫乏了。”后来,王致诚对中国园林的介绍促使十八世纪欧洲的艺术趣味发生了变化,打破了统一对称的法国园林传统格局。形成不对称、不规则、回归自然的中英式园林。
二、来华耶稣会士向欧洲传播中国文化
有一位耶稣会士在他们的信中向欧洲介绍了中国的考试制度。这种考试制度对法国知识界影响很大。中国的官员并不属于贵族阶级,也不是世袭的,得经过漫长的一系列科举考试的筛选。十八世纪欧洲哲学家们梦寐以求的就是凭本人“学问”攀登仕途高峰。以文化高低作为发现个人“才干”的首要因素,重个人价值,轻出身特权。耶稣会士的信中,肯定了中国的科举考试:“先生,您可以看到这种各级考试制度是由一种明智的政治决定,除了中国人天性爱好他们的文字以外,这种频繁不断的考试使他们在一生最美好的时光始终不懈往上攀登,防止他们无所事事、吃喝玩乐而对国家制造麻烦。他们一到识字的年龄就要准备考业士(秀才),他们往往要付出许多努力才能取得业士资格。他们取得业士资格后,为了保住这个资格,几乎一生都要不断去经受新的考试或者再去参加更高一级的考试。他们一级级考上去,仕途一级级晋升,他们享受到某些有别于百姓的特权,这些特权给予他们贵族的头衔。”“如果大官们的子弟不继承父辈业绩,不象父辈那样用功读书,他们就会重新跌入他们第一第二代祖辈所处的百姓行列。”
法国大革命在其教育计划中高度重视竞争性的考试。耶稣会士介绍的中国科举考试制度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模式。这种考试制度打破了世袭贵族政治符合资产阶级平民登上政治舞台的要求。法国至今仍行之有效的学士、硕士、博士分级学位制也还是有这种科举考试制度(秀才、举人、进士)的痕迹。当然法国人并不是照搬中国的科举制度,他们只是抓住这个遥远东方的模式,按照自己的理想和想象提出新的模式。正如他们推崇亲自下田耕作的中国开明君主雍正皇帝一样,他们用遥远东方的雍正皇帝作为参照系,来阐明他们对于开明政治的向往和理想。
中国历史悠久,又特别重视历史记载。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都有案可查。康熙宫廷里的法国神父巴多明特别钦佩中国编年史的真实性。他面对世界年代不可否认的证明,指出世界历史在公元前早就存在:“我是否能希望希伯莱先生们不要管犹太教长们所谓的信仰,让我们把世界存在的时间拉长一点,他们自己为了推后救出主降临,不也把世界存在的时间缩短了?”我们可以看到,巴多明神父强烈要求尊重历史,大胆提出把圣经编年拉长,使其和中国编年史吻合。这是他长期研究中国历史接受中国的历史观的结果。
巴多明神父熟谙中国的语言文字,拒绝把中国和埃及相提并论。巴多明神父从中国人早在大洪水之前就懂得炼铁、使用铁器这个事实,指出中国和埃及“并不是一个民族是另一个民族的分支或移民”。作为耶稣会士,巴多明神父提了这个与圣经相悖的论点是难能可贵的。他提请历史学界注意中国的存在。他说:“欧洲人相信古人,总是相信埃及人、查尔斯人和波斯人的科学。我想化点时间进一步验证这三个问题,让欧洲人跳出这种自然的成见。……在马可·波罗之前,中国一直被遗忘了。马可·波罗到过中国,他的游记起先被当作一部编造的故事集。后来到中国去的方济各会传教士们提供了关于这个辽阔帝国的知识,人们也不屑一听。”他又说“相当长时期内,有的学者认为在传教士把天文学知识教授给中国人之前,中国人不懂天文学,我对这些人该说什么呢?只是近几年来,通过翻译中国的书籍、他们的测算、和他们的古代观察记录,人们才开始睁开眼睛,开始想到他们中间也可能有值得引起重视的知识。”他不仅接受了中国文化存在,还要为中国文化呐喊。
十八世纪的欧洲哲学家们从中国文化中取得不少养分,尤其是伏尔泰。他在《风俗论》中说:“我们的天文学家看了他们的计算,非常惊讶地发现这些教据几乎全都符合实际。其他的民族编造了轻松的寓言故事,而中国人手拿一支笔和一个卜星测算器书写他们的历史,他们用的语言简洁明了,在亚洲国家中屈指可数。”“他们每一个的皇帝当政情况都有案可查。他们统治的方式从无不同,他们历史记载也从不自相矛盾……我们必须实行这样的原则,一个民族形成初期的历史是其后成为辽阔、强大、明智的帝国的根由,一个民族应该用其几个世纪的历史来把自己的人民凝聚成一个整体。”伏尔泰认为中国悠久历史最有效地把中国人民凝成一个整体。这是巴多明神父坚持有案可查的历史观的继续。
十七、十八世纪有着强烈的改革要求的欧洲人在传教士们的报道中发现了东方古国中国的存在。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卢梭等思想先驱无不涉猎传教士们对中国的报道。这些报道打开了他们的眼界,使他们发现当欧洲还在文化蒙昧时期,与之相距千里的东方民族已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中国开明的政治结构、以农为本的治国之道、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促使西方思想家们对全人类的命运作新的思考和宏观设计。伏尔泰的《风俗论》、孟德斯鸠的《法意》、狄德罗的《百科全书》等光辉巨著都充满了中西文化碰撞和交融结晶。
十六—十八世纪法国耶稣会士在进行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对中西两种文化的优劣不同作了比较。巴多明是积极进行科学传教的耶稣会士,他给欧洲的一些科学家和学者写过不少有关科学和教理方面的颇具趣味的信件。他分别于一七三○年八月十一日、一七三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和一七四○年九月二十日从北京给当时巴黎的科学院院长、物理学家和数学家梅朗先生写了三封信,回答了他有关中国历史、天文和文化的问题。
巴多明神父知识渊博,观察问题敏锐、清晰,他以一个异域人的眼光观察中国,对中国人和欧洲人的不同思想心态作了比较研究。巴多明认为欧洲人总是处于“焦躁不安”的状态,这使得他们在科学上不断进取。而中国人有一种惰性,保守、实际、固步自封,因此科举研究就不能有发展。此外,当时中国的体制促使中国知识分子主要靠文章谋取仕途晋升,实用科学得不到应有的地位,这也是中国的科学研究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巴多明认为:“阻碍科学进步的因素就是钦天监内外都缺乏竞争。如果中国在它的周围是个重视科学的独立的王国,如果中国文人们能指出中国人在天文学方面的错误的话,那么他们也许会从昏睡状态中清醒过来,皇帝们也会比较积极地推动科学进步。”他又说:“(钦天监)内没有竞争,或者有竞争存在但是不易察觉。我已经说过,那是因为天文学研究根本不是获取财富和荣誉的途径。谋取好职位的最好途径是研究经书、历史、礼法和思想,就是要学习他们所说的‘文章’,也就是说文章要好,辞必达意,切合主题,通过这个途径可以当博士,当了博士就能受人尊敬,得到俸禄,生活马上改观,因为他马上就可以当官。即使那些侯补官员回到乡里也很受地方官员的尊敬,他们的家属也受庇荫,他们享有好些特权。”
伏尔泰读了巴多明的通信后,在《风俗论》中讨论了中国停滞不前之谜:“人们要问为什么有那么悠久历史的中国总是停滞不前;为什么在他们国家天文学又古老又狭窄,好象自然之神对于这个和我们大不相同的人种一下子给了他们完善的器官来找到一切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可是后来又不能再向前超越了。而我们正相反,我们开蒙很晚,而我们又迅速地完善了……如果要探究为什么长久以来那么多艺术和科学在中国一直被精雕细刻,然而进步很缓慢,可能有两点原因:一点是因为这些中国人异常尊重前辈留下的东西,一切古老的东西在他们眼里都完美无缺的;另一点是因为他们的语言的特性,他们把语言放在一切知识之上。”(第一章)
三、文化戒备心理是文化交流的障碍
耶稣会士们为中国皇帝服务最终目的是为了传教。因而,传教士们对与他们教理相悖的事情是很敏感的。他们时刻都有一种文化戒备心理。乾隆朝时,汪宏达神父在一七六九年九月十五日写往巴黎的信中叙述了一件事:“我们在宫中干活很平静,我们手下有一些人听使唤,没有人要我们操心。我们在异教徒官员们面前无所顾忌地做祷告。您瞧,我们是多么自由地做我们教会的日课,皇帝对我也睁一眼闭一眼。有一次,他们想把一只铁瓶涂上兰色。他们问我是否能做这件事。我不知道这种瓶的用途,我起先回答可以试试。可是后来我听说这种瓶是作迷信用途的。了解此种瓶的用途的官员想瞒我。于是我找到他们,笑着对他们说:‘你们要我涂这只瓶的时候没有告诉我它和我们的圣理不相符合的用途。因此,我绝对不能做这件事。’官员们笑了起来,他们并不勉强我,他们显得对他们的上帝并不很在意。”
类似的事件在康熙朝时也发生过。当时在皇太子那里照管数学仪器的陆伯嘉教士旨令把一些铁瓶涂成兰色,神父们以为这些瓶是偶像崇拜的器皿,或是某些超人使用的法器。他们和皇太子顶撞得很厉害,皇太子发了怒,充当翻译的白晋神父甚至被囚禁了一夜。其实,据皇太子说,那是他自己使用的东西,他一再说明这种瓶根本不是偶像,白晋神父才磕头谢罪。
其实中国人有中国的文化传统,无论康熙朝时的白晋神父,还是乾隆朝时的汪宏达神父大可不必如此大惊小怪、大动干戈。他们可以着意了解有关的文化知识,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再作表达不迟。相对地说中国人就比较轻松自如得多,他们只是一笑了之,并不要求传教士们勉为其难,还让他们无所顾忌地祷告上帝、做日课。“(中国人)对他们自己的上帝并不很在意”,中国人本来宗教观念就比欧洲人淡薄得多。耶稣会士的这种文化戒备心理,往往会引起文化上的误会,甚至冲撞,成了他们接受异族文化的障碍。
文化交流是双向的。耶稣会士到了中国,他们的音容笑貌、衣着谈吐、随带物品、基督教义向中国人民展示了一个崭新的西方文化存在,同时他们身处与西方文化迥异的东方文明古国的文化氛围中也产生了一种文化震惊。他们在学习、接受中国文化的同时,渐渐改变了自我文化形象,也改变了他们固有的文化观念。这种改变的过程也是中西文化作用与反作用的过程,是两种相距甚远的文化冲撞与交融的过程。他们身兼中西文化的传播者和接受者,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作了大量意义重大的工作。正如莱布尼兹所指出:“其中的伟大意义超越了我们所能想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