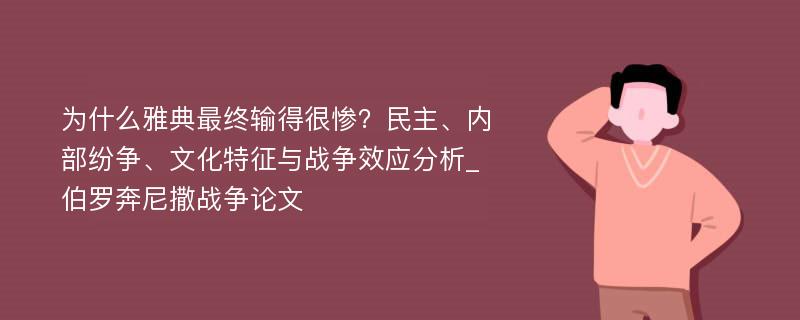
雅典为何终告惨败?——关于民主、内争、文化特质和战争效应的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雅典论文,特质论文,效应论文,民主论文,战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公元前5世纪发生于古希腊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古典时代一场决定性的国际大冲突。它历经27年,以雅典近乎毁灭性的失败而告终。作为同时代人的史学家修昔底德对这场漫长和惨烈的战争做了深刻的悲剧式的探究、思考和总结,自觉地从中探寻后世可以借鉴的深层历史经验。然而,修昔底德尽管关注甚而在不同程度上揭示了其中的所有基本动能和方面(但他未像对待军事和政治那般引人注目地凸显出比军事和政治更深刻、甚至更具终极决定性质的要素;与此同时,他的“让事实本身说话”的古典史述和史论方式也增加了后人从中“读出”这些根本要素的困难)。不仅如此,修昔底德的史书是一部不完整的著作,只记述到战争第20年的夏季便戛然而止。
关于战争的最后阶段,即雅典的西西里远征军于公元前413年覆灭往后至战争结束,修昔底德有一句概括性的论断:“他们大部分的舰队和其他军队在西西里丧失之后,雅典内部已经发生革命,但是他们还支持了8年,以对抗他们原来的敌人(这些敌人已经有了西西里人的增援);对抗他们自己的同盟国(它们大部分已经暴动);对抗波斯王子居鲁士(他后来帮助伯罗奔尼撒方面,以金钱借给伯罗奔尼撒人建造舰队)。结果只是因为他们自己内部的斗争,毁灭了他们自己,他们最后才被迫投降。”① 修昔底德的这一论断一直引发后世探究的兴趣。毁灭雅典人、迫使他们最后投降的“他们自己内部的斗争”是什么?自古以来,最为流行的观点是雅典在根本上败于其民主政治,或者败于这一民主政治在其最后阶段的巨大混乱和严重失控。一些史学家还最为重视雅典民主制城邦的政治家、国务家个人的素质和行为方式,将雅典的失败特别归咎于这类无疑确实至关重要的因素。然而,所有这些关于雅典失败的解说都有其局限性,都在事实上留下了未经提出的重大问题和未能给予的重大答案。
一 民主政治与战争后期的雅典
“贯穿大部西方历史,雅典民主政治本身一直臭名昭著。”②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最后阶段,雅典民主政治的混乱、失控与其种种军事后果是雅典终告惨败的重要原因,也是两千多年来雅典民主政治为世人所诟病的缘由之一。修昔底德本人对民主政治也颇有微词,他总是将雅典公民大众描述为缺乏足够的理智和易受情绪驱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最早英译者、现代政治思想的创始人之一霍布斯就此断言:“关于城邦的政体,修昔底德显然最不喜欢民主政治。”③
雅典民主政治(无论其体制或其运作)有重大的局限性,蕴涵着促使雅典人以某种远非健全的方式操作其战争的巨大可能性,并且确实由于经久的战争重压而成了雅典最终惨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如果仔细阅读历史文本,就可以发现没有确凿的理由认定民主政治必然导致雅典战败。不仅如此,甚至还可以发现即使在雅典极为困难的岁月里,民主政治就战争操作而言仍屡有非凡的表现。
西西里远征覆没后,雅典政局持续动荡,内争激烈,人心动摇,财政匮乏,兵力短缺。然而总的来看,民主政治中的雅典公民大众保持着热烈的爱国激情,民主派具备非同小可的应变素质,由此赋予内外交困中的雅典引人瞩目的振兴能力,而寡头派却总是倾向于出卖祖国。在危难之中,雅典的民主政治表现了非凡的创新能力。修昔底德写道:“和一切民主政治的政府一样,因为他们恐慌了,他们准备把一切事情都整顿好。”④ 公民大会以民主方式议决雅典的10个部落各推选一名贤哲(probouloi)组成一个团体,其职责在于为城邦提供建议和指导。在这10人中间,经考证已知的有西西里远征军统帅之一尼西阿斯之子哈格农和伟大的悲剧作家索福克里斯,他俩都曾跟随伯里克利多年,富有政治和军事经验。⑤ 当代研究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权威、耶鲁大学古典史教授唐纳德·卡根高度赞扬了雅典民主政治的这一举措,认为这个团体忠诚和有效地领导了抗击斯巴达的战争。到公元前411年的寡头政变为止,它从未采取任何与民主政治相悖的措施。“西西里之后,已经没有伯里克利和尼西阿斯之类人物为此时的雅典提供急需的审慎温和的领导,因此,事实上这个团体体现了伯里克利式的温和特征。”⑥ 依靠经民主产生的这一审慎克制和富有成效的领导,雅典度过了西西里惨败后初期的严重危机,基本上平定了帝国范围内的叛乱,并且在海洋上再次显示了雅典的优势。
雅典寡头派的表现与此截然相反。修昔底德揭示了寡头派的政变动机,指出这些最有势力的阶级的成员之所以图谋夺取政权,是因为急欲以任何方式结束这场使其财产大受损失的战争。寡头派以恐怖手段发动政变,其可怕程度不亚于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被大书特书的雅典瘟疫以及科西拉城邦因内战而来的社会急剧蜕变:“会议中发言的都是寡头党的人……人民看见他们就害怕了,没有人敢说反对他们的话。如果有人真的敢说反对他们的话,他们就马上用适当的方法把他们杀死……人民默然无言……”⑦ 政变成功后,寡头派对内实行暴力统治(即“四百人议事会”统治),对外急于同斯巴达商谈和约,结束战争。在雅典发生党争时,修昔底德告诉我们,寡头分子希望首先保全寡头政治,其次要占据海军要塞以“保全独立”,而如果这也做不到的话,他们“不愿意自己成为民主政治恢复后第一批被杀戮的人,宁愿招请敌人来,把舰队和要塞交出,根据任何条件订立和约,只要保全他们的性命,不管雅典的将来如何”。⑧
与寡头派的政变及其叛卖行为成鲜明对照的是驻萨摩斯岛的雅典海军民主派对政变的反应。民主派舰长色雷西布拉斯和色雷西拉斯两人说服所有士兵(特别是寡头派的士兵)严肃发誓,保证遵守民主宪法,团结一致,尽力对斯巴达继续战争。萨摩斯驻军由此成为坚固的民主堡垒,这对雅典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因为这支舰队构成当时雅典全部的海上力量,从而是雅典安全的根本屏障。它对斯巴达海军的两度胜利——公元前411年在塞诺西马和翌年在塞西卡斯——不仅振奋了连遭灾难备感沮丧的雅典人,也直接促成了雅典民主政治的恢复。
可见,雅典民主政治即使在政局严重动荡中仍有其一定的精神活力和取胜能力,它本质上并非必然导致战败的根本祸因。柏拉图等古典作家对雅典民主制的责难包含着强烈的偏见,甚至修昔底德本人对伯里克利之后雅典民主制运作的批评也不无偏颇。20世纪以来,人们逐渐抛开对雅典民主制的偏见和鄙薄。1972年,英国著名的古典学家芬利爵士将雅典描绘为不仅文化上最为杰出、而且内部最为和平的古希腊城邦;10余年后,两位著名的美国古典学家也认为,总的来说“雅典的政治社会非常稳定”。⑨
然而,正如修昔底德所说,“战争是一位严厉的教师”。⑩ 在一场用我们当代话语来说是持久的总体战性质的战争中,任何国内体制,无论其原本的素质如何,都必定经受其无情的折磨,发生在其经久的重压下殊难避免的畸变。雅典如此,斯巴达也如此。后者的社会和精神同样在长期的战争中蜕变败坏,战胜雅典后仅35年便彻底崩溃。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最后阶段,雅典民主政治尽管有上述部分优良表现,但它们远不足以掩盖参与导致雅典最终失败的那些政治上的混乱、失控和愚蠢。问题在于,在雅典民主制后期运行中的这些混乱、失控和愚蠢是如何发生的?
二 内争和政治领导素质的蜕变
修昔底德认为内争是雅典失败的主要原因,而内争又被他非常明确地首先归咎于伯里克利死后雅典政治领导个人素质的蜕变。(11) 自修昔底德以降,关于雅典的几乎所有论说者都至少在相当大程度上赞同修昔底德的这一论断。主要的差异在于,卡根等现代研究者指出并批评了修昔底德多少过分地赞颂了伯里克利,淡化乃至掩饰了伯里克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一事上的重大责任;他们还不太赞同修昔底德对伯里克利死后“对人民影响最大”(12) 的克里昂的过分贬抑,并且指出修昔底德多少掩饰了克里昂的主要政治对手尼西阿斯等的不良素质和严重过错,他们对雅典西西里远征的发起及其惨败负有巨大责任。(13)
在战争的最后阶段,雅典主要领导个人素质的蜕变和雅典的内争交互恶化到空前严重的地步。不仅如此,本文第三部分将着重论说的文化特质以及城邦政治和社会心理的病变与这两者紧密交织,互为因果。政局混乱多变,其间有如前所述的寡头政变、暴力统治和贵族卖国行径,连同异常复杂和波动的党争、政变和反政变。这些重大事态有些不见于修昔底德的未完成的史书,而后人根据各种资料提供了大体完整的画卷,其中卡根的探索尤为杰出。在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晚期史中,(14) 尤为突出和关键的是“独特的人物”亚西比得。“围绕雅典人生活中这个独特的人物产生了种种个人竞争、派系争斗和普遍的不信任,这危害了他的城邦,并且与雅典的失败有巨大的关联。”(15) 在这一点上,卡根的看法与修昔底德和普鲁塔克等古典作家大体一致。(16)
亚西比得具备了雅典人因其深层文化传统而倾慕的所有个人特质:年轻、英俊、才气不凡、生机勃勃、出身高贵、能言善辩。不仅如此,他还是在古希腊人眼中比得胜的将军还荣耀的奥林匹克赛车冠军,并且连获殊荣。更有甚者,他少时的监护人是伯里克利。他从小在伯里克利身边长大,习染了娴熟的政治技能。因他的家世和才能,他周围的人都盼望他获得举世的荣耀,由此助长了他无穷的政治野心,包括意欲在个人成就和声誉上超过伯里克利。(17)
一旦克里昂战死,亚西比得的势力便开始崛起。他很快成为民众领袖,挑战尼西阿斯为首的温和派。在亚西比得身上,“向善和向恶的两种倾向同时并存”。(18) 在他看来,导致战争暂停的《尼西阿斯和约》(公元前421年)仅以其政敌的名义签订这一点就足以决定他不足信赖。缔约次年,他被选为雅典十将军之一,随即便暗中策动,力图重新开战。据普鲁塔克说,使雅典人蒙耻的弥罗斯屠杀的主使就是亚西比得。紧接着,他又煽起了远征西西里的狂潮。然而,他平时毫无道德顾忌的生活使他失去了人们的信任,并且易招政敌的攻击,结果远征前夕他被指控有亵神嫌疑,不得不从他统兵所在的西西里逃亡斯巴达。这位背叛自己城邦的雅典叛徒由其“向恶”的一面驱使,为个人私利替斯巴达人出谋划策,为祸祖国。他毫不掩饰自私的目的:“我所爱的雅典不是那个现在迫害我的雅典,而是那个我常在其中安享公民权利的雅典。……我要努力恢复我过去的国家。真正爱国的人不是那个当他非正义地被放逐的时候还不攻击它的人……”(19)
到战争的第20年,终于有了这样的时机。同行的斯巴达军官阵亡和米利都战役之后,斯巴达人认为亚西比得可疑,下令将他处死。(20) 亚西比得难以在斯巴达和雅典容身,因而在惊慌中出逃,投奔小亚细亚的波斯总督替萨斐尼。从修昔底德的史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此后雅典政局的急剧动荡首先出自亚西比得这一分裂性人物。他利用替萨斐尼的影响蒙蔽雅典人,同时又利用自己在雅典人中的影响欺骗替萨斐尼。他写信给驻萨摩斯的雅典军队:倘若贵族政治取代那个放逐他的腐败的民主政治,他就准备回国,和他的同胞一起尽自己责任,办法是先后获得替萨斐尼和波斯国王的友谊,使其供给雅典急需的金钱。正如颇有远见的雅典将军福里尼卡斯指出的那样,对亚西比得来说,无论寡头政治或民主政治都无关紧要,他要求的只是改变现行宪法,以便他的朋友们可以召他回去。(21)
然而,雅典在战争灾难和困窘的重压之下,外交技巧和军事才能兼具的亚西比得越来越被视为可能的救主。在参与指挥并取得辉煌胜利的塞西卡斯海战之后,亚西比得于公元前407年在全城的欢迎和歌颂中回到雅典。雅典人选举他为首席大将军,统领海陆两军,其影响和权力达到顶峰。(22) 他的罪恶已被遗忘,人们记得的只是他的天才。可是,资金的匮乏和肆无忌惮的个性再度毁了他。公元前406年3月在诺丁姆,面对敌军主力,他将舰队交给一个急于表现自己的领航员,自己则率领少数舰只,欲以正当性大成问题的手段为舰队筹措银两。(23) 机敏的斯巴达统帅来山得抓住机会,大败雅典舰队。噩耗传到雅典,亚西比得的敌人立即得势。被操纵的公民大会剥夺了亚西比得的指挥权,这位“最能干最有才能的将军”再度耻辱逃亡。(24) 普鲁塔克就雅典人对亚西比得的看法评论道:亚西比得被相信具有莫大的聪明才智和冒险精神,如果他努力了,他就无事不能;如果他失败了,原因就必定是他没有尽心尽力。(25) 雅典人所以给他超乎寻常的权力,就是因为期望他能创造奇迹。
卡根认为,从政治角度看,亚西比得是城邦的负担,一个制造分裂的人物。他能引起人们强烈的赞美和同样强烈的厌恶,而不能获得多数公民的稳定的支持;他不能赢得多数人支持他的政策,却能阻止其他人赢得如此的支持;情势恶化时,雅典人常常指望他的魅力和许诺来获救。亚西比得流亡不到一年,大喜剧家阿里斯托芬在他的剧作《蛙》里写道:“人们念颂他,怨恨他,又盼望他回来。”(26)
公元前406年,雅典倾其所有而建立起来的大舰队在阿吉纽斯击溃斯巴达舰队。胜利再度冲昏雅典人的头脑,因而斯巴达的求和再遭拒绝。但是,当公民大会获悉雅典将领没有营救25艘被敌击沉的战舰上的官兵以致其溺毙时,群情激愤。冲动的人们相信这些淹死者得不到适当的埋葬,其魂灵将永不安宁,四处游荡。他们控诉归来的官兵未尽救援责任,要求将凯旋的将领全部处死。此项提案获得通过,随即死刑的执行与其判决一样匆忙草率。几天后,雅典人感到后悔,公民大会遂将煽动处死将军的人判处死刑。这件事情“对法律、公正和雅典民主的应有程序的违背令人吃惊”,(27) 也成为后人用来诟病雅典民主的一大证据。这番审判和死刑不仅减少了雅典需要的军事将领,而且在最需要团结和互相信任的时候分裂了雅典人。不仅如此,其后果一直延至公元前405年决定性的伊哥斯波塔米战役,(28) 雅典在其中败北的主因之一就在于“审判将军导致的猜疑和胆怯”。(29) “亚西比得不是军事天才,只是二流的有才能的军人,而自信和野心远远超过了他的才能。况且,他作为军人所做的贡献也毁于他在雅典政治中扮演的分裂角色。”(30) 亚西比得耻辱的逃亡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牵累了他的朋友和同伴,而这些人的军事和政治才能正是雅典此时迫切需要的。战争的最后两年里,富有海战经验和战功卓著的色雷西布拉斯和特拉门尼不在将军之列,也未指挥阿吉纽斯和伊哥斯波塔米战役。“雅典的生存希望大概在于色雷西布拉斯和特拉门尼的联合领导,是亚西比得的耻辱剥夺了他们的领导职务。”(31)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亚西比得及其引起的“内部斗争”导致了雅典战败。
三 深层文化特质与雅典的惨败
修昔底德的史书对政治、社会和战争做出了杰出的探究和反思。然而,他也许太专注于政治和战争这两项最“高层”的集体行为,以致他虽然屡屡涉及甚或透视到公元前5世纪雅典乃至整个希腊世界的社会、文化特质连同它们与战争的深刻互动,但毕竟未像对待政治与战争那样,格外突出地呈现它们,足够清晰地让后人(也许也让他自己)洞察这类实际上更具终极决定性的要素。而且,作为同时代人,他也无法免除“当代史研究难以消除的‘天然’缺陷”,包括观察的局限性和观察者本人情感及利害关系造成的扭曲效应,还有视距过近难免引起的视野过窄问题,(32) 虽然在尽可能大的程度上克服这类缺陷方面,他属于古代作家中做得最好的。与他相比,我们可以有更好的条件来“读出”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更深层的历史大力量。
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最后阶段雅典失败的因果判断无疑是正确的。雅典的失败首先是出于其内部政治在伯里克利之后愈演愈烈的混乱和失控,出于主要围绕亚西比得这一人物而引起和加剧的内争。西西里远征惨败是雅典命运的转折点,而倘若雅典有统一和并非自私的政治领导,远征根本不会被鼓动起来。不仅如此,即使在西西里惨败之后,雅典在其擅长的海战方面仍然足够强大,大可维持自身独立并保有帝国的主体部分。然而,事实证明无可挽救的是政治局势的严重动荡和国务运作的摇摆不定。这些连同少有节制的内争和自私短视的领导使雅典输掉了战争。
然而,以更开阔的视野和更锐利的目光审视,我们可以察觉,雅典的失败从根本上说是在一种更深层的意义上的失败,其根本的败因是植根于雅典社会本身的某些深层文化特质以及政治社会在经久的战争重压之下的脆弱性。
伯罗奔尼撒战争剧烈并持久地搅动了整个希腊世界,逐渐颠覆了城邦内部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心理。这场战争对城邦内部社会的破坏从雅典战时爆发瘟疫的可怕精神后果可见端倪,在科西拉内战招致的社会道德沦丧中显露无遗。(33) 修昔底德就此写道:“就是在有法律的地方,人性总是易于犯法的;现在因为文明生活的通常习惯都在混乱中,人性很傲慢地现出它的本色,成为一种不可控制的情欲,不受正义的支配,敌视一切胜过它本身的东西。”(34) 从雅典瘟疫、科西拉内战、西西里远征最后阶段和雅典寡头政变导致的混乱状态中,修昔底德由关于人性的悲观主义信念相助,察觉到了在持久的战争重压和侵蚀下城邦社会解体的必然性。
因此,雅典的问题不只在于它的民主政治中自私的领导和严重的内争,而且在于(从根本上说)“希腊政治文化不能经受得住一代人那么长的战争的压力”。(35) 以前,希腊城邦之间的冲突大多经过一场短暂的战役就得到解决,但现在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经过27年和无数战役才终定胜负。像其他城邦国家一样,同质和单一的雅典社会因其规模狭小而相对脆弱。雅典不可能进行27年战争而不遭受社会基础的可怕裂变和社会精神的严重病变。没有任何城邦能够这样,包括斯巴达和后来的罗马。斯巴达是寡头政体并赢得了战争,但它的社会基础和精神同样败坏于长期战争,以致胜利仅35年后便彻底崩溃。罗马共和国也是寡头政体,在其长期的对外战争中虽然相当成功,但也必定付出政治变更代价:罗马共和政体经百年内战而终告倾覆。
植根于希腊文化传统和城邦生活经验最深层的是由荷马咏颂并由赛会竞技加强的一种追求——希腊人对荣耀或卓越的追求,亦即对同侪赞誉和后人称颂的追求。希腊文化中浪漫的英雄是极端个人主义的,其行为准则是个人荣耀。因而,在承受巨大压力的时候,希腊人倾向于置私利于公益之上。这一倾向可以回溯至《伊利亚特》中的年轻英雄阿基琉斯,一个既伟大又极端自私的勇士,为了一己之得失而不顾万千士卒丧命黄泉。而且,一旦立意追逐某项私利,固执和要面子就促使他难归正途。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希腊文化中的这种倾向在每个雅典政治领导人身上——从伯里克利、克里昂到尼西阿斯和亚西比得——都有体现,只是程度不同。伯里克利至死都不承认无数雅典人因他的战争决定而殒命;克里昂热衷于战争和蛊惑进攻,因为这至少有助于他的民望;尼西阿斯小心翼翼,竭力避免战争或大力进取的征伐,以便至少保全他“常胜”和节制的美名;(36) 至于亚西比得,如同特洛伊战场上的烈马、当代的阿基琉斯和人们渴望因之获取救赎的英雄,则是上述倾向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的头号典型。
两位美国学者将这种倾向称为“亚西比得综合症”:一方面是非凡的才能——雄心、魅力和高超的说服能力;另一方面则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将与永恒的个人荣耀紧密相连的政治权势定为生活的最终目标,友谊、教育、竞技、政治和战争等等都从属于这一目的。(37) 随着战争的延宕,“亚西比得综合症”从个人扩散到近乎整个社会,私利差不多普遍优先于公益,个人争夺和派系争斗泛滥成灾。雅典的政治文化已在战争重压下被彻底污染,拒负责任和寻找替罪羊已成当下之风,处死将军、出卖同伴和背叛城邦乃习以为常。在最后输掉战争之前,雅典政治文化的蜕变已使战败难以避免。
与此密切相关,我们还必须指出,雅典文化中独异于希腊的是其空前的“傲慢(hubris)”,那在古希腊的含义是逾越人类的界限,最后必然招致神的惩罚。用伯里克利的话说“我们的冒险精神冲进了每个海洋和每个陆地”;(38) 用科林斯人敦促斯巴达对雅典开战时的话说,躁动不安、立新求异和渴求进取的雅典人“和你们多么不同”!(39)
雅典人有着“亚西比得综合症”的基因,民主制和帝国可以说为之提供了近乎独特的温床和到头来发作的很大部分诱因。伯里克利在世时实行有所节制的内外政策并提供了一心为公的楷模,但在他的教诲和鼓舞下,崇奉雅典伟大辉煌的雅典人到头来逾越了界限。到发动西西里远征时,雅典人的征服欲望已经少有限界,或用亚西比得的煽惑之辞说,“我们已达到了一个阶段,我们不得不计划征服新的地方,不得不保持我们所已经取得的,因为如果别人不是在我们统治之下,我们自己有陷入被别人统治的危险”。(40) 与此同时,他们中有太多的人在城邦内部政治生活中变得太自大、太贪婪,往往由赤裸裸的权势欲驱动。可以说,到战争末期,雅典人大致已变得和亚西比得一样自私、不稳定、易背叛。研究修昔底德的权威、美国著名学者罗伯特·科纳评论道:“冒险和革新是雅典成长的关键,但也是它过度伸展和惨败的诱因。(41)
“衰落是修昔底德著作的主题。”(42) 曾经辉煌的民主雅典,连同其内部政治领导,在旷日持久的大战中经历了病变、蜕化和覆灭的过程。雅典终告惨败的一大根本原因是长达一代人的战争,是这格外漫长的战争给雅典社会、其政治机体和国民性格施加了难以承受的经久压力,它撕裂了愈益脆弱的社会纽带,侵蚀掉雅典赖以打赢战争的内在活力,将雅典深层文化特质中的病因恶化到空前程度。修昔底德如此悲叹雅典的陨落:“我的年龄相当大了,我了解事物发展的意义。”(43) 无限惨痛,尽在其中。
注释:
① [古希腊]修昔底德著,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70~171页。
② Jennifer Tolbert Roberts,Athens on Trial:The Antidemocratic Traditional in Western Thought,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p.1.
③ Thomas Hobbes,“On the Life and History of Thucydides,”该文1628年11月15日发表于伦敦,为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英译本的序言。
④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637~638页。
⑤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637页;Donald Kagan,The Fall of the Athenian Empire,Ithaca,N.Y.:Cornel University Press,1997,pp.5—6。
⑥ Donald Kagan,The Fall of the Athenian Empire,P.7.
⑦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683页。
⑧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704~705页。
⑨ 转引自Jennifer Tolbert Roberts,Athens on Trial:The Antidemocratic Tradition in Western Thought,p.306。
⑩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268页。
(11)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70~171页。
(12)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231页。
(13) 主要见Donald Kagan,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9; Donald Kagan,The Peace of Nicias and the Sicilian Expedition,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1.
(14) Donald Kagan,The Fall of the Athenian Empire,1997.
(15) Donald Kagan,The Fall of the Athenian Empire,pp.321—322.
(16) 特别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六和第八卷;Plutarch,Alcibiades,http://www.classics.mit.edu/Plutarch/alcibiad.html.
(17)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六和第八卷;Plutarch,Alcibiades,http://www.classics.mit.edu/Plutarch/alcibiad.html.
(18) [古罗马]普鲁塔克著,陆永庭等译:《希腊罗马名人传》,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548~549页。
(19)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549页。
(20) 普鲁塔克认为,实际上最主要的原因是亚西比得炫耀他与斯巴达王后所生之子,毫不掩饰地说他的后代有望成为斯巴达王,从而引起当时的斯巴达王阿基斯的无比耻辱和仇恨。见Plutarch,Alcibiades,http://www.classics.mit.edu/Plutarch/alcibiad.html.
(21)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671页。
(22) N.G.L.Hammond,A History of Greece to 322 B.C.,3rd edi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413.
(23) 详见Plutarch,Alcibiades; http://www.classics.mit.edu/Plutarch/alcibiad.html; Donald Kagan,The Fall of the Athenian Empire,pp.312—315.
(24) Donald Kagan,The Fall of the Athenian Empire,pp.321—322.
(25) Plutarch,Alcibiades,http://www.classics.mit.edu/Plutarch/alcibiad.html.
(26) Donald Kagan,The Fall of the Athenian Empire,p.324.
(27) Donald Kagan,The Fall of the Athenian Empire,p.374; Hammond,A History of Greece to 322B.C.,p.416.
(28) 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最后战役导致雅典全部180艘战舰仅剩逃走的10艘,3500名雅典人被杀。翌年,雅典在被围3个月后最终投降。
(29) Donald Kagan,The Fall of the Athenian Empire,p.382.
(30) Donald Kagan,The Fall of the Athenian Empire,p.420.
(31) Donald Kagan,The Fall of the Athenian Empire,p.421.
(32) 时殷弘:《国际政治——理论探究、历史概观、战略思考》,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274~275页。
(33)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二卷第五章和第三卷第五章。
(34)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271页。
(35) Barry S.Strauss and Josiah Ober,The Anatomy of Error:Ancient Military Disasters and Their Lessons for Modern Strategists,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0,p.50.
(36)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第500、549、539页。
(37) Barry S.Strauss and Josiah Ober,The Anatomy of Error,P.71.
(38)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51页。
(39)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55页。
(40)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492页。
(41) W.Robert Connor,Thucydide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pp.246~247.
(42) Gregory Crane,Thucydides and the Ancient Simplicity:The Limits of Political Realism,Berkeley,Calif.: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http://www.ark.Cdlib.org/ark:/13030/ft767nb497.
(43)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420页。
标签:伯罗奔尼撒战争论文; 雅典论文; 伯里克利论文; 修昔底德论文; 斯巴达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战争论文; 政治论文; 斯巴达教育论文; 政治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