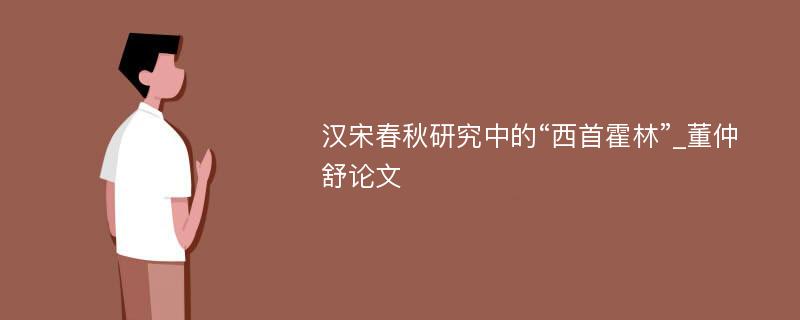
汉、宋《春秋》学中的“西狩获麟”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春秋论文,学中论文,西狩获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79(2014)02-0042-06 《春秋》学史上的“西狩获麟”为人所熟知,同时,《春秋》为何断限于此的问题,自西汉发端且延续到宋代,未能获得一致见解。难怪连朱熹也说“《春秋》获麟,某不敢指定是书成感麟,亦不敢指定是感麟作,大概出非其时,被人杀了,是不祥。”①由于历来的传、注、疏作者们都乐于阐发《春秋》微言大义,因此极其重视《春秋》一字一句,《春秋》断限问题自然也被纳入学者的视野中。他们思考的是:倘使西狩获麟为孔子有意的“结束”,则其意义为何?以及此一结束又与传统以来被认为是太平之瑞的“麟”有着什么样的关系?这些,都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 一、西狩获麟与黜周王鲁 如所周知,麟在古代被视为仁兽,乃圣王嘉瑞,只有当太平之世,随着圣王出现或喜庆祥瑞之时才现于世②。时无明王而遇获麟,孔子伤周道之不兴,感嘉瑞之无应,故曰:“丘犹麟也!麟之出,因不遇明王而遭害;丘生不逢时,不遇明王,故吾道难行于世,而终至于穷矣!”纵观《公羊传》全文,是认为麒麟出现乃嘉瑞之兆,而此次出现在周道不兴之时,孔子因此感伤自己未遇明主而道难行于世,故有意绝笔于获麟。 至西汉初年,公羊学名家董仲舒以为“西狩获麟”是孔子的“受命之符”,孔子于受命之后乃作《春秋》以“明改制之义”(《春秋繁露·符瑞》)。因此,他认为“西狩获麟”是《春秋》撰作的动机,即《春秋》乃孔子“感麟而作”,孔子以麟至,制《春秋》以应嘉瑞,正是要显示他禀受天命继承商、周二统之后所要建立的新王之道:“故《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黑,绌夏,亲周,故宋。”(《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然则,孔子受命而未王,必待后圣继起以为拟鲁之新王,以行《春秋》之道③。孔子作《春秋》有这样神圣的缘起,西汉统治者便不能不加以尊重。但孔子有德无位,只能成就“素王”功业,历史上真正继承周朝的是汉朝,汉代统治者为了证明刘汉的兴起符合天命所归的趋势,具有统治的正当性,他们就必须虚心接纳《春秋》实现新王之道的理论。因此实质上,董仲舒关于“西狩获麟”的论述,关注的焦点并非是《春秋》“起笔”与“绝笔”时限,而在于其所点明的“受命”与“改制”含义,后一点得到了汉儒的充分发挥。董仲舒本人就说:“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汉书·董仲舒传》)此处,董仲舒将孔子作《春秋》与“素王”联系起来,而据前所述,《春秋》又是孔子“感麟而作”,因此,“获麟——《春秋》——素王”便成了一个有机的体系。 但是,董子虽言西狩获麟为孔子受命之符,却并非认为孔子即为新受命之王,而指孔子受命作《春秋》之义,这样,西狩获麟之后受命而王的具体对象便是《春秋》,孔子于《春秋》中加之“王心”使之成为“天子之事”,具体而言“《春秋》作新王之事”。这里,董仲舒所指的新王是具有“上通五帝,下极三王,以通百王之道,而随天之始终”的圣王,此绝非人力所能致,而是来自上天的受命。然而“新王”虽获麟受命,但董仲舒的说法中却始终在孔子与素王之间留下了空间,即不明言孔子为受命之王,而反复强调“《春秋》当新王”、“见素王之文”:这是因为孔子即便获麟受天之命,依旧没有成为王者,故圣人王者之行仅能从《春秋》来展现,即孔子所谓“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而东汉何休在继承董仲舒之说的基础上,不但将“黜周王鲁”之说系统化,更赤裸裸地援引谶纬之说来宣称西狩获麟乃预言汉室将兴。《春秋》西狩获麟,《公羊传》只言“记异”,而何休《解诂》则附会孔子已知周室既衰,刘季当兴,而为之“豫位”。何休此说除了在加强西狩获麟与孔子作《春秋》的意义之间的联系外,并无可取之处。因为,且不论孔子有无彼意,只从汉代灭亡本身便可知讨论《春秋》为汉制法之说已经毫无意义。 至宋代,汉代的《春秋》为素王、《春秋》“新王”说以及“黜周王鲁”说等遭到严厉批判。公羊家创造的“新王”与“王鲁”说④,是在周天子尚存的情况下,就设计出一个新的“王”来取而代之,实与《春秋》为王见义之旨相悖,故被视为“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在宋儒看来,《公羊》家主张“黜周王鲁”之说,实际是未能把握夫子作经之旨。如欧阳修在其著名的《正统论》一文中曾说:“仲尼以为,周平虽始衰之王,而正统在周也,乃作《春秋》,自平王以下,常以推尊周室,明正统之所在……刺讥褒贬,一以周法,凡其用意,无不在于尊周。而后之学者不晓其旨,遂曰黜周而王鲁。”[1]P8欧阳修以当时的“正统”观念否定“黜周王鲁”的诬枉,虽然有后人勉强前人之处,但亦反映了当时《春秋》学多以“借事明义”阐发见解的趋势。北宋末期的李如篪分析得更为详细:“孔子只是思得明王,以行所蕴,既终不可得,于是作《春秋》,见诸行事,以明己志耳,岂可以匹夫欲以天子之事为己任哉!”[2]P3其意谓先儒不明孔子作经之旨,才会得出黜周王鲁、孔子素王等妄说。孙觉也反驳何休之“黜周王鲁”:“如经书‘王正月’者,大一统也:先王人者,卑诸侯也;不书王战者,以见天下莫之敌也;书‘王’而加‘天’者,别吴、楚之僭伪也。《春秋》尊王如此,安得谓之黜周乎?”[3]序正是由于周王不振,王室衰微,孔子才作《春秋》以冀恢复王道盛世。且如上述所言,孔子本人也志在兴周,又怎么会黜周而王鲁呢?因此何休之说实乃谬误。 刘敞认为以“《春秋》当新王”之说与《春秋》“达王义”的性质相悖,有厚诬圣人之嫌:“《公羊》谓《春秋》以隐公当新王也。有王者作,方治内之时而忘恩于其卿佐乎?故事在可以然之域则归之三世,在不可以然之域则致之新王,使其言如循环而不可训,以迷世罔民也,此学者之祸也。”[4]卷八“新王”说是错误的,因为在刘敞看来“圣人作《春秋》,本欲见褒贬是非,达王义而已。王义苟达,虽不新周,虽不故宋,虽不当新王,犹是《春秋》也。”[4]卷八显然,刘敞认为孔子作《春秋》本意是要凸显历史人物与事件的善恶并且加以褒贬、发扬王者的义理教化正道,倘若得以行之,即使不“新周、故宋、新王”,也无损于《春秋》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圣人撰《春秋》只是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以标示王道,寄寓褒贬是非之法,并非有僭越而取周王自代之意⑤。叶梦得亦不信《春秋》有假托之新王:“传虽不正言王鲁,而其说则实以鲁为王,而鲁为内,非何休之私矣。”[5]卷五《公羊传》在叶梦得看来,黜周王鲁之说也并非自何休始,对此,叶氏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春秋》本以周室微弱,诸侯僭乱,正天下之名分,以立一王之法。若周未灭而黜之,鲁诸侯而推以为王,则启天下乱臣贼子乃自《春秋》始,孰谓其诬经敢至是乎?”[6]卷一可见,“黜周王鲁”关乎孔子作经本旨,因此“不可以不察”。[7]对于公羊家以《春秋》“内鲁”为“黜周王鲁”说,程公说则对此辩道:“《春秋》所以托鲁者,约鲁史以明王法,以尊天王,正列国,训大夫,非独为鲁也,而必因鲁以见也。”[8]卷四七《春秋》本为鲁国史书,其记载史事以鲁为主亦是应当,因此,公羊学者以《春秋》多记鲁事而推论《春秋》“当新王”等说的确无法令人信服。 由上可知,宋儒皆谓孔子必无黜周之意,斥《公羊》学派“王鲁”等妄说皆何休一人所造。平心而视,宋儒之论亦有众多漏洞。如其言三科九旨为何休妄作,而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亦屡见新王、王鲁等说,徐彦《疏》引《春秋说》本即有“《春秋》设三科九旨”之语,因此,专罪何休似嫌过当。其次,宋儒断论三科九旨《公羊》本无明文,然而《公羊传》揭示的三世异辞与异内外之论,以及新周、为天下记异之例十分明显。即使《公羊传》中无王鲁之明文,但传文假鲁以言王义亦多次提及。可见,宋儒上述这些疏漏也都是十分明显的。当然,细校之下也可发现宋儒所着眼之处并非与汉儒讨论新周、王鲁等说的真实性,而是在否定汉儒本就误解了孔子本意,他们强谓夫子为周臣,不当假天命改制立法。 先讨论“获麟”与“黜周王鲁”、“《春秋》当新王”之说。西汉公羊学者刻意标举“西狩获麟”,其真实用意在于证明孔子之受命。因为自西周始,盛行的天命观主张“以德受命”,而后的大儒孔、孟、荀都继承了“以德取位”⑥的思想,若西狩获麟乃孔子受命之征,则进而孔子作《春秋》亦成为“天子之事”,这就使孔子在身份上没有了僭越嫌疑,此如王光松所论,儒家人物对孔子“有德无位”的伤感,是奠基在一种对“位”的特定理解与期待之上的。孔子为“不遇”(即“无位”)而“泣”,为“道不行”而“哀”,孔子的哀伤源自“无位”所带来的“道不行”的结果。其次,孔子受命之后便可以“为汉制法”,圣人在“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基础上,还顺应时代地提出了“改制”的主张。因为孔子见麟而叹“吾道穷矣”,既如此,则是寄厚望于所作之《春秋》,欲使后人可以从中寻求新的理想社会,这一理想社会的实践就是孔子之“志”,也因此才有了“吾志在《春秋》”之说,太史公正是因为理解孔子之“志”,所以阐述道:“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史记·太史公自序》)太史公亦一再引用董仲舒之言,阐述孔子撰述《春秋》的苦心,虽然他们还没有将《春秋》作新王专指为汉制法,但却开启了这样的论述。 因此,在汉儒的理解中,孔子生当周道徒文而无质之际,故以“《春秋》当新王”,欲以殷质之亲救周文之弊,欲拨乱世反诸正。如上文所述,宋儒多批评汉儒未能领悟圣人意旨,但宋儒自身所作的批判就合乎圣人之意么?即以反驳“黜周王鲁”等说最为激烈的刘敞为例,他曾斥何休质文改制之义道:“夫《春秋》,褒贬之本也,文质末也,车服、器械、封建、制度皆《春秋》所后言也。居周之世,食周之粟,擅易其时,岂仲尼所谓:‘非天子不制度,不议礼,不考文’者乎!此不可通之尤者,而儒者世世守之意,乃欲尊显仲尼,而不知陷于非义也。”[4]卷八这一观点在宋代具有较大的普遍性,但其中亦有两点阙漏:首先,刘敞谓《春秋》以褒贬为本,文质为末,自议论之始就抛弃了孟子以来就揭示的《春秋》文、事、义的内涵而仅存褒贬之效,他忽略了《春秋》褒贬的活水源头就是以礼为核心的“文质”。其次,对于以尊王为首要观点的宋代《春秋》学者而言,在周天子既存的前提下,又怎能以“《春秋》当新王”呢?这正是他们未能领悟汉代公羊学者苦心孤诣所在。子曰:“非天子制度,不议礼,不考文。”正因为如此,汉儒假借“西狩获麟”予夫子以受命之兆,自此之后,夫子为“素王”,《春秋》中寓有“王心”,则《春秋》乃是“天子之事”的具体体现。由此可见,汉儒如此“委曲求全”,将“西狩获麟”至“《春秋》当新王”之间搭建了合理的让渡路径,正是因为孔子为人臣不能行天子之权,但受天命之后便名正言顺,因此,无论是“西狩获麟”还是“《春秋》当新王”,对汉儒的“使用价值”无非是一假托而己,是“道德的、义理的标榜”[9]P204,并非以孔子为王而夺时王之位,宋儒多不明此理,故作无谓之争。 二、感麟而作与文成致麟 前述董仲舒未对感麟而作的具体原因作出分析,而是重点论述获麟乃天命符瑞,孔子应天而作《春秋》,遂被继起之儒尤其是东汉何休所利用,发展成为孔子素王、黜周王鲁、为汉制法等诸说。对此,晋代《左传》学家杜预予以了批判。这是因为汉儒所倡论的“素王”说背后所代表的为汉制法说虽然随着汉朝的灭亡而无意义,但是“孔子素王”之说在《春秋》学领域却依旧延续下去⑦,直至杜预之时,贾、服之注尚存于世⑧,且贾、服之注中也多有素王之说,故杜预不得不辨明之。杜预以为不论“素王”或是“黜周王鲁”皆为先儒妄说,所谓“伤时王之政”,杜预在注《左传》时有明文指出麟本圣王之嘉瑞,当时既无明王却出而遇获,故孔子伤周道之不兴,感嘉瑞之无时乃作《春秋》以正王道,并以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为终。杜氏此说已经抛弃了汉儒纠缠于“西狩获麟”“假借”之义,而专注于《春秋》成于孔子感获麟而作。接着杜预又言:“麟凤五灵,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时,虚其应而失其归,此圣人所以为感也。绝笔于获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故所以为终也。”这种感麟而作的说法实际就是指圣人以麟出非其时以“自况”。 杜预所谓“麟出非其时”,《春秋》乃孔子感麟而作之说得到了不少宋代学者的呼应,如孙复说:“孔子伤圣王不作,圣道遂绝,非伤麟之见获也。”原因在于天子失政而至夷狄迭制之,是故《春秋》尊天子所以黜诸侯也[10]卷十二,因此,孔子实是因“获麟”而感叹“中国”之事,《春秋》正是在这种时势下才有“感”而作。如果说孙复论《春秋》感麟而作之义稍显隐讳,崔子方、高闶等则明言之。如崔子方指出:正是因为圣人不在其位,不得已而寓《春秋》之褒贬见于行事而著罚”,因此,圣人感麟实因“圣人无所试用,其道不行,然后退而著书以自见焉。”[11]卷十二高闶也认为麟曰“获”,乃因“孔子卒于获麟之后二岁,则是时孔子已老,故感以作《春秋》而绝笔于此一句也……圣人为是作《春秋》,深有望于天下后世,苟有王者作,能举吾《春秋》之法以拯天下之民”[12]卷四十。主《左传》以解经的苏辙更是以史实来说明孔子《春秋》乃感麟而作,他以“名分”与“礼义”注解“西狩获麟”条:“名分立,礼义明,使斯民皆直道而行,则圣人之褒贬未始作也。”此时乃周之盛时,时人“犹知名分礼义之所在而不敢犯者”;“奈何东迁之后,势已陵僭”,然尚有可救者,五霸起而合诸侯、尊天子:又幸而一时卿士大夫事君行己,忠义之节,间有三代人才之遗风。“逮五霸既没之后,终于田常篡齐,六卿分晋,圣人于此,知夫名分不足以导之使戒,礼义不足以谕之使畏”[13]卷一六四。圣人知道再也没有什么可以挽回衰世的办法了,故绝笔获麟。此即孟轲所谓“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而后《春秋》作”之意也。 在宋代,对于《春秋》成书与“西狩获麟”的关系,仍然存在着对立的说法。例如,程颐对上述自三传以来诸家所谓“感麟而作”进行了反驳,还反对汉儒以“西狩获麟”为孔子受命之符一说:“麟不出,《春秋》岂不作?孔子之意,盖亦有素,因此一事乃作,故其书之成,复以此终。”[14]P206在程颐看来,西狩获麟与河图、洛书之出一样只是具有偶然性,对《春秋》与八卦之作不能产生关键影响。孙觉观点近于二程,认为孔子见获麟乃以为“异”,故绝笔于此。因此,《公羊传》所言“记异最为得之”。在此基础上孙觉反驳杜预云:“人道之乱如彼……于是西狩获麟,物理之异而人事有所不可知者,孔子书之绝笔焉。盖慨叹当世至于无言,而深有意于后世也。”[15]卷十三祥瑞之象并非与“君德之修”相应,至春秋之时已经世势“大乱”,即使如孔子之《春秋》虽“王道备、人事浃”,亦已无力挽救颓世,因此,正值西狩获麟之“异事”,孔子以此绝笔。孙觉反驳之论虽然也充满了天人感应的色彩,但也透露出一个迹象,即宋儒并非一概认定孔子之《春秋》乃“感麟而作”,而是主张与其相反的“文成致麟”说。其中,最有代表意义的是胡安国与赵鹏飞。 胡安国也是不厌其烦地论证麟之出应天时而至,并云:夫子作《春秋》“气志天人,交相感胜之际深矣,制作文成而麟至……至于勇夫志士,精诚所格,上致日星之应,召物产之祥,盖有之矣。况圣人之心,感物而动,见于行事,以遗天下与来世哉!”[16]P502胡氏认为《关雎》之化与麟兽之来,皆因王者之德所感。杨士勋《榖梁传正义》曰:“其诗,《周南》则始于《关雎》篇,终于《麟趾》,故《春秋》之文,亦义始于隐公之道,终于获麟。”也是以《诗经》比喻《春秋》,以《周南》始于《关雎》,终于《麟趾》,比喻《春秋》始于隐公,终于获麟。胡安国还从天人交感的角度分析了孔子获麟的心理动机:“《易》曰:大人者,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舜、孔子,先天者也。先天而天弗违,志一之动气也。”[16]P502故胡安国之意是指《春秋》先成,麒麟乃现,这既是孔子的心理感应⑨,也是经成道备、嘉瑞乃应之事,与贾逵、服虔、颖容等人所说之义相近,所以,胡安国也特别强调“箫韶九奏,凤仪于庭,鲁史成经,麟出于野,亦常理尔”,注重拈出其中“何以绝笔于获麟,其以天道终乎”之意。 赵鹏飞在胡安国的基础上指出《春秋》之教重于《关雎》之化,因为“化行于国而教立于书,行于国者利一时,立于书者利万世”,《春秋》中寓有夫子二帝三王之道,因此,《春秋》之教行则如同二帝三王之治,因此才可以说“麟为圣人而出,非为鲁而出也,鲁哀何德以将之。”[17]卷十六鲁哀公有其位而无其德,孔子无其位而致力于王道盛世,故麟瑞应时而至。且孔子所欲正之者春秋之世皆反之,故经书所载之事乃为正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与朋友之义,且“五者正,则王道成,此所以致麟之应也。”但是,“麟出于鲁之囿”且不幸见获于狩而伤焉,如何得知一定是为圣人而出呢?赵氏答曰:麟本为王者之嘉瑞,而只现于鲁国,非为圣人而应又是为何呢?《春秋》中,凡狩皆书地,志非其地。今书“西狩”,意指狩于鲁囿尔。鲁囿曰大野,在鲁之西,举西狩则知其在大野矣。《春秋》书法中,自得曰得,以力曰获。可惜的是,圣人之瑞无人能识反以力相加,“圣人虽睹其获不能无伤,然亦足以彰吾作《春秋》之志,非虚文也,于是落笔。”[17]卷十六 三、蜕变与新生:获麟之义的因革损益 麟为嘉瑞,圣王之兆,这一点是汉、宋学者共同的内在体认,因此,他们共同关注的焦点在于,获麟一事在孔子思想世界中的重要意义。无论是“感麟而作”抑或“文成致麟”,均出于学者对孔子思想世界中对获麟一事意义的追寻。孔子所感伤与震惊的,正是以麟为代表的“仁”这一根源性的价值观沦丧殆尽,西周之世的复兴再无希望。因此,汉、宋学者积极关注此一问题,也正是冀希望于当世,以避免孔子所绝望的乱世再次出现于本朝。 那么,为何汉、宋之际的学者在面对《春秋》西狩获麟所引申之义时又有如此大的差异呢?本文第一部分已经有所陈述,但仅限于两朝学者的观点在学理层面的差异,此处要进一步说明造成这种差异的更深层原因。在西汉公羊家眼中,春秋之乱、七国争雄、暴秦覆灭都表明了政治已背离了以礼制为核心的王道王法,君臣肆其欲而无所顾忌,百姓敢于揭竿问鼎。要应对这种滔滔乱世,唯有重新审视治国之方与礼法制度的变革存废,以制定新的行为规范,使政治秩序进入一个“天下为公”⑩的礼法秩序下。于是西汉公羊家着力于从天人合一的角度为《春秋》这部先王经世之大法、礼义之大宗赋予一个更为崇高神圣的寓意,并主要凭借《公羊传》来阐明这部经典所蕴之奥义,从中关注政治秩序的合法性问题与礼法制度的变革存废问题。这才出现如西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新王统虽需改正朔、易服色,改乱制创新制,但仍能采纳、保存旧统之善的“通三统”理论,以及揭示出《春秋》中改世卿制为选贤制、改不亲迎制为亲迎制的“孔子改制”学说等等。即是希望以孔子礼乐精神为依归,并体现儒家仁德、王道的政治礼法制度,藉此来规范人的言行举止以达成公共政策的实行,实现王道(11)。可见,西汉公羊学作为一种“政治儒学”,其重心则落在政治社会的治国方法与制度上。当然,汉代公羊学也不是一种维护君主专制权力,无原则的接受和支持一切政策及制度的理论学说,而是具有“批判性”、“革命性”独特性质的儒学理论学说(12),它是希望藉由批判来促进社会进步,以达王道、太平的政治理想。 而在宋儒看来,理想世界是上古“三代”,“道德仁义之风”是三代盛世的唯一以及最高标准。因此,对这种“道德仁义之风”进行传承的朝代,才是值得期待与尊重的时代,而汉、唐则不值得期许。因此,即使汉代遵从公羊学家实行“改正朔、易服色,改乱制创新制”等诸多措制,在宋儒看来仍然只是“汉革秦,不能尽循周之道,王道于斯驳焉。”因此,宋儒努力的方向是重新恢复三代“道德性命之理”,且这种努力也不需要再像汉儒那样走受命于天的曲折途径(13),而是主要依靠个人的“诚心正意”、“格物致知”、存天理而灭人欲等方式。可见,宋儒关注个体生命的明心见性、成德成圣,企图对生命的价值、存在的意义、人格的增进及道德的完善等问题,找出解决方法。 因而可知,宋代儒学重在使人们能知修养心性、正心诚意,通过个体生命领域之道德自觉涵养,来完善人性、关怀生命,实现存在价值造出理想国度,异于重视王道王法之政治礼法制度的政治儒学。公羊学的实践方式不像心性儒学的实践功夫,重视个人的道德实践,其借西狩获麟所逐渐推衍出的“受命改制”之义的“最终落脚点是制度创新(继周损益)”[18]P141,因此,他们重视社会的政治实践,期望藉由提出理想的政治来转化现实中的种种弊端,力图通过建立及推行制度,使理想的政治秩序与礼法制度落实于现实社会中,达到所谓的“通经致用”的理想(14)。正是这种差异,才是导致汉、宋儒者对“《春秋》当新王”、“黜周王鲁”等说产生歧义的重要原因。 再从宋代《春秋》学的角度来观察可以发现,在《春秋》经文的诠释过程中,宋儒基于《公羊传》“大一统”思想的前提之下,对于历史文化进程的基本描述,体现出两条相互矛盾且相互补充的历史发展路径。一条是春秋的乱象:王权失坠而导致的诸侯专封、大夫专权,伦理败坏而出现的臣弑君、子弑父,中国不振而引发的夷狄入侵,这是一条真实的历史路径。而另一条则是其所阐发的《春秋》中所蕴含的贬天子、退诸侯、贤贤贱不肖、尊中国贱夷狄的“大义”,这是一条虚拟的历史路径。前一条路径,是宋儒对历史进程清醒睿智的洞察,是一种“现世主义”的忧患与悲观:而后一条路径则是作者为思想的活力与生活的热情所激发的历史乐观精神,均以哀公十四年的“西狩获麟”为象征。前一条路径的终结是孔子见麟而伤:“孰为来哉,孰为来哉,反袂拭面,涕沾袍”,这是对历史现实的忧虑与哀伤。而后一条路径的终结乃是“为获麟而大之”,“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这既表明宋儒对孔子之道延续性与永恒性的肯定,也是对创造新的文明阶段的自信与期盼。很显然,这两条路径交织补充所产生的新思想,便是蜕变与新生的统一,即在旧的肌体之中孕育出新的生命。在《公羊传》则是于旧的“一统”逐渐崩毁的过程中,新的“一统”渐次诞生。这是《公羊传》优于其它二传的胜义所在,同时也是深刻反思之后的历史结论。 注释: ①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172页。当然,朱熹之后此一争论仍然未能停息,至清儒仍然对此问题较为关注,可参阅胡楚生:《试论〈春秋〉之文化史义涵——以俞樾之说为探索中心》,载《经学研究续集》,台湾学生书局2007年版。 ②如《礼记·礼运》、《诗经·麟趾》、《汉书·武帝纪》、《后汉书·明帝纪》等文献中均有记载,可见,在当时,“麟”仍然被视为祥瑞之兆。 ③对于“《春秋》新王”或孔子“素王”的涵义,钱穆解释说,依照董仲舒的观点,“即使当时的天子,孔子《春秋》里也要褒贬,所以说《春秋》是‘新王’,又说孔子是‘素王’。‘素’,犹近代语说‘空’。孔子并没有真个当新王,《春秋》褒贬,也不是当时真有一个新王朝,真定了那样的法律来褒贬,于是孔子《春秋》只成为‘素王’了。这犹如说是一个‘无冕的王者’,或是一‘空头王者’了。”钱穆:《孔子与春秋》,收入《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72页。 ④“《春秋》新王”、“《春秋》王鲁”等说的详细含义,可参阅蒋庆:《公羊学引论》,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曾志伟著、林庆彰、车行健指导:《〈春秋公羊传〉三科九旨发微》,台湾国立东华大学中国语文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 ⑤如同赵伯雄所说:西汉公羊家“‘以《春秋》当新王’,‘缘鲁亦言王义’,都是把鲁作为一种政治模型”。见氏:《春秋学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55页。 ⑥参阅:王光松:《在“德”、“位”之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页。另有: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北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 ⑦如晋挚虞《孔子赞》中便言:“仲尼大圣,遭时昏荒,河图沉翳,凤鸟幽藏。爰整礼乐,以综三纲。因史立法,是谓素王。”故可知素王背后的意义虽已经消失,但是素王之论却深植人心。孔继汾:《阙里文献考》(续修四库全书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乾隆二十七年刻本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卷三十八,《艺文第十二之七·赞·挚虞孔子赞》,第231页。 ⑧《隋书·经籍志》载注《左氏传》者有近十种,其中贾逵、服虔等注俱存。 ⑨朱熹虽然认为这种心理感应不是很值得肯定,但仍赞成胡安国的推想:“胡文定公谓《春秋》绝笔于获麟,为‘志一则动气’,意思说得也甚好。”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862页。 ⑩“天下为公”本为《礼记·礼运》中之语,至宋代胡安国,其《春秋传》中亦多次拈出此义。 (11)蒋庆谈到:“公羊家在旧政权及制度崩溃、新政权及制度尚未建成之时,生命一无所依,心中也强烈的存在着实存性的焦虑,只不过公羊家认为实存性的焦虑不是孤立存在的现象,而是旧制崩溃、新制未立带来的必然结果,所以公羊家认为只有解决了制度性的焦虑,才能解决实存性的焦虑,或者说减轻实存性的焦虑。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公羊学才把关注的重点放在政治制度上,而不是放在生命心性上。”蒋庆:《公羊学引论》,第3页。 (12)关于公羊学的“革命性”、“批判性”,杨雅婷的《春秋公羊家之革命改制思想》(张永儁指导,东吴大学哲学系2002年硕士学位论文)作了比较详细的分析,现代学者也非常关注这一问题,可参阅:蒙文通的《经史抉原》,(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173~174页。)陈柱的《公羊家哲学》(见《经典与解释20:犹太教中的柏拉图门徒》,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刘小枫的《儒教与民族国家》(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85~194页)等。 (13)刘浦江认为宋代儒学复兴后,经学与纬学才彻底分家。刘浦江:《“五德终始”说之终结——兼论宋代以降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另外,王光松认为:“在道学家们的描述中,孔子勤奋修德而至于‘与天同德’的圣人境地,此种圣人形象非关天命、与‘位’无涉,而仅与修为有关,该形象可亲可学,是道学家们的学习楷模”。王光松:《在“德”、“位”之间》,第104~105页。 (14)蒙文通所说:“微言的内容是‘经世之志’,是‘天子之事’,是‘一王大法’,是新的一套理论,是继周损益的一套创造性的革新的制度,这和宋儒所谓性命之道才是微言的意思全然不同。这套制度要见于礼家如两戴记之类,而《春秋》家和《公羊》只空言其义,见不出什么具体制度,所以大家就以为是非常可怪之论。”蒙文通:《孔子与今文学》,收入《经史抉原》,第1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