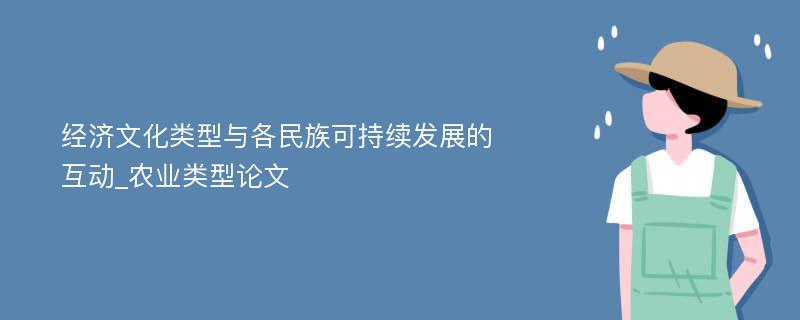
经济文化类型的相互影响与各民族可持续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可持续发展论文,各民族论文,类型论文,经济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F127.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ISSN 1000—5218(2000)—01—0005—05
经济文化类型是指居住在相似的生态环境之下,并操持相同生计方式的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经济和文化特点的综合体。(注:关于经济文化类型的定义、分类和各类特点、民族分布等方面的研究,本文综合参照了张海洋的《经济文化类型》一文和杨庭硕等人的《民族、文化与生境》一书,并根据需要做了取舍。文中定义采用张海洋的观点, 见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 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81页。)一般将人类各民族的经济文化活动区分为狩猎—采集、斯威顿耕作、畜牧、农业、工业五大类型。(注:经济文化类型的分类以四分法为常见,五分法是把斯威顿耕作型从农业型中分离出来另立一类,这样做有着特殊的意义,符合本文立意,故本文采用五分法。斯威顿耕作生计的基本特征是:使用人为的手段从自然生境中划定生产操作地段,让经过人选中的有用植物(或动物)在该地段内以其原生状态自然生长繁殖,以利人类获取和利用。所谓人为手段包括水淹、锄掘、排水等特化办法。在民族学发展史上曾将本类型称为刀耕火种、锄耕农业、游耕、灌溉园艺业等,这些名称有的仅适用于本类型的部分样式,有的容易与农业类型名称相混,故一律改称斯威顿耕作。参见杨庭硕等著《民族、文化与生境》,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1、92页。)解放初期,除未形成工业经济文化类型民族外,我国各民族在其他四大类型中均有分布。
当代中国学界对中国各民族经济文化类型的研究始于50年代后期,其主要成果是林耀华与苏联民族学家切博克沙罗夫合著的《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一文。〔1〕但此后20多年中断了这方面的研究,直到80 年代中期,林耀华的学生张海洋才重又接上香火〔2〕。 但当时还止于类型学的探讨,从时间上看仍基本停留在对解放初中国各民族所属经济文化类型的认识。随后,林耀华等人开始注重从变迁的角度探讨各民族所属经济文化类型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系问题,〔3 〕使经济文化类型研究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不过这一阶段的研究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一是在理论上多习惯于把经济文化类型范畴纳入到社会形态框架里考察,并缺乏与新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的自觉对接;二是对各民族经济文化类型变迁及其相互影响的研究还很零散浅显,不成体系。对于前者,杨庭硕等人的著作《民族、文化与生境》是一个重要突破,〔4 〕可以说本文的写作正是受了该书观点的启发。对于后者,在费孝通的倡导下,马戎等人按照“区域—民族”的研究方法做了大量“田野工作”,积累了丰富的个案例证,使问题有所深化。〔5〕也许条件还不成熟, 但本文还是试图以此为基础,全观式地把经济文化类型变迁及相互影响(注:王俊敏《民族经济文化类型当代变迁》, 《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1999年第4期。故本文侧重突显经济文化类型相互影响的视角。 )与中国各民族的可持续发展紧密联系起来,使这方面的研究有所推进。
一、经济文化类型变迁及相互影响研究对民族社会发展的意义
社会形态旨在把每个民族的所有成员划分为不同的等级,以体现其生产关系状况,依此将中国各民族分别划归于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农奴社会和封建社会(有的已有资本主义萌芽)四种类型。经济文化类型则把每个民族视为一个整体,体现该民族与其所处自然生态环境的关系,突出了生产力的标准。解放初期对各民族社会的改革,主要是在社会形态意义上的改革,土地改革、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无不是如此。当然,受社会形态变革的影响,各民族所属经济文化类型也发生了变化,尤其生产关系的变革对生产力有所解放,各民族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和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其精神风貌也大异于从前。但是,比社会形态更为完整和复杂的经济文化类型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尤其是被解放了的生产力并未得到真正发展。实质性的变化始于“大跃进”,显著特征是各民族所属经济文化类型在空间分布上的交叉切入、时间进程中的转换更替和具体内容上的重叠融汇,其中主要是农业经济文化类型的扩张和工业经济文化类型的嵌入。导致变化的力量并非发自各经济文化类型的内部,而是来自整个中国经济文化系统的发展方向——工业化(其极端表现为“以钢为纲”)和农业化(其极端表现为“以粮为纲”),以及与此相应的技术推广、政策调整和体制改革这种强大的外力。而这种外在力量又是以另一种单线进化史观“狩猎→畜牧→农耕→工业”为理念支撑的。而且问题的关键在于,变化并不等于发展,如果我们看到那种荒唐的所谓生产关系革命对生产力的践踏,所谓“高级”经济文化类型对“低级”经济文化类型的“殖民”所导致的自然生态环境破坏,就会相信仅用某种“先进”生产关系或某种“高级”经济文化类型来衡量民族社会进步确是一种误会。由此,我们可能还会增强对各少数民族“所以然”的理解,而不是对其所谓“落后”的指责。
农业经济文化类型的扩张,尤其是工业经济文化类型的崛起,包括国家现代化大工业和乡村工业,对各经济文化类型民族均提出了严峻挑战。本来,分属传统的各经济文化类型的民族,对人地关系都有着历史久远的良性调节传统。不用说狩猎—采集型民族,就是斯威顿耕作民族和畜牧型民族的经济文化行为,也不会导致不可复生态危机,最多只是出现暂时的和局部性的生态阻滞,其经济文化类型都有使生态系统自我修复的机制。〔6〕(P.83 )虽然以改变自然生态环境为前提的农业型民族的经济文化行为会造成不可复生态危机,但那一般不是发生在它自己所处的有效自然生境内,而是发生在征服其他经济文化类型民族所处的有效自然生境内;而且这种生态危机也是暂时的局部性的,随着它撤出不适宜于其经济文化发展的无效或低效自然生存环境,由当地各经济文化类型民族重新加以有效控制和利用,这种生态危机也能逐渐克服。而工业经济文化类型则天生是造成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不仅它本身还未形成修复自然生态失调的机制,而且也改变了其它经济文化类型与其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的内在关联和协调。现在,不论哪一经济文化类型,也不论汉族和少数民族,由于嵌入工业经济文化类型并进而向这一类型转化,都正在改变着或已经改变了原有的价值观念和经济行为,并构成了对其所处自然生态环境的难以预料和控制的威胁,并进而影响到各民族的可持续发展。
二、各民族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抉择
多种经济文化类型、同一经济文化类型内不同亚型并存发展,相互制约,是解决生态危机、保持文化多样性的必要前提。因而为了某些民族的经济文化运作的需要,依靠某种经济文化类型本身所具有的强势,使用能量输出移置企图改变其他民族、特别是弱小民族的经济文化运作的做法必须加以制止和限制。现在我国各种非农业经济文化类型对于农业经济文化类型的侵蚀已经或正在进行有效抵制,但对工业经济文化类型的扩张还未给予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重视。由于工业经济文化类型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最高经济文化类型,所以世界所有民族几乎均以步入该类型作为实现现代化目标的核心,我国各民族亦不例外。但是对工业经济文化类型必须一分为二,在承认它对人类贡献的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到它对生态危机所应承担的责任,其他类型经济文化各民族应当动员起来,有效地限制其扩张。事实证明,不论已经工业化的民族,还是正在工业化的民族,工业经济文化类型所带来的发展都不能说是真正的发展,其发展都在可持续发展面前遭到否定。其实,我国各民族既然在各经济文化类型中均有分布,而这正是抵御生态危机、保持文化多样性、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最大优势,没有必要非得跟在别人后面赶时髦,走工业化以实现现代化的弯路。我们当然要发展农业和工业,但是我们不要“农业化”和“工业化”;我们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各经济文化类型民族互补互助、相互制约、共存共荣的弹性社会,而不应仅是一个农业化(民族)或工业化(民族)的刚性社会。经济文化类型多样化之于中国各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价值,正如生物多样性之于自然界的价值。对中国各民族来说,要慎谈通过工业化以实现现代化,而要高扬可持续发展大旗。这一人类处于转折点上的发展战略,不能因为我国工业化整体水平不高、某些少数民族水平更低而遭到反对或大打折扣。
主张多种经济文化类型、同一经济文化类型内不同亚型并存发展,相互制约,并不意味着使原有各经济文化类型保持现状,恰恰相反,必须对其加以改造。但是为发挥和利用各传统经济文化类型民族对其所处自然生态环境的特化优势以抵御生态危机,对其改造必须慎之又慎,不可轻举妄动。现在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对某种经济文化类型的改造,必须充分考虑该类型与其所处自然生态环境的内在关联,考虑其经济与文化的内在关联,其实也就是必须从该类型民族实际出发,这也是各民族可持续发展的应有之义。各经济文化类型民族的变迁表明,新中国建立以后,党和政府以及科研部门对处于传统经济文化类型的民族的定性评价是“落后”,随之而来的一切扶助都是为了使他们尽快摆脱“落后”,各方面的现成条件都是为了取代这种“落后”,同时却忽视了传统的不一定是落后的,即使落后也能从中发展出先进的因素,忽略了很多落后现象是为了生存需要、生产需要而顺应客观环境的产物。其实,当我们面对落后的狩猎、斯威顿耕作、畜牧和农业经济文化类型时,并不意味着必须通过定居转产而抛弃传统,发展现代化的狩猎、斯威顿耕作、畜牧和农业经济文化才是改变落后的正确选择,因为它们都是符合特定自然生态环境的因地制宜的经济文化类型,同时也是各有关民族文化传统、民族个性的物质依托。总之,在民族发展的方式选择上,“取代不如改造”,而改造又必须符合地区实际和民族特点,立足于激发当事民族的内在发展活力。郝时远和他的同事们通过对鄂温克族猎民群体的微型解剖,也得出了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7〕(P.37—39)
前文指出,仅用生产关系标准来衡量民族社会进步确是一种误会,而应通过对经济文化类型的透视突显生产力标准;但同时也不能忘记,生产力标准是中立的,其本身亦有局限性,必须对其加以必要的限制。我国各民族所属经济文化类型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忽视了各自的特殊性而一律向农业或工业经济文化类型看齐,其生产力发展水平貌似发生了跃进,实则仍在较低的层次上徘徊,甚至长时期内有所倒退。吸取这方面的教训,在对各民族所属经济文化类型进行改造转化时,既要努力将其生产力逐步提高到高一阶段经济文化类型的水平上,又要重视其生产力状况对特定自然生态环境的特化和适应,既要看到生产力水平在短期内明显提高的直观性,更要注意生产力在长期内持续发展的潜在性,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其生产力才会有真正的发展,各民族也才会有真正的发展。这也是可持续发展战略对发展生产力的内在要求。否则,所谓“生产力标准”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就会演绎为“生产力第一主义”的引导,这必将使中国各民族误入歧途。
三、各民族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探索
由于工业和农业经济文化类型目前处于强势地位,人们总是给予极大的关注,也多抱以极大的希望,在讨论民族未来发展模式问题时,在此先搁置不论,而是重点看看处于弱势地位的狩猎、斯威顿耕作和畜牧经济文化类型民族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以东北鄂伦春族和鄂温克族来说,其狩猎经济文化类型早已走上一条改造发展的路子。直到近世,鄂伦春族和鄂温克族猎民们仍在因袭用弓箭、扎枪等捕猎工具进行狩猎的生产方式,当火枪、快枪传入并代替了这些原始的捕猎工具之后,其狩猎业的生产水平和生产效益迅速提高。在这一变革中,猎民经历了从最初接触快枪的不适应,到成为弹无虚发的“神枪手”的过程,但是这个转变很自然也很迅速,其原因是先进的生产工具符合其生产需要,从而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又不断为猎民更新枪支,配给半自动步枪、小口径步枪和充足的弹药,使猎民的传统狩猎业展现了现代狩猎业的面貌。由此可以说,先进生产工具的引进和狩猎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无疑是猎民群体进步发展的标志。鄂温克族猎民的驯鹿业也应按此方式改造。可惜的是,鄂伦春族和鄂温克族的狩猎业和驯鹿业还是无可挽回地衰落了,而这主要是由大规模的森林开发和森林工业发展使林区环境恶化、工业和农业经济文化类型人口大量移置使滥捕滥猎成风造成的。因此,要使狩猎业重振雄风,只有等待林区开发高潮以后的长期休养生息来恢复森林生态环境。另外,采集和捕鱼在今天仍是我国渔猎民族的主要经济活动和食物来源,甚至从传统采集业中发展出来的木耳椴培植等生计已形成气候,从传统捕鱼业中也延伸出了养鱼的新苗头。(注:上述体会主要来源于我1998年暑期参加的一项有关鄂伦春族发展问题(国家课题)的实地调查。鄂伦春族 猎转产后主要转向农业,但我担心东北森林生态系统很难适宜于农业的发展。)就此而言,北欧三国(瑞典、芬兰、挪威)对居住在北级圈从事驯鹿业生产的萨阿米人(即拉普人)进行的比较成功的社会改造可供我们借鉴。〔8〕
当代属于斯威顿耕作经济文化类型的民族,主要是分布于滇西南及与缅甸、老挝、越南相邻地带的彝族、哈尼族、傈僳族、拉祜族、佤族、景颇族、布朗族、普米族、怒族、德昂族、基诺族、独龙族、瑶族、苗族等约19个山地民族。〔9〕(P.25)有人认为, 这些民族的刀耕火种仍然会延续发展,但这并不是包袱,而是发展旅游农业的优势所在。因为刀耕火种旅游资源既具有明显的民族性,又具有十足的野性,基本上依托于山、火、刀、林和草棚、篱笆、狩猎、耕作礼仪等构成的野趣浓郁的旅游项目,共同编织出一幅悠悠古韵、浓浓乡情的世外桃园图。而旅游农业也许正是滇西南山区脱贫致富的最佳抉择。这一地区过去的经济建设经验告诉我们,按照传统的方式,单一地去发展民族农业和民族工业以摆脱贫困是不可能的,而重点发展效应高、带动面大的旅游产业,才有可能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这种经济效益也必然带来良好的社会效益。同时,从生态效益看,刀耕火种生计有一定的轮休期,不会造成自然环境的破坏,因而也利于旅游业的持续发展;以之作为扶贫,还会防止脱贫后重又出现“返贫”现象。〔10〕(P.25—30)当然,旅游业自身的发展也需服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以国外的经验来说,这种发展模式是可能的,新加坡和泰国资源十分贫乏,但他们战后靠区位优势,首先发展以旅游业为主的第三产业,使得经济腾飞,并为世人瞩目。
对于畜牧经济文化类型,针对长期以来形成的农牧矛盾,费孝通在80年代中期考察了内蒙古赤峰市以后认为,这一地区必须改变传统的经济结构,结束盲目扩大农业的历史,一方面因地制宜恢复林业、牧业,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工矿业。要实行这个方针,首先是恢复自然生态平衡,制止水土流失所引起的经济上的恶性循环,就是要种草种树,退农还牧。这对于有畜牧传统的蒙古族来说是十分欢迎的,但是对杂居在少数民族地区务农的汉人则存在着现实困难,最好的办法就是使农牧矛盾转化为农牧结合。过去农牧矛盾是在一定农牧业生产水平上发生的,那就是一方面是自然牧业,一方面是粗放农业。如果农牧两方都在技术上提高一步,牧业方面改变单纯靠天然牧场来放牧而能部分地以饲养来补充,就是用种的草或精饲料来喂牲畜;农业方面能改变粮食的种植,腾出土地来种植精饲料为牧业服务,这样,农牧就不仅不再矛盾,而且互相结合了起来。这在一些国家早已成为现实,费孝通在英国和澳大利亚就亲自目睹了这种比靠天放牧高一级的饲育畜牧业;而在他重点调查的赤峰市翁牛特旗这个半农半牧地区,也看到了农牧结合的前景。〔11〕虽然后来他的助手和学生们在对翁牛特旗进行追踪调查时发现,退农还牧、农牧结合还存在着许多现实问题,但同时也承认当地已步入牧业现代化的道路并在向前迈进。〔12〕(P.108—111)当然,畜牧经济文化类型抵制了农业经济文化类型的侵害,并不等于它自身问题的完全解决。经济体制变革造就的新型的一家一户小牧经济,虽然更深切地感受到发展草业对牲畜繁殖的重要性,但由于分散的家庭经济即使在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扶持下,也难以承担大面积的草场建设任务,迅速发生的社会分化和地方政府权威弱化,使这一任务进一步增加了难度,而公共草场和承包草场长期并存使牧民很容易损公利己,市场皮毛价格的高涨极大地刺激了牧民对利益的追求欲望。这一系列因素综合起来,使过牧超载长期持续成为常态。(注:王俊敏《一种新型社区——牧区社区》,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2 期;《牧民家庭及其经济》,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1期。 另参见张敦福《公共资源灾难理论与内蒙古牧区的体制变迁》,《西北民族研究》1997年第2期。)而这已属于另外的问题,非本文探讨的范围。
东北鄂伦春族和鄂温克族狩猎采集经济文化类型的改造模式,曾经是通过引进先进生产工具使传统狩猎生计逐步演进为现代狩猎生计,这是同一经济文化类型在发展阶段上的提高。云南各少数民族斯威顿耕作经济文化类型的改造模式则试图从原有的斯威顿耕作生计中衍生出新的产业——旅游农业,这是新型经济文化在旧型经济文化上的叠加。内蒙古蒙古族畜牧业经济文化类型的改造模式则是变农牧对立并存为农牧结合互补,是通过吸纳新型经济文化来为原型经济文化服务。虽然三种模式各有不同,但共同特点都不是用一种所谓先进的经济文化类型来取代原来落后的经济文化类型,也就是都没有单纯走农业化或工业化的路子。虽然它们还处于理论探讨和实践摸索之中,有的甚至出现了危机,但是,我们还是从中看到了希望,而且为各相关民族可持续发展计,为各相关民族发展的终极价值关怀计,这种探索是值得特别肯定和支持的。
收稿日期:1999—04—13
标签:农业类型论文; 生态环境论文; 经济论文; 环境经济论文; 可持续发展论文; 农业发展论文; 农业论文; 三农论文; 经济学论文; 斯威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