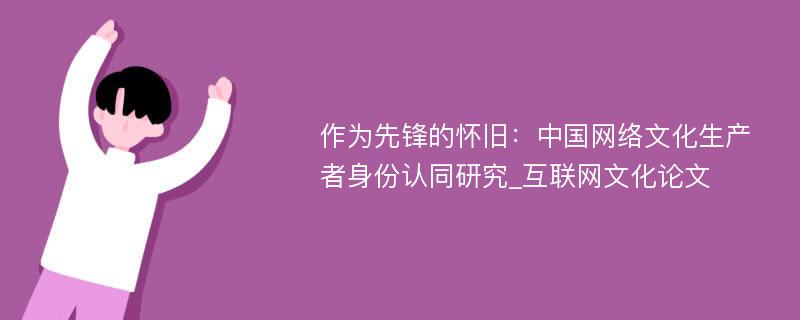
以先锋的姿态怀旧:中国互联网文化生产者的身份认同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锋论文,生产者论文,中国互联网论文,姿态论文,身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主流学界对“互联网文化”(cyberculture)的界定以及对其基本特征的描述驳杂且宽泛,但在下述三个方面可以达成共识:(1)互联网文化是由于人们在使用计算机网络进行交流、获取娱乐或从事商业活动的过程中形成的文化;(2)互联网文化是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而形成的、在形态上有别于传统媒介环境下的形态的文化;(3)互联网文化以“共享”为基本特征(Morse,1998;Silver et al.,2006;Turner,2008;Nayar,2010)。本文对互联网文化的考察也建立在上述理解之上。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中国独特的“国家-市场”二元结构对于中国当代文化的塑造有别西方社会的情况:一方面,中国的网络文化生产者至少在姿态上具有更鲜明的反建制色彩(常江,2013);另一方面,中国的网络文化形态因历史、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等原因也与西方社会的情况不尽相同,如“微电影”等在中国十分流行的网络文化形态,在西方国家却并无严格的对应物。 互联网在中国的勃兴催生了一系列以“后”和“微”为标签的文化形态,并与传统媒体环境下的流行文化形成显著的区别。对此,国内已有相当数量的研究。 从内容上看,现有的研究成果大抵包括两类。第一类是对于互联网文化的形态特征做出总体上的描述。这些研究得出的结论具有较强的相似性,并带有显著的悲观色彩,集中体现为对于“文化工业”、“商品拜物教”、“负价值”等语汇的过度使用(杨聪,2008;阎真,2004;李美敏,2012;雷启立,2009;许正林,2011;钟琛,2013)。第二类则是对较为具体的文化形态,如同人写作、网络流行语、青年亚文化、微博文化等,展开专门的分析,并尝试从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研究以及传播学等角度做出基本的归因分析(王玉香,2012;尹良润,2009;李晓南、王新,2009;孙秋云、王戈,2012;施宇,2011;杨玳婻,2010;乔秀峰,2013;常江、文家宝,2013)。 总体上看,现有的研究成果数量较多,且得出了一些有启发性的结论,却也存在下述三个比较显著的问题:第一,大多直接套用西方文化理论,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和英国文化研究的受众中心视角对现象做出直接的解释,进而做出或悲观、或乐观的价值判断,基本上忽略了这些理论背后的独特历史与社会语境。第二,无论将互联网环境下的文化视为“人生上网忧患始”(杨聪,2008:109),还是“公民社会崛起的象征”(李岩、纪盈如,2013:25),其实均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研究者的焦虑感和对新传播技术的文化潜力的某种不切实际的期待,这影响了其对研究对象——互联网环境下的文化——的准确观察和客观判断。第三,现有的研究主要基于对互联网文化形态(formats)的文本或机构观察,却并无针对这些文化形态的生产者的专项研究,这很容易使得相关结论和判断陷入某种文本中心主义的抽象性;而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区别于其他研究文化的路径(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culture)的一个显著特色,恰恰在于对于抽象性的反对(Hall,1996a:39),这种“反抽象”又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反对将文化、经济和社会机构剥离具体的语境,“好像它们之间只存在一种外在的或者机械的关系”;二是反对将形式、结构与内容割裂开来(Gibson,2007:58)。这意味着我们对于特定技术环境和特定社会结构中的文化形态只能进行具体而微观的观察,并杜绝将形态和内容视为独立于生产情境(the context of production)的“超时空”的存在。 本文是一项针对中国当下互联网文化生产者的研究,着重考察一个问题:中国互联网文化的生产者究竟具有怎样的身份认同(identity/identification),以及这种身份认同对于公共文化与政治空间的民主化有什么样的作用。 之所以选择身份认同而非其他社会文化机制作为理解互联网文化生产者的关键,主要基于如下三个原因。 第一,由于全球化及其催生的关于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的讨论和争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身份”问题开始成为文化研究的核心议题,也成为不同文化群体,尤其是为主流文化建制所排斥和边缘化的群体寻求文化认同、实施“符号抵抗”的重要手段(Barker,2008;Hall,1996b)。身份既关乎意义生产的主体对于“我是谁”的认识论意义上的理解,也关乎不同群体如何在各类文化话语中被再现(represent)的差异政治(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是我们理解当代文化现象的关键所在(Hall,1990,1992,1996b)。在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看来,身份认同不是一个确凿无疑的结果而是一项持续进行的工程(project),关乎个体和群体在历史、当下和未来的情境下对自身进行界定的过程(process)(Giddens,1991)。因此,巴克(Chris Barker)指出:“与其说身份是我们所拥有或发现的一个一成不变的东西,不如说身份是一个我们对自身做出描述的持续不断的过程”(Barker,2008:7)。而中国互联网流行文化的生产者同时作为全球化和中国当代语境下的重要群体,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化格局中不容忽视的存在。“他们”究竟是“谁”?“他们”如何界定和理解自己的身份?他们的身份与传统媒介环境中的文化生产者的身份有什么异同?对于这些问题加以理解和分析,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互联网技术对中国固有的流行文化生态进行改变(乃至颠覆)的过程。 第二,关于积极的互联网用户的群体特征,西方社会学和传播学围绕“虚拟社群”(virtual community)展开的大量研究已经做出过较为详尽的描述,这为我们更进一步对其展开身份认同机制的剖析提供了学理和经验的基础。总体上,主动的互联网使用者可被视为一个我们看不见的数字社群,其成员和普通网民的区别在于其使用互联网进行主动交流和意义建构的意愿和能力,在互联网技术的支持下,不同的成员围绕着不同的话题和兴趣形成了无数个不同的小社群,他们进行交流的工具则包括互联网论坛、聊天室、社交媒体、网络游戏平台,等等。网络虚拟社群具有某些真实社群的关键特征,包括:(1)表达的自由;(2)缺乏集中控制;(3)泛向而非点对点的传播;(4)成员行为完全出于自愿(Rheingold,2000;Song,2009;Leimeister & Rajagopalan,2014)。这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对于印刷术通过建构民族国家想象从而改变了传统的基于物理空间的传统社群的考察一脉相承,可被视为更为宏观意义上的“社群研究”传统在互联网时代的发展(Webber,1963;Wellman,1979;Anderson,1991;Prodnik,2012)。抛开这一思路中的技术决定论色彩不谈,虚拟社群与真实社群在构成形态和关键特征上的相似之处使得我们将文化研究传统下的“身份”考察方法应用于对互联网用户的分析成为可能。 第三,在以西方为相对参照点的中国本土文化问题的研究中,身份认同问题的重要性也日渐凸显,因其关乎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背后可能具有的政治维度和政治解放性潜力,因此具有显著的研究价值。徐贲(2011:16)就曾宣称:在当下的中国,文化批评的话语中和在政治的话语中一样,“我们”并不是毫无疑问地天然给定的,而是批评话语在其实践过程中构建而成的。而文化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也曾指出,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集体身份认同往往包括两种不同的因素——“初级性认同”和“公民性认同”。前者表明第三世界国家人民需要寻找某种获得世界公开承认的身份,即“我们是世界的重要一员”,是一种被动性的认同;而后者则表明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努力“追求进步”,并“建立更有效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公正”,是一种对于“我们应当如何存在才算是好”的能动性的认同(Geertz,1972:258)。毫无疑问,互联网文化生产者的生产行为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实践,而非建立在血缘、种族、语言、地域、宗教等初级文化维度上的集体无意识,因此不可避免将是政治性的;互联网生产者的身份认同也必然“拒绝为属于过去的决定因素所束缚,而代之以一种积极的、开创的共同体建设实践”,强调“普通人作为能动主体和有效参与者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徐贲,2011:18-19)。而这种价值取向与现代民主政治的价值观是相一致的。因此,借助对于互联网文化生产者身份的研究,可以为我们观察和剖析借助文化生产以扩大民主政治空间的路径提供可能性。 二、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借鉴“主动受众”(active audience)研究的视角,将一部分积极参与文化生产的互联网使用者与一般意义上的网民区分开来,并以前者为研究对象。互联网文化生产者与普通网民的区别在于:前者对于互联网的使用是一种主动的、生产性的意指实践(signifying practice),他们积极使用互联网提供的各种技术便利,一方面对传统媒介文化产品——如电影和电视剧——做出符合自身需求的阐释和表达,一方面也围绕着特定的文化类型(genres)或内容(content)进行着积极的文化生产。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者自身的经历和观察,本文拟对如下三种主要的互联网文化形态背后的典型虚拟社群展开个案研究:论坛文化(以天涯社区为代表)、原创视频文化(以优酷网原创频道为代表)与专业社交媒体文化(以豆瓣网为代表)。 天涯社区(www.tianya.cn)创办于1999年3月1日。据其官方公布的数据,网站注册用户超过9000万。该网站不但在全球华人网民中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更是目前中国网络事件与网络舆论最重要的发源地之一。①优酷网(www.youku.com)创立于2006年,并于2012年3月12日与土豆网以换股方式合并而成为中国最大的分享类视频网站,其移动终端日播放量于2013年4月突破1.5亿,并在月度使用时长方面位居所有App第三位,仅次于微信和QQ,其原创频道不但吸引了数量最多、质量最高的微电影作品,更曾获得诸多微电影比赛与影展的重要奖项。②豆瓣网(www.douban.com)成立于2005年,是以网友自创评论(书评、影评、乐评)内容为主要产品,集博客、交友、小组、阅听等服务于一体的新型网络社区,月独立用户超过5500万。③上述三个网络平台不但拥有数量巨大的深度用户,更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文化与群体氛围,是中国当下互联网文化生产领域的典型代表和最为活跃的因素。 具体而言,研究者对上述三个网络平台的各15位资深用户(总计45位受访者)进行深度访谈。访谈对象的选取主要通过网络征集与人际推荐进行招募,并根据性别、年龄等人口统计学维度对样本进行了相关的筛选,以使其尽可能具有代表性。最终确定的45位受访者包括23位男性和22位女性,年龄全部位于25至40岁区间(以确保受访者同时具有独立经济地位和使用互联网技术的能力和意愿)。值得注意的是,全部应征者均接受过大学教育,其中超过80%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武汉、南京、杭州等经济、文化发达城市生活。 由于互联网用户具有匿名性、地域分散性等特征,导致百分之百的面对面访谈几乎不可能实现,因此本项研究的访谈全部通过网络即时通讯工具(如QQ)和移动社交工具(如微信)完成。使用互联网进行媒介文化研究中的受众/生产者研究的方法在国际质化研究方法论体系中已得到较为广泛的认可,不但在方法的规范性上达成了共识,而且也针对研究伦理和研究信度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Hine,2000;Jones,1999;Mann & Stewart,2000;Markham,1998;Lots & Ross,2004),囿于篇幅,此文不再赘述。需要强调的是,为确保研究的可信性,所有受访者都被要求提供真实身份信息(姓名、年龄、所在地),并与其网络ID做出了严格的一一对应。访谈时间从2014年1月初持续至2014年6月底,单次访谈的平均时间为60分钟左右。 通过对质化材料的收集分析,本文尝试回答如下问题:(1)受访者如何将自己与“他者”区分开来?(2)受访者群体在现时是否有可被清晰描述的身份特征?(3)受访者如何描述或界定自己的文化生产行为或习惯? 三、研究发现 访谈过程以半结构方式展开。对于每位受访者,除围绕研究设计中提出的三个问题进行针对性发问外,还会根据受访者的具体回答将话题进行拓展和追问。在访谈资料的呈现中,以A1-A15代表天涯社区的15位受访者,以B1-B15代表优酷网原创频道的15位受访者,以C1-C15代表豆瓣网的15位受访者。需要申明的是,本文的分析对象包括45位受访者的全部访谈资料,但囿于篇幅,只选取最具代表性的受访者言论进行呈现。 具体而言,我们可以将受访者的身份认同机制描述为如下五个方面: (一)受访者总体上呈现出显著的“排外意识”,即潜移默化地将自己所属的群体的成员身份与“非成员”做出严格的区分。 当被问及作为社群成员与其他非成员有何不同时,几乎所有受访者都能够给出明确的标准和界限,这表明尽管互联网在技术上已经实现了对进入者的高度开放和平等,但“互联网文化生产者”仍然有着如传统社群一样的较高的准入门槛。 A3:天涯的“老人”们对社区的忠诚度很高……虽然天涯现在和微博、微信比已经有点儿土了,但是我们还是一直待在这里……算是一种守护吧。 A15:天涯的大部分东西写得都可以用四个字形容:自命不凡……谁都能看出来,有的人知道得很多,喜欢讽刺,让人看起来不舒服,但是天涯就是这样的。 B12:微电影也是电影,要想拍微电影,首先要对电影有所了解,好歹知道新浪潮、新现实主义、新好莱坞是咋回事……平时光看那些恶搞的东西,是拍不出片子的。 C1:把书评写得像小学生作文一样,在这里会被笑话死。 C6:豆瓣还是比较难混的……如果没读过什么书,在这里最好不要发言,要不然也是被人讽刺。 C7:我大约是国内为数不多的熟悉邪典电影(cult film)的专家…… C11:就是……你要能看懂这里的人说的是什么,而且你也要按照这样的标准来说话……虽然有的时候显得很矫情,但是豆瓣就是这样的。 从访谈资料中,大致可以归纳出上述受访者将其自身与其他网络用户做出区隔的几种策略:第一,忠诚度:不同网络社群的用户往往十分看重自身作为某一社群成员的独特性和排他性,在访谈中发现,除优酷网原创频道用户的身份认同相对较为随意外,其他两个平台的用户均体现出高度的“排外”色彩,并会认为自己所在的社群具有高于其他社群或社群之外的普通网民的文化上的优越性。第二,资深:大多数受访者均有超过10年使用互联网的经验,并表示“小白”④在互联网的世界里是一个侮辱性的词汇,几乎等于“一无所知者”或“白痴”,使用互联网的时间和经验在某种程度上被等同于掌握信息和知识的能力。第三,某一方面的专业知识或能力:天涯用户普遍具有对于文史、经典影视剧或西方文化等领域中某一个或几个方面的知识积累,优酷网原创频道用户则大多接受过影视制作的相关训练,而豆瓣网用户多对文学、戏剧与电影有一定的了解并具备良好的文字表达能力,而三类受访者均认为如果一个新来者不具备社群成员所普遍认可的知识或技能,会很容易成为他人轻视和取笑的对象。第四,相似的表达风格:不同的社群就其成员发表言论的表达方式(如行文、语气、句法等)形成了相对固化的方式,不能够按照群体所共同设定的规范进行表达者会被轻视、排斥乃至嘲笑。 上述情况表明,尽管互联网技术消弭了传统媒介环境下文化生产者和文化消费者之间存在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壁垒,但“互联网文化生产者”还是建立起了某种行之有效的文化与符号层面上的壁垒。新的壁垒并未杜绝“网民”介入互联网文化生产的可能,但互联网生产社群内部所产生的强大的同侪压力会导致不具备相应知识或技能,或不能够顺应社群内规范的“闯入者”选择退出或保持缄默,互联网文化生产者得以维护了自身身份的“纯洁性”。 (二)受访者并未在总体上表现出对传统媒介环境下文化形态的抵触或反抗,反而大多呈现出对经典文艺及影视作品的维护和敬畏。 与研究者的预想不同,尽管受访者均为网络虚拟社群的资深成员,其文化生产与表达行为完全基于互联网平台,却并未在总体上呈现出对传统文化形式的厌弃或抵触。访谈所得资料呈现的结果恰恰相反:受访者多流露出明显的怀旧情绪。于他们而言,对于各种带有反建制色彩的元素——如流行语、恶搞视频、“人肉帖”等——的使用,更多是在表达对当下主流商业文化的话语体系的不满,是手段而非目的。大多数受访者均明确表示自己对于“文化经典”有较强的敬畏感。 A3:李少红拍的《红楼梦》从观念到细节,完全是错误的,是对原著的侮辱,和老版相比简直是个笑话……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A14:任何一部改编“四大名著”或金庸小说的电视剧,只要电视上一播,肯定会在天涯被骂惨……没办法,天涯里懂行的人太多,这些人都是专门挖坟的。 B7:我在拍片的时候会有意识地模仿欧洲文艺电影,无论讲故事还是镜头的设计…… B8:现在的网络视频粗制滥造,内容也低俗……那些人应该首先好好感受一下大师的作品。 C4:我基本上不读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红楼梦》我读过20多遍,王扶林拍的那个电视剧也看了七八遍吧,经典就是应该反复去看的。 C12:现在书评越来越难写了,因为所有人都在旁征博引。 具体而言,受访者对于自己所敬畏和推崇的传统文化形式和作品进行维护的策略包括下述两种。第一,对某些商业色彩显著的流行文化形态持对抗式解码立场或干脆拒绝解码。例如,豆瓣网曾有影响力较大的用户在小范围内发起过拒绝评论某商业化特点明显的青春文学作家拍摄的电影的倡议,并曾取得一定的成效。第二,采用典型的后现代式的互文(intertextuality)策略,尝试在文化生产过程中,通过对传统文化元素的引用和组合,创造新的文化形态。这一策略极为近似吉姆·柯林斯(Jim Collins)曾描述过的“新式泛型”(emergent type of genericity),即在文化创作中有意识地引用、提及乃至照搬其他文化中的某些元素。在柯林斯看来,创作者通过这种方式而形成了“混搭爱好者”的群体,获得了正当的快感(Collins,2009:47)。而彼得·布鲁克尔(Peter Brooker)和威尔·布鲁克尔(Will Brooker)也曾表示,这种互文式的文化产品中,存在着“一种全新的历史感……孕育着……积极自信的怀旧的力量”(Brooker & Brooker,1997:7)。 在某种程度上,受访者总体流露出了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悲观精英主义论调十分相似的文化观,认为过分商业化的流行文化对人性构成了束缚和戕害,而受其欺骗的大众并不具备自我救赎的能力(Horkheimer & Adorno,1972)。在大多数受访者看来,完美的文化存在于过去(欧美经典文艺电影、“四大名著”、金庸武侠小说、20世纪80年代的古典小说改编电视剧等),好的当代文化应该借助互联网技术提供的便利(如混搭和互文策略)来实现对于“文化经典”的致敬和模仿。 (三)受访者非常明确并在意自己作为“文化生产者”而非“文化消费者”的身份,并将这一身份视为自身作为“文化精英”并区别于“网民”的重要依据。 在访谈中,绝大多数受访者明确拒绝“网民”和“消费者”这两个标签,在他们看来,自己所在的网络社群的成员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网络用户,而具有某种意义上的“文化精英”或“知识分子”的身份。 A10:虽然我们经常自称屌丝,也叫别人原丝,但其实很多人是把自己当成知识分子的。实际上,天涯的很多人也真的是知识分子。 B1:在微博上,我就是个普普通通的ID,但是我拍的视频在优酷很受欢迎,评论中有人教我“大师”,让我非常有成就感。 B4:我从小就喜欢电影,想拍电影,但是家人不支持我考电影学院……大学之后我就自己练习拍,不懂就问其他人,摸索着做了几个片子……我想当导演,但是在中国太难了。不过我的作品被几个网站做了推荐以后,就有一些网站和广告公司来找我拍片了,虽然都是一些小宣传片,但这也算梦想成真了一点点吧……现在拍片的人太多了,什么人都有,片子也很烂,有的网站为了赚钱,专门搞些低俗下流的片子。 C3:我喜欢豆瓣的原因主要是这儿的人都很纯粹……在别人看来,豆瓣好像挺小资、挺浮夸的,但是至少我每个星期读一本书,很少人能做到这一点……这里有很多精英,深藏不露的那种。 C15:豆瓣的影评质量比那些乱七八糟的电影杂志都好……我的理想职业是做一个杂志专栏作家。 总体上,受访者在承认互联网给原本“无权”的自己带来了传统媒介环境下难以获得的空间和自由的同时,又通过对(他们眼中的)网络文化以及时常呈现为非理性的网络舆论的激烈批评来表达了某种文化精英主义的立场。这种多少有些自相矛盾的心态体现了互联网文化生产者十分复杂的身份认同机制:一方面,他们首先作为无权的大众的一分子,借助互联网带来的文化民主化力量,以自身具有的知识和能力为基础,拥有了“生产者”或“准生产者”的身份,互联网是其得以完成从消费者到生产者的身份转化的必要条件;可另一方面,互联网对他们而言更多只是一种纯粹的技术或媒介,而且互联网技术可能对文化形态产生的影响——如碎片化、去政治化、民粹主义倾向等(Turner,2008;Silver et al,2006;Dery,1997),是一件需要保持十足警惕的事。在他们看来,互联网环境下的文化形态不应当拥有迥异于传统文化语境的新评判标准,互联网文化应当是传统媒介文化的一种更加高级、更加进步的形式,而不是对后者的颠覆或破坏。 (四)同一网络平台的成员之间的关系十分随意,其真实社会身份的异质性较强,是一种以“兴趣”(interest)和“品位”(taste)为核心概念形成的松散的虚拟社群。 从访谈样本来看,受访者在构成上具有下述两个特征:第一,人员流动性大,平台(天涯社区、优酷网原创频道、豆瓣网)在提升成员凝聚力、促进社群内组织的形成上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第二,社群成员几乎不与同一社群内的其他成员进行所谓“真实的”、与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交流,社群成员内部的交流主要基于文化和审美的维度,而几乎与他们的政治经济地位无关。我们不妨认为不同网络平台的成员是一个个围绕着相近的兴趣与品位而非政治经济地位形成的松散的虚拟社群,社群内的身份认同机制和交流机制完全建立于符号系统之上,而并未如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1984)所言是建立在既存的政治经济权力体系之上,因此而成为当下社会语境中一个极为特殊的存在。 从访谈对象的情况看,本文考察的三个虚拟社群的成员的社会身份的异质性相当高,他们从事着几乎截然不同的行业,收入水平(部分受访者同意透露自己的收入状况)亦有显著的差异,但他们全部接受过大学教育,且大多生活在文化生活繁荣的大都会中。互联网提供的虚拟的、平等的交流环境使得文化(生活方式)得以在相当程度上与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相互剥离,而具有了某种自洽的地位。访谈中发现,受访者在这一文化生产与消费环境下所能体会到的快感几乎完全是符号意义上的,只有极少数受访者表达了渴望通过网络文化的生产行为谋取经济利益或改变社会地位的想法(如获得新的工作机会、获取商业收益等),绝大多数受访者认为自己借助网络平台进行“创作”的行为是一件非常纯粹和愉悦的过程。不过,成员与成员之间的相互认可和认同也完全建立在符号层面上,大多数受访者表示自己不会尝试和其他成员成为朋友,一些受访者表示曾经参与过网站组织的线下聚会,但这些活动总体上令人失望。 (五)受访者的文化生产行为并未形成稳定、持续的机制,而总体呈现为一种随意的、碎片化的状态。 在针对文化生产的方式和习惯的提问中,三类受访者给出的答案出现了显著的差异。所有15位优酷网原创频道的受访者均认为自己就是“艺术创作者”,并声称自己的创作源自灵感和兴趣,与社会事务关系不大;而来自天涯社区和豆瓣网的受访者则大多认为自己创作的主要方式是就具体的事件发表观点和评论,如热门电视剧的开播、争议电影的上映、著名作家的逝世,等等。 A8:其实天涯的精华在跟帖……比如2005年的那个TJJTDS的牛帖⑤,本来是个无关紧要的小事,但是最后变成了一个著名的事件……其实大家没什么时间在这认认真真写东西,都是看见什么评什么,智慧就都出来了。 A13:郭敬明的《小时代》一上映……我立刻跑到天涯看帖子……我根本不会买票看这种垃圾电影,但是我就是要知道它烂到什么程度。 B6:我从来不去做那些乱七八糟的搞笑视频……胡戈⑥的那个片子我上大学就看过,没意义……他自己拍的都不行。 B9:我要拍的作品,故事大纲在上大学的时候就构思好了。 B12:拍了片子往上一传,也没工夫看别人的片子咋样。 C1:马尔克斯去世之后,我才认认真真写了第一篇《百年孤独》的书评,写的时候很难过……以前没有好好读……那些天冒出了很多马尔克斯的书评,质量都挺高。 C2:以看为主,偶尔评几句,很少认认真真创作点什么。 从受访者给出的答案可以看出,尽管在生产习惯上微电影创作者与论坛、专业社交媒体的用户并不相同,但三者在本质上均体现为一种随意性,既缺乏明确的规划,也没有成体系的理念和诉求。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声称自己完全可以把虚拟世界和现实生活区分开来,进而也就暗示了其关于现实世界“优于”虚拟世界的价值预设。这样,结合前文的发现,不难得出中国语境下的互联网文化生产所具备的一种内在的分裂:这种文化在生产方式上是后现代性的,具有混仿(pastiche)、互文(intertextuality)和碎片化(fragmentation)等后现代文化的典型特点,是一种“引用的文化”、关于“前人之言”的文化(Jameson,1985:115,1988:105;Eco,1984:49);但在风格或文本特征上却是现代性的,具有鲜明的文化政治诉求,其潜在地反对文化的价值多元,主张文化对社会现实的参与和改造,并渴望借助互联网重建已经坍塌的旧的文化标准(而非设立新的标准)。这种分裂在表面上似乎得以平缓、有效地运行,但其产生的结果,往往是导致互联网文化走向保守,并最终为它所反对的主流商业文化所“收编”。 四、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天涯社区、优酷网原创频道和豆瓣网的总计45位资深用户的访谈,我们可以大致描摹出中国当下互联网文化生产者在身份认同上具有如下一些总体性特征: 第一,在群体心态方面,互联网流行文化的生产者与传统媒介环境下的文化生产者十分相近,具有显著的精英主义立场,竭力将自己与一般意义上的“网民”区分开来,体现出高度的主动性和建设性。但同时,这一群体内部又体现出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大家在总体上处于“单打独斗”状态,对他人的创作活动并不关心,更不具备明确的美学与文化政治理念。 第二,作为网络虚拟社群的互联网文化生产者以不同的平台(如论坛、分享类视频网站、专业社交媒体)和不同的知识领域(如侧重文艺的豆瓣网和专事科普的果壳网)为基础形成了无数个松散的次级社群,这些社群存在于符号的真空中,其得以形成的依据是成员之间的共同审美习惯和文化旨趣,与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并无直接的关联。成员内部的构成具有极高的异质性,其身份特征和生产行为几乎仅止于符号层面上,其文化生产机制中并未发现明确的政治或经济的利益诉求。 第三,中国当下的互联网文化在生产方式上是后现代式的,而在文本特征上则是现代主义的,即为“作为权宜之计的后现代性”(常江,2013)。文化生产者的生产行为大多围绕业已存在的文化产品或文本展开,通过混仿和互文等方式对历史和现实中的其他文化形态进行颇富解构色彩的“再创作”,但其生产出来的新的文化形态却体现出显著的现代主义气质,其主要的文化政治诉求体现于令主流文化重归“前商业时代”的纯粹状态。 上述结论似乎验证了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1987)的观点:“符号抵抗”正在成为当代社会中一种愈发明晰的文化生产方式,其生产者通过对意义、快感与社会身份的关注,在符号层面推动社会变迁,且这种文化生产方式正日渐成为与“社会抵抗”——即在实际上推动社会经济系统的变革——同等重要的过程。不过,在我们没有对本文所考察的互联网环境下的流行文化的社会影响进行科学研究的前提下,仅从既有经验资料和质化数据判断,似乎很难得出如费斯克这般乐观的结论。 一方面,可以明确感觉到互联网流行文化生产者对于互联网所具备的解放性潜质的认知处于相当保守的状态,他们乐于使用互联网技术带来的表达的便利,却又对互联网环境下的大部分“原生”文化形态持有怀疑和批判的态度,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这些人的文化生产活动处于一种自相矛盾的状态:既进行着积极的互联网文化生产实践,又因对互联网流行文化的轻视而渴望“回归”传统媒介下的文化环境。因此,绝大多数人实际上在利用互联网做传统文化意义上的表达,对于他们来说,对于互联网技术的使用更多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 另一方面,互联网流行文化生产者群体所呈现出的这种多少有些自相矛盾的身份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互联网流行文化的生产过程是高度随意、高度碎片化的。当随意化与碎片化的形式被用于传统的/现代主义意义上的文化表达,最终就形成了某种“以先锋的姿态怀旧”的局面。对于互联网流行文化的生产者而言,互联网并不是给文化生产带来本质甚或颠覆性变化的要素,而毋宁是一种更加便利的媒介与工具,是“技术新贵”克服自身所欠缺的传统意义上的身份标识(如特定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使自己得以“跻身”传统意义上的文化精英行列的权宜之计。互联网文化的生产者的这种弥漫的怀旧情绪及其与旧媒介环境之间藕断丝连的关系,使之非常容易为其所反对的主流商业文化“收编”而不自知。 正如杜赞奇(1991)所指出的,我们不能在西方的“精英-大众”二元对立结构中对中国文化的特征做出准确界定;在中国,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始终难以分割,国家象征符号、家族、市场、商会等机构与符号要素一直在中国扮演着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调和者的角色,始终努力使之纳入共同话语系统。如今,互联网成了最主要的中介,在互联网的场域内,那些在真实社会情境下缺乏必要的文化资本的“无权者”得以用激进的方式来获取文化生产的快感,但这种“激进”又往往因采用了某些排他性的框架而演变为另一种“符号的”精英主义。互联网的这种调和关系,在很多以“反智”为特征的网络名人的走红过程中得到了彰显:网民通过追捧“丑角”而实现对传统精英话语的反抗(张慧瑜,2014),但我们往往发现当传统的文化和美学规范被互联网流行文化的生产者所解构之后,这些人并未继续致力于创造新的文化,而是将目光转向了昔日时光。大卫·波特(David Porter,1996:11)便反对视网络文化为“精英阶层的一块飞地”,而将其视为“一种独特的交往形态”,即意味着互联网技术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而非网络文字或视像文本自身,才是我们把握“互联网文化”之含义的关键所在。从我们对45位受访者的访谈资料中可以明确归纳出该群体的如下身份特征:是生产者与文化产品,以及生产者与生产者之间的关系,而非文化产品自身的美学属性,成为互联网文化生产者进行身份认同的最主要动因;他们自我认同或想象性认同为“精英”,却不得不采用深受国家-市场结构影响的大众文化的生产方式从事文化生产;在创造了“流行”的同时,又鄙夷或厌弃这种流行,俨然一种自我否定的辩证法。 当然,互联网文化生产者的上述多少有些内在矛盾性的身份认同机制是有着独特的历史与社会根基的。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随着国家主义与消费主义话语日渐对知识阶层的所谓“精英话语”加以吸纳和消音,基于传统媒介环境的文化生产也逐渐与知识阶层的旨趣分道扬镳,一如周小仪(2002:5)所言:“高蹈的审美情趣与精致的艺术形式被世俗的趣味与商业化的文艺垃圾所取代。”这一过程无疑令自90年代初开始失去了体制认可的精英身份的知识阶层不断在大众文化时代积攒着源于“身份丢失”(identity lost)的深层焦虑感。当互联网技术“横空出世”并得以在多个维度上对密不透风的“国家-市场”权威构成渗透,这些有着相似的文化理念和审美旨趣的人便重新获得了“发声”的途径。不过,这种与社会政治经济基础缺乏关联的文化生产活动注定只能停留在符号层面和虚拟空间之中,最终只能演变为一种阿多诺式的“美学弥赛亚主义”,其用商业文化与国家文化的逻辑去从事对抗性的文化生产,最终的结果往往纳入主流国家-市场话语而不自知。在中国当下文化受制于国家-市场二元格局的独特形势下,互联网文化往往被寄予极高的期望,人们期待互联网的土壤中生发出真正意义上的“新的”文化形态,打破旧有格局,促进文化的多元性(钟琛,2013;杨聪,2008;李岩、纪盈如,2013)。但从本研究结论看,互联网流行文化的生产过程呈现出一种典型的悲观主义和精英主义的气质,这种文化生产行为建立在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和交流模式的基础之上,其创作者则是依相近的文化旨趣临时结成的松散联盟,并未形成意义的生产、流通、消费与再生产的严密结构,故而也不可能真正在实质上推动社会文化的多元。 可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能从中国的互联网文化生产者的身份认同机制中发掘出一些或许值得我们持续关注与分析的解放性潜力。一方面,从互联网生产者的身份认同中所体现出的互联网文化相对于政治经济结构的独立性,与布尔迪厄所悲观地描述的“文化作为统治阶级生产社会差异并将其合法化的工具”的状况已有显著不同(Bourdieu,1984)。这种新的文化并未如詹明信(Jameson,1984:89)所言将政治经济结构“文化化”进而消弭了现代主义的“批判空间”,而是基本实现了与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并行。互联网文化生产者的政治经济地位并未在本质上对其身份认同和文化生产行为产生显著影响,这至少为互联网文化对当下“国家-市场”格局构成一定程度的挑战争取了相当大的空间与可能性。另一方面,即使部分互联网文化生产者最终选择与主流国家文化或商业文化妥协并进入传统媒介生产领域,其在互联网世界里形成的关于文化生产的价值观、知识、技能和思维方式,也势必会对主流的文化生产机制构成冲击,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主流的“国家-市场”商业文化的某些面向,迫使其进行自身的革新或吸纳更为多元的文化质素,从而为文化民主乃至政治民主空间的扩大做出贡献。 不过,出于主题集中的需要和研究规模的限制,本文将讨论的重点集中于互联网文化的生产者一端,而并未对互联网文化生产的机构特征展开讨论。因此,有必要在此强调: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兼有商业企业和宣传机构的属性,是“国家-市场”二元结构的具体化,这势必会对互联网文化生产者的身份认同和生产行为产生影响。2014年和2015年国家宣传部门和互联网管理部门对于网络视频和网络文学的严格调控及其产生的警示效果,⑦表明互联网环境下的文化生产机制的复杂性或许与生产者们过于理想化的设想相去甚远。对于互联网平台自身的政治经济属性及其如何影响了文化生产的机制,应是后续研究的重点。 ①参见天涯社区官方网站:http://help.tianya cn/about/history/2011/0602/166666.shtml。 ②参见优酷网官方网站:http://c.youku.com/aboutcn/milestone。 ③参见豆瓣网官方网站:http://www.douban.com/about。 ④“小白”,互联网流行语,意指经验不足或相关知识匮乏的互联网新手。 ⑤TJJTDS,2004年天涯网上出现的著名网帖(后又多次出现在其他论坛上),其内容为询问汉语拼音TJJTDS是什么缩写,海量网友回帖提出五花八门的回答,成为当年十分著名的网络事件。很多网友借此表达自己对特定人物或事件的看法。 ⑥胡戈,著名互联网视频创作者,其于2005年创作的网络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重新剪辑了陈凯歌电影《无极》和电视节目《中国法治报道》,以滑稽、荒诞的风格对《无极》进行无情的嘲讽,瞬间风靡全国。 ⑦这一运动的正式官方名称为“扫黄打非·净网2014行动”。其宣称的主要目标在于打击互联网淫秽色情信息,并由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以及公安部联合执行。包括新浪网、快播在内的多家著名互联网内容提供者受到处罚,相关负责人获罪。国内网站纷纷展开自查,删除可能触犯律令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