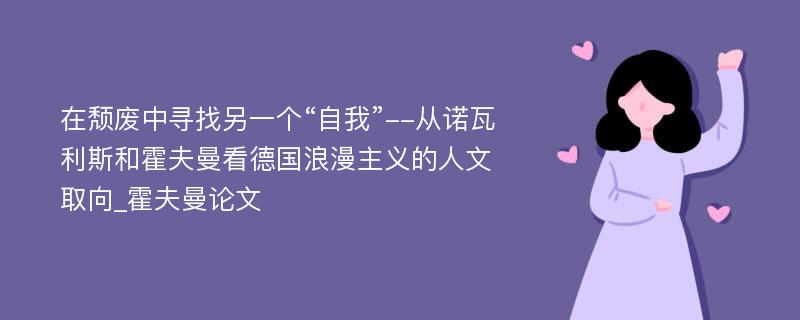
于“颓废”中寻觅另一个“自我”——从诺瓦利斯与霍夫曼看德国浪漫主义的人文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国论文,浪漫主义论文,取向论文,利斯论文,颓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在现实的无奈中退守内心
德国浪漫主义者对法国大革命一开始就抱敌视态度,对革命后的社会秩序也表示不满,这并不仅仅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还有文化态度和民族情感上的原因。在文化思想上,18世纪的法国在西方世界中属于强势国家,但德国文化人对此抱有抵触情绪。“狂飙突进运动”是德国浪漫主义的先声。狂飙运动中的青年作家们对法国启蒙哲学是排斥的,这集中表现在对理性主义的否定上。他们把启蒙哲学“冷冰冰”的理性主义看成是法国的文化霸权,这就在这些浪漫主义先驱者的怒火上增添了不满,他们本来就不愿意让自己的国家被迫处在劣势的地位。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德国在政治经济上处于明显的弱势。拿破仑时期德国的部分领土被法国占领,整个国家处于法国势力的威慑之下。这在民族感情上招致德国人对法国的不满,对大革命与法国式“自由”思想的不满,对大革命的暴力过火更是感到恐惧与抵制。他们对民族独立却有一种强烈的渴望。然而,当时德国四分五裂、国势衰微的现实,无法使他们实现民族自由与独立的理想,但这并不能泯灭他们内心对这种“自由”的渴望。因此,“德国浪漫主义者无论在法国的政治强权和理性主义的文化强权面前,都深感不满又无可奈何”(Drabble 842),正是在这种双重矛盾中他们在总体趋向上退守内心,寻找精神的自由。他们在一种压抑、恐惧、迷乱与无奈中营造着一个精神的世界。无怪乎,德国浪漫主义呈示的是一颗“扭曲的”、“病态的”灵魂。
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病态”与“颓废”的特征,确实是一种客观存在。勃兰兑斯曾将德国浪漫主义称为“病院”:
德国的浪漫主义病院里又收容了一些多么古怪的人物啊!一个患肺病的兄弟教徒,带有亢奋的情欲和亢奋的神秘渴念——诺瓦利斯。一个玩世不恭的忧郁病患者,带有病态的天主教倾向——我指的是蒂克。一个在创作上软弱无能的天才,论天才他有反抗的冲动,论无能则属于向外部权威屈服——韦里德里希·施莱格尔,一个被监视的梦想家,沉溺于半疯狂的鸦片幻境中,如霍夫曼。一个愚妄的神秘主义者,如维尔纳,以及一个天才的自杀者,如克莱斯特。(8)
这里的“病人”当然不是指像诺瓦里斯这样在生理上患病的人,而是指精神、心理、情感上“病态”的人。这种“病态”主要表现在他们作品中的怪诞、梦幻、疯狂、神秘、恐怖、悲观、厌世等等精神状态上。对此,文学史上通常给予较多指责。指出并批评这种“病态”是必要的,也是合乎事实的。然而,笔者认为,我们应该看到,德国浪漫主义文学恰恰在这种“病态”与“颓废”中曲折地表达着一种自我扩张的欲望与个性自由的理想。因此,对浪漫主义文学的新认识,重要的是要在这“病态”与“颓废”的表征背后找出特定的人文内容。
二、诺瓦利斯:在歌颂死亡与黑暗中体悟生命与自我
诺瓦利斯是德国早期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之一,也是典型的“病态”、“颓废”的诗人。诺瓦利斯是法国大革命和自由思想的竭力反对者。他的政论文“基督教还是欧罗巴”(1826年)认为,宗教改革前的欧洲是和谐统一的,宗教改革后的新教带来了自由思想,自由思想又使世界走向分裂,因此,应该恢复中世纪时期的欧洲社会秩序。他认为宗教是国家的基础,宗法制的中古世界是理想的社会。诺瓦利斯曾这样写道:
当欧罗巴还是一片基督教大陆、还是一个未分裂的基督教世界的时候,那些日子是美好的、光明的……教会的贤明的首脑理所当然地反对牺牲宗教意识而冒昧地培养人类的禀赋,反对科学领域里不合时宜的危险的发现。所以,他禁止大胆的科学家们公开宣称地球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行星;因为他非常清楚,人们如果不看重自己的家宅和地上的祖国,那么就会对天上的故里和他们的同族也丧失敬意,他们如果宁愿以有限的知识代替无限的信仰,那么就会习惯于蔑视所有伟大神奇的事物,并视之为僵死的立法而已。(转引自勃兰兑斯197)
从政治、历史角度看,诺瓦利斯的观点显然是消极的、颓废的乃至反动的,表现出了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者普遍存在的那种对现代科学、对启蒙哲学的理性主义以及资本主义新秩序的不满情绪。但是,这种情绪所体现的不只是政治态度问题——但在当时这种革命的时代,这种情绪很容易被认为是政治态度问题——还有文化态度和观念的问题。政治态度和文化态度是不应该混为一谈的。在特定时期被认为是正确的政治观点,从人类文化的角度看未必是正确的,反之亦然。毋庸置疑,诺瓦利斯站在基督教的立场敌视和反对现代科学,显然在历史观上是消极和保守乃至反动的,今天我们依然无法对之表示赞同。历史上若没有科学的进步,没有科学对迷信的宣战并取得胜利,就没有人类社会的今天,也没有今天的西方文明与文化。但是,如果针对18世纪末19世纪初西方社会中人们头脑里的科学主义、理性主义过于膨胀,人们对科学与理性的崇拜取代了对宗教上帝的崇拜的现象,针对人们凭借科学而对自我力量盲目乐观的现象,那么,诺瓦利斯的言论显然是对这种现象的一种批判。比如,他对理性主义的启蒙哲学在批判传统文化与文明中表现出来的片面性是执批评态度的。他说:“人们把现代思维的产物称为哲学,并用它包括一切反对旧秩序的事物”(转引自勃兰兑斯198)。这里,他显然对启蒙哲学的理性主义扩张表示反对。“启蒙运动和科学主义在摧毁教会统治与蒙昧主义的同时,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失落无疑使人的精神产生空虚感与无依托感”(Abrams 122-129)。这类似后来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时人们的信仰失落感。在此,诺瓦利斯的思想代表了精神与信仰追寻者的焦虑与恐慌。他说:“现代无信仰的历史是令人触目惊心的,是了解近代一切怪现象的钥匙”(转引自勃兰兑斯199)。我们不能不说,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和近代科学主义在推动西方社会走向进步的同时,又因其客观存在着在理性与科学指向上的片面性,因而带有负面性,这正是从卢梭到德国狂飙突进青年和浪漫主义者所要“反叛”的。也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诺瓦利斯那些在政治观、历史观上确有“反动”与“消极”、“颓废”的思想,在文化观上却未必没有合理性。他向往中世纪基督教时代的欧洲,固然在历史观上是复古倒退甚至是反动的,但针对18世纪末19世纪初那战争与动乱的时代,中世纪曾有的统一与宁静以及基督博爱给人的精神安抚,无疑使人有一种稳定感、安全感和道德与精神上的归属感,而这正是大革命后的西方社会所缺乏的,也是科学与理性所无法给予的。因此,诺瓦利斯的理论中隐含着对灵魂的与精神的“人”的追求,代表了当时一部分文化人对人的“自我”与本性的另一种理解与关注。当然,宗教文化固然可以充实人的精神世界,可以与科学理性文化形成对立互补之势,但如果因此就让时代倒退到中世纪去,那是不可取的,这正是诺瓦利斯理论的谬误之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诺瓦利斯如此推崇基督教世界的欧洲,但他却绝不是一个有高度自制力和清心寡欲的基督徒,而是一个执着于世俗生活、执着于个体生命之现实意义,一个“内心燃烧着最炽烈的感情”的人,“最深层、最放纵的感情就是他的原则”(勃兰兑斯180)。可见,诺瓦利斯身上似乎存在着一种令人费解的自我矛盾现象:他是宗教的和信仰主义的,又是世俗的和现实主义的。与他对科学与理性的排斥相一致,诺瓦利斯以心灵体悟的先验式宗教感悟思维,抵斥智性推理的经验式理性思维。然而,他所要体悟的又不是冥冥中冰冷的、神秘的信仰世界,而是现实中的人的炽热、真实的感性世界;他通过对这感性世界的真实体认,从而感受生命的存在、自我的存在乃至生命的意义。由此我们似乎可以看出,诺瓦利斯赞颂基督教世界,但并没有以宗教理性去抵斥人的感性世界,而是用宗教式的先验感悟去体认被当时的科学与理性遮掩了的人的感性世界,因而,他的观念在本质上又是非宗教、非信仰的,而是世俗的、感性的。由此,我们找到了更准确地认识诺瓦利斯的一个突破口。
海涅称诺瓦利斯为“死亡诗人”。确实,他的诗作致力歌颂“死亡”与“黑夜”,因此人们也很容易地就和他对基督教世界的歌颂与向往联系在一起,称他为“病态的”、“颓废的”诗人。笔者以为,这样去认识诺瓦利斯未免显得简单化——海涅亦同样如此。其实,从体悟感性世界的角度去看,诺瓦利斯的“死亡”与“黑夜”是别有一番人文意味的。
“夜的颂歌”(1800年)可谓是使诺瓦利斯获得“死亡”与“黑夜”诗人“桂冠”的代表性作品。它是作者为悼念早逝的恋人苏菲·封·库恩而作的。诺瓦利斯爱上苏菲时,她只有12岁,而在15岁时,她因患肺痨死去。苏菲的去世,使诺瓦利斯痛不欲生。在“夜的颂歌”中,他把由爱而生的痛苦转变为对死的渴望与夜的歌颂。作品的第一章里,他这样写道:
我转而沉入神圣的、不可言传的、神秘的夜。世界在远方,仿佛陷进了深邃的墓穴:它的处所荒凉而孤寂。胸口吹拂着深沉的忧伤……黑魆魆的夜呀,你可曾在我们身上找到一种欢乐呢?……从你的手里,从罂粟花束上滴下了珍贵的香油。你展开了心灵的沉重的翅翼……我感到光亮是多么可怜而幼稚啊!白昼的告别是多么可喜可庆啊……夜在我们身上打开的千百万只眼睛,我们觉得比那些灿烂的群星更其神圣。他们比那无数星体中最苍白的一颗看得更远;它们不需要光,就能看透一个热恋的心灵的底层,心灵上面充满了说不出来的逸乐。赞美世界的女王,赞美神圣世界的崇高的宣告者,赞美极乐之爱的守护神吧!她把你送给了我,温柔的情人,夜的可爱的太阳。现在我醒了,因为我是你的,也是我的:你向我宣告夜活了,你使我变成了人。用精神的炽焰焚化我的肉体吧,我好更轻快,更亲切地和你结合在一起,永远过着新婚之夜。(转引自勃兰兑斯189)
诺瓦利斯描写的“夜”,不是通常万籁俱静、一片漆黑令人恐怖的夜,而是一个潜伏和充盈着生命欲望的冲动、“不需要光”却又比白昼更透亮的令人充满“逸乐”的夜,此乃作者幻想的、憧憬的心灵之夜。在这样的“夜”里,万物隐退,白昼里沉睡的“自我”醒了,仿佛是“夜”把“我”赋予了肉身。在此,自我的感觉是如此超常的清晰,于是,这“夜”就像“在我们身上打开的千百万只眼睛,我们觉得比那些灿烂的群星更其神圣”,我们借此“就能看透一个热恋的心灵的底层”,随之,心灵里产生了难以言说的“逸乐”。在如此的境界中“永远过着新婚之夜”,这是在白昼中难以感受到的爱的体验、自我的体验、生命的体验。所以,诺瓦利斯描写“黑夜”,歌颂“黑夜”,并不是在歌颂夜之死寂、黑暗与恐怖,而是在借夜之黑暗去突出心灵对生之欢悦的体悟,并通过这种体悟去感受生命和自我的存在。这是一种对生命的执着。
由此我们再联系到诺瓦利斯对“死亡”的歌颂,又可以看到他描写的“死亡”背后强烈的生之欲望。他在“夜的颂歌”中写道:“我漫游进死亡/那天,每一种痛苦都会成为/激动的喜悦/一瞬间,我自由了/沉醉在爱的源头/无限的生命;在我心中有力地生长/……啊,耗尽我吧,我的爱侣/我要最猛烈地去沉睡和爱/我想到了死亡更新万物的潮水/我的血液/变成柔软的香脂和苍天/因为生活于白昼之时/我充满体会和勇气/当黑夜降临/我死于神灵之火”(转引自勃兰兑斯191)。一如借黑夜去突出自我对生命的感悟,这里,诺瓦利斯也是借“死亡”对生命的威胁,“死亡”对人的心灵引起的恐惧与震颤,去更强烈、真切地感悟生命的存在。“我”步入“死亡”后产生的“无限的生命”。在“死亡”中“猛烈地沉睡与爱”,表达的正是在生之时难以感受的强烈的生命冲动和爱的体验。
总之,在“黑夜”中洞悉光明,在“死亡”中感悟生命,在极度的痛苦中体悟深沉的爱,这就是所谓“死亡诗人”和“黑夜诗人”诺瓦利斯的诗所致力于追求的境界。当我们联想到中世纪的厌世主义者抛弃现世的生命欢乐,追寻死后天国的永恒的极乐时,我们分明可以看到诺瓦利斯对人的个体生命有执着之爱。正是由于对生命的强烈之爱,导致了他对死亡的极度恐惧;为了消除这种恐惧,于是他赞美死亡,赞美黑夜,赞美疾病!在所有的这些赞美中,永远深藏着一颗炽烈而怪异的心灵,一个感性而内倾的“自我”。
三、“鬼怪霍夫曼”:自我的二重化
霍夫曼的“病态”或“颓废”在于他总是以怪异的眼光观察人的心灵,并在作品中热衷于描写神秘、怪诞、阴森、恐怖而又不乏滑稽感的形象。“这个一心一意观察自己心境、观察别人荒诞行径的人,对自然很少感觉”。在日常生活中,他有与常人不一样的“过分敏感、过分紧张的神经”(勃兰兑斯163)。他常常把酒当作兴奋剂,“每逢在酒精的影响下,他会突然看见黑暗中闪现着磷火,或者看见一个小妖精从地板里钻出来,或者看见他自己周围是一些鬼怪和狞恶的形体,以各种古怪装扮出没无常。”“他的许多灵感,许多幻想,那些开始只是出自想象,后来越来越认真的错觉,大都得之于酒”(勃兰兑斯163)。他对人与世界的这种怪异的观察,我们可以从他的日记中看到:
一八○四——从四时到十时在新俱乐部饮比肖夫酒。傍晚极度兴奋。这种加香料的烈酒刺激所有神经。突然想到死亡和离魂。
一八○九——在六日的舞会上突发奇想。我通过一个万花筒设想着我的自我——在我周围活动的一切形体都是一些自我,他们的所为和所不为都使我烦恼。
一八一○——为什么我睡着、醒着都常常想到疯狂呢?(转引自勃兰兑斯163)
由于霍夫曼这种怪异的心理气质,他总是为一种神秘的恐怖感所折磨,甚至害怕自己生活中出现离魂及各种狞恶形象,以至他的整个生活溶化成为情绪。由此,他观察人,也总是关注人的情绪和心理状态,把人生分解为各种情绪:“浪漫的宗教情绪;紧张到使我经常多生疯狂思想的、兴奋的情绪;幽默的愤慨情绪;音乐般的激昂情绪;荒诞的情绪;发展到极端浪漫、极端反复无常的最愤慨的情绪;坦白地说吧,还有莫名其妙的恶劣情绪,非常兴奋、但像诗一样纯洁、十分舒适、粗鄙、嘲讽、紧张而又乖张的情绪,以及十分颓废、异样而又糟糕的不热情、不高昂的情绪”(勃兰兑斯172)。霍夫曼从自己这种怪异的心理气质出发进行文学创作,“按照自己的模型创造了他的主要人物”(勃兰兑斯172),“把自己对于鬼怪的恐怖也传达给他所创造的人物了”(勃兰兑斯164),以至于人们称他为“鬼怪霍夫曼”。
“鬼怪霍夫曼”的小说创作典型地表现了德国浪漫派文学的特色。他的作品往往借助离奇的想象,描写怪诞的情节,塑造神秘古怪的人物,展现幻想与现实交融的世界。正是在这种离奇怪诞的描写中,展示了人的双重自我以及为自我冲突而生的心理张力。
《金罐》(1814年)是霍夫曼早期的作品,它描写了一个童话般离奇的故事。从《金罐》的显层意义上看,故事对世俗世界和超世俗世界作了对照描写,并明显地肯定了充满诗意的超世俗世界,否定了庸俗、丑恶的世俗世界,因而小说具有批判现实的意味。从隐层意义上看,《金罐》又揭示了人内心深处幻想与现实、世俗与信仰、无限与有限、精神与物质、灵与肉等多重矛盾,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人的自我的分裂。大学生安泽尔穆斯生活在客观的现实世界里,体验到了生活在世俗之中的平庸的“自我”,幻想又使他陶醉于充满诗意的超世俗的世界,体验着保留了纯真童心的“自我”。妖婆的魔镜似乎是两个世界的中介,使他时而生活在平庸的现实中,时而生活在纯真的幻想世界中,从而生活在双重自我的矛盾中,因此,对立的世俗世界与超世俗世界恰恰是安泽尔穆斯双重自我的外化。正如歌德笔下的浮士德,内心深处隐藏着不同走向的双重“自我”,一个要与另一个各奔东西。不同的是,歌德描写人物的双重自我,完全隐身于人物的内心世界,并通过内心矛盾冲突展示出来;霍夫曼则把这内心世界的两个自我借助离奇的想象、怪诞的情节外现于两个不同的世界,从而使人的双重自我呈分裂的状态。小说中的档案管理员也是一个双重身份的人:白天是管理员,是人,夜晚是一条蛇。因而,他白天奉公守法,过着严谨而规范的官场生活;晚上则放纵自我,过着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这实际上也表现了档案管理员自我的双向分裂:不满足现实的平庸生活,又无法挣脱它;既向往满足欲望的自由生活,又无法真正进入这种生活境界。其实,这是人的内心世界普遍存在的双重自我。
霍夫曼小说中最能表现这种自我分裂的作品是他的《魔鬼的万灵药水》(1815-1816年),它也是霍夫曼的代表作。小说借“魔鬼的万灵药水”把处于平静中的梅达杜斯推向欲火焚烧而又自我矛盾的情境之中。小说又用相貌酷似梅达杜斯的“疯修道士”把真正的梅达杜斯的自我从空间与时间上分成两半,使梅达杜斯处于人格分裂、找不到完整自我的精神狂乱之中。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是我表面上的那个人,我表面上却不是我真正的自己;我认为我自己是一个解不开的谜,我竟同我的自我发生了龃龉!”(转引自勃兰兑斯165)人物的自我分裂,不仅使霍夫曼的小说充满了心理张力,还增添了怪诞与神秘的色彩,这是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突出特征。
启蒙哲学从宗教的蒙昧主义中解放出了人的理性的自我,却又通过对理性的过分强调而蒙蔽了感性的自我,遮蔽了人的心灵与情感的多姿多彩和矛盾冲突。启蒙思想家在张扬了人的理性思维和认识与感知能力的同时,忽略了人的感性与直觉的体悟能力;在肯定了理性自我的同一性与稳定性的同时,忽略了感性自我的差异性与多变性。浪漫主义特别是德国浪漫派所张扬的恰恰是启蒙思想家、文学家所忽略的感性的自我与心灵的世界,从而展示了多变的、不稳定的和具有非理性色彩的自我,进而从另一侧面展示了人性的丰富性。
被勃兰兑斯称之为精神“病院”的德国浪漫派,从诺瓦利斯到蒂克、施莱格尔、霍夫曼、沙来索、维尔纳到克莱斯特,都是内心敏感、善于体悟人的情绪与心理状态,热衷于描写离奇怪诞充满神秘色彩事物的作家。他们对人的感性自我的关注远远胜过对理性自我的张扬。他们热衷于表现的怪诞、梦幻、疯狂、神秘、恐怖等等,恰恰是人的理性的触角所难以指涉的感性内容。诺瓦利斯用“黑夜”、“死亡”以及相伴而来的巨大的痛苦与恐惧,去强有力地表现对爱与生命的渴望,其间隐藏着一个被压抑而又力图扩张的自我。
霍夫曼如此关切人的自我并总是表现双重的、分裂的自我,标示着他对人的内宇宙和感性世界的关注。理性主义所理解的自我是完整同一而稳定的,然而事实上这只不过是显意识层面的自我而已。人的感觉是不稳定的,人的深层意识对自我的体认可能是自我矛盾的,这就导致了自我的双重性、多重性与自我分裂。霍夫曼的小说通过梦幻、错觉、疯狂等,把被理性主义遗忘了的人性的感性内容以一种不稳定、不完整的形态显示出来,同时也把人物的深层意识通过双重或多重“自我”的矛盾冲突展示出来。因此,霍夫曼等浪漫派作家对人的双重自我的关注,正说明了他们对人自身的关注,特别是对人的感性世界、深层心理的关注。可见,无论是诺瓦利斯还是霍夫曼,虽然他们与宗教、与神秘主义有着密切联系,但宗教与神秘主义并没有使他们变得愚昧守旧,而是使他们步入了启蒙作家与思想家所极少涉足的人的深层心理与感性世界,他们使“人”更贴近了精神的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