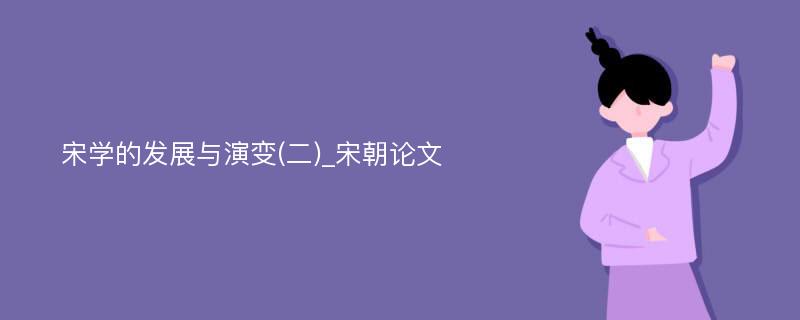
宋学的发展和演变(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宋学诸家多汲取老庄佛图的思想,以丰富自己,理学诸家也并不例外。但理学家们为了把自己说成是纯而又纯的儒家正宗,则千方百计地回避这一问题。然而事实俱在,又怎么能够回避得了呢。约50年前在昆明西南联大历史系读书时,曾从冯芝生友兰先生学《中国哲学史》课程,深服先生博学高识。冯先生曾经指出,程明道程伊川兄弟二人形成了此后对立的两大派别,陆九渊的心学派来自于程明道,而朱熹的理学派则传自程伊川。心学一派显然受禅宗的影响,从程明道那里已见端倪,试看下面的记载:
谢显道习举业,已知名,入扶沟见明道先生受学,志甚笃。明道一日谓之曰:尔辈在此相从,只是学某言语,故其学心口不相应,盍若行之?请问焉。曰:且静坐。伊川每见人静坐,便叹其善学。(56)
按程明道用静坐的办法,让学者解决“心口不相应”的问题,这种方法与佛家的禅定有什么两样?至于陆九渊的明乎本心与禅宗顿悟之间的联系,学术界早已说过。朱熹不止一次地称“江西之学只是禅”(57),说明了明道系统的理学受佛家禅宗的影响。鹅湖之会,朱揭陆为禅,陆揭朱为道,双方揭得都对,两大系统的理学都各自吸取了佛道的思想。可是,为了争正统,都隐瞒不说。朱陆两家都强调以诚以敬磨练自己,他们自己都在说谎话,又怎么能够管得住他们的弟子不说谎话呢?
(3)理学和宋学都探索经学,但理学是宋学的一支,是从宋学演变来的,那末,理学和宋学的基本区别是什么?过去不谈宋学,无从提出这个问题,而现在必须回答这个问题。先看看朱熹对苏轼等的评论:
……东坡与伊川是争论什么?只看这处,曲直自显然可见,何用别商量?只看东坡所记云:几时得与他打破这“敬”字!看这说话,只要奋手捋臂,放意肆妄,无所不为,便是。
问:“东坡与韩公如何?”曰:“平正不及韩公。东坡说得高妙处,只是说佛,其他处又皆粗。”又问“欧公如何?”曰:“浅!”久之,又曰:“大概皆以文人自立。平时读书,只要把做考究古今治乱兴衰底事,要做文章,都不曾向身上做工夫,平日只是以吟诗饮酒戏谑度日。”(58)
按“敬”字是程氏兄弟从事内心反省工夫的一个总结或概括,在洛学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前面曾经提到。东坡要打破伊川洛学的这个敬字,深刻反映了苏氏蜀学与洛学之间的分歧。这个分歧表现在:洛学把敬字亦即其内心反省工夫放在绝对重要的位置,因为它是实现儒生们(更明确地说理学家们)最高理想--“内圣外王之道”的根本,而苏学则没有把这种内心反省工夫看得多么重要。唯其如此,所以朱熹非常明确地说,欧阳修、苏轼等“皆以文人自立”,“都不曾向身上做工夫”。从宋学派生出来的理学,把内心反省工夫放在首位,脱离社会现实的实践,以静、诚、敬等向自己身上使劲,这大概是理学之异于宋学的一个基本点。
按我国古代教育,自儿童时即通过洒扫应对进退给以相应礼节教育,以期在其生活行为上具有一定的规范。胡瑗以“冬日之阳”教导学生,但在继承上述传统教育时对学生则严格要求,前举徐仲车一入太学胡瑗即要求其“头宜正”,即是一例。这种规范教育不能不影响于个人的身心修养,胡瑗的教育方法不能不给程氏兄弟以极其深刻的影响。特别是程颐在太学时,所作《颜子所好何学论》一文,强调圣人是可以学而致之的,深受胡瑗的称赞和提拔。而这种圣人可学而致之的见解,同来自胡瑗的个人身心修养工夫相结合,于是从安定之学过渡到程氏兄弟的内心反省这一基本点,从而完成了洛学的转变。程氏兄弟称周敦颐的字,茂叔如何,而对胡瑗终身以先生呼之,这大概是由学术上的这一渊源及其重要转变造成的吧!
(4)程氏兄弟的“洛学”形成于熙丰之间的十七八年间,程颢自变法派中游离出来,因而程学处于民间。这个以发扬圣人之学自居的学派,在服饰上也有其特点,幅巾大袖与一般人不同。“绍兴初,程氏之学始盛,言者排之,至议其幅巾大袖。胡康侯力辩其不然,曰:伊川衣冠未尝与人异也。然张文潜元祐初赠赵景平主簿诗曰:明道新坟草已春,遗风犹得见门人。定知鲁国衣冠异,尽戴林宗折角巾。则是自元祐初为程学者幅巾已与人异矣。衣冠近古,正儒者事。讥者固非,辨者亦未然也。”(59)“伊川所戴纱巾,背后望之如钟形,其制乃似今道士谓之仙桃巾者”(60)。此虽系细微末节,但牵涉到理学派的形象,也在此一提。
南宋乾道淳熙时候,一个名叫员兴宗的四川士大夫曾对荆公之学、洛学和苏学作过如下的评论:
昔者国家右文之盛,蜀学如苏氏,洛学如程氏,临川如王氏,皆以所长,经纬吾道,务鸣其善鸣者也。……考其渊源,皆有所长,不可废也。然学者好恶,入乎彼则出乎此,入者附之,出者污之,此好恶所以萌其心者。苏学长于经济,洛学长于性理,临川学长于名数,诚能通三而贯一,明性理以辨名数,充为经济,则孔氏之道满门矣,岂不休哉!……今苏、程、王之学,未必尽善,未必尽非,执一而废一,是以坏易坏。置合三家之长,以出一道,使归于大公至正。(61)
员兴宗对三家所学之长的评论是否正确,是另一问题,但他认为三家各有所长,不可偏废,则值得注意。按员兴宗蜀人,对苏学不能不有所偏向,而在其写作是文时,程氏洛学正为显学,而荆公之学则受到宋高宗的不遗余力的打击,此时强调了不可偏废,“合三家之长,以出一道”,这样才算“归于大公至正”,不啻为受压制的荆公之学鸣冤叫屈,从这一侧面也反映了,荆公之学即使到宋孝宗时在社会上仍然有它的重要影响。
四、宋学的演变阶段
南宋是宋学发展演变的第三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从宋学中发展起来的理学则兴盛起来,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学派,同时与理学对立的则是浙东事功派。下面围绕三个问题加以叙述。
(1)理学在南宋初年高宗朝已经取得很大的发展。陈亮在《送王仲德序》一文中,即已谈到这个发展的趋势:
二十年之间,道德性命之说一兴,迭相唱和,不知其所从来,后生小子读书未成句读,执笔未免手颤者,已能拾其遗说,高自誉道,非议前辈,以为不足学矣。(62)
本师邓恭三先生在《略谈宋学》一文中,考订此文写作于1190年前,上推二十年,道德性命之学是在“宋孝宗即位之初期,亦即隆兴乾道年间(1163-1173)”发展的。前面说过,二程洛学形成熙丰之际,处于民间。一个影响不大的学派经靖康乱后,到宋孝宗即位之初成为社会上有如此重大影响的学派。很明显,它在宋高宗一朝取得很大发展。
为什么二程系统的道学能够在宋高宗朝发展起来?程门嫡传弟子杨时以及胡安国父子在朝野上下的努力提倡,对二程理学的发展当然有重要作用。但尤为重要的是,高宗一朝的客观历史环境,给程系道学提供了充分发展的土壤和条件,这是首先值得注意的。从北宋末到南宋初,是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交织发展,而以民族矛盾作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时期。在这个非常时期建立起来的以宋高宗为首的南宋王朝,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方针、政策来应付这个极其严峻的政治局面?从最本质最根本的方面来看,由宋高宗-秦桧一小撮当权者集团制订的、实质上是卖国投降的对金和议,是宋高宗一朝的总方针总政策。它的具体表现是:
(甲)为实现其卖国投降的主张,在政治上不遗余力地打击抗战派,逐步地把军队纳诸宋高宗-秦桧卖国投降的政治轨道上,加强对内的控制和镇压,最后在时机成熟之际,惨杀岳飞等爱国将领,签订卖国投降的和议。
(乙)为实现这个卖国投降的反动政策,宋高宗-秦桧集团便十分需要舆论上、思想上乃至学术上与这个反动政策来相配合、呼应。而胡安国的《春秋传》就是在学术上与之积极配合呼应的一个例证。
《春秋传》三十卷,胡安国“潜心是书二十余年,以为天下事物无不备于此”,并自诩为“传心要典”(63)。四库馆臣们称这部书,“多借以托讽时事,于经义不尽相符”(64)。楼钥在《春秋后传序》中论及胡安国《春秋传》的学术地位说:“自王荆公安石之说盛行,此道(指《春秋》之学)几废,建炎绍兴之初,高宗皇帝复振斯文,胡文定公安国承伊洛之余,推明师道,劝讲经筵,以后复传,学者以为标准。”(65)现在就看看,承伊洛二程之学的胡安国,是怎样借解释《春秋》之际“托讽时事”的。
在鲁僖公十八年秋八月丁亥葬齐桓公条下,胡安国发挥其义理道:
〔桓公〕虽名方伯,实行天子事,然而不能慎终如始,付托非人,柩方在殡,四邻谋动其国家而莫之能恤,至于九月而后葬,以此见功利之在人浅矣。《春秋》明道正义,不急近功,不规小利,于齐桓晋文之事有所贬而无过褒以此。(66)
胡安国是根据孟子有关齐桓晋文的评论而阐发的,义理之所在主要体现从孟子董仲舒到二程要义不要利的义利观。胡安国的这个议论,对现实政治生活,也不是无的放矢,而是针对朝廷上批判荆公之学而发的,后面还要提到。在鲁隐公十年鲁公子翚帅师伐宋条下,胡安国发挥其义理道:
夫乱臣贼子积其强恶,非一朝一夕之故,及极势之成,威行中外,虽欲制之,其将能乎?故去其公子,以戒兵柄下移,制之于未乱也。(67)
在鲁庄公二年夏公子庆父帅师伐于馀丘条下说:
(馀丘,邾邑也,其曰伐)志庆父云得兵权也。庄公幼年即位,首以庆父主兵,卒致子般之祸……鲁在春秋中见弑者三君,其贼未有不得鲁国之兵权者。(68)
在鲁闵公二年十二月郑弃其师条下说:
……人君擅一国之名宠,杀生予夺,唯我所制尔,使[高]克不臣之罪己著,[郑伯]按而诛之可也;情况未明,黜而远之,可也;爱惜其才,以礼驭之可也;
焉有假之兵权、委诸境上,坐视其失伍离散而莫之恤乎?然则弃师者,郑伯!(69)按胡安国在其所著《春秋传》序言中曾说,他的这部书的写作是“尊君父,讨乱贼,辟邪说,正人心,用夏变夷,大法略具,庶几圣王经世之志,小有补云”。上述引文,胡安国左一个兵权,右一兵权,一再强调兵柄之重要,而不能为乱臣贼子占有,这些对谁说的,又对谁“有补”呢?今查《宋史》《胡安国》本传,胡安国于绍兴元年(1131)“兼除侍读,专讲《春秋》”,绍兴五年(1135)“提举江州太平观,令纂修所著《春秋传》”,“书成,高宗谓深得圣人之旨,除提举万寿观兼侍读”。此前,胡安国受朱胜非排挤之时,“右相秦桧之上章乞留之”。上述这些,足可以说明胡安国与宋高宗秦桧之间的关系。胡安国之受到宋高宗的重视,是很清楚的。宋高宗曾说:“他人通经,岂胡安国比!”胡安国《春秋传》中有关兵柄不可下移的观点,宋高宗秦桧是非常熟悉的。绍兴五年前后的六七年间,正是朝延上宋高宗-秦桧集团吆喝收夺大将兵权的关键时刻。而在这个关键时刻包括张浚、赵鼎、吕颐浩甚至李纲在内,都在吆喝收夺兵柄。而胡安国向宋高宗秦桧们一再灌输兵柄之不可下移,难道说对宋高宋-秦桧集权收夺大将兵权无任何作用?姚瀛艇等同志《宋代文化史》最先注意到胡安国的这些言论,并引用了王夫之《宋论》进行了评论(70)。王夫之在《宋论》上说,“尝读胡氏《春秋传》而有憾焉”。他认为胡安国对公子翚之伐郑、公子庆父之伐于馀丘,“两发兵权不可假人之说”是“考古验今”的,与秦桧是“以志合相奖”的。不论怎样说,胡安国《春秋传》是从思想上学术上配合了呼应了这样宋高宗-秦桧集团收夺兵权的政策,为这个集团的卖国投降不是“小有补”,而是“大有补云云”。“承伊洛之余,推明师道”的胡安国立了功,二程系统的道学之受到宋高宗朝的重视也就可以理解的了。
(丙)宋高宗为维护赵姓的统治,开脱乃父宋徽宗的亡国罪责,将全部罪责推卸给蔡京,又转弯抹角地推卸给王安石和王安石变法,为此不遗余力地打击王安石,打击荆公之学。绍兴四年(1134)八月,宋高宗令范冲修改神宗哲宗“两朝大典”。范冲趁机攻击王安石“尽废祖宗法度,上误神宗皇帝,天下之乱实兆安石”。宋高宗认为“极是”,并且表了态,“朕最爱元祐”。宋高宗又论王安石之奸,“至今犹有说安石是者,近日有人要行安石法度,不知人情何故直至如此”。范冲重复了程颐对王安石的诬蔑,称其“心术不正”,“顺其利欲之心”,故“为害最大”(71)。翌年三月,兵部侍郎王居正献《辩学四十二》,“以旧所论著王安石父子平昔之言不合乎于道者献之”。王居正曾问宋高宗:“久闻陛下深恶王安石之学久矣,不识圣心灼见,其弊安在?”宋高宗回答道:“安石之学杂于伯道,取商鞅富国强兵,今日之祸,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乱生于安石。”(72)宋高宗从政治上彻底否定了王安石和荆公学派,认为北宋亡国之祸“生于王安石”。
二程系统的道学,与宋高宗的这些谬论是合拍的。立雪程门的嫡传弟子杨时,是蔡京汲引起来的人物,一般材料没有记载也许是讳言这件事情,但一篇小说《勘皮靴单证二郎神》倒是记录了这个事情。这位为蔡京汲引的程门道学家,于蔡京垮台之后又成为后蔡京的英雄,是他最早把北宋亡国之祸同王安石联系起来的:“[蔡]京以继述神宗为名,实挟王安石以图身利,故推尊王安石”;“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还称“[王]安石挟管商之术,饰六艺以文奸言,变乱祖宗法度”(73)。试看杨时的这些话,同宋高宗所说的是多么一致!在绍兴四、五年朝廷上反王安石、荆公之学的一片叫嚣中,胡安国也是参加这个大合唱的。前引《春秋传》对功利的批评,就是指向王安石、荆公学派的。《宋史杨时传》(卷四二八)针对杨时南宋初年的活动及其影响说道:“凡绍兴初崇尚元祐学术,而朱熹、张栻学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脉络皆出于时。”总之,宋高宗是以二程系统的道学从政治上、学术上打击王安石,二程系统的道学家如杨时胡安国也趁机攻击王安石、荆公之学,向南宋反动政府靠拢,从而借助这个反动政府发展程系道学的。
宋高宋-秦桧集团的卖国投降政策终于付诸实现。自绍兴和议以后,轰轰烈烈的抗金斗争被压制下去。尽管“中原父老望旌旗”,但是以宋高宗秦桧为代表的反动统治阶级却沉浸在罪恶的縻烂生活之中。到处是灯红酒绿,到处是歌舞升平。在这样空虚的时代里,就只有空洞无物的“道德性命”的说教,来装饰这个时代。这是理学得以发展的客观环境。而且,在宋高宗-秦桧集团推行其卖国投降政策之时,程系理学杨时、胡安国等在思想上、学术上与之呼应、配合,从而得到南宋政府的支持,程系理学成为了显学。当然,也要看到,秦桧也曾迫害过胡氏父子,不遗余力地打击程系理学。但程系理学终于得到此前未有的大发展,像陈亮所说的那样,在高喊“道德性命之说”的人群中,情况是很驳杂的,应当像当年孔夫子所说,有不少的甚至是大批的“小人儒”。但也就是在道学驳杂的队伍中,到乾道淳熙年间,出现了在社会上负有盛名的三个讲学家,即朱熹、张栻和吕祖谦。至少前两人即朱熹和张栻,是伊洛理学的继承者和发扬者。他们要算是这个时代的君子儒了。当然,在他们之间,思想上也是有所不同的,例如前面说的朱熹和陆九渊,就代表着两个不同的理学派别。
(2)在理学大发展的时期,则形成了与理学对立的浙东事功派。事功派主要由金华学派吕祖谦、永康学派陈亮、永嘉学派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为代表的。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都出生于南宋的浙东路,称为浙东学派;在思想上,他们之间也有分歧,但他们共同继承北宋从范仲淹到王安石宋学主流中的重实际、讲实用、务实效的思想观点,所以称之为浙东事功派。这个学派同南宋朱陆为代表的理学在认识上、思想上有着严重的分歧,它主要地表现在:
(甲)自韩愈的《原道》以来,强调周公孔子以下形成一个完整的、渊源有自的道统,表示韩愈们是儒家正统的继承者,理学家们继承了这个道统论,二程成为儒家的正统,借以提高他们的地位。对这个根本性的大问题,浙东事功派则持怀疑的否定的态度,对此问题最先发难的是薛季宣,他在两道策问中先后提出了“道学之统、源流之辨”的问题(74),以及“传道之序”,认为从形式上看,“自孔子、曾子、子思、孟轲,端若贯珠”(75),似乎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可是从年龄上看,此前的记载,“记事参错”,应当“祛其妄而辨其惑”,由此来说明道统之序的不可靠。叶适继之,在《习学记言》,中称:“孔子没或言传之曾子,曾子传子思,子思传孟子”,认为“孔子自言德行颜渊而下十人无曾子”,而且“参也鲁”;也许“曾子于孔子没后德加尊、行加修”,能够单独继承孔子之道,“然无明据”(76)。这是浙东事功派以其史学方面的专长,对理学家道统说的一个致命性的打击。
(乙)正因为浙东事功派重实际、讲实效,所以他们对理学家们尽心言性的空谈,无补于社会的实际,表示极大的不满。在这个问题上,浙东事功派一再提出评议,其中陈亮以其犀利的笔锋,给以深刻的批判。他说:
往三十年时,亮初有知识,犹记为士者必以文章行义自名,居官者必以政事书判自显,各务其实而极其所至,人各有能有不能,卒亦不敢强也。自道德性命之说一兴,而寻常烂熟无所能解之人,自托于其间,以端悫静深为体,以徐行缓语为用,务为不可穷测,以盖其所无,一艺一能,皆以为不足自通于圣人之道也。于是,天下之士始丧其所有而不知适从矣!为士者耻言文章行义,而曰“尽心知性”;居官者耻言政事书判,而曰“学道爱人”;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77)
陈龙川对理学的这一批判是多么精彩。我们一些理学研究工作者,如果读读这篇文章,从理学的对立面去观察理学,就不致把作为传统文化的理学说得完善无缺了。
(丙)浙东事功派务实精神是深得北宋以来宋学的精髓,但也仅仅限于思想上。浙东事功派也没有形成一个强大的力量,在政治实践中实行自己的务实的主张。但浙东事功派在这方面的论述,则是充满了活力的。吕祖谦在给朱熹的一封信中,曾称薛士龙(即季宣)“向来喜事功之意颇锐”,“于事务二三务如田赋、兵制、地形、水利甚曾下工夫,眼前殊少见其比。”(78)薛季宣在回答薛象先的信上说:“务为深醇盛大,以求经之正;讲明时务本末利害,必周知之,无为空言,无戾于行”(79),来表明他对治学的态度。在给一位心学派理学家杨简的信中,薛季宣指出,“灭学以来”把“言学判为两途”的偏颇不对,称“那些矫情之过者,语道乃不及事”,徒发空论,等于无知,表明他对那些“清淡脱俗之论”,“未能无恶焉”(80)。因此,他对那些“言道而不及物”的空谈家,视为“今之异端”(81)。不言而喻,薛季宣的这些话,是他立足于事功的立场上对那些空洞无物的道学家而发的,从而表现他们之间的对立。
(丁)由于理学同浙东事功之学存在上述的原则性分歧,因此在一系列的重大问题上,诸如理欲观、义利观和历史观诸方面,都是对立的。在理欲观上,程朱理学派强调“存天理,灭人欲”,把一般人的基本生活欲望也要灭掉,而浙东事功派中的陈亮则主张节欲,承认人们的基本的生活欲望。在义利观上,理学家们从二程到朱熹,把义和利对立起来,要义不要利,继承了孔孟、董仲舒到司马光等儒家正统派的观点;浙东事功派则继承了李觏、王安石的义利观,进一步发挥了义利统一论。对上述问题,我在《宋代经济史》(下册)有关经济思想的部分,作了叙述,这里不多赘。
(戊)理学同浙东事功之学之所以存在如此重大的分歧,从学术思想的渊源看,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是,浙东事功派学者出乎经而入乎史,他们在史学上都有所成就和贡献,而南宋的理学则纯本乎经学,虽然朱熹本人对史是极其熟悉的,也是有其见解的。对这一点,朱熹是非常清楚的,他说,“伯恭(吕祖谦)、子约(吕祖俭)宗太史公之学”,“抬司马迁不知大小,恰比孔子相似”;“伯恭于史分外仔细,于经却不甚理会”;“伯恭更不教人读《论语》”(82)。朱熹还批评陈亮,“看史只如看人相打,相打有甚好看处?陈同父一生被史坏了”(83)。朱熹对史学的评论自然是偏颇不对的,无须多论。刘向刘歆父子在议论先秦诸子学术源流时,增提出“诸子出于王官”之说,这里也不必多论,他们认为,“道家者流”的主张,之所以能成为“君人南面之术”,是由于道家“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抓住了“秉要执本”的根本道理而成功的(84)。浙东事功派通过对历史的探索,不仅对历代典制因革变化提出了不少有益的见解,而且从历史发展过程中了解了一些切合现实的一些问题,从而丰富了自己的学说。
(己)当然,在浙东事功学派中,对许多问题的认识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差别。吕伯谦同张栻、朱熹分别在浙、楚、闽三地讲学,是宋孝宗一朝非常有影响的著名学者。虽然朱熹对他有不少的议论,但不论怎样说,吕祖谦是浙东事功派中最接近于理学家的一个。他曾经强调,“儒者当通世务”(85),认为“儒者所悖以胜功利之说者,执圣人之经也”(86)。看起来,吕祖谦当是理学转向事功之学的一个代表人物,处于理学向事功之学转化的中间环节。陈亮则是浙东事功学派中最为激进的一个,他非常赞成戴溪(永嘉学派中的一员)“财者人之命”这个说法,认为是“真切而近人情”(87);同时还认为,只有破仁、义、礼、智、信所谓的“五贼”,亦即破仁义道德之类的说教,才能够发家致富(88)。陈亮的思想在某些方面已经突破了儒家思想的范围。永嘉诸子如薛季宣、陈傅良和叶适,算是事功派中的温和派。虽然有上述区别,但浙东事功派的基本观点则是一致的。
(庚)浙东事功之学继承北宋宋学的务实精神,成为南宋独树一帜、赋有特色的学派。朱熹曾称“浙学却专是功利”,认为这个学派要比陆九渊的“禅学”难办得多:“禅学后来学者摸索一上,无可摸索,自会转去。若功利,则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甚可忧!”(89)把事功之学看成为自己的理学最为厉害的对手。
(3)前面从宋学发展演变的总趋势看,南宋宋学已不像北宋那样发展了,而且在演变中理学兴盛起来了。尽管理学在南宋晚期得到政府的支持,元明两代得到顺利发展,但在南宋兴盛阶段中,已隐伏了它的不可避免的衰落因素。根本原因在于,理学已经失去了宋学那样勃蓬发展的气势,从日益空疏之中,使其生命力日益萎缩的。下面就围绕这个问题加以叙述。
从理学正统程氏兄弟说起,他们所追求的唯一的事物,就是把“道”放在绝对的不可动摇的位置上,把一切他们认为有害于“道”的事物摒诸一旁。程颐曾明确地指出:“今之学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牵于训诂,三惑于异端。苟无此三者,则将何归?必趋于道矣!”(90)异端指的是释老,无须多论,因作文、作诗在程颐看来,都是有妨碍“道”的:
问:“作文害道否?”曰:“害于道。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天地同其大也?《书》曰:‘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91)
或问:“诗可学否?”曰:“即学时,须是用功,方合诗人格。既用功,甚妨事。……某素不作诗,亦非是禁不作,但不欲为此闲言语”(92)。
学者先学文,鲜有能至道。至如博观泛览,亦自为害,故明道先生教
余曰:贤读书,慎不要寻行数墨(93)。程氏兄弟把作文看作是“玩物丧志”,把诗歌看作是“闲言语”,把阅读古书的必须具备的基本功--训诂工夫,以及把取得知识的“博观泛览”,也都认为是“有害于道”而予以摒除;那末,以程氏兄弟为正统的洛学,就只有依赖所谓的内心反省、静坐冥想,去追求那个虚无缥缈的“道”了!
继程氏兄弟,并成为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在如何摄取各种营养,以充实自己的性理学的各方面,也存在极严重的缺陷。如何看待作文写诗,朱熹则继承了二程的见解,称“近世诸公作诗费工作,要何用?”“今言诗不必作,且道恐分了为学工作。就到极处,当自知无益。”(94)诗固然要不必作,作文也是一样:“才要作文章,便是枝叶,害着学问。”(95)朱熹认为,“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只要能够“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这就是说,“文”不必学,就自然而然地作成了(96)。因此他批评“苏(轼)文害正道,甚于佛道”(97)。叶适曾经批评文章越来越不行的原因是,“及王氏(指王安石)用事,自比周孔,掩绝前作;程氏兄弟,发明道学,从者十八九,文字遂复沦坏”(98)。文章衰落的原因归诸王安石、程氏兄弟,未必就对,但程明道以下的理学家在文学上不行,不能说与程氏兄弟无关,朱熹虽有别于二程,对文学的评论也是过分的、不恰当的。
对史学,程颐曾认为,“读史须见圣贤所存治乱之机,贤人君子出处进退”(99),是格物致知的一个途径。可是,朱熹对史学则不遗余力地加以贬斥。前面曾经引用几条,说明他对浙东学派重视史学的否定态度。而且在一次答问中,“义刚曰他(吕祖谦)相承那江浙间一种史学,故恁地”,朱熹却不顾一切地说:“史什么学?只是见得浅!”(100)公然否定史学是一门学问,就走得更远了。
我国古代学术主要由经学、史学和文学(语言、文字包括在内)这三者构成的。这几门学问是互相补充、互相影响、互相推动的。任何一门学问都不能孤立起来,不同其他的学问不相来往。试想,经学能离开文字、训诂之学吗?离开文字、训诂之学,连经文字义尚且弄不清楚,又怎么能够通经明理呢?二程兄弟和朱熹都是饱学之士,特别是朱熹,一生尊德性而道学问,是南宋时期最为博学的学者,当时罕与伦比。而程氏兄弟贬低文学,朱熹连史学也一概摒斥,把经学同文学、史学割裂开来,使经学走上了狭隘的道路,对人才的作育和培养是极其不利的。唯其所此,在南宋初乾道淳熙之际出现了高谈“道德性命”而不成句读的无知小子,以及此后又出现一批一批的“冬烘”之辈,使理学承受了应当承受的惩罚。
理学不仅从学术上由于与史学文学脱节而日益走上空疏的道路,尤为严重的是,由于它脱离实践,同现实生活脱节,更成为理学的致命伤。前面提到,儒生们为实现“内圣外王之道”这个最高理想,只有从政这条途径,在政治实践中成德、立功。虽然这种政治实践非常狭隘,但它毕竟还能够同社会现实接触,通过对实际问题的解决实现其政治上的理想和抱负。所以从范仲淹到王安石,一些在经学上有成就的宋学者,不做隐士,积极地入仕,就在于经仕宦之途施展自己的理想。荀子说,始为儒生,终为圣人;孟子说,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始终之间,穷达之际,也必须经过这样那样的实践。从来没有过,静坐在那里就可以成为孔圣人!从来也没有过,光靠冥想,就能成德立功!从程夫子到朱夫子的理学,都异想天开地靠内心反省工夫去登上大成殿:
谢子与伊川别一年,往见之。伊川曰:相别又一年,做得甚工夫?谢曰:也只去个矜字。又曰:何故?曰:子细检点得来,病痛尽在这里。若按伏得这个罪过,方有向进处。伊川点头,因语在坐同志者曰:此人为学,切问近思者也。
……伊川每见人静坐,便叹其善学。(101)割断与客观世界的联系,靠自己的内心反省工夫去成德、立功,不亦戛戛乎其难也哉!不仅如此,静坐冥思,只有走上野狐参禅的路子,又岂有他哉!
五、论宋学演变的社会历史环境
汉学之向宋学演变,不仅是在学术上以义理之学代替了章句之学,而且由于宋学之重实际、务实效,与社会现实生活紧密结合,使宋学得到了蓬蓬勃勃的发展。宋学之向理学演变,亦即是与现实结合的义理之学,向与现实脱节的性理之学或道德性命之学演变。演变的关键在于是否务实,在于是否与现实结合,因而这个演变是极其深刻的。宋学之所以发生如此深刻的演变,同两宋社会历史的演变是息息相关的。只有从两宋社会历史演变中才能寻找宋学的这一内在的深刻的演变。
经过唐中叶以来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动,由山东士族、关陇豪族代表的封建农奴制衰落下去,而由士族以外的地主和中下层地主代表的封建租佃制得到发展,到宋代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制度。这个剧烈变动给社会生活带来某种宽松和盎然的生机。广大地区的客户有了迁徙的自由,比此前庄园制下的农奴的人身依附关系宽松了一些,自由多了一些。对士族以外的地主阶级带来的宽松和自由更多一些:随着压在他们头上的士族门阀的衰落,他们的社会政治地位上升的机会增多了。同时,山东士族代表和维护的封建礼法以及道德规范也由于这一变动而发生一定的变化,这对于整个社会特别是对中下层地主士大夫的束缚有所宽松,因而也就有了更多的自由。陈寅恪先生在《论再生缘》一文中,曾经提到我国古代的魏晋六朝是思想自由的时期。在宋代,这种自由也并非漫无边际,而是像上面说过的,是较为具体和非常有限的。尽管如此,但在这经济领域所发生的以及导致上层建筑领域里这个变化,给社会各方面都带来了勃勃生机。敢于把“周公孔子驱为奴”的傲歌,不能不反映此前封建礼法及其道德规范的削弱,不能不说明了封建士大夫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的自由是多了一些。唯其如此,在经学的探索上,宋人敢于疑经,敢于否定汉儒的家法,亦敢于充分发挥自己的见解,从而以勃勃有生气的义理之学代替了繁琐不堪的章句的之学,建立了与汉学对立的宋学。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士族外的庶族地主和中下层地主,不仅经济地位的上升有了更多的可能,而且还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制度在政治上取得一定的地位。正是这样一批来自中下层地主阶级的士大夫,在他们通过科举走上政治历程时,一方面创建了上面说的宋学,而另一方面则又在政治上形成一个赋有改革意识的政治集团,力图把他们从古典经学探索来的经世安邦之学同社会现实中的具体问题结合起来,通过政治实践,革除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积弊,从而使宋走上富强的道路。庆历新政和熙宁新法,便是宋学家们的两次著名的政治实践,虽然这两次实践的内容以及深度和广度都有所差别。这两次政治实践,对宋学的创建者和发展者说,是施展其学术上通经致用的才能,实现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亦即所谓“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而这样做的结果,也就是实现儒生们始为儒生、终为圣人,成德、立功这一“内圣外王之道”的最高理想。
归纳上面的叙述,宋学之务实际、赋有与社会现实相结合的实践精神,建立在或者说表现在庆历新政、熙宁新法两次政治改革,而这两次改革则建立在中下层地主阶级的经济力量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政治力量上。
宋学之向理学的演变,亦即从务实、从与社会现实结合,向尚空谈、与社会现实脱节的演变,也是宋代社会经济演变的结果。当然,形成于熙丰之际的洛学,由于程颢之从变法派中游离出来,政治态度的变化对此后洛学的形成不能不产生相应的影响。但最重要的还是经济变动带来的影响。
南宋经济的发展同北宋经济的发展已经有所不同。这个不同表现在地主阶级方面是,经过北宋末年宋徽宗统治期间和南宋初期土地兼并猛烈发展的结果,中下层地主阶级的经济力量削弱了。一个有一二百亩田地的地主,收入不过一二百石地租,由于“和买折帛之类,至有用田租一半以上纳税者”(102)。“今之家业及千缗者,仅有百亩之田,税役之外,十口之家,未必糊口”(103)。中下层地主阶级经济力量在两宋的这个变化,我在《宋代经济史》(上册)中,已经作了说明,不再赘述。中下层地主经济力量的削弱,径直地造成了他们在政治上不能形成一个有力的政治力量,从而不能像他们的前辈那样,表演出有声有色的庆历新政和熙宁新法。从南宋建立之日到南宋灭亡,一直是大地主专政,而且在某些时期内表现为权臣如秦桧、史弥远、韩侂胄、贾似道们的大地主专政。
在这样的政治局面下,出身于中下层地主的士大夫,要么依附权臣大地主阶级,杨时、胡安国就是极为明显的例子;要么,屈居于地方州县。以务实、讲究事功的浙东学派诸子,如薛季宣、陈傅良和叶适等,终生不过州郡,但他们不负其所学,在州郡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有着可以称道的政绩。博学的朱夫子,也不是向皇帝光讲正心诚意,而是在漳州、南康军等地,对赋税、盐法进行改革或提出改革意见,并非安于当时的积弊的。理学家们诸如陆九渊、杨简、袁絜等也都有德政可言的。所有这些话,无非是归结为一点,在宋代社会经济的变动下,南宋社会历史环境,已经不能向理学和浙东事功之学这两个学派提供政治实践条件,让他们实现他们的“内圣外王之道”这一最高理想。这就是说,理学力主的与实践相脱节的内心反省工夫是这个学派的内在弱点,而客观历史环境则不给理学家、事功派学者们以政治实践机会,则是客观的原因。这两者相结合,便决定了理学日益走上空疏的道路,终于为历史进程遗弃和淘汰。
我国自汉到清两千多年以来的经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曲折道路。两汉的章句之学,由于陷于繁琐哲学的困境,被生机勃勃的宋代的义理之学所代替,这是宋学对汉学的否定。宋学演变为理学之后,日益走上空洞无物的道路,于是清代的乾嘉考据之学对宋学否定,以恢复汉学的治学方法,这是否定之否定。从这个否定之否定的学术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到,否定了汉学的宋学,把经学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而否定宋学的考据之学,不是对汉学的一个简单重复,而是在文字训诂方面突破了汉人的成就,足以弥补宋学之不足,但就规模、成就而论,乾嘉之学则不能与宋学相提并论。否定之否定这就是从汉历宋到清经学探索上的辩证法的发展。
宋学与社会现实、政治实践是结合的,而理学则是与社会现实、实践是脱节的,这个演变和分歧是非常明显的。七八十年来,我国哲学史思想史的研究有着突出的成就和贡献,但其中也有不少的弱点和不足。其中一个主要的弱点和不足。由于研究者们自身与政治的脱节,因此在考察古代学术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往往习惯于沿着从思想到思想的认识路线进行,割断了这些思想同社会经济关系的联系。这样一个研究结果,就只能寻找到这种思想同那种思想的联系,而找不到形成这种思想的政治经济诸关系,以至使这种思想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孤零零地无从挂搭处,象朱熹所说的失去了气的理所遇到的那样。于此同时,也就不自觉地夸大了这些思想的作用和意义,使这些思想成为超时空的绝对的观念,成为只能歌颂不能动摇的绝对真理。本文提出的上述问题,是否恰当,还请方家指正。
注释:
①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5页。
②邓广铭:《略谈宋学》,1984年《宋史研究论文集》。
③《论六家要旨》,《史记·太史公自序》。
④《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魏略》。
⑤吕木中《杂说》,《长编》卷二一○熙宁三年四月己卯注引。
⑥《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七八,《易童子问》卷第三。
⑦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傅斯年全集》第2册第364页。
⑧《毛诗本意》。
⑨《四库全书》《诗本意》提要。
⑩《蔡忠惠公文集》卷三三《胡瑗墓表》。
(11)《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周易口义》解体。
(12)《洪范口义》卷下《五日恶六日弱》释义。
(13)《洪范口义》卷上。
(14)《四库全书》《洪范口义》提要。
(15)(17)(33)《郡斋读书志》卷一下、卷一下、卷四下。
(16)《直斋书录解题》卷三。
(18)以上诸段引文均录自《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十之二《安定胡先生》。
(19)薛季宣:《浪语集》卷二三《又与朱编修书》。
(20)《直讲李先生文集》卷五至十四。
(21)陆佃:《陶山集》卷一二《答崔子方秀才书》。
(22)《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三四《徂徕石先生墓志铭》。
(23)《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二七《孙明复先生墓志铭》。
(24)《胡适文存》二集第一卷《记李觏的学说》。
(25)《直讲李先生文集》卷二七《寄上范参政书》。
(26)《宋史》卷三一四《范纯仁传》。
(27)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张载集》,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81页。
(28)《朱子语类》卷一二九《自国初熙宁人物》。
(29)《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二○。
(30)范仲淹《政府奏议》卷上。
(31)《朱子语类》卷一三○。
(32)陆佃:《陶山集》卷一五《傅常墓志》。
(34)《王临川先生文集》卷六五。
(35)释惠洪:《冷斋夜话》卷六。
(36)《临川先生文集》卷七三《答曾子固书》。
(37)(38)《陶山集》卷一二《答崔子方秀才书》。
(39)《宋会要稿》选举三之四四;《长编》卷二二○;《王安石变法》。
(40)王安石:《周官新义·序》,粤雅堂丛书本;集本卷八四。
(41)《通考》《选举考四》。
(42)《郡斋读书志》卷一上。
(43)《朱子语类》卷一三○。
(44)《温周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七四《迁书·士则》。
(45)《王临川先生文集》卷六五《洪范传》。
(46)《王临川先生文集》卷六七《行述》。
(47)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50页。
(48)《温周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六一《答李大卿孝基书》。
(49)《朱子语类》卷一三九《论文》上。
(50)《嘉集》卷八。
(51)《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三四《苏洵墓志铭》。
(52)《四库全书》《书传》提要。
(53)(54)《宋元学案》《苏氏蜀学略》,第四册,第3289、3297页。
(55)《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三四《苏洵墓志铭》。
(56)《河南程氏外书》卷一二,《二程集》第二册,第432页。
(57)(83)(89)《朱子语类》卷一二三。
(58)《朱子语类》卷一三○,《本朝四·自熙宁至靖康用人》。
(59)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九。
(60)《河南程氏外书》卷一二,《二程集》第二册。
(61)员兴宗:《九华集》卷九,《苏氏程氏王氏三家之学是非策》。
(62)《龙川集》卷一五《送王仲德序》。
(63)《宋史》卷四三五《胡安国传》。
(64)《四库全书》《春秋传》简目评语。
(65)楼钥:《春秋后传序》。
(66)《春秋传》卷一二僖公中。
(67)《春秋传》卷三,隐公十年夏帅师伐宋条。
(68)《春秋传》卷七,庄公二年夏公子庆父帅师伐于馀丘。
(69)《春秋传》卷一○,闵公二年十二月郑弃师条。
(70)姚瀛艇:《宋代文化史》,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第115页。
(71)《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九,绍兴四年八月戊寅。
(7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七,绍兴五年三月庚子。
(73)《宋史》卷四二八《杨时传》。
(74)薛季宣:《浪语集》卷二八,策问二十道(第四道)。
(75)《浪语集》卷二八,策问二十道(第十六道)。
(76)叶适《习学记言》卷四八,参阅了周梦江《薛季宣的生平、著作及其对道学的异议》载1984年《宋史研究论文集》。
(77)《龙川集》卷一五,《送吴先成运干序》。
(78)吕祖谦:《东莱集·别集》卷七,《与朱侍讲》(第一七封信)。
(79)《浪语集》卷二五《答象先生侄书》。
(80)《浪语集》卷二五《抵杨敬仲简》。
(81)《浪语集》卷二五《抵沈叔晦》。
(82)《朱子语类》卷一二二《吕伯恭》。
(84)《汉书》卷三○《艺文志》。
(85)(86)《东莱外集》卷六、卷二。
(87)《龙川集》卷一五,《赠楼应元序》。
(88)岳珂:《程文》卷二。
(90)(91)(92)(93)(99)《河南程氏遗书》卷一八,伊川语录。《二程集》第一册。第187、239、239、427、258页。
(94)《朱子语类》卷一四○《论文》下。
(95)(96)(97)《朱子语类》卷一三九《论文》上,第八册,3319页。
(98)叶适:《习学记言》卷四七《吕氏文》。
(100)《朱子语类》卷一二二。
(101)《河南程氏外书》卷一二,《二程集》第二册。
(102)《水心先生文集》卷一《上宁宗皇帝扎子》。
(103)张守:《毗陵集》卷二《论淮西科领扎子》。
标签:宋朝论文; 朱熹论文; 胡安国论文; 秦桧论文; 王安石论文; 南宋论文; 理学论文; 吕祖谦论文; 儒家思想论文; 宋高宗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