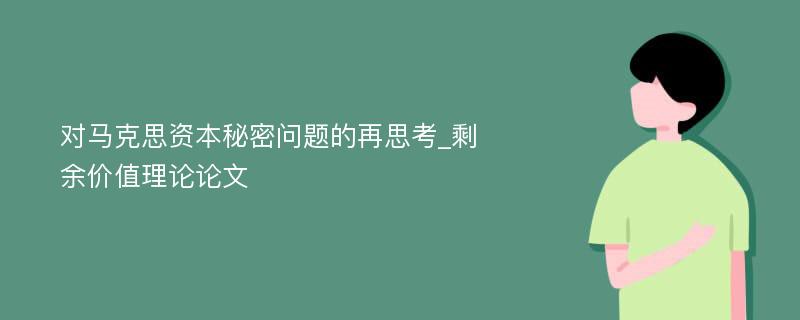
重思马克思关于资本的秘密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资本论文,秘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之前就有学者探索过资本现象背后的“秘密”。然而,斯密、李嘉图、约·威尔逊等经济学家尽管研究了地租、利润等这些剩余价值的具体形式或转化形式,但从来没有超出历史上关于利润和地租的常识,从来没有把产品中这个无酬部分当做一个整体即“绝对形式”——剩余价值来研究过。 马克思虽然在资本主义世界过着大半辈子的流亡者生活,但他没有因此“抹黑”这个现代社会而把资本主义社会视为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坑蒙拐骗、掺假使坏,也“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肯定资本家是以商品交换规律作“根据”的,整个资本家阶级不能自己欺骗自己,“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在商品质量上弄虚作假也是非正义的”,[1](P379)把资本主义社会看作一个理性社会。所以,马克思在前人经济学成果基础上以高度分析力、抽象力拂去了浮在“资本”之上的层层雾水或种种谜团,和盘托出了资本这只会“生金蛋”的“母鸡”秘密。他进行这项科学工作的杰出之处不是从资本获利的派生形态如利润、利息、地租等,而是从其一般形态——“剩余价值”入手,判定商品“流通领域”只是提供或准备了剩余价值生产的前提条件或剩余价值的实现条件,不是剩余价值产生的“原始出处”,剩余价值的“出生地”是生产领域,资本“赚钱的秘密”正直接发生于这个领域,这才是现代资本不同于高利贷资本的根本区别所在。 那么,剩余价值是如何生产的或者说“金蛋”是如何“生”的呢?马克思依凭他那世所罕见的逻辑抽象力澄清了前人在这个问题上诸如“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价值”之间关系,“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间关系,“地租、利润、利息”与“剩余价值”之间关系的模糊认识,廓清了“劳动的价值”、“货币”、“工资”等概念似是而非之处,创立了一系列崭新概念如“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劳动力价值”等,在科学上还原了剩余价值生产的逻辑过程:劳动力一天的维持费和劳动力一天的实际耗费或者说劳动力价值与劳动力在劳动过程中所实际实现的价值增殖是两个不同的量,资本家在购买劳动力时就意在这个价值“差额”。虽然某个劳动力(如能制造棉纱或皮靴)的有用属性只是一个必要条件,这是由于商品的使用价值构成商品的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但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这个商品即“资本家换来这样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使资本得以保存和倍增,从而变成了资本的生产力和再生产力,一种属于资本本身的力。”[2](P232)正是工人的劳动力在生产过程的使用即“活劳动”——创造“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才“使对象化的死的劳动增殖价值,赋予死劳动以活的灵魂,但与此同时也丧失了它自己的灵魂,结果,一方面把已创造的财富变成了他人的财富,另一方面只是把活劳动能力的贫穷留给自己”。[3](P110)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对资本这一增殖的“秘密”予以“连珠炮”式的无情抨击。美国经济学家索尔斯坦·凡勃伦把这个“资本主义”模式归结为“一个海盗抢掠的高级系统”。[4](P10)当然,正如我国经济学家所指出的,马克思对资本“唯利是图”、“见物不见人”或“资本的残酷”的揭露与谴责主要是“就英国原始积累的主要倾向和趋势而言的,没有反映其中有勤劳致富的一面”。[5](P179) 在资本的秘密即“赚钱的秘密”问题上,马克思在逻辑上没有回旋余地把“剩余价值”归源于雇佣工人工作日里的“剩余劳动时间”或“剩余劳动”,进而把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财富归源于雇佣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及其积累。他在1854年《给工人议会的信》中挑明“大不列颠的千百万工人第一个奠定了新社会的真实基础——把自然界的破坏力变成了人类的生产力的现代工业。英国工人阶级以不懈的毅力、流血流汗、绞尽脑汁,为使劳动变成高尚的事业并把劳动生产率提高到能造成产品普遍丰富的水平创造了物质前提”。[6](P134)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认为剩余劳动时间是劳动群众超出再生产他们自己的劳动能力、他们本身的存在所需要的量即超出必要劳动而劳动的时间,这种剩余劳动时间同时物化为剩余产品,而这种剩余产品又是除劳动阶级外的一切阶级存在的物质基础、社会整个上层建筑存在的物质基础、整个社会发展和全部文化的物质基础。[7](P215、220~221)林肯也肯定“资本只是劳动的成果,假使不先有劳动,就不可能有资本。劳动是资本的前辈,应该受到更多得多的尊重。”[8](P175)后来,恩格斯说工人阶级是生产全部价值的“唯一阶级”,列宁也说全人类的首要的生产力就是“工人”,就是“劳动者”。显然,尽管马克思在《资本论》特别是《资本论》第一卷中至始至终站在历史的高度对剩余价值现象投下了否定或批判的眼光,但他通过一系列经济学概念所构建的剩余价值理论,实际上科学界定并肯定了工人阶级对“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在历史上空前的文明成就所作的历史性绝对贡献。 然而,一些学者公开地蔑视或“反驳”马克思资本学说中这个核心内容,或者说要摘除这颗“心脏”。哈贝马斯提出科学技术的进步业已成了一个独立的剩余价值的“来源”而同马克思原先只知道考察的那一种剩余价值的来源没有关系。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中册、下册分别提出利润是事业心和技术革新的“报酬”、“一小群拥有资本的节俭或幸运的资本家现在可以收取一笔剩余即一笔利润、利息率”,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提出过去是劳动创造价值而现在是知识、技术创造价值,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中提出需要创立一种知识价值理论来“代替”马克思过时的劳动价值理论,托夫勒在《预测与前提》中提出现在可以另编一套“资讯价值说”,西罗塔在《新马克思主义:一种改革的尝试》一文中提出劳动价值论在信息科学和生产变为科学的运用的时代“站不住脚了”,许永和在《生产分配与资本积累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一书中提出,马克思将机械设备视为过去劳动的成果、死劳动在商品生产过程中仅能转移自身的价值、无法创造新价值这个看法是错误的,因为机械设备作为一种生产工具,是一种“生产的力量”而创造新价值。 这些观点似是而非之处,一方面在于这些学者囿于西方“正统”范式不愿承认雇佣工人阶级对于剩余价值的绝对贡献、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所拥有的财富与繁荣的绝对贡献,正如美国学者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揭露了剥削,而新古典经济学则掩盖剥削,并把它作为当然的规则。那么,就不难得知,剥削者倾向于哪一种经济学,而对另一种,则是感到不安,甚至宣称它已经消亡”;[9](P3)另一方面在于他们没有准确理解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逻辑本身而把它简化为只有物质生产劳动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商业活动实现价值和剩余价值,其他的社会活动既不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也不实现价值和剩余价值而属于消费商品的活动。[10]虽然马克思肯定剩余价值仅仅源于工人的剩余劳动或剩余劳动时间,但同时承认机器或科学技术在创造剩余价值过程中相对于“活劳动”的“手段”作用、承认资本增殖形式的科技化或智能化趋势,他在《资本论》手稿中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3](P359)“机器使工人能够把自己的更大部分时间用来替资本劳动,把自己的更大部分时间当做不属于自己的时间,用更长的时间来替别人劳动……通过这个过程,生产某种物品的必要劳动量会缩减到最低限度”,“提高劳动生产力和最大限度否定必要劳动……是资本的必然趋势。劳动资料转变为机器体系,就是这一趋势的实现”。[3](P192、186)不过,工人提供的“剩余劳动”或“剩余劳动时间”是资本家攫取“剩余价值”或整个社会财富之“源”,用马克思的话说即“酵母”,“资本通过使用机器而产生的剩余价值,即剩余劳动,——无论是绝对剩余劳动,还是相对剩余劳动,并非来源于机器所代替的劳动能力,而是来源于机器使用的劳动能力”,[3](P287)机器或智能化工具只是资本家攫取“剩余价值”的有利条件,后者与前者并不存在排斥关系。 当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所说的剩余价值(果实)无偿地被资本家占有现象,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实际上仅仅属于发生在资本生产过程的“初次分配”,而在这个“生产过程”领域之外的“流通过程”又会出现对剩余价值(果实)的“再分配”现象,如“利润要在两种资本家”即“货币资本家”与“企业主”或“职能资本家”或“能动资本家”(也叫“产业资本家”)中间分割。就是说,生产领域的资本家仅是剩余价值的“第一个占有者”而非剩余价值的“最后占有者”,他还要同整个社会生产中执行其他职能的资本家以及土地所有者等共同瓜分剩余价值。只是由于剩余价值这一资本的绝对形式被其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派生形式如利润、利息和地租等层层“包裹”着,马克思资本学说的重心不得不落在这个范畴上。 同样,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里所说的剩余价值(果实)完全由雇佣工人在剩余劳动时间的剩余劳动过程创造而与资本家“无涉”,这实际上是针对“生息资本”或“借贷资本”在资本“生产过程”中不“在场”或没有直接扮演生产性角色而言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资本的所有者与资本的使用者或资本的经营者(“能动资本家”或职能资本家)——实业家或企业家往往一身而二任,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里便揭示了二者“分离”的趋势。就这种职能资本家即实业家或企业家而言,马克思显然肯定他们的劳动或管理工作创造价值,说“随着许多雇佣工人的协作,资本的指挥发展成为劳动过程本身的进行所必要的条件,成为实际的生产条件。现在,在生产场所不能缺少资本家的命令,就像在战场上不能缺少将军的命令一样”,[11](P384)明言资本家的“管理”具有生产性即“资本主义的管理……是制造产品的社会劳动过程”,[11](P385)“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资本家指挥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他的企业主收入是同资本的所有权无关的东西,宁可说是他作为非所有者,作为劳动者执行职能的结果。”[1](P426~427)并且明确把产业资本家定性为“劳动者”阶层,说“同资本所有者相区别的产业资本家,不是表现为执行职能的资本,而是表现为甚至与资本无关的执行职能的人员,表现为一般劳动过程的简单承担者,表现为劳动者,而且是表现为雇佣劳动者。”[1](P429)熊彼特虽然在总体上对马克思资本学说持否定态度,但他在这点上与马克思存在相切之点。他从“企业家利润”角度把这部分资本家所创造的价值或者说“利润”分为两类:一是作为革新者的“利润”即“企业家只是更好地使用了现有的商品,并且实现了新的更有利的组合,以此来获取利润”,一是作为“开拓者的利润”即“寻找新的市场,并销售该市场不熟悉也不生产的物品,能给企业家带来丰富、持久的利润”。[12](P78~79、81) 善于从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中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或生产关系,这是贯穿于马克思资本学说始终的基本特征。“生产关系”概念的“专利权”属于马克思。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一文第一次把“资本”与“生产关系”予以直接“链接”,认为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才成为奴隶;纺纱机就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才成为资本,而脱离了这种关系就不成其为资本。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他从资本与货币之间的关系中进一步辨明资本的本质“只能是生产关系”,从历史上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比较角度把资本即现代资本归结为一种“为财富服务”的“所有制形式”或“所有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他从“法律”角度把生产关系称为“财产关系”。在《资本论》第1卷中,他从再生产角度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仅视为商品生产、剩余价值生产的过程,而且视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的再生产过程。 在马克思资本学说中,资本专指某种资本物所具有的“一种社会规定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人包括劳动者都“天生是社会动物”,而资本作为自乘的价值属于一种社会形式或社会关系,“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它们同工人的关系中,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社会规定性,这种社会规定性使它们变成资本,给它们以支配劳动的权力。”[13](P426)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认为,一个人拥有货币、生活资料、机器和其他生产资料而没有被迫自愿出卖自己的人即雇佣工人还不能成为资本家,只有在这些资本物充当剥削、统治工人的手段这一条件下才成为资本。因而,资本的实质在于活劳动是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在于作为手段来实现的那种一定的、特殊的“目的”即实现对“物化劳动”或“死劳动”的增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强调资本的本质只能“被理解为关系”,赞赏威廉·配第等古典经济学家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批评庸俗经济学只在这种生产关系“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 那么,资本作为一种生产关系具体所指是什么呢?就是指一定历史阶段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之间的结合方式或者说生产方式的社会形式,以生产过程中人们之间的“利益”形式表现出来。马克思认为,自由工人本身或货币所有者和劳动能力所有者之间、资本和劳动之间、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交换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作为一种独立的资本关系只有在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才能出现。资本的这种经济关系具体表现为直接生产者被剥夺,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的、积聚的生产资料,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以所有者的个人劳动为基础的所有制被以剥削他人劳动即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所排挤。概言之,资本作为一种生产关系或社会关系特指除了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的劳动者与劳动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一方面是社会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资本家或资产阶级则是这种生产关系的人格化即“专指资本拥有者阶级”[14](P326)或“自为存在的资本”;[2](P261、262、277)另一方面是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它具有不仅创造再生产劳动力的价值,而且创造出超出这个价值的剩余价值的劳动能力,正是“这种生产关系把工人变成资本增殖的直接手段”,[11](P582)架设了资本赖以增殖的“产床”。 作为资本的生产关系或社会关系人格化的资本家和雇佣工人本身都是资本增殖过程的产物。其中,“资本家”只是资本的“人格化”、“对象化劳动、自行保存的价值的主体和承担者”,[7](P42)其“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即“资本”的本性是“增殖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工人本身,按其概念是赤贫者,是这种自为存在的、与自己的对象性相脱离的能力的化身和承担者”,“只是他本身劳动能力的主体、人格化”。[7](P44、42) 那么,作为资本的生产关系或社会关系之“两端”——资本家与雇佣工人“最初是从哪里来的呢”?就西欧“原生型资本主义”而言,资本家最初来自“用自己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的手工业者或农民”,或者说是“被解放的农奴”或“自由小土地所有主”。其中,最初形式的租地农场主在英国只是农奴的管事。可以说,近代资产阶级与近代无产阶级即早期资本家、雇佣工人共一个“始祖”——逃自乡村的农奴或小生产者,他们之间的分化本不是上天的预设,而属于特定条件下的历史现象或历史范畴。 资本作为一种生产关系形式既不等于一般的“生产关系”,也不等于一般的私有制生产关系,而仅仅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这种社会关系构成一种“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而“凡能被称为权力的东西,总是表达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其一。其二,权力之为权力,总是指称这样一种人与人的关系,即人对人的支配与被支配、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舍此,不能言‘权力’二字。其三,既言支配与被支配、控制与被控制,权力就必定是一种感性的力量。”[15] 资本作为一种“社会权力”在于资本直接购买活劳动力以便在生产过程中“不经购买而占有”所使用的劳动的一部分。马克思认为资本的“本质”就是“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即对剩余价值的索取权和控制权,而“一切剩余价值,不论它后来在利润、利息、地租等等哪种特殊形态上结晶起来,实质上都是无酬劳动时间的化身。资本自行增殖的秘密归结为资本对别人的一定数量的无酬劳动的支配权”。[11](P611)并且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或资本的发展,资本越来越表现为一种“社会权力”,资本家则是这种社会权力的“执行者”。正是这种“社会力量”铺就了资本在生产与竞争中的强势地位或主体地位之基。列宁曾经把资本的这种社会权力直接称为“资本权力”。[16](P286)不过,对资本作为“一种社会权力”的命题能不能因为马克思说它是“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而把马克思资本学说简单“终结”于资本=剥削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剥削形式,说“没有对国内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就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对国外人民首先是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同样没有资本主义”、“在国内排挤和消灭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直接生产者的私有制,剥夺、制造和盘剥一无所有的、‘自由’的雇佣劳动者阶级;把这种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推向世界,在世界到处再生产出这种私有制,——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原始使命和两个支柱”呢?[17](P198)我认为,对其中的具体环节进行具体分析对于深化马克思的资本理论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篇中运用商品劳动二重性理论一方面阐明,工人在劳动过程发生的“抽象劳动”属性“不仅再生产出劳动力自身的价值,而且生产出一个超额价值”即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绝对剩余价值”。就此而言,马克思认为这是资本家对工人劳动力的“劫掠”过程。另一方面阐明,工人在劳动过程“发酵”的“具体劳动”属性在同一劳动时间内达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就是“把新价值加到劳动对象上和把旧价值保存在产品中”,正是工人的具体劳动活动使资本家预设的那些“死”生产资料“由死复生,使它们从仅仅是可能的使用价值转化为现实的和起作用的使用价值。它们被劳动的火焰笼罩着,被劳动当做自己的躯体加以同化,被赋予活力以在劳动过程中执行与它们的概念和职务相适合的职能,它们虽然被消费掉,然而是有目的地,作为形成新使用价值,新产品的要素被消费掉”。[11](P214)这种作为工人“活劳动的自然恩惠”的“加进价值而保存价值”的“副产品”的确不费工人分文,但保存了原有资本的价值。如一个纺纱工人,就其劳动的抽象的一般的属性而言是把新价值加到棉花和纱锭的价值上,而就其劳动的特殊的有用的属性(纺纱过程)则把这些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保存到新产品棉纱上而出现了纺纱劳动在同一时间内所获得的双重结果。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发生的生产资料的“旧价值保存”或“转移”是由工人劳动的“具体劳动”属性所实现的,这种“具体劳动”属性在价值形态上不费工人“分文”,但无偿地为资本家实现了生产资料“保值”。能实现生产资料的这种“保值”是资本家生存的根基和生产发展的前提。否则,这些生产资料就变成死物,甚至由于自然侵蚀所出现的有形耗损或再生产该资产的成本降低所出现的无形耗损而自行贬值,作为这些生产资料人格化的资本家也必将随之丧失生存的根基。 马克思在《资本论》“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篇中具体陈述了资本家对无偿劳动“占有”或“掠夺”的特殊情形。工人作为劳动力的出卖者和资本家进行交易时是自己劳动力的所有者,他出卖的只是他所占有的东西即他个人的单个劳动力,如资本家支付的是100个独立的劳动力价值而不是100个在资本家工厂条件下的结合劳动力价值。工人作为独立的人是单个的人,他们在和同一资本发生关系之前彼此之间不发生关系即处于“被否定的孤立劳动”状态,他们之间的“关系”或协作是在资本的工厂(公司)里的劳动过程中才开始的,但是在这种劳动过程中发生的这些“关系”或协作,即处于“被肯定的社会劳动或结合劳动”状态所“融合为一个总的力量而产生的新力量”,便不再属于工人自己而“表现为他人的客体性(他人的财产)”或“他人的主体性(资本的主体性)”。作为协作的人或作为工作机体的一个肢体,他们本身成了只是资本这种特殊存在方式的各个“零件”。因此,工人作为结合劳动力或社会工人所发挥的那种生产力就直接呈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在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形成的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无须支付报酬而发挥出来,而资本正是把工人置于这样的条件之下的。因为,一方面劳动的这种社会生产力在资本家与工人交易时没有费资本分文,另一方面工人在他的劳动本身属于资本以前不能发挥这种社会生产力,所以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在直观形式上呈现为资本天然具有的生产力或资本内在的生产力。作为标准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的核心内容正是这样无形地间接地无偿占有这种由雇佣工人之间协作而形成社会生产力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当然,资本不仅如此巧妙地无偿“吞并”别人的这种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而且吞并他们的科学或知识,还把纳入生产过程的自然力如蒸汽、水等等“不费分文”地据为己有,因为“受自然制约的劳动生产力也表现为合并劳动的资本的生产力”。 显然,马克思所谓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即对雇佣工人“无酬劳动的支配权”,这个被资本无偿占有或支配的相对“无偿劳动”或“相对剩余价值”不是由其作为“单个的劳动力”、“单个的人”或“单个劳动者的力量”所创造的,仅指雇佣工人在资本条件下由其作为“结合劳动力”、“作为社会工人”、“作为协作的人”所创造的部分,或者说由工人的“集体力”或“结合劳动者或总体劳动者”[11](P378、380)所创造的剩余价值部分,同时包括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由雇佣工人的“科学”力量、“生产过程的自然力”所带来的剩余价值。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篇中还分析了为机器大工业即科技含量高的“不变资本”所带来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情形:资本无需工人用手工工具做工,只需工人用一个会自行操纵工具的机器做工。这样,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从而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只是生产力的这种提高不是靠增加劳动消耗来实现的。机器像不变资本的任何其他组成部分一样不创造价值,但它通过工人的劳动活动把自身的价值转移到它所生产的产品中去,机器所转移的这部分价值构成新产品总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机器不是使产品变便宜,而是使产品随着机器的价值相应地变贵。他在《资本论》手稿中还指出了资本通过使用机器去占有“科学力量”这一“不费资本分文的生产力”事实:在劳动资料转变为机器体系、活劳动转变为机器体系的“活的附件”的情况下,工人的劳动过程只是资本价值增殖过程的一个环节;在机器体系中,物化劳动成了支配活劳动的力量,单个劳动能力创造价值的力量与物化在机器体系中的价值相比微不足道而趋于消失。[18](P91~92)由于生产“绝对剩余价值”的工作日的有限性,资本就竭尽全力加快发展机器体系来生产“相对剩余价值”,资本家占有无偿劳动果实或剩余价值的形式出现了普遍地“通过机器进行的资本的自行增殖”趋势即剩余价值生产的“相对剩余价值”化趋势,只是这一趋势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变为“工人人口总是比资本的增殖需要增长得快”的表象。 资本世界的复杂性或“狡猾”性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把资本这种“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的实质“包裹”起来,具有“神秘性”。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科学及其应用被并入资本,同单个工人的技能和知识相分离。“在固定资本中,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固有的属性;它既包括科学的力量,又包括生产过程中社会力量的结合,最后还包括从直接劳动转移到机器即死的生产力上的技巧。相反地,在流动资本中,劳动的交换,不同劳动部门的交换,它们的交错连结和形成体系,生产劳动的并存,表现为资本的属性。”[18](P111)同样,“利息”作为“资本的所有权”在资本关系下表现为某种在生产过程本身之外“属于资本的东西”而不直接显示为生产过程本身的“果实”,它不是把“资本的所有权”表现为同劳动对立而是与劳动“无关”,表现为似乎是一个资本家对另一个资本家之间的博弈关系;“利润”只是在资本家之间的“分配”而与工人劳动“无关”。总之,在这些形态上,资本的对立性质已经“完全消失”,利息不仅幻化出货币、商品等等具有“增殖自己价值的能力”,并且把剩余价值幻化成是货币和商品自身的“自然果实”而非“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为了揭掉这个曾经迷惑了古典经济学家的资本“神秘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论述资本的实现问题部分把资本的“总产品”(总“收益”)同资本的“总收入”、资本的“纯收入”区分开来,认为资本的“总产品”应包括整个社会再生产出来的全部产品即价值形态上的c+v+m或实物形态上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资本的“总收入”则是总产品扣除用于补偿在生产中消耗掉的不变资本的价值部分及其产品部分的余下部分,即总收入=工资+利润+地租;资本的纯收入是被实现为或转化为利润、利息、地租的剩余价值m而不包括工资,因为工资对于资本家而言不属于其直接“收入”。 资本作为一种“社会权力”当然不同于封建时代或古代那种“强制力量”或“直接的身体上的强制”或“统治关系”,而属于“一种拒绝的权力”,“资本家可以拒绝他人使用他的资源,但他不能强制人们和他一道工作,这种权力明显地需要那种使制止他人的使用成为一种要他人承担严重后果的行动的环境,这样一种环境只有在一般民众不接触私人资源或财富便无法度日的情况下才会出现。资本就这样成了权力的工具,因为所有者可以索取产出作为准许他们使用其资产所应付的报酬。”[19](P378)这种“拒绝的权力”虽然呈现了“资本权力”的“有限”性,但相对于“土地”等实物资产占有量上的有限性而言则表现为一种可以无限膨胀的社会权力。 总而言之,无论是就马克思资本学说内容的丰富性或这个学说自身发展的生成性而言,还是就资本世界本身的复杂性或“狡猾”性而言,都需要我们对资本现象进行新的具体分析或科学分析而不能驻足于既有定论或思维格式。标签:剩余价值理论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剩余价值规律论文; 生产资料所有制论文; 资本论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经济论文; 利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