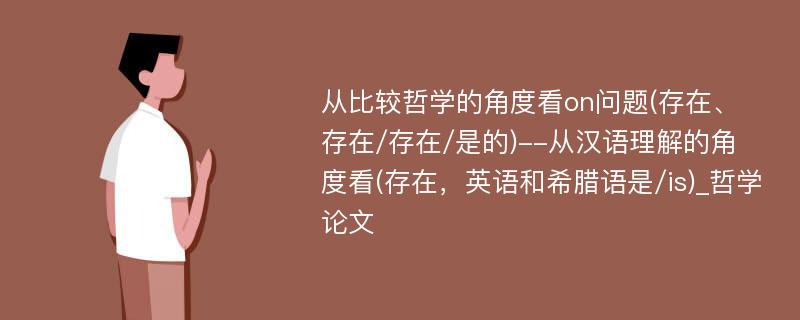
从比较哲学角度考察on(Being,有/在/是)问题(上)——从中文理解的角度看英文与希腊文中的on(Being,有/在/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希腊论文,英文论文,角度看论文,中文论文,文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0)06-0021-06
一、on(Being)的问题
当西方哲学进入中国之时,其实质是什么引起了中国学人的关注,而用怎样的汉译才能得西方哲学的神髓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在这两个问题的后面隐含着另一个问题:中国哲学应怎样借助西方哲学,并通过与其对话,走向并且形成一种具有世界性的哲学。
西方哲学来源于古希腊哲学,而古希腊哲学最核心的范畴是on,这一范畴也成为以后发展着的西方哲学的最核心范畴。在这一意义上,西方哲学主要就是关于“on”之学(ontology即是on加上logy[逻辑/理论/学]而成,中译为本体论、存在论或第一哲学)。当西方哲学于19世纪末在英国人的坚船利炮的支持下大举进入中国之时,on是以英文形式Being进入中国的。关于Being之学,中国学人中最先系统翻译西学的严复对之(Being)甚为头痛,以音译(庇因)对之,在意义上,一方面用了Being中“是”的内容,注为“然”、“如”;另一方面借助与之紧密相关的substance,解释为“本质”。至民国时期,中国学人陈康从古希腊哲学和希腊文的根源,并结合中国现代哲学的处境,提出了这一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现代哲学的主潮从西方哲学转向苏联哲学,Being变成了“存在”,并进而变成了统而言之的(客观)“世界”和质而言之的(抽象)“物质”,Being的问题被转化而消失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学人重新面对西方哲学,Being的问题被再次提出,并在两代学人(叶秀山、汪子嵩、王太庆、杨适、陈村富等及赵敦华、余纪元、王路、王晓朝、张志伟、李晨阳、章雪富等)中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和言说。而现代以来,西方哲学也从两个方面,讲究精细的分析哲学(如罗素《数学原理》)和讲究人生的存在哲学(如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对Being及其问题提出了质疑和新解,引起了西方哲学对Being的新研究。这样,Being成为中西方哲学共同关心的问题。当然,中西学人对Being的关注,其聚焦点是不同的。西方学人主要是在自身的语言之中,想把这一问题搞清楚,而中国学人则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Being的本义是什么,二是用什么样的汉语词汇来翻译Being。
由于西方哲学是世界的主流哲学,世界其他各种哲学要进入这一由西方文化所主导的统一世界之中,必然且必须与西方哲学进行对话和互译,因此,Being的问题成为一个世界哲学的问题。在这一世界性的哲学视野中,该问题主要分为两个系列,一是Being问题所由产生的西方语言区中的Being问题,二是非西方语言区的哲学在与西方哲学进行接触或对话时,面对西方Being问题而产生的问题。在这里,第一个系列主要是理清Being是什么,第二个系列不但要理清Being是什么,还要在自己的语言中找到怎样把Being正确地表达出来,正是在这一寻找正确表达的过程中,西方哲学的特点凸显了出来,同时与西方哲学不同的自己哲学的特点也会凸显出来。正是在这种由寻找而来的凸显中,新的世界哲学走向形成之途。
目前,中国关于Being的研究基本上凸显了西方哲学的特点,但没有在凸显西方哲学特点的同时把中国哲学的特点凸显出来,而正因为没有从凸显中国哲学特点的角度去寻找Being的表达方式,因此,Being所内蕴的西方哲学的特点也没有真正凸显出来。
虽然中国学术界关于Being的研究尚未进入凸显中国哲学特点的堂奥,但基本上把Being的复杂性呈现了出来。在这里,且先转述一下这种复杂性,再从世界哲学的角度讨论这一问题对于世界哲学对话的意义,并试着为进入这一对话提供一个参考路径。
二、从英语的角度看on(Being)的复杂性
中国学人关于on的研究,主要是面对英语这一世界主流语言而进行的。因此,对于on这一具有哲学本体论(ontology)意义的问题,本文先以英文的形式Being来进行讲解。用英文讲解的好处,第一,英语是世界主流语言,用它来讲,更容易理解;第二,英语比希腊语在词形变化上更简单,相对而言更接近词形无变化的中文。有了英文的理解,再进入希腊文就容易了。
人在面对人、物、事,或面对整个世界时,需要作出判断:这是……(什么)?一旦被问的对象(这个什么)得到了正确结论,人就心安理得了。在这一意义上讲,知识都来源于“是什么”之问和对“是什么”之答。“是什么”问得越多,人的视野越宽越深;“是什么”被答得越多,人的知识越广越全。换言之,“是什么”之问与答构成了人的知识历程(哲学的问题也包含于其中,但未得到凸显)。在日常生活和知识领域中,“是什么”的问与答都是具体的:这是一个人,那是一只鸟,这是两棵树,那是三块石头,这是一个国家,那是一面旗帜……而且这些具体的东西都存在于一定的时空之中。在空间的变化中,这里出现的东西到别处就消失了,而新的东西又出现了。在消失和出现中,那不变的东西是什么?在不同空间中出现的不同的东西的共同点是什么?在时间的变化中,曾经出现的东西消失了,曾经没有的东西出现了,现在出现的东西以后会消失,现在没有的东西以后会出现,在时间的流动变化和事物的生灭出没中,其共同点是什么?这些提问都把问题从常识和知识层面提升到了哲学领域。
在英语中,“是什么”是用to be(是)来表示的,我们要用to be(是)来判断事物,前提是有事物,因而to be同时意味着“有”。Here is a pen(这里有支笔),有物于此,即有物在此,因此,to be就是“在”,The pen is here(这笔在此)。在英语中,to be同时关联着“有”、“在”、“是”。在这三种含义中,“有”是一般地肯定(有物于此),“在”是具体地肯定(此物在此),“是”是对在此之物作一确切判定,这是此物。因此,在英语中,to be不仅表达“有”(物),指出(有物)“在”此,还要指出(正)“是”(此物),更要指出此物为真(是)。正是to be作为有/在/是的语义和语用的统一,凸显了西方知识体系的特质:第一,西方的知识是以“有”(物)为特征的;第二,西方的知识是以“有”(物)在具体的时空中的(存)“在”为特征的;第三,西方的知识对于“有”物“在”此,重要的是求得此物之“是”,即科学性和真理性定义(这三点构成了与印度知识重“空”的比较,也构成了与中国知识重虚实相生的比较)。具体时空中的具体事物的to be(有/在/是)总是在时间之中的,因此,to be有现在时is(单数)和are(复数)、过去时was(单数)和were(复数)、将来时will be,用以表示现在而有、过去曾有、未来将有的有/在/是。另外,事物存在还有各种复杂的状态,因而要用进行时、完成时等语言形式来予以分别表现。如此等等,都主要与语言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建构相关。在日常生活和知识层面,to be(有/在/是)总是指向具体的事物,to be总要具体地变成to be something(有某物/某物在/是某物)。而哲学所要求的是一般(不受具体的时空限制)和永恒(不受具体的生灭出没左右),因此,如果说出了to be(有/在/是),而又不说to be所系的something(具体物),就超越了具体的知识,而变成哲学的总概,显示出了哲学的特征。说了to be(有/在/是),但既不化为具体时空中的有/在/是(is/are/was/were/will be),又不指向具体的物(something),而只是“to be”(有/在/是)本身,并把to be(有/在/是)变成动名词,将其凝固化、完成化、名词化,成为being,其哲学的提升就成功了。Being是有/在/是,但又不讲有何物,何物在,是何物,而是有本身,在本身,是本身。说是有,又不说有何物,就超越了任何具体之物,而成为“有”本身(是“有”而不是“无”成为西方哲学关注的重心);说了在,又不说何物在,就超越了任何具体之物,而成为“在”本身(是“在”而不是“非在”成为西方哲学关注的重心);说了是,又不说是何物,就超越了任何具体之物,而成了“是”本身(是明晰的而非模糊“是”,是确定的而非不确定的“是”成为西方哲学关注的重心)。从to be到being,西方思想完成了从知识到哲学的飞跃;从being到Being,西方哲学完成了哲学本体论的建构。Being这一核心概念显示了西方哲学的基本特征:第一,对“有”的强调,拒绝了“无”的思路;第二,对“在”的强调,凸显了西方哲学的明晰性和科学性;第三,对“是”的强调,凸突了西方哲学的真理观和确定性。
三、从希腊语的角度看on(Being)的复杂性
从to be到being再到Being,已经以英语的形式显示了一种完全不同于汉语形式的哲学方式。Being问题起源于古希腊,英文的be希腊文动词原型是eimi,英文的不定式to be的希腊文是einai,分词being的希腊文是on。然而,希腊语还有更复杂的结构。杨适在《希腊哲学史》中指出,希腊文eimi的词形变化有第一人称单数、第二人称单数、第三人称单数、第一人称复数、第二人称复数、第三人称复数,这六种单复数形式又都有现在时、未完成时、未来时的不同词形变化,还有不定式、分词及命令、祈使、假设语气的形式变化。与英语being相对应的分词形式,在希腊文中有阳性、阴性、中性之分[1](P32),三种形式都可以英译为being。英语being所对应的是希腊文的中性分词on,这是因为巴门尼德在对eimi进行从语言到哲学的转化时,用的是on,而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把on作为哲学的核心。在希腊文中,分词、形容词、不定式加上冠词(to)就可成为名词形式,因此,希腊文eimi的中性分词on成为名词,其意义与后来英语的be加上ing成为动名词being的内涵是一样的。当on被哲学化时,整个eimi的关联系统也进入了哲学的场地,具有了哲学的气息。亚里士多德的十范畴(ousia、量、质、联系、地点、时间、姿态、状态、主动、被动)就是on的体系性展开,而位于十范畴之首的ousia来源于甚至可以说等同于eimi的阴性分词ousa。汪子嵩、王太庆说,亚里士多德把希腊文中的阴性分词ousa写成ousia(余纪元说,ousia是由ousa变来的),该词可以译为“载体”或“基质”,即“是的东西”,这一由ousa而来的哲学的关键词通过拉丁文翻译成为substance,被译为实体,但最好译为“本体”[2]。这一在西方语言中广泛使用的词体现了西方哲学的特质,西方人看事物要求得到本体,而这一本体是实体。余纪元指出,在亚里士多德的十范畴体系中,ousia是现实世界的形而上基础,而其他范畴则成为ousia的属性。他还指出,ousia又被拉丁文翻译成essence(本质),在西方语言后来的运用中,essence(本质)与existence(具体存在)成为相对的对子[3]。
葛瑞汉(A.C.Graham)更详细地指出,on(Being)衍化成existence和essence这一对子,有一个更为复杂的世界哲学的演变过程,它是由用希腊语的古希腊哲学经过用闪族语的阿拉伯哲学再回到用拉丁语的西方哲学而产生的。“历史上看,这对概念(即existence和essence)最早出现于阿拉伯哲学,在这个阶段,西方传统正在从一种印欧语言(希腊语)通过闪族语(Semitic)、古叙利亚语(Syriac)、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Hebrew)的中介向另一种语言(中古拉丁语[Mediaeval Latin])过渡。……阿拉伯人,用闪族语进行哲学思维,发展了一套以wujud(existence,存在)和mahiyyah(quiddity,本质)为中心的新术语。仅仅用字面翻译成阿拉伯语的中介,亚里士多德变成了这类思想家,他时而说存在,时而说本质,从不言及being。出现了一种新的本体论,那里存在不属于任何本质,除了唯一必然的存在、真主,据伊本·西那(Ibn Sina,公元980-1037年)的说法,其是把存在加于事物的本质之上而创造的。拉于语翻译者从阿拉伯语造出quidditas用来指mahiyyah,但也保留它为essentia(esse的派生词最初造为希腊语ousia的对应词),同时用esse指wujud;这区别被进一步澄清为动词existere,其呈现有别于后者。结果,对于经院哲学家来说,从阿拉伯语引入的本质和存在变成合并于从古希腊继承的being,甚至在阿拉伯哲学自身的拉丁语翻译里也是如此。”[4](P465)在这里,阿拉伯哲学一方面以自己的语言和思想特性对西方哲学作了一种具有文化特性的引申与改变,另一方面又在与西方哲学的互动中丰富了西方哲学关于on(Being)的语汇。
这样,essence与substance一样,成为可以是存在于事物之中的,决定事物之为此事物的本质。由eimi(有/在/是)这一语言运用和哲学思考产生了三个西方哲学中最根本的词:一是超越了具体之有/在/是的本体之on(Being有/在/是),一是作为与on(Being)紧密关联的而且为其最核心的实体的substance,一是作为与on(Being)紧密关联而且为其本质的essence。这三个词由希腊文具有内在统一性的词通过哲学的提炼,中间还有古希腊思想和阿拉伯思想的碰撞与融和,由希腊文到拉丁文再到各西方语言的转换而来,在普遍的语用中,呈现出了西方哲学的基本特征:第一,on(Being)呈现了超越于具体的有/在/是的普遍性的有/在/是;第二,如果要把具体的有/在/是的现象世界与普遍的有/在/是的本体世界关联起来,有essence或substance可以往来于具体与普遍(现象与本体)之间;第三,超越了具体的世界是一个substance(实体)的世界。当然,在希腊文与英文的比较中,还可以有一系列的问题提出,但上面讲的由希腊文而来的三个词Being(有/在/是)、substance(本体/实体)、essence(本质)基本上呈现了西方哲学基本概念演进的复杂性。
然而,这只是由希腊文的on(有/在/是)及ousia(本体/实体)进入拉丁文继而进入其他西方语言而来的哲学演变的一种,而且是进行了思想简化的一种。余纪元指出,在希腊文的哲学化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那里,on有一个自己的衍化序列:on(有/在/是),ousia(本体/实体),ti esti(是什么),to ti en einia(本质)。余纪元说,按照希腊文的原意,on应该译为“是”,ousia同理即为第一“是”,可译为“本是”,ti esti是在on(是)的基础上对事物的本质追问,可译为“是什么”,to ti en einia是在on(是)的基础上的事物本质即事物中具有恒定性的东西,可译为“恒是”。to ti en einia(恒是)即事物不变的本质,在后来的英文翻译中,也被译成essence[3]。这样,to ti en einia和ousia都可译为essence,但在希腊语中,正如上面的序列所示,二者是有区别的。这也显示了希腊语比英语更为复杂的一面。最主要的是,在古希腊哲学中,on作为第一哲学、形而上学与本体论,突出的是一个与中国语言和中国哲学差别甚大的“是”。在这里,呈现出了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难题: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是”还是“不是”,这真是一个问题)。
一方面,知晓西方哲学从古希腊以来演变形成的三个基本词Being(on有/在/是)、substance(ousia本体/实体)、essence(to ti en einia本质),可以使中西哲学的汇通有一个较好的基础;另一方面,清楚作为西方哲学源头和基础的古希腊哲学中on(是)、ousia(本是)、ti esti(何是/是何)、to ti en einia(恒是)的特色,有利于使中西哲学在汇通过程中达到一种历史与现实的深度。
四、on(Being)应该用怎样的中文来表达
如上文所述,现代中国接受西方哲学主要是从英语开始的,而对于中国现代哲学语汇的形成,同属汉字文化圈的日本起了重要作用。日本学者最早用汉字“有”翻译西文的Being;后来西方的翻译者把《老子》中的“有”和“无”分别译为being和non-being。经过中西文的“双向格义”,与西文Being相对应的中国哲学的概念被确定为“有”。1950年代之前,中国学者普遍用“有”来翻译和理解西方形而上学研究的Being[5]。“有”在中国不仅是指某一事物所拥有的属性,如英语中的have,而且是指有物存在(如《论语》云“有朋自远方来”),继而泛指一个大的群集,即在这一群集前加一“有”字(如有唐一代,有宋一代),进而指称事物全体(如《老子》云“天下万物生于有”)。因此,中文的“有”也就是存在之“在”,既是have又是to be,一物的属性之有(have)是“有”,一物的存在(to be)也是“有”。《周易·序卦》说:“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中文讲的人生天地间,既是讲人存在于天地间,又是讲人来源于天地,是天地之物、天地之“有”。在“有”与“在”的关系中,已经透出了中西哲学的异同。进一步而言,在中国,“有”是哲学概念,而“在”(或者“存在”)却不是哲学概念(“存在”因为翻译西方哲学而成为中国现代哲学概念,中国现代哲学是按照西方哲学的框架建立起来的,这已是另一问题了,不在这里扯进来)。因为“有”天然地与“物”相连(可以是一物,也可以是万物),而“在”却无法与“物”相连,当我们说“有物”时,“有”等于“物”,而说“物在”时,“在”却不能等于“物”。更为紧要的是,中文里的“有”与“在”基本上与“是”无关。“有物在此”,既是“有物”,就已经“是”(存在)了,既然有“在”此,就已经确认“在”了,再提“是”乃画蛇添足,因此,“是”不是一个哲学概念。“是”作为系词出现晚于古代汉语的形成(严格说来,由于古代汉语与印欧语言的语法体系不同,用西方语言体系中的系词来找出“是”在什么时候成为系词,只是在中西语言比较上有意义,而对于理解古代汉语本身的文化和哲学意蕴而言,这不是中国哲学研究,也不是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主要问题),“是”无论什么时候成为系词,也无论“是”在字源上的词义可以怎样与哲学有关联,但“是”从来不是哲学概念,决定了要让“是”进入哲学,不但要克服诸多困难,即便在西方Being的大力支持下,克服了这些困难之后,还有一系列问题。因此,on(Being)作为世界主流文化的核心哲学概念进入中国之后,由于中西哲学的差异,中国学人面临着两个问题:第一,如何让中国人以汉语的方式洞悉西方哲学的原意和精髓;第二,如何让西方哲学的原意与精髓真正在汉语的表达和形式上成为哲学概念。这是两个虽有关联但又不同的问题。可以说,从民国时期的陈康开始,中国哲学界对on(Being)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一个问题上。当然,研究第一个问题必然要关联到第二个问题,但正是这种关联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第二个问题的思路和视野,因此,当由第一个问题的明晰而走向第二个问题时,收获不大。先看第一个问题。
陈康在1944出版的《柏拉图巴门尼得斯篇》译注中,第一个把on译为“是”,并强调,翻译的目的就是要传达中国未有的思想,因此,虽然这样译不是中文的习惯,但正是这种非中文习惯的译法,让从未这样思想过的中国人知道,原来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思,并且是用这种非中文的方式,逼着中国人学会用这种方式去思。可见,陈康译on为“是”,是为了让中国学人去看、去思、去知西方哲学,并在这看、思、知的基础上,进入一种世界哲学的思考。这里突出的是以汉语形式去传达西方哲学原意和精髓的问题。然而,这一研究思路在共和国前期被时局的转变中断了。
如果说,在民国时期,中国哲学界主要有三种哲学相互竞争,一是学术型的西方哲学,一是新儒学型的中国哲学,一是苏联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那么,在共和国前期,苏联型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统天下,并以自己的思想体系去改造学术型的西方哲学和包括新儒学在内的中国哲学。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框架中,世界的一切首先分为物质与精神,其中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是由物质所产生或派生出来的;物质和精神也就是存在与意识,其中存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是由存在所产生或派生出来的。在这样一个体系结构中,首先,由希腊文on而来的、与英文Being等同的德文中的sein被理解为宇宙第一性的“存在”;其次,在“存在”与“意识”的对子中,要强调存在的客观性。这样,第一,存在在本质上被等同于matter(物质性的存在),being的复杂性完全消失了;第二,其在现实中等同于existence(现实的存在)而非being(抽象的存在),包括物理存在和社会存在。在这里,being不但被简化了,而且被固定了,最重要的是,它在汉语中变得很好理解了。因此,on(Being)的问题在共和国前期完全消失了。on(Being)在苏联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作为“存在”,又在整个共和国前期的哲学氛围中,以苏联型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去读解西方哲学,因此,在这一时期,on(Being)不但在古希腊哲学的翻译中被译为“存在”,而且在现代西方哲学的翻译中也被译为“存在”,只是为了进入海德格尔关于on(Being)的语群上的区分,才把Sein译为“在”,把Dasein译为“亲在”(熊伟)。这一做学问的惯性一直延伸到改革开放时期。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西方哲学的研究从苏联型哲学模式中解脱出来,回到西方哲学的原样,on(Being)的问题重新被提了出来。由on(Being)的重出而来的研究,主要在如下的方向上进行:
第一,on(Being)在西方哲学中的原意是什么。这主要关涉到on(Being)与中文的对应关系,即在可以与之对译的几个中文词(是,在,有……)中,其主要的含义是什么。赵敦华根据宋继杰编的《BEING与西方哲学传统》,对“on(Being)的一般意义是什么”归纳出了五种解释:(1)是“存在”(韩林河、孙周兴等);(2)是“有”(叶秀山、邓晓芒等);(3)是“是者”(王路、俞宣孟等);(4)Being在古希腊哲学中的一般意义是“是者”,但对Being在全部哲学史中是否有一般意义的问题存而不论(汪子嵩、王太庆);(5)不论在西方哲学史上,还是在古希腊哲学中,Being都没有一般意义,“有”、“存在”、“是者”三种译法各有合理性(赵敦华、陈村富等)[5]。在这五种解释中,其实(3)与(4)可归为一种,只是对on(Being)的历史地位的进一步定位有所不同,因而应该归纳为四种。这四种解释要言之成理,都牵涉到对on(Being)的词类和语用的关联域的考察及论述。这不仅关系到on(Being)的历史源流(包括语言和哲学两方面的源流),还包括当代西方学者对其语言和哲学源流的研究,以及中国学人对西方研究成果的不同理解,特别是美国的on(Being)研究专家卡恩(Kahn,C.H.)的成果,于1966年发表的论文《动词“to be”与“being”概念研究之回顾》(The Greek Verb“to be”and the Concept of“being”)和1973年出版的专著《古希腊语动词“to be”》(The verb“to be”in A ncient Greek)在王路与王晓朝、陈村富之间引起的讨论。这些言说基本上呈现了on(Being)的原貌、复杂性、范围,使中国学人对其不同于中国哲学的面貌有了深刻认识。
第二,用中文来翻译或表达on(Being),用什么样的词最好。由于陈康在民国时期就提出把on(Being)译为“是”,而“是”又确实最能体现on(Being)的古希腊哲学面貌和西方哲学精髓,加上有共和国前期译为“存在”对民国时期译为“是”的否定,因此,汪子嵩、王太庆对自己在共和国前期译为“存在”作了反省,并大声急呼应当译为“是”,这一呼吁得到了王路等的有力应合。于是,将on(Being)译为“是”成了当前中国哲学界的主流。然而,虽然用“是”来对译西方哲学的根本概念突出了on(Being)的原意,但毕竟不符合中文的哲学性质和语言习惯,因此,又出现了三种情况:一是强调在翻译的过程中,要随具体语境而使用“是”、“在”、“有”等不同译法;二是主张加上其他词,以全面呈现on(Being)的原意,如李晨阳就提倡译为“是-有论”,因为只要以中文为参照,就会显示为,on(Being)有时讨论的是“是”的问题,有时讨论的是“有”的问题[6](P14);三是通过把on(Being)的整个语群都加上“是”,而把哲学意味强力灌注进去,如前面所说余纪元的“on(是),ousia(本是),ti esti(何是/是何),to ti en einia(恒是)”语群,以及王路在翻译海德格尔的语群时应运用的系列:“是”(Sein),“是者”(Seiende),“此是”(Dasein)[7]。
需要补充一下,虽然“是”已成为on(Being)研究的主潮,但由于中国学人从德语翻译海德格尔的传统(熊伟、陈嘉映、王庆节等),对“存在”的坚持仍有相当的力量。当然,这里也有一系列问题,如Sein(相当于英语的Being)与Seiende(相当于英语的beings),有译为“在”与“在者”,有译为“存在”与“存在者”,但问题不大,而关于Dasein,问题就多了,有“亲在”(熊伟),有“此在”(陈嘉映),有“缘在”(李晨阳)。
对于on(Being),无论是用“是”来译,还是用“在(存在)”来译,也无论在译成“是”或“在(存在)”的时候,用语群的统一性来强化,还是以“是”(或“在”)为主,因其出现的具体语境而兼用其他词,其实质都存在一个on(Being)进入中文之后,如何在语言层面和哲学层面真正进入中文的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一问题,由on(Being)而来的“是”(或“在”)就只能局限在中国哲学界中的西方哲学研究,而不能普及(或曰上升)到中国哲学界的总体之中。
这里的问题是,在一种语言体系中,哪些词汇可以成为哲学语汇,而哪些则不能,需要加以明确区分。在西方语言中,eimi(be)可以成为哲学词汇,而在中国语言中,“是”(或“在”)不能成为哲学词汇,因此,当“是”(或“在”)因为要呈现西方哲学原意,而强行成为哲学语汇时,它基本上只是理解西方哲学概念的传达“工具”,而不是哲学概念的“实体”。这里姑且生造“工具词”(或曰“借词”)和“实体词”(或曰“实词”)两个概念。所谓工具词,是要传达原意而不得不用此词,但此词不是哲学词,也不可能成为哲学词,只是借来作为工具用的;所谓实体词,是此词不仅可以传达原意,而且同时就是哲学词,或可以成为哲学词,具有哲学的实体性,是实实在在的。以此而论,“是”、“在”等都是工具词,而“理念”、“物质”等则是实体词。工具词只能在讲述其他文化的哲学思想时用,而不能在论述一般哲学思想时用;实体词则既可以在转述其他文化的哲学思想时用,又可以在讲述一般哲学思想时用。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在语言上同构的词,如希腊文的“eimi”,英文的“be”,中文的“是”,在西方语言中可以成为哲学词,而在中文里却不能?
[收稿日期]2010-08-20
标签:哲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古希腊哲学论文; 世界语言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本质与现象论文; 中国哲学史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西方哲学论文;
